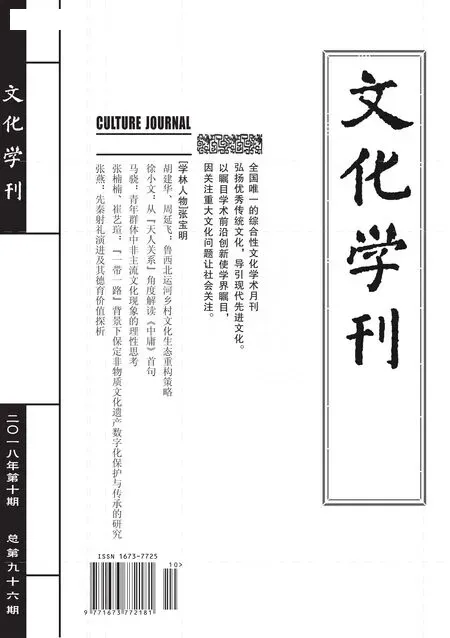康德哲学中的溯因思想研究
朱耀桦
(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071)
一、溯因推理的来源
溯因推理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期,他曾在《前分析篇》中提出了一种“还原的推理模式”,但它当时并没有被确立为一种逻辑推理。具体提出溯因推理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哲学家皮尔士。皮尔士最初将其称为假设,而后更名为溯因推理,其溯因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
皮尔士早期主要从推理形式上对溯因推理与归纳和演绎推理进行区分,并沿用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形式。他认为,演绎推理是通过已知的规则和事例推断出结果;而归纳推理则是从事例和结果推断出规则的过程;溯因则是根据已知的规则和结果来确定事例的可靠性的过程。
二、溯因推理与因果性
皮尔士后期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三段论对推理的分类,而是将溯因、归纳和演绎这三种推理与科学探究的过程相关联,分别对应假说的形成、评价和预言过程。溯因推理虽然是一个为结果寻求解释性假说的过程,但皮尔士指出它仍是具备一定逻辑形式的推理,并将其定义为:“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C。并且如果A是真的,则A可能引起C。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溯因推理推断出A可能是真的。”
皮尔士运用了逆向假言推理的逻辑形式,但在溯因推理中A与C的这种关系并非经典逻辑中的实质蕴含。在假言推理中,如果A→C,那么A是C的充分条件,C是A的必要条件,且非C是非A的充分条件。而在溯因推理中,我们可以用天下雨来解释地为什么湿,却不能用地没有湿来说明天没下过雨。溯因推理在形式上虽然相似于假言推理,但却只具备其逆向的形式,其中A和C的关系具有非对称性,且它们在时间上往往是相继发生的,这也是因果关系的特性。皮尔士在利用三段论定义溯因推理时,也将其描述为根据已知的规则和结果来回溯解释性假说的过程。内格尔也将其定义为:“假说推理(也称为溯因,逆推法,假说),在于从一些事实或假说,推断一个解释、原因,后者可以作为一个假说的结果。”[1]
英国哲学家J·L·Mackie在The Cement of Universe中对因果性和充要条件进行了详细区分,他指出:“一个事件的原因既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但它存在于该事件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之中,并是其中必要不充分条件或非盈余部分,即INUS条件。”[2]通过溯因推理也可以看出,“因果关系具备不对称性和方向性,而条件关系在逻辑上是没有方向性和不对称性的,或至少它不能穷尽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和不对称性”[3]。我们可以说,如果A是C的充分条件,那么非C也是非A的充分条件。但是当天下雨导致了地湿时,我们无法通过地没湿来说明天没下过雨,这也就是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可其在时间的方向性上却面临一个困境。如果通过原因发生在结果之前来判断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就无法解释火车头拉导致火车跑存在的因果关系,因为二者在时间上是同时发生的。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英国逻辑学家Von Wright提出了可控性标准的概念,他认为:“当两个事件A与B中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不用B就能产生和制造出A,而B因为A而出现,即A是B的原因,而不是B是A的原因。”[4]但是很明显,它只适用于我们可能进行实践操作的范围内,超出我们实践范围的事物,我们仍无法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那我们如何能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呢?
休谟曾指出:“因果被人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但又不是仅凭经验。”[5]“要论证思维的客观真理性必须诉诸于实践,而非理论。”[6]“例如火药的爆炸能力并不是通过先验论证所得出的。”[7]因此,休谟认为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是无法通过经验来证明的,因为“根据经验得来的一切推论都只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8]。基于此,因果关系便失去了普遍必然性,因为他只是人们一种主观习惯。也正是在休谟怀疑论的冲击下,康德走出了“独断论的迷梦”。
三、康德对因果性的辩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我们认识的对象其实是物自身刺激我们的感官所形成的现象,因果性是属于认识主体的十二个先验知性范畴之一。我们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其实是运用先验的知性范畴把握经验现象的过程。由此可见,我们认识的对象其实是我们自身感官所建立的,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并不是缺乏理性的习惯。但知性与感性只有在图型的中介作用下才能结合,康德在其“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形法和原理体系”中指出,“要将先验范畴运用到直观杂多,就必须依赖于作为范畴与直观的中介的图型”[9]。要将先验的知性范畴与物自体刺激感官所形成的现象相结合,就必须依赖于图型的作用。康德认为:“当先验的知性概念应用到每个可能的经验时,它们的综合是数学性的或力学性的。”[10]其中“范畴的数学性使用原则是一种绝对的必然和知觉的确定性,它包括直观的公理和知觉预测。而范畴的力学性使用原则是一种间接且不自明的,仅仅具备一种推论上的确定性,它包括经验的类比和一般性的思维公设”[11]。康德在经验的类比中,对时间进行了三种样态的划分,即持存性、相继性同时并存。其中,因果性范畴的运用则是力学性的,它将时间中的前后相继作为图型,因而因果性范畴在运用中所具备的确定性是推论上的,例如在观察到“太阳晒而石头热”时,我们并未直接看到其中蕴含的抽象因果,而是通过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所做的判断。康德在“知性纯粹概念的先验演绎”中也指出,“我们是通过知性范畴把握经验现象的过程来形成知识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理性的作用”[12]。
四、知性活动中的溯因思想
康德认为:“我们的理性是有因果作用的,或者说,我们至少是对我们自己把理性描写为有因果作用的。”[13]他指出这种绝对的因果在知性范畴把握直观杂多的过程中起到的是范导性作用,将知性的活动目标指向绝对化的超验“绝对全体”。但理性并没有直接参与到知性的建构中,而是使知性的建构沿着正确的方向最大限度地扩展经验知识。康德认为这种倾向是人类的天性,它不会止步于得到任何东西而结束追溯的过程。例如,“物自体”这个理念并不是作为知识的建构而存在,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对物自体的本性进行探究和预测,它被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对知性范畴起到范导性作用,指引范畴的综合统一沿着正确的方向扩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依然认为“物自体”本身是不可知的,因而理性的范导性规则是指引着我们为了认识它而不断追寻,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我们的经验知识,这也就形成了以绝对因果作为开端的因果链,其中包含了一段段的因果追溯。康德的“范畴的先验演绎”已经蕴含了溯因思想,且他对因果性范畴的论证也相对最多。而皮尔士诉诸于“知觉判断”这种“潜意识”概念为溯因推理寻找根据,受其影响也颇深。
皮尔士认为,“只有包含了普遍性的知觉判断才能成为溯因推理的根据,并且没有什么理智中的东西不是预先存在于知觉之中的。”[14]在康德的理论中,溯因的思想存在于知性把握直观杂多的过程中而非知觉判断,皮尔士与康德一样虽然确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并在因果性的基础上将溯因确立为一种推理形式,但仍将溯因推理的根据诉诸于一种先天存在的“潜意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