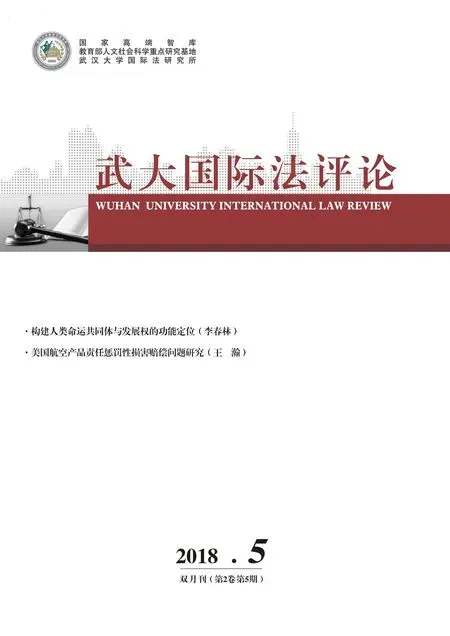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仲裁同意问题
肖 军 康雪飘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备受关注,如何平衡投资者与国家间的利益成为该机制改革的核心问题。①参见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133页。被诉东道国提出反诉或反请求(counterclaim)被视为实现此种平衡的一个重要途径。②参见陈正健:《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中的国家反诉》,《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第164页。实际上,在投资仲裁中适用的仲裁规则通常都允许被申请人提出反诉,无论是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以下简称《ICSID公约》)及其仲裁规则还是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例如,《ICSID公约》第46条规定:“仲裁庭应对直接因争议事项而产生的附带或附加的请求或反请求作出决定。”2010年《UNCITRAL仲裁规则》第21条第3款亦规定:“被申请人还可在仲裁程序的稍后阶段提出反请求或基于一项仲裁请求而提出抵消要求,只要仲裁庭对此拥有管辖权。”然而在已有的投资仲裁案件中,国家提出的反诉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有学者对截至2015年的仲裁案件进行统计后发现,从公开可得的资料可以确定28个案件包括国家反诉,但反诉只在4个案件中获得(即使只是部分的)成功;并且很多反诉在管辖权问题上就失败了,而“分析反诉管辖权的核心问题经常是同意问题”。①Ina C.Popova&Fiona Poon,From Perpetual Respondent to Aspiring Counterclaimant?State Counterclaims in the New Wave of Investment Treaties,2 B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view 226(2015).
当事方同意是仲裁的基石,是认定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国际投资仲裁也不例外。《ICSID公约》第25条规定,ICSID管辖适用于缔约国(或缔约国向中心指派的下属机构或单位)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直接因投资而产生并“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的任何法律争端;2010年《UNCITRAL仲裁规则》第1条也规定,“凡各方当事人同意”,争议应按照本规则解决。因此在投资者质疑仲裁庭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时,投资者对反诉没有作出同意通常是关键性理由。②陈正健:《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中的国家反诉》,《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第167页。一般而言,在根据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合同提起的仲裁中,同意的范围较为清楚——合同的争端解决条款通常允许合同双方就对方的违约行为提出仲裁请求,那么仲裁庭总是可以受理国家以投资者违约为由提出的反诉。③See Jean E.Kalicki&Mallory B.Silberman,Case Comment:Spyridon Roussalis v.Romania,27 ICSID Review 10(2012).但是,实践中投资者大多是依据以双边投资条约(BIT)为主的国际投资条约提出仲裁请求,并且这些条约一般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反诉④仅有极少数例外,如2007年《东南非共同市场投资协定》。,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投资者对国家反诉的同意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鉴于此,研究基于条约的投资仲裁中投资者对国家反诉的同意问题,对于我国在投资仲裁中的应诉⑤截至2018年4月,我国已在3个投资仲裁案中被诉:2011年的伊佳兰(Ekran,马来西亚投资者)案是中国首次被诉,最终双方和解,未设立仲裁庭;2014年的安城(Ansung,韩国投资者)案中,以仲裁请求的提出超出时效为由,中国提出异议并获得仲裁庭支持;2017年的海乐西亚泽(Hela Schwarz,德国投资者)案是中国第三次被诉,2018年1月8日,仲裁庭设立。以及投资条约文本的设计和谈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投资条约中影响同意范围的规定
基于条约的投资仲裁中,认定投资者同意的范围无疑要考虑投资条约的规定。通说认为,此类条约仲裁的仲裁合意是这样达成的:东道国在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中作出将相关争端提交仲裁的承诺,该仲裁提议构成东道国对于仲裁的同意;投资者通过将特定争端提请仲裁表达了对于仲裁提议的接受,这构成投资者对于仲裁的同意,合意自此达成。这一过程通常被类比为合同法中的要约与承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如果认定投资者同意的范围涵盖反诉,那么投资者接受反诉的义务并非来自于投资条约,而是来自投资者自身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如果东道国在投资条约中作出的仲裁提议本身都未包含反诉,则很难认定投资者同意的范围涵盖反诉,因而投资者同意范围的认定又和投资条约的规定密切相关。①本文讨论的是以该“要约-承诺”方式达成的仲裁同意,不涉及投资者在仲裁中直接同意仲裁庭对反诉的管辖权的情形。
(一)纳入有关仲裁规则的规定
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都会规定应适用的仲裁规则,通常是ICSID或UNCITRAL规则,而如上所述,这些仲裁规则都允许被申请人提出反诉。则能否就此直接认定投资者的同意范围涵盖反诉?
这一问题在罗萨尼斯(Roussalis)诉罗马尼亚案中被提出并引发争论。该案被诉东道国罗马尼亚主张,当投资者将诉请提交ICSID时,投资者就已经对解决所有与投资相关的争端作出同意,包括被诉方的反诉。这一主张最终被仲裁庭的多数意见驳回,但仲裁员赖斯曼(Reisman)持不同意见。赖斯曼认为,当投资条约的缔约国附条件地同意了ICSID的管辖,《ICSID公约》第46条的同意要件——根据事实本身——就被引进投资者选择提起的任何ICSID仲裁。②Spyridon Roussalis,ICSID Case No.ARB/06/1,Declaration by Michael Reisman.赖斯曼的观点可理解为,投资条约的其他规定与是否允许反诉无关,只要条约中有纳入相关仲裁规则的条款就足以认定对反诉的管辖权。有学者主张类似观点,也有学者持批评意见。③See Dafina Atanasovaet al.,The Legal Framework for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3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65-369(2014).
本文认为,分析相关仲裁规则关于反诉的规定可以发现,这些规定本身并不决定仲裁庭对反诉的管辖权。ICSID《仲裁规则》第40条第1款规定:“除当事双方另有协议外,当事一方可提出直接因争议事项而产生的附带请求、附加请求或反请求,但以这些请求在当事方同意之范围内且在其他方面在中心管辖范围内为限。”根据这一规定,仲裁庭审理反诉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④See Christoph 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 751-75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第一,反请求与争议事项直接相关;第二,反请求在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内,并且在管辖权的诸项必要条件中,当事方同意被特别强调。①因此有些仲裁庭将“同意”视为前提条件之一而进行单独考查,进而形成第40条的“两条件”和“三条件”的不同表述,但这一差异的实质性影响不大。2010年《UNCITRAL仲裁规则》第21条第3款也特别要求,“只要仲裁庭对此拥有管辖权”。上述条文用语清楚地表明,它们本身并不确立仲裁庭对反诉的管辖权,而是以仲裁庭享有管辖权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仲裁庭在裁决是否对反诉享有管辖权时,仍应该遵循仲裁规则中关于管辖权的判定条件,而仲裁规则都将当事方同意作为认定管辖权的必要条件。自罗萨尼斯案开始,仲裁庭在确定对反诉的管辖权时,也都将当事方同意视为首先必须满足的条件。②Tomoko Ishikawa,Case Comment:Marco Gavazzi and Stefano Gavazzi v.Romania:A New Approach to Determing Jurisdiction over CounterclaimsinICSIDArbitration?,32 ICSID Review 723(2017).因此,即使投资条约纳入了仲裁规则,投资者能够预见的只是仲裁庭将考虑对反诉的管辖权,管辖权的认定仍要符合同意的范围。投资条约纳入仲裁规则本身并不能证明投资者的同意范围涵盖反诉,认定投资者同意的范围需要考虑投资条约的其他规定。
(二)“争端”范围的规定
投资条约规定的可提交仲裁的“争端”范围表明了东道国仲裁提议的范围,既然投资者的同意表现为对提议的接受,那么其同意范围也受限于提议的范围。易言之,如果东道国在投资条约中都没有将反诉争端(即与投资者义务相关的争端)列入仲裁提议,投资者接受提议当然不等于对这些争端表示仲裁同意。投资仲裁实践中,认定投资者对反诉的同意时,投资条约如何规定可提请仲裁的“争端”常常是一个重要问题。
传统BIT以保护投资者和便利外国投资为宗旨,投资者依据条约享有权利而非承担义务。③在晚近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的背景下,一些投资条约(如印度2015年BIT范本)开始直接规定投资者义务。已有投资条约中,有的“投资”定义要求投资应符合东道国法律,也可视为一种投资者义务。不过,一项不符合该要求的投资不能获得条约的保护,仲裁庭在拒绝对投资者诉请的管辖权之后,也会否定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相应地,不少投资条约只规定投资者可以就缔约国违反义务的行为提请仲裁。例如,在前述罗萨尼斯案中,希腊—罗马尼亚BIT第9条规定,可仲裁争端是“缔约一方投资者与另一缔约方之间与投资相关、涉及该缔约方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争端”。仲裁裁决认为,该项规定“毫无疑问将仲裁庭的管辖权限定于投资者就东道国义务提起的诉请”。①Spyridon Roussalis v.Republic of Romania,ICSID Case No.ARB/06/1,Award,para.869.这是仲裁庭多数意见否定争端双方对反诉的合意的主要依据。
与此相反,萨卢卡(Saluka)诉捷克案涉及1991年荷兰—捷克斯洛伐克BIT,其第8条规定的“争端”是“缔约一方投资者与另一缔约方之间与投资相关的任何争端”。仲裁庭认为:“第8条规定的‘任何争端’足以涵盖反诉中涉及的争端,当然,其他的相关要求仍需满足。”②Saluka Investments B.V.v.The Czech Republic,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ver The Czech Republic’s Counterclaim,para.39.
综观已有仲裁实践,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中“争端”的界定是确定反诉管辖权的关键因素:在所涉条约规定类似于罗萨尼斯案的仲裁案中,仲裁庭全都否定了对国家反诉的仲裁同意的存在;相反,在条约规定类似于萨卢卡案的仲裁案中,除了伽瓦兹(Gavazzi)诉罗马尼亚案③Marco Gavazzi&Stefano Gavazzi v.Romania,ICSID Case No.ARB/12/25,Decision on Jurisdiction,Admissibility and Liability,paras.148-162.之外,其他仲裁庭都支持了对反诉的仲裁同意。④Tomoko Ishikawa,Case Comment:Marco Gavazzi and Stefano Gavazzi v.Romania:A New Approach to Determing Jurisdiction over Counterclaims in ICSID Arbitration?,32 ICSID Review 726(2017).
(三)适用法的规定
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规定的适用法会影响投资者同意范围的认定。究其原因,仲裁庭应依据条约规定的适用法解决争端,若适用法没有规定投资者应承担的义务,则国家反诉将缺乏法律依据,即可推定东道国仲裁提议的争端范围不涵盖反诉。易言之,适用法的规定影响可仲裁的争端范围,进而影响同意的认定。对此,罗萨尼斯案裁决作出了代表性论述:“BIT中规定的义务是对东道国而言的,而非投资者。因此,当BIT明确指定适用法为BIT自身时,就将反诉排除在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外。”⑤Spyridon Roussalis v.Republic of Romania,ICSID Case No.ARB/06/1,Award,para.871.
然而,罗萨尼斯案所涉BIT规定的适用法实际上不只BIT本身,还包括“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仲裁庭并未论证不考虑后者的理由。严格来说,“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能否作为国家反诉的法律依据,是一个复杂的争议问题,难以一概而论:第一,对“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范围可能存在争议;第二,尽管国际法以调整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为主,但不排除某些国际法规则直接规定私人投资者义务的可能。因此,在AMTO诉乌克兰案中,面对同样规定仲裁适用法律为条约本身及“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能源宪章条约》第26条第6款,仲裁庭的裁决更加谨慎:“仲裁庭对投资条约下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取决于条约争端解决条款的规定、反诉的性质以及反诉与原诉的关系。”由于乌克兰提出的是关于其名誉损失的反诉,仲裁庭认为反诉在适用法律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故而拒绝了对反诉的管辖权。①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MTO v.Ukraine,SCC Case No.080/2005,para.118.
类似问题可能出现在投资条约对适用法不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投资者基于此类条约提请仲裁时,仲裁庭都认定,该条约构成争端方默示选择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默示选择是否包括其他国际法规则,仲裁庭的立场则并不确定。②See Christoph 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 578-58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无论如何,仲裁庭都赞同某些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如禁止反言、公正程序等。学者认为,这些原则涵盖了私人投资者的义务,可能成为国家反诉的法律依据。③See Yaraslau Kryvoi,Counterclaim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21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48-250(2012).而在已有实践中,当被诉东道国认为投资者申请仲裁的行为违反禁止反言等一般法律原则时,通常会以此为依据进行管辖权抗辩,而不是选择反诉。东道国也可能同时提出附带请求,要求裁定申请人支付法律费用。同时,在AMTO案中,乌克兰的反诉包括判令申请人支付法律费用的请求,仲裁庭认为此类请求不应属于反诉,因为它是全部裁决之后必将处理的问题。④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MTO v.Ukraine,SCC Case No.080/2005,para.116.
一般而言,投资者义务主要来自东道国国内法或投资合同,相应地,国家反诉也多数主张投资者违反东道国国内法或投资合同。因此,如果投资条约规定的适用法限于国际法且不直接规定投资者义务,仲裁庭很可能认定东道国的仲裁提议不包含反请求,拒绝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相反,若适用法规则较为灵活或者(像部分投资条约那样)直接包括东道国国内法,则它不会构成国家反诉的管辖权障碍。⑤当然,这不是说再无其他法律障碍:实践中多个仲裁庭(如萨卢卡案)认定,主张违反普遍适用的国内法的反诉与基于条约的原诉不是“直接相关”,并据此裁定反诉不在仲裁庭管辖范围内。此外,在条约仲裁中,国家基于投资者的合同义务提出反诉,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仲裁庭出于两个原因很可能否定管辖权:一是条约之诉和合同之诉的区分,二是投资合同基本上都规定了专门的争端解决条款。
三、推定同意与投资者的同意权利
上述关于投资条约规定对同意范围的影响,是从东道国仲裁提议的角度进行考量。仲裁同意需要当事双方作出,因此认定投资者同意,还需要进一步考虑:若投资条约的规定未排除与反诉相关的争端,投资者提请仲裁的行为是否表示同意反诉。这种“推定同意”是国家反诉中关于投资者同意的又一个争议问题。
对该问题进一步审视可知,推定同意问题的核心在于投资者是否有权决定同意范围。正如有学者所言:“让这一问题变得如此难以解决的原因是对如何确定同意范围存在不同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谁确定同意范围的问题:是只能由东道国决定还是东道国和投资者都有权决定?”①Andrea Marco Steingruber,Case Comment:Antoine Goetz and Others v.Republic of Burundi:Consent and Arbitral Tribunal Competence to Hear Counterclaims in Treaty-based ICSID Arbitrations,28 ICSID Review 296(2013).
有学者考察了实践中投资者提请仲裁的方式,发现仲裁申请很少明确表示对反诉的同意,具体而言,申请书的表述通常采取下述三种方式之一:(1)援引(invoke)BIT中的仲裁条款;(2)同意依据适用条约进行仲裁(consent to arbi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3)“接受被申请人的仲裁提议,同意仲裁庭对投资者诉请的管辖权”[accept the Respondent’s offer to arbitrate and consent to the jurisdiction...over(the investor’s)claims]。②See Pierre Lalive&Laura Halonen,On the Availability of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2 Czech Yearbook of Internaitonal Law 149(2011).前两例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投资条约中包括反诉的仲裁提议,但第三例中,投资者只同意将自己提出的诉请诉诸仲裁而不包括国家反诉。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投资者是否有权限制同意的范围便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有学者主张允许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同意范围。例如,朔伊尔(Schreuer)教授认为:“同意应限定在投资者接受仲裁提议的范围内。如果投资者仅就其特定诉请接受仲裁提议,则同意将受到该接受的表述的限制。如果投资者以启动仲裁程序的方式表示同意,同意仅存在于处理投资者诉请所必需的范围内。”不过,他紧接着又表示:“但是如果国家的反诉和投资者的申诉密切相关,有理由认为反诉属于当事双方的同意范围。”①Christoph 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 75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在关于国家反诉的讨论中,更多学者倾向于反对投资者拥有单方面限制同意范围的权利。拉里福(Lalive)和哈罗内(Halonen)认为:“投资者不能对BIT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挑挑拣拣,正如它不能对投资条约的其他规定挑挑拣拣一样。”②Pierre Lalive&Laura Halonen,On the Availability of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2 Czech Yearbook of Internaitonal Law 150(2011).例如,投资者不能一面请求仲裁庭审理自己的征收申诉,另一面却不允许国家提出“基本安全利益”的抗辩,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BIT争端解决条款中的仲裁提议也只能按照它的规定予以接受。如果它规定了国家反诉的可能性,投资者就不能通过限制性的接受来排除这种可能。根据这种观点,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向投资者提供的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选择。只有国家可以限制同意的范围,投资者只能表示接受或者拒绝。以合同法原则为借鉴,斯泰因格鲁伯(Steingruber)也支持上述立场:如果允许投资者限制同意的范围,这种“投资者的接受”便只能视为“反要约”,而非“承诺”,因而不符合通常认为的条约仲裁中合意的达成过程。③Andrea Marco Steingruber,Case Comment:Antoine Goetz and Others v.Republic of Burundi:Consent and Arbitral Tribunal Competence to Hear Counterclaims in Treaty-based ICSID Arbitrations,28 ICSID Review 297(2013).
在2016年12月的乌贝斯(Urbaser)诉阿根廷案中,仲裁庭第一次处理“推定同意”问题,并明确否定了投资者单方面决定同意范围的权利。该案所涉BIT中关于“争端”和适用法的规定较为宽泛,既未将“争端”限定为对BIT条款的违反,也没有规定只有投资者才能提请仲裁。尽管如此,申请人主张,这些规定只是表明东道国未限制其仲裁提议,而投资者所表达的同意范围才可决定反诉是否在仲裁庭管辖范围内。在指出申请人对仲裁提议的接受没有明确排除国家反诉之后,仲裁庭认为:相关仲裁规则要求反诉在当事方同意范围之内,并不等于允许任何一方单方面划定仲裁庭的管辖权;申请人根据BIT争端解决条款作出的同意,与该条款规定的东道国仲裁提议的范围应完全相同;即便申请人的接受可以比东道国的提议范围更窄,结论也是双方未达成合意。④Urbaser S.A.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The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7/26,Award,para.1147.
若在推定同意问题上关注的投资者的同意权利是一种否定性权利(即限制双方同意的范围),则理论上可能存在肯定性的投资者的同意权利。具体而言,即使投资条约对反诉管辖权的规定并不明确,甚至解释相关条款的结果是东道国仲裁提议不包括反诉争端,在具体案件中投资者也可以行使其“同意权利”,不对国家反诉提出异议,进而与东道国达成一项针对反诉的特别合意。这种个案性质的合意作为当事方同意的一部分,可以超出投资条约规定的争端范围,解决投资者同意问题。在伯灵顿(Burlington)诉厄瓜多尔案中,当事双方便达成协议,申请人不对国家反诉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排除任何其他司法机制(包括国际和国内法院)的管辖权,以确保最大程度的司法经济和一致性。①Burlington Resources Inc.v.Republic of Ecuador,ICSID Case No.ARB/08/5,Decision on Liability,para.93.这种肯定性的投资者的同意权利扩张了仲裁庭管辖权,在依据《UNCITRAL仲裁规则》的投资仲裁中无疑是可行的。但在ICSID仲裁中难以一概而论,因为通说认为,即使有当事双方的合意,《ICSID公约》对管辖权规定的某些客观边界也不能逾越,例如当事方国籍要求。理论上,不能排除投资者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国家反诉却超出前述某项客观边界的可能性。
四、仲裁裁决对国家反诉的考量因素与发展趋向
通过考察不同学者的观点和仲裁裁决,上文对在国家反诉问题上如何认定投资者同意进行理论梳理,澄清了各方立场的基本论证路径。那么,未来仲裁庭对这些问题将如何裁决?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由于国际投资仲裁既没有遵循先例制度,也缺乏统一的上诉审查机制,在投资条约没有明文规定或者需要对条款进行解释的情况下,仲裁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仲裁裁决产生差异乃至冲突的现象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当事双方都会援引已有案例中支持自己立场的(不同)裁决,仲裁庭也有责任予以考量,即使对已有裁决持反对意见也不能置之不理。已有裁决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一仲裁庭所说:“谨慎地将判例法中发展出的原则作为有说服力的法律依据,可能有助于法律的发展,进而维护了可预见性,这对投资者和东道国都有利。”②ADC Affiliate Limited and ADC&ADMC Management Limited v.The Republic of Hungary,ICSID Case No.ARB/03/16,Award,para.293.因此,通过总结仲裁庭审查时的下述考量因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判裁决的未来发展趋向。
第一,在基于条约的投资仲裁中,同意范围的认定离不开条约解释,尤其是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它界定了东道国仲裁提议的范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体现了习惯国际法规则,所有仲裁庭都表示遵守并以之为解释和适用条约规则的出发点。由于该解释方法以条款用语为基础,如果争端解决条款的用语构成国家反诉的障碍,仲裁庭很难驳回申请人对反诉的管辖权异议。
第二,被诉东道国提出反诉,应承担证明仲裁庭对反诉的管辖权的举证责任。①Saluka Investments B.V.v.The Czech Republic,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ver The Czech Republic’s Counterclaim,para.34.由于管辖权是先决问题,如同申请人证明仲裁庭对其诉请的管辖权一样,仲裁庭的审查适用“初步证据”(prima facie)的举证责任标准。具体而言,只要主张管辖权的当事方合理证明,表面上可以作出肯定性认定,则管辖权成立;仲裁庭推定该当事方所陈述事实的真实性,除非陈述是不可信的、随意的、无理的或恶意的。对此,萨卢卡案裁决指出,在确定反诉管辖权时仲裁庭的任务是考虑被申请人答辩状中提出的反诉,并依据初步证据确认反诉属于仲裁庭的管辖权范围;若对特定事项存有争议,仲裁庭在确定管辖权时应客观审查这些反诉陈述,考虑是否至少存在合理可能,在实质性审查后可以作出有利于被申请人的认定。②Saluka Investments B.V.v.The Czech Republic,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ver The Czech Republic’s Counterclaim,para.36.
第三,在条约解释允许的仲裁庭自由裁量范围内,政策考量的影响不容忽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将所有相关争端放在一个程序下解决,有助于避免平行程序和冲突裁决,节约诉讼成本。此种司法经济的考虑是促使赖斯曼在罗萨尼斯案中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投资者选择仲裁,就是选择在东道国之外的机制解决争议,而ICSID仲裁庭拒绝对反诉的管辖权,势必促使被诉东道国在其国内法院主张诉求,从而将投资者推上被告席。因此,“除了导致重复和低效等原本希望通过反诉得以避免的交易成本之外,在我看来,这种结果是讽刺乃至荒谬的,与国际投资法的宗旨不符”。③Spyridon Roussalis,ICSID Case No.ARB/06/1,Declaration by Michael Reisman.
如果说仲裁员的立场可以分为倾向于国家和倾向于投资者两派的话,那么前者支持国家反诉的权利容易理解,而赖斯曼的意见表明,国家反诉也并非完全不符合投资者的利益。即使投资仲裁庭拒绝审理相关反诉争端,国家仍有其他救济方式,例如国内法院诉讼。①这一点可能是投资条约对国家反诉不作规定的重要原因,即投资者的投资和投资活动处于东道国的主权管辖之下,东道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原则上已经可以确保让投资者履行其义务。不过,东道国的这一能力与其国内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不难理解,尽管近年来发达经济体也在推动投资仲裁机制的改革,但其晚近投资条约仍倾向于不规定国家反诉,如美国BIT范本、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等。而发展中国家更希望条约纳入国家反诉,以平衡其与投资者在投资仲裁机制中的权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9.19(2)条便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与其迫使投资者到其不信任的国内法院诉讼,倒不如选择国际仲裁。在伯灵顿案中,投资者与被诉东道国达成协议,不对国家反诉提出异议,应该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因此,无论仲裁员的立场是否真的具有倾向性,他们都有理由支持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此外,仲裁员一般也不会轻易拒绝管辖权。总之,在仲裁庭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尤其在投资者的推定同意问题上,上述政策考量都有利于管辖权的肯定性认定。
第四,投资者只能“全有或全无”地接受东道国仲裁提议,是支持投资者的推定同意的根本理由。而投资者能否“挑选”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不仅仅涉及国家反诉的管辖权问题,也涉及其他争议问题。例如,投资者是否可以依据最惠国待遇条款来规避条约的某些仲裁程序规则?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仲裁员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要求投资者全部接受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②参见肖军:《规制冲突裁决的国际投资仲裁改革研究——以管辖权问题为核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这也将影响仲裁员在国家反诉方面的立场。
第五,在投资仲裁领域中,仲裁员与学者之间联系密切,且不少兼具双重身份,因而学者意见对仲裁员的立场有较大影响。前已述及,近年来更多的学者意见支持投资者的推定同意;即使朔伊尔教授的基本立场是维护投资者的同意权利,其在国家反诉问题上也有折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仲裁裁决的发展趋向。
五、借鉴与启示
被诉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提出反诉时,需要承担证明仲裁庭享有管辖权的举证责任,投资者的同意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前述分析表明,认定投资者同意的法律障碍并非仲裁员的立场偏好,而是BIT的某些规定,因为它们与投资者同意的范围密切相关。因此,我国若要确保在投资仲裁中拥有提出反诉的权利,就需要在缔结条约时对相关的条款加以注意,具体包括:
(1)争端解决条款中规定的“争端”范围。应明确提出与投资者责任相关的争端也属于可仲裁的争端范围,或采用已有实践中的“任何与投资相关的争端”的规定方式。
(2)仲裁条款中有关适用法的规定。将适用法的范围扩大至东道国国内法,同时可规定仲裁庭无权审查国内法的合法性,且应遵循东道国法院和有关机构对于国内法的解释。
(3)仲裁提议的性质。为避免投资者“挑选”仲裁条款,可以明确规定,当投资者未能满足仲裁条款所规定的任一条件时,应被申请人请求,仲裁庭应拒绝管辖权。
(4)在规定投资者应遵守东道国国内法的同时,明确国家以此为依据提出反诉的权利。
以上对国家缔约实践的建议一方面是防患于未然,旨在于未来的投资仲裁中明确国家反诉的权利,避免可能产生的管辖权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已有投资条约大多并未顾及国家反诉问题,当投资者以这些条约为依据提起仲裁时,被诉东道国仍可努力从条约规定、既有判例、法理和政策层面寻求有利依据。
由于忽视国家反诉问题,从同一条约的不同条款可能得出不同结论。例如在哈姆斯特(Hamester)诉加纳案中,所涉BIT规定的“争端”是指“涉及东道国本条约项下义务的争端”,但又规定任一当事方可提请仲裁。因此,仲裁庭认为,尽管涵盖争端的范围是限制性的,但BIT承认国家也可能是受害方,也有权将争议诉诸仲裁。①Gustav F.W.Hamester GmbH&Co.KG v.Republic of Ghana,ICSID Case No.ARB/07/24,Award,para.354.尽管仲裁庭最终驳回反诉,但理由是加纳没有论证其反诉,仲裁庭回避了对管辖权的明确认定。该案表明,被诉东道国仍有机会利用不同条约规定,结合司法经济的政策考量,说服仲裁庭认定管辖权。
此外,司法经济还可成为被诉东道国的谈判筹码,促使投资者不对反诉提出管辖权异议,从而形成在投资条约之外的当事双方专门的仲裁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