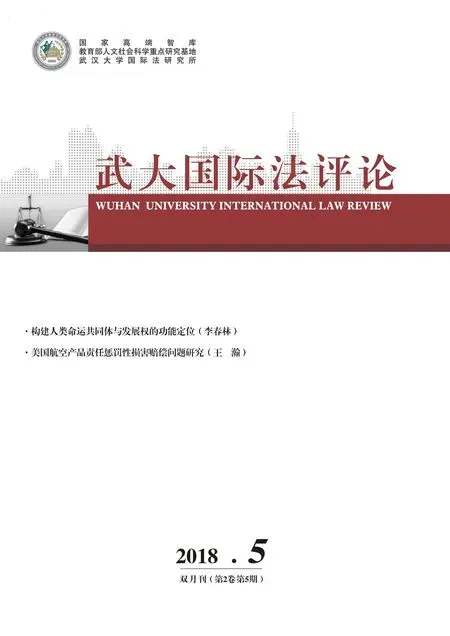全球化逆动中的“新自力救济”:“国家干预经济”的合法性探析
赵海乐
一、缘起:“国家干预经济”引发“新自力救济”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亚当·斯密以来就一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从“重商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华盛顿共识”,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经济运作、“看得见的手”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世易时移,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答案。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论战,甚至贯穿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自“二战”以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更是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升到了国际合作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只会导致零和游戏;只有为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创立规则,才能确保全体国家都能享受到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因此,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造法活动,通过国家间谈判为国家行为划定合法性边界。此种“国际造法”可能包括少量原则性规范的确定,如WTO领域中的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但更多的还是针对具体的国家行为设定详细的行为模式,如反倾销、反补贴规则。
通过国家间合意推进国际经济的法治化,在“二战”以来有效减少了国家间纷争的自力救济。当国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使用法律手段化解贸易与投资争端。WTO的五百余起争议以及数量无法统计的投资争议仲裁均是例证。然而,近十年来,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领域,却先后出现了一种“新自力救济”:一些国家不满足于当前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对别国政府的约束,借用现行规则提供的救济手段,对原本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别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实施制裁。具体来讲,在反倾销调查当中,欧盟、澳大利亚、美国先后在判例中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市场扭曲,从而认定该国存在“特殊市场情况”,并最终对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结构价格”计算倾销幅度。在外商投资审查当中,某些国家一旦认定企业母国对企业存在影响,就会将该企业划定为“国有企业”并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此外,企业母国对经济的干预,更是判断该企业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
与普通的贸易与投资保护行为相比,此种“新自力救济”的特异性有三:第一,制裁国使用的自力救济手段——反倾销与外资审查,均为当前贸易与投资规则所明确允许的手段,因而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这使得“新自力救济”明显区分于国际法上的“反措施”、“报复”、“制裁”等传统单边行为。进一步讲,“新自力救济”正是在国际法对于传统单边行为界定了详细的适用规范、从而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之后产生的。正是由于行为国无法继续以传统单边行为维护其经济利益,这些国家才会转而使用表面合法的“新自力救济”。第二,制裁国所针对的国家干预经济措施,不是在当前贸易与投资规则项下本身违法的行为。其违法性至多是有待商榷。某些措施甚至处于国际经济法刻意留有空白的领域。第三,传统的单边行为往往针对别国的特定措施而为之,目的往往极为明确,例如美国针对朝鲜的制裁就明示以核试验为缘起;然而,“新自力救济”却往往体现为针对对方一系列经济政策甚至是经济体制展开,更像是针对对方国家某种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挑战。
“新自力救济”手段翻新,且进展迅猛。采用“新自力救济”的主要国家,行为基本开始于2010年前后,且在2016年前后集中爆发,其中核心法律问题无不直接涉及或即将涉及中国。此种做法的合法性问题也同样引发了热议。国家安全审查或许无法提交投资争议仲裁,但至少在反倾销领域,上述做法就直接引发了DS473、DS474、DS480、DS494、DS529等一系列WTO争议。对中国而言,“新自力救济”必将具有切肤之痛;如何联合其他受害国,将国家间经济纠纷重新拉回法制解决的轨道,无疑具有研究意义。本文首先对贸易与投资领域的“新自力救济”逐一展开分析,研究其中的难点问题并分析其本质,最终从中国利益出发,对此问题的后续发展提出展望。
二、反倾销调查:“国家干预”用于认定“特殊市场情况”
(一)特殊市场情况的认定方式
反倾销调查是一国处理国家间产业纠纷的常用手段之一。通过认定出口商以低于产品正常价值将产品倾销至本国,该国即可课征反倾销税并因此导致对方产品在该国市场丧失竞争力。通常来讲,“正常价值”的认定方法,首选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但是,如果调查机关认为对方国内市场存在“特殊市场情况”,就有权采用包括“第三国价格”在内的“结构价格”用于计算倾销幅度。不论是WTO《反倾销协定》还是各区域贸易协定,目前均未对“特殊市场情况”进行清晰的穷尽性列举,各国对“特殊市场情况”的认定也因而较为随意。①齐琪:《新“替代国”做法及其WTO合规性探析》,《江淮论坛》2018年第1期,第36-44页。在本文所论及的“新自力救济”当中,反倾销调查机关就先后将各类国家干预经济措施作为认定“特殊市场情况”的原因。
通过认定存在“国家干预”从而认定存在“特殊市场情况”,具体方式共包含如下几类:
第一,最简单的认定方式,是将配套实施的若干贸易措施共同认定为国家对市场的扭曲。例如,在欧盟—生物柴油(阿根廷)案中,涉案措施就是阿根廷的出口税制度:阿根廷大豆的出口税为35%,而大豆制成品(如生物柴油)退税后的出口税率仅仅是14.58%。欧盟因而认为,这就客观上导致阿根廷国内大豆价格被人为压低,因此不能用于计算生物柴油的正常价值。①European Union-AntiDumping Measures on Biodiesel from Argentina,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473/AB/R,para.6.85.在欧盟-生物柴油(印尼)案中,涉案措施则同样是印尼针对生物柴油和天然棕榈油的不同出口税率。②European UnionAnti-Dumping Measures on Biodiesel from Indonesia,Report of the Panel,WT/DS480/R.
此外,调查机关还可能针对一国某一产业的整体产业政策,认为产业政策造成了该国整个产业的扭曲。澳大利亚较常使用此种体系性认定方式。例如,在对中国、巴西、印尼、泰国展开的A4复印纸反倾销调查中,澳大利亚认定印尼存在“特殊市场情况”时就明确表示:对于印尼而言,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首先表现在其“2015-2035国家森林发展战略”,该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造纸业。此外,印尼政府还实施了如下一系列政策:扩大木料可获得性;对原木的出口禁令、废止了禁止使用天然林木用于纸浆原料的要求;700万亩天然森林允许用于造纸业。澳大利亚调查机关认为,这些政策均对印尼原材料市场造成了扭曲,并导致原材料价格无法用于计算A4纸的正常价值。③Statement of Essential Facts No.341,Alleged Dumping of A4 Copy Paper Exported from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nd Alleged Subsidisation of A4 Copy Paper Exported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paras.122-129.
在较为例外的情况下,调查机关甚至还会将第三国市场中存在的国家干预,用于认定被调查国存在“特殊市场情况”。①Department of Commerce,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Certain Oil Country Tubular,Preliminary Results of Antidumping Duty Administrative Review,2015-2016.
(二)“特殊市场情况”认定的合法性之争
上述各种特殊市场情况的认定,除“补贴”的合法性有待商榷之外,其余诸如出口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环境保护政策等,本身并不必然违反国际法,有的甚至是国际法完全不会触及的领域。然而,合法的经济政策却遭遇了同样看似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二者冲突的直接结果是出口国企业遭受损失。对于出口国而言,此种认定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随意性:不受国家干预的理想市场仅仅存在于经济模型当中。但在实践中,究竟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会从“量变”上升为“质变”,导致一个正常的市场产生“特殊市场情况”?
对于这一问题,《反倾销协定》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便是上述一系列案例中的反倾销调查机关也无一作出过清晰的解答。调查机关通常会列举一系列“国家干预”措施,随后直接得出结论:这些措施导致“特殊市场情况”的形成,因而应直接适用结构价格计算正常价值。考虑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取消国家干预,因此,特殊市场情况存在与否取决于调查机关的需求。在澳大利亚对印尼等国的A4复印纸反倾销调查中,澳大利亚调查机关在分析印尼市场时指出,印尼“2015-2035国家森林发展战略”使得造纸业直接受益;对原木的出口禁令、废止了禁止使用天然林木用于纸浆原料的要求;700万亩天然森林允许用于造纸业等,均造成了印尼国内纸浆市场的扭曲。尽管调查机关强调其在分析中同样考量到了印尼的比较优势,如气候和树种适合造纸、生产技术和规模经济足以降低成本等,但或许足以决定“特殊市场情况”认定的当属一个事实:印尼纸浆价格显著低于区域基准,且无法解释此种低价如何形成。②Statement of Essential Facts No.341,Alleged Dumping of A4 Copy Paper Exported from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nd Alleged Subsidisation of A4 Copy Paper Exported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paras.122-129.印尼对于此种“特殊市场情况”的认定方式极为不满,且已经提交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然而,此处的问题在于,印尼或许能够在个案中获得胜诉,但寄希望于WTO争端解决机构从根本上厘清规则的可能性并不高。这是因为,印尼诉澳大利亚A4纸反倾销案,并不是WTO历史上第一起针对“国家干预”和“特殊市场情况”问题展开诉讼的案件。阿根廷和印尼此前已先后针对欧盟对生物柴油的反倾销调查提起了诉讼,目前已完成了全部诉讼程序。两案核心诉因完全一致:欧盟认为两国的出口税制度直接导致其国内市场价存在扭曲,因此被调查企业会计记录当中的成本数额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2.2.1.1条“此类记录……合理反映与被调查的产品有关的生产和销售成本”的要求,因此不应采信,转而使用结构价格计算其正常价格。对此,WTO上诉机构在率先作出判决的阿根廷诉欧盟案中认为,对于《反倾销协定》中的“合理”一词,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生产商或者出口商的会计记录中的成本合理反映了实际支出的成本”,强调的是会计记录本身的真实性,而非会计记录是否反映了调查机关认定的、更加合理的虚拟情形之下原本应当支出的成本。①European UnionAnti-Dumping Measures on Biodiesel from Argentina,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473/AB/R,paras.6.38-6.41.随后作出的印尼诉欧盟案中,专家组也直接援引了这一结论。
从表面上看,此案的WTO裁决已经足以否定欧盟对“特殊市场情况”规则的滥用。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首先是因为,阿根廷在此案中虽然提出了“本身违法”之诉,但上诉机构认为,欧盟反倾销法律仅仅是授权调查机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而非“必须”认定特殊市场情况的存在,②European UnionAnti-Dumping Measures on Biodiesel from Argentina,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473/AB/R,paras.6.261-6.262.这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本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不代表欧盟未来无权针对类似问题继续判断特殊市场情况是否存在。其次,具体到本案的裁决,WTO争端解决机构仅仅认定,欧盟无权将本案的“出口税”问题升级为“特殊市场情况”加以处理,也无权评判何种市场情况应当比阿根廷的现状更加合理。但是却并未完成事实上的“司法造法”行为——针对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足以引发特殊市场情况认定给出明确的规则。以上两方面原因共同意味着,欧盟完全可以以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为借口,再次认定阿根廷国内存在特殊市场情况。
事实也的确如此。针对阿根廷出口至欧盟的生物柴油,欧盟在2017年再次作出的反倾销裁决中,一方面完全回避了引发争议的“特殊市场情况”一词,另一方面依然认为出口税对价格的扭曲是客观存在的,并根据调整后的阿根廷生物柴油出口价格,计算出了4.5~8.1%的反倾销税率。①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2017/1578 of18September2017 Amending Implementing Regulation(EU)No.1194/2013 Imposing a Definitive Anti-dumping Duty and Collecting Definitively the Provisional Duty Imposed on Imports of Biodiesel Originating in Argentina and Indonesia,paras.55-80.这就足以说明,只要WTO争端解决机构并未对能够构成特殊市场情况的情形进行穷尽性列举,就完全无法阻碍反倾销调查机关对此的认定。WTO争端解决机构至多能够以一事一议的方式,事后评判涉案反倾销措施的合法性。考虑到WTO裁决本身并不溯及既往,此种救济真正的效力尚待商榷。因此,WTO目前尚未审结的俄罗斯诉欧盟、印尼诉澳大利亚等一系列案件,未来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遏制此处的“新自力救济”仍然是未知的。
(三)本质:经济发展模式的“怀璧其罪”
如果本文论题为反倾销法的改革,对“国家干预”的讨论或许可以停留在上诉机构如何司法造法以作出应对。然而,本文探讨的中心在于对国家干预的“新自力救济”,这就不能不将问题置于更加抽象的层面进行研究:第一,国际经济法是否真的内嵌了绝对的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第二,即使国际经济法真的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那么,WTO成员缔约之初是否同意通过“特殊市场情况”条款达到这一功能?第三,如果对特殊市场情况的认定本身有违法治精神,那么,相关国家如此行事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国际经济法提倡自由市场,但从未反对过国家干预。现代国家与现代政治更不可能容许市场独立于国家权力而独立存在。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国际经济法即便为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立法,也是通过细致的规则厘定主权国家的行为边界。WTO争端解决机构更是通过事实上的司法造法,不断细化既有规则以指导国家行为。倘若“特殊市场情况”条款果真被允许成为制裁一切国家干预的武器,那么,整部国际经济法的其余无数条款就会均无用武之地。因此,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最终,回归到第三个问题——相关国家扩张使用“特殊市场情况”条款的原因所在,这似乎可归结为国际经济的法治化进程与国家产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尚不存在之时,国家行为至多受到国际习惯法的干预;然而,“二战”后,尤其是WTO成立后,以单边手段处理贸易摩擦原则上已被禁止,而贸易救济则是少数合法的单边制裁手段之一。因此,将侵害了本国利益的对方国家干预措施认定为倾销或补贴并加以制裁,显然是更加快捷且表面合法的做法。事实上,此种对贸易救济措施的“跨协定滥用”,在WTO历史上并非首次。例如,DS194案的核心争议,就是美国认为加拿大的出口限制措施构成补贴,并因而对加拿大出口的软木课征反补贴税。该争议措施虽已被WTO争端解决机构认定为违法,但本文的分析足以表明,“跨协定滥用”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事实上,对国家干预的反倾销制裁,之所以在2016年前后集中爆发,原因未必在于此前全无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失效,彰显着一个制度性歧视的时代已然终结,从而迫使习惯于替代国制度的国家改弦更张,制定更加普适性的规则以重新实现其原有目的。欧盟的反倾销法改革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早在1982年,当时的欧共体就先后通过三个条例,用于处理与“国营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①Council Regulation(EEC)No.1765/82 of 30 June 1982 on Common Rules for Imports from State-trading Countries;Council Regulation(EEC)No.1766/82 of 30 June 1982 on Common Rules for Impor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uncil Regulation(EEC)No.3420/83 of 14 November 1983 on Import Arrangements for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State-trading Countries.1998年,又通过第905/98号指令,确立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五条标准:企业关于价格、成本、投入(包括诸如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产出、销售、投资的决策都是根据供求关系释放的市场信号作出的、没有重大国家干预;企业拥有一套清晰的基本会计记录;企业生产成本和财政状况没有被此前的非市场经济体系造成严重扭曲;企业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汇率换算根据市场汇率进行。①Council Regulation(EC)No.905/98 of 27 April 1998 Amending Regulation(EC)No.384/9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上述五条标准一直沿用了数十年,直至俄罗斯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中国入世“非市场经济条款”失效,欧盟2017年贸易救济新规则②Regulation(EU)2017/23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7 Amending Regulation(EU)2016/103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ulation(EU)2016/1037 on Protection against Subsidis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中方才正式确定了适用于全部非欧盟国家的反倾销规则。其中第1条首次出现了“存在严重扭曲的国家”的概念,并表示,此种国家的国内市场价格将不能用于计算正常价值。所谓“严重扭曲”是指,价格或者成本并非自由市场力量的结果,而是受到了严重的政府干预。为了判断是否存在政府干预,应当考量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国当局所有、控制下、政策监管或指导下运营的企业组成;国家在公司中的存在,允许其对企业的价格或成本进行干预;公共政策或措施歧视性地有利于国内供应商或者影响自由市场力量;破产、公司及物权相关法律的缺失,或歧视性适用,或执法不力;工资成本被扭曲;从执行公共政策目标或非独立于国家的机构获得融资。③id.,Article 1(1).
比较之下不难发现,用于判断所谓“严重扭曲”的“政府干预”因素,无疑就是先前五项标准的翻版,只不过新考量标准适用范围已然包含了全部非欧盟国家而不仅限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欧盟的这一新规则同时说明,考量“严重扭曲”还应当关注,该国是否遵循了核心劳工标准与多边环境公约。在选择替代国价格以计算倾销幅度时,替代国也应当优先选择进行了充足的劳工与环境保护的国家。④id.,Article 1(1).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将原本仅停留在学术讨论中的“社会倾销”概念引入了反倾销法当中,其对他国内政的干预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此规则能够实施,那么即便是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其市场经济状况都会遭到挑战。
综上,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部分原因或许在于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但核心仍然在于国家利益之争。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未必值得指摘,但此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疑会引发他国的敌视。此问题的解决,如不出现比较优势的自动丧失,就只能有赖于WTO制定更加详尽而有力的规则对国家间纠纷进行疏导。
三、外商投资审查:“国家干预”引发的特别关注
反倾销的实质,是阻碍他国货物进入本国。货物本身是中性的,一旦出口就与生产者和生产国脱钩。“国家干预”唯一可能发挥的作用,就是降低其出口价格。而外商投资审查的实质,则是阻碍他国资本进入本国。“资本”一词并非中性,进入东道国后仍然控制在其出资者手中,出资者母国理论上仍然拥有对其一定程度的规制权。因此,来自资本母国的国家干预可能以两种方式影响投资:第一种是直接控制资本,干预其海外投资。第二种是资本母国虽不控制资本本身,但能够通过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对资本产生影响。前一种方式通常体现在国有企业与国家持股企业的对外投资;后一种方式理论上可以作用于任何企业,但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会让东道国担忧其背后的母国可能影响本国的经济甚至是国家安全。因此,在开展了外商投资审查的国家中,不论审查内容是“国家利益审查”还是“国家安全审查”,已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明确将是否存在“国家干预”纳入了审查要件。
(一)对投资者身份的特别关注
东道国对“国家干预”的特别关注,首先体现在对投资者身份进行筛选,对于可能被国家干预其行为的投资者进行特别关注。其中,政府持股或参与经营的企业所从事的并购首先成为了关注重点,相当一部分国家均对此种投资者进行了区分,并规定了额外的审查条件。例如,澳大利亚的外资审查法律要求全部“外国政府投资者”进行的投资均须提交“国家利益”审查,其中的“外国政府投资者”是指,外国政府或者政府机关;外国政府拥有至少20%的股份的公司或者信托;或者多个外国政府拥有超过40%的股份的公司或者信托;外国政府拥有至少20%的股份的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或者多个外国政府拥有超过40%的股份的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①参见澳大利亚政府外资审查委员会网站,https://firb.gov.au/resources/guidance/gn23/。这一定义是严格按照外国政府持股比例进行的区分,也是较为传统和经典的定义方式。然而,此处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各国外资审查法律的改革,却倾向于将“母国对投资者的影响”,用于识别该投资者是否须受到特别关注。例如,加拿大2015年外资审查法律修订时,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就不仅包含了政府持股企业,还包含了“外国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拥有、控制或者影响的企业”。②参见《加拿大关于国有企业的净利益审查指南》,https://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eng/lk00064.html#p2。又如,美国2018年《外资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中,使用的则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这一概念,其内涵包括“任何能够导致美国企业被外国政府控制或者被外国政府控制的人、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人所控制的交易”。③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Section 1703(a)(7).根据美国、加拿大的规定,在其境内进行的任何外资并购,理论上都有可能成为“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二)对投资者行为的要求
一旦确定投资者或某项交易需要特别关注,各国通常就会在外资审查过程中实施更加严格的标准,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划定更低的并购金额下限④例如,加拿大外资审查中,2017年起,国有企业投资审查下限为3.69亿加元,而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审查下限为10亿加元,https://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eng/h_lk00050.html。或规定全部此类交易均须提交审查⑤例如,澳大利亚对于提交国家利益审查的“外国政府投资者”并无资本下限的要求,https://firb.gov.au/resources/guidance/gn23/。。而即便投资者本身并未引发特别关注,各国审查标准也往往会涵盖正反两方面标准:其一,投资者须保证其并购企业按照商业考量进行经营;其二,投资者须证明其不会携带母国政府的政治目标。例如,加拿大政府对于“商业考量”就进一步细化为如下标准:投资者是否遵循加拿大有关公司治理的标准;该企业向何处出口、在何处进行加工、加拿大人是否参与了该公司在加拿大或他国的经营;投资对加拿大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投资是否对加拿大的研发与创新进行了支持;投入的资本是否有利于增强加拿大在全球的竞争力。此外,投资者还须主动说明,自己“多大程度上被国家控制以及其行为和经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影响。
澳大利亚的规定与加拿大较为类似。一旦确定了投资者属于“外国政府投资者”,外资审查机关就须关注投资者的治理结构是否会导致外国政府对并购后的企业进行控制(其中也包括通过融资安排进行控制)。此外,澳大利亚也将“投资者须遵循商业规则”这一标准细化为如下考量因素,投资者的股本结构,如非政府股份的比例、性质、组成、投票权分配;投资者的治理结构;投资者是否能够采取措施保护澳大利亚利益不受非商业交易影响;目标公司是否会或者是否继续在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的证交所上市。而这一标准是所有投资者均须接受审查的内容。
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相比,美国并未明确要求投资者本身遵循商业规律行事,其国家安全审查程序更加偏重于对投资者“政治目的”的分析。这是因为,“存在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本身就是其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定考量因素之一。同时,考量此种交易能否获得批准,还须审核“投资者母国是否遵循了核不扩散规则、是否配合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交易是否会导致军用技术的扩散”等内容。①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of 1950,Section 721(f).
欧盟于2017年9月推出的《欧盟境外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草案》,从审查内容上讲与美国较为相似,仅包括公共安全和公共政策审查,其中同样未包含对投资者身份的特别定义,仅列举了计划中的欧盟统一外资审查框架所须考量的因素②这些因素包括:外商投资对于关键基础设施的影响、对于关键技术的影响、对于关键原材料供应的影响、外资企业能否因而获得敏感信息或控制这些信息。,同时该草案特别强调,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都可以考量,外国投资者是否被第三国政府所控制,包括通过大量的融资安排所控制。③参见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Foreign Direct Inz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Article 4.对此,《草案》序言第16段还特别强调,外国政府对于企业的控制,可以通过给予大量资金支持、补贴的方式进行。
(三)目的:阻却外国投资带来的国家影响
上述对于外国投资者身份和行为的审查,各国标准区别明显但共性同样突出。
首先,对投资者身份的鉴别,目的在于预估可能存在外国国家干预的风险。“持股比例”有助于判断国家作为股东在企业中能够直接发挥的作用。但考虑到现代公司治理中5%以上的持股已足以对公司决策构成重大影响,用“国家对企业的影响”这一标准作为兜底条款加以补充也是题中之义。
其次,对投资者行为的“商业化”约束,实际上是反向降低投资者背后“国家”带来的影响。“国家”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要求投资者行为须遵循商业规律,实际上是通过市场规律规范企业的行为,让它以“更像企业”而非“更像国家”的方式行事。例如,关注目标公司是否会在主要证交所上市,就是因为,上市公司须遵守包括定时召开股东大会、强制进行信息披露等一系列要求。要说明的是,投资者证明其遵循商业规律,在实践中除证明自身具有市场化的经营方式之外,通常还会主动承诺,并购后的企业将按照“本地化”和“国际化”的方式经营,例如雇佣本地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当地公司法、以国际价格为基准进行定价等。①举例来讲,中海油在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时就曾作出如下承诺:将加拿大卡尔加里作为中海油在中北美洲的管理中心、将企业股票在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上市、保留尼克森公司的既有管理层,http://www.cnoocltd.com/art/2012/7/23/art_8361_1669321.html。又如,兖州煤业并购澳大利亚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作出的承诺包括,其股票在澳大利亚上市、煤炭价格依照国际煤价确定、将企业经营中心和总部设置在澳大利亚、至少2名董事主要居住在澳大利亚、企业首席执行官与首席财务官的主要居住地位于澳大利亚,http://ministers.treasury.gov.au/DisplayDocs.aspx?doc=pressreleases/2012/009.htm&pageID=003&min=wms&Year=&DocType=0。“本地化管理”、“国际化定价”均代表着企业主动减少了来自母国的干预。
再次,直接将投资者行为的政治性纳入考察范围。某些国家侧重于“商业化”约束,但美国与欧盟的考量则直接以政治性为内容。并购审查是法律问题,但一旦将其中的政治内核进行分析,审查内容就相对复杂。例如,美国分析企业可能存在的国家干预时,会将企业母国与美国的关系纳入考量范围。欧盟在分析过程中还要考虑到企业母国的扶助政策等。事实上,东道国也同样不讳言其政治考量的具体思路。例如,加拿大政府明确表示,其担忧的外国国有企业可能带来的威胁包括:(1)外国政府对其的影响,可能导致其不符合加拿大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目标;(2)国有企业并购加拿大企业也可能影响被并购企业的效率、生产力与竞争力,从而对加拿大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国有企业针对某一领域的集中并购可能导致该领域受到大量的外国政府干预。①Statement Regarding Investment by Foreign State-owned Enterprises,http://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eng/lk81147.html,visited on 9 September 2018.
而欧盟在《欧盟境外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草案》通讯稿中也表示:“在某些经济体中,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当中占有显著份额,在某些情形下还会服务于政府既定战略。除了政府直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我们还发现,某些企业是政府通过其他手段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政府会协助本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尤其是通过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进行协助。因此……这些并购会让这些政府使用并购所得资产。这不仅会损害欧盟的科技优势,也会损害其安全和公共秩序。”②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European Council,The Council,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p.5.
加拿大与欧盟对此的阐述无疑表明,在外商投资审查中,东道国对于外国政府干预的忧虑,既包含企业母国有预谋的政治目标,也包含对方经济政策无意中“外溢”对本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与贸易领域不同,投资领域并不存在多边条约对东道国的行为进行统一规范,也并不具备多边纠纷解决机构集中解决纠纷,因此,这一领域的问题解决也更加任重而道远。
四、原因探析:国家干预为何遭遇新自力救济?
(一)贸易与投资领域“新自力救济”的差别与联系
在贸易与投资这两个领域,先后均出现了针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力救济”,不过在采用的方法上存在相当的差异。在贸易领域,“新自力救济”主要“新”在对既有贸易救济措施的扩张解释;而在投资领域,“新自力救济”主要“新”在东道国投资措施的手段创新——使用“外商投资审查”直接与他国的政府干预形成对抗。换句话讲,二者与现行国际规则的关系存在本质差异:贸易领域的“新自力救济”体现为对现行贸易规则的“借用”,而投资领域的“新自力救济”则体现为对国际投资规则尚待构建的领域进行开拓。从法治的角度,此种差异不难解释:贸易问题主要涉及海关和边境措施,贸易自由化这一概念也已在“二战”以来不断发展并已然深入人心。因此,贸易领域实现了高度法制化,即便出现某些领域没有统一的规则,也是各国在谈判后刻意的“留白”。这就直接决定了,在贸易领域,某国想要开发新的自力救济手段只能采用表面合法的方式。而投资领域则恰恰相反。由于对外商投资的规制与国家主权牵涉极深,主权国家保留其规制权的意愿更加强烈,对投资可能携带的别国国家干预同样更加敏感。因此,投资领域自由化程度较低,也并不存在成文的多边行为规范。甚至“投资保护”与“政策空间”之间的界限都比较模糊。因此,投资领域则无须“借用”某种现行的救济手段,完全可以在现行规则之外开辟与之并行的新手段。
此外,在审查内容上,外商投资审查的考量因素显然更加政治化。不过,考虑到外商投资审查本身包含了国家安全审查、而反倾销调查至多涉及产业安全而不会触碰国防、外交等政治安全,这一差异的存在也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说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手段的选择,那么,二者的共性就表现在“救济”所指向的国家干预措施。这些被针对的措施首先包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如出口税、产业政策、经济规划战略。美国曾在其官方文件中承认,“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引发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关键诱因。①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Subcommittee on Digital Commerc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Perspectives on Reform of the CFIUS Review Process Prepared Remarks of the Honorable Kevin J.Wolf Partner,Akin Gump Strauss Hauer&Feld LLP Form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Export Administration,26 April 2018,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IF/IF17/20180426/108216/HHRG-115-IF17-Wstate-WolfK-20180426.pdf.其次,被针对的措施还包括国家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的行为。欧盟在贸易救济调查中对“市场扭曲”的认定以及各国对“国有企业”或者“外国政府投资者”的特别关注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最后,两种救济方式在运作过程中均出现了对市场力量的推崇。反倾销措施推崇不含任何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外商投资审查呼唤不含任何政府扶助的纯商业经营行为。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各种国家干预的变相“排挤”。
综上,反倾销与外商投资审查均为国际经济法中的老问题,但以此为契机直接挑战他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却是近年来的新变化。从理论上讲,反倾销与外资审查规则的制度设计本身,或许自始至终均留有针对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发难的可能性;然而,2010年以来,此种可能性突如其来地集中爆发且愈演愈烈,却预示着行为国的行为模式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尤其考虑到反倾销与外资审查手段各异、但指向的国家干预措施却高度一致,这无疑进一步揭示了行为国背后的真实意图。
(二)实质:“规锁”战略下的国家间矛盾
如果暂不考虑贸易与投资领域“国家干预”问题之间的关联,仅仅从投资角度来看,强调东道国对外资的规制权本身并不罕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强调,到“卡尔沃主义”对外交保护的排斥,再到21世纪以来对东道国政策空间的强调,东道国对其主权的维护就从未中止。然而,这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最大的差异在于,此前数次运动的推进者均为发展中国家,而此次外资审查的兴起,积极进行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均为发达国家。考虑到贸易领域进行特殊市场情况认定的国家也与推进外资审查的国家高度重合,因此,“新自力救济”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国家主权的强化,而是应当从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下综合分析。更具体来讲,“新自力救济”的产生,更类似于我国社科院张宇燕研究员所论及的“规锁(confinement)”政策,即“致力于运用综合手段塑造目标国的发展路径、锁定目标国的发展空间,”从而达到“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挑战当今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①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xscg/xscg_sp/201807/t20180710_4500114.shtml。此处的“塑造目标国的发展路径”,恰恰是“新自力救济”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对他国国家行为进行单边制裁,从而迫使其基于本国产业压力或本国资本压力放弃某些经济发展措施,或者,至少抵消这些经济发展措施所能够带来的好处。举例来讲,在贸易领域,一国政府对热轧钢市场进行干预,目的不外乎促进热轧钢本身出口或鼓励下游产业对其深加工。然而,一旦该市场被认定为“严重扭曲”,则下游产业或将使用进口原材料加以替代,或减少生产规模。而一旦此种“市场扭曲”被“传导”至第三国、成为调查机关对第三国生产商适用“特殊市场情况”规则的借口,则热轧钢本身的出口亦将困难重重。①潘锐、余盛兴:《美国对韩国输油管产业“特殊市场状况”的认定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韩国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第197-208页。又如,在投资领域,一旦境外投资贷款本身被认定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则各国国有进出口银行的主要业务将形同虚设。
“规锁”的出现,根本原因必然是国家利益之争,或者说是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权力之争。而直接原因,则要包含内因——经济与政治的两重矛盾,以及外因——国际制度不能为发达国家提供有效的支持。
经济与政治的第一重矛盾,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逻辑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逻辑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的市场理念天然地与国家干预存在矛盾。对于很大程度上化身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而言,市场越自由,其权利空间就越大。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不受控制的全球市场只会导致本国的边缘化,因而政府干预与扶持经济是势在必行的。因此,国家利益的冲突,直接体现为发达国家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国家干预的自力救济。
经济与政治的第二重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随着“非传统安全”一词的深入人心,国家安全已远远不止于军事的强大与国防的无懈可击,而是包含了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诸多方面。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会根据“232调查”而非惯用的“301调查”先后对中国和土耳其的钢、铝增税以及美国为何认为中国并购其高新技术企业会危及其国家安全。贸易与投资或许会给美国带来绝对收益,但当其并非相对收益最大的一方,它就依然会据此认定其竞争优势受到了挑战,从而威胁到其在国际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而威胁其国家安全。此种将贸易与投资问题进行“安全化”的做法,无疑又将刺激这些国家获得国内支持,寻求更加激进的国内立法。考虑到上文已经论及,发达国家国内资本同样呼唤自由市场、反对他国国家干预,此处的“国内支持”的获得也同样是水到渠成的。
除“发达国家的资本利益”与“安全需求”这两重内因之外,驱动“规锁”措施的外因,则在于当前国际制度不能继续维护原规则制定者的利益。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国际制度的一大功能即在于以制度的形式锁定霸权国的优势。从GATT到WTO的八轮谈判,当前国际贸易规则的形成基本体现了美欧之间的贸易博弈,也体现了二者主导下的世界贸易利益分配。随着BIT的大规模缔结,“公平公正待遇”、“征收和充分补偿”等一系列投资待遇条款的订立,国际投资规则同样基本反映了跨国资本的利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先前的国际制度再无法服务于其利益,反而限制了其行为。①杨国华:《中美贸易战中的国际法》,《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3期,第120-141页。美欧等国虽有动力谋求变局,但其实力却又无力支持新规则的达成。因此,原先占据主导的一方就更有可能抛开既有规则另辟蹊径,本文所讨论的“新自力救济”就是其中的具象之一。从TPP到TTIP再到美欧日的零关税协定,也均是此种趋势的反映。
五、对策:以共同利益促成国际共识的达成
对于“规锁”思路下的“新自力救济”,首先必须承认,企业能够寻求的救济相对有限。这是因为,不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其中涉及的相当一部分问题均有着坚硬的政治内核,而这是司法审查竭力避免触及的。举例来讲,在常茂生物化学工程有限公司诉欧盟委员会案当中,对于中国的原材料市场是否存在“市场扭曲”、增值税退税是否影响了中国国内市场定价等问题,欧盟法院明确表示,“在涉及共同商业政策时、尤其是涉及贸易保护措施时,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情况的复杂性,欧盟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此的司法审查仅限于审查程序规则是否得到了遵守,涉案措施用以作为依据的事实是否正确表述,以及对事实进行分析时是否存在明显错误或者权利滥用。”②Changmao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Co.Ltd,v.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Eighth Chamber)1 June 2017 in Case T442/12,para.33.这也因此意味着常茂公司不可能就实体问题得到任何救济。而即便中国将争议提交至WTO,裁决结果也很可能是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的翻版。与之相类似,在罗尔斯公司诉奥巴马案当中,罗尔斯公司获得胜诉也是由于其被剥夺财产权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要求,而并未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决策内容本身进行审查。①Ralls Corporation,(Appellant)v.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ppe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pp.37-38.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善于利用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是必需的,但应当尽量避免将重心放在政治问题上。
其次,不论是贸易救济还是外资审查,都仅仅是“规锁”策略的具象之一。我国政府和企业还应当谨防“新自力救济”的变体。当前的国际制度之下,发达国家固然不能为所欲为,但其毕竟仍然是既有制度的主要构建者,因而完全有能力利用其世界话语权创造新的发难手段。举例来讲,欧盟虽在对印尼的生物柴油案中败诉、被WTO裁定不得以出口税为由否定印尼的自由市场,但2018年6月起,欧盟正式对外宣称将逐步停止在运输燃料中使用棕榈油制造的生物柴油。其官方理由之一,就是印尼因生产棕榈油而砍伐了大量原始森林。然而,印尼媒体同样反驳,欧盟此举的真正缘由是欧盟广泛使用菜籽油制造生物柴油在成本上处于劣势,且生产棕榈油并不比生产大豆、牛肉、玉米更加毁坏森林。②Khalil Hegarty,The EU’s War on Palm Oil Will Continue,http://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8/07/06/the-eus-war-on-palm-oil-will-continue.html.如果将棕榈生物柴油禁令、欧盟对印尼“特殊市场情况”的认定、欧盟反倾销新规则中对“环境保护”的特别强调这三者结合起来,不难发现,三者手段迥异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其中,后二者在WTO法律体系中未必于法有据,但棕榈生物柴油禁令虽然同样可能引发关于“工艺和生产方式(PPMS)”、GATT第20条例外等争论,却至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因而也更加难以对抗。
再次,从我国政府的角度来讲,当前,“新自力救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转化为2016年后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待遇问题。韩国、印尼、阿根廷所遭遇的问题,我国未来极有可能会同样遭遇,而外商投资审查由于国际监管的缺失,未来更会愈演愈烈,诸如美、澳先后阻止华为、中兴进入的问题也很可能不断上演。而问题的解决,固然有赖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①例如,对于诸多国家在外资审查中强调的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我国完全可以在商业类国有公司改革过程中加以注意。相关论述参见王建文:《论淡马锡董事会制度在我国商业类国有公司改革中的运用》,《当代法学》2018年第3期,第60-67页。但最终仍然要靠博弈达到平衡。“新自力救济”的根本原因是基于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而展开的博弈。问题因而并不在于国家干预是否真的合法,而在于国家干预是否侵害了对方的利益。正如我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在2018年7月26日WTO总理事会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发达国家是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发明者和主要使用者。正是18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开启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先河”。美国与欧盟质疑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政策,但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同样大行其道。②《张向晨大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反驳美国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指责》,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xwfb/201807/20180702770570.shtml。考虑到“新自力救济”很大程度上“新”在其不断推陈出新的手段,而当前的国际经济法已经在现实的挑战之下屡屡出现疏漏,乃至于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显现,问题的根本解决,仍然取决于在世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法律冲突仅仅是表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冲突。因此,如能通过政府间合作推动贸易深化、通过行业协会进行游说交涉缓解各方利益冲突;通过并购企业的社会责任承诺、本地化承诺、治理结构承诺等取得当地社区乃至上下游产业的支持,则无疑会减轻对中国的特别针对。③王宇鹏:《欧美加严外资安全审查的趋势特点和分析建议》,《国际贸易》2018年第5期,第28-30、36页。对于某些进行“外资并购国家利益审查”而非“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国家,由于国家利益一词远比国家安全范围广泛,此种与东道国分享利益的做法更加可行。
对于贸易问题,考虑到即便是当前的FTA谈判也多会简单纳入当前的WTO项下贸易救济条款,确立新的贸易救济规则可能性并不大;更加可行的方案,是将新动向提交争端解决。争端解决机构的处理结果未必能够完美维护我国的利益,但至少能够通过法庭辩论和第三方参与促进相应问题的国际共识达成。例如,仅仅是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一起案件,就有包括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在内的十个第三方参与。而在印尼诉欧盟生物柴油案中,第三方则增加至十三个。争议各方与第三方的总和,涵盖了除泰国之外世界排名前十五位的生物柴油生产国。因此,WTO争端解决如能推动生物柴油的主要生产国以此为契机形成行为规范共识、或至少能够求同存异,将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此例充分表明,国家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国家干预经济同样无处不在。因此,从理论上讲,本文中的反倾销措施,受害国可以是任何一个与美欧产生了利益冲突的国家。而相反相成的是,当利益冲突产生,进行关注的也必然不只是贸易救济措施的实际受害国。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如能通过争端解决程序突破“中西之争”,将矛盾转化为利益之争,将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取得更多国家的支持。
对于投资问题,由于外资审查本质上仍然是外资准入问题,而相当一部分BIT仅仅涉及准入后待遇问题而非准入前待遇,即便是以负面清单管理外资准入的国家也未必愿意承诺准入前国民待遇。因此,投资审查过程中对国家干预的态度,国家在条约谈判阶段能做的相对有限,目前仍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与东道国利益集团的沟通与协调。不过,贸易领域对相同或同类货物的歧视是被明确禁止的,投资领域的国别歧视却是常态而非例外。早在2006年迪拜世界港口并购案中,问题就并非该港口能否被外资所控制,而是港口控制权能否由英国企业交由迪拜企业。因此,在投资问题上,中国企业目前尚无法争取别国盟友以共同对抗国家安全审查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