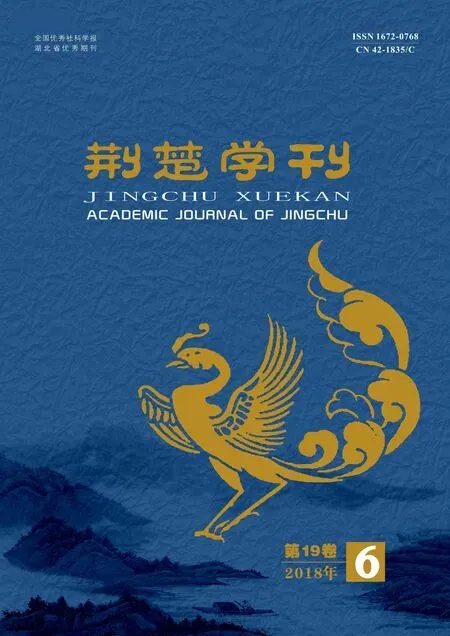身体的狂欢与消费:“抖音”短视频的审美反思
曾 蒙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2017年,短视频盖过了直播的热度,在互联网上大放异彩。短视频App在手机应用市场上层出不穷、更新不断,其中又以“快手”“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抖音”等App最为火热。短视频的第一个特点如其命名,强调短,其时长多以秒为计算单位。沃霍尔曾言,“将来,人人都可以著名15分钟”[1]。如今,只需在短视频软件上发布短短15秒视频,草根也能出名,获得众人的围观。短视频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的社交性,在人际传播上“具有巨大的可分享性(share-ability)”[2],正因其高度社交性,短视频软件都能获得极大的用户流量。
“抖音”作为一匹“黑马”在短视频领域中脱颖而出:“抖音的国内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5亿,月活跃用户超过3亿。”[3]“抖音”的短视频类型丰富,从主题上大致可以分为“明星、才艺创意、旅行美食、晒娃秀宠、美女帅哥、婚礼现场”[4]等类型。其短视频多为配音发布,热门的配音多为节奏性强、抒情性强的歌曲,极具听觉刺激性和情感渲染性。不管是何种主题视频,视频发布者大多在音乐的伴奏下以自己身体的夸张动作或任性舞蹈来表现自我。比起以往其他大众媒介,身体元素在“抖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展示更为直观。作为当今视觉时代新兴审美媒介的突出代表,“抖音”将视觉时代的审美路径彰显到极致。将其作为视觉时代的一个镜像,从身体这个关键词入手,可以管窥视觉时代语境中的独特审美路径与身体狂欢、身体消费现象,并对其中潜藏的审美困境提出合理建议。
一、审美路径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媒介的发达带来审美媒介在当代社会的主导、叠合和泛化现象”[5]72,使得审美媒介走向了多元化;但也不得不承认视觉元素在其中日益占据突出的地位。当今主导的审美媒介甚至可以说已经从由文字走向图像/视觉,“音响和画面,特别是后者构成了美学,指导着观众”[6]105。而审美媒介作为沟通和连结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工具,在审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具体地实现审美意义和信息的物质传输,而且给予审美效果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5]70。审美媒介的变迁不仅给人们带来新的审美体验,更塑造了一种新的审美路径。
黛布雷以媒介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时期:书写(writing)时代、印刷(print)时代和视听(audio-visual)时代[7]。其认为与视听时代相对应的是视觉(the visual)。前两个时代也可统称为文字时代,该时代中的人们对于文字尽管也是以看的形式来进行,似乎也是一种视觉文化,但实际上人们是在读文字。“视觉活动的本质是视觉化(Visuality)”[8],但人类阅读文字所产生的视觉化其本质是间接的、次生的,是发挥主观想象的产物。这要求审美主体在“理解一个论点或思考一个意象时调节自我的速度,与之对话”[6]108,由此出现所谓“诗无达诂”的现象。因而文字时代对审美主体的要求更高,其需要懂得文字形象所潜藏的意义,否则文字符号对其而言便为无意义之物。故该时代的审美具有主动性、高雅性与精英性。其次,文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有其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区分,这种二分模式导致语言在表情达意时必然存在着某种困难或局限。一方面,语言符号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是对万事万物的抽象式把握;另一方面,任何抽象的把握都不能整全地反映现象世界。因此人类在使用语言时总是面临各种言不尽意的尴尬与困难。中国古人以“立象以尽意”的巧妙形式来解决这一困难,本来语言就和自在世界存在一层能指的隔离,“立象”之后又多了一层“象”的隔离,最终语言与自在世界之间无疑变成了双重隔离。因而文字时代的审美具有明显的凝神静观特点,人往往进行着有深度的思考,追寻所指内涵与返回自在世界的过程必然需要一种沉思。
而视觉时代则突显出与文字时代迥异的审美路径。首先,在语言和图像二元对立的传统中,“语言被认为高于图像,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就是‘逻各斯’”[9]43。人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所直接目睹的现象总是不断变化、异常复杂,视觉的地位也因此常常遭到贬低。在巴门尼德看来,“一切感官知觉仅仅提供错觉,其主要错觉恰恰在于它造成了一种假象”[10]。柏拉图更是继以“相”论将活生生的现象世界视作对“相(理念)”的模仿,视作“相”的影子,一种虚假。当代视觉文化的繁荣,正是对传统以语言为中心的思想文化的反叛,不再是追寻所谓的“本质”“真理”而是掉转头直击感性现象世界。因此视觉时代一个突出的审美特点就是直击感性存在,解放感性,带来一种震惊式的生理快感体验。“抖音”正是以青春、美、身体等感性元素而爆红,“抖音”便是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冲动,特别是激发人的笑,这种充满笑点和感官刺激的视频在大众中尤其是年轻人群中大受欢迎。再次,在视觉时代,审美主体在面对不同图像时,尽管有着选择的自由;但一旦选定看的对象,“运动中的图像总能抓住你的视线,把你引向某一方向”[11],人在这一过程之中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图像。最后,图像相比文字而言,使得人与自在的世界之间不再是一种隔离状态,图像往往直接刺激着人们的视觉。视觉文化对审美主体要求相对降低,文化抑或审美都不再是精英的专权、不再独居高雅之堂。“抖音”作为新兴视觉文化的代表,没有对象的限制,只须会使用手机即可,人人可以观看、分享、留言讨论短视频。人人也可以上传自己的视频,由一个看者转变为被看者。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大众参与性的新兴媒介。
审美媒介由文字到视觉的转变,不仅带来了审美体验的变化,更带来了一种审美路径的变化。也即以何种方式进行审美,这种方式不仅包括物质媒介层面,也包括思维与心理层面。简而言之,文字时代的审美更加高雅化、精英化、理性化、审美主体具有较大主动性和创造性,多以凝神静观方式进行;视觉时代的审美则更加通俗化、大众化、感性化,审美主体呈现出被动性特点,往往被震惊、被惊艳。“抖音”中最常出现的热门评论是“别人的男朋友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抖音中的狗也能上清华”等等,诸如此类的高居被点赞榜首的评论也正体现了这些短视频的震惊风格。
二、身体能指的狂欢
视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感性文化。人类的感性可以分为认识活动层面以及肉体官能层面,前者“以感知、表象、想象、联想为感性认识”[12],后者“是以生理欲望、原始冲动、感官快适、自然本能等为表现形式的感性生活”[12]。尽管鲍姆加通将感性提高到一门科学的层面,建立了感觉学,也即美学,但他只顾及到感性的认识活动层面而“悬搁了一个重要的感性存在——肉体,身体的作用和意义”[12]。这个被压抑的、遗忘的身体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运动中不断得以解放,甚至极端地强调“回到身体自身,就是回到身体直接的肉体性”[13]。同时身体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符号,其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也极力地迎合了“小时代”人们表现自我、展示自我的欲望,由此身体也成为了当代视觉文化中最重要的审美对象和审美媒介之一。
(一)“小时代”语境与身体语言登场
“小时代”(1)是相对“大时代”而言的。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治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直接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语境之下,“小我”不具有合法性,也是要遭受到批判的。改革开放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确实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使得更多的个体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勤奋而致富和实现自我”[14]7。此外,市场经济发展不仅促进了“个体的兴起”,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个体化”[14]358。换言之,“小我”的地位由此得到重视和保障。此外,“小时代”还与当代哲学思潮转变有关:“从本体论走向了功能论”[15]25。前者是一种深度模式,伴随着本体的都是沉重的、宏大的话题,如灵魂、绝对精神、本质等。而功能论也即“效益、功用和利害得失,成为衡量一切的首要的也是最终的尺度”[15]25,简而言之,关注什么是有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价值论哲学。价值是相对主体而言,这种功能论或价值论将主体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小我”的地位得以提升。生活在“小时代”的人们执着于追求“小我”的最大化,在生活中处处表现自我,展示自我。
改革开放后,在文化上这种“小我”追求大致呈现出三个阶段,可谓之“三部曲”。首先体现为从纯文学走向网络文学,尽管这二者都以文字为媒介,但网络文学却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细分类型以及私密的体验。人们在仙侠、玄幻、言情等等细分的类型中找到自我的归属感,在大量私密写作中满足了“小我”的窥视欲望。这种文字的解放,带来了文化上最初的小我感,网络文学因此也被视为“文化转轨与文化解放的开路先锋”[16]。其次,当图像时代来临时,网络文学又让位于各种图片文化。比如各种表情包风靡网络媒介,视觉化的表情包以最迅速、最直观、最形象的方式传递着发送者的感情、心理、个性。再次,直播以及短视频的兴起又让图片比如那些表情包退出“小我”表达的时尚圈,因为图片给众人的小我感似乎还不够。“小时代”中的人们对“小我”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文字与图片都是借助外在于我自身的媒介,它们与“小我”始终隔了一层。最终,“我”便直接用自己的身体亲自登场,开直播、录小视频,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小世界的最好感性代言。因为身体不同于文字和其他图像,身体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即便是同一个人的身体也很难做出两次一致的身体动作。所以,当人们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展现和表达自我的语言时,“小我”被塑造到近乎极致的状态。
(二)身体在狂欢之中沦为能指的空壳
“抖音”正是“小时代”最新代表物之一。它最初火起来是源于各种各样配着音乐的身体舞蹈,诸如海草舞、拍灰舞、喵喵舞、开车舞等新奇、时尚的舞蹈。这些舞蹈表演者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借着电音、舞曲配乐短时间内爆红网络,引发众跟风模仿,呈现出一种集体狂欢。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青年研究者往往泛用、滥用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来描述“抖音”文化现象,笔者在这里所使用的“狂欢”仅从其字面含义也即纵情欢乐角度而言。因巴氏“狂欢”的特性,尤其是“颠覆等级性”在“抖音”中表现得并不醒目,相反“抖音”文化之中始终隐藏着等级的建构。
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an animal symbolicum)”,“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7]43。身体符号作为视觉时代的“时尚符号”,在使用中走向了能指的狂欢。这种能指的狂欢一方面体现了言语(2)活动的迅速生产,能指的消费。例如,“抖音”视频中曾经火热的一个动作桥段:逆天化妆,该视频的第一个画面是表演者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在配音响起后画面随之切换:表演者用一件衣服挡住自己并迅速将其甩开,而呈现在观看者面前的对象立马变得或楚楚动人,或帅气时尚,可谓“颜值”忽然“爆表”。如果说该系列动作的首演者通过自己的身体,将某种青春活力,或人要靠衣装、化妆等所指传递给观看者。那么在该动作不断地被大众模仿,迅速生产出一系列的身体“言语”活动之后,这种个人性的身体言语不断发生着“原初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发生了二度或三度能指的情况”[18]。身体动作的模仿于传播过程之中沦为了形式意义和生理快感的传播,而其所指则是贫乏性的,“因为其仅仅作为一种能够使意义和快感在社会中流通的中介;作为对象本身,它们是贫乏的”[19]123。另一方面,这种能指的狂欢也反映出大众对身体语言符号的外置(excorporation)过程,也即“每个人都有权在商品系统所提供的资源之外,创造自己的文化”[19]15。例如在逆天化妆系列视频中有模仿者第一个画面不变,但将甩开挡住自己的衣服的动作修改为抖动衣服欲找衣架挂着。这种结尾的突转或不按套路出牌,超脱了身体动作所具有的最初含义,从而不断带给观看者新的感官体验和生理刺激。大众的外置能力,将符号意义“见之于使用的方式,而非被使用的事物”[19]15,无疑加剧了身体语言符号能指漂移的过程。观看者会在这些意料之外的能指中沉醉与发笑,意义在身体能指狂欢之中丧失或缺席,并最终将沦为能指不断漂移的这一行为过程本身。正是不断漂移的过程给观看者带来了新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猎奇和娱乐化的需求。由此“身体作为符号的表达,其成了符号的器官或工具”[18]。
三、身体消费的悖论
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在狂欢之中既是自由的,又是受束的。一方面,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运动后,“宗教与意识形态教条在界定、规训、控制身体方面的权威性的削弱”[20],身体从灵魂束缚中走向了自由。另一方面,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号的操纵”[21]114。符号无疑成为一位新神,身体作为当今消费社会的重要符号,也从实用地位走向了一场“氛围”的游戏,也即将身体作为突出自己的符号而加以塑造与消费。由此观之,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又走向严厉甚至残酷的自我控制与约束之路。
(一)身体在消费之中的自由与解放
在中西方社会中,长久以来灵魂可以说是一个中心(center)。解构主义认为中心“是一个绝对的或者说先验之物”[22]15,是西方历代传统哲学建构的基石。解构主义所好奇的正是“如果这个中心被移除后会发生什么,结构会做如何改变”[22]15。而事实上,“身体在今天成为救赎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它取代了灵魂之中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功能”[21]129。换言之灵魂这一中心已被移除,由于失去灵魂这一中心的控制,身体处于一种四处漂浮、游走的状态,人似乎一瞬间一无所有;但转而却将自我存在的感觉完全归之于身体,因为“至少身体好像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在现代世界中重建可以依赖的自我感觉的基础”[20]。
在“抖音”大量的短视频中,表演者纷纷以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身体,身体在“抖音”中是自由的。有健身房秀肌肉的,有穿着比基尼秀身材的,也有对着镜头眨眼卖萌的,当然,最时尚的方式是以舞蹈的动态形式来进行,各年龄层次的人群都加入到这场舞蹈的狂欢之中。在中西方文化中,舞蹈的文化意义最初都是近乎神圣的、沉重的。因为其作为人神沟通的中介,所要解决的多为关乎部族兴亡的重大事情。李泽厚先生指出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彩陶盆上所绘的舞蹈“直接表现了当日严肃而重要的巫术礼仪,而决不是大树下、草地上随便翩跹起舞而已”[23]。如今的“抖音”中恰恰也流行过一段类似舞蹈,也是三五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跳舞,然而“抖音”中的舞蹈者,随时随地都可以翩跹起舞。尽管并排牵着手,似乎有了某种仪式之感,但这种动作行为本身的意义只是停留在行为本身所造成的视觉奇观上——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与青春靓丽的外貌。移除中心之后,身体在感性视觉的狂欢之中,是“典型的以形式之重,承载着精神之轻”[9]155。这种形式之重,也即形式的自由化,身体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自己。这一看似自由的、我行我素的身体行为,有时甚至挑破了道德伦理的束缚,无论是对于视频表演者而言,还是对于观看者而言,都享受到一种极大的感官刺激和生理快感。本雅明指出“游荡者”(flaneur)的形象:他们沉醉于四处游荡所带来的“动感凝视”,“游手好闲者屈就的这种沉醉,如顾客潮水般涌向商品的陶醉”[24]。而在“抖音”中,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位“游荡者”。在一个接一个的身体动作中,人们的视觉不断遭受着动态的震惊,不断游荡、陶醉在变换的身体动作形式之中。
(二)身体在消费之中的控制与约束
“资本已把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商品化了,包括人的身体乃至‘看’的过程本身”[25],在资本渗透之中的视觉文化之中潜藏着等级与束缚的内核。身体在不断变换的形式之中看似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但不得不承认人们在消费身体,给予其自由时,也在不断束缚身体。身体在现代消费文化中如聚光灯一样,聚集着看者的目光与凝视,造成一种集体围观效应,这一看的行为也将被看者推向了视觉焦点。但在看与被看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而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实际上,“抖音”背后的看者绝大部分拥有“一双男性的眼睛”。这种拥有并不意味着肉体上的具有,而是指心理上或文化上的拥有。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26],在男性话语规训下,即使是一双女性的眼睛也最终多少变成了一双男性的眼睛。比如“抖音”中的那些获得高点赞量的女性身体,大多“颜值爆表”,或青春洋溢,或妖娆妩媚,或苗条性感。这些身体形象正是男性话语中的理想身体,是男性不断以话语权力去支配女性的产物。但在视频的留言中却不乏众多女性人群,她们具有女性的双眼却对这些理想身体纷纷投出了羡慕和惊叹的目光。换言之,她们也想变成这些理想身体,她们也幻想着自己的身体能登上舞台的中央,享受众人的凝视。现实中身体是天生的、自然的,然而在话语的规训下,人们认为“身体不是自然生成的、固定的,而是可以改造的、可塑造的”[20]。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按照社会话语权力所标举的理想身体去改造身体。“如果说以往是‘灵魂包裹着身体’,如今则是肌肤包裹着身体……肌肤作为一种声望的服饰与声望的第二故乡,成为符号以及时尚的参照”[21]130。“模式”或者说“理想身体”会让人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不断地修改以求达到模式的标准,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控制和束缚,更是一种自我对身体的暴力行为,“身体在这一行为中简直就是祭品”[21]143。“抖音”在给予人们一个身体自由表演的舞台时,也潜藏着让身体走进一间暴力牢笼的困境。对于“抖音”中每一个所谓理想身体的点赞及夸赞的留言,都将为未来的“身体暴力”埋下伏笔。总之,“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21]174,“抖音”中身体的狂欢不仅是展现身体、表演身体的自由狂欢,更是一场控制身体和约束身体的狂欢。
四、审美的困境及出路
尽管“抖音”给予了大众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人人获得了看似平等的表演权和观看权,同时也促进了当下审美文化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抖音”作为视觉时代的新兴审美媒介,无疑将身体极力地推向了狂欢与消费之境。而这其中也潜藏着审美的困境:本来通俗、大众的短视频却逐渐走向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化”。而且身体作为审美的对象和媒介,也在消费之中越来越走向自我控制和自我暴力的境地,沦为娱乐至上的奴仆。这一困境也是视觉时代与消费时代双重叠加的产物,对其不能不做理性反思:“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7]。
(一)表层的审美化与娱乐至上
“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美学的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28]3,但“不幸的是,在审美化标题之下,人们经常光是言及它的肤浅含义,而未能思及深层次的审美化”[28]4。当今的审美化更多的是在表层上进行,而且处处可见。大到店内精心设计的壁纸、桌椅、板凳等,小到商品包装袋、商标、灯光色调等,都围绕着美来进行。但这种美是最直观的视觉注视下的美,这种注视并非凝神静观,而是处于动态游走之中。消费者所体验到的美,来自生理的快感和感官的刺激。“抖音”也正是迎合了消费社会中的这种表层的审美化,身体在舞蹈中所流露出来的是肉体的感官刺激。正如许多“抖音”视频的评论“看到你,我感觉恋爱了”“看到你的一瞬间,我连我们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糟了,是心动的感觉”等等所反映出的,这些观看者对于美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生理快感层面。这无疑也显示出“当代审美文化的低幼性”[15]254,其所提供给人们的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最低层次,也即生理需求。而今的消费者,其生理需求实际上在吃、喝层面多已得到满足,但却将生理快感作为新的“粮食”来消费,而这种“生理快感的饥饿”状态实际上很难得到满足。“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形态,是一种快乐原则的文化,一种欲望的文化”[29]316,快乐和欲望是交织在一起,彼此循环,互相促进的。所以当“抖音”以身体将这种快感引向狂欢时,人也陷入了追寻生理欲望的无底洞,而人们自我实现的需求与深层次的审美无疑将被娱乐至上所遮蔽和遗忘。
(二)技术崇拜与“三俗化”
“抖音”从最开始的时尚化、大众化、通俗化,到如今却逐渐与“快手”的审美模式趋同。“快手”视频因其观看者可以给表演者打赏“鲜花”“幸运星”“小金人”“666”等虚拟礼物,这些礼物可以变现。故在金钱的刺激下,“快手”视频表演者往往做出“三俗”——庸俗、媚俗、低俗之举。而“抖音”尽管一直未开通虚拟礼物这类让视频发布者赚钱的功能(3)。但其所采用的智能算法,却也让用户发布的短视频逐渐趋向于“三俗化”。该模式“就是利用编程技术解决信息如何实现精准分发问题的一种机制”,“使受众便捷地获得自己恰好想了解的内容”[30]。以“新浪微博”为例,其并非采用智能算法模式,只有所谓的“大V”才能获得大量的关注。而在“智能算法”模式下的“抖音”,会给予每一位视频发布者同等的推荐权。而且智能算法会根据用户对视频的浏览及点赞,自动为该用户推荐该类型的视频。显而易见,“算法一直走在越来越懂你的道路上”[30]。但是智能算法是在缺乏人作为主体的情况下独自做出的判断,其可以判定人喜欢什么,但并不能判定人所喜欢的是否存在价值,是否健康。例如以智能算法著称的“今日头条”,在技术中立中忽视了人的监管,“旗下的‘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和相关公众号因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等突出问题被永久关停”[31]。智能算法下的“抖音”会越来越给受众推荐满足其欲望的视频,而这些不断被点赞的小视频反过来又会刺激那些视频表演者继续发布此类视频。由此循环导致短视频逐渐走向了“三俗化”之路。技术崇拜突出了工具存在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当人沦为物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时,毋庸置疑,这是一种非审美化的异化状态。”[29]289
(三)出路:重申理性与因时而化
“抖音”审美文化的困境只是当代审美文化“感性泛滥”困境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困境说到底还是源自中心的移除。理性、灵魂、本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之物,关联着沉思之物,权威不再,由此“我们发现,取代沉思的,是感性、同步、直接和冲击”[6]111。这种“直接、冲击、同步和感性效果作为审美模式和心理体验,将每一时刻戏剧化了”[6]118,这正是人类在失去沉思,感到生命之轻后所采取的措施。人们以不断的生理刺激、感官高潮来狂喜狂悲,来承受生命之轻。然而“被一阵感性刺激的旋风裹挟之后,剩下的只有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6]118。如果不重新正视那些中心,这种由枯燥的日常生活到心理高潮的刺激仍会不断循环。但恢复中心,重申理性,并不意味着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无情地驱逐诗人那样,“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32]。若将“抖音”这类短视频软件一律强制关停,抑或只准许在“抖音”上发布传统形式讲述正能量与理性的作品,这都将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不能以审美匮乏来治疗审美困境。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媒介。重申理性的正确做法是因时而化,视觉时代这一大的语境并不可逆,但在这些不断发生的新变化中却能够以新形式去重申理性,“创新是文艺的生命”[27]。同时政府应发挥好引导与监督职能,利用好“抖音”这类新兴审美媒介,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之物以新的方式,寓教于乐的形式去呈现(4)。让“抖音”既百花齐放,又有真善美的引导,重申理性。如此,我们的文化也终将回归正常之路,我们的审美也将走上促进人们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康庄大道。
注释:
(1) 本人选择“小时代”而非“微时代”是从哲学思潮转变、国家历史进程角度来立论作为主体的“我”碎片化了。而学界对“微时代”的使用多强调的是客体,诸如文化的碎片化和细微化。
(2) “语言”和“言语”是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重点区分的一对概念,他认为前者是属于社会的、重要的;后者是属于个人的、从属的和偶然的。
(3) “抖音”没有打赏功能,只有收藏和喜欢、评论以及转发等功能。“抖音”的打赏功能设置在用户直播模式中,而非本文所讨论的短视频发布模式。
(4) 例如“四平警事”(四平市公安局官方抖音号),以娱乐形式做普法视频,在抖音上发布88部作品共收获5 024万点赞,并吸引了1 071万粉丝关注(2019年1月5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