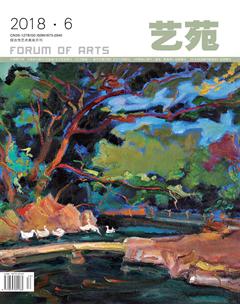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与日本能剧
郭苏苏

【摘要】 美国现代戏剧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晚期戏剧《送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是一部具有静态戏剧特点的作品,与日本能剧在人物形象、戏剧结构和美学追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这部剧不刻意追求戏剧的外部动作冲突,以剧中人物的回忆和讲述的故事作为全剧的主体情节,表达了美国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信仰缺失和心灵危机,并展现了东方哲学对解决西方精神危机的启示。
【关键词】 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能剧;精神危机;东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一、《送冰的人来了》与能剧简介
《送冰的人来了》创作于1939年,是美国现代主义戏剧家奥尼尔(1888-1953)晚期戏剧的代表作,也是他最满意的一部剧作。奥尼尔创作晚期的四部作品——《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休吉》《月照不幸人》,剧中充斥着人物的回忆,角色陷入往事的记忆和编织的白日梦中徘徊无前,戏剧外部动作处于停滞状态,总体上呈现出静态戏剧的特点。静态戏剧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早期希腊悲剧一般被称为早期静态戏剧,但由于亚里士多德《诗学》所奠定的重外在行动的动态戏剧传统的不断延续和扩展,这一戏剧形态被完全淹没于西方戏剧史中。因此,西方戏剧最早虽是起源于静态戏剧,但并未形成以静态戏剧为典型的戏剧传统。直到19世纪末,梅特林克提出“静态戏剧”观,契诃夫、品特等戏剧作品中也呈现了静态戏剧的美学特点。
14世纪末期,东方的日本出现的能剧是静态戏剧的典范,观阿弥、世阿弥父子二人集能剧之大成,将其发展到顶峰。能剧不注重表现戏剧激烈的外部冲突,也“不再重表现剧中的角色做什么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重在呈现剧中角色所谈论的往事”[1]79,它“将复杂的情节归入剧中主角回忆中”[2]85,展现过往经历对现在所造成的心灵创伤;观众所看到的不再是角色之间激烈的现时冲突和向悲剧结局发展的动态行动,而是他们对已经发生的悲剧的静态追忆,感受到的是对往事的悲叹以及生活的悲凉感、无奈感。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叶芝(1865-1935)最早将能剧元素引入西方视野,并在戏剧创作中有意识地吸收、运用,其戏剧思想影响到奥尼尔、贝克特等在内的西方众多现代剧作家。1932年,奥尼尔在《美国观察家》(American Spectator)文学月报中刊登的《面具散论》(Memoranda on Masks)中,提到了日本能剧,他说任何一个对面具所带来的巧妙戏剧效果“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应该去研究一下日本能剧面具”[3]101,可见,奥尼尔对日本能剧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奥尼尔在1939年创作出的《送冰的人来了》在戏剧形式上与日本能剧有诸多相似之处,亦是有迹可循。
《送冰的人来了》以1912年夏天美國的一家下等酒馆——霍普酒馆为背景,戏剧时间集中在两天,出场19人,共有四幕,并以剧中人物回忆和讲故事为整体情节架构全剧,塑造了常驻在霍普酒馆中一群社会失意者的群像。第一幕时间是一天的早晨,故事从酒吧晚间侍者罗基和酒馆客人拉里的对话开始,随后酒馆中昏睡的酒鬼们陆续醒来,他们随意散漫地聊天,“回忆”自己的往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个叫希基的人每年在霍普生日时会来酒馆中请他们喝酒、给他们讲笑话;直到幕尾,希基才出现,并向酒馆中的人宣布了两个消息——第一是他已经戒酒,第二是要把这群酒鬼从白日梦中拯救出来,并告诫他们不要再用“子虚乌有的明天来哄骗自己”[4]791,这群人对希基流露出“不解、不满和不安的神情”[4]798。第二幕时间是当天的午夜时分,酒馆这时的氛围与希基到来之前已经有所不同,这群酒鬼在为酒馆老板霍普准备生日宴会的过程中,其语言和动作中都透露着不安和不耐烦,他们互相指责,对希基的说教亦感到厌恶,故意拿希基妻子与送冰人私通的事情来嘲笑希基,随后希基向他们宣布自己妻子已经死亡的消息。第三幕时间是第二天早晨,这群酒鬼纷纷抱怨希基破坏了他们的宴会,虽然口头上说讨厌希基,但他们还是在希基的影响和说教下,纷纷走出酒馆,试图重新生活,酒馆老板霍普刚走出酒馆门就被汽车吓得缩回来,大家在围着霍普聊天时,希基又宣布一个消息——自己的妻子伊芙琳是被人杀害的。第四幕时间是第二天午夜1点半左右,这群酒鬼又都重新坐在酒馆中,并抱怨喝的酒没有味道;希基向他们讲述与自己妻子之间的往事,揭开了他与妻子之间关系的真实面貌——妻子伊芙琳对希基非常忠诚、宽容,根本不存在与送冰人私通的事情,反而希基生活混乱,并且杀害了伊芙琳;最终希基被捕,帕里特自杀,酒鬼继续在狂欢的白日梦中饮酒作乐,拉里陷入沉思,戏剧到此结束。
这部剧虽以“送冰的人来了”作为题目,但直到结束“送冰人”也没有“来”。奥尼尔曾对这部剧的题目作过解释:“它有一个表层的含义,剧中有一个旅行推销员,他杜撰了一个送冰人和他的妻子之间有奸情的玩笑,它还有一个深沉的含义,同死亡相联系。”[5]39这个题目蕴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剧中旅行推销员希基杜撰的妻子与送冰人私通的故事,“送冰人”是通奸者;其二是源于《圣经》中十二个新娘等待新郎来(cometh)的典故,喻示只有做好准备的人才能等到耶稣基督,剧中酒鬼们翘首以待希基的到来与其有相似之处,这里的希基成为耶稣基督的隐喻,他是救赎者同时也是带来死亡的人。在整部剧中,回忆和讲故事是主要的戏剧动作——酒馆中的人在等待希基的过程中回忆讲述自己的故事,到来的希基向酒馆中的人讲述自己与妻子的故事。这个“送冰人”在剧中虽从未真正出现在观众面前,但却隐隐存在于剧的始终:在前三幕中,我们从酒鬼们口中得知,送冰人是希基告诉他们与自己妻子私通的人;而第四幕中,希基将自己与妻子的故事和盘托出时,我们发现“送冰人”是希基杜撰的,而且他就是故事中“送冰人”的翻版,是一个通奸者。整部剧充斥着对往事的回忆和讲述,真假难辨、虚实相融,其角色设置、戏剧形式和美学特点与日本能剧都具有相通之处。
二、相似的角色设置
能剧演出一般只有两三个演员:一部剧有一个主角,被称为“仕手”,这个主角一般以鬼魂的形象出现,“经常超越时间界限而生活在被称为‘梦境的无始无终的空间之中”[6]199,是剧中故事的回忆者和讲述者;主要的配角称为“胁”,常以僧侣的身份出现,有时是单个的人,有时是两个人或者更多,他(们)是“仕手”故事的聆听者,其作用是最终帮助“仕手”驱除执念,获得灵魂上的解脱,回归正道。
《送》剧中,虽然人物众多,没有出现僧侣和鬼魂,人物也并非是“仕手”和“胁”,但其戏剧人物的设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方:一方是希基,一方是霍普酒馆中的群体,他们分别承担了类似于“仕手”和“胁”的职能。剧中的希基出现时,酒馆中的这群酒鬼就像能剧中的僧侣可以感受到鬼魂一样,几乎都感受到了希基身上的死亡气息。在这里,希基就如同一个幽靈一般游荡在这群酒鬼之间,并向他们讲述自己与妻子从相爱到最后相杀的过程,这与日本能剧中“仕手”的鬼魂向僧侣讲述自己的往事非常相似。能剧中“仕手”通过向“胁”讲述往事,得到帮助和超度;希基向酒鬼们讲完故事之后,内心的悔恨得到宣泄,最终亦卸下心灵的重担,获得解脱。
但奥尼尔剧中的“仕手”和“胁”之间的角色并非如此简单,其扮演“胁”的酒鬼群体,也具有“仕手”的特点;反之,在剧中扮演“仕手”的希基,亦承担着“胁”的任务。剧作以霍普酒馆夜间侍者罗基和宿客拉里的对话开场,罗基说霍普酒馆“就像一个太平间,这些酒鬼都是些死人”[4]740。待在这里的酒鬼原本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霍普曾是一名政客,威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麦格洛因曾是一名警察,拉里曾是世界产联的一份子,雨果曾是报社编辑,吉米曾当过战地通讯记者,布尔人韦乔恩曾当过布尔人部队首领,英国人刘易斯曾做过陆军军官,黑人乔曾是一家赌场的老板,意大利人罗基是一名皮条客,等等。但他们现在共同生活在霍普这个下等酒馆中,没有有身份和地位的差别,都成为生活的失败者。他们都有对过去的执念,不想面对现实生活而躲到这里饮酒消遣,这些人虽身处现实,但无一例外都活在自己编织的白日梦的虚幻世界中,弃绝了当下真实世界,执着于过去和未来的幻影中无法自拔,在这个被时间遗忘的一角苟且偷生。他们犹如能剧中已死的滞留于人间的“仕手”鬼魂一般,虽存在于世间,但并不属于世间,既无法回归执念所在的过去,更无力到达向往的未来。这群酒鬼时刻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梦想重现往日的辉煌,但他们的行动一直飘浮于子虚乌有的“明天”,这种无止境的往事重现和未来缺席,逼迫他们持续不断地回忆和憧憬自己的人生,而使当下的生活受到过去和未来的压抑停滞不前,成为一群找不到出路的现代“仕手”。他们被困在这个阴森肮脏的酒馆之中,等待着希基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欢笑。后来出现的希基,就像能剧中的灵魂超度者“胁”一般,他来自现实世界,具有现实的洞察力,他与酒鬼们进行交谈,鼓励他们抛弃酒精和白日梦,直面不堪的过去,勇敢走出酒馆与外界残酷现实搏斗,找寻和争取自己的位置,从而让自己的时间得以延续,获得解脱。这群酒鬼也接受了希基的“超度”,勇敢走出白日幻影,离开酒馆直面现实。剧中,“仕手”和“胁”之间相互转换,剧中角色都成为“仕手”和“胁”的复合体,具有拯救者和被拯救者、超度者和被超度者的双重身份。
可是,希基作为“胁”,并不像日本能剧中的僧侣那么可靠,他自身本就陷入杀妻之后编织的白日梦中无法自拔;酒鬼们灰溜溜地重回酒馆,也证明了他最终也未能成功拯救酒鬼“仕手”的灵魂;另外希基将酒鬼们拼命掩藏的失败人生揭穿,导致了酒馆氛围的紧张,打破了酒馆表面上的平衡和友谊,造成酒鬼之间的疏离和仇恨。这不仅没有拯救他们的灵魂,反而使他们更加痛苦,丧失赖以生存的支撑,导致了帕洛特的自杀,造成了他心灵和身体的双重死亡。是拯救还是扼杀?希基的真理代言人和拯救者的身份变得不确定。另外,酒鬼们亦没有真正承担起“胁”的责任,真正拯救“仕手”希基的人其实是他本人,他因为认识到自己不能再自欺欺人,因而选择向酒鬼们坦白真相,并提前叫来警察,让自己真正离开“白日梦”的幻影;因而,酒鬼群体作为“胁”,只是“仕手”希基的故事聆听者,并没有成为其灵魂的超度者。剧中无论是希基还是酒鬼群体,作为“胁”,他们都没能承担起灵魂拯救者的职能,奥尼尔隐晦地表现出了他对拯救者存在性的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能剧和早期希腊悲剧中都有歌队的存在。只是两者略有不同:能剧的歌队不跳舞,“只呈现场景并为仕手和胁吟唱台词,并且从来不会扮成独立的角色表达主观意见”[1]273;而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则一般在颂唱的时候表演,并且扮成角色表达意见。《送》剧在角色安排上虽与日本能剧相通,但若作为歌队的酒鬼群体,更像是早期希腊悲剧中的歌队,他们倾听主角的声音,并会作出回应。所有这些职能,让酒鬼群体的这一角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表现了奥尼尔对西方现代戏剧形式的探索和丰富。
三、相似的戏剧结构
日本能剧一般是以梦、回忆和讲故事的情节来架构全剧,即以僧侣“胁”的梦为戏剧整体,通过其梦中主角“仕手”的回忆,呈现“仕手”往事和“仕手”执迷于往事“迷梦”而产生的执念。在梦中,配角“胁”是“仕手”往事的聆听者和灵魂的超度者,通过听取“仕手”所讲的故事,了解“仕手”的经历,化解“仕手”的执念,让“仕手”回归正位。最终僧侣醒来,发现故事只是一场梦而已,戏剧结束。在能剧中,戏剧的现时外部情节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剧中人物之间基本不存在戏剧冲突,冲突存在于“仕手”回忆的往事之中。正因为能剧主角的回忆不受时空限制,所以能剧虽剧情简单,场景单一,却能够容纳深广的社会内涵;能剧中的故事虽只是一场梦,却是来源于现实、贴近现实,因而给人一种如梦似真的感受。
《送》剧可以说是一部回忆剧,其整体结构与能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整部剧的剧情几乎可以概括成“回忆”和“讲故事”,剧中人物或回忆自己的往事,或回忆他人的往事;或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讲述他们的故事。威利回忆自己在法学院学习的辉煌往事,韦乔恩津津乐道于自己以前的战功,黑人乔说到以前自己的赌博技术和赌场老板身份感到洋洋得意,霍普对自己错失当选市议员耿耿于怀并归咎于自己因妻子贝西去世伤心过度,麦格洛因一再宣称自己当警察时的恪尽职守,莫舍自豪地谈论自己成功从姐姐贝西那里捞到剩余零钱的“智慧”,希基细致地向酒馆中的人讲述自己与妻子伊芙琳之间的往事;而另一方面,罗基述说了威利的落魄,刘易斯透露出战争时韦乔恩的狼狈,希基说霍普本就只想醉醺醺混日子无心参政,拉里讲述了麦格洛因当警察时的贪赃枉法,霍普说贝西非常清楚莫舍“偷钱”的把戏,等等。整部剧的情节节奏非常缓慢,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件发生,充斥着的都是这些人毫无中心主题的语言。这些人物之间虽然有一些打闹和争吵,但始终没有发展成为推动戏剧故事情节发展的事件,反而让观众觉得他们更像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痛苦,但又互不交叉。酒馆中的群体虽然对一本正经的希基表现出了不解和不满,但他们之间始终没有发展成现时的激烈矛盾。整部剧几乎就是一群社会失意者坐在酒馆中一起回忆往事和讲故事,直到希基被捕才出现一点戏剧的“紧张”部分,甚至帕里特的自杀也只是被处理成拉里听到了一些声响,反而姗姗来迟的希基宣布的几个消息——戒酒并且要拯救酒鬼脱离白日梦、自己的妻子伊芙琳死了、妻子伊芙琳是被人杀死的,成为霍普酒馆中气氛转变的“节点”,使戏剧的外部情节有了一些缓慢的推进。
同样地,这部剧跟日本能剧的结构相似,也运用了梦的形式,奥尼尔本人曾说“这是一部关于幻梦的剧本”[7]112。酒鬼们最初沉醉于酒精和白日梦,夸耀地谈论着自己的辉煌往事,他们每一个人都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梦中不愿醒来,迷失在“希望”的梦境中,躲在霍普(原文Hope)这个小酒馆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往事时总是添油加醋地加以美化,而在别人口中他们的往事又是另外一番样子,这种对比构成了真假难辨、虚实难分的效果。而且,希基到来宣布的要打破白日梦的消息,使这群酒鬼们的心理逐渐失衡、不安——两个侍者罗基和查克互相挖苦、讽刺对方,霍普无端向酒鬼们大发脾气,科拉和伯尔、玛吉之间相互辱骂,酒馆中的人对黑人乔也表现出敌意,等等。酒馆中的所有人都陷入一种躁动不安、愤怒的状态,互相指责、揭短、辱骂,酒馆氛围陷入紧张的状态。这群酒鬼之间本就脆弱的友谊破裂,纷纷说着要离开霍普酒馆,期望重新开始以证明自己;但真正离开时,又找各种借口踯躅不前,几乎都是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刺激才走出霍普酒馆的门;而帕里特在直面了自己的背叛、没有了白日梦的支撑之后选择自杀。所有这些情节都证明,“梦”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真与假、实与虚的界限变得模糊,整部作品呈现一种虚实相融的特点。
能剧的环形叙事结构背后蕴含的是佛教的“轮回”思想,把整体的故事框架归结为一场梦,蕴含的是佛教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的观点,如梦如幻的氛围呈现的是东方的美学特点。奥尼尔的藏书中亦有涉及佛教的著作,较为权威的就是A.K.库马拉斯瓦米的《佛陀及其妙语纶音》,可见,奥尼尔对佛教并不是一无所知;奥尼尔在后期还非常钟情东土道家思想,读过詹姆斯·理雅各的《道书》(这本书收录了老子《道德经》及其庄子几乎半數的著述译文和评论),甚至将自己后来居住的别墅命名为“大道别墅”,《送冰的人来了》就是他住在大道别墅之后创作出的第一部剧作。在《送》剧中,奥尼尔对勇于打破白日梦的希基和帕洛特的毁灭结局以及沉迷白日梦的酒鬼们的欢乐结局的安排,表现了他对“白日梦”的理解和看法——白日梦虽然让他们的生活停滞,但却支撑着他们的生存。剧中这群酒鬼们的生活既是真实地,又是虚幻的,他们生活在与现实世界相连又相隔的“希望”酒馆中,拥有“真实”的过去和虚幻的“未来”;他们的回忆是真实的,但其中亦包含许多虚假的成分,真假相互包含、虚实相互交融,这种打破二元对立、真假虚实交错的戏剧氛围,具有典型的东方美学特点。
结 语
能剧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家强调慈悲、怜悯和普渡众生,能剧中“胁”的形象常常是志在普渡众生的游僧形象,他们有着拯救天下苍生的强烈责任感,洞察世事,了解民生疾苦,因而具有度化“仕手”的能力;另一方面,“仕手”亦是在“胁”的启发下醒悟,主动选择“放下”和“宽恕”而得到解脱,获得“重生”。奥尼尔深刻推崇的道家哲学是“个人主义”的,主张依靠个人力量和个人意识,超然世外,获得个人身心的自由和解脱,就像剧中希基所说的“我内心的平静不能代替你内心的平静,你内心的平静要靠自己去找”[4]812。这两种东方哲学虽有很大不同,但又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主张从人的自身寻找摆脱痛苦的根源和极乐境界的自我体认,而不是祈求于外在世界或者外在的神,这与西方基督教中将拯救者寄托于上帝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同。
《送》剧的背景虽设置在1912年,但剧中人物的年龄大都在60岁上下,他们的壮年时代一般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他们所怀念的辉煌年代正是资产阶级到处宣扬“美国梦”神话的时期。这群生活在霍普酒馆中的人生失败者,他们都曾怀揣着成功的梦想来到美国,也短暂地实现过或者狂热地追求过自己的“成功梦”,都曾激情澎湃,追逐着物质、名利。但现在的他们都沦为失业者,“既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又失去了身外之物”[7]75,躲避在下等酒馆中靠酒精麻痹自己,“美国梦”不复存在。1939年的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剧中酒馆的生存状态也是经历过经济泡沫的美国人的真实写照。显然,奥尼尔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他通过刻画这一群底层人物的群像,不仅仅呈现了个人“白日梦”的不切实际,更是映射出整个“美国梦”的虚幻。这些经历过虚幻、跌落谷底的人,不断玩弄着“声音的游戏”[8]409,用声音重复往事、诉说未来打算,而不是用行动支撑和实现梦想,沉迷于自己编织的虚幻梦境,从成功的造梦者沦为白日梦的奴隶,在物质主义的追逐中丧失自我。奥尼尔个人对基督教的质疑以及西方普遍的信仰缺失,让他放弃了从西方本土文化寻找出路的努力,而是探索从东方获得拯救自我灵魂的灵感。《送冰的人来了》在形式和美学追求上与日本能剧的相似,蕴含的是奥尼尔期望用东方艺术形式表现西方精神危机的尝试,以及东方哲学对解决西方精神危机的启示。
参考文献:
[1]Stan,Lai.Oriental Crosscurrents in Modern Western Theatre[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3.
[2]李幼新.港台六大导演[M].台北:自立晚报社,1986.
[3]尤金·奥尼尔.戴面具的生活[M].肖舒,高颖欣,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4]特拉维斯·博加德.奥尼尔集(下)[M].汪义群,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5]Eugene,ONeill.CommentontheDramaandtheTheater[M].Baltimore:the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7.
[6]詹姆斯·罗宾森.尤金·奥尼尔和东方思想——一分为二的心象[M].郑柏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刘海平,徐锡祥.奥尼尔论戏剧[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8]Travis,Bogard.Contour in Time: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l[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