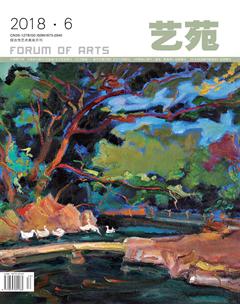高效的邪典演绎
李青
【摘要】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香港电影新浪潮不仅突破了此前多囿于厂棚的佳构剧格局,也为接下来的港片黄金年代铺陈了话语空间,其中为警匪片开拓的新格局就是典例之一。本文将通过香港电影新浪朝时期10余部犯罪题材的电影中关于犯罪的诠释、警匪关系与正邪定义、邪典氛围与黑色风格的运营等方面,探寻其突破与启发。
【关键词】 香港新浪潮;犯罪片;邪典;本位与错位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犯罪题材对于电影语言而言有种默契的讨巧,这种讨巧首先源于一种默认的叙事背景:充满隐患的空间、边缘却共情的人格、暴力与性的多义化以及对身份乃至命理的否定。而视听手段更能突出这种毁灭感,正如徐克作品《第一类危险》(1980)中主角四人只需要用肆意投放炸弹、肆意纵火、肆意杀生、肆意穿梭墓地就能明确表示新时代青年对未知势力甚至杀戮的蔑视,这种身份与罪名的搭配在影像铺排中又轻易暗合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新生的复杂文化命题。故而在新浪潮开始的三五年间,尽管出现各位导演突显各自风格的多元景象,但是相近的文化熏陶、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让他们在讲述某种时代的错位时,多以犯罪故事起手。不论是徐克的求新手段、章国明的宿命意识,还是余允抗对破坏感的内化处理,都在各自版本的警匪故事里达成一种融通,让人从该时期一系列对于社会危机的讲述里看到一种暗合起来的脉路:正义命题中加入了灰色的权衡空间以及恩怨间的计算,一种普遍的边缘化成了犯罪最原始的动机,实验性的镜头背后仍是港式节省思路,意念因此被叠加,故事也因此在高效的叙述中维持风格。
一、理性承前:九本铺排中的身份思考
大卫·波德威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中提及关于香港电影制作的节约与高效:
“……香港导演划一片长,一般为90-100分钟,或9至10本拷贝之间,戏院便可每隔两小时放映一场,务求一天之内安排最密的场次,增加票房收益。正如前文所述,导演把九本作为铺排剧情的单位,第一本首先抓住观众注意力,第四本开展一条重要的剧情线,第六或第七本出现另一个重大转折,最后二至三本是延宕的高潮与结局,即若落幕后仍余音袅袅,以盼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1]
而在新浪朝时期,在个人话语空间输入身份与本位意识的新思路面对九本制作的默契时不仅瑕不掩瑜,而且还更加碰撞出符号意义。以该时期的犯罪题材为例:灰色边缘的落魄警察、反社会的年轻人、做困兽斗的悍匪、无辜受难的孤独英雄,充满探究性的身份置于日常生活,让观众看到在官能刺激之外的另一种触动:它们在90分钟的故事里只能作为剪影掠过,却因为这种简化而营造出一种抽离于时代的共情,甚至可以作为一种警醒。
对于这种“警醒”,该时期作品大致有两种处理手法:其一是用具有视觉冲击的暴力表现手法来直陈,诸如徐克作品《第一类危险》(1980)、余允抗的《山狗》(1980)、许鞍华的《疯劫》(1979)、牟敦芾的《打蛇》(1980)、谭家明的《爱杀》(1981)、严浩的《夜车》(1979)等;另一种则是借警匪身份与关系的边缘化谈某种关于生存的难堪,其中有章国明的《点指兵兵》(1979)与《边缘人》(1981)、唐基明的《杀出西盘营》(1982)、翁维铨的《行规》(1979)、于仁泰的《墙里墙外》(1979)和《救世者》(1980)、麦当雄的《省港骑兵》(1984)等,语境浑然天成,直接影响了后来警匪片的批量生产。
前类作品中,《第一类危险》通过无知少年出格的暴力犯罪来讲述大环境下的毁灭意识,作为主角之一的少女阿珠呈现出完整的反社会型人格,并讓这种异样事出有因:她的警察哥哥具有过激的暴力倾向,不仅随手伤害阿珠,更会因为案件行凶者是美国大兵便在街上肆意攻击洋人泄愤,凭着警察身份在正义的加持下尽情施展暴力,这种披着正义外衣的恶几乎是新浪潮时期多部警匪片中的标配。该片更值得提及的是对于“面孔”的思考:同阿珠的警察哥哥一样,三位少年在被洋人挟持后,在茶餐厅见到外国面孔就惊慌逃窜。三位少年选择的第一次试爆的场景是电影院,电影院正在放的是战争片,贯穿全片的也正是犯罪与战争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后众人在墓地之间的枪战,虽然只是数人对峙,却有兵有匪,施暴者同时又是受害人,从分明的阵营身份以及少年们的应对策略而言,再次近乎一种战争的格局。影片最后美国大兵扫射墓碑,镜头扫过一片石碑姓名,已经喝下滴露的濒死少年反而打死洋人,当他也学着举枪向墓地扫射时,画面切到数十组暴力事件的黑白照,接回故事开端三位少年在楼顶恶作剧地将血浆丢下楼,宣布着此刻将死之人的胜利。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前后两年前牟敦芾的《打蛇》、谭家明的《爱杀》以及严浩的《夜车》中,近乎一种“无因的反叛”式启发。《山狗》稍异,讲的是出离道德的复仇故事,质感更邪典,但仍然落实了人物身份的塑造。如果说《第一类危险》中少女阿珠用针扎白鼠、残害猫致死乃至最后和猫一样的死法是为了形容青年的兽性,那么《山狗》则更加铺展了这种兽感:为了区分行凶者的洞穴世界和露营者的居民世界,开场便是“山狗”们将活猪分尸、众人与猴子狼狗同居、蛇佬去酒吧也要与蛇分酒。制造视觉刺激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人物逻辑:当他们将青年阿华的手指斩断,并且放蛇迫其坠崖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杀人如杀动物的行为。肥佬最后对队友活埋告密者表现出不忍,也并非出于道德约束,而是因为身处团体底层他与动物关系更亲密,暴露的并非是人性而是一种由于亲兽的感情。反观他们对立面的露营年轻人,表面上是文明学生、见到一只老鼠被夹死都惊得打翻热水、小情侣沿途试探性的肢体接触、Louis用喝阿玲喝过的水来表达暗恋,实则又是另一种受规训的兽性。当平行镜头切换,阿玲危机逼近时,小情侣却在不远处自顾自地缠绵,让观众无法同情他们的文明与示弱。这种理解与不同情让影片有了一种超出邪典风格的厚重。同样讲述青年与暴力,许鞍华的《疯劫》中已经显示出了导演后来的意念与格局:虽然取材于真实凶杀案,却在影片开头直陈“唯与女死者青梅竹马之邻居少女,对该案情则另有剖白”,将一桩直白的傻佬杀人事件处理成萦回的错杀,直观无奈的凶狠变成了有迹可循的情感拉锯。少女连正明在片中是无畏的新青年,她不断发掘真相并引导观众对李纨同时产生怜悯与怀疑,直至影片结尾处的合力施暴,使观众明白是傻佬在模仿李纨行凶,仍然暗合了前述作品中无知暴力的可怖。横亘的墓碑、走夜路的尼姑、住在森林里的傻子、用菜刀开膛取出遗腹子、新生儿的啼哭中画面再切回仍在望眼欲穿的老妇与身旁的佛像,影片的连环起伏有旧时传奇的形状。更值得讨论的却是对于一桩案件改弦至此,从前的奇案系列充分满足官能上的猎奇,把视角转向真实的生存境况,厂棚定光定位的佳构剧理念结合街头巷尾的危机,更加暗示了真实生活空间中的隐患,它与复杂的社会背景、与青少年的成长相关联,其本土意味本土情感乃至于本土使命感,都值得后来的奇案片凭之自省。
如果说前类作品过于导演风格化,另一类作品的进步则更近乎扬弃。警匪片大热的征兆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邵氏出品的《天网》与《香港奇案》系列中已有迹可循,并且80年代《最佳拍档》《警察故事》等卖座系列也获得了直观的成功,可是相比于这种杂糅动作、佳构以及喜闹等商业元素的工业生产,章国明在《边缘人》(1981)中开启的对“警察身份”就事论事的严肃,更加能引起观众对正邪乃至身份的定位思考:主人公阿潮作为卧底,协助警方却也被迫杀人赌博欠债,比起此前作品关于正邪定位的脸谱化操作,影片男主是一个不断换工作的年轻小警察,在责任的命题上,他从在影片的开场表现出来的就是年轻人特有的言行不一,不同于以往一无所有的英雄,他既要面对市侩而懦弱的亲人,也要经历由赌钱、欠高利贷、抢劫一路顺势而为的堕落。《边缘人》中一些实验感的镜头直陈而不突兀,在警察当街抓小贩时,小卖部老板一边围观,一边看着自己店内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的场景,每个捉捕动作的节点都落回到他的中景表情上,最后冷眼对警察,他作为旁观者与这场动作之间产生了见证关系,而从围观到态度呈现到最后一句斥责引起的警察心里的波动又简单地形成了连贯逻辑,警察小贩与旁观者之间多切到近景表情,充满人文关怀。这种镜头出现在影片每一个关于日常叙述的环节,不论是阿潮与女友的打闹,还是与各种人的对谈,更类似于内地第四代导演的社会质感。相比同时期其他犯罪片而言,章国明把暴力与血腥使用得更克制,在小警察伙同他人第一次作案时,连杀人都被处理成误杀,面对情敌不论是谈判还是抢击,都止步于“破坏”,而非同期作品中更泛滥的“毁灭”。这种克制使影片虽然不及邵氏出品的观感刺激,却更接近一种生活的真实,所以当黑帮老大在险些发现阿潮的身份,并当着他的面枪击替死鬼后,阿潮的痛哭与后怕,反而最能触动观众。
相对于《边缘人》着力在枝节上呈现警民关系以及警察身份,强调紧张与特殊性,《点指兵兵》则是遣散了这种身份感,故而在动作性上,该片显得平和,在生活格局的呈现上却因此显得更加通融,更像是在阐述一种犯罪环境,在日常化的叙事节奏中,元素是饱和的,视点是均分的,采用初出茅庐的小警察视角,反映犯罪环境中的众生相,只是一切轻微错位。在该片中,贩夫走卒与卧底的功能,是在日常动作中顺承下来、具有人情的,犯罪的事件反而略过,而对于“参与其中”的人物的动作的描摹突出各方对于罪案的态度以及行为。包括警察在对待民众、对待知情不报的小贩、对待记者以及对待社会边缘人士时,跳出了警匪片的关系格局,而在聊某一种警察生活,或说是斗鸡眼匪徒与警察这个身份之间的私人恩怨。小警察在被他击中手臂后,害怕得忘记自己是警察而找巡警求助,最后击暴歹徒是出于求生本能的反抗,当他在斗鸡眼的尸体旁颤抖到呕吐时,这种恐惧和《边缘人》中阿潮的后怕又暗合起来。
同样是节奏修正,《救世者》的明朗节奏继承了厂棚制作的高效,同时也在90分钟内争取到了更加足够的抒情空间。影片在前10分钟就用三个小段落,分别交代了警察汤帮办正义而勇敢的性格、其懂事的养子与懂事的红颜知己、贯穿影片的五女连环被害案件,搭档的二人在吃饭间便轻松解决了一桩抢劫案。紧接着便直接介绍最大的嫌疑人及其悲惨的童年,甚至汤的红颜知己也愿意为他亲身接近罪犯。在一切过于传奇化的顺畅中,影片将全部力道发挥到了结尾处,当汤帮办让保罗的父亲先出现在天台,使保罗仓促间枪杀了自己的父亲,又趁其惊乱而将其击毙后,红颜知己因此与他决裂,最后养子也因他无力抚养而被他人领养,故事至此揭示出所谓救世者主题:为了正义而使用边缘化的手段,而罔顾自己的亲人,最终只能是孤独的英雄。同样是关于孤独英雄的讲述,《杀出西营盘》则继承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古龙系列的武侠质感,即使用枪,采取的也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手上功夫,体现出英雄作为人的突出性。这方面更突出的处理在于后段关于枪战的段落,当警察与杀手同时出现在西盘营的阁楼上,三声枪响便拉开阵营,每一枪都是经过考量,结尾处男主作为落难英雄在废弃仓库被摩托车队追杀,以一人之力避开数十铁骑,甚至支撑到最后一刻兄弟二人在雨夜的废弃仓库举枪决斗,武侠片式对峙又唤醒了观众对英雄的信念。最大的遗憾是在处理男女主的感情线时,仍维持旧武侠片式无理的浪漫:男主高达夫几乎是强奸了好心照顾他的女主唐可儿,在高进入她身体同时,镜头切到女主挣扎中手指触及高背部的伤口,遂在一种隐喻中产生了依附的爱意。至于后来“你为我撑伞,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她在死前叫着你的名字,她一定是非常伤心,最可惜的是,她喝不到你亲手煮的汤”之类的台词,更像是略早时期古龙武侠中的浪漫符号,包括为了保證爱人的安全而在海边亲手将她枪决,这种无理与弱化虽然能使观众动容,却使它变成了一个迁就的故事。
二、智性启后:生存责任与内向化邪典的质感
谈及香港新浪潮电影犯罪题材对后来作品的启发,不论是对警匪身份与关系的探讨,还是将作者意旨隐匿为元素的“春秋笔法”,都在模仿中渐渐聚集成一种类型,甚至一些尚未超越的手法仍值得借鉴。
从《边缘人》开始,到林岭东的《龙虎风云》(1987)、90年代系列改编、一直到《无间道》(2002),作为卧底的心路历程一经展开,便开启了数十年关于身份认知的共情效应,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被无限探讨的命题思路:如何是没有身份的出路。相对于《龙虎风云》《无间道》以及同类的卧底片而言,《边缘人》的节奏更慢,更注重男主关于社会责任的心态叙述,在后来的卧底故事中,获得这个身份只是接受命令的一种动作,然而在该片中,却变成了长官与下属之间关于安身立命与社会责任的讨论。然而,仍然是港式的节省,在真正成为卧底之前,只用下班后的一串行为镜头,便既落实了男主在成为卧底之前的准备工作,又补充了关于他生长环境的叙述。当阿潮成为卧底之后,影片直接呈现出他如何自如地扮演一个小混混应有的姿态,呼应开头警察当街抓小贩的动作,暗示了警匪之间没有区别。如此相比而言,20年后的《无间道》的孤独挣扎反而显得过于英雄。同时陈帮办的态度并不正义,他更像是一位实质的领导,而非符号意义上的警察。这种失职感在于仁泰《墙里墙外》中被明朗化,黑化的关系网更甚于游达志导演的《暗花》(1998)。《暗花》中突出的是阿琛作为凭着个人警觉心游走于正邪势力的腐败警察如何因为被动的正义而自取灭亡,而《墙里墙外》用更大的笔力交代了一种格局。如同《点指兵兵》开场便明朗地以孩童间“点指兵兵”的游戏以及接下来一段音乐抒情段落来交代故事主题,以歌词“兵贼仿似早分配来”交代文本的一种宿命观,这种注定之中的错乱在后来韦家辉的《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中被更加落实。
而其间另外有一种黑色风格的雏形启发了新港产时代的警匪演绎。《杀出西营盘》一夜之间四个兄弟被杀,亲信之间的猜疑对应高层之间的忌惮,使犯罪的格局拓展成权益斗争。这种结构使人想起杜琪峰执导的《黑社会》(2005),叙事的推动力是一股不断叠加间的消解。而在众人分别遭袭的段落中,影片用来均衡节奏的是杀手各自的手段,如同英雄各有高下,杀手也各有快慢,这种铺陈不仅带出了犯罪世界的真实质感,使画面始终保持张力,并且整体段落仍是简洁高效的。影片有很多至今都值得参考的节奏处理办法,比如一个场景与一段动作就能概括说明事件逻辑:在建筑工地的暗杀段落,男主跳入手脚架,追凶者随之跳入却直接摔死。《杀出西盘营》中开场的日本漫画色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来的《夕阳天使》(2002),后段又有了《天若有情》(1990)的雏形。回头浪子被江湖追杀,影片前段只有杀戮而没有缘由,这种观念类似于《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江湖世界总会有一股力量来扑灭异样,这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主题在之后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街头》、杜琪峰的《暗战》《真心英雄》等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传奇化。游达志在1998年执导的《非常突然》则更加直指麦当雄导演的警匪经典作品《省港旗兵》(1984),或说是其一种黑色幽默的版本,影片在同样主线俨然的警匪对峙中,将悍匪改成突然闯入三个由内地来打劫的笨贼。《山狗》中开小卖部的村长谎称村内无电话,做假供误导警察,称阿华是贪玩跌入山猪陷阱,认为他人露营是在污染环境。飞仔们对证人的报复更加呼应了小村庄在空间上的封闭,这是一种默契的道理,同《边缘人》中富翁发家后仍住在屋村一样,因为屋村又是一个江湖的空间,邻居之间自然有一套替天行道的义气法则,所以当警察最后把大门锁死,如同关闭的江湖,只有规矩没有法律,最后阿潮在锁死的铁门前被暴民乱棍打死,死于自己的善念,也是死于他人的正义。
在新浪潮的邪典試验后,低成本的思路与视听刺激的可行使得邪典电影接踵而来,进一步说,新浪潮时期对恐怖元素的点缀运用,也使得后来者有了一个高质量的模板。后来《羔羊医生》(1992)将奇案进行电影化的声张,出租车司机化身奸杀女乘客的雨夜屠夫并藏尸家中的病态犯罪变成港产cult片经典桥段之一,乃至引发一众“人肉”系列,故事中的剑走偏锋与生存困境突破了邵氏70年代已经批量生产的奇案构思。
《第一类危险》类似《无因的反叛》,社会背景也几乎同迹。该片在犯罪事件之间的承接铺排已经十分具有《英雄本色》时的格局,时代背景自然是省力的因素,使它不需要特别强调政治颜色也能够在情节顺承之间体现出复杂的社会层次,但是导演仍然以一种非常自由的手法,既没有特别强调这种特殊,使得犯罪的关注点全都在本性与外界关系;也没有过于抑制这种阐述,让政治矛盾变成一种推动事件发展的元素,而不是一种基调。整部影片对于死亡的处理是,弱化动机,以及弱化生死的重要性,这种呈现更接近于一种犯罪的情绪。相比而言,后来的《香港制造》(1997)则显得更用力,虽然该片将人物的自我边缘化详尽展开,处处细节通融,比如中秋关于阿屏的恐怖春梦中坠楼后的白色血液,既是暗喻精液,也是通过将性与同情、沮丧与信念的类比,应和影片如何表现青年的希望变成绝望、敬畏变成杀戮的主题。然而,在“营造”感上,《第一类危险》中四位青年互相轻视,只是受罪名牵制的同行人;从一路合伙与僵持至结尾处众人逃亡墓地,同样是空间氛围的运营,相比于《香港制造》中青年借墓地来眺望风景,前者在行为上增加了合理性并强化了象征感,在单一的抒情作用上增加了诉说意义。
另一种可以从《山狗》中的双向犯罪说起,仇杀过程支撑了影片后段叙事,阿玲父亲选择的报仇手法是以自己木匠身份制造丛林陷阱,招式之间也有冷兵器时代的精致,受创后的拼死搏斗也更近乎武侠世界的质感,它的流畅度更甚于后来的《杀死比尔》,并且更加落实了人的能力。玲父在第二轮仇杀中便受重伤,在与悍匪老大对决中已近脱力,在拼死一击中,老大的死被处理成肥佬想救水中挣扎的表哥却误将抛出的救生绳捆在表哥的脖子上,从而使其被拖上岸时生生勒死,而此时虚脱的玲父也无力处决实则无辜的肥佬,只能黯然离去,暗合了港片惯有的“天道”意念。而作为港产cult片经典,当蛇佬为了照顾蛇而独自离去,见床有异动便疯狂挥刀,掀开床帐才知是蛇盘踞在他床上,而他仍然发狂地一刀刀将蛇斩得血肉横飞,直至切断蛇头。这个段落整体营造出近乎梦境的玄虚元素色彩:一窝窝盘踞在屋顶、灯架以及水缸里的蛇,蛇佬向水缸反击时却只是疯狂扯出一条条蛇。而收尾的处理势必能得到cult片爱好者的认可:他的尸体被倒吊在阁楼,晃动时同步切换到撞钟声,整体形状类似钟楼,暗合一种宗教式的忏悔,同伙扯开他的裤裆,却从里掉落出一窝蛇尸。影片视听营造出一种报复的快感,同时也讲述了更深一层的罪恶观。同样,当被强暴的少女阿玲精神失常后,在精神病院用马桶水刷牙,用力刷出满口鲜血,透露出精神失常后潜意识仍有关于侵犯与肮脏的创伤,血和暴力的视觉刺激被用来讲述内化的毁灭。
结 语
在网络围观与直播不断迭起的当下,更加高效与饱和的故事也更能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故而犯罪悬疑以及新闻改编题材重新成为了一种捷径,却也多暴露出拘泥于“罪”的弊端。回顾香港新浪朝时期的犯罪片,即使是罪感不强的故事也会使观众产生反省与后怕,因为它们通过了电影语言的审视。科技的精进为视觉刺激不断提速,而如何在高速中维持故事所需要的节奏,也许能从香港新浪潮影片中得到启发。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