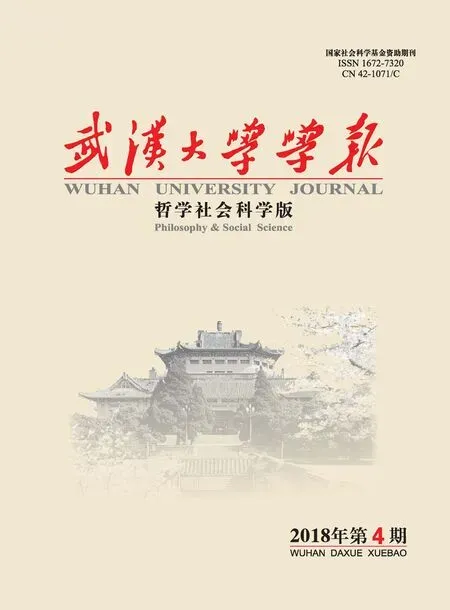硬实力的软约束与软实力的硬支撑
——国际法功能重思
何志鹏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一长期困扰着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者的问题,有必要在深刻考察国际社会实践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上予以分析。从理论的维度上,国际法的功能不仅联结着国际法的性质(本体)与价值,而且还必然牵涉国际法运行的多个方面,因而是国际法体系与进程的核心领域。
对于国际法功能问题的研讨,在提供私人跨国交往的出入境资格审查、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和信息传递的基础环境方面,被广泛认可,且探讨已多。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者则更多地从国际法是否能够为国际争端提供司法解决[1](P5-17),进而是否在国内法律体系、国际关系中有意义(relevant)[2](P2515),具有约束力(binding),或者是否为国家所遵循(compliance)、在何种意义上遵循[3](P1823)的方面予以分析。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出现了弥合彼此之间鸿沟的趋势[4](P28-35),切实认识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5](Pxi)。例如,古兹曼谨慎地考量了对国际法规范的遵从[3](P1823-1887),马库斯·伯格斯塔勒分析了国际法作用的社会动力学原因[6](P38)。有中国学者沿用法理学对于法律作用的阐释,例如万霞认为,国际法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体现各国的协调意志来为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交往中的需要服务,同时认为国际法的规范作用体现在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个方面[7](P75-79);杨泽伟认为,国际法的作用包括约束国际行为主体、促进国际文明、调整国际关系、缓和安全困境和紧张局势等四个方面[8](P9-16);刘志云认为,国际法的作用包括服务、制约、规范、惩罚、示范、惯性等[9](P65-72)。还有学者指出,现代国际法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废止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例如,江海云认为,应对国际法规范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现实和理性的认识[10](P45-49);科斯肯涅米认为,国际法必然会涉及政治诉求[11](P19);扬·安·沃斯认为,国际法重在要求行为体通过实践理性构建、重构国际社会[12](P5);大沼保昭则认为,除了国际法的约束性,还应当考虑确立行为规范,建立国际组织,确认国家行为正当性,提供国际交流工具,提供全球社会的法律动力,作为国家边界、国际、全球等概念的基础,等等[13](P195-199)。但是,大沼保昭的研究还不足以对人们所批评的国际法的软弱性、不公正性等方面加以解释[14](P105-139)。
总之,既有研究并未有意识地区分现实与理想,这不利于对国际法的位置和功能进行有效的评价,更无法对国际法未来的改进方向与路径进行有益的估量。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视角[15](P113-128),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观察与分析方式[16](P148-163),勾勒出研讨国际法作用的框架。
二、国际法功能的现实境况:硬实力的软约束
从理想的角度看,国际法应当承载政治格局的规范化设定、政治选择的规范化指引、政治行为的规范化约束、政治纷争的规范化解决等使命。不过,关于国际法是否真的实现了这一目标,人们的认知存在很大不同。有人较为乐观地认为,国际法积极发挥了这些功能[17](P46-49);而批评者则指出,国际法的功能远不像一些国际法学者想象的那么显著[18](P211)。真相可能恰恰在二者之间。带有美好理想意味的国际法在这个因领土和主权而割裂的现实国际关系语境中,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它对于前述理想中的指引、协调、评价、预测期待功能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同时又都有变形,在很多时候受到诸多局限,因而转化为对现状的宣示和确认。其主要差距就在于法律规范的政治化:规则运作过程中多受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大国强权在软弱的法律面前耀武扬威,而国际法却无能为力,沦为政治语境中的“橡皮泥”。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研究领域,国际法的理想功能都产生了一些变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范的确立进程存在政治化倾斜
从总体格局的层面看,国际法是促进政治安排固定化的模式。国际立法确有可能固化政治上的安排––“政治考量,虽然与规范不同,是我们所称的国际法的决策程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所谓法律外的情况的评估是法律过程的一部分,正如参考过去裁决和现在规范的集合一样。拒绝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并不能使法律中立化,因为即使是拒绝也并非没有政治与社会后果。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基本联系是无法避免的”[19](P85)。
但问题在于,在划定国际格局的进程中,大国利益总是被优先考虑和表达,因而呈现出大国政治的倾斜。国际法没有能力体现所有国际行为体的立场和期待,而是采取了强者主导的模式。也就是说,在国际体系中更有实力的行为体(往往是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更有优势的大国)通过谈判的日程确立、程序确立获得更多的决定权和影响力。以此为前提,通过谈判草案和谈判策略的确立,大国即可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优越的地位,而弱小的行为体则可能被客体化和边缘化。反之,如果是大国不予支持的结构格局,则无论在道义上如何正当,有多高的公众支持率,也很难成为有效力的国际法律秩序,因而只能驻足于宣示状态①例如,联合国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的讨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通过的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以及WTO的多哈回合,都属于初衷很美好、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的机制。。事实上,取得优势地位的一方总是更愿意通过明确的规范将已经取得或期待取得的利益固定下来,以形成清晰的预期;失势的一方也不希望出现毫无规则的状态,因为那样很可能意味着赢家通吃,输家的损失无限扩大。故而,国家之间对于确立规则以明晰、载定并确立其地位、权利及义务就形成了共识,即通过国际立法的方式固化新形成的国际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秩序是政治秩序的固化,是双方为了避免混乱而形成的一个共同的理性选择[18](P64,209)。
(二)法律规则的具体内涵具有政治模糊性
从具体内容的层面看,国际法呈现了行为方式判定上的严重模糊性。而这种模糊就可能被政治力量和利益所左右,进而变成政治的代言者甚至奴仆。尽管所有的法律都具有不确定的特征[20](P147-149),但国际法在这方面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国际法确立合法性,预测行为结果,指引行为方式,配置资源、权力、权利与义务,形成组织格局,其所确立的制度框架不仅为国家树立尺度,而且对公司和个人均有影响。当然,在形成权利义务方面,很多愿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
理想状态下国际法维护的是以公正界定的利益,现实状况中的国际法更多实现的是权力所界定的利益,国际法在两种状态下均无法使任何主体在任何情况下获得利益。历史与现实无数次地表明,强权者或许认为国际法确认并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但对为数众多的弱小国家而言,却绝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在霸权状态下,利益是以大国的意志为导向的,就如殖民国家的利益会在殖民时代被国际法所充分体现一样––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角逐成了国际法认可和固化的主题,小国的利益也就难免被边缘化;在后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的理论成为国际共同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国际法则主要从推进和促进自由市场、民主人权等角度支持了西方大国的利益。
正是因为国际法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主导权力的多元性,形成和加剧了国际法条块切割、分层堆叠的不成体系状态。所以,在很多时候,人们都不能清晰地找到正确与错误、鼓励与遏制、支持与反对的尺度,以至于难以很好地达到公平、正义、可预期的目标,这不仅导致大多数人认为国际法是弱法(weak law)[21](P12)、是不正义的规范,或者认为国际法体系仅限于在有机可乘、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被利用,而且形成了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国际社会顽疾。
(三)法律规范的施行过程难以约束硬实力
依据理想状态假设,国家应秉承诚实信用的理念而遵从国际法,使规范得以妥善地实施。但事实上,传统国际法长期缺乏有效的责任措施,这种缺憾至今也未能完全弥补完善。
总体来看,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实施与监督的方式相对软弱。“由于国际组织的软弱无能和实施国际法的困难,许多观察家误以为国际机制无足轻重,他们有时甚至无视国际法机制的存在。”[22](P16-17)例如,大多数试图发挥作用的国际法都会通过国际组织的运作而约束以国家为主的行为体,这些国际法采取报告的方式,要求成员向组织机构定期提交人权、贸易方面的情况说明,并由专家、其他成员、非政府组织对报告予以审议,敦促改进。有些人权条约还引入了调查机制,即在一定条件下,国际机制可以委派专员对某国家或地区的人权情势做出调查,并提出建议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一些国际人权条约确立了国际调查机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机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派专门人员对某一地区的人权情势进行调查,并做出报告。。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区域性或者专门性组织会议针对一些情势而做出的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决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评价的作用,这种评价主要提供了一种国际舆论导向,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某一行为体、某种行为方式的态度。不过,舆论既可能对强硬的国家无可奈何,也有可能被强大的国家所误导,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较为软弱的施行手段。而针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的反馈方式有国家的报复、反报、封锁(reprisal,retorsion,blockage)等,鉴于主权国家地位平等,国家之间不存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只有一种“主体间性”的作用力,所以这些机制都比较薄弱,责罚方式不一定总是见效[23](P43-52)。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际执法不完善是普遍现象,很难界定国家是否有效施行国际法的规定。
在此种境况下导致的后果就是国际法实施的不对称性(asymmetry)。美国等西方国家2011年针对利比亚政府军的武装打击,表面上有着堂而皇之的国际法根据,但反对者也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无可奈何的是,美国等诸多北约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相较之下,利比亚政府如巨石之下的危卵。国际法能否提供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至今仍是一个极为存疑的问题[23](P43-52)。2012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在联合国各个机构中主张对叙利亚政府进行打击,其理由包括制止人道灾难、反对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等等。这些主张表面上都有可靠的国际法理由,但这些主张的依据都没有经过核实,有动机不纯之嫌。如果不是中俄等国据理力争,安理会早就通过了打击叙利亚的决议。因而,作为体系和过程的国际法往往更直接、更显著地反映出国际政治格局的状况,体现着国际权力斗争的格局。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才有研究指出:在辅助那些不够成功的政府重建国家的过程中,国际法必须把握自身的界限––既提升一国国内的治理水平,也避免国际强权的侵入。因此,既不能一味主张不容许外国批评、国际体制干预,也不能允许国际体制随意干涉,让国际法变成强权的工具[24](P97-100)。
二战之后美国在越南等地发动的战争,都显示出国际法的脆弱性。一般而言,安理会的决议被各国及国际组织所遵守,欧洲联盟的规范对成员国有优先适用和直接适用的效力。这些运行有效的机制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认同,究其背后,都有着政治权力的保障。从北约滥用安理会的授权攻打利比亚政府军并颠覆利比亚的合法政府这一事件中,不难理解大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法提供的支持。虽然国际法在总体上被遵守,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法上的权利主要靠国家自助而得以维护。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常可能是出于恐惧、计算或者信念去遵守国际法,并分别采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予以证明[25](P52-58)。同样,国家遵守国际法的程度总是基于成本收益的对比而做出选择,影响其遵从策略的核心变量是外在的权力压力和内在的利益动力。因而,国家在利益很小、代价很大的时候,就不太容易遵守国际法的立场[26](P469)。
(四)法律适用的审判过程体现出选择特质
司法审判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人们预期国际法具有定纷止争的职能,但现实中的司法体制却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稳定、中立、权威。虽然所有国家试图用国际法来维护利益,但由于很多国际规范体系都是没有监督机制和司法机制的,因而国际法的司法职能并不强。也就是说,除了 WTO一揽子规定的DSB(争端解决机构)还算得上被积极应用,欧洲联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CJEU)、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ECHR)这样的区域司法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他很多领域都没有确立良好的争端解决方式。而且,就这些已经形成司法体制的国际法板块而言,适用国际法也仍然未能完全严守“规则导向”的法治原则,而是经常会出现“权力导向”的政治化痕迹。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存在着价值选择,所以国际法更有可能变成政治中的规则。进而,国际司法裁决是否能够被执行是更具实践性的困难,其中的关键是相关行为体的自觉。如果被裁决承担某些义务和责任的国家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外国可能采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措施对这种国家予以约束,则这些国家无奈之下会履行义务;类似地,如果国家认为执行某些裁决可能带来长远的利益,则它们也会考虑执行,否则,可能会怠于执行。国际法规则受到责任机制的影响,在被违背的状况下,其所能给强大的行为体带来的代价很小,这就使得大国恣意地违背规则。
在一个相对成熟的法治体系中,应当呈现出规范化的政治,即政治的运行应当在法律规则所设定的环境之中(规则中的政治),政治决策与政治过程应当更多考虑规则的因素(政治中的规则)。而在一个法制不够完善的体制里,则经常呈现出政治化的规范,法律经常处于政治干预的生态环境之中(政治中的规则),法律规则的创设、运行进程不得不高度重视政治的因素(规则中的政治)。国际法作用的核心缺陷就在于规则中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语境中的规则,其中存在的诸多差异,表面上可以说是因为国际法的初级法特殊性质,但从深层来看,则是由于国际法的实现受政治因素,特别是大国权力所左右,呈现出政治化的规则。
人们期待国际法能公正、均衡、稳定、严格地实施,固化政治过程的结果,指引政治行为的模式,评价政治措施的正误,预测政治战术的得失,然而现实中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由于缺少惩治机制而导致的国际法说服无效、预测不准、劝导乏力、宣示空泛等状况。法律规范从确立、遵守、监督执行到判定的过程中都有明显的权力政治痕迹,政治权力和利益追求为法律运行提供了动力,显示出极强的不对称性。
三、国际法功能的文化呈现:软实力的硬支撑
国际法在规划和配置国家硬实力方面的作用固然受到了诸多限制,但其在国际观念等文化领域却备受重视。当国际法在制度层面上经常被边缘化时,人们责备的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那些不认可、不遵守国际法的行为体。由此,国际法具有文化的内涵[27](P48-51),它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话语,代表着国际社会的交流方式,象征着国家的外交形象和文化实力。
(一)国际社会的横向结构决定了国际法硬实力的局限
国际法的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强烈的反差并呈现出文化转向,需要从历史与社会的解释视角来予以说明。以社会视角论之,真正能够解释国际法作用具体表现的是国际关系①国际法功能的特色与局限,是由国际法的性质决定的。例如,我们可以说,国际法是平位法、协定法、弱法,因而无法像国内法那样更加严格有效地发挥作用。但这种解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深层原因。国际法的性质是由国际关系的结构决定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结构特征同样也决定了国际法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法的性质与国际法的功能同属由国际关系的格局状态所导致的结果。彼此之间虽然具有相关性,但并非决定关系,二者同受国际关系之决定,而非相互决定。功能可以用来说明(illustrate)性质,性质是将包括功能在内的国际法诸共性与个性的提炼、概括、总结和升华。因此,不太适于将其中的一项用来解释另一项。。理解国际法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首先必须了解国际法所处的外在体系。国际政治的格局为国际法的存在设定了一个宏观的环境,国际法无法超越这个环境。以历史视角论之,当国际政治处在殖民体系之中时,国际法就是殖民者之间力图平等相待,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确立剥削与压迫关系的差异化规则体制;在以战争为解决纷争主要方式的时代,国际法就是确立合法战争与非法战争界限,并形成战后胜利者主导秩序的规则体制。由此不难理解,在当今这个经济利益深度相互依赖、政治格局高度动荡的时期,国际法一方面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竭力维护着大国的利益,在大国与小国、主权与人权、自由与平等诸多主张和价值之间摇摆不定。
这证明国际法在实施上受制于军事、政治与经济权力。国际法在现实中能否定分止争,能否有效地预测和指引,均属未定。以作用而论,国际法所未为,并非因其保守,而是因其能力不足。从渊源的角度,国际法更多是特别法,而非普通法。而在社会中,只有普遍的规则,其指引、评价、预测的作用才更明显。国际法在时代的局限性之中力求形成一种相对稳定而可预期的秩序。国际法所处的这个环境,用“无政府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是非常恰当的。有无政府的前提下,不能指望国际法拥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一个社会的境况里,也不可能完全听任强权的摆布,视规范为无物。基于这样的环境,国际法不是像国内法那样处于国内有政府社会的纵向格局之中。没有世界政府,就不能强制国家去做什么,不做什么。早在1928年,布莱尔利就提出,既不能否定国际法的意义,认为仅有武力打击才是有效的制裁,也不能认为国际法已经强大到可以禁止战争[28](Pv)。国际法体现出了法律与政治之间的互动(interplay),法律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推动作用[29](P118-123)。如前所述,国际法的无政府背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其不可能具备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位阶,因而彰显出不成体系(fragmentation)的特色。而与之相对,国内法则是以议会运作的方式更好地平衡了背后的利益差异,以更加成熟、更加精巧复杂的方式掩盖了利益纷争,从而使国内法的政治性大幅降低,因而国际法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必须更明确其所处的政治语境和其中的政治力量。在国际法的规范中,必须正视其政治运作的因素,必须从整个国际政治的语境中去认识国际法,而不宜将国际法“纯粹化”、独立化[30](P225-249)。
(二)国家意志与利益考量推进了国际法软实力的效果
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是使国际法不能在其约束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同样,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是使国际法在观念和文化领域发挥明显作用的原因。
国际法不可能脱离国际政治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所以必须认识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考量是其存在的第一需求,由此国际法在维护国家硬实力方面的作用势必有限。一些学者和实践家试图论证:国际法能够维护国家利益[31](P48-249)。对于这个论断,需要结合大国政治的国际秩序环境与国际法不对称性的现实予以认真反思。在法治完善的社会中,法律的权威会受到共同体内绝大多数行为体的充分尊重、信任甚至信仰,被视为公允与善良的标志,客观中立的指引体系和被动的裁断尺度,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左右规范适用的影响力比较低。每个行为体的利益都被清晰界定并有效落实、易于救济,法律能够维护合法的权益,却并非贪婪地攫取利益。反之,在法治不够完善的社会中,法律具有高度的权力导向特征,从规范的确立到适用都容易被强者利用,使其获得大量利益。法律这种选择性的适用方式会使得规范的公正性遭到怀疑,其他的行为体则更相信法律可以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由此推之,如果进入了国际法治的形态,国际法可能维护国家的合法利益。而在国际法治尚不完善的状况下,国家利益成为国际法发展的动力与约束。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是具有选择性的。大国确实可以利用其强权创制和维护其利益,它们为了利益而制定国际法,为了利益而推动国际法的变革,为了利益而选择服从或者不服从国际法。国际社会是一个法治形态非常初级的社会,所以很多国家在认识和使用国际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形成良好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正义,而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强大的行为体不仅可能通过选择、解释等方式来利用法律的规范,为自己本来不当的行为寻求正当性;而且会推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确立新的规则;不仅确立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而且将其不欣赏、不喜欢的行为推入非法的行列。在高政治的领域中,更多体现出国家利益的争斗和博弈,国际法施展的能力的空间非常有限,发挥的作用也经常有限。倒是在与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不太相关的经济贸易领域,国际法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比较深。虽然很多时候弱小的国家都需要国际法来避免更大的损害,或者说除了国际法之外别无所依,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国际法可以维护和促进弱小国家的利益,恐怕是不准确的[32](P33-48)。从这个意义上讲,靠国际法来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关于国际法作用的不完全命题,反映的是偏向政治化的、权力主导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际法地位与工具意义。
然而,如果就因为国际法的不对称性而认定国际法可有可无,显然也违背了国家的理性。因为,国际法是主权国家的产物。此时,就有必要借鉴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合作的产物与工具[33](P78-90)。国家基于理性而采取的合作策略确定了国际法的前提,也决定了国际法的作用缺陷。国际法的指引、评价、预测作用必然局限在政治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对比,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方面。“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仅反映了己国的利益,也体现了他国的利益,还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总的来说,国家遵守国际法符合该国的利益,一个有序和稳定的国际社会应当是各国所乐见的国际环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34](P7)法律规范是政治力量与道德信念相结合的产物,而道德力量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长久、更广泛地存续而形成的信条和价值。具体而言,即“生存法则”从自利的起点生存法则出发,培养出利他的观念,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演化出一系列的禁忌。不容否认,有时一些道德理论、原则仅仅在某些假定的前提下有效,一旦遇到真实的问题,就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国无恒强,任何大国在某些情况下都可能会变成弱者。此时,国家为了不可预期的境况,会选择确立、共同认可一些规范,展示它们在某一阶段的协调意志、一定限度的共同利益。国家基于此种考量的行为就促成了国际法作用的文化转向。
(三)话语共识与身份认同保证了国际法软实力的支撑
在国际法约束硬实力作用弱化的同时,其附带效应在国际关系中被主流化。根据前述分析可以论断,由于国家的利益追求,从法律本应发挥的作用上理解,国际法未必能有效地评价国家行为、维护行为体的权利和利益,作为严格的“法律”没有起到充分的效果。国际法对于国家硬实力的影响,与其说是作为法律在实现作用,不如说是政治权力在发挥作用。一系列的案例充分地表明了规则中的政治具有关键意义,科弗海峡案、柏威夏寺案也说明了国际法规则只有有限的功能①在科弗海峡案中,国际法院认定,英国军舰在阿尔巴尼亚所属的科弗海峡遭到损失,阿尔巴尼亚应负责任,并且确定了阿尔巴尼亚的赔偿数额,不过阿尔巴尼亚并没有真的执行这一判决。在柏威夏寺案中,国际法院将该寺的主权判归柬埔寨,但泰国并没有真正为柬埔寨有效占有提供便利,反而设置了障碍,所以柬埔寨请求国际法院解释前一判决。,但是,它又绝非对行为体的利益毫无影响。国际法作为国际交往的“语言”、表达国家利益和立场的“话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现有的国际法研究中,讨论国际法如何认识和维护文化权利、文化财产的很多,但将国际法自身作为一种文化来讨论的还不多。同样的,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分析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在相互交往中的作用与地位者甚多,但将国际法制度和观念作为一种文化来理解的甚少。不过,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对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做出有效的理解:人是社会化的,社会关系构建了人,同样,国际社会的关系构建了国家。个体、机构与规则之间都有着相互构建的关系[35](P3-14)。“一旦我们将对国际政治的讨论放置在某些术语框架内,相关的利益和认同就显而易见了[36](P127)。”如尼可拉斯·奥努夫所分析的,法律并非仅仅像实证法学者所讨论的仅限于命令或者强制。法律规则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自身就具有行动的性质。因此,法律塑造着人们的认同,形成了一种文化圈,沉淀着社会的秩序[37](P66-144)。作为法律的一种,国际法被赋予了庄严、中立、公允、善良、秩序的意象。鉴于人们对法律已经形成了公正与善良的印象,即使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强制实施,仍然被广泛遵守。国际社会广泛相信国际法是正当的,并且具有道德约束力[38](P337-339)。国际法律体制作为社会建构的一部分[39](P6),依然构成了一种社会工程,意味着已经对社会心理进行了深度考量[40](P129),以公平正义的形象植入普通民众的思想[41](P42)。“一旦行为与公正原则之间的差异趋于扩大和明显,那么依赖于这种差异的秩序便会随之削弱或崩溃[42](P26)。”进而言之,尽管政治主导的国际社会结构是国际法作用有限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境况中,国际法还是承载了国家之间的享有共同文化的意义,成为彼此身份认同的符号,因而构成了国家之间交流的语言基础[43](P113)。在此种情况下,很多国家的外交部门、军队,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都会寻求国际法上的根据,以为其采取一定的措施提供支持。国际司法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推进国际法律秩序进化方面的重要意义也被国际公众所认可。例如,国家在规定外交邮袋的尺寸,规定在专属经济区确立的管辖和授权制度,准备边境地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等方面,都试图用法律的术语表述自身的观点,用法律的原则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由此可见,国际法在树立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较为突出。国际法在为实现理想状态下的作用而协调国家行动的时候,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规则不仅是国家之间国际交流、论辩、谈判的基本沟通语言(从提供共同理解的基本术语的角度理解),而且构成了讨论问题的前提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规则框架。正是由于具有这一作用,也是由于国际法具有不成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国际法作用的实现面临着共性的问题:国际法在现实中经常被国家用作追寻自身利益、维护自身立场、辩护行为正当性的修辞,也就是变成了国家话语的工具。强国对国际法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例如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自卫(preemptive self defense)。国际法的强国突破了国际法,却有可能解释为对国际法的发展[44](P35-65)。再例如,当各国认为美国2003年攻打伊拉克违背国际法,美国却认为其行为属于预防性自卫,虽然事后证明自卫的证据完全是虚假的,但讨论各方都在用国际法来说明问题,而不是否认国际法。这说明,在国际法有限的作用中,各国还是将其作为正当性的标尺来维护自身的立场。各行为体都仅仅着眼于对其立场、观念、利益有支持性的规范而予以主张,对于对自己不利的规范则不予理睬或者否定其效力,这造成了国际法实施的选择性,也造成了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状况。
人们通过各国对国际法的态度,对国家的形象和声誉予以评价,使国际法日益成为人们对国家形象进行比较和衡量的重要指标。国际法作为表达立场的话语,所具有的沟通作用不断提升。这种软影响、话语效应是一种次级的作用,但是经过长期反复的累积,有可能反作用于基础架构,改变国家的权力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在国际法面前需要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才能达到制度引领的高度,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
四、发挥国际法功能的全球视野与国家举措
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理解成一个在政治行动中加入规范,使政治安排越来越多地受到制约的过程。从政治化的规范到规范化的政治,国际法的作用不断完善,国际法不断成熟。正由于此,国际法理想作用的提升和完善仰赖于国际法的变革,其核心着力点则是实现规范化的政治,也就是做到政治中的规则因素和规则语境中的政治[45](P36)。减少国际规范建立和运行中的政治因素,增加国际政治格局和交往中的规范考量;降低在政治框架下认识和解决规范问题的几率,提升在规范语境中分析和处理政治问题的空间,是国际关系进步的表现[17](P1)。
(一)在全球视野内促进国际法的功能
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国际法的作用主要是要对国际法所处的环境予以完善。就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言,完善国际环境的供给在于进一步促动国际社会从政治化的规范迈向规范化的政治,使得政治行为被法律所判定,由法律提供行为体立场与行为的评价机制,是国际法作用完善的尺度。国际法作用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国际法律体系的特质,同时也是国际法完善的方向。当我们了解了国际法在现实中的作用,也就能够较容易地找到国际法近期的发展方向。在国际关系中,提升国际法的作用,其核心在于以政治与规范的互动促动政治的再规范化。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个思路,约束国家,尤其是大国的行为。不难发现,在国际法的应然和实然作用之间,存在着鸿沟。从规则中的政治和政治中的规则的角度来探讨国际法的作用,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终结大国政治,改变大国罔顾原则、强权操纵原则的状态,形成国际社会契约,达致法治理想。既然国际法作用的最大弱点是政治语境中的规范和规范进程中的政治因素,那么,如果能够对大国有所约束,能够限制大国对规范的干预和破坏,则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在约束大国强权的手段上,笔者提出了一个经由政治手段来达到法治目标的思路。具体考虑的方式包括三种:
首先,通过大国之间的彼此制约(均势)来限制大国的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注重均势维护国际秩序的必要性。在大国之间彼此制衡之时,大国就不会总是显示出强权,而是会显示出温和的一面。在大国彼此均衡之时,行为体就会通过制定规范和遵循规范来确定行为的可预期性。联合国安理会虽然不是一个完善的形式,但本质上仍然是大国之间相互制约避免恶果的形式。在大国彼此约束的结构中,还有可能是大国联合小国对抗其他的大国;或者大国各自组成集团,相互抗衡。
其次,通过小国之间的团结来对大国构成平衡,从而避免大国的霸权。大国可以制约大国的基础在于权力,小国之间的团结一致也可以形成权力来制约大国。虽然在很多时候,国际法确实是强者用来压制弱者的辞令,但也存在一些例外。在国际法领域备受瞩目的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就说明了小国在适当的机会下也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取得胜利。在WTO中,对于美国的交叉报复也在法律上成为可能。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具有“一极”的分量是最典型的实践;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七十七国集团对摆脱发达大国在经济事务上的约束,确立和实行国际经济新规范,也是典型的实践。
再次,通过大国的自我约束来实现。虽然权力具有扩张和滥用的天然趋势,但也存在大国理智地自我控制、不滥用其权势的可能性。正如中国古代的皇帝可以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大国也不必然野蛮地利用强权。这不仅是由于当今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为所欲为,也是由于经验反复证明,滥用权力压迫小国极容易招致反抗,即使没有强大国家作为对手,即使小国没有团结起来制衡大国,大国权力的滥施也会损耗其自身的实力。因而,明智的大国会以长远利益为基础,在发挥其影响之时,建章立制,形成一个规则之下的秩序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社会将使平衡的模式常态化,从而逐渐以规则来约束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提升国际关系的法治化水平。
国际法作用强化与改善的目标就在于使国际法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环境,如果人们都形成了一种法律至上的观念,崇尚法律,反对大国强权就会被视为是必然,而非天方夜谭。这就是规范化的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不久的将来,希求国际法能够逐渐驯服大国,在规则的确立、实施、权利救济过程中弱化政治的作用,转而越来越多地彰显规则对权力的约束。
第二个思路,提升国际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要充分有效地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就非常有必要通过道德性的完善,程序性的改进,在伦理上建构国际法的公正地位,在技术上提升国际法的形式理性。属于国际法发展完善层面的问题,需要在确立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讨论。不仅针对新领域、新行为体要确立新理念、新规范,即使针对传统领域,也需要明晰理念,确立原则,解决冲突,梳理体系。当前,国际法对于人权与主权、自由与秩序、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等问题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尺度。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方面,但是,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法规范的语境之中,会使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考虑国际法的因素,这能促进国际政治的规范化,这也符合人们对国际社会的期待。因而,延续康德以来的传统,倡导全球公民的法律秩序[46](P25-37),增加规范化和可预期的程度,是一个健康、正义的国际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是不断提升国际关系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构建正义的国际法、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很多突变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社会理想必须与社会现实达成妥协,改革的努力方能有成果。20世纪之初,欧盟因为急于立宪而招致《欧盟宪法条约》失败;WTO因为急于实现公平发展,而导致多哈回合屡受挫折。同样的,人们提出的诸多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目标,国际人权体制完善的目标,都因为与当前国际政治的结构无法契合而未能成功。因此,不能在心态上焦急,在行动上浮躁,而是更应当坚持法治的方向持续变革。
(二)从国家对策维度提升国际法功能
对于国家而言,参与完善国际法固然重要,但同时还有一项关键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任务,即利用现有的国际法作用促进本国发展,建立和发展国际交往的话语体系。当前,对于国际法的存在与运行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学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论。但是,理解国际法对于国际关系行为的交流手段是十分重要的。国际法作为通行的社会知识,指引着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方式、行为预期。通过国际法的语言实现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社会化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现象。
时至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仍以大国为核心。但是,此时的大国,不仅应当拥有硬实力,更应体现软实力,敢于运用、善于运用作为话语的国际法,促进国家立场,建构国际制度,而非局限于实施霸权。“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制约群体凝聚力、辐射力及外部影响的精神资源。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相似的说法,譬如,有组织群体或个体的形象、名声、信誉。”[47](P45)一个仅将自身的立场局限在政治和权力上的国家,其国际声誉必然较低。一个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和阐述利益的国家则会营造良好的形象,造就良好的声誉,并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作为21世纪的大国应当承担起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责任,应当体现出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大国姿态。例如,中国是一个对国际司法机制持高度警惕态度、抵制大多数国际司法机制的国家①中国在签署和批准国际条约之时,对于通过国际法院解决相关国际争端都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体现了对于国际司法的警惕态度。。尽管中国明确地主张对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相关的领土争端不会采取国际司法或者准司法的手段予以解决,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顾国际法的存在;尽管中国在面临钓鱼岛等国际纠纷的处理上,甚至直接反对考虑领土争端中的国际法因素[48](P3-17),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行动中、在政治策略的选择中,无视国际法的因素。国家要在军事打击、政治协商、经济制裁、法律解决之中找到最佳的利益保护手段[49](P151-160)。很多国际法专家在探讨中国的领土边境、海洋争端问题,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建议[50](P45-52)。一些专家建议中国更多地重视和接受司法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51](P142-152),这些建议也确实受到了国家决策者的重视,不过相关的信息还不全面,部分政策建议还有待于商榷。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国际法没有国内法那么成熟,无法像在国内法律环境中那样清楚地预测行为结果,但其存在仍然具有推断国际行为体决策的作用。国际法概念、原则、规范成为国际关系参与者的共同语言(lingua franka)[52](P22)。当参与国际关系的谈判者、行为者都具有国际法的知识与素养,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时,则国际法就会成为这些外交官彼此身份认同的基础,外交行动就会形成一种以国际法为共同知识的社会氛围,国际法自然也就会在外交行动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进而也就成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参照尺度[53](P23-24)。
从国家的视角观察,发挥国际法的作用,还需要立足于提高个人的法律职业水准,深化从业人员的规范素养。在将国家行为分解成个人行为的情况下,更准确地改进国家行为,提升国家形象,其核心在于通过调整交往行为增加国际行为的社会性。国际关系最终是由个人来完成的,国家由其具体的工作人员来代表,进行磋商、谈判,所以所有的国际行为都可以还原成为个人行为。个人在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国家行为,表面上是国家的意识、立场、表达、行动,但归根结底是通过那些具有教育背景、性格、道德观念的个人实现的。
国际法有其欠缺,也有其力量。其功能既不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认知,也远未达到理想主义的愿望。当今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强权大于公理、实力优于美德的世界。并不是没有美德存在,并不是没有公理起作用,但在强权和实力面前,它们仍然显得单薄而脆弱。国际法的功能就是既在分化的国际关系之中构建共同未来,又在世界蓝图的背景下表述国家话语。在国际关系的语境之下,国际法对于国际行为体硬实力的影响比较弱,对于软实力的影响比较强。从对策上看,在全球层面,发挥国际法作用的关键在于推动国际关系从政治化的规范迈向规范化的政治,使得政治行为被法律所判定。由法律提供行为体立场与行为的评价机制,是国际法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国家层面,欲发挥国际法的作用,一方面要促进国际社会的法治化,另一方面要充分理解国际法在衡量国家文明程度和制度实力方面的作用,用法律的话语来表述国家的立场和主张。
就中国而言,以领土、人口、经济体量和政治地位为标志的硬实力已经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但是在软实力方面的提升空间仍然很大,需要更大程度地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对于国际制度的话语权。中国在促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求同存异的国际日程议定模式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21世纪,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新主张,积极参与金砖国家、G20等体系。此时,中国不仅需要在通过国际法构建国际秩序体系的过程中表达自身的理念,拓展自身的影响①学者研讨指出,中国应当在推广和促进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倡导和平、可持续发展。国际法的创制成为各国形成法律共识的平台,国际法的实施成为各国在共同的法律框架内行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保障。在价值层面上,国际社会本位理念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法学研究的新视野,国际正义理念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54](P18-24),更需要在观念上深入理解国际法作为话语方式的重要作用[55](P50-54),在技术上熟练把握这种话语。
[1]Hersch Lauterpacht.The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Richard A.Falk,Burns H.Weston.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Palestinian Right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1991,32(1).
[3]Andrew T.Guzman.A Compliance-base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California Law Review,2002,90(6).
[4]M.Byers.The Role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Andrew Clapham.Briely’s Law of N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6]Markus Burgstaller.Theoriesof Compliancewith International Law.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5.
[7]万霞.论国际法的性质与作用.外交学院学报,2000,(3).
[8] 杨泽伟.国际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9] 刘志云.国际法的“合法性”根源、功能以及制度的互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9).
[10]江海平.现实主义状态下国际法“规范功能”刍议.现代国际关系,2004,(1).
[11]Martti Koskenniemi.From Apology to Utop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2]Jan Anne Vos.The Func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Berlin:Springer,2013.
[13]Onuma Yasuaki.A Trans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on International Law.Recueil des Cours,2009,342.
[14]Onuma Yasuaki.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3,14(1).
[15]王彦志.什么是国际法学的贡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1).
[16]何志鹏,高玥.作为国际法研究方法的批判现实主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3).
[17]Louis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Law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18]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
[19]Rosalyn Higgins.Integrations of Authority and Control//W.Michael Reisman,Burns H.Weston.Toward World Order and Human Dignity.Washington,D.C.:The Free Press,1976.
[20]James Crawford.Chance,Order,Change.The Hague: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2014.
[21]梁西.国际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22]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London:Longman,2012.
[23]罗国强.实在国际法的危机与强行法的作用——从朝鲜进行核试验说起.法学,2007,(2).
[24]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5]Madalina Cocosatu.The Priority of European Law over National Law of EU Member States and the Direct Application of European Law.Administratio,2014,6(2).
[26]Oona A.Hathaway.Between Power and Principl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5,72(2).
[27]Martti Koskenniemi.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8]J.L.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8.
[29]R.A.Mullerson.Ordering Anarchy.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0.
[30]Jörg Kammerhofer.Kelsen-Which Kelsen?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9,22(2).
[31]李英芬.对国家利益的国际法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6).
[32]刘志云.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5).
[33]刘志云.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一种“自下而上”对国际法分析的理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
[34]黄瑶.国际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5]Nicholas Greenwood Onuf.Making Sense,Making Worlds.London:Routledge,2013.
[36]保罗·科维特.国家认同建构中的行为体和结构关系//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尼古拉斯·奥努夫,保罗·科维特.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7]Nicholas Greenwood Onuf.World of Our Making.Columbia,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
[38]Andrew Heywood.Global Politic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1.
[39]Carlo Focarelli.International Law as Social Construc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40]Antony Anghie.Imperialism,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41]Antonio Cassese,J.H.H.Weiler.Changeand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88.
[42]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43]Julie Reeves.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Routledge,2004.
[44]M.Fitzmaurice,C.Redgwell.Environmental Non-compliance Proceduresand International Law.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2000,31.
[45]Martti Koskenniemi.The Politics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Hart Publishing,2011.
[46]H.Patrick Glenn.Cosmopolitan Legal Order//Andrew Halpin,Volker Roeben.Theorising the Global Legal Order.Oxford:Hart Publishing,2009.
[47]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行动与世界体系.庄晨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8]金永明.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国际法分析.当代法学,2013,(5).
[49]徐崇利.软硬实力与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现代法学,2012,(1).
[50]余民才.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国际法分析——兼论解决争端的可能方案.法商研究,2005,(1).
[51]张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司法造法”问题——以“南海仲裁案”为例.当代法学,2017,(5).
[52]Vaughan Lowe.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3]David Armstrong,Theo Farrell,Héléne Lambert.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54]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9).
[55]李英芬.关于话语权的国际法思考.前沿,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