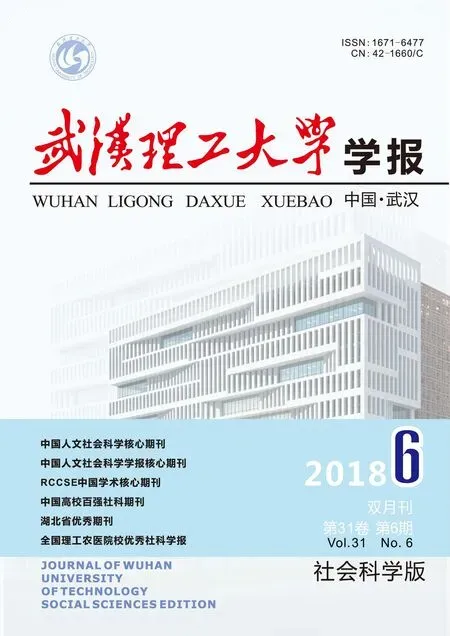“三三制”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关系
王祝福,刘小静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的“三三制”①至今仍为人们所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有着学理的意义,同时更有着一种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三三制”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就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它与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设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互纠缠的地方,需要给予恰当的说明。
一、“三三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
“三三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其实就是作为“三三制”的载体参议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参议会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雏形和重要渊源。虽然它们的形式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有很大的差别,但从本质上讲却是一致的”[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以参议会制为其政权组织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奠定了直接的模型基础”[2]。或说“如果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连续性看,参议会制度是一种中断。从政权性质和政权形式看,它与过去的苏维埃和后来的代表大会制度都不相同。”②“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参议会制度,至少在形式上隶属于国民党政权体系而不属于代表会议制度体系,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在完全可以听凭自己的意志从事政权建设的时候,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选择参议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政权形式,而是在人民代表机关的性质及其基本原则方面与特定历史条件下中断的苏维埃制连接起来,在解放区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取代参议会制度,并逐渐向人民代表大会制过渡”[3]。前者可以称之为“雏形说”,后者可以称之为“中断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确实与苏维埃制度更接近。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4]1953年3月1日,周恩来在招待民革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属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的体系,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5]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机构设置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原则的基本一致。工农苏维埃制的实践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它们共同具有的人民性(阶级性)显然比参议会制明显得多。
即使是持“雏形说”的袁瑞良也承认:“假使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没有由日本侵华战争而引发的民族矛盾的上升和阶级矛盾的缓和,没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也许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必经过参议会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这些历史环节,就直接从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转化而成。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和阶级斗争的方向,从而也打破了这种历史可能性,使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在新政治形势面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参议会制度取而代之。”[6]268这种说法其实倒是对于“中断说”的支持。
袁瑞良著承认,参议会制度中,与苏维埃制(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在内容上毫无联系,完全创新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权机构组成人员上的“三三制”分配原则,共产党员在其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二是选举制度中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原则,以及允许各党派公开竞选的原则[6]270。这两条是根据地所实行的参议会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既区别于苏维埃,更区别于国统区的所谓参政会。这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实践。因为,参议会制度之后,代表机关的产生及其运作对这两条或没有吸收,或大打折扣。就曾经作为民主符号的“三三制”而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政治体系中,是淡化了的。1947年12月,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讲:“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7]这里表达的意思是,统一战线还是要的,要防“左”反右;政权工作中吸收一些党外人士的参与还是必要的,但也只是“个别人物”而已。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曾指示,临时代表大会的“代表总额不可超过四五百人,就中非党员最好能占三分之一,但如事实做不到太勉强也不太好。”而实际情况是,“大会实到代表542人,其中中共党员376人,非党员166人,即非党员代表占实到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弱。”[8]这一时期,毛泽东非常关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提出:
无论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9]。
它表明,三分之一的党外人士的比例,是这一时期总的思路和原则,因为它“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给叶剑英、陈毅、彭德怀等领导人的电报和函件中,或要求“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或要求组成的政权机构中“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③。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与三分之一的民主人士两者所传达的政治内涵是不一样的,是不能都定义为“三三制”的。更何况,在远离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民主人士的三分之一也不是一个常数了。至于普选与竞选,则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而无法把根据地曾经的实践加以全国化。当然,即使是根据地时期,这一点也不是完全的和平衡的。从这两点来说,“中断说”是有道理的。
“雏形说”和“中断说”都喜欢在参议会的组织原则是“议行合一”还是“议行并列”的判定上寻找支持。但“三三制”的实践却表明无论这两种中的哪一种说法对于实际运行中的参议会而言都是不完全的。参议会的建立及其发展确实表现出了议会制的倾向,“与一般民主制度国家相同”[10]。1945年3月,在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议上,议长申伯纯的报告就讲:“三年来驻委会对政府工作,虽然没有故意地起了制约作用,却起了一种或多或少的迟缓作用。”当然,他认为“这是应该提出批评和纠正的”[11]。但根据地的实践还有另外一面,即政府并不只是一个孤立的执行机构。1943年4月25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中所写“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在参议会闭会期间,边区政府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10],并不只是一种思考,而是根据地的工作实际。边区曾多次采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与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形式,作出有关的重大决策,并制定和颁布一些法律等。尤其是在“九一决定”之后,“一元论”打倒“二元论”更是成为思想的主流。李维汉当时的主张就是“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议行并列的参议会制应改为符合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制,只有这样,才能适用于边区,便利于人民”。[10]虽然,这种一元化的实际内容与经典表述也是有偏离的,但“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却是实际表现着的。林伯渠讲,政权实践中,既要保持苏维埃民主制度的长处,又要实现适应于抗战的民主制度。其结果就是“议行合一”与“议行并列”两种思想的长期争论。从机构设置看,呈现出“议行并列”的模样,但从机构的实际运作来看,则还是“议行合一”。1944年12月,谢觉哉提出改参议会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议,表明他已经更多地倾向于民主集中制的“议行合一”。而在这之前,他是“二元论”的支持者。
袁著还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吸收参议会制度中的“三三制”原则,但却注重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组成人员的广泛的代表性,不仅强调政治上的代表性,要求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还强调专业的代表性、性别的代表性、民族的代表性等等,比“三三制”原则的内容更为丰富[6]275。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回避了人民代表大会实践中党政干部代表过多的事实,也忽略了人民代表是按地区组成代表团参加大会,因而代表的利益表达就可能更多地是着眼于地区利益而不是社会群体利益。而这与“三三制”所具有的统一战线色彩,所表现的党与非党的联盟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无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尤其是在今天,当人民代表大会中官员比例超过70%的情况下④,那种“三三制”所表现的自我约束倒是令人追忆和留恋的。
二、“三三制”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关系
对于“三三制”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也有两种。一种也可以称之为“雏形说”。如“共产党的这种自我约束无疑推动了党派合作,并奠定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⑤;“‘三三制’政权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各派共同合作参政的最好形式,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2];“与其它任何政治制度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则是这一制度的雏形,形成了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13]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萌芽形态。它不但包含着‘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我国政党制度所弘扬的团结合作的精神。”[14]另一种则置而不论,可以称之为“非相关说”。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论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时,基本不涉及根据地的“三三制”实践。如:“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应该有一个过程。1948年5月,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多党合作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共同理想基础上开始萌生、酝酿;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多党合作制度初步形成的标志;1956-1957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和明确,是形成过程的结束。这其中,多党合作制度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共同理想向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转变。194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形成这一制度不可缺少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背景。”[15]其中所讲“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并不是指根据地的实践,而是指中共和其它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协调行动。
那么,“三三制”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到底有没有关系?这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出发来加以说明。最简单地说,这种内在的规定性就是一个,即各中间党派新民主主义化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中间党派发生向民主党派的转化。扩展开来说,就是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这种领导地位是面向全国政治的而不再是局限在根据地之内;二是中间党派政治上的转向新民主主义,接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
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充分保障一切抗日的党派的合法权利。毛泽东就讲:“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应该不问他们有否党派关系及属于何种党派。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16]应该说,这个表示是真诚的。但问题是根据地“素无中间党派”⑥一些研究者喜欢列举一些数据,比如某个参议会中有多少个国民党员,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没有材料表明,这些非共产党的其它身份的党派成员有过相应的党派活动。党派只是他们的一个身份而已,他们在“三三制”政权中与其说是某党人士,不如说是党外人士。党外人士也就是非共产党人士。在“三三制”中,他们的活动不具有党派色彩。因此,多党合作也就无从说起。“三三制”体现更多的还是阶级的合作,如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则只能说成是党与非党的联盟。李维汉当时就认为“‘三三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和非党联盟,而是在我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各革命阶级包括中间派在内的抗日联盟。”[10]这其实就是说它的阶级合作的意义大于党和非党联盟的意义。
但是否因此就说“三三制”与多党合作制度毫无关系呢?当然不能。只是不能以上面那样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三三制”的实践,改变了政权中共产党员独占的现象,从而也改变着或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党观念。共产党人因此强调了下面这些观念: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除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7]。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16]760。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6]742。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18]9。
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18]12。
这些思想观念提供了多党合作的可能的观念基础。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中共的自我约束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它让多党合作有了一个可能的生长空间。同时,“三三制”的实践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运作方式,即政治协商。在周恩来看来,“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它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19]这是一种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议会民主的“新民主”。周恩来反复陈述了这种“新民主”的特点。他说:
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20]。
他还讲: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而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体现了新民主的精神。因此,“凡是重大议案不只是在会场上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于此。”[21]这并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根据地实践的总结。“三三制”政权如何运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总结是:“反正一切重要问题全靠、至少主要靠会前会后经过个别协商,以座谈方式决定,提到正式会议上只是取得合法手续而已。这经验在边区的实践中已充分证明。”[22]当然,在1948年以前,协商不仅仅只存在于根据地,也存在于国共之间,共产党与中间势力之间;协商的舞台,在根据地就是“三三制”政权,而在大后方,则主要就是国民参政会。其中,“三三制”的协商比较起国民参政会的协商具有更大的非对称性⑦。可能的观念基础与新的政治运作方式,让共产党人面对不同于根据地的多党并存的局面而充满信心。
注释:
① 本文是从广义的角度使用“三三制”这一概念的。狭义的理解是指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人员分配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相当多的时候,它也被简化理解成“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但“三三制”同时又是“敌后抗战最好的政权形式”(见于《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见于《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这就是广义的理解。
② 见于蔡定剑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他还讲:“它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实践,参议会完全是国民政府的地方议会形式。‘三三制’政权结构与马列的人民专政理论也是两码事。”见该书第15页。
③ 转引自李蓉的《人民民主:毛泽东的理想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④ 参见俞可平主编的《中国政治发展30年(1978-2008)》,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7页。就各级代表的结构现状与我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各方面社会成员来对照比较,人大代表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官多民少、男多女少,中共党员多非党员少。我国的人大代表大多是各类官员的兼职。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中共党员的比例高达70%以上,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中共党员2178名,占代表总数的72.99%。
⑤ 出自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该书还讲:“三三制政权为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见该书第108页。
⑥ 这是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即杨家沟会议上的内部讲话用语。原话是:“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转引自龚育之的《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⑦ 所谓“非对称性”是指共产党在参议会中或者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中都具有相对优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但也有区别。在参议会中,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要面对三分之二的非党人士的绝非无足轻重的政治压力;而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国民党员占总数的44.5%。(见周永林等《论国民参政会》,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17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野党派的比例显著降低,甚至难以达到提出议案所规定的人数。梁漱溟说:“党外在野人士转见减少,尤其敢言之士多遭排斥”。(参见闻黎明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非对称协商”的观点可参阅储建国的《非对称协商:中国的共和传统》,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六辑:《中国民主的制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