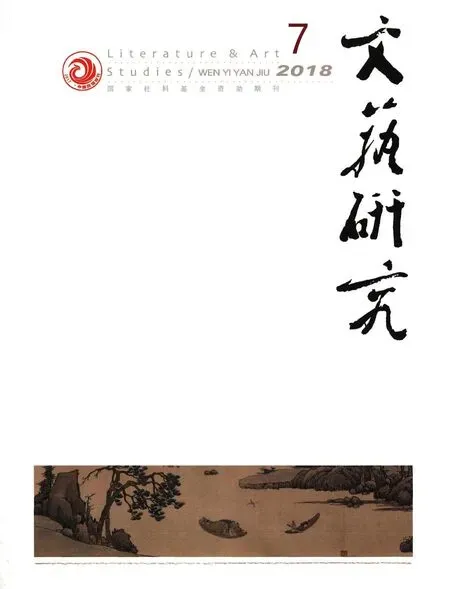戏曲中的“第五堵墙”及其理论意义
刘晓明
在没有“三一律”之类的戏剧理念,甚至没有主、客二元这一认识论的神话(本雅明语)的古代中国①,会发生一种怎样的艺术形式?感觉器官从来都不仅仅是生理的,而且是一种认知器官。其中的差异是,认知器官是由诸种认识论软件改造了的生理器官。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的主客认知理念是如何影响感知官能的,这导致了对存在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观照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从摹仿到表现的艺术形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饶有兴味地发现,在一个非西方国度里,一种与西方戏剧形态迥然不同的中国戏剧如何在一种迥异的土壤里生发出来。
一、戏剧之“墙”所隐藏的戏剧观念
众所周知,在镜框式舞台上,存在着三面实体的“墙”,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墙”。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西方戏剧家突破“墙”的实体性,将舞台上空阔的面向观众的那一面也称为“墙”——“第四堵墙”,即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所存在着的一道“无形的隐墙”。那么,“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墙”?显然,这在戏剧中意味着一种表演体系。这种表演体系建立在模仿、再现的基础上,也即舞台上的表演是现实生活真实性的独立再现。如果戏剧再现的是古希腊生活,那么,舞台上的演出与当下的观众就隔着两千年的时空,这是一堵横亘在表演的存在与当下的存在之间的“墙”,二者之间不存在交流的空间。这种戏剧观念奠基于这一认识论:被模仿的对象乃是独自存在的客体,而主体乃是外在的观看者。这一主、客二元的认知在西方戏剧观念中由来已久,被认为理所当然,一直未受到质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这堵表演与现实之间的“墙”,布莱希特等人称之为“第四堵墙”。
令布莱希特“惊异”的是,“第四堵墙”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并不存在,中国古典戏剧的表演者与观众可以随时交流。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种戏剧表演的“方法”,但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戏剧认识论与本体论。就认识论而言,中国古典戏剧中主、客从未截然二分,表演对象(角色)、表演者(脚色)与观看者是互相介入的。就本体论而言,其潜在的提问就是什么才是“戏剧”。在模仿、再现的戏剧理念中,现实存在与戏剧存在之间所间隔的无形之墙使得二者不可能存在交集。但是,如果转换为另一种戏剧理念:戏剧的存在是被当下表现的,观看者不仅观看表演者所再现的曾在,也观看表演者当下的“表演”本身;与此同时,表演者不仅是表演对象——剧中人,也是表演主体,演员就可以同时出入二者之间。这种戏剧观念不再认为戏剧仅仅是曾在的“再现”,也是曾在的“表现”。也就是说,戏剧本身作为一种存在身兼二任:既再现其表演的事物,也再现“再现”——表演——本身。这是一种“元戏剧”观念。在这种戏剧观念中,主、客的对立消失,再现的存在与当下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也即没有那道“第四堵墙”。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引起了布莱希特的“惊异”。
1936年,布莱希特在观看中国京剧后在其经典的《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中指出:“中国戏曲演员的表演,除了围绕他的三堵墙外,并不存在第四堵墙。”“演员与被表现的形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力求避免将自己的感情变为观众的感情。谁也没有受到他所表演的人物的强迫;坐着的不是观众,却像是亲近的邻居。”②这个发现导致布莱希特著名的戏剧理论——“间离效果”的提出,被后人认为是“关于中国传统戏剧方法的第一次重要阐述”③。
布莱希特虽然观察到中国传统戏剧中不存在第四堵墙,但这道墙是以何种方式破围的,他却未加阐释。中国传统戏剧中第四堵墙的突破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演员还原为脚色,以脚色的身份和观众交流,此时的脚色便脱离了其扮演的剧中人。例如《宦门子弟错立身》第一出中的末不再是剧中人,而仅仅是“末”脚自身:“(末出白)【鹧鸪天】完颜寿马住西京,风流慷慨煞惺惺。因迷散乐王金榜,致使爹爹捍离门。为路岐,恋佳人,金珠使尽没分文。贤每雅静看敷演:《宦门子弟错立身》。”④另一种则是保持剧中人的身份,但却跨越第四堵墙与台下的观众交流。例如中国戏曲脚色上场时所作的自我介绍往往是直接与观众交流的。如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楔子”:“(赵太公上,云)自家是赵太公。城中索钱去来也,不曾索的一文钱,且还我那家中去。兀的一簇人,不知看甚么?我试去看咱。”⑤当然,最典型的是所谓的“做背科”,也即将内心外化,这种外化正是建立在剧中人与观众的直接交流上。“做背科”作为一种传统的戏剧表现方法,从元杂剧到现代京剧,都有大量运用。例如元杂剧《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第一折⑥、元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第一折⑦皆有这种“做背科”。朱有燉杂剧《新编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郑元和云:“小生尽有,便与兄弟。”(做唤六儿科)、(与金银科),(正净谢科),正净背云:“钱,你也下一钩子。”⑧
二、“第五堵墙”及其类型
“第五堵墙”是笔者提出的一种关于中国古典戏剧表演形式的概念。第五堵墙是针对第四堵墙而言的。如果将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的隐墙视为“第四堵墙”的话,那么,在场表演之中的诸种隐墙则可视为第五堵墙。作为实在物,第五堵墙当然并不存在,它不是一道感官的、阻挡着视野的“墙”,而是一种“在场”之中虚拟的“墙”。在中国戏剧的表现中,场上的演员往往对舞台上存在着的某种事物视而不见,造成“现隐”效果,即虽然某种事物在场上显现,却“规定”表演者不能看到;与此相反,不在场的诸事物也可以被视为在场,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正是以第五堵墙为条件的。由此,第五堵墙不仅大大拓展了戏剧表现的空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在场与不在场,更重要的是,第五堵墙具有“能在”也即发生性的意义。
尽管我们在此是针对第四堵墙而提出所谓第五堵墙的,但是,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第五堵墙并不仅仅是一种戏剧的表演方式,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戏剧理论或艺术理论,它所内涵的哲学意蕴具有重要的阐释力。
(一)“在”而“不在”的第五堵墙
“在”而又“不在”的第五堵墙指舞台上的表演者虽然在场却被规定为不在场,也即表演者虽然“下场”却仍然留在舞台上而隐含的一道隐墙。这就是中国古典戏剧表演术语中的所谓“虚下”——表演者在剧情中离开了舞台,却仍然留在场上。这意味着表演者虽然在场,却必须被视为不在场。作为“在”的表演者之在场存在正是通过第五堵墙这一隐墙将其“间离”开来的。这里的“不在场”指的是舞台上对表演者的规定情景——此表演者需要离开舞台,但事实上在舞台呈现中却依然在场,此即“在场的不在场”。
元杂剧《李太白贬夜郎》第四折有一段关于“末”的表演说明:
(虚下)(水府龙王一齐上,坐定了。)(正末唱)【夜行船】画戟门开见醉仙,听龙神细说根源。向人鬼中间,轮回里面,又转生一遍。⑨
这段文字中的“虚下”,指正末虽然下场,但并未真正离开舞台,只是暂时从舞台的注意中心退出,或在后场,或背对观众,并没真正下场。因为从上述剧本中,正末“虚下”后,没有再次上场,接着就重新进行表演了——“正末唱”。“虚下”的主要作用是快速地转换舞台背景,省却了人物上下场的繁琐。在上例中,通过“虚下”,场景从堤岸边快速地转换为龙王水府。
元杂剧《辅成王周公摄政》第一折有如下文字:
(到太庙科,做开金縢看卜兆书科。)(外上,宣了。)(正末做将文册同卜兆书一发放在金縢柜中了。出来科。云:)嗨!不想贪慌,将先天祝册错放在金縢中,待取去,争奈宣唤紧!日后再取也不妨。(虚下)(驾上,云住。)(正末见驾科。)(驾又云。)(正末云:)陛下放心。⑩
上述引文中,通过扮演周公的正末“虚下”,表现了一种舞台空间的转换:正末离开太庙,转到在宫廷见驾。但事实上,正末并未离开舞台,场上也无任何场景变换,却实现了空间的转移。
孙仲章的《河南府张鼎勘头巾》第三折中,正末让张千下场买合酪:
(张千云)我下合酪去。(虚下复上,云)没了合酪也。(正末云)你这厮不中用,既没了合酪,就是馒头烧饼也买几个来可也好那。⑪
在这场戏中,张千通过“虚下”“复上”,在未真正离开舞台的表演中,完成了去另一空间的购买行为。
类似的表演还见于乔吉的《玉箫女两世姻缘》第二折、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第三折等元杂剧中,此外,八千卷楼《元明杂剧》本朱有燉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第三折中有末、贴、外净“虚下”等等的提示,这说明不在场的第五堵墙是当时戏剧普遍采用的表现方法。
有趣的是,在中国戏剧中,“虚下”的不仅有人,而且还有“物”。在曾永义编导、由台湾国光剧团演出的《青白蛇》“水漫金山”一场中,表现“水漫”的是演员,当第一轮波涛渐渐退却时,表演者退至舞台边缘,并未真正下场,此即在场的不在场;当下一轮波涛再一次“水漫”时,表演者则从边缘进入中心,从而表现了水漫的再一次“在场”。
“在”而“不在”并非仅仅只有“虚下”,一切将在场处理为不在场的表演,都隐含着这类第五堵墙。元杂剧张国宾《罗李郎大闹相国寺》演尚书左丞苏文顺奉敕主修相国寺,发现随身携带的银唾盂不见了,怀疑是书童受春所偷,遂将其“吊”起来,正巧受春父亲汤哥路过发现,正待解救,苏文顺认为受春所偷银唾盂被送与其父汤哥收藏,于是将汤哥也“吊”起来。而书童实际上正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外孙,汤哥则是其女婿。这时,汤哥的养父也即苏文顺二十年前赴京赶考时将女儿托付的老友罗李郎经过相国寺,于是,该剧第四折在相国寺中有以下一场戏(这场戏由“俫”扮演书童受春、“正末”扮演罗李郎、“净”扮演汤哥):
(俫云)那来的不是我罗李郎爷爷?待我叫他一声:罗李郎爷爷,你救我咱。(正末云)好奇怪,怎么又有人叫我?(唱)【川拨棹】谁家的小魔军,两三番迤逗人?我这里扭项回身,吃我会抢问。你畅好是不知个高低远近,向前来审问的真。
(俫云)罗李郎爷爷,你救我咱……(正末云)怎么又是一个叫我。(看科)(唱)我则见汤哥儿吊得不沾尘。告哥哥说个缘因,怎生的惹祸根?⑫
在中国古典戏剧表演中,所谓“吊”往往处理为站在桌上,此刻被“吊”者是“在”场的,也就是说,舞台上的演员实际上随时可以看见书童。而按照规定情境,书童被“吊”起来,应该悬在空中,作为在平视的演员是不会立刻注意被“吊”起来的人物,需要将此“在”处理为“不在”,也就是“在”而“不在”。剧中罗李郎多次被受春、汤哥叫唤,此时,罗李郎正表演为只闻声不见人而非常疑惑:“怎么又是一个叫我?”对罗李郎来说,正是第五堵墙导致了“在”而“不在”。
(二)“不在”而“在”的第五堵墙
“不在”而“在”的第五堵墙指的是在舞台中,并不存在之物却被视为存在这一现象所隐含的一堵隐墙。著名花旦表演艺术家小翠花在京剧《坐楼杀惜》中饰演阎惜娇,其中有一段宋江到阎惜娇“家中”见面的表演,但舞台上并没有“家”——作为道具的房屋,表演者正是利用第五堵墙表现出“家”的存在。当时的规定情景是,宋江来到阎惜娇家门外,阎惜娇在“家”内,她入场所走出来的一段路,正好和宋江面对面,由于隔着作为“家”的虚拟的楼板墙壁——第五堵墙,双方必须视而不见。于是,舞台便处理为,宋江斜脸对着阎惜娇,而阎惜娇虽然面对宋江,眼睛却不能直着看。而后,还有一段表现着第五堵墙的存在:阎惜娇下了楼梯,要翻身进门,在翻身进门的时候,两人又一次面对面,但中间还是隔着虚拟的墙壁,仍然需要视而不见。而且,这一次宋江则是正面对着阎惜娇,双方都需要在“可见”之中表现“不可见”。这段双方近在咫尺面对面却不能相互“看见”的表演,难度很大,以至于后来小翠花在回忆录中说,真是非常“别扭,要到阎惜娇进了门,再转身才能相见”⑬。
这段戏典型地体现了“不在”却显现为“在”的方式:表演者以对不在场事物的反应将其显现为在场。这表明,在场者不仅表现为在场的事物,而且表现为在场主体对该事物的反应。但是,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尤其是当二者的表征出现矛盾时,也就是在场物不在而主体对其反应为在场这一现象时,正是第五堵墙成为表演者对不在场事物的反应根据。也就是说,主体对不在场事物的在场反应建立在第五堵墙的基础上。
(三)内心的第五堵墙
内心的第五堵墙指的是在表演者在现场表现角色内心状态时预设的一道隐墙:当角色在舞台诉说自己的内心时,这道隐墙将其自我与场上的其他角色间隔开来,因此,这道墙是在场者相互之间内心状态可表达的前提。具体的表演形态即中国古典戏剧表演术语中的“背云”“背供”“做背科”。
元杂剧《都孔目风雨还牢末》第一折有以下一场戏:由正末扮演东平府负责文案的都孔目李荣祖,在家中为夫人庆贺生日,搽旦扮演的小妾出身青楼,见此十分嫉妒:“(搽旦背云)一般都是夫妻,如何也饮一杯!”这时,正遇梁山泊好汉李逵来李荣祖的家中拜访。此前,李逵因在东平府误伤人命,为了避免暴露身份,谎称李得,因得到都孔目李荣祖的辩护而获救,但李荣祖并不知道前来感谢的李得便是李逵:
(正末云)你不是李得可是谁?(李云)您兄弟是梁山泊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则我便是山儿李逵。
(搽旦背听科,云)哎,原来李孔目结交梁山泊强盗!我听者,看他再说甚么。
(正末背云)哎,原来是梁山泊好汉!我待番悔来,则怕兄弟心中不稳实,到如今也罢。兄弟,我无甚么相送。大嫂,将你那一双金钗与兄弟权为路费。(做与钗科)
(李云)量兄弟有何德能,受哥哥路费,恩义难忘。(正末云)兄弟,拜义如亲,礼轻义重,笑纳为幸。(李云)多谢了哥哥。兄弟无物回答,这一对匾金环与哥哥权为谢礼,(正末云)兄弟,我不要,你自拿去做盘费。
(李背云)哥哥不要,则除是这般。(回云)则今日辞别了哥哥,便索回去也。(拜别科)⑭
这场戏虽短,却有三人的内心独白:搽旦因不满李孔目,通过“背听科”,表露出其试图通过偷听拿住李孔目结交梁山泊强盗的证据。而李孔目通过“背云”显现内心因发现其解救的李得乃梁山泊李逵顿生悔意以及送路费的动机。李逵则通过“背云”表现其辞行时将一双金钗偷偷留在门边的内心感激。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杂剧》第二折:“(做背着云)我待与这厮些钱物,婆婆决是不与。我别有个主意,目下且不与。”⑮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第一折扮演王充的正末与董卓寒暄后,紧接着“做背科”唱:“只怕你这狠心肠无了休。”⑯又如元杂剧《晋文公火烧介子推杂剧》第三折:“净背云了。”⑰此类表演一直沿用至今。
(四)自指性的第五堵墙
自指性的第五堵墙指表演者在现场戳破戏剧作为“扮演”而非真实存在的这道“墙”,也即表演者在演出中直指戏剧“假定性”自身,这就是中国古典戏剧表演术语中的“说破”。如果说第四堵墙彰显了表演与观众之间存在的那堵无形之墙,那么,自指性的第五堵墙则揭橥了戏剧与存在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指向的是戏剧之为戏剧的本体。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所载《张协状元》第十六出由丑扮演“卓”——桌子,但在这一过程中,桌子却不时地返归脚色本身,进行“偷吃”“喝酒”“说话”,甚至应声答话“在卓下”,最后还说破:“告我娘那卓子,人借去了”:
(净)亚公,今日庆暖酒,也不问清,也不问浊,坐须要凳,盘须要卓。(末)这里有甚凳卓?(净)特特唤做庆暖,如何无凳卓!叫小二来,它做卓……(末)甚般敛道!你好似一只卓子。(丑)我是人,教我做卓子。(净)我讨果子与你吃。(末)我讨酒与你吃。(丑)我做。(末)慷慨!(丑)吃酒便讨酒来。(末)可知。(丑)吃肉便讨肉来。(末)可知。(丑)我才叫你,便是我肚饥。(末)我知了,只管吩咐你做卓。(丑吊身)(生)公公,去那里讨卓来了?(丑)是我做。(末)你低声!(安盘在丑背上、净执杯、旦执瓶、丑偷吃、有介)……(丑接唱)做卓度,腰屈又头低。有酒把一盏,与卓子吃。(末白)你低声!(旦唱)【红绣鞋】小二在何处说话?(丑)在卓下。(净)婆婆讨卓来看,甚希姹!(丑起身)(净问)卓那里去了?(丑接唱)告我娘那卓子,人借去了。(末问)借去做甚么?(丑接)做功果,道洁净,使着它。⑱
从丑脚的上述表演中,我们看到,丑脚不断地在其扮演的对象——桌子与脚色自身进行交替转换。正是这种交替转换,自指性地揭示出二者之间存在的那堵墙。显然,这堵墙不是实际存在的墙,而是在脚色与扮演对象之间的一堵墙,也即戏剧存在与真实存在的那堵墙。交替转换的自指,就使得这堵墙在观众的感知中被凸显出来。《张协状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南戏,其产生年代很可能早到南宋。因此,自指性地揭破扮演者与扮演对象之间那堵墙的效果是中国戏剧最早的戏剧性因子,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剧最具标志性的表演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一直保存到现存的京剧中。
京剧《连升店》中店家请出崔老爷,他本是由下场门内的“房间”出来的,说完话后,他应该由原路返回,但崔老爷却走向了上场门,店家指着下场门告诉他:“老爷,您回来,您的屋子在那边哩。”崔老爷回答说:“混蛋,这边也通到那边!”⑲崔老爷的回答就是对第五堵墙的一种自指:在舞台上下场的两侧,可以经由后台相通。在京剧《开茶馆》中,算命先生也即瞎子来到茶馆,有以下对话:“(跑堂吆喝、先生上)先生:‘求财问喜来占算,图财害命。’跑堂:‘你来买卖铺,你哪图财害命?’先生:‘这是哪个小猴崽子,打我这么一下吓?’跑堂:‘我说先生你别骂人,你来在我们铺子里头。’先生:‘你告诉我出科。’”⑳所谓“出科”也即做出进入茶馆的科范,才能进入舞台上没有任何间隔的茶馆内,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第五堵墙的设定。但瞎子看不见,尚未做出进门的科范就入内了。瞎子的“出科”云云即是对第五堵墙的“说破”。京剧《马上缘》演樊梨花因薛丁山老不出面,嘱咐丫环,在城边叫阵。丫环说:“薛丁山吶薛丁山,你要再不出来,我就把城给你撕喽。”㉑“城”居然可以被“撕”,就是说破场上的第五堵墙——画出的城。
三、“墙”的形上之思与第五堵墙的理论意义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阐释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墙”?
表面上看,墙是一种间隔。但在第五堵墙中,这堵墙既不是表演区的空间分割,也不是第四堵墙那样是表演与观众之间的间离,那么,第五堵墙间隔了什么呢?它间隔的是在场与不在场。我们在第五堵墙的四种表征类型中所列举的“在”而“不在”、“不在”而“在”,显然间隔的是在场与不在场;而“内心的第五堵墙”作为在场角色表现内心状态预设的隐墙,使得内在意识的在场成为可能,换言之,这道墙间隔的是内在意识的在场与不在场;至于自指性的第五堵墙通过“说破”这一元戏剧方式,使得“戏剧”本身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得以在场,也就是让观众意识到这是“戏剧”。
但是,我们在第五堵墙中不仅没有看到任何现实存在的“墙”,也没有看到像“第四堵墙”那样固定的表演区与观看区的间隔。尽管我们在上文中列举了第五堵墙的四种表征,但实际上这种表征还可以进一步罗列。也就是说,第五堵墙体现的乃是一种“区分性”,它是发生性的。除了我们上文呈现的在场空间、内在空间、自指空间之外,还可能不断地“生产”出新的空间。因此,正是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区分性,使得第五堵墙超越戏剧成为一种存在论。一切存在者都以差异的方式才能得以存在,而墙作为这种区分性正是存在者成为可能的东西。中国古典戏剧不仅将实体之墙非实体化,而且不像第四堵墙那样固定化,而是不断地“生产”又“破除”,不断创造“区分性”的可能,这就具有解构的意味。
我们知道,德里达在论及“差异”这一概念时,反对将“间隔”等同于“差异”。在德里达看来,虽然差异也意味着一种间隔,但差异并不仅仅是空间的,而是一种在场与不在场存在的区分:“间隔概念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甚至任何其他概念。间隔不能说明差异——不同的事物,这些差异提示了间隔。不过,间隔也限定了它们。但是,间隔这一概念被给予了一种目的论的作用,即期望它成为所有有限空间和不同事物的一个解释原则。自然,间隔要在所有领域里起作用,但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领域中起作用。它的作用每次都不同,表达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㉒在德里达的辞典里,从“差异”演化而来的“延异”被表述为“一种构成的、生产的和本原的起因,表述为可能产生或构成不同事物或差异的裂变和分化过程”㉓。延异的这种生产的可能与第五堵墙的发生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将“墙”的本质理解为第五堵墙的区分性,那么,“墙”便是存在的形而上学,“墙”生产了存在者。汉特克在《谩骂观众》一文中不仅否定传统的“第四堵墙”,而且将一切都作为“剖开”的墙加以否定:
这个空间不会冒充空间。对着你们的敞开的一面不是房子的第四堵墙。世界在这儿不需要剖开。你们在这儿看不到门。你们看不到旧剧中的两道门。你们看不到那个不应被观众看到的人得以溜走的后门。你看不到前门,那位不愿看见那不应被看到的人的人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没有后门。也不是没有像新剧中的那种门。门的缺少不是表现为缺一扇门。这儿没有别的世界。我们不做得仿佛你们不在场似的。㉔
这种看法接过布莱希特等人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否定,由此取消作为被再现的存在与作为再现存在的戏剧的差异,看似很激进,但这样一来,也就取消了戏剧。在此,中国古典戏剧反倒表现出更为前卫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观点。在中国古典戏剧中,虽然没有第四堵墙,但并不完全否定“墙”的存在,甚至创造出各种“墙”。中国古典戏剧只是没有那种实体性的、确定意义的“墙”,但却具有“墙性”——区分性。
那么,第五堵墙作为一种创造性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主要表现在它不是具体的间隔或者区分,而是一种区分的可能,也即能够对任何在场进行区分,也即对在场存在进行生产。它既生产在场,也生产不在场。梅洛—庞蒂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空间想象为充满所有物体的一个苍穹,或把空间抽象地设想为物体共有的一种特性,而是应该把空间构想为连接物体的普遍能力。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使得我们“从被空间化的空间转到能空间化的空间”㉕。在我看来,传统各种“墙”包括第四堵墙仍然属于“被空间化”的范畴,而第五堵墙作为一种区分的可能则属于“能空间化”,这是传统之“墙”与本文所论之“墙”的区别所在。
第五堵墙作为“能空间化”具有不断地空间生产能力。在中国古典戏剧常见的“虚下”中,“在场”的“虚下”经由第五堵墙而生产出“不在场”,“虚下”其实就是在场的不在场。而其之所以可能,就是依靠第五堵墙。“虚下”的在场性使得在场存在不仅是柏格森的时间绵延体,也是空间的漫延体: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存在着一个边界模糊的过渡,它是一种双向沟通,一端连接着在场,一端则抵达不在场。“虚下”作为背景存在对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论进行了解构:它既在场也不在场,于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绝对对立便被消解了。
同样,在“背云”“背供”中,内心的当众表白却能让近在咫尺的对手听而不闻,也是依靠第五堵墙,而“说破”则揭示了戏剧存在与真实存在之间的第五堵墙。事实上,第五堵墙有着更多的区分的可能性,由此,也就生产出更多的戏剧表现的空间。
在前述“不在”而“在”的第五堵墙所引《坐楼杀惜》例子中,宋江隔着不存在的“家”与阎惜娇面对面地遭遇,这个不存在的“家”得以存在,就是依靠第五堵墙的区分性。也就是说,第五堵墙从不在场中生产出了“家”的在场。第五堵墙使得“家”的不在场成为在场,体现了一种在场的缺席性。在哲学上,正是由于这一缺席性的发现,形成了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攻击思潮。但如果将呈现者不加分析地都视为“在场”则是一种简单的看法。第五堵墙告诉我们,“在场”也隐含着“不在场”,而这种“不在场”又恰恰可以是“在场”。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观众正是潜在地接受了第五堵墙这一观念后进入戏剧的。但是,第五堵墙并不仅仅在戏剧中才存在。由第五堵墙所建构的不在场的在场,不仅仅是一种“戏剧”,也同样展示了真实的存在方式。事实上,任何时代的人们,都需要接受某种对在场视而不见的观念,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共同世界。库恩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阐释他的“范式转移”理论的。经典物理学的时代,并不是相对论的事实不存在,而是存在的视而不见——爱因斯坦尚未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一范式的有效性,就是因为对这一范式达成了共识,尽管这一范式遮蔽了某种存在。因此,任何此在的存在都不是完全自我的,而是一种受制于共同世界的自我世界。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具有这种经验的人不是一个认识的主体,一个纯自我,而是具有其事实上的生活经验的历史的自我。把世界和自我连结在一起的东西不只是一种意向性的关系,而是这样的事实:每一自我在其本质中都是向世界而在。”㉖第五堵墙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超越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而揭示了交互主体性是如何建构共同世界的过程。
① 转引自林赛·沃斯特《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②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94页。
③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布莱希特与方法》,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④⑱ 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9页,第86—88页。
⑤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⑥⑨⑩⑮⑰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1—292页,第461页,第648页,第251页,第513页。
⑦⑯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6卷,第563页,第563页。
⑧ 朱有燉:《新编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吴梅辑《奢摩他室曲丛》第2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5页。
⑪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2卷,第543页。
⑫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4卷,第324—325页。
⑬ 小翠花口述《京剧花旦表演艺术》,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53页。
⑭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7卷,第818—819页。
⑲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京剧丛刊》第26集,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⑳ 《开茶馆》,薛晓金主编《京剧传统剧本汇编·续编·丑角戏》,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㉑ 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
㉒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㉓ 德里达:《延异》,张弘摘译,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㉔ 汉特克:《谩骂观众》,宁瑛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35—736页。
㉕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1页。
㉖ 约瑟夫·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陈小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