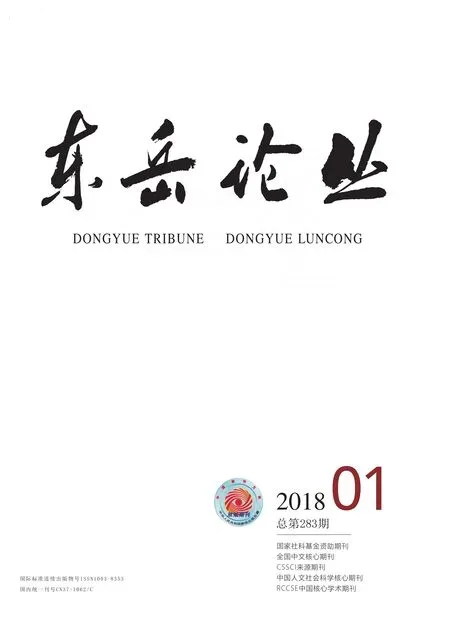自然中的人
——论华人移民文学中的生态意识
丰 云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作为自然之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数度变化,从最初匍匐于自然的威力之下、诚惶诚恐,到自诩为自然的主人、试图改天换地,再到今日开始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处、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一路逶迤,不乏血泪。而作为社会发展记录薄之一的文学书写,也相应地走过了从颂赞自然神灵的神话,到高扬人的主体地位的“人学”,再到现下的“生态文学”的螺旋式轨迹。
“生态文学”肇始于20世纪中叶,以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在1962年的发表为标志。这一概念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内地。当时正是内地工业化急剧推进的时期,各种环境问题开始陆续显现出来,引起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也因此将目光投注于此,自此开启了中国内地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热潮。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众的经济条件普遍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于是对生活质量的关切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开始了现代性设计的模态转换,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具有修正中国现代性工程意义的理论话语。”①雷鸣:《生态文学研究:急需辩白的概念与图谱》,《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各方的共同关切,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推进到了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地带。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注目新世纪以来的华人移民文学,可以发现,有不少华人移民作家将写作的触角探入到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中,通过散文、小说等不同的体裁,呈现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陈河的小说《猹》、李彦的散文《大雁与乌龟》、朱颂瑜的散文《大地之子穿山甲》、陈谦的小说《虎妹孟加拉》、袁劲梅的散文《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黄鹤峰的小说《西雅图酋长的谶语》等都蕴含较强的生态意识。这些作品涉及了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关切、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等主题,展现了新世纪以来华人移民文学具有的超越性视野。
一、动物关切:对物种关系的重新思考
在生物学上,人被定义为一种高级动物。当人类从直立行走开始,从制造工具开始,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之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新的物种间关系。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折射着人类对自身在生态系统中地位的定义的演变。最初人类信奉“万物有灵”,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自然的恩赐。在各种有神论信仰中,人类通常把自身和其他生物都视为神的创造物。而且,人类的纯粹自然的力量在很多时候是逊于大型动物的,这种力量对比的不对等带来的畏惧使得人类对动物抱持了某种敬意。但随着人类拥有的技术性力量日渐增强,人类凭借先进的工具在动物面前具有了极大的力量优势,自信心的增强使人类将自己定位在了凌驾于动物之上的物种,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于是,人类对动物的看取成为高高在上的审视,动物成为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低层级生物,只是在服务于人类的意义上才具有存在价值。人类与动物之间构成不平等的权力关系。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引起了各领域学者的深度忧虑,生态意识、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等观念从生物学、环境科学领域逐步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在文学中如何呈现人与动物的关系,如何想象人与动物的关系,开始成为一种创作潮流。这使得动物关切成为生态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新世纪以来的华人新移民文学中,这种主题也多有表现。
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作家陈河的短篇小说《猹》,是一个人与动物之间爱恨交织的故事。叙述者阮冬是生活在多伦多的华人,妻子为了在家里的后园种菜,自作主张把鱼杂碎埋在花圃里沤肥,结果引来了浣熊觅食。阮冬看到浣熊的样子,联想起了鲁迅在《故乡》中写到的动物“猹”,觉得浣熊就是鲁迅笔下的“猹”。浣熊第一次虽然是偶然到来,但有了开端,“来”就变成了常态。夫妻俩自此被迫展开了与浣熊斗智斗勇的较量,压石头、铺花枝、猛浇水等,都没有彻底奏效。深秋时,浣熊干脆入侵到阮冬家的阁楼上安了家,还生下了三只小浣熊。天花板上悉悉索索的动静、便溺的水渍,令阮家苦不堪言,噩梦不断。春天到来时,他们靠着邻居借给他们的诱捕笼终于捉住了浣熊一家,把它们流放到了百公里之外的大湖边。虽然痛恨浣熊入侵了自己的家园,带来了说不尽的烦恼,但当阮冬在河谷散步时偶然看到了1878年拍摄的棕熊在河里捕食三文鱼的照片后,不能不由衷地发出感慨:“人类才是真正的入侵者,只有野生动物才是土地本来的主人。”*陈河:《女孩与三文鱼》,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页。阮冬由此领悟到人熊之战的根源并非是浣熊的入侵,而在于自己不当的行为方式,只有自己在生活方式上时时检点,避免招引动物,顺其自然,才可以与周围的动物和谐相处。然而,阮冬没想到,三个月后,浣熊一家经过“万里长征”居然又返回了阮冬家,并展开了动物式的报复行动。阮冬家的草地、菜园、鱼池都被浣熊破坏得惨不忍睹。阮冬被折磨得几近崩溃,于是又想起鲁迅的《故乡》,遂模仿少年闰土,用一支木旗杆痛打了浣熊一家。粗暴的行为引来了警察。阮冬被控“残暴对待动物和使用危险武器”的罪名。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动物保护组织赶来他家抗议,社区的邻居张贴海报强烈要求他们搬家。阮冬狼狈不堪,百感交集。在法庭上,阮冬震惊地获知,当天报警的三个电话中,居然有一个就是从自己家打出的。显然,面对阮冬粗暴殴打动物的行为,即使是同样备受困扰的家人也不能接受。阮冬的这一场人熊大战,虽然赶跑了浣熊,却也把自己赶进了困局,在一个关爱动物、注重环境友好的社区中成为难堪的众矢之的。
《猹》的故事情节虽不复杂,却趣味横生,引人深思。自然中的万物,各有自己的存在方式。自然本身,于人类而言,其实无所谓友好与否。因为自然并非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动物的兽性本身也无所谓善恶,动物对人类没有道德义务,动物所遵循的仅仅是自然生存法则而已。动物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客体而存在。如果人类对动物的爱憎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情感投射,或者是一种基于自身需求的价值取舍,那么人类在动物面前就没有任何价值超越性可言。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框架之中,人类真正可以体现自己价值超越性的地方只能是担负起对动物的道德义务。尤其是当动物的生存方式对人类生活本身构成困扰时,是接受这种困扰的合理性并调整自身来解决冲突,还是依仗自身所拥有的力量优势来对动物施加恶意的打击,是检验人类理性的最好时刻。美国“环境伦理学之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人是生态系统最精致的作品”,是具有“最高内在价值的生命”*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这种内在价值并不是体现为改天换地的能力,而恰恰应该体现为在自然面前的理性与谦卑,以及责任的担当。因为人类是万物之中唯一有理性的物种,对自己的理性的善加运用,才是人对造物的尊重,对自身价值的最大发挥。
与《猹》的爱恨交织相比,同样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作家李彦的散文《大雁与乌龟》,则是充满温情的。作者以淡淡的笔触勾勒出在北美的大学校园和居民区中人与雁、人与龟和谐共处的美好图画。作者母子因施救龟卵而结下的人龟之间的深情,令人感慨。结尾处,老乌龟绕园徘徊的一幕,被作者理解为是前来送别即将远行的儿子。乌龟能否报恩和表达情感,在生物学上很难确认,但从古至今的东西方文学都有大量的此类描写。这当然也是一种典型的满足人类自身精神需求的情感投射。但这种出自对动物的真诚关切而生发的情感投射,终究是人类善意的一种表现,也是人类担当对动物的道德义务的一种具体化表达。
瑞士华人移民作家朱颂瑜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常驻日内瓦的代表,多年来围绕环境问题写作了大量知性散文,《大地之子穿山甲》发表于2016年3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穿山甲公子”成为热点新闻后,这篇文章也随之被大量转发,影响甚广。朱颂瑜的散文兼具知识性与抒情性,可以说是思接千载,纵横万里。在这篇散文中,她从穿山甲的生物学特征谈到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从台湾民俗“穿柴屐趱鲮鲤”说到孙思邈对动物入药的反对,从国内穿山甲的濒临灭绝联系到瑞士的敬畏自然,知识含量极大。在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爬梳之中,“森林卫士”穿山甲的“前世今生”跃然纸上。而“人与自然之间榫卯相接的依存关系”则是作者真正要传达的要义。穿山甲的濒危,一方面在于栖息地遭受破坏、食物短缺和农药中毒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养生食材而被人类大量捕捉导致。这正是人类没有担负对动物的道德义务的典型反例。虽然有部分生物学家认为,物种灭绝一直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但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说明当代的物种灭绝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极其密切,许多科学家认为,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就进入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时期。面对当下物种的加速灭绝,人类当如何担负责任?朱颂瑜从中国与瑞士的对比中给出了答案。
陈谦的短篇《虎妹孟加拉》也是关涉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作品,但作者的思索倒不仅仅止于生态,而是从人与动物的关系一直延展到现代社会中人伦亲情的淡漠,人与人之间甚至远不如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和力更大。留学美国的富二代玉叶,虽然家境富有,却从6岁开始就辗转在各式寄宿学校,与父母家人情感疏离。寄宿学校的严苛管教,以及周遭虚伪冷漠的人际关系,使得她的真实情感无处安放,不断退避,或紧张如惊弓之鸟,或退缩如小小蜗牛。情感满足的极度匮乏使玉叶对不知虚伪为何物的动物产生了超乎寻常的热爱。尤其是独行兽老虎,其独来独往的百兽之王的威猛,让自幼独自成长、缺少安全与温情的玉叶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认同。当她在美国“绿洲珍稀动物收容所”遇到被收容的孟加拉小母虎时,毫不犹豫地收养了它,给它起名虎妹。得知虎妹要被安乐死时,她不顾一切地带着它逃离收容所,在暴雪之中送她回归自然。然而,猛兽毕竟是猛兽,虎妹饥饿时发出的狂躁怒吼令玉叶手足无措,陷入万分惊恐之中,不得不电话求助长辈老树。老树出于安全考虑,催促她开枪保护自己。玉叶虽然在仓皇中开了枪,但随即痛悔万分。她感觉自己伤害、背叛了虎妹。于是,又不顾生命危险,独自闯入暴雪中的森林去寻找受伤的虎妹。
玉叶的行为具有较为典型的“斑比综合征”(Bambi syndrome)的特征。斑比是美国迪士尼公司1942年出品的动画片《小鹿斑比》的主角。这部动画片通过小鹿斑比的成长故事,既展示了森林中动物世界的美好与复杂,也呈现了人类对动物世界的侵入所造成的悲惨结果——小鹿斑比的母亲被猎人杀害了。这部动画片播出后,影响深远,并随之产生了“斑比效应”“斑比综合征”等术语。斑比效应指的是受到此动画片影响的人,会极力反对人类杀害一般被公认为“可爱”的动物(比如鹿),但同时却不会反对杀害那些“不可爱”的动物。这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正常、不符合道义的心理现象。斑比综合征在心理学上指的是沉迷于虚假的世界,无力面对现实的世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认为自然是完美的,人类是邪恶的。玉叶与猛虎之间的强烈情感认同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热爱动物、热爱自然,她最后痛哭着去追赶受伤的虎妹时,向一向爱护自己的老树发出了愤怒而犀利的谴责:“人真的太坏了!……说什么动物跟人没有界限,其实你心里就是觉得动物比人贱的。”*陈谦:《虎妹孟加拉》,《北京文学》,2016年第11期。显然,在玉叶的思想意识中,动物的生命价值与人类是等同的,甚至动物比人类更加完美。
当然,玉叶的“斑比综合征”表现,并不是简单地来源于外界的教化或者是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而是由特殊的成长背景形成的。玉叶的成长历程在当下的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许多深陷于名利追逐的所谓“成功人士”都把孩子托付给了各种昂贵的寄宿学校,他们以为付出足够多的金钱,就可以为孩子铺就一条坦荡的成长之路,殊不知亲人陪伴的缺席所导致的情感匮乏是无法在金钱中得到补偿的。饥渴的情感必然寻找其他的替代。玉叶没有如一般的富二代那样以物质上的丰裕来填充精神和情感上的虚乏,而是移情于动物。除了陪伴的缺席,作为女孩,玉叶同时还承受了父母重男轻女观念所带来的精神伤害。在玉叶的生活中,平等和公正亦是匮乏的。双重的匮乏使得玉叶成为父母和周围人眼中的怪胎,她的笑容只展示在动物面前。动物成为她的情感投射目标。现代社会中,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动物是相对弱势的,动物的生与死、存续与灭绝,都取决于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在人类自身的关系中,女性是弱势的,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在男权的笼罩之下勉力挣扎。虎妹孟加拉曾被人遗弃在野外,而玉叶曾在情感上被父母遗弃。相同的弱势地位,是玉叶对虎妹产生强烈情感认同的根由之一。由此,虎妹孟加拉成为医治玉叶情感匮乏的一剂良药,是她“自我认同的另类对象”*何可人:《虎兕出于柙——读陈谦新作〈虎妹孟加拉〉》,《北京文学》,2016年第11期。。收养孟加拉,无疑是玉叶的一次不自觉的自我拯救。然而,从“斑比综合征”的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拯救显然并不是灵丹妙药,只是一种无奈的替代。人与动物之间应该建立何种情感关系才是适度的呢?陈谦并没有给出回答,只是给读者剖开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小小切口。
二、生态危机与生态伦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工业化时代以来,生态危机逐渐发展成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引发了从知识群体到普罗大众的广泛而持续性的生态焦虑。许多思想家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解读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指出:“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这段论述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直指现代性。人类正是在追逐现代性的过程中,从自然的一份子变成了自然的奴役者,自然异化成为人类资源的提供者和废弃物的承载者。而将人类带出蒙昧的科学和理性,也成为人类奴役和掠夺自然的工具。这是现代性的生态悖论,“数世纪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部分成就已经被人类与自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的生态恶化抵消了。”因此,人类必须重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我们必须培养起‘对待生物圈的新的敏感度’,并且‘恢复人类与土壤、动植物生活、太阳以及风等的交流’。”*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现代性的生态悖论,使得生态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期以来成为伦理学、哲学和文学等领域关注的热点,其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是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宇宙中心,以人类的生存利益为终极尺度,不承认自然的独立内在价值,只承认其工具价值,认为人对自然的道德关切最终仍是为了人类本身。而“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颠覆了长期以来被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它要求人们不再仅仅从人的角度认识世界,不再仅仅关注和谋求人类自身的利益,要求人们为了生态整体的利益而不只是人类自身的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王诺:《生态整体主义辩》,《读书》,2004年第2期。
在华人移民文学中,虽然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尚不多见,但已有部分作品涉及生态危机和生态伦理问题,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批判,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思考。
美国华人移民作家袁劲梅的《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就是一篇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痛切谴责的作品。这是一篇怀念父亲的散文,但作者着墨处既不在于梳理家族历史、展现家庭中的人伦温情,也不在于为父亲树碑立传,而是通过父亲作为一个鱼类生物学家,终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却始终未能阻止环境持续恶化的悲凉,对现代性、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痛切谴责。父亲与老谷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带着研究生们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水坝、以亡羊补牢、聊胜于无的无奈方式帮助它们完成洄游的场景,深深刺痛着读者的心灵。
自从西方以船坚炮利令古老中国意识到现代性的魔力后,中国就开始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西方在现代性的道路上狂奔。能源,对于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元素。于是,人类在发展的旗号下,为了向自然索取最大化的能源,不断改天换地,大修水坝就是其中之一。“在属于现代性话语谱系的人类中心论神话中,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主体,需要通过‘使自然人化’来改造、解放、照亮人之外的领域。正是这种改变、塑造、控制万物的冲动消灭着世界的多样性,造成了‘自然之蚀’乃至‘自然之死’”*王晓华:《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于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生态危机在华夏大地以比西方更为触目惊心的方式发生着。水力发电曾经被视为清洁的、可持续的能源获取方式。然而,这种能源利用方案与鱼类的生态需求之间却存在着冲突。于是,人类现代性的发展结果成为鱼类的物种灾难之源。虽然人类从自己的思维出发,自以为是地给鱼儿修造出了洄游的过道,但对只认本能的鱼儿来说,这个过道却是形同虚设的。最终只能靠两个生物学教授和弟子们使用人力来协助鱼类的洄游。这种荒诞的现实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思维弥漫在每一条江河、每一座高山、每一片平原上,使得“带领徒孙一年一年移鱼不止”的愚公教授,到死都在孤军奋战,到死都记挂着长江上洄游的鱼儿。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环境史学创始人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中指出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页。因此,不检点我们的文化系统中对经济发展、对现代性的盲目追求,就不可能真正发现生态危机的源头和最终的解决之道。人类只有“全面检讨现代性的社会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等维度,拒斥理性对世界的完全祛魅,放弃机械自然观、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还原论,走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论”,才能“重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求索诗意栖居的可能。”*雷鸣:《生态文学研究:急需辩白的概念与图谱》,《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作者袁劲梅在文中感慨“父亲到死对长江一步三回头”的深深眷恋与忧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袁劲梅:《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会想起父亲这样的具有科学和人文精神、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地球未来负责的知识分子们。因为正是他们,才真正懂得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框架中,人不仅不应该是万物的尺度,而且应该从万物的尺度上来理解自身,将人类置放在自然中的合适位置,抛弃那种“万物灵长”的傲慢,人与环境才能和谐共生。
生活于美国的华人移民作家黄鹤峰的小说《西雅图酋长的谶语》则是一篇涉及“生态整体主义”以及环境正义的作品。
在生态文学研究领域,《西雅图宣言》(或《西雅图的天空》)是影响非常大的印第安生态文学作品。1854年,美国政府向Suquamish部落的酋长西雅图要求购买他们的土地设立华盛顿州,而让印第安人迁居到划定的保留区。西雅图酋长在愤怒与无奈之中,向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发出了质问。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语言,睿智的生态整体观念,使得这篇宣言广为流传,成为生态文学的重要作品。这篇著名的宣言正是小说《西雅图酋长的谶语》的灵魂所在。小说以两代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为叙事线索,从多个侧面展现了古老的印第安文化,颂赞以印第安人为代表的美洲原住民文化所具有的万物有灵、自然平衡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作者将这篇著名的宣言贯穿全篇,让每一章节都回荡着西雅图酋长的激越情感:
“对我们来说,野兽的生命与人一样宝贵,只是为了生存,我们才猎杀他们。”
“这里每一寸的土地,在我人民心中都是神圣的,每一块平原,每一个幽谷,每一片山坡和森林,都因我族人心爱或悲伤的回忆而成为圣地。”
“生命之网并非由人类编织,他只是网上的一线。凡是他对这网所做的,其结果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他们把大地母亲,天空兄弟,当做可以买卖和劫掠的东西,如羊群、面包、珍珠。但那可以买卖自己母亲、兄弟姐妹的人,终将为保暖而烧掉自己的孩子。”
“湍急的河川,春日里动物们清晰的足迹,池水晶亮的涟漪和色彩绚丽的鸟儿,和我们一样是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那闪亮的松针,温柔的海岸,那山中繁荣空谷和振翅的鸣虫,甚至黑森林里的水汽,在我们的经验中都是神圣的。”*黄鹤峰:《西雅图酋长的谶语》,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45、47、125、148页。
这些动人的诗一般的语句,让读者在故事的字里行间时时都能感受到一百多年前的西雅图酋长的睿智,以及印第安原住民文化中所秉持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从而思考这种观念之于今天的启示。
“原始民族的文明,通常建立在野生动植物基础之上。”*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小说中提到的印第安玛喀部落,生活于奥林匹克半岛,被称为“海角印第安人”,世代以海洋捕捞为生,尤其是捕鲸,部落的标志雷鸟就象征着神把鲸鱼赐给他们。对玛喀人来说,“捕鲸既是获取食物的手段,也是考验人的意志、勇气和智慧的方式。”年青一代的勇敢、自信与传统生活经验的获得都靠风浪之中的搏击来完成。捕鲸手就是部落里的英雄,酋长就是捕鲸队里的首领。捕鲸“在1000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已深刻地融入到部落饮食、祭祀、装饰、雕刻、歌舞等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像植物盛开美丽的鲜花一样。捕鲸,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精彩的一章。”*黄鹤峰:《西雅图酋长的谶语》,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捕鲸,是部落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因此,捕鲸活动之于玛喀部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将近2000年的捕鲸中,他们恪守“顺应天地的律法”,遵循着先人的礼仪,满怀敬畏,以虔诚和感激之心,领取神圣的大海送给他们的礼物,不贪多、不滥捕,一代代自觉地维护着自然的平衡。
然而,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人的商业化捕鲸,导致鲸鱼数量锐减,使得禁止捕鲸在全球成为生态保护的必须。1920年,美国政府作出了禁止印第安人捕鲸的决定。欧洲人疯狂追逐商业利益的滥捕所造成的生态恶果,却由无辜的印第安人首先来承受,使得他们世代传承将近2000年的部落文化濒临消失。禁止捕鲸,改变了玛喀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像没有船的水手,折了翅膀的鹰,精神涣散萎靡,连对春天的企盼都没有了激情。政府的供养,反而使他们日益懒散,部落变得毫无生气。对玛喀人而言,“鲸是部落的魂。”禁止捕鲸成为玛喀部落最大的生存灾难,甚至超过他们当初被迫失去自己的土地。
部落的青年酋长尼尔,热爱部落,热爱自然,他一家祖孙三代为部落重获捕鲸权而努力,希望以此来振兴部落。尼尔并不一味地保守拘泥,而是谨慎地促成部落文化与现代社会运行方式的更好对接。为此,他力排众议选派自己的好朋友卡第斯到华盛顿大学去读书,希望他能学会运用白人的法律和政治手段为部落的生存与发展争取机会,使部落重获生机。肩负重任的卡第斯在校园里结识了人类学系的白人女学生金娜,受到她的很多影响,从生活习惯到文化认知,都有了一定的改变。金娜的叔叔马丁,有一段与印第安少女秀丽特扎的生死恋。这直接影响了金娜对印第安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她一直兴致盎然地通过卡第斯追索印第安人的古老传说和文化传统。在了解到捕鲸对于玛喀部落的文化意义时,金娜积极奔走,帮助卡第斯为玛喀部落争取重新获得合法捕鲸权。在密切的接触中,两个人渐渐互生情愫。然而,卡第斯在部落早已有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西西,他曾在部落的古老图腾柱旁发过相爱到永远的誓言。这使得卡第斯的情感在金娜与西西之间纠结徘徊,如同他在没落的印第安文化和强势的白人文化中间难以简单取舍一样。当玛喀部落重获捕鲸权时,尼尔率领部落的勇士遵循古老的仪式出海捕鲸。卡第斯违背了对尼尔许下的诺言,偷偷带金娜观看捕鲸。在忘情拥吻之时,不知是由于西西的咒语还是违背誓言的惩罚,亦或是为了求得情感困扰的解脱,他们拥抱着飞下了万丈悬崖。
作为小说,《西雅图酋长的谶语》在故事建构、人物塑造、叙事技巧上都偏于简单,但这是华人移民文学中较为少见的突破本身的族裔视角,将关注点投诸居住国的其他少数族裔的命运,以及真正思考生态伦理的作品。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写作,并没有以对自然的绝对赞颂、以呼吁人类彻底放弃对野生动物的杀戮为书写基点。相反,故事的主线是对印第安人捕鲸权的肯定。只是这种肯定不是基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而是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探讨一种更为中正的自然伦理、生态伦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意味着人绝对放弃对动物的猎杀。“生态整体主义并不否定人类的生存权和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害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更不是反人类的生态中心理论。”*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而是关注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存续与发展,关注包括人类的长远利益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维护。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部分动物的捕猎与食用,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与程度之内、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进行,其实是无可厚非的。罗尔斯顿甚至认为,这反而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尊重。
印第安人捕鲸,是生存所需,且千百年来一直谨守“顺应天地的律法”,以满足部落食用所需为限度,并没有肆意杀戮,更没有像商业捕鲸那样以之谋取巨大利益。在捕鲸活动中,他们完全靠自然工具和人本身的力量,不借助于任何机械装置。这种使用自制的狩猎工具所进行的狩猎活动,是最纯粹的狩猎,“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真切地嗅到其间所蕴含的‘拓荒者价值’的气息,观赏到最高水平的有关人与土地关系的戏剧化情节。”*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这也就是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狩猎伦理”的内涵之一。在人与鲸的搏杀中,人与鲸是地位对等的双方,都是自然的儿女。人能够杀死鲸,鲸也会杀死人。尼尔的父亲就是在捕鲸中死去的。人与鲸之间千百年来就是自然地相爱相杀、相共相生。这是生态系统的一种常态。在今天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现状之下,部分激进环保主义者难免恨屋及乌或者矫枉过正,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绝对的自然中心主义,单纯强调对自然维持原貌的重要性,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尺度,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观念与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对于目下生态危机的解决,其实是无所助益的。
另外,《西雅图酋长的谶语》这部作品实际上还涉及到了环境正义的问题。印第安人的捕鲸只是生活方式而已,以他们近乎原始的捕鲸手段对鲸鱼的生存而言本没有大的危害。然而,作为弱势族群,他们却被迫放弃捕鲸文化,无奈地承受了商业捕鲸造成的生态恶果,几十年无法在这个涉及族群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小说中,玛喀部落最后虽然经过艰难的争取重新获得了合法的捕鲸权,但这一权力的获得却不仅仅是玛喀部落自己的努力,还与白人女孩金娜的帮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这意味着,印第安人在这一关系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仍然没有足够的参与度和话语权。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主题开掘,轻轻掠过了。
在上述所分析的华人移民文学作品中,虽然并非都属于典型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品,但在这些作品中都蕴含着很强的生态意识,其中贯穿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对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期许。人类是万物之中唯一具有理性的物种,其制造工具的伟大能力决定了人在自然之中必然具有其他生物难以比拟的力量优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自然、改造自然,这一点是其他物种无法做到的。尤其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的,这种改造对于解决人类温饱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我们已然无法回到前工业化时代,那么这种改造也就无法希冀它彻底停止。这种显著的力量优势,使得人类在自然面前必然具有主体性,这是不能回避的。但也正因为人类是有理性的唯一生物,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力、利益考量的能力,那么反省自身、反省过去,自觉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就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正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所说:“地球生态系统支撑了并仍在支撑着自然和人类的历史,那我们应该如何形成对此生态系统的世界观呢?也许人类最基本的义务,就是对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条伟大的生命长河的义务。”虽然改造自然已经无法避免,但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兼顾生态稳定、自然平衡,却是可行而且是必须的。罗尔斯顿对此提出一个原则:“这种改造应该是对地球生态系统之美丽、完整和稳定的一种补充,而不应该是对它施暴。我们的改造活动得是合理的,是丰富了地球的生态系统;我们得能够证明牺牲某些价值是为了更大的价值。因此,所谓‘对’,并非是维持生态系统的现状,而是保持其美丽、稳定与完整。”*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第30页。这一原则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这种在生态整体主义前提之下,对人类主体性的承认,相对来说更为符合生态保护的现实。
目前活跃的华人移民作家大多生活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生态灾难、环境破坏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相关联的,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以及在应对措施上的多方努力也是相对先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使得部分作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并体现于自己的创作之中,这是华人移民文学在新世纪以来所呈现的一种新面目,说明很多华人移民作家的书写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族裔视角,开始深度切入居住国的重要社会议题,而且在对故国的关注上也超越了普泛的乡愁和怀旧,在继续书写故国回忆的同时,也开始发挥他们作为跨国华人群体的价值,对故国的社会发展路径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这是新世纪以来的华人移民文学所表现出的超越性文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