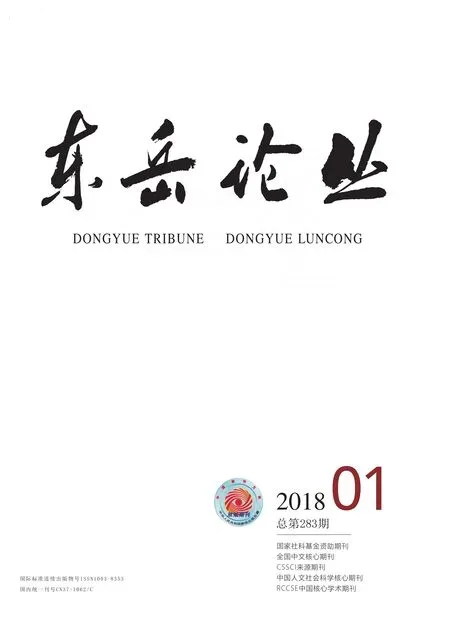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王 成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一、暴露:晚清写实小说的表层叙事景观
“小说”这个术语早在《庄子·外物》篇中就已出现,即指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浅薄言论;可以说,小说肇始之初,它就面临着本体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晚清时期,社会动乱,作为一种更高层面的文学样态的小说,时变其变,世易其易,小说的地位有了根本性转变,其本体论言说已经成为晚清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与传统价值抉择的融合中彰显出独特的魅力,成为晚清文学现场的“弄潮儿”。正如时人所言:“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相颉颃;然就中国而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①姚鹏图:《论白话小说》,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在纷繁与杂多的晚清小说文类②据统计,晚清小说进行文类表示的多达200种以上。中,写实小说无疑数量巨大,且影响深远。当然,我们所说的写实小说是广义上的泛化范畴,其既包括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描写与刻画的小说,如谴责小说、官场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等;又包括那些以“情”反映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写情小说,社会言情小说等;还包括以现实社会进程为基础,进行客观联想与描绘的小说,如政治小说等。在晚清众多小说期刊中,写实小说以其特有的魅力——暴露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追捧和关注:以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分别从政治、道德、风尚、人情等多个维度透视了晚清社会场域中的芸芸众生与黑暗现实,暴露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风雨飘摇的尴尬境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经《新小说》刊发,即引起广泛的关注,从1903年—1905年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其总共108回直到1910年才得以出齐,由上海广智书局以单行本分册发行。该小说所述“虫蛇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之“怪现状”,均可视为社会现实之丑态,而不应简单等同为“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作者似乎有意借“游戏笔墨”暴露世相与世态,在不露身份的前提下,笔锋却渗透出各种尖刻,贬责嘲讽之意溢于言表。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官场小说直面官场黑暗,揭露官僚腐败,形象、生动、直白地勾勒出晚清社会官场一幅幅“百丑图”。《官场现形记》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作者李伯元认为“中国官场魑魅魍魉靡所不有,实为世界一大污点”(载《世界繁华报》1904年6月17日《〈官场现形记〉初二编售书告白》),遂以犀利的笔触将晚清官场黑暗腐朽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正如茂苑惜秋生为其作序所言,“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狼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可以说,这类小说就如同一把刺入官府和朝廷心脏的匕首,让当权者有揪心之痛。当然,晚清官场小说直接暴露的是官场腐败,而间接暴露的却是晚清“新政”的虚伪,以及清政府的极其腐朽而难以为继的历史宿命。以吴趼人的《痛史》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以便利大众阅读为出发点,讲史叙事而不“愚人益愚矣”。《痛史》1902年开始在《新小说》刊载,作者以沉重而深情的笔触叙述了在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这一历史阶段,贾似道、文天祥等大臣的相关事迹与故事。这类历史小说虽然标榜要发明“正史实事”,以期达到为正史先导之目的,却实际上并不在写述历史,“是针对着晚清政治而说……每个讲史的作者,也都反映了他自己的时代。”*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即使这种叙事建立在对社会、现实、官场、朝廷等的暴露基础上的,他们仍试图在历史的回音中苦寻民族国家强盛的药方。科学小说在晚清大量出现,并且体现出晚清小说家于“科学强国”特定时代背景下思维、知识、视野的扩移,体现出一定双重现代性特性。有人类寄希望于科学发达而对自身生存空间拓展的想象,如《月球殖民地小说》;有人类关于未来“美丽新世界”的宏图设想,如《电世界》;也有人类对于科学工具的炫耀和崇尚,如《发明家》;还有人类对于科技发达的未来隐忧,如《新野叟曝言》;也有对科学家的典型塑造和推崇,如黄之盛、黄震球等科学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晚清科学小说不是简单的科学+小说的嫁接,其往往“通过小说来描绘奇特的科学幻想,寄寓深刻的主题思想”(叶永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科学文艺))。晚清科学小说家既有关于西方科学器物的直接描写与展现,也有关于民族国家器物层面落后的客观写实与暴露,还有关于文学小说启蒙、审美现代性的现实诉求与体验,更有关于自身、国家、人类命运的深层次思索与探求。也就是说,就晚清科学小说而言,它是游走在写实与幻想的双重思维中兴盛前行的,并且“所论所述,也深饶历史文化意义”,也是我们“一窥世纪之交,历史及政治思潮嬗变的好材料。”*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页。写情小说在晚清亦大为盛行,吴趼人的《恨海》《劫余灰》等就标榜“写情”,“吴沃尧之所撰著,惟《恨海》、《劫余灰》,及演述译本之《电术奇谈》等三种,自云是写情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他将人之情、物之情予以揭露和展示;尔后,“鸳鸯蝴蝶派”接过其火苗,遂形成一股“写情”的狂焰。晚清写情小说以“情”为内核,但是其立足点还是“言情”与“论礼”,即言男女之情和忠孝慈义,其中亦对社会之情给予暴露,“把时代社会的使命感与道德人伦的理想,寄托在男女言情作品里面”*黄锦珠:《论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质变与发展——以〈泪珠缘〉、〈恨海〉、〈玉梨魂〉为代表》,《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于风花雪月之中见出有关国家、民族、社会、现实等的揭露与预想。此外,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生态,晚清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政治小说,这类小说从“改良群治”和“新民”出发,暴露政体弊端,“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提倡维新爱国”*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尤其倡导“立宪”,进行思想政治启蒙。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多政见、演说,经常“商榷国计”;旅生的《痴人说梦记》以充满激情的笔调于“揭发伏藏”之中亦有关于社会政体和改革的思索;颐琐的《黄绣球》的“自由村”改造思想、现代教育制度、经济改革与女权观念的流露,等等。晚清政治小说家能够正视社会政体弊端,主动为群体、为国民教育代言,并且“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饮冰室合集·专辑》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在一种“明显偏于‘我们’的公共性的话语表达”中,“使小说成为建立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的试验场,给社会进步规划出了基本路向和结构草图”*罗晓静:《“群”与“个人”:晚清政治小说与五四问题小说之比较研究》,《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
总的来说,晚清时期,小说文体虽种类繁多,但居于大类的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当然,与传统的“诗言志”或“不平则鸣”理念相融合,晚清写实小说家在进行社会黑暗揭露与暴露的同时,也于文本内外体现出“情”与“礼”的某种冲突与调合,这与他们自身传统文化本位主义是一致的,即既不满足于社会文化现状,又寄希望于从“传统”中激发和寻找社会文化变革的因子和动力,即使这种努力在一定层面上看是徒劳的。
二、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叙事的深层意蕴
纵观晚清写实小说发展史,由于时代裂变与社会衰败,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选择以官僚体制腐败为突破点,对社会黑暗现象进行彻底暴露,进而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担当”与价值立场。然而,晚清写实小说的这种叙事取向只是表层景象,它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某种批判立场之下,似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为此,我们认为,晚清写实小说创作的繁盛,可能在深层次上指向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集体式”狂欢:既有个人政治抱负的表达,也有个人情欲私欲的宣泄与隐藏;既有个人生存欲望的现实诉求,也有个人内在精神意志的彰显;既有个体的冷落,也有个体的张扬;既有个体的隐痛,也有个体的佯狂;既有个体的自卑,也有个体的羡媚……也就是说,晚清写实小说的狂欢化表征实际上是一种个体意识引导下的市民化狂欢,而这一特性恰恰首先体现在晚清写实小说创作由集体到个人转换的发展路径上。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个体创作,不是表面上的单个人创作,亦不是与集体(群体)创作相对应的概念,而是说晚清写实小说家在创作意识上更多体现出某种超越旧伦理道德,寻求“自尊贵己”新道德的现代主体的萌生与建构。就创作情境而言,晚清写实小说家大多栖居于“热闹非凡”的都市中,从而以一种真实而又极具矛盾张力的笔触尽情描摹都市景观和品评世俗。一方面,他们放浪形骸、狂放不羁,浪迹于世俗的洋场,如李伯元“既而同上酒家楼买醉,醺然挟某入娼门,某不从,伯元固强之,途人见之笑,某大窘,乃托故遁去。而伯元竟黄冠狎妓,其狂放有非斗方名士所得而及也。”*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另一方面,他们也敢于乐于抛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维度,进而直面社会现实,体现出一种更为俗化、平民化、大众化的文化品格。显然,无论是哪一种生存态势,都是晚清写实小说家本真的生存方式,都是他们对于“个人”在场的真实流露。为此,我们看到,晚清写实小说家在具体创作上不再只为传统道德、主流价值马首是瞻,也不过多地追求小说的深度思想旨趣与宏大叙事立场,而是更多地将其作为“个人”感觉的再现、谋生的手段,甚至不惜迎合“浅人社会”,“以合时人嗜好”,进而导致小说文本“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63页。。而这些小说文本所表征的,恰恰彰显出晚清写实小说中所萌发的,却体现为创作主体自身还不显成熟的“个人”观念。也就是说,晚清小说家的创作动机往往更在乎“个人”,即个人的体验、个人的满足、个人的生存、个人的宣泄。晚清写实小说家这种由集体到个人转换的创作路径,显现出晚清文人早于五四文人之于“个人”文学的努力,不仅五四文学(包括小说)是“人的文学”,晚清写实小说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在北平少年学会讲演》,《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即使此阶段的小说中这一“个人”观念的萌生与发展还极不成熟与合理。
晚清写实小说对“个人”的言说更倾向于是一种个体情感的宣泄,且体现出晚清小说家颇为复杂的情感体验。从客观层面来说,晚清小说虽体现为“个人”之于现实社会人生极为不满与无奈,“下至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取乐饮酒,则视为故常”,却直指晚清政体与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若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以其位之高,以其名之贵,以其权之大,以其威之重,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茂苑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序》)从主观层面来看,晚清小说彰显的仍是晚清一代小说家较强的个人意识和情感,即对中国旧有的、传统的、腐朽的事物的憎恶与对西方新奇的、新兴的、进步的事物的惊羡。翻开晚清每一部写实小说,我们都能很清楚地感受到晚清小说家深深的憎恶情感,“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吴趼人:《最近社会龌龊史》自序∥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80年版,195页。总的来说,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晚清写实小说家将笔触直面当下,以至在个人情感层面无所不用其极,进而激扬文字,谩骂讥笑,放诞乖张,肆意想象,大胆宣泄。我们发现,晚清诸多写实小说家常常谈及自己关于“情”的看法,其在具体创作上亦体现出对这一“情”字的现实传达,正所谓“上自碧落之下,下自黄泉之上,无非一个大傀儡场,这牵动傀儡的总线索,便是一个情字。”*吴研人:《劫余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恨海、劫余灰、发财秘诀、情变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不可否认,晚清写实小说家笔下的“情”字仍然遵循着男欢女爱的传统礼俗叙事逻辑,如吴研人《恨海》中伯和、仲蔼、棣华、娟娟的离乱之情,符霖《禽海石》中秦如华和顾韧芬的欢喜悲愁,李涵秋《瑶瑟夫人》中瑶瑟夫人与摩立在英伦的悲欢离合,小白《鸳鸯碑》中桃绯霞与柳云的苦命鸳鸯情,陈蝶仙《泪珠缘》中秦宝珠的恋爱婚姻,佚名《春梦留痕》中闵绶章与秋姑、织成、金风等少妇少女以及举人周象浚与弟妻秋姑之间的风流韵事,以及林纾翻译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等,它们皆没有摆脱旧有“才子佳人”式情爱的藩篱,只不过这种“情”融入了更多的“一己”之思之忧。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晚清写实小说所叙之情,不仅仅是旧式的男女之情,还有关乎现实社会的世情,更有由于其抒情方式的狂诞而传达的“非常之情”。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晚清写实小说家在具体创作上以极为尖刻讥讽的笔墨处处彰显出个体对世道、对政治、对社会、对种族、对民族问题等诸方面的不满与控诉;另一方面,晚清写实小说家也通过对叙事对象的选择宣泄出一种“非常之情”。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中的和尚爱情、徐枕亚《玉梨魂》中的“寡妇恋爱”、李伯元《海天鸿雪记》中的所谓“嫖界指南”等等,在情感宣泄上更是惊世骇俗、特立独行,而这一写作倾向更显现出晚清小说家狂欢化叙事逻辑下的个体言说路径和理路。
晚清写实小说经由群体创作转向个体言说,进而在内质上体现出个体情感的彻底宣泄,这种叙事逻辑在表面上突显出晚清小说创作的繁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启蒙着民众的思维,“以小说之为世俗读物,书名的标新亦足以映现社会通行观念的转移。”*夏晓虹:《小说年代纪的意义》,出自《晚清的魅力》,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晚清写实小说的场域中,这种个体的佯狂、歇底斯里的情感宣泄在狂欢化的表象下更多地体现出个体价值的虚无,即在颠覆突破传统宗法礼教后彰显出个体的无所适从和情愫的无处安放。翻开晚清写实小说具体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其突出的矛盾张力,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然情感激愤暴露以泄其苦痛之情怀,但亦感伤过溢,厌世救世之念交杂相生,使其在新闻谈资娱乐之余,更显作者个体价值之空泛虚无。李伯元的《醒世缘》极力暴露封建迷信之荼毒,可谓“俗耳针砭”之作,但仍然游走在科学观念与宿命论之间,耿家病痛之因果循环亦彰显出作者价值旨归的缺失。曾朴的《孽海花》也是以讽刺之笔“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在一种无意义的叙事模式中游走在价值与无价值之间。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暴露了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糜醉生活与市井恶徒的卑劣行径,但却无核心主流价值之引领,难免被胡适称之为“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胡适:《胡适文存三集》卷六,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62页。此外,晚清的写史小说如《东西汉》《新三国》《东西晋》《两晋演义》等也多效仿古人,牵强附会之处甚多,即常为无稽之言,使“愚人益愚”,实难有思想的深度与价值的建构。
总的来说,晚清写实小说所引导的个体民众狂欢,虽然我们能够从中听到多方的声音;但是,一方面,其彰显出一种挣脱束缚和牵制后的冲动和宣泄;另一方面,在狂欢、共舞之后,谁来捡场、收场?文学、精神的碎片化不仅容易滋生价值虚无,而且又难以承担起民族国家形象的现实建构。可以想象得到,晚清至五四,文学的热闹可能实则是政治的热闹!
三、重构意识形态:晚清写实小说叙事的可能走向
如前所述,晚清写实小说的创作是繁富的,其所呈现的叙事景观也是颇引人关注的,即便晚清写实小说在深层次上不可避免地容易走向狂欢后的价值虚无,其仍旧为后世小说乃至文学创作提供了各种可能发展面向。尤其在意识到既有意识形态破灭后,在各种可能的向度中寻求和重构意识形态,就成为晚清写实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虽然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
作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以及对事物的观念、思想、价值等表征的意识形态,我们将其介入到晚清写实小说的言说,主要是基于其所存在社会场域中的政治维度来展开的,即晚清写实小说在形上层面为晚清社会运作提供了观念源泉,并在一定程度上预设出某种社会秩序的蓝图。写实小说除了言道、缘情之外,在晚清诸多小说家那里,他们以为小说亦可超越伦理道德框架,甚至可在社会现存制度之外而新生事物与社会。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无论在对封建官僚、维新派、帝国主义的社会功效与价值态度上,还是对中外众多城市万象的集中描绘上,尽显新旧过渡时代作者对晚清写实小说创作之于社会秩序的思考,其观念形态都极富批判性与建设性,“他对于这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是不满意的,但他相信这是过渡期的必然。他把这些事无情的揭露出来,希望能为改进的一助。”*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梁启超亦认为小说(主要是写实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及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虽然其小说观念为政治服务的主观目的极为明显,但是仍然体现出梁启超之于晚清写实小说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之维的期望、认同与实践。顾琐的《黄绣球》以“自由村”式的“乌托邦”构造社会蓝图,极言“公德”“宪法”“改良”“教育”“尚武”“合群”“平权”“国民”“独立自治”“自由”等,将各种现代政治话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元素,以期为当下社会转型与变革寻找到可资借用的话语资源,“对新文明世界的强烈向往,推动着近代中国人走出传统去寻找人类文明的‘新大陆’……对于晚清人来说,这种‘新文明’是借鉴于西方而又超出西方的。”*耿传明:《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作为写实小说大类的政治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更是直言“政治”“法律”“演说”“立宪”,全书俨然一幅思想启蒙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面孔;佚名的《宪之魂》、陆士谔的《新中国》、吴趼人的《立宪万岁》等小说皆可作如是观。
除了晚清写实小说文本所透露出的建构意识形态倾向外,小说文本载体——报刊编辑行业也显现出较强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努力,而这本身就成为小说创作和小说编辑出版的重要动力。晚清之际,各种小说期刊、集刊及著述层出不穷,而“国民”“化民”“群治”“教育”“社会”“自由”“民主”等,几乎是所有的发刊辞、序言、评语等必然出现的“关键词”。晚清四大小说期刊《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其宗旨即多为“改良群治”“开启民智”,其他小说期刊亦是如此,而刊载在上面的诸多写实小说毫无疑问力图传播文明利器,启迪国民意识,补助匡救国民社会,有的小说家甚至直言“小说界革命”,使写实小说自身自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起了晚清社会政治转型与变革的推手、中介,以及话语资源,“他们亦采取通过小说理论向小说发号施令的方式,使其担当起政治代言的新工具的重任”*罗晓静:《“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晚清写实小说叙事的可能走向之一就是重构意识形态,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的突显仍然是一种狂欢化表征。也就是说,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换句话说,就意识形态重构方面而言,晚清写实小说在背离传统经学知识范式与意识形态话语维度后,体现出一种多元的、杂义的,甚至是含混模糊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晚清写实小说不再仅仅作为封建正统文人的“言道”“缘情”之作。市井俗人亦创作小说,并且评论议论小说,使晚清写实小说在创作主体与思维向度上更加面向大众,真正走向民间,从而以一种通俗化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引领民众接受,“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复合矣。余又乌知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上海书店,1994版,第556页。另一方面,晚清写实小说意识形态的“民间”立场体现在其话语的多维视角与平民视角。这里既有一般市井俗人嘲笑谩骂社会人生之所作,也有写情泄愤乃至描写两性私生活之所作,亦有晚清大众文人写史爱国讲政治之所作,更有体现民众行乐享受张扬怪诞之所作……可以这么说,晚清写实小说关于意识形态的建构不仅为晚清文学的走向提供了多种价值维度与可能发展路径,而且也展现出了晚清文人早于五四文人之于文学转型,以及文学启蒙与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努力。即使这其中所折射的更多的是政治的问题,思想观念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回避这种文学热闹所呈现的政治的热闹背后,晚清写实小说的这种意识形态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所昭示的晚清文人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现代国家观念的萌生,而这对于文学的宏大叙事,对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是极具意义的。
四、晚清写实小说叙事的价值衡估与历史反思
中国近现代小说叙事的逐渐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酝酿与发展过程,那就是晚清小说尤其是晚清写实小说叙事的生发与多元发展过程。毫无疑问,晚清写实小说并不应该只是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向近现代小说转型的过渡阶段文学样态,也不应仅仅作为一种不成熟的、杂乱的、多义的文学表征。首先,晚清写实小说叙事中关于“西方”想象的话语形态对近现代小说话语生成极具建构意义;其次,晚清写实小说叙事逻辑中所体现的文学地理学视阈对近现代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也颇具先导性;再次,晚清写实小说叙事对民族性的深刻体验和超前传达与近现代小说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建构异曲同工;此外,晚清写实小说叙事的边界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近现代小说叙事特有的矛盾张力与现实抉择。
在叙事过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处处体现出一种中西文化比照的二元思维方式与独特话语形态。晚清写实小说将更多的笔触深入到晚清现实社会场域,在某种复杂的情绪体验中想象“西方”这一他者形象。我们看到晚清写实小说文本里充斥着各种时髦词语,比如痴人说梦、苦社会、活地狱、改良、革命、立宪、共和、民主、自由、文明、欧美、外洋、洋人、鬼子、洋祸、邪教、舍宇洋楼、科学、新民、新中国、未来……这些词语虽然经历了一段以中国化与再地方化为中心的西方形象认识阶段,彰显出晚清小说家情理冲突之中的现实抉择,但其无疑建构起了晚清至五四前后中国小说叙事的一套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小说启蒙/革命话语的话语资源,并且在深层次上体现出国人长期以来关于中西关系的考量和对理想民族国家创建的预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近现代小说价值体系的发展理路,包括个体精神生活理念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既存文化精神中固有的人生向度替国人提供内心自省的机遇,小说文类地位的改善为边缘化的文人找准了心灵之舟的港湾,文化转型的阵痛因为感性的超越与理性的强化,逐步形成晚清民初小说的情理统一趋向,生命本位价值的失落,以及当下社会在情理观念认识中的系列曲解,促使和加速悲剧观念的本土化进程,从而导启‘五四’洞察现实、检讨人生的文学理性向度。”*贺根民:《晚清民初小说情理的把握方式与观念变迁》,《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显然,中国近现代小说关于生命本位的诉说、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关于小说审美的体验,是离不开晚清写实小说叙事话语逻辑之开启与生发的。
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内容在具体构成上显现出一定的文学地理学视阈,其将小说叙事的地缘性与文学意识很好地结合起来,体现出中国小说固有的中心意识和聚合理念,为后世小说流派的形成孕育出极好的土壤。晚清写实小说的繁盛在地域上并不是平面展开的,而是以数个中心城市为基点遥相辉映,这种发展态势不仅体现出晚清写实小说相应的文化属性与地理属性,而且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见出晚清至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场域与文化地理源头。晚清小说家大多聚集在经济较为发达、文学市场发展较为充分的北上广等城市和海外相关国家,作为中国社会最后一批士人,他们在一种末世情绪与改良改革的复杂心态中艰难地向近代知识份子转型,并且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文学的话语方式营造着自身堡垒。如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人在上海,林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广州,黄世仲、陈天华等人在新加坡、日本等海外国家。一方面,这些晚清小说家在极不完善的稿费制度下以市场为导向经营生计,另一方面以一种知识份子的觉悟和担当在启迪民智的使命中固守着文学的地域堡垒。正是因为这种生存视阈下文学抉择的复杂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晚清小说家聚集的地域性特征,并且形成了小说文本独特的文化地理景观(城市景观),这种文学地理分布甚至延续到五四以后,尤其是对近代小说流派的生成彰显出某种先导意义,如后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小说、京派小说等。
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在对民族性与国家意识的深刻体验与传达上是极为显著的。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讲,晚清写实小说就是在深重的民族危难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并且自觉将小说的民族性体验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彰显作为题中之义。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部分,晚清写实小说家也在通过文学想象建构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一方面,晚清写实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处处标榜着文学的“国民精神”维度,以及古典传统的笔调风格与章法结构,体现出小说独有的“中国文学”向度;另一方面,晚清写实小说家在一种文学比照中时时游走在“民族化”与“西化”的文学悖论中,进而孕育出晚清文学现代性这一任重道远而影响深远的历史话题。当然,晚清写实小说对民族性的把握是与民族国家意识的传达紧密相连的,在晚清写实小说,尤其政治小说中,这一主张尤为明显,晚清写实小说家甚至直接在文本中大呼改良改革,将文学创作作为民族国家创建的试验田,以文学文本构制未来民族国家蓝图,进行文学乌托邦与民族国家乌托邦的双重想象与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小说’改良‘群治’是中国近代知识份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采取的迂回路线。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小说或者文学整体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之路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如此直接、鲜明,并持续作用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罗晓静:《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晚清“乌托邦”小说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显而易见,晚清写实小说在民族性与民族国家意识体验与传达上不仅是极为鲜明的,而且是较为果敢与超前的。
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的边界意识上体现出一定的特色,其将小说的叙事性与文学性、审美性与政治性进行了某种嫁接与融合,不仅较好地彰显了晚清写实小说所内在遵循的启蒙/审美这一话语维度,而且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叙事边界的抉择做了很好的尝试。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边界上是较为宽泛的,其所涵盖内容涉及文学、审美、政治、文化、历史等诸多层面,体现出晚清小说家之于文本极强的包容性与模糊性。一方面,这一文本边界意识体现了晚清写实小说家寄予小说文本厚重的政治使命,将晚清写实小说作为启迪民智,再造新社会的重要武器;另一方面,文本边界意识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创作范围与价值立场,使小说文本游走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显现出晚清写实小说发展之于传统审美价值之外的多种可能向度,“充满乌托邦想象的内容和未来完成时的叙事使中国小说固有的文化模式、叙述话语被完全打破,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与传统小说审美空间完全不同陌生而新颖的幻想世界。”*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维新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当然,晚清写实小说家关于文本的边界意识从主观用心上是较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也是极为突出的,其甚至在这种文本泛化意识下时常体现出小说文本启蒙与审美话语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维新派的政论小说,就直接将政治话语、政治口号杂糅进小说文本,于一定的审美意识中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宣扬,将小说文本的视阈拓展到文化的视阈、政治的视阈,在小说的审美传达上罩上了浓厚的政治面纱,形成了政论小说文本文学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鲜明的裂痕与鸿沟,“篇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自不必与寻常说部稍殊。”*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饮冰室合集·专辑》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即使他们深知小说文本自身弊病所在,但这一文本张力仍是晚清至五四以来小说家之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无法真正逾越与解决的。
作为晚清社会文化大染缸中的弄潮儿,晚清写实小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不平则鸣与言志载道传统,并且于一种狂欢化的文学场域中彰显出较为强烈的个体观念与民族国家意识。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逻辑上的建构是富有成效的,其基于暴露与狂欢、“启牗民智”、审美政治化的小说发展路径引导了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潮流,并且在某种视阈中体现出对“五四”小说叙事逻辑的内在规定性。晚清写实小说叙事是具有先验性、复杂性、多元性的,其内在逻辑发展也是充满矛盾张力的,为此,我们应该明确,“五四”以来的小说叙事逻辑固然不是对晚清写实小说叙事逻辑的完美对接,“五四”诸多小说家甚至标榜是对晚清小说的“再革命”,但晚清写实小说叙事逻辑之于“五四”以来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