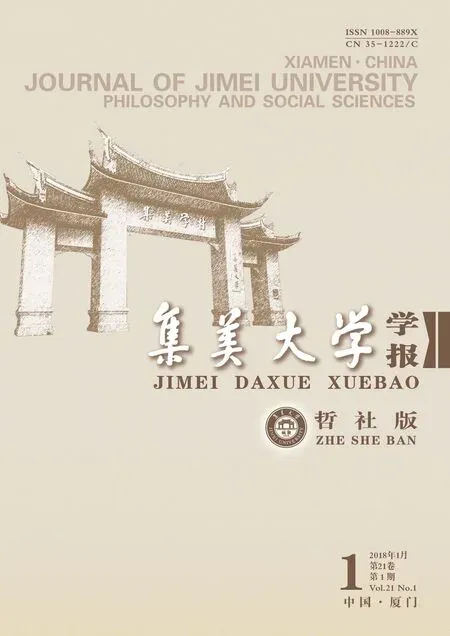理学与明代福建省志编修
王 强, 王汐牟
(1.宁德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2.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一、明代福建省志编修概况
明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都十分热衷于志书的编修,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福建地方志书的编修也迎来了繁荣。根据巴兆祥先生的统计,明代福建共修有方志200种,现存有通志3部、府志23部、州志4部、县志52部、乡镇志1部、卫所志1部,共计84部。[1]
目前尚存于世的三部福建省志分别是黄仲昭《八闽通志》、王应山《闽大记》以及何乔远《闽书》。其中《八闽通志》与《闽书》的编修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八闽通志》的修撰最初源于时任福建镇守太监陈道的提议,同时黄仲昭在修志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陈氏的大力支持。至于《闽书》,其编修者“虽然仅署何乔远一人,但是实际上它的前期资料工作,已经由各府县完成。他只是被当时福建地方当局延请,就各府新修志书,汇总编纂成省志而已,带有半官修性质”。[2]前言,4
不同于得到官方大力支持的《八闽通志》与《闽书》,《闽大记》一书虽然最初也与明代中期官方续纂省志的计划有关,但由于此事的主要负责人林燫去世,故而“志事中寝”,官方修志的计划遂宣告搁浅。王应山作为参与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一员,因为不忍“糜费馆饩,殚心数月”所搜集到的众多材料“遽之高阁”,故而“窃不自揆,奉宗伯(林燫)详定科条,以予所闻,捃摭论次,著其大者”,并明确表示这部书乃是“自述鄙意”。[3]5-6
明代方志编修在体裁上可说是百花齐放,而福建这三部省志在体裁选择上也是形式各异。其中成书时间最早的《八闽通志》采用了当时官方倡导的平列门目体,而《闽大记》一书则效仿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设置,设有图、记(纪)、表、考(志)、列传等体例,体现了明人视方志为史书之流别,并鉴用史裁规划志体的理念。[4]
至于何乔远的《闽书》,其体裁则较为独特,全书仅有“志”这一种体例,分为二十二类。相比于常见的方志,《闽书》这二十二志不但在命篇上极其独特,同时在内容上也有特殊之处,例如《岛夷志》记载当时琉球、台湾、吕宋的情况,《宦寺志》则记载五代林延遇,明代张敏、萧敬这三人的事迹。何氏另一部史著《名山藏》采用了近似的体裁,但在具体分类上存在着差异,并改“志”为“记”。对于何氏这两部史著究竟属于何种体裁,学界观点尚存在分歧,同时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闽书》点校者认为何氏“采用的是常见的门目体,但标题和分类却是别出心裁”,[2]点校前言,2-3而钱茂伟则认为这种体裁“似纪传体而又非纪传体。从记载对象的范围和叙事顺序的安排来看,它还是纪传体模式,所不同的是,仅仅是在名称方面由纪、传、表、志易为‘记’而已”。[5]瞿林东也认为何乔远在《闽书》与《名山藏》“书中所谓的‘记’,实则仍是纪、志、传的统称”。[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将何氏开创的这种史志体裁命名为“分类传记体”,特点是“类似纪传体而又分类叙述”。[7]《四库全书总目》对于《闽书》所采用的这一特殊体裁评价较低,认为其“标目诡异,多乖志例”,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一特殊的体裁体现了何乔远勇于突破传统成见的探索精神。[2]点校前言,2-3
从具体内容来看,最晚完成的何乔远《闽书》卷帙最为浩大,对于福建建制沿革、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史事人物的记载也最为详实。而王应山《闽大记》一书则篇幅最为短小,并呈现出重视记载人物事迹、书志部分内容相对单薄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与《闽大记》编修缺乏官方支持有关。古代史家曾有“修史之难,无出于志”的感慨,书志的编修除了要“老于典故”外,还要拥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而版图、建置、户籍、赋税、食货等方面的情况,除了依靠官方所掌握的材料外,单凭史家私人之力,很难完整获取。王应山在官方放弃省志续修的情况下,凭着自己对于家乡的热爱之情以及著史的使命感,靠私人之力完成了《闽大记》,因此其书志部分内容薄弱也情有可原。
学界根据这三部省志成书时间以及体例内容方面的不同,对三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评价。黄仲昭的《八闽通志》因为成书时间最早,体例内容亦较为完整,故被视为“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性的地方志”。[8]前言,1王应山《闽大记》由于自身在书志内容上的单薄,被形容为“差堪视为我省第二部‘省志’”。[3]初版前言至于成书最晚,但内容最为详实的何乔远《闽书》,则被学界评价为“福建现存最早的完整省志”。[2]点校前言,1
二、福建学术文化传统中的理学因素
程朱理学在明初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开始走向极盛,《八闽通志》、《闽大记》以及《闽书》这三部成书于明代的福建省志,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受理学影响的情况。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福建得到全面开发的时间相对较晚,文化事业亦长期落后于北方地区。两宋以来,伴随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闽地学界更是异军突起。这一时期,福建作为朱子学大本营,涌现出了许多在理学发展与推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学者。以《宋史·道学传》为例,共收录学者24人,除寓居的朱熹外,籍贯为福建的学者共有七人;除此之外,还有胡安国、真德秀、蔡元定等一批虽不入《道学传》但却在理学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闽籍学者。而闽地的文化事业亦受此影响,开始日趋繁荣,“闽学”一词在思想界也变得声名鹊起。
晚明时期的闽籍名宦叶向高在为何乔远《闽书》作序时感慨闽地人文学术“渊源所自,实本宋儒。故宋儒之功,于闽不啻辟鸿濛而开天”。[2]序,5清代道光年间重纂《福建通志》时,学者梁章钜更是直言“道学莫盛于宋,亦莫盛于闽,此(道学传)在他史可无,而在宋史则应有;在他志可无,在闽志则应有,不可删也”。[9]因此,明代福建地方史志的编纂,无论是在思想旨趣,还是在体例设置上,都带有鲜明的理学烙印,体现了地域文化氛围对于史志编纂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福建修成的三部省志在命名时,没有一部采用“福建”这一官方称谓,却都不约而同的的选择了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的“闽”字,显示了当时福建学者对于家乡地域文化,特别是以朱子学为核心的“闽学”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但从整个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理学虽然在明代开始走向鼎盛,但这一时期同样也是理学开始由顶峰走向衰落并逐渐解体的一个历史时期,各种非理学思潮在当时思想界所造成的冲击同样十分剧烈。思想界的种种变化,无疑对当时的史志编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八闽通志》成书于明代前期弘治年间,《闽大记》完成于明代中后期万历年间,《闽书》的编修则处于晚明时期,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分布,为我们考察明代学界整体思潮剧变对于地方学界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象。
三、《八闽通志》对《宋史·道学传》的完善
理学的兴起,一方面促进了史书体裁的发展,出现了以《伊洛渊源录》为代表的一大批专门的学术史著作,同时还催生了借史事来论述义理的纲目体史书;另一方面,理学对于传统体裁史书编纂方面的影响也同样明显,其中尤以体例设置方面的变化最为直接。
在《宋史》之前,各代正史列传部分在涉及学者时,若其人在学术史上极其重要,则会为其设立专传或是几人为一合传,例如《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汉书》的《扬雄传》、《后汉书》的《马融列传》等;若其人在学术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但却并非一个时代最为出类拔萃的学者,且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亦无事可书,则按其学术旨趣进行分类,录入类传之中,或为《儒林》、或为《文苑》。但在理学崛起的背景下,成书于元代的《宋史》在“儒林”“文苑”之外,又专门设立了“道学”这一新类传篇目。虽然,《元史》与《明史》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再设立这一类传篇目*《元史》类传部分只设“儒林”一篇,不但没有“理学”这一篇目,甚至连“文苑”这一传统的类传篇目也被取消,笔者个人认为这可能与《元史》主编宋濂“折衷群说”,唱朱陆“本一”的学术理念有关。至于《明史》为何不设《道学传》,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与明末清初学界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具体可以参见吴海兰:《试析清初〈明史·理学传〉的论争》,《南开学报》,2011年第4期,第89-99页、张涛:《〈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影响》,《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第79-83页、曹江红:《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98-103页,等等。,但《宋史·道学传》的创设,还是对明清时代地方志的体例设置产生了极大影响,“道学”(亦或“理学”)这一人物类别在当时的众多方志中频繁出现。
《八闽通志》作为成书于明初的福建第一部省志,其“人物”部分仿效《宋史》,亦分别设立“道学”与“儒林”这两个大类,但相比于《宋史·道学传》,《八闽通志》对于“道学”人物的界定标准进行了补充与完善。
《宋史·道学传》为了突出程朱理学在道统传承中的正统地位,除收录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朱熹、张栻这几位理学发展史上的骨干人物外,其编修者在序中提出“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10]12710从中可以看出,其收录人物的标准在于强调濂、洛、关、闽一脉的纵向学术传承关系,至于同时代学者之间的横向学术互动关系则很少给予关注;换言之,《宋史·道学传》在考察理学人物时,只注意“师”“徒”关系,却忽略了“友”这一层关系,这也直接导致其在人物收录方面呈现出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被《宋元学案》评价为“朱学干城”的蔡元定、蔡沈父子,不但学术思想上源于朱熹,而且双方在个人私交上也是关系密切,朱熹对蔡元定更是有着“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10]12785的评语,但在《宋史》中,蔡氏父子却被置“儒林”之中,不在“道学”之列。又如胡安国、真德秀、魏了翁等被现代学术界视为在理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学者,也因为其与濂洛关闽一脉没有明确而又直接的师徒传承关系,故而也被排斥于《道学》之外。清代学者尤侗曾批评《宋史·道学传》:“吕祖谦、蔡元定、胡安国、真德秀、魏了翁皆道学嫡派,并入《儒林》,岂为当乎?”[11]
《八闽通志》的主要编修者黄仲昭本人乃是明代前期一位略有名望的理学家,根据《明史》记载黄仲昭早年“性端谨,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学”,后在江西提学佥事任上“诲士以正学”,致仕后“日事著述。学者称未轩先生”。[12]4753-4754黄氏在编修《八闽通志》时,其“人物”部分仿效《宋史》亦分别设立“道学”与“儒林”这两个大类,但相比于《宋史》,《八闽通志》对于“道学”人物的界定标准进行了大幅的补充与完善。
《八闽通志》“道学”部分共收录福建八府一州共44位学者(见下表1)。

表1 《八闽通志》“道学”人物统计
对比《宋史·道学传》,可以发现除了游酢(建州建阳人)、杨时(南剑将乐人)、罗从彦(南剑人)、李侗(南剑人)、黄干(闽县人)、陈淳(漳州龙溪人)、李方子(昭武人)以及朱熹这八位名列《宋史·道学传》的学者外,胡安国父子、蔡元定父子以及真德秀等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也都被《八闽通志》的“道学”条目所收录。
黄仲昭在解释《八闽通志》的“道学”与“儒林”人物分类标准时,表示“道学则取其渊源伊洛,师友考亭,而弗畔于其道者。儒林则取其学明经术,行循矩度,而足以表率后进者”。[8]凡例,1对比《宋史·道学传》仅收录“程朱门人”,《八闽通志》“渊源伊洛,师友考亭”的录选标准,无疑更为合理,使得胡安国(胡寅)父子、蔡元定(蔡沈)父子这些与程、朱一脉关系密切,并在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身份更接近于“友”的人物能够进入“道学”的范畴。
除了收录在学术思想方面对道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外,黄仲昭也十分重视那些在推广道学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例如在“嘉定更化”时力求解除党禁,恢复了朱熹名誉的刘爚,以及被《宋史》誉为“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的真德秀,虽不在《宋史·道学传》之列,但也都被《八闽通志》列入了“道学”人物的范畴。[10]12964
黄仲昭作为生活于明代早期的理学家与史学家,其《八闽通志》在“道学”人物选取标准上进行的修改与完善体现了明初学界对于理学学术史叙述的再思考。但遗憾的是,黄氏本人也没有能够站在理论的高度,对“道学传”的含义与范畴提出一个明晰的标准,再加上《八闽通志》作为一部省志,需要突出褒扬闽地士人,因此黄氏在“凡例”部分将“人物史有载于儒林,而今列于道学者;史有载于文苑,而今列于儒林者;史有载于循吏,而今列于名臣者”这一现象解释为史与志之间的差别,认为“盖史以纪天下之人物,志以纪一方之人物,其品第差异,自不能不少异也”。[8]凡例,2
四、《闽大记》推崇理学的体例特点
明代中期,学界思潮开始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传统儒家学者对于当时流行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理念开始进行了反思与批评;另一方面,理学系统内部的王学崛起,并对程朱之学一家独大的局面产生了巨大冲击。学术活动集中于万历年间的王应山,在治学修史的旨趣方面无疑受到了当时学界整体环境的影响,并体现在《闽大记》的编修上。
明代初年,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念在思想界开始逐渐流行*参见唐大潮:《宋元明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理路》,《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第55-62页;唐大潮:《南宋元明时期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略论》,《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第47-54页;胡华楠:《明初的三教合一思想》,《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第162-165页。,这一趋势发展到明代中期弊病渐显,“儒不儒、禅不禅、玄不玄”的三教相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伦理秩序继而受到挑战。因此一些儒者尝试回到三教根源处,重新确立以孔子之道为规范的合流原则,以期能解决当时的失序危机。[13]
王应山作为朱学一派的拥趸,面对学界当时的状况,对“三教合一”理念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他本人为《闽大记·儒林传》所做序文中,王氏开篇便借自己业师之口提出“儒正学,与二氏之教不相入”,同时还不忘强调闽地自“龟山先生程门立雪,载道而南,彬彬儒学,遂并于邹鲁。垂髫总角之童,知斥二氏,尊孔子”[3]220的理学传统,针对明代学界有人“又言孔、释、老氏之教同出于一人。士贸贸莫知适从”的情况,明确提出“三教不可合,亦不必合。朱、陆之学不必同,亦不害其为同。舍所学之正以企圣修,犹航断汉绝汙而求至于海也,胡可得哉”[3]220,显示了自己对于“三教合一”理念的反对。而在《仙释传》的序中,王应山又再次强调“(释、老二氏)要其归与孔门背而驰。近言三教合一,予谓二氏不相为谋,况援儒以入于二氏乎?”[3]689
另外,针对当时学界风头正劲的阳明之学,王应山同样给予了批评。在《闽大记·李杏传》结尾的论中,他提出“正学本洙、泗,衍于濂、洛、关、闽。总之博文约礼,所由适道。近世士大夫不务宗洙、泗正传,一第以后,窃禅宗之似,缘饰高论,鼓动愚俗,逐臭之夫,靡然从之。圣哲微言,厌弃诋讥,犹以盗主翁谓同室之人盗也”。[3]405此处王应山虽然没有具体点明自己所批驳的对象为何家之学说,但从其“窃禅宗之似”一语可以看出,其矛头所指的便是明代中期思想界风靡一时的阳明学及其诸多后学。
除了在史论中公开阐发自己的观点,王应山还在体例设置等方面竭力维护和体现程朱之学的正统地位。《闽大记》作为一部纪传体史著,其体例上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重新设置了“世家”体例。“世家”体例虽源自《史记》,但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极为少见,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仅《新五代史》设置了这一体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世家”主要记载十国政权的事迹。笔者认为《新五代史》这一做法乃是与司马迁设“世家”体例的褒贬初衷相悖,考察十国政权的性质,以唐修《晋书》“载记”来命名当更为恰当。。一般认为司马迁创设“世家”意在褒扬,其地位虽低于“本纪”,但尊于“列传”。《史记》的“世家”部分除了记载郑、赵、魏、韩等先秦诸侯国以及陈胜、萧何、张良、曹参等秦汉时代风云人物外,还专门立有一篇《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认为太史公此举是因为“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14]1905张守节《正义》则认为“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14]1905
王应山本人极为推崇司马迁与《史记》,同时为了突出朱熹的地位,他在《闽大记》中设立了《朱子世家》,而在此篇的史论中,王应山提出“昔太史公序帝王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孔子一鲁司寇,无爵土可传,得附世家。予稽仲晦氏躬行著述,祀以公礼,禄秩延世,闽南孔子也。作朱子世家”,[3]219明确表示自己立《朱子世家》乃是仿效《史记》为孔子作《孔子世家》,并将朱熹比喻为“闽南孔子”。
《闽大记》编纂体例方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其列传部分仅设有“儒林”传,而并没有像《宋史》或是《八闽通志》一样专门设立“道学”传。王氏此举看似与其学术主张相悖,但仔细考察《闽大记》之“儒林”人物,可以发现此传以杨时、游酢等道南学派奠基人物开篇,主要收录程朱一系的闽籍学者,虽名为“儒林”,其实则“道学”。
笔者认为,《闽大记》这种“儒林传”仅收录道学人物的做法,可以用清代学者陆陇其有关“道学”“儒林”是否需要两分的观点来进行解释。陆氏认为“既为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学;不知道学,便不可为儒者。自儒林与道学分,而世之儒者,以为道学之外,别有一途可以自处。虽自外于道,犹不失为儒,遂有俨然自命为儒,诋毁道学而不顾者。不知《宋史·道学》之目,不过借以尊濂洛诸儒,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今若合而为一之,使人知道学之外,别无儒者,于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学于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儒林之实”。[11]
在陆氏看来,道学是儒学中的唯一正途,《宋史》设《道学传》乃是为了尊崇早期奠定道学基础的濂洛关闽诸学者,而在这些人之后,已经再没有学者值得专门别立一传以示敬仰。由于道学是儒学唯一正途,故而只需立“儒林”一传但专收理学学者即可。
可以说,相比于《宋史》《八闽通志》等史志的“道学”“儒林”两分,王应山直接将“儒学”等同于“道学”,同时又单独将朱熹列为“世家”的做法,在尊崇理学的力度上远大于一般的史志编修者。
五、《闽书》中的理学服从于体例设置
《闽书》成书的晚明时代,一方面政治局势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思想界也开始变得再度活跃起来,明代中叶喧嚣一时的王学开始解体,部分学者开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封建思想本身;同时也有许多学者有感于现实局势的崩坏与此前学风的空疏,提出治学当“致用”,逐渐兴起了一股批判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末流和佛、道思想体系,强调经世致用、敦本务实的实学思潮。而时代思潮的激烈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何乔远的史学思想以及《闽书》的编纂。
后世对于明代学风曾有过极其严厉的批评,认为其太过空疏,经常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而在进行史志编纂时又抄书成风,没有大的建树。何乔远作为一名活跃于明代中晚期的学者,在治学方面虽然体现出了许多新的因素,但时代旧学风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浓厚的烙印。清代学者对何乔远及其著作批评甚多,前文提及《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闽书》“标目诡异,多乖志例”,除此之外,《总目》还认为何氏著述“其文辞亦好刊削,字句往往不可句读。盖不能出明人纤佻矫饰之习”,而《明史》亦认为何乔远《名山藏》与《闽书》这两部著作“援据多舛”。[12]6287客观来说,清人的这些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何氏为《闽书》和《名山藏》各篇所拟定的名字确实极为诡异,初看标题会极为困惑,不知其所叙究竟为何,但细看其内容却并未脱离常见的史志内容分类。例如其《闽书》之《我私志》实与《史记·太史公自叙》近似,但却别立一名,故而《四库总目》称其“虽仿古人自叙之例,而称名不典,语多鄙野”;又如《名山藏》一书中的《典谟记》记载洪武至隆庆十三朝重要史事,《坤则记》记载后妃事迹,《开圣记》则记载明太祖追封的祖先,其所记均是史书常见内容,但仅看典谟、坤则、开圣等篇名,却着实令人费解。
从《闽书·我私志》的自叙来看,何乔远家族理学背景深厚,何氏本人亦被清代成书的《闽中理学渊源考》视作明代晚期福建理学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相比于传统理学家,在晚明诸多新思潮的影响下,何乔远身上体现出了众多不同之处。谢国桢先生在论及何乔远时,认为他是一个“受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何氏的著作除了记载帝王将相以及文人学者外,还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工匠、商人等群体上面,“反映了明朝科学技术及社会上工商业经济的发达”。[2]点校前言,2-3
相比于《八闽通志》与《闽大记》这两部之前完成的福建省志,《闽书》已不再将“道学”人物设为单独的一个门类。在全书的“凡例”部分,何乔远解释道“闽学惟朱文公最重,当如《史记》立为世家,乃见尊朱之意。但如此,则当分道学、文章、政事诸门,体裁方得归一。且何德行之无文章?何文章之无政事?老子、韩非同传,古人有之。而嘉靖中,《浙江通志》一概叙列善恶邪正,取备褒诛,初无分别,今稍仿之,然而恶与邪不列矣”。[2]凡例,7何氏言语之中,对朱子依旧尊崇有加,但《闽书》中有关理学人物的内容已经需要服从于全书的体例安排,而不是像《闽大记》一样,让全书的体例设置服务于突出理学独尊地位这一目的。
六、结 语
通过对明代福建三部省志的考察可以发现理学在编修过程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黄仲昭《八闽通志》在地方人物分类上仿效《宋史》专门设立了“道学”这一类别,并收录了大量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闽籍学者。王应山《闽大记》虽然整书篇幅较为短小,但在体例设置上却极为用心,竭力突出程朱一脉的学术正统地位,并对心学以及“三教合一”理念多有批评。何乔远《闽书》作为明代福建成书时间最晚同时也是内容最为完备的一部省志,相比于之前两部,已不再将推崇理学视为自身编纂的要务之一,同时书中涉及理学人物的相关史事内容也服从于全书的体例安排,不再进行特殊处理。
闽地省志修撰中有关理学内容的变化,一方面与理学在明代学界的地位浮沉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又和福建本地学风的嬗变关系密切。
理学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在明初成为官方统治思想,而福建作为朱子学术活动的大本营,闽籍学者更是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书于明代前期的《八闽通志》作为一部官修方志,自然需要响应官方推崇理学的政策导向;同时,为了达到“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宗旨,也需要突出福建理学名邦的地方特色。因此,黄仲昭根据自身对于理学发展史的理解,针对《宋史·道学传》在人物收录标准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完善与补充,并借此彰显了闽籍学者对于理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至于王应山在《闽大记》中对于理学正统地位的坚决维护,一方面体现了福建作为理学重镇,地方治学风气以推崇理学为先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程朱之学在学界的垄断地位于明代中期已经开始受到严重挑战,因此主要活跃于万历年间的王应山才不得不在书中对于学界诸多反理学思潮进行回击。晚明时代,伴随着社会危机的日趋加深,学界的自我反思也日渐深入,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又成为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源头之一,在上述双重因素影响下,成书于明末的《闽书》开始将自身注视的焦点投向社会现实,而不再专注于维护理学的崇高地位。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明代福建三部省志在编纂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体现了史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与地方小环境对于著述的影响,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地域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学者治学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
[1]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J].中国地方志,2004(4):45-51.
[2]何乔远.闽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3]王应山.闽大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黄燕生.明代的地方志[J].史学史研究,1989(4):58-72.
[5]钱茂伟.论晚明史家何乔远及其《名山藏》初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2):74-78.
[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7]张晓松.略论何乔远《名山藏》中人物传记的特色[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67-70.
[8]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9]陈忠纯.学风转变与地方志的编撰——道光《福建通志》体例纠纷新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74-79.
[10]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吴海兰.试析清初《明史·理学传》的论争[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89-99.
[1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魏月萍.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J].中国哲学史,2008(4):95-104.
[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