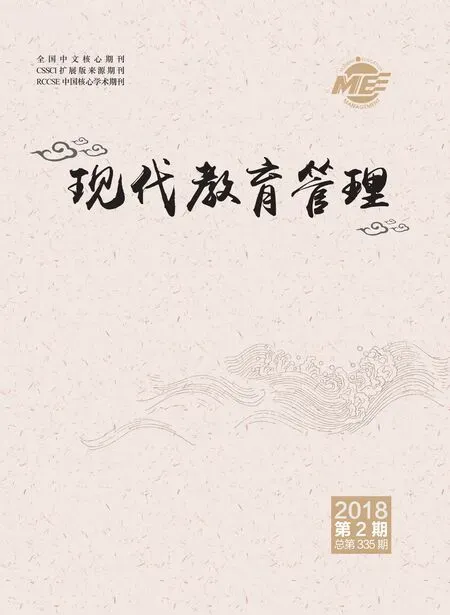着眼全球共同利益:“世界公民”教育的国际研究新趋势①
宋 强,饶从满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世界公民”教育(Global/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是将各民族国家的公民培养为“世界公民”的教育,希冀公民在保证国家认同的同时形成一定的世界认同及相应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进而促进全人类持续和平健康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0年将“国际理解教育”正式更名为“世界公民教育”后,“世界公民”教育及研究逐渐突破了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考虑国家共同体内他者的生活,转向关注、理解人类共同体内的他者生活,突破了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中不引导学生朝向任何既定的善的想法,教授与学生走向合作、包容多元文化,朝向共同解决全球问题促进全球发展而努力。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走向深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威胁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也对民族国家开展的传统公民教育提出了更多挑战。全球问题的消解需要全球共同利益的驱动。为了最广泛地实现全球共同利益,从教育上培养在国际交往中从容应对的“世界公民”成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现实需求,着眼全球共同利益开始成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国际研究新趋势。
一、着眼全球共同利益——全球公民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
2015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塞罗那发布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强调要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报告指出,“共同利益可以定义为人类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例如价值观、公民美德和正义感。我们必须反思公民教育,在尊重普世价值观的多元性和关注共同人性之间需求平衡”。[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检验“世界公民”教育成果的关键指标更能从学习与认知、社会情感、行为等维度具体反映公民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学习者具备了关于‘全球性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和群体间的相互联系与依赖’的知识、理解以及批判性思考;学习者拥有了归属全人类,分享价值观、分担责任、坚持权利的意识;学习者对差异和多样性表现出感同身受、休戚相关和相互尊重;学习者从地方、国家再到全球语境中为一个更加和平与持续发展的世界而有效和负责任地行动”。[2]当前,国际组织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世界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和课程,“世界公民”教育日益进入全球的学校生活和研究视野。
(二)超越短期利益,推进学习者成为2030年的“世界公民”
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正式采纳《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议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议程》“促使我们必须以超越国界和短期利益的眼光,为长远大计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议程》提出,要“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世界公民’意识”[3]。《仁川宣言》提出了到 2030 年,“确保所有学习者获得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通过教育促进生活方式、人权、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发展、推进学习者成为‘世界公民’并欣赏文化多样性及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世界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应在国家教育政策、课程、教师教育和学生评价中成为主流”。[4]
(三)“世界公民”教育研究随着全球共同利益的突出成为学界热点
自威尔斯(H.G.Wells)191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智慧的世界公民》一文以来,“世界公民教育”又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在追求国家之间平等合作的前提下,学者们开始探讨实现全球共同利益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往殖民主义“你输我赢、非此即彼”的利益观开始解体。通过分析世界公民教育主题文章的发表年度和数量可知:在1919-1976年期间,每年基本只有一篇世界公民教育研究相关文章,其中只有1922年是3篇,1971年、1973年是2篇;自1977年开始,相关文章开始逐渐增多,但每年都没有超过5篇,在1-3篇之间浮动。20世纪60、70年代后,世界主义与公民资格理论进行了更好的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和平教育项目也在理念上与世界公民教育相契合,为世界公民教育随后的快速发展做了准备。1988年后世界公民教育研究开始再次增长,1988年为6篇,1989和1990年为8篇;自1991年后,论文数迅速由个位数上升到十位数,由1991年的9篇达到了2004年的64篇;2005年后论文数快速增长到百位数,由2005年的101篇增长到2015年的391篇。
二、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基于世界公民教育研究文献的分析
(一)世界公民教育的意义:人权保护与共同发展
世界公民教育可以促进普适性的人权保护。以往各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由民族国家保护即可,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区域共同体做出的促进本国和本地区发展的决定却有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和区域产生消极影响。奥斯勒(Audrey Osler)教授指出:“世界公民教育的特征包含了公民教育中的‘当地、国家、区域(例如欧盟)、全球’四个维度。”[5]这就需要涵养个人、国家、区域、全球四个层级的“世界公民意识”来保护普适性人权。“学者们提出要发展‘后民族公民资格’(postnational citizenship),这种公民资格依附在人类个人权利而不是特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上”。[6]根据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律顾问的瓦萨克(Karel Vasak)提出的“三代人权”理论,“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关乎普适性的人权,以探讨关涉人类生存条件的集体‘连带关系权利’,如和平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人类共同遗产权、环境权等为主要内容,因为这些人权的实现只能‘通过社会中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包括个人、国家、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以及整个国际社会’”。[7]“公民资格通常被政府机构视为重要身份,所有人包括无国籍者都有人权。为了保护人类普遍拥有的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等,除了民族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庭等全球共同体也承担了一部分职责。沃克(George Walker)还乐观地认为:“普遍需求一定会创造出普适价值。有一些并不难判断: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向往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於恐惧和匮乏”。[8]保护人类的权利是为了共同发展,营造一个更加更加生态、环保的地球。国际组织世界未来协会(the World Future Council)表达的愿景就是:“我们希望一个可持续、正义、和平的未来,在那里普遍的人权得到尊重”。但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普适人权存有质疑。如印度哲学家桑迪普·瓦斯菜克所说:“虽然有过关于利用那些被神圣地记录在《普世人权宣言》中的种种原则来约束各人类社会的争论;可是,这些思考仍然是把民族国家当成是社会组织的首要形式。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一种全球性的文明或者一种全球性的共同体。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经验性的、实在的经历(empirical experience)能够被用来检测这个‘作为世界的世界’概念”。[9]
(二)世界公民教育的维度:国家认同到世界认同
全球化带来了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的矛盾。“在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差异性的他者明显存在时,自我会对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产生强烈的感知……那些一向被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10]“世界公民并不是国家公民的一种供替代的选择,而是对加强世界范围内代议制和参与性民主坚实的补充,争取捍卫有关个人权利的社会民主公约,而不仅仅是财产权。换句话说,世界公民为国家公民增添了附加价值。国家公民的建构可以看做是未完成的事业。因此,世界公民的附加价值应从另一层次来支持公民资格形成中的转变,最终将公民教育转变为建立在全世界人民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基础上”。[11]
世界公民教育呈现三个认同倾向:第一,立于国家角度培养世界公民,主要是民族国家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第二,立于全球角度培养世界公民,主要是国际组织和一些自称为世界公民的社群、个人。第三,兼顾国家与全球培养世界公民,主要是民族国家中世界认同重于国家认同的机构和公民。以上三种倾向都无法单一回应“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的张力”这一核心问题。正是由于世界公民教育思想对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两者的关系难以把握,德里克·希特便尝试分析其原因:“如果世界主义的愿景没有深深触动人们的心灵,就要从民族传统的强固力量与相比之下脆弱的全球情感联结中寻求原因。公民们需要共享一种共同体的感觉,而这种情感最有可能得到有效培育的方式是成长与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有着明晰的共同点,尤其是语言、文化、深刻的历史叙事以及绚烂的神话故事。……问题是,不存在这样一种类似的文化、历史和神话,在空间范围上如此普适,以致世界主义的认同感可以牢固地扎根其中”。[12]
(三)世界公民教育的载体:全球治理到世界政府
世界各国对在全球化语境下加强全球治理,实现全球共同利益有着广泛的共识。全球治理为世界公民教育提供了价值指导,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的缪艾特莱菲尔德(Michael Muetzelfeldt)等人指出:“要分析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公民资格,需要聚焦全球治理。正如民族国家会促进或阻碍国家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全球治理机构也会促进或阻碍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世界层面的公民社会将会在与全球治理中强大的推动机构的互动中茁壮成长。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全球治理,我们能在战略上认同政治和社会参与适当的形式,以使世界公民资格的前景得到最好的发展”。[13]通过治理与公民资格的层次可见,全球治理与世界公民、世界权利与义务、世界机构等构成了一个紧密相关的体系(见表1)。

表1:治理与公民资格的层次[14]
在各国同意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国际组织和一部分世界公民教育研究学者对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政府、世界联邦的建立提出了设想。“一些学者竭力主张建立一个超越各国政府之上的世界政府,像国民政府在国内行使主权功能一样,世界政府将在全球范围内行使主权职能。少数学者直裁了当地指出,应当强化联合国对各成员国的强制性约束力量,逐渐将联合国改造成为世界政府”。[15]但是,许多学者并不看好世界政府的产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丁斯(Nel Noddings)指出:“尚未有一个世界政府,让身为个人的我们去效忠,也没有国际法律来约束我们,除非我们的国家政府接受它们。因此,我们不能援引一般所熟悉的公民资格的技术定义,来帮助我们说明‘世界公民’资格。”[16]因为世界政府与世界联邦遥不可及,世界公民教育思想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当前世界公民教育的主要载体和实施主体还是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
(四)世界公民教育的普适性:西方式普适思想与多元文明共生
当前,对世界公民教育的研究和阐释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这难免会使一些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世界公民教育本身进行反思,探寻其背后是否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是否适用于多样文明。一些学者更是运用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如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就试图“伸张一种尊重文化差异、强调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内部实行有效抵制的混杂化策略,最终落在一种不同文化互相交杂、不同民族彼此尊重相互依存的后殖民的世界主义上面”。[17]文化相对主义者也持有以下观点:“价值观只有在某一特定文化中才有意义。因此,所谓‘绝对的文化中立价值观’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由此断定,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不能被理性地认为绝对比另一种文化优越,因为没有一种文化中立的立场仅仅是从‘异文化价值观可以理解’的哲学角度获得的,更不必说能容许基于绝对价值观的标准来公平地比较和理性地判断”。[18]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在提出包含争议的“文明冲突”同时,也明确阐释了两类普世文明的区别:“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19]但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坚持普适思想,对学校不谈论价值以免文化引起争议的做法深恶痛绝。马特恩就坚信,这些价值“不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的公民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每一种道德制度都十分看重诚实;每一种道德制度都教导人们尊重他人的权利尊重这一种制度;实际上,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提倡民主;每一种社会都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仁爱”。这种对于世界公民教育是普适思想还是适用于多样文明的争论直至今日仍未平息。
三、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
(一)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教育中的国家认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培养良好的“国家公民”是开展“世界公民”教育的前提,公民教育应当遵循国家认同到世界认同的逻辑顺序,否则受教育者就会由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公民”高度堕落到无根的流浪者,甚至是极端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虽然中西均存在公民教育立场的变化,但强调公民对国家或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培养却是基本共识。”[20]当下由于国家认同削弱导致国家公民身份模糊、精神迷茫乃至战乱分裂的事例不胜枚举,其本质是民族国家内部治理失败和全球化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发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则遭遇国内转型压力和全球化压力的交互影响,使其兼具了常态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21]我国应注重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培养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公民。在国家公民的培养中,既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又需规避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当前一些公民的言行中还存在着狭隘的民族意识,存在排外情绪,不能包容其他民族和国家。但坚持爱国情怀、创新精神、世界眼光相结合,应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征。对世界公民教育的研究和把握有利于思考并处理好爱国主义与国际理解、多元文明的关系,使学生在坚持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学会关心全球事务、尊重理解别国文化、与他人和谐共同生活,形成“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共同进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识,从而加快我国的国际化进程,增强国际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
(二)培养社会主义“世界公民”,提升国际话语权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愈来愈表现出高度的依存性、渗透性和互动性。”[22]全球化的影响力正在迅猛扩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世界各国需要联合起来对全球问题做出回应。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中需要重视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主动引入全球性的新观念及动态信息。这样有利于思考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公民”教育中,如何在世界认同方面制定教育政策、传递相应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以及如何处理公民教育中多元认同的关系。最终培养既具备强烈全球责任意识又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满怀人类理想追求“天下大同”,又脚踏实地秉承“和而不同”的“世界公民”。公民个人正当利益与国家利益、全球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公民资格上,参与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而对世界公民来说,需要更多履行参与义务,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事务中来,为全球共同利益所服务。我国培养的社会主义“世界公民”应当既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又具备理解、合作、包容、共生的大国气质,能够从容合理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教育治理,不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三)引导公民寻求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共同利益”与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有着内在一致性。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注重承担全球责任。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中国表达了“提高教育质量,维护公平正义,加强环境保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全民共建共商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并肩,合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而不懈努力”的立场。我国倡导的这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正在逐步获得国际共识。面对世界公民教育研究的新趋势,我国公民教育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塑造全球公民”主题青年论坛致词中所期望的那样,培养“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献瓦”[23]的世界公民。
[1]UNESCO.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EB/OL].http://www.unes cocat.org/en/rethinking-education-towards-a-globalcommon-good,2015-07-15.
[2]UNESCO.MeasuringProgressin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EB/OL].http://www.unesco.org/new/en/media-services/single-view/news/measuri ng_progress_in_global_citizenship_education/#.VS5kQt z23wY.2014-11-7.
[3]UN.Transforming ourworld:the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OL].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2015-9-25.
[4]UNESCO.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 ion Towards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EB/OL].http://acuns.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Education-2030.pdf.,2015-11-5.
[5]Audrey Osler,Hugh Starkey.Learning for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Theoretical Debates and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s[J].Educational Review.2003,55(3):243-254.
[6]Natalie Delia Deckard,Alison Heslin.After Postnational Citizenship:Constructing the Boundaries ofInclusion in NeoliberalContexts[J].Sociology Compass,2016,10(4):294-305.
[7]王广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87-90.
[8]George Walker.Educating the Global Citizen[M].Suffolk:John Catt Educational Ltd,2006:95.
[9]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1-114.
[10]吴玉军.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问题: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的一种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
[11]Carlos Alberto Torres.Global Citizenship and Global Universities.The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 dence and Cosmopolitanism[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15,50(3):262-279.
[12]Derek Heater.What is Citizenship[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150-151.
[13][14]Michael Muetzelfeldt, Gary Smith.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Possibilities for Global Citizenship[J].Citizenship Studies,2002,6(1):55-75.
[15]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0.
[16]宋强.谁来赋予我们世界公民资格?——世界公民教育的合理性反思[J].外国教育研究,2015,(3):21-31.
[17]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4.
[18]George Walker.Educating the Global Citizen[M].Suffolk:John Catt Educational Ltd,2006:94.
[1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3-45.
[20]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J].教育研究,2006,(12):3-11.
[21]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3,(9):16-27.
[22]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J].中国社会科学,2016,(6):5-14.
[23]新华社.致词祝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习近平: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N].新华每日电讯,2015-1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