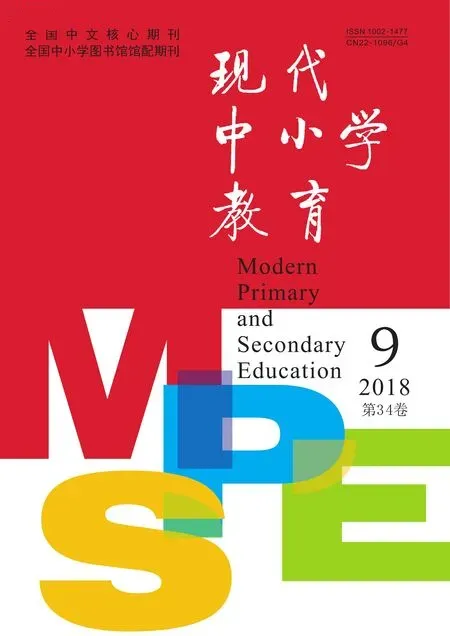应对·合作·参与:课堂改革的三种路径
——兼谈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一书
马 天 保
(广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广东 广州 510540)
《静悄悄的革命》是日本学习院大学文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佐藤学的名作,是他近20年深入基础教育实地考察调研的成果结晶。佐藤学在走访日本1 000余所学校、参观7 000多间教室后,提出要改革日本学校教育的划一性和效率化两大弊端,在学校课堂里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旨在创造一种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学习,更好地推进“学习共同体”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性、合作性、反思性的学习是通过与教材相遇对话、与师生相遇对话、与自我相遇对话,以任务学习和小组活动等形式,把自己的理解用作品呈现出来,在多重交往中相互欣赏启发的学习。这是一种从个体经验出发,经过集体合作探究,再返回个体经验积累的过程。它既不是简单地追求“自我学习”,也不是把整个教室分割解体成零零散散的个体,而是通过应对、合作、参与这三种路径改革课堂教学,在学生、教师和家长中形成共同学习的良好氛围和教育合力。这场直面日本课堂教学实践的“静悄悄的革命”亦可成为一面参照镜,在促进我国课堂改革深化、提升我国学校办学实力的同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开拓有效的改革途径。
一、倾听对话,构建师生“应对”模式
课堂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通过师生互动达到完成教材内容的教育行为。“学生”、“教师”、“教育环境”和“教材内容”是课堂教学的四大要素,“学生”因新型师生关系建构后的主体地位成为其中的焦点一环。一线教师在“自主—合作—探究”模式影响推动下,渐渐改变着过去的“一言堂”,把课堂完全交付予“学生”这个主体,由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自我学习”一度被认为是值得效仿的理想形态。佐藤学认为,这已经将学生的主体性绝对化了,“是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与教材以及学习环境等割裂开来,让教育成为仅仅针对学生的需要、愿望、态度等学生自身的性格取向来进行的神话,成为把学习理想化为只由学生内部的‘主体性’来实现的神话”[1]。课堂中的形式主义是产生这种主体性假象的温床,比如手势教学,单一机械地把师生交流分为赞同、反对、提问三种立场,看似课堂互动积极活跃,实际上教师已经人为排除了学生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意见,忽略了模糊多义的观点能够激发创造的重要意义。
要粉碎主体性假象,超越主体性神话,课堂必须建构以“应对”为中心的教学,重视倾听对话的效能。润泽的教室所营造的是一种轻松自如、无拘无束的学习氛围,师与生、生与生之间构筑着一种彼此尊重、相互信赖的关系,大家应当追求的不是“发言热闹的教室”,而是“用心地相互倾听的教室”[1]。以“应对”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第一要义是倾听,教师应以慎重、礼貌的姿态倾听每一位学生的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在“倾听”中既要站在“理解了意思”的层面听其内容,也要站在欣赏、体味学生的立场听其心情,听其想法;既要像服装裁剪般地量体裁衣,倾听每一个的学生的心声,也要像指挥交响乐团般地融合激荡不同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认识;既要倾听“单向交往”、“双向交往”和“反向交往”的交际语言,也要倾听思路各异的“异向交往”话语。对此,佐藤学打了一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倾听学生发言类似棒球投球训练,准确接住学生的投球,他们的心情会格外愉快,学生投偏的球如果也能被准确接到,学生后来便会奋起努力以便投出更好的球。“不擅长接球的教师,应当专心一意地正面直对学生,去接住他们的每一个球,重视他们的每一个球,而不要以为只有按自己的教学计划上课才是上课。”[1]倾听对话是师生课堂教学互动的基本策略,也是构建师生平等友爱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开放教学,实现同事“合作”关系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所完全相同的学校、两间完全相同的教室。然而,互不相同的课堂环境却时时生成着大同小异的教学模式,学校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改革显得步履蹒跚。佐藤学认为,学校改革是以每十年为一个周期的事业,至少也需三年的实施过程作为渐进性变革的思考。第一年,在校内建立教师公开授课的教研体制,人人都要参与,人人都要做授课者;第二年,提高研讨会质量,借助公开授课和教研活动,简化部门,重组机构;第三年,根据师生的共同转变,正式固定课堂教学的新课程和新方式。
学校改革发展依托课堂教学改变,课堂教学改变依靠教师观念转化。佐藤学指出,把“学校”作为“学习共同体”创造的关键问题是“以教学的创造为核心展开,而推进教学创造的基础在于建构教师切磋教学、相互学习的‘同事性’(collegiality)”[2]。教师之间要敞开教室的大门,相互开放教室,强调开放教学,实现一种“合作性同事”关系。构建愿景一致、平等互惠的合作共生关系需要每位教师都以教育专家的角色积极融入、互相欣赏、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学校变革必须从课堂行为开始。学校借助专家力量,通过开展课堂观察和课例研究达到这一目标。课例研究是改变课堂文化、落实学校文化的有效工具,能够切实改造教师研究行为,促进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发展。”[3]教师在参与校内教研时,应把关注点聚焦在授课的“困难”、“乐趣”以及“师生应对”上,即把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教师的教学态度作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而教材内容设计和教学结构安排更应从课堂中师生教与学的实况出发对应讨论。“观摩者不是‘对执教者建言’,而是阐述自己在观摩了这节课之后‘学到了什么’,通过交流心得来相互学习。”[4]同时,以教育专家的角色参与校内教研的每位教师在公开授课、合作研讨的过程中,应该时刻明确教研课题,带着自己的挑战课题致力于课堂教学研究,既作为理论能动者,也作为实践行动者,将理论势能有效转化为实践动能,才能激发课堂的创造性、丰富教学的多样性。“即使是像普通高中这样的‘铁板课堂’,通过能动者的联动,发现课堂教学中的真正问题,分析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引入解决此类问题的专门理论,生成学校变革中的先锋力量,逐渐促使课堂教学合理有效地发生变革,也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与质量。”[5]
三、联动课程,倡导家长“参与”机制
家长也是教育工作者。这个观点的确扩大了“教育工作者”这个概念的内涵,但基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深刻作用,把“家长”纳入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在一定意义上是合情合理的。即便家长并非教师,从事行业与教育毫不相干,但作为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的启蒙作用是任何教育工作者都不可替代的。鉴于此,课堂教学在完成“教师—学生”应对模式和“教师—教师”合作关系这两步校内改革后,改革“手臂”就到了向外延伸,即学校向社区开放、课堂向家长开放,赢得校外力量大力支持的时候。
学校向社区开放、课堂向家长开放的改革实施起来绝非易事,必须要突破教师与家长互不信任、隔阂疏离的最大障碍,倡导建立从“参观教学”到“参与教学”的家校协同机制,联动综合课程,推动共同学习。家长的“参观教学”常常采用“听—评”模式,即以听授课、提建议为基本形式的带有参观性质的家校互动;“参与教学”在延续“参观教学”思路作为联动改革第一步的同时,进而完善深化出“听—评—讲—思”模式,即在“参观教学”的基础上赋予家长登台讲课的机会,并以教师与家长合作讨论、反思评价为终结。考虑到大多数家长并非教育专业人士,改革伊始还难以直接胜任学科课程的教学任务,但可以尝试安排其成为学生小组学习的助理导师。“家长是具有丰富经验系统的社会人、知识人,因而家长对教育性经验的认同并非仅限于国家、地方和学校规定的课程内容,而是往往打破教科书边界,根据个体经验体系融入了更多的综合性经验。”[6]结合家长的工作特点和人生经验,提供相应的兴趣特色课程,让他们以主讲人的身份参与学校第二课堂的教学管理当中。当第二课堂的教学改革初见成效,这种“参与教学”就可以嫁接到综合实践课程之中。家长在教师的专业指导下,以学生的认知兴趣和发展需要为目标追求,以现实的“主题(课题)”为核心设计,把“知识”和“经验”组织成单元,将以往“目标·达成·评价”的阶梯型课程改变为“主题·探求·表现”的登山型课程,系统地完成经验的设计、经验的教学实践、经验的反思评价等综合创造学习的全过程,以综合学习推动学科学习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家长又在参与联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以主角身份同学生、教师一起成为“学习共同体”的重要成员。
佐藤学指出学校改革的基本哲学原理之一是:“将21世纪的学校设定为‘学习共同体’,学校是学生共同学习成长的地方,是教师作为专家相互学习的场所,是家长与市民参与教育实践进行连带性学习的场所。”[7]这一论述突出了学生、教师、家长在21世纪学校改革、课堂改革中的主人翁地位和学习者角色,明确了学生、教师、家长共同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意义。观照当下,我国的素质教育改革已步入发展的“深水区”,多年以来虽有开花结果,但路在何方仍不明晰。作为“付诸行动的研究者”,佐藤学的教育改革思想或许可以给我国基础教育的变革发展提供些许思路。在阅读《静悄悄的革命》一书后,笔者认为,应对、合作、参与是我国新时期课堂改革的三种重要路径,即构建以倾听为基础的师生应对模式,实现以开放为前提的同事合作关系,倡导以联动为目标的家长参与机制,在学生、教师、家长三个层面积极推进“学习共同体”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让教室里的学习成为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尊重、每个学生都能放心地打开自己的心扉、每个学生的差异都得到关注的学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