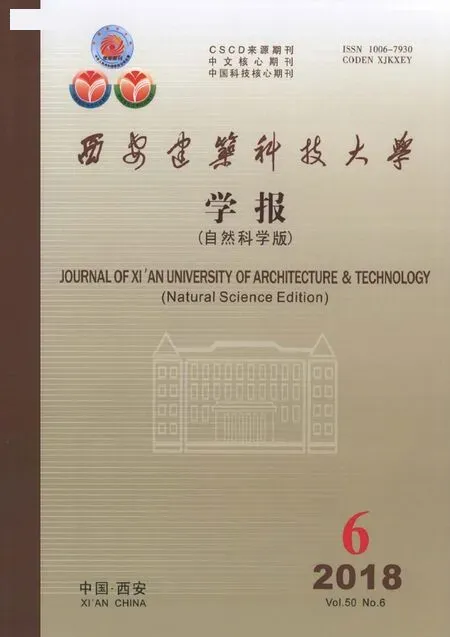城市居住组团公共绿地面积约束下容积率极限值估算
郑晓伟,黄明华,2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2. 西安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55)
城市绿化是指栽种植物以改善城市环境的活动,而在城市各类绿化当中,对市民生活环境或者是公共利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住区绿化.好的绿化环境是确保居住用地内公共环境品质的基础,故而不论是从《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规范”)还是地方性的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来看,对于城市居住用地规划设计在绿化配置指标方面的相关指标都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根据“规范”,城市居住区内绿地指标包含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地率两种类型.由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涉及到居住用地的人口规模,那么该指标就必然会影响到居住用地内的其他控制指标(例如总建筑面积、容积率、公共设施规模等)[1-3],而相比之下,绿地率更多地是反映居住环境综合质量的一项指标,与其他指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居住用地开发是确保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前提,但这往往又是以牺牲绿地面积为代价,因此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必定会涉及到居住用地开发的综合效益.但从目前来看,关于居住用地绿化指标和容积率之间的相互约束关系,特别是现行“规范”提出的相关指标是否能够与国内居住用地容积率整体水平相匹配还鲜有研究.仅有黄一翔[4]等人探讨制订了一个以碳平衡为原则,根据容积率的不同而变化的绿色住区绿地率动态指标;林茂[5]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探讨了居住用地内容积率与绿地量随建筑层数的变化规律,得出不同类型住宅建筑低层、多层、高层的高密度最优化值,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容积率的估算;李旭光[6]、李晨[7]、李飞[8]等人分别从日照标准、道路边缘至建筑物距离、基本理论概念等方面论述和证明了现行“规范”的种种不适应性;黄明华等9-10提出了容积率“值域化”的控制方法.此外,其他关于居住用地绿化指标的研究也主要停留在对于“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关于绿地率自身指标体系合理性的探讨两个方面.随着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带来的高密度开发需要和市民对居住环境品质需求的不断提高,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特别是开发强度的控制同时满足居住用地内充足的绿化面积和高密度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达到“规范”规定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前提下,居住组团的容积率最大值是多少?该极限值与“规范”所规定的最大容积率是否一致?抑或是过高的容积率本身就与“规范”的其他控制指标存在矛盾?
1 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容积率”约束模型建构
根据“规范”,城市居住区按照居住户数和人口可以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三级.作为居住环境中的最小组成单元,居住组团的最大作用在于承担整个居住区内的居住生活功能,而对于主要的公共服务功能来说,则更多地是由居住组团层面以上的居住小区和居住区来承担,这就意味着在居住组团层面的建筑基本由住宅构成,即“规范”中的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就可以近似地看作是居住组团的容积率指标.故为了更加方便地计算和论证居住用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容积率之间的关系,避免其他变量对研究过程的影响,本研究将范围限定在居住用地的最小单元——居住组团层面.
1.1 模型假设
1.1.1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P)
如前文所言,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P是居住用地绿化指标体系的核心,也是从绿化配置的角度决定居住用地容积率的唯一规范性绿化指标.因此要建构在满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条件下的居住组团容积率约束模型,首先必须确保组团层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P满足规范规定的要求,即MP=0.5 m2/人.由于因变量容积率F必然会随着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MP的增加而减小,而根据“规范”,0.5 m2/人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是作为下限值进行控制,因此有且只有当MP=0.5m2时,因变量容积率F才会出现最大值.
1.1.2 人均居住建筑面积(EP)
1.1.3 组团公共绿地的设置方式
根据“规范”的规定,居住组团层面的绿地可以分为院落式组团绿地(图1左)和开敞型院落式组团绿地(图1右),其区别在于前者四面都被住宅建筑围合,空间较封闭,故要求其平面与空间尺度应适当加大;而后者至少有一个面,面向小区道路或建筑控制线不小于10 m的组团级道路,空间较开敞,故要求平面与空间尺度可小一些.不难发现,不论是哪种组团绿地的设置方式,由于其本身规模相对较小,为了确保组团层面公共活动的展开都要求公共绿地必须集中设置,而非分散设置在组团内部.故而本次研究也将假定组团层面的公共绿地必须为集中式的设置方式,并且为了确保控制组团绿地的最小规模,可将其进一步限定为院落式组团绿地.

图1 居住组团绿地的布置形式Fig.1 Arrangement of public green space area in urban housing cluster
1.2 居住组团容积率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函数关系建构
众所周知,居住用地容积率提高的同时居住人口密度也相应提高,但往往容积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牺牲绿地的规模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满足“规范”中其他指标规定的前提下,容积率的提高势必会带来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下降.因此,研究以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P为约束条件入手,在依据“规范”所确定的组团层面各相关指标的基础上建立城市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的约束模型.
由于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是居住组团公共绿地面积与居住人口的比值,那么就会存在:
MP=Sp/N
(1)
其中:MP表示组团层面的人均公共绿地(m2/人),Sp表示组团层面的公共绿地面积(m2),N表示组团层面的人口规模,根据“规范”,组团层面的人口规模为1 000~3 000人,即Nmin=1 000,Nmax=3 000,那么对应的公共绿地面积Spmina=500,Spmaxa=1 500.但在“规范”中对居住组团最小用地规模已经做出400 m2的限定,故而研究最终将调整修正后的组团公共绿地面积限定为Spmin=400,Spmax=Spmaxa=1 500.
此外,根据“规范”的规定,居住区内的公共绿地除了要满足一定的面积需求以外,同时还要满足一定的日照标准,即组团绿地应满足有不少于1/3的面积在标准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这就说明,城市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的建构除了要考虑绿化指标自身的影响因素以外,还要考虑日照条件的约束.对于满足日照条件下的居住组团来说,其容积率最大值为基地内所有建筑底层窗台正好满足大寒日2h日照标准的临界容积率值,故而在最大容积率的状态下,基地内除住宅建筑以外的空地(包括绿地和道路)大部分都将无法满足大寒日2h的日照标准.为了确保不少于1/3的组团公共绿地面积在标准日照阴影线的范围之外,就必须使原有基地内在保证2/3的组团公共绿地面积基础上,必须通过增加集中式的标准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绿地,从而确保“规范”中对公共绿地在日照标准方面的规定,如此总的用地面积将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假设满足日照条件下的居住组团计算得出容积率最大值为AFmax(即该最大值为居住组团最大建筑平均层数与建筑密度的乘积),其对应的地块面积为SX1,那么此时的总建筑面积A1就可以表示如下:
综上所述,在现下网页制作中,CSS技术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便捷手段,其不仅可以提高网页设计的灵活性和功能性,而且还能增强网页浏览速度。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CSS技术在网页制作中的实效作用,不仅要对其应用形式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要重视其代码优化方法的有效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网络需求。
A1=AFmaxSX1
(2)
对应的居住人口可以表示为
N1=A1/EP=AFmaxSX1/30
(3)
对于在标准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1/3组团公共绿地面积(假设为SX2)来说,其在周围没有任何建筑影响的前提下可以确保SX2全部的区域都能满足大寒日2h的日照标准,但是一旦将其置于满足日照条件下居住组团中就可以发现,除将该部分绿地置于整个基地的最南侧(即不受基地内住宅建筑的日照影响,但这与假定条件限定的集中式公共绿地不符)以外,仍然会有部分面积进入到无法满足大寒日2h日照标准的建筑阴影区范围.进一步研究计算发现,该部分面积基本上与SX2的面积呈一定的倍数关系,并且居住组团的建筑高度越高、建筑密度越大,进入到无法满足大寒日2h日照标准建筑阴影区范围的1/3组团公共绿地面积也就越大,其最大值(当建筑平均层高取最大值时)可以达到SX2面积的12倍左右.因此,对于城市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来说,既满足日照条件下又能保证1/3组团公共绿地面积在标准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实际地块面积为12SX2.
与此同时,如果假定居住组团内的道路是均质分布的,为了使居住组团的功能构成更加完善,上述增加的12SX2地块面积中必然还要将最大占总用地15%的组团级道路用地考虑在内.因此,增加到居住用地满足日照条件下居住组团限定的地块范围内并仍然能保证1/3组团公共绿地面积在在标准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地块面积可以最终确定为12SX2×(1+15%)=13.8SX2.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上限值的地块面积就变成了SX=SX1+13.8SX2,但由于新增加的仅仅是组团公共绿地和道路,因此上述模型中居住人口、总建筑面积等变量将不会发生改变,故而会有
A=A1=AFmaxSX1
(4)
N=N1=AFmaxSX1/30
(5)
根据“规范”,组团层面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P=0.5,那么就有
Sp=MPN=0.5N
(6)
式中,Sp表示居住组团的公共绿地面积,进一步将公式(5)代入公式(6)可得:
Sp=0.5AFmaxSX1/30=AFmaxSX1/60
(7)
根据组团绿地的设置应满足有不少于1/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要求,则有
SX2=Sp/3=AFmaxSX1/180
(8)
此时,城市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上限值对应的总用地面积就可以表示为
SX=SX1+13.8SX2=SX1+ 13.8AFmaxSX1/180
(9)
将公式(4)与公式(9)进行合并,就可以得出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上限值的函数关系为
Fmax=AFmaxSX1/(SX1+13.8AFmaxSX1/180)= 1/(0.077+1/AFmax)
(10)
可以看出,城市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是一个容积率指标随满足日照条件下的地块容积率变化而变化的函数,这就意味着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仅与地块建筑平均层数和地块内的建筑密度有关,而与地块面积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2 居住组团容积率最大值计算以及与“规范”间的矛盾分析
2.1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约束下的居住组团容积率最大值计算
对于城市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来说,在满足组团级公共绿地的面积和日照标准的前提下,如果限定居住组团内的平均建筑层数为35层(按住宅最小层高2.8 m计算,总高度不超过100 m),根据“规范”,在自变量建筑密度M取20%时,居住组团满足日照的容积率最大值为AFmax=7.00,根据公式(10),居住组团满足日照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地块容积率最大值Fmax=4.55.这就意味着,若要满足城市居住组团层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少于0.5 m2/人的前提条件,同时又能满足“规范”规定的日照要求,那么在居住组团层面的容积率指标最大值为Fmax=4.55.该容积率水平基本上能够满足目前国内城市居住组团内高密度开发建设的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所制定的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在自变量定义和选择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规范”对居住组团层面人口规模的限定.如果根据居住组团(即假设组团地块规模SX在4~6 ha的定义域范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的容积率最大值计算相对应的人口规模和总的公共绿地面积,那么计算结果就如表1所示:

表1 居住组团层面容积率极限值对应的相关指标统计
续表1

地块面积/ha最大容积率总建筑面积/m2居住人口规模/人公共绿地面积/m25.24.55236 6007 8873 9435.34.55241 1508 0384 0195.44.55245 7008 1904 0955.54.55250 2508 3424 1715.64.55254 8008 4934 2475.74.55259 3508 6454 3235.84.55263 9008 7974 3985.94.55268 4508 9484 47464.55273 0009 1004 550
2.2 与现行“规范”之间的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规范”中所限定的居住组团层面的人口规模为1 000~3 000人,即Nmin=1 000,Nmax=3 000,公共绿地面积为400~1 500 m2,即Spmina=400,Spmaxa=1 500.但研究发现,根据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计算得出的容积率最大值所对应的人口规模(6 067~9 100人)和公共绿地面积(3 033~4 550 m2)最大值都远远超出了“规范”的规定.即使根据“规范”规定的3.5容积率指标上限计算所得出的结果(4 667~7 000人的人口规模和2 333~3 500 m2的公共绿地面积)也远高于“规范”中对人口规模和公共绿地面积的规定.这不仅说明高密度的开发完全可以实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保证,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规范”在组团层面的人口规模和开发强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矛盾.换言之,如果对居住组团的人口规模按照“规范”进行限定,这就意味着居住组团在满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的前提下的最大容积率Fmax只能小于2(基本上为多层住宅和中高层住宅的容积率上限水平),这不仅与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住用地高密度开发建设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目前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等相关政策相违背.
笔者认为,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所对应的人口规模上限远远超出“规范”规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规范”对于居住组团层面的人口规模限定太低,从而导致据此计算得出的最大容积率也只能在1.6左右.如果同时要满足居住组团层面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那么其最大容积率必然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降低.该问题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从时代背景来看,颁布并实施于1990年代初期的“规范”由于更多地借鉴了苏联模式而存在一定的“计划”色彩,对于当时来说,虽然国内也有部分大城市出现了高层住宅,但对于绝大部分城市来说大部分的居住用地开发仍然处在多层、中高层住宅的建设阶段,在当时现实的土地开发状态下很难出现较高的容积率.
3 基于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约束对现行“规范”的调整建议
综上所述,随着建筑建造技术的进步和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攀升,进入新世纪以后高层住宅逐渐成为城市新建居住用地内住宅开发建设的主流模式,但“规范”中所制定的各项标准和控制指标一直沿用至今,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故而越来越不能够适应性现实的居住用地开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基于此,笔者基于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和结论,即在确保居住组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情况下对未来“规范”的调整和修订提出以下两点建议,希冀对解决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3.1 提高居住组团的容积率(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上限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面对现阶段国土资源稀缺、人口基数庞大及城镇化快速发展等基本国情时,都倡导以较高的开发强度来开发城市居住用地.笔者通过对全国主要城市不同规模、不同区位居住地块开发强度的数据统计发现,我国城市居住地块开发强度不管是东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西部城市,其居住用地开发建设都处在一种高容积率的状态,其平均容积率水平基本在3.0~3.5左右,而对于部分地块面积较小的城市居住组团的容积率往往会更高.
一般意义上讲,之所以对居住用地的容积率进行控制,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良好的环境品质以及舒适宜人的空间尺度.而良好的居住环境质量除了日照、采光、空气、卫生等因素以外,关键在于通过满足本研究的重点——人均公共绿地指标来体现.在满足人均公共绿地指标的前提下,如果能尽可能提高居住用地的容积率指标即可以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保障公共环境品质的“双赢”.现行“规范”中的3.5容积率上限值虽然能够确保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但不利于形成更紧凑、更集约的开发状态,仍然存在对城市土地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可能.因此,笔者建议将“规范”中高层居住组团容积率(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上限值由3.5调整为4.5,而中高层住宅建议以满足日照标准为前提对其容积率上限适当进行上调,由于低层与多层住宅不是未来城市住宅开发建设的主导,因此不建议调整(表2).

表2 调整前后的组团层面居住用地容积率(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指标对比建议
3.2 提高居住组团的人口规模上限
居住组团容积率上限的提高必然会带来人口规模上限的提高,这也与国内目前居住用地内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的趋势相一致.从目前来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标准中均将居住小区的人口规模上限提高,如北京市为0.7~2万人,深圳市为1~2万人左右,故而对应的居住组团人口规模也应该相应提高.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人口结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和私家车等因素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家庭人口减少,居住水平提高,公共服务设施逐渐从小区中迁出等因素导致小区已经逐渐变成单纯的居住用地,因此原有规模也应相应有所调整;李飞8]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水平以及未来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的总体判断,提出居住小区的合理人口规模应该在2~3万人.
综上所述,与前文中居住组团层面的容积率指标调整相对应,研究建议未来城市居住组团的人口规模采取上限值的控制方式,其最大值宜根据居住组团用地的规模不同控制在6 000~9 000人,从而确保0.5 m2/人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以此类推,居住小区的人口规模宜为20 000~30 000人,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宜为50 000~80 000人(表3).

表3 调整前后的城市居住用地人口规模对比建议
4 结论
(1)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增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城市居住环境绿化空间的规模和品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但这必须以占用一定规模的土地为前提,这往往又与国家推行的土地集约化利用政策相违背.
(2)根据“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容积率”约束模型计算得出的容积率最大值是完全能够满足目前城市居住组团高密度开发需要的,只是由于“规范”本身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导致了“现实开发”和“规范指标”的差异.
(3)现行的“规范”对于居住组团层面的人口规模限定太低,从而导致据此计算得出的最大容积率也只能在1.6左右,不仅与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住用地高密度开发建设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目前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等相关政策相违背.
(4)研究通过数学建模的手段将研究结果与现行“规范”中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建议未来城市居住组团的人口规模采取上限值的控制方式,其最大值宜根据居住组团用地的规模不同控制在6 000~9 000人,居住小区的人口规模宜为20 000~30 000人,居住区的人口规模宜为50 000~80 000人.
——以天津市和平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