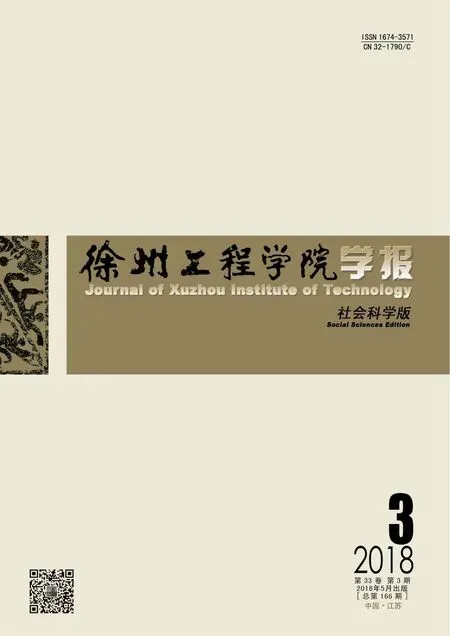“学”何以“问”:古今“学问”之异
汪晓云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
现代“学问”为专业知识,古代“学问”为“道”,“道”为帝王之道,古代“学问”实为帝王学政。
首先,“学”为“学道”。《论语》言“好学”16次,《学而》首言“好学”为“就有道而正焉”;《泰伯》则言“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而”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德”即“道”,即言“学者”所“学”为“道”。
其次,“问”亦为“问道”。《淮南子·修务训》亦言:“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性善”“成仁”“为义”即“合于道者”,“尧、舜、文王”则为“合于道者”之典范。《大戴礼记·保傅》“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好学”即“笃仁”,“问”者为“天子”,“道”者为“导天子以道者”。
第三,“道”为帝王之道。《荀子·君道》明言“道”为“君道”,并以“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言“道”即仁政。《春秋繁露·王道》言“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廖平言“道为君道,南面之学”[1]227。章太炎将“道艺之根”与“政令之原”相提并论[2]17。张爾田《史微》言“道为天子之术”,“道为君人之要术”,然“史统既归孔子,百家废黜,道始失传,遂使千古君人南面之术埋没于神仙方伎之中,迄无一人心知其意耳。苟知道家为君人南面之属,则虽有疑义,皆可推之而通,而老聃、庄、列诸书亦昭然若发蒙矣。此余之所以不惮反复证明也。”[3]13张舜徽在《周秦道论发微》中曾急迫而慎重地表示自己“尝博考群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乎心性。自宋明学者目为传心之要,而本意全失。于是浩然有志阐古义之幽,发千载之蔀,举后起一切传会支离之说,悉摧陷而廓清之。”[4]
第四,“道”“难道”,故须“学”“问”。“道”是统治者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与王权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无道而自称有道非“天道”“圣人之道”而自称“天道”“圣人之道”,从而使“道”具有特殊的隐秘性与欺骗性,古代文献凡言“道”者皆暗言“道”被“盗”,此即“怨声载道”。与此同时,“道”亦变为“难道”。因此,古代道论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道”为帝王政治,更重要的,是帝王无道自称有道,此即“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现在说到封建社会有“殉道士”“卫道士”,“殉道”“卫道”实针对“取道”“无道”言。古代先贤不厌其烦、反复啰嗦地论“道”,不仅以种种方式表明“道”为帝王之道,同时以种种方式揭示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使“道”“难道”,故须“学”“问”。《荀子·大略》言:“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
第五,古代“仁”“义”“德”“性”“善”等皆为“道”,故“学问之道”亦以“仁”“义”“善”“德性”等言。《论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告子上》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前亦言“仁”“义”。《日知录·求其放心》言:“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宋明理学以“善”“德性”“良知”等言“道”,朱熹《论语集注》言:“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第六,“道”为帝王之道,古代“学问”即帝王学政,所谓“学而优则仕”。《论语》“学而”后即“为政”,《论语》9言“问政”,7言“问仁”,3言“问君子”,问“为邦”“行”“耻”“知”各2次,此外尚有“问友”“问成人”“问事君”“问陈”“问交”“问津”“问为仁”,其实皆为“问为政”。《庄子·应帝王》阳子居问老聃“学道不倦”“可比明王乎”,其后即问“明王之治”。《国语·晋语八》言:“敬学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敬学”与“好仁”并列,“政”与“道”同言。《荀子·大略》“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下》明确指出:“政事学问原自一贯,今人学自学,政自政,判而为二,所学徒诵说而已,未尝施之政事。政事则私意小智而已,非本之学问也。故欲政事之善,必须本之学问。”顾炎武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5]98张爾田言:“《论语》首言学,学也者,又汉志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者也。”[3]25“古之道术浑沦,教合于政,学丽于文,离政无以明教,离文亦无以显学。”[3]29
第七,“道”为政,“学问”为帝王学政,故特别强调帝王之道德品性与日常修养,具有日常性与实用性,强调“身体力行”。《礼记·中庸》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邓豁渠《南询录自叙》言:“渠自幼质赣,与流俗寡合,即慕修养。既壮,知慕道学,情状虽累坠,则有凛然与众不同之机。四十二岁,遇人指点,于事变中探讨天机,为无为之学。久久知百姓日用,不知的是真机。学者造到日用不知处,是真学问,遂从事焉。”[6]《文史通义·史释》言:“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人伦日用”“体”“用”皆强调实用性。古代学问用今天的学术术语表述即“政治哲学”“实践哲学”。“文以载道”“道问学”“经世致用”等实为古代学问之概括,这些表述虽然只是在清代提出,但从来都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古代许多看似有差异的概念恰恰具有同样的意义,如“道问学”即“尊德性”,仅以余英时先生所举诸例看,陆九渊“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方以智“德性、学问本一也”“性在学问中”、戴震“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钱大昕“天下岂有遗弃学问而别为尊德性之功者哉”、龚自珍“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等[7]197-203,皆明言“尊德性”即“道问学”,后世学者昧于文字表面,将其看作清代特殊的思想观念,从而忽略了古代学问的根本问题。
第八,由于古代“学问”为帝王政治,古人强调“大学问”为“先王之遗言”“圣贤之道”。《荀子·劝学》言:“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王阳明曾著《大学问》,以“大人之学”“大学”“大学问”言“学问”,言古代“学问”为“亲民”“止至善”“明明德”,指出“大学问”“大乱”“不传”:“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今日。”其实皆言古代学问为帝王“亲民”“明道”。
第九,由于“道”为善政、仁政,“学问”为帝王学“道”、问“道”,古人强调“学问”要“真”,即不可无道而自称有道,而是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四·论学书》言:“学问思辨,即是尊德性下手功夫,非与笃行为两段事。如今人真有志于学,便须实履其事。中间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学问思辨之功。学问恳切处,是之谓笃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后为真学。学而真者,知行必合一,并进之说,决无益于行,亦非所以为知也。”黄宗羲指出,“大抵学问只是一真”,“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
第十,由于“学者”“问者”为帝王“亲民”“明道”,古代“学问”强调“下学上达”。《论语·先进》言:“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论语集注》言:“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8]146-147朱熹《孟子集注》以“下学上达”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呻吟语摘·内篇·礼集·谈道》明确指出:“下学学个什么?上达达个什么?下学者,学其所达也;上达者,达其所学也。”“形而上与形而下不是两般道理,下学上达不是两截工夫。”“下学上达”之方式即“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与“后进”“野人”与“君子”之异,即“下”与“上”之异,“吾从先进”即“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二
“学问”之“问”以“口”为中心,古代“学问”非为“文字之学”,而为“口耳之学”。王阳明《大学问》明确指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
《说文》:“聖,通也,从耳,呈声。”段注“从耳者谓其耳顺”,并引《风俗通》“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周礼》“六德教万民”,言“凡一事精通亦谓之聖”。“聖”强调的“从耳”“闻声知情”实即“口耳相传”。《史微》言“自古人口耳相传之例不明,而古书为后人变乱也”[3]136。
“口耳相传”实与“文字相传”对立,“口说无凭”“耳听为虚”实暗示对民众话语权的打压;“打听”亦暗示对“听”的“打击”,使“听”变为“耳边风”;“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百闻不如一见”等,则将“眼见”与“耳听”“闻”与“见”构成对立,强调“听闻”的边缘性、次要性,以及“眼见”的重要性。显然,由于话语权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对“听说”的贬低即意味着对“读写”的抬高,同时意味着对口语的贬低与对书面语的抬高,其本质是以文字与书面语霸占话语权。
然而,“听天由命”表明,“听”是知“天”“命”的主要方式;“耳熟能详”表明,“耳”是能了解详情的重要途径。“据说”“说法”则表明“说”为“法”为“据”。然“销声匿迹”“默默无声”表明“声”被消失、隐匿,故有“声讨”以“讨回公道”“讨个说法”。与此同时,本为“说道”“道听途说”之“说”变为“胡说八道”“胡说”“乱说”“瞎说”,与“耳”“听”“声”“闻”等相关的日常用语“耳朵”“耳光”“耳垂”“耳坠”“耳聋”“耳背”“耳边风”则暗示诉诸“口耳”之语言被边缘化,官方语言占绝对优势。
与书面语对口说言语、耳听声闻的贬低相应,日常用语则表达出对文字书写的贬低,如“文不对题”“一文不名”“舞文弄墨”“身无分文”暗示出“文”的无用与矫饰;“咬文嚼字” “抠字眼”则暗言对“文字”的斤斤计较、小心翼翼;“字字珠玑”“字正腔圆”暗示出“字”与“王”“政”之关系;“字如其人”则“字”与“人”之德密切相关,此“人”当为掌握文字霸权之人;“造字”“生字”“错别字”“一字之差”则言“字”非天然而为人有意为之,且有错乱;“长字念半截短字念半边”“一个大字不识”“斗大的字不识”“人生识字糊涂始”则对“字”的功能进行讽刺与嘲弄。
文字与书写相关,然而,日常俗语中与“书”相关之表述则多暗言“读书无用”,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暗言“书”不如“话”;“书非借不能读也”暗示“读书”须“借助”“不能读”之书,也就是禁书;“读书破万卷”则暗示“读书”为“破”“书”,而非“全”“书”,“下笔如有神”亦言“写字”为“下”“笔”,“如有神”则暗言非真神;“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则言“书中”“黄金屋”与“颜如玉”为“自有”,也就是自夸,而非实有;“书到用时方恨少”暗示“书”不够“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则暗示读书并不能知世事;“书虫”暗示读书的破坏性;“书呆子”暗示读书无用;“教书匠”则暗示教书者为工匠。古人所强调的“书法”即“师法”“家法”,也就是“学问之法”,正是通过口耳相传与文字相传、听说与读写之异体现的公与私、民间与官方之对立。
“礼失求诸野”,古人强调的“大学问”“真学问”,其实即为“百姓日用”之口语、成语、谚语、俚语、俗语,此即“俗话说得好”。《文心雕龙·书记》即强调俗语谚语的重要性:“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踰于此,岂可忽哉!”谚语、俚语、俗语、方言、歌谣实寓“真道”,此即“童言无忌”“口无遮拦”“小孩嘴里道真言”“打开天窗说亮话”。
与“口耳之学”为“大学问”“真学问”相应,古代文字之学为“小学”,具有微言大义,今人不可以今日之义理解古代文字。清人廖平指出:“经传制事,皆有微显、表里二意,孔子制作,里也、微也,託之文王,表也,显也。自喻则为作,告人则云述。以表者显者立教,以改作之意为微言,故七十子以后,此义遂隐,皆以《王制》、《春秋》为文王西周之政,不复归之制作。”[1]176“微”与“显”“里”与“表”,即中国古代文字之双重意义,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热闹”为“显”“表”之义,“门道”为“微”“里”之义,“无理取闹”即无“内行看门道”,只有“外行看热闹”。“表者显者立教”者,立王政之教也;“微言”与“表者显者”相反,为“大义”“圣学”:“微词隐避,致使大义中绝,圣学晦而不彰。”[1]191“大义”与“圣学”,显然是与王政之教相对立的圣人之道,因与王政之教背道而驰而遭王者镇压。《史微》言经、史为“古帝王经世之大法”,其目的在于“垂训后王”,然却“逆官政”,而“孔子以匹夫尊为万世帝王之师,删述六经,以制义法,其微言大义则口授儒者,宣而明之,所以警戒君人而立教本者甚备,此固圣者之所期而世主之所大不便也。”[3]70,172“微言大义”之目的在于“警戒君人而立教本”,“圣者之所期而世主之所大不便”表明其因触犯现实帝王的利益而被禁止,也就是“逆官政”。刘知几言:“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9]62“直笔”即“见诛”,“曲辞”“不”“获罪”,这正是中国古代叙事几乎无处不为隐微叙事的根本原因。章学诚指出:“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也。”[10]142“六经皆史”[10]1,126,“史学皆经”[11],中国古代经、史,几乎无一不是为“贤者讳”,“史”与“经”一样,亦处处皆藏隐微之义。“隐微叙事”之所以“隐”“微”,乃因其直言则“见诛”或“获罪”,其“见诛”或“获罪”之原因,实为“拟圣”或“僭窃王章”。章学诚发出如是感叹:“嗟乎,经世之业,不可以为涉世之文。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从古然矣。读古乐府,形容蜀道艰难,太行诘屈,以谓所向狭隘,喻道之穷,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岖如是!是以深识之士,黯默无言。”[10]86
“微言大义”与“王政之教”背道而驰,遭王者镇压,因此遂隐而为“小学”。与此相对,言王政之教之显义则为“大学”。“小学”乃相对于“大学”而言,“小学”与“大学”实即“隐微”之义与“显白”之义。“隐微”之义之所以要“隐”、要“微”,乃因其为统治者忌讳。在清人笔下,“小学”或称“六艺之学”,或称“六书之文”,或称“六艺”“六经”,皆取其隐微之义。戴震言“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12]77;章学诚言“盖小学与经学,古人未尝分也”[10]300。刘师培言:“今欲诠明论理,其惟研覃小学解字析词以求古圣正名之旨,庶名理精谊赖以维持。若小学不明,骤治西儒之名学,吾未见其可也。”[13]503而《释名》“虽为小学之专书,实为群经之津筏”[14]483,将“小学”理解为古文字之学,亦因为“小学”作为文字之学,揭示了隐藏在文字“显白”之义背后的“隐微”之义。《孟子·滕文公下》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之为“天子之事”,乃因“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作《春秋》,乃因于“惧”。故《春秋》必然涉及“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而“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乃言“君”无“道”,言“君”无“道”则“见诛”或“获罪”。因此,“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罪我者”即持不同政见者。《春秋》之“辟”“隐”“省”“去”等“书法”,实即屡屡见诸其中的“不可书”“不忍书”“不足书”“不胜书”,皆暗言其中深藏隐微之义。
由于历代统治者皆讳言“小学”之“微言大义”,因而使得“小学”或“六艺之学”湮没不闻。《颜氏家训·勉学》即言:“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戴震言:“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12]47廖平哀叹“六艺之学,原有本真,自微言绝息,异峰端起,以伪作真,羲辔失驭,妖雾漫空,幽幽千年,积迷不悟,悲夫!”[1]173有清一代盛行的考据学,正是建立在对“小学”的解释与对经传“小学”隐微之义的阐释、整理、加工之上。戴震指出:“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路书。纲领既违,伪谬日滋。”[12]77“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作不曾识字。”[15]643戴震之所以言“文字”“纲领既违,伪谬日滋”,“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作不曾识字”,乃因为“今之学者”不了解“小学”的隐微之义,不了解“小学”的隐微之义,即不“识字”,亦不能“明”“六书”与“经学”。梁绍壬亦言:“读书必须识字,今人口习授受,漫不经心,《说文》、《玉篇》等书束之高阁矣。”[16]252
戴震指出:“古人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12]145“故训”实为“古”“贤人圣人之理义”:“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12]214“贤人圣人之理义”即“至道”:“故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12]44相反,“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懼焉”[12]153。此处“圣”与“经”相提并论,其义自明,即“六经皆圣人之所作”、明圣人之道。然“故训音声,自汉以来,莫之能考也,无怪乎释经论字,茫然失据”[12]50。“故训音声”“莫之能考”,乃因“后世道阙,小学不修,故绝于嬴氏”[12]66。“后世道阙”即“圣人贤人”之“道”“阙”。因此,与对“小学”的推崇相应,戴震主张“变乱大学”,其在《经考》中专列“变乱大学”条,提出“《大学》之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明善择善,孟子之尽心、知性、知天”[17]547,548。将“大学”之“明明德”变成了“明善择善”,也就是君行仁道,此亦为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知天的本意。“变乱大学”实即将“大学”所提倡的以君为尊“变乱”成小学提倡的以民为尊。
由于“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作不曾识字”,考据之学在当时显得颇为“异类”,戴氏自己不止一次地发出其骇人听闻的感叹,如《与是书》开篇即言:“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18]182章学诚亦谓:“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外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15]643实际上,正是由于章学诚深谙自己之学同于戴氏,因此而将自己不为世人所同之感付之戴震。仅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就不止一次地发出类似之感叹,如“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频遭目不识丁之流横加弹射”,“今吾不为世人所知,馀邨虎脂,又牵官守,恐未能遂卒其业,尔辈于斯,独无意乎?”
且不说章学诚之所为是否真如其自身所言为“举世所不为”,单以其“为学”与“求道”而言,历代类似于戴震、章学诚之类的感叹并不在少数,王阳明就曾言“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19]章学诚等对戴震的评价也表明,清代像戴震这样“识字”“通训诂而能知道”的学者甚多。章学诚谓“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此“学者”与“学”,皆非今日纯粹学问意义上的“学者”与“学”,而为政治意义上的“道学”。由于政治立场不同,“道学”者所通之“道”亦有所不同,这正是古代经学与史学的内在张力。
“微言大义”之根本为“阴阳五行”“以气寓道”[20]。《悟真篇》言:“报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乱为。”[21]其“悟真”之方式即以“阴阳”为“秘诀”,然“欲向人间留秘诀,未逢一个是知音”表明,“阴阳五行”被误解。实际上,历代大儒多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明代王崇庆言“以气寓道”[22]。“阴阳五行”之所以被误解,“都缘学者自迷蒙”。
“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乃贯穿中国古代叙事的核心,其微言大义之表述方式亦为中国古代叙事一以贯之的传统,不明白此传统,便无法整体把握中国古代学问之核心,亦无法把握中国古代学问的本质精神。清代的考据学,正是中国古代“道问学”在行将衰微之时猛力的挣扎,或者说是即将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所幸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不仅指出了古经的双重意义,亦指出了“解经”或“治经”的方法与门径,这就是以“六书”或“小学”“解经”。章太炎明确指出:“治经学者,当参考古训,诚以古经非古训不明也。”[23]3戴震言:“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12]66章学诚则以《说文》为“经解史论”之本,章学诚《文史通义·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专言《说文》,似言《说文》为“初学课业”。《说文》之所以为“初学课业”,乃因《说文》所“说”,为“经传”之“文”。章氏言《说文》字少,经传字多,依经传之文而对《说文》,“是经传文字未及考正,却已先得一卷《说文缺字考》矣”。此实暗言《说文》乃“考正”“经传文字”。章氏又言“至《说文》所无之字,但空此格,不必填注,盖由古字少而后世字多,经传文字,多有后世传写,因义变化,故不必合也。然亦有《说文》原有其字,而今之传本脱落无存,如……”章氏之意再明显不过,《说文》之字,乃“古字”,也就是“经传文字”!而“初学课业”,乃“经解史论”,之所以为“经解史论”,实因为“经史”所言为“道”,“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化无穷之业”者,“道”也。
以“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为基础,中国古代“数术”“方术”“天文”“地理”“农学”“医学”“兵学”等皆为“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之“微言大义”。历代统治者为了遮蔽“微言大义”的本原面目,将“道”由帝王政治哲学转变为普遍性的道德伦理,同时将“气”变为“器”,从而产生现代意义之“数术”“方术”“天文”“地理”“农学”“医学”“兵学”。由于“微言大义”的存在,中国古代学问无法与现代学问对应,唯有借助于《说文》《尔雅》《释名》等“小学”解释古代文献之“微言大义”,才能显示古代学问之本原面目。
参考文献:
[1]廖平.廖平选集(上)[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章太炎.章太炎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3]张爾田.史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A]//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邓豁渠.南询录自叙[M].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
[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9]刘知几.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0]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1]章太炎.箌汉三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2]戴震.戴震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A]//刘师培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14]刘师培.国学发微[A]//刘师培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15]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A]//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6]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7]戴震.经考附录[A]//戴震全书(二).合肥:黄山书社,1994.
[18]戴震.与是书[A]//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王阳明.传习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0]汪晓云.“阴阳五行”的来历与变迁[J].民族艺术,2009(1).
[21]张伯端.悟真篇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王崇庆.山海经释义[M].万历二十五年蒋一葵尧山堂刻本.
[23]刘师培.经学教科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