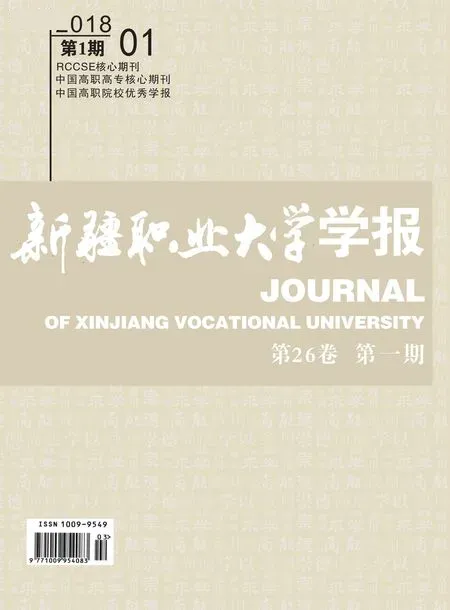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都市书写
张珂欣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中国的新感觉派是现代主义和日本新感觉派影响下的产物,新感觉作家的作品大都以上海为描写对象,着重表现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荒诞的生活,作品风格新奇、大胆。都市生活高度的物质繁荣催生了人们精神上的空虚,新感觉派作家运用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和现代心理分析的手法对这种精神的空虚进行了深刻解剖,与五四以来的文学形成了明显不同的风格,进一步表现了现代都市风景线和都市人生的丰富内涵,虽然这一流派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市文学写作上形成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摩登都市人的缤纷都市生活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因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一跃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外表和内心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衣着光鲜、靓丽的都市人出入于夜总会、电影院和百货大楼等高级场所以不断地追求新的刺激。新感觉派的作家们敏锐的察觉到了这种都市生活带给人们的变化,他们身在其中,常常被其“引诱”,沉迷于享乐。面对着新式的都市生活,人们一方面耽于享乐,一方面又想摆脱对物质的深深依赖,苦苦挣扎依然深陷其中。
刘呐鸥是中国新感觉派的创始人,他从日本引介来了新感觉派。在他的笔下,女性不再是旧家庭中的悲剧主角,而是拥有着明眸,短发,性感嘴唇,身着“那欧化的痕迹很显明的短裾的衣衫”(《风景》)的都市女郎,她们超出自己生活实际所需的超量购物,和男人在“探戈宫”的节奏里摆动着身体,周围的场景,使人觉得“好象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游戏》)。但是这“缤纷”的都市生活不能驱赶走她们精神上的空虚,她们大胆而寂寞,有钱的生活不能再带给她们什么新的刺激,于是主动去寻找新的“爱情”,与偶遇的男性在田野里发生“爱情”,对爱情抱着游戏的态度“忘记了吧!我们愉快地相爱,愉快地分别了不好么?”(《游戏》),甚至对自己的丈夫也是非常的“大度”的“找个可爱的女人陪一两天”(《风景》)。这些都市女郎还把商品交易带进了家庭,在《礼仪与卫生》一篇中,妻子与洋古董商人将古董铺子给丈夫作为换取妻子与洋古董商出游的筹码,妻子又怕丈夫去妓院不卫生便把自己的妹妹做替代品。都市的物质生活已经将人异化,家庭生活变了味,妻子不像妻子,丈夫也不再像丈夫。而小说中的都市男性有着医生、律师等现代都市职业,却没有了从前那种至高的地位,没有了独立的个性,变成女性的玩物。他们有着西方的礼节,身穿笔挺的西装,轮流在都市女郎面前献殷勤。他们渴望浪漫的爱情,却被都市女郎玩弄,惨遭抛弃,因而伤感、颓废,就像比也尔,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梦中的情人,不曾想一句“给我五百元好么?”彻底打破了比也尔的美梦(《热情之骨》)。
在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中上层人与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有着天然的区别。铁轨上火车呜呜的叫着,汽车里儿子亲吻着姨母,舞厅里莺歌燕舞,饭店里烟雾缭绕、歌舞升平,而工人为了生存“把他的力气,把他的血,把他的生命压在底下”,婆婆跟媳妇“合伙”卖淫,只为有口饭吃。上层的人整天游戏人生,到处享乐:看电影、跳舞、打弹子,下层的劳动者为生存葬送生命。
二、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建筑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都市写作,有很多建筑意象,通过作家一系列的文学修饰就具备了美学意义。他们从都市入手,用现代化都市书写,来展示城市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在现代都市中到处充斥着喧嚣、忙碌、奔波和色彩,根据都市建筑、都市景观升华出现代都市所蕴含的各种不安、失落与孤独的精神世界。
20世纪的中国只有上海可以被称为都市,是因为这时的上海不仅保留有中国的传统建筑,还大量新建了很多的西式建筑,这些都市建筑使得上海成为与巴黎比肩的大都市。同时,这些建筑也促进了都市文学的繁荣。新感觉派作家多以“建筑文本”来建构都市感受。本时期新感觉派小说中常见建筑有:(1)以沙逊大厦、上海银行、海关大楼为代表的“万国建筑博览群”;(2)林肯路、哥伦比亚路、霞飞路等交通要道;(3)大光明、巴黎大戏院等俱乐部;(4)咖啡厅、华东饭店;(5)跑马场;(6)惠罗公司、百货大楼等,这些新建的西式建筑,包含了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电影院、各大夜总会为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提供了娱乐消遣的场所,南京路、霞飞路等主要街道则增添了“声光电”等装饰影像,百货大厦培养了上海上层市民的消费意识,众多的西式建筑在小说中熠熠生辉,再现现代都市的繁华与色彩。建筑自身有着提供生存空间的实用功能,同时给小说的故事情节提供了背景,建筑具备了人物事件的定位功能,给故事发生提供活动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位移,形成了故事的发展情节,由此看出,建筑的登场给人物出场奠定了基础,人物所处的建筑又同样反映出人物的身份,建筑的书写起着衬托、渲染的作用,而建筑文本带有着作家编码、读者解码的双向功能。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中几乎每篇都有灯红酒绿的“探戈宫”,高速行驶的火车、男女进出的电影院、塞满“赌心狂热的”赌徒的跑马场和永安百货公司等等,特定的都市空间,表现出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繁华、浮躁、醉生梦死的都市生活。这些大都市建筑不再是像茅盾的《子夜》那样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成为了这故事的对象之一,它们似乎有了生命力,在这场纸醉金迷的故事中竭力成为一个故事的主角。这些“一夜崛起”的现代建筑,迅速成为了人们寻欢作乐的洋场,电影院不是纯粹看电影的地方,那里昏暗的的灯光下掩藏着人们心中的“性欲”,赛马场是认识新的“货色”的场地,富丽堂皇的各大饭店供人们“交际”。这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快节奏跳跃同时又充满着诱惑和欲望的都市一隅。
在新感觉派都市书写中,街道成了尤为关注的焦点。它是一座城市变迁发展的见证标志,是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文化元素的反应。在穆时英的笔下,街上那一排排的五光十色的街灯成了“小姐们晚礼服的钻边”(《公墓》),映衬出都市的繁华。街道是都市“风魔的眼”,从街道这个窗口,可窥视到现代都市的灵魂——繁华却空虚。这些街道像一位位见证人,默默注视着生活于其中的“都市人”,它们感受着都市的生命力,品味着都市生活的真真实实,虚虚假假。由此发现,新感觉派作家在小说中充分使用建筑的使用功能,并在娱乐消费中体会人生的寂寥、颓废和失意,从而表达出建筑所引申的审美意义。
三、物欲横流的都市欲望
繁复多元的都市文化常常让人在辨别是非时遮蔽了双眼,往往无意识地随波逐流,物的快感之后又是无法摆脱的苦闷和绝望。在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人物,虽然常常身居现代都市,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享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设施,奔走于都市的快节奏中,但又分明被挤出了都市生活的轨道。不甘寂寞,却因为享受奢侈的生活而拮据不堪,因为奔波于所谓的“都市生活”而感到深深的疲倦,于是随波逐流,不知所措,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可以给予自己一时新鲜刺激的物质的享乐时,则往往又表现出对大都市的渴望、对物质的贪婪和对摩登女郎的深深迷恋。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使他们纵欲过后迷失了自我,不断地寻求刺激和麻醉,放纵、逃避又使他们坠入精神荒原。
刘呐鸥的《游戏》中,步青感觉到“我觉得这个都市的一切都死掉了”,这死了的一切有“轨道上的电车”“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余下的则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姑娘肩膀上的山猫皮变了一只老虎跳将出来,使步青猛吃了一惊 。忙碌的城市生活,难掩步青精神上的空虚,繁华过后是遮不住的落寞,心爱的女人要跟别人走了,只留给他一夜梦幻。
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就是生活在上海这十里洋场的人们的典型代表,破了产的胡均益被“吹成野兽,吹去了理性,吹去了神经”,这位近代商人的心碎了;失了恋人的郑萍,嘴唇碎了;失了青春的黄黛茜,“心给那蛇吞了”;怀疑主义者季洁被各版HAMLET笑着;失了公职的缪宗旦的地球末日到了。可是周六的晚上,这五个人又都变了快乐的人儿,一同游进了皇后夜总会,在那里没有破产、失业,他们尽情享受着周六的夜晚,无休止的舞着,放肆的笑着,这笑来的莫名其妙,乐师约翰生的伤心无人体会“我要哭的时候,人家叫我笑”。深夜结束了,夜生活的人走了,“剩下来的是一间空屋子,凌乱的,寂寞的,一片空的地板,白灯光把梦全赶走了。”夜总会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梦,喧嚣过后,生活还是继续着前一天的步伐,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施蛰存比较前两位作家的作品在取材上更为宽广,还包括上海附近一些城镇生活场景的书写,他笔下的巴黎大戏院充满摩登色彩的都市诱惑,已婚的男性约会美丽的都市女郎,接到女郎递给他的手帕,先闻了手帕上的气味,然后在黑暗的掩护下他舔了这块手帕,似乎是“抱着她的裸体”,用这样的行为以满足自己内心的“性欲”。终究因为心中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得他“发乎情止乎礼”。《春阳》中为了千亩的土地抱牌位做亲的婵阿姨在春阳和煦的日子里内心萌动了想要恋爱的念头,她渴望有一个男人陪伴她,但是她不想浪费了自己用毕生的幸福换来的财产,所以始终吝啬。金钱和传统道德观念终究打败了本能的欲望,占据了上风, 萎黄的容颜使她失去了冲破寂寞的勇气,只能继续在寂寞中独身禁欲。《雾》中从小城来的素贞小姐的传统的观念与在上海生活的表姐妹对电影明星的崇拜形成鲜明对比。享乐是都市的代名词,纵欲是都市人的风向标,无所顾忌,消遣娱乐,使得都市成为一座精神的空城,物质战胜一切。这里有着“酒精的刺激味”“浓洌的色情”(《夜》),在反理性的极度浪漫行为中,人们抛弃了有人性的自我,道德价值观念不断被城市的奢华生活冲击着,都市中男男女女,深深陷入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博弈之中,迷失自我。
新感觉派作家将目光聚焦于都市人灵魂的不安定状态,以此,折射或呈现都市人的生存悖论。他们对都市生存两难状态进行揭示,面对复杂多元的都市文化,面对是非难辨,善恶不分的的都市人生,都市人迷失了自我。在一种都市阴影的笼罩下,人生充满着孤独、漂泊、失意。都市令生活在其中的都市男女快乐并痛苦着。他们在城市中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生活,总是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左右着,支配着。都市令人黯然神伤,也就无可置疑地流露出一层浓郁的感伤色调。
四、物质对人性的异化
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下,出现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这些先进的公共设施和有序的管理方式,很快使上海本地的人民“臣服”于此。物质的高度繁荣一方面给上海带来的是方便快捷,一方面也使得人性在物质的作用下异化。弗洛姆认为人性即人的本性,它包括吃、喝、性等各种最基本、最原始的需要,其通常表现在人所处的情景中所体现的生存的欲望和本能的需求,同时弗洛姆指出,这种基本的原始的需求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所以人对这种需求有高度的追求热情,并且已经远远超出了“自我保存”,即人的异化的外在表现是人的生存欲望和需求的异化。内在的异化表现则是人心理的异化,即人本身与所处环境的分裂,人虽然生活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却不能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这样的人就像一只洋葱,能将其皮一层层剥开可找不到核心,他们的核心已被异化了。”①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34-335.
当时生活在上海的都市女郎和都市男子在这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中渐渐地迷失了自己。女人沉迷于购物带来的快感,这大都市为其提供了百货商场方便她们的购买,汽车可以让她们将她们的“战利品”省时省力地送回家,购物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是供这些都市女郎打发她们的时间,为她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消费观念是物质对她们生存欲望和本能的侵蚀,过度的消费欲使的她们不停的购物,已经严重超出了“自我保存”的冲动,上海的各种霓虹灯广告牌更进一步的刺激了她们的消费欲望,使她们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和纯粹的“消费者”,她们的生存欲和本能外在被异化。除了购物,与男子的恋爱游戏也是她们生活中一件极其愉快的事情,她们不停地寻找男子进行“恋爱游戏”,这种游戏的态度体现出都市女郎的不安和紧张感,她们与自己喜欢的人度过美好的夜晚,然后选择一个有钱的人结婚,她们怕失去这富裕的生活,这是她们心理的异化。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她们获得健全的人格,反而使她们陷入了更深的“生存的两歧”①“生存的两歧”:是指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是经常处于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之中”。转引自李红珍.人性的异化与回归:弗洛姆人性异化论新探[J]东南学术,2013,(3):131-136.状态中,内在外在不断地被异化。男人则是这种人性异化的牺牲品,他们虽然有着自己独立的事业,却没有了独立的精神,这是物质文明对男性人性的异化,这些有工作的男性无法满足女人越来越膨胀的欲望,所以他们渴望美好的爱情却爱而不得,于是即使知道自己是“消遣品”,却依然在女人的邀请下一次次“束手就擒”,不能维持正常的恋爱关系使他们感到失望甚而是绝望,于是他们在黑暗灯光的遮掩下通过想象或嗅女人的手帕以满足他们内心对性的渴望和精神上的愉悦。
上海的物质文明没有带来精神上的文明,女人因物质的追求放弃爱的人,嫁给有钱人,精神依然空虚就通过寻找新的男人企图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却发现更加得空虚,二者循环往复,使女人彻底的陷入“生存的两歧”状态。男人渴望时髦女郎的青睐以获得完美的爱情,却负担不起女人的消费支出,于是甘愿成为女人的“消遣品”以获得心灵上的满足。男人、女人彼此相互“利用”,他们是生活在大上海的“空心人”。
五、结语
新感觉派作家用自己的笔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异化的现代化大都市,一方面物质的高度繁荣带给人们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都市生活,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获得了极大的物质满足;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中的男男女女在高度的物质文明驱使下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分裂和人性扭曲。都市中的人们既想要获得物质的极大享受,又想要获得精神的最大愉悦,从而导致他们人格的分裂,追求物质舍弃情感,再以寻欢作乐的方式填补精神的空虚,自我放逐,于是肉体沉浸于性和消费,灵魂却四处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