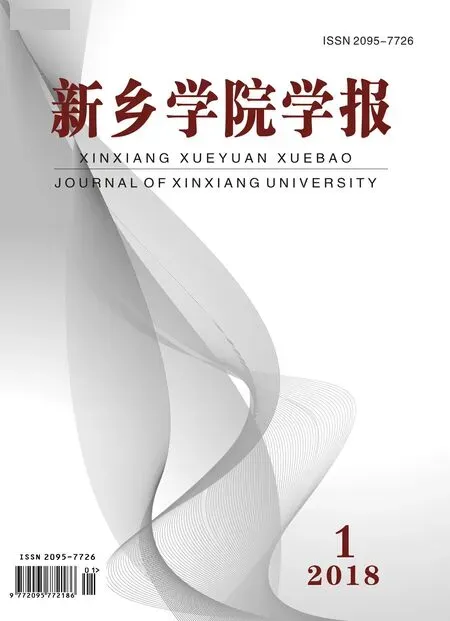试论苏童小说里的逃亡主题
——以《米》为例
张子晴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苏童的写作既没有启蒙角度的叙述压力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也没有刻意营造苍凉无力的文化失落感,他进行的似是一场无助的写作。他穿越充满罂粟气息的南方,穿越自己颓败谨慎的童年,仓促地来到自己的文学世界,悲壮而满足。这似乎是其作品中重复出现的“逃亡”主题的原型。苏童在和林舟的访谈录中说,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具体来说,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成长的少年,似乎喝醉了酒,始终在逃亡的路上。
苏童还说,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他的人生的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在苏童营造的美学空间里,重复的奔跑即是重复的逃亡,每一次都事关重大,每一次都在时间、空间的极限中侥幸逃脱。可逃到哪里去呢?作品叙述了逃亡者回到原点、无处可逃的绝望,或者追捕者与逃亡者虚假的关系——“各自消失在对方的监视中”[1],逃亡同时也是接近原点,似乎从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一趟趟的逃亡完成了人类生存“永劫回归”圆圈。
一、 逃离家园后的无助
《米》写的是五龙逃亡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追捕者与逃亡者虚假性关系的命题。逃亡者五龙来自农村——枫杨树乡,在城市兜兜转转后仍然渴望回归家乡。“五龙”谐音“乌龙”,逃离家园的五龙最终回到了家园,这一场逃亡似乎从未开始,逃脱了乡村的灾难,又身陷都市的罪恶,所有的一切只是子虚乌有的生存游戏。
米是生存最重要的粮食,是逃亡的圆心,苦难、欲望、罪恶、生之挣扎、死之灾祸都从这里发源,然后辐射出去,构成了一个家族、一帮码头兄弟的灾难历史。五龙为了吃米逃离家园,来到城市,自然而然地来到了米店,又莫名其妙地来到了码头。随着五龙内心欲望的不断扩张,“米”的含义也在不断拓展:“米”隐喻着精神食粮、钱财和地位,“吃米”隐喻着满足、能力强和征服,“米”更是一个渴望、毁灭和无所不包的灾难之源。
五龙是以一个佯睡在火车上的寒酸青年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显得很突兀,同时也很危险。逃票的五龙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抓住,他不得不拼命逃亡,逃到有米吃的地方——城市。
如果说五龙第一次逃亡是为了逃避饥饿,那么他的第二次逃亡便是为了逃避死亡。刚到城市的五龙拍了拍路边熟睡的男人的肩膀,带来了同是家园逃亡者的问候,可男人竟然已经死了,大惊的五龙拔腿就跑。文中写“后来五龙一直在陌生的街道上奔跑,死者发蓝的脸跟随着,像一只马蜂在他后面飞翔”,肯定了逃亡的意义。但后面遇到的“码头兄弟”阿保却否定了逃亡的真实性,他笑着,不可置信地看着五龙,无法相信死人追人的真实性。死人的追捕对别人来说是玩笑,对五龙来说则是避无可避、无处可逃的恐惧,在多年后,他还梦见过那个饿毙街头的男人。五龙回忆起自己漫长的逃亡经历时,说他总是看见陌生的死者,那个毙命于铁道道口的男人,那个从米袋里发现的被米呛死的孩子。
苏童最著名的文本《妻妾成群》写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旧时代女性的故事,苏童说是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是“痛苦与恐惧”的故事,这份恐惧延续到《米》中就是反复出现的“死人”的追捕形象。这是苏童虚构的恐惧,也是五龙精神里最真实的恐惧。五龙拼尽全力地逃亡,前面是欲望的幽谷,后面是死亡的深渊。可人的一生无非都是走向死亡的过程,逃亡似乎是对这一“预言”的反抗,可无人能逃脱这“预言”的诅咒。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从第一次卖血以后,就在疯狂地透支生命,愈是重复地卖血愈是加快了许三观的死亡。显然,五龙的形象更像是一个逃避生活本身的醉汉,他一无所有又想拼命占有,他拼尽全力的同时也放弃了一切。他狂奔着,怒吼着,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
五龙老实本分的农民形象在长期的忍辱负重中受到严重的扭曲。他以忍辱负重作为生存的智慧,代价是无时无刻不在压抑本能,内在的精神也愈发残缺。城市的夜晚是充满诱惑的,是躁动不安的。睡眼惺忪的女人向五龙招手,五龙飞快地奔跑了几步停下来,心里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这次不由自主的逃亡又是为了什么呢?答案有些苦涩:在五龙尚未拥有“皮鞋”的时候,连欲望也是被遏制的。在后期的作品《河岸》中,库东轩和此时的五龙一样,因丢了地位而丢了欲望,不得不采取残忍的自我束缚。库东轩带着阉割的决心损伤了生殖器,这样是道德的表现,也是群众玩闹的对象。面对外界不公正的压迫,库东轩逃到了飘忽不定的船上,远离城市。而五龙则要血债血偿,他认为罪恶的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人自投罗网。
逃离家园意味着重生。在陌生的城市里,物质上的满足阻挡不了精神上的严重扭曲。织云和六爷畸形的爱恋关系更刺激了无助的五龙,当他终于当上米店老板时,“他的各种畸变的本能和破坏的欲望也就同时找到喷发的契机。他本能的破坏性由自我转向外部世界,以变本加厉的施虐方式补偿曾经受虐的缺憾”[2]。
二、 身份奴役下的空虚
五龙找到米店后,他的逃亡似乎暂时结束了,接下来的则是精神逃亡。五龙想要一双皮鞋,想逃脱可怜的底层生活,这是他对自己身份的第一次逃亡。织云刚提出要给五龙买鞋的时候,五龙虽然嘴上客气着,实际上心里已默许。他想,我再穷再贱也是血肉身子,怎么会喜欢受冷呢?在他看来,人和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甘愿挨冻受苦,这无疑是对旧有等级制度的挑战。织云真切、善良的问候给五龙的心里带来了快乐,可这快乐马上被冯老板的态度打破了。冯老板让织云给五龙买双结实耐穿的鞋,别买皮鞋,因为五龙是干力气活的人。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却激起了五龙内心的仇恨。五龙马上看出了米店没有人真心对他好,他残忍的复仇马上拉开了序幕。
五龙以跳槽威胁冯老板,得到了五块大洋,可去街上转了一圈又空手而归,不免遭到冯老板的嘲笑,也证实了他最初的推断——干体力活的人不能穿皮鞋。晚上,五龙看见自己在漆黑的街道上狂奔,听见自己恐怖的叫声回荡在夜空中。这样失落、无助的狂奔,带着必死的绝望,带着重生的希望。皮鞋在苏童巧妙的安排下已成为身份的象征。阿保有皮鞋。五龙去看阿保的尸体时,认出了阿保敞着襟的黑绸褂子,觉得他还应该有一双皮鞋,它曾经残忍地踩过五龙的手。六爷也有皮鞋。当织云被问到肚里的孩子时,她偷眼瞟了下六爷,很快又躲闪开,眼睛很茫然地盯着他脚上的皮鞋。甚至织云刚出现时就穿着一双高跟鞋,“踢哒踢哒”地走着,漫不经心。草鞋是底层人民的象征,而穿着有洞的胶鞋的五龙,更是逃亡者的形象。逃亡者只顾着逃命,怎么会穿着一双好鞋?鞋的破损程度更体现了逃亡的迫切性和无意识性。
这样就可以理解五龙对满口金牙的痴迷了,一双简单的皮鞋已经满足不了他迫切向别人证实身份的愿望。他指着橱窗里的那排金牙说,把我的牙敲掉,换上那一排金的。换牙的过程更像是五龙在现实中重生的过程:五龙满嘴血沫,他的整个身心在极度的痛楚中轻盈地漂浮。他漂浮在一片大水之上,恍惚又看见水中的枫杨树家园,那些可怜的垂萎的水稻和棉花,那些可怜的丰收无望的乡亲,他们在大水的边缘奔走呼号,他看见自己背着破烂的包袱卷仓皇而来,肮脏的赤脚拖拽着黑暗的逃亡路。精彩的描写,刻画出了五龙无家可归的窘境和无片刻安宁的心。一口金牙是五龙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是“对自我身体政治性的装潢”。葛红兵说:“‘文革’的时候,大多数人相信,到乡下劳动——通过劳动锻炼,改造知识分子的身体——可以改造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五龙则相信,金牙可以改造他的贫贱出身,让他从流氓无产者上升到富有阶层征服者。”[3]
五龙寻求皮鞋和金牙的过程也是被耀眼的身份奴役的过程。他漫长的换牙过程更像是被奴役中的仪式:他回忆起枫杨树乡和亲人,可并没有获得归属感。耐人寻味的是,他看不清楚熟悉的家人和孩子,那城市生活的收获对于他来说又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亲属关系也不及枫杨树乡的诱惑,不及尊贵身份的认可,甚至带不来心灵片刻的安宁。
三、 始终在路上的还乡
逃亡的人渴望还乡。不管是《1934年的逃亡》中的“我”,还是《逃》里面的“我”的叔叔陈三麦 ,都将还乡看成一件美好的事情。可逃亡本身都并非真实,还乡的可能性更大打折扣,但这始终是逃亡者的精神寄托。五龙还乡时要将一车最好的白米带回家,然后在自己购置的土地上生活。不难看出,小说的“逃亡”并非真实,五龙逃离故乡的同时渴望逃离城市,他始终回忆起枫杨树乡的稻田,又为茫茫大水带来的灾祸感到难过。他在垂死之际躺在儿子准备好的火车上,可火车仍然往南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逃亡都是相逆的,“但时间错置和空间位移却是叙述的重心不在于对故乡的失落或改变,而在于对城市(异乡生活)的厌弃和存在性烦恼”[4]。
五龙梦中的枫杨树乡村是一片颓败的景象,茫茫大水侵占了宝贵的农田,摧毁了房屋,人在种种困境中艰难地存活着。但他并不迷恋故乡,并没有对其进行乌托邦式的想象。即使是生存在枫杨树故乡的人仍不明白自己的归属,个体“我”仍然处于被放逐的状态,始终在寻乡的路上。苏童在《1934年的逃亡》中写道:“当我想知道我们全是人类生育繁衍大链环上的某个环节时,我内心充满甜蜜的忧伤,我想探究我的血流之源,我曾经纠缠着母亲打听先人的故事。”
五龙时常感到“依然在路上,离乡背井的路又黑又长”,五龙的精神上始终没有归宿,他所有竭尽全力的逃亡不过是无望的挣扎。更深刻地说,他逃避的不是某一具体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并非物质食粮、精神食粮——地位,他逃避一些无形的恐惧——无家可归的失落感。苏童在写完这部小说后说:“《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喘息、狂喜或痛苦的叫声。”[5]
显然,《米》中的五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善恶形象,而是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的化身;小说并非叙述底层小人物的反抗,而是暗含着“人”觉醒的过程。这个“人”是五龙自己,也是千千万万逃离乡村来城市的普通人。逃离家乡这个选择是无奈的,但问题是,即使五龙拥有了身份,在城市里过得风生水起,他本身居无定所的漂流感并没有被很好地安顿。他意识的深处永远是认可自己属于枫杨树乡的,他有传统意义上很强烈的“叶落归根”的想法。
不幸染上花柳病后的五龙,“意识到了自己唯一的也是真实的恐惧——死”。他抓着米从头顶往下灌,感受圣洁的米流经自己身体上的伤疤,居然渴望米能救赎他肮脏的灵魂。在对枫杨树乡的回忆中,他感受到枫杨树乡相比城市是一块安全的净土。五龙还想自己重新回到久违的黑土上走一走,甚至愿意将自己毕生积累的钱财用来买地,他沉浸在自己衣锦还乡的假想中不能自拔。他要求儿子拉一火车的白米送他回家,他躺在米堆上,听着火车滚过铁轨的“哐当哐当”的响声,安稳地离开了人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龙是幸运的,还乡对他来说并非必将实现的理想,还乡更多地代表了魂归故里、叶落归根的想象。这是一种宝贵的归属感,和寻根文学中理性的寻求文化之根不同,这是逃亡在外的人们的精神归宿。可五龙在城市兜兜转转的这一趟苦旅,是一场虚假的逃亡,失魂落魄的五龙仍渴望魂归故里,可惜始终在路上。
四、 欲望之花:人性之恶
“欲望”一词并无褒贬,此处所指的是“占有欲”和“情欲”。五龙作为家园逃亡者,始终怀着还乡的热情,也对城市的罪恶抱有反抗性的心态。他认为他是米店的假人,他的真人还在枫杨树的大水里泡着。他否定自己在城市存在过的真实,但欲望的真实又令他苦恼。欲望的根本在于情欲,五龙渴望占有织云和绮云进而成为米店老板,他的占有欲更体现了他近乎变态的情欲。但农民阶级出身的他自有其简单的欲望,仇恨的和情欲的,都无法上升到理性,所以他的欲望带来了复杂的性关系。
米由于五龙对它的渴望而显得如此宝贵,因为为之亡命充满那么多的苦难。米同时也是喷薄欲出的欲望的化身,为之生与死的意志携带着层出不穷的罪恶,使五龙在这场逃亡中变得无比健壮。织云的虚荣是命运中的毒瘤,她为仅有的处境沾沾自喜,她以玩弄男人的感情为荣,必将为男人的虚荣吞噬掉。绮云偏安一方,守了米店一辈子。这两个女性的命运被五龙这个无赖改写,他从灾难遍地的乡村逃到罪恶堕落的城市。在大水淹了水稻的生存困境中,五龙逃向城市,以朴实可靠的农民工形象得到了米店的经营权。但五龙体现出来的人性之恶,使得冯老板在死前也要戳瞎五龙的眼。这里面或许隐藏了某种农村对城市的仇恨或者城市对农村诱惑的意念,但“城市更像一个逃亡的终结,一种现代性的新型罪恶的重新开始”[6]38。
逃亡后反抗的欲望来得很快,也很残酷。一封匿名信解决了欺负过五龙的阿保,当然这里也有对织云的暧昧情绪。五龙忍住笑走到店堂内,米店这家人在他眼里的形象是脆弱而可笑的。这是胜利者的微笑,逃亡者终于掌握了城市间人们生活的薄弱环节,就像一只贪婪的大老鼠发现了米仓一样窃喜着。随着他的强大,米店一家在他的眼里也是可以戏弄的对象。在织云离开米店去找六爷时,他顺理成章地占有了绮云。他的逻辑很怪,认为米店一家三口,每个人都给他留下了伤口。
五龙逃亡后的反抗,以占有织云开始,继而占有了绮云,掌控了米店和船帮,逆袭而上的五龙围绕着米走完了自己的复仇之路。他不再是那个没米吃拼命逃亡的穷酸青年,他掌控了米店。“米”成为他权力的象征,“米”也是他独特的性工具,“米”还是他荣归故里的标志……重复出现的米同时也是一种时间、空间静止的暗示,“米”并没有增多或减少,却一直承担了诸多象征性的意蕴,“米”始终是粮食而已,救活了他也成就了他,最终也是他的葬身之所。
五龙在物质上的占有欲不断扩大,但“米”对他始终意味深长。他在释放自己欲望的同时,对米仍然有不可割舍的爱恋,他觉得唯有米是世界上最具催眠作用的东西,它比女人的肉体更加可靠,更加接近真实。五龙在床笫之欢中不想关灯的细节和《妻妾成群》中的陈佐千相似,是一种目的更明确的做法:光亮可以帮助他保持清醒,在一种生活开始之前他必须想透它的过程、它的未来。
冯老板把织云嫁给五龙的时候,五龙受宠若惊地同意了,可殊不知他正跳进一个巨大的圈套。运米之行充满着死亡的气息,冯老板故意少给的钱财断送了五龙的一根脚趾。五龙觉醒后变得凶残,他粗鲁地对待织云,愈是野蛮愈能证明他强大的征服力。在织云愤怒地咬断了五龙另一只脚趾后,五龙对织云的情感越来越复杂了。终于在米仓的诱惑下,五龙第一次尝试了用米来“清洁”女人的身体,米已经不是简单的生存粮食了,它是五龙心理的象征。苏童自己也坦言写《米》是“为了残酷而残酷”。他说:“我在主人公五龙身上寄予了心中一种来历不明的愤怒,它发泄在所有人身上,甚至是善良的人。我借描述一个农民流落到城里的命运,将这种愤怒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它的指向有时候是人性恶,有时候是伦理。”[6]57
五、结语
五龙作为家园逃亡者,始终怀着还乡的热情,也对城市的罪恶抱有反抗性的疏离感。随着欲望的升腾,他一步步地占有了织云、绮云、米店和码头,但他仍然是失落和颓唐、渴望还乡的。正如他最初不知道火车将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一样,他的逃亡之途充满了扑朔迷离的不真实感:从未有真实的人追捕他,而他却无缘无由地先逃跑了。逃亡的虚假性也带来了还乡的不可能性,即使最后带了一火车米“衣锦还乡”,仍然在半路上身亡。故乡的亲人和他自己,没有一个人能证实这次还乡的真实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龙最沾沾自喜的金牙也被儿子撬走了。
《米》这部作品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病态的象征符号:五龙对应欲望,织云对应虚荣,绮云对应野心,冯老板对应势利小人,六爷则对应残暴的统治阶层……还有那个不起眼的阿保,虽然死了,但他的阴影一直贯穿全书,终于在织云的肚子里得以重生,以六爷唯一的继承人身份拥有了码头。五龙陷害了阿保,活在阿保的阴影下也是一种惩罚。
《米》中那种令人窒息的逃亡主题似乎也在表明五龙在一次次的逃亡后渴望救赎的心理。在苏童后期的《黄雀记》和《河岸》中,他通过“罪与罚”的命题来表现“逃亡”和“赎罪”,传达出对人性和存在的本质的质疑。苏童在文学作品中超越现实去理解人的本质和痛苦,理解历史,理解事物的存在,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造成逃亡现象的社会的反思。
[1]陈晓明.无边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99.
[2]颜敏.破碎与重构——第四章 颓败的历史景观:新历史主义小说[J].创作评谭,1997(3):54-59.
[3]葛红兵.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236.
[4]张学昕.灵魂的还乡:论苏童的小说《米》[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3):61-63.
[5]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21.
[6]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