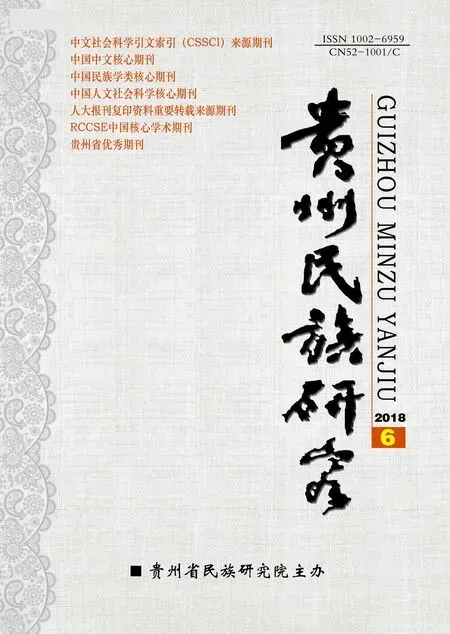国外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复兴宗谱研究
杜玉红 田有兰
(1.贵州理工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贵州·贵阳 550003;2.云南财经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昆明·云南 650221)
一、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复兴的前期发展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初欧洲的古物学、语言学和方言学,以及后来美国的人类学。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欧的古物学家试图将人们对消失对象的怀旧情结与对进步的承诺相结合进行研究。[1]他们记录即将灭绝的物种,从过去收集的碎片来维持它当前的存在。18世纪后半期收集方言词汇变得流行起来,也是更广泛地收集来自过去或现在的元素过程的一部分。方言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在这方面,古物学家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政治力量很快跟着效仿,第一个对语言和语言使用的国家语言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可以追溯到法国革命的后果,当时的革命政府开展了一项任务,调查国家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言。[2]方言学家对语言维护不感兴趣,相反他们试图记录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3]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和复兴的研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如博尔斯和后来萨丕尔沃尔夫的工作,或者更普遍地拯救人类学研究,如格鲁伯和克利福德的研究。[4]虽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北美20世纪早期出现的种族主义,但是其拯救模式的一个模糊之处在于它认为收集和集中的东西对人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另一个不同的背景下,上世纪70年代,施特劳斯认为传统社会的消亡预示着人类学未来的命运,这也是类似当代语言学的先驱。[5]
语言描述的基本原理最初是受到美国西部边疆消失的刺激。在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中,正如语言学的几个领域一样,类似的动力学正在发挥作用,他们的研究是基于鲍曼的前提:人类的独特之处是多样性和变化性。[6]用美国人类学家格鲁伯的话说,在20世纪早期,进步文明的前沿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很快就被人们意识到了,这为很多人奠定了人类学在早期研究的基调和方法。[7]当时的重点是为后代记录那些仍然可以记录下来的东西,并且这一行动在濒危范式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范式关注一个社会规划:语言恢复是重建一个健康的社区环境,对个人的健康、福利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8]
然而,社会语言学传统却受到了最高的关注度,语言社会学家费什曼在工作中成长起来,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北美犹太社区中保存意第绪语。费什曼认为语言相对论和决定论之后,沃尔夫的第三种类型是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支持语言多样性。语言逆转被宽泛地解释为“对当地受到威胁的语言社区的援助理论和实践,这些社区的本土语言因为两代人之间的连续性是消极的,而且使用母语的人越来越少。”[9]。除了术语外,费什曼在语言逆转方面的努力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量关于语言恢复的工作中,这一点我们快速浏览一下语言学中有关语言濒危和语言复兴的参考书目就可以得到证明。在他最近的出版物中,费什曼自己使用了“语言复兴”这个词。[10]值得注意的是,费什曼早期关于双语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研究将一个社会语言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应用到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和复兴这个话题上。接受过社会学培训这一派的社会语言学家指出,一种处于次要地位的语言,要么被替代,要么标准化。替代(或同化)与在其他地方被描述为语言死亡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标准化则需要语言标准化以及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作为正常交流语言而强制使用的一个过程。[11]拉蒙特呼吁双语逆转,实际上与费什曼后期的语言逆转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也许是为了支持这个事实,关注的焦点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在提升双语的结构性条件上。[12]
二、描写语言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濒危
这里应该关注三个极其重要的领域,首先,语言多样性是描写语言学和纪录语言学中一个陌生的硬伤,对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应该立刻引起整个行业的重视。致力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工作的语言学家也强调需要了解这些特定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处理的数据类型,因此,需要根据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话语者的流利程度以及他们生成的数据类型把话语者和被调查者进行分类。[13]其次,语料库已经成为(或者至少成为19世纪20年代)语言学资助项目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和汉斯濒危语言项目(HRELP)。最后,语料库和少数民族语言复兴是使语言学与社会相关的重要方法,并且在过去的几年中,除了双语教育研究外,少数民族语言濒危比任何其他语言学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更多媒体的报道。奥斯汀的书或哈里森的流行专栏等也证明了这一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要求学术机构对知识库做出贡献。[14]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语言复兴的三个主要原则可以用以下方式总结:语言消失、死亡或濒危是可以测量的,并且越来越重要的是,它是可量化的。当后者的元素还没有在语言学家中间产生共识时,对于许多语言学家来说,它就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焦点。
当罗宾斯和乌伦贝克出版《语言濒危》一书时,他们也强调了美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环境,但没有提及欧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15]但是我们知道,关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学术辩论的出发点在拉丁美洲。1991年,一群在中美洲和墨西哥工作的语言学家在美国语言学会(lSA)年度会议上提出了他们认为的令人担忧的问题: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语言在逐渐消失。美国语言学会会议论文被翻译成一系列的短论文,标题为“濒危语言”,并在第二年出版了《语言》一书。[16]
上述文章中提供了关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可以量化的观点,并用大量的数据来说明目前语言的濒危程度,这些关于语言濒危的数据很多学术论文和媒体上仍然在使用。在讨论关于语言学家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种语言濒危悲观的未来之前,克劳斯认为,以现在语言濒危的速度进行合理地计算,那么即将到来的世纪将会看到90%的人类语言消失。[17]这个过程,用一个生态的类比是完全恰当的,就如动物界和植物界同时丧失多样性一样相互关联。[16]克劳斯自己认为,“语言濒危”这个词大概是起源于生物学的使用,并把濒危鸟类和濒危哺乳动物相类比于濒危语言。为什么人们对这种相对温和的威胁有更多的关注,而濒危语言多样性威胁的影响远远大于世界生物多样性,为什么我们的语言学家比生物学家更安静呢?[17]
三、少数民族语言复兴与语言学
然而,语言学家所做的是把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工作变成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有共同的标签,共同的参考文献,并在其旗帜下把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们联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它基于一种通过濒危语言论述来构建的紧迫感,以及关于某些事情可以并且必须完成的观点。南希在秘鲁从事教育工作,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她的工作上,她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土著语言的复兴值得一做,不但是为了讲这些语言的人,也为了想要了解这些语言编码和表达方式的人。[18]
克雷格在1992年的《语言》系列论文中讨论了尼加拉瓜的新桑地诺政府国家计划解决土著问题,即社会和文化问题,她参与了“拉玛语言文化项目”,一种在语言灭绝的过程中拯救语言的尝试计划。在有利的宪法环境下,项目本身被与之紧密联系的社区成员协会和语言学家认为是成功的。如前所述,《语言》中的系列论文包括所有的濒危语言元素,今天当人们谈论语言复兴时仍然会提到这些因素——最显著的是濒危本身的生物隐喻以及濒危的数据和程度。后来,法国语言学家克劳德宣称,每两周就会失去一种语言。[19]问题的进一步戏剧化表现是,像迪克森这样的语言学家呼吁语言学重点关注正在消失语言的语料库——甚至把这当作每个有自尊心的语言学家的一项强制性任务。[20]
语言学家的工作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随着时间的积累发生的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换句话说,语言学家不仅仅引起了当地扭转语言转变的努力,而且通过一系列关于人类知识形式将随着语言的消亡而消失的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和热情。在对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和语言复兴的全面叙述中,最后的话语者是最重要的。最后的话语者的照片,比如,最后一位说曼岛语的人在纳尔和罗梅尼的《消失的声音》中被使用。最后的话语者也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就像在墨西哥的阿亚马内诺语的最后两名话语者一样。这一事件在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甚至是报纸的嘲讽,如《卫报》 《电报》 《英国每日邮报》。[21]彼得拉迪福吉德认为,语言的保存和维护是一个多层面的话题,有不同的意见是可能的。这些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与许多负责任的语言学家所持的相反,也是很正常的。他补充说,与动物物种的比较是对我们的情感的吸引,不是我们的理由。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家们应该远离政治。[22]
这里的中心观点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争论:语言学家该怎么办?客体本身既不受质疑也不存在争议。哪种干预类型的讨论在这个领域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于此本文对其利弊展开了辩论。事实上,这是一场语言濒危领域重要的、归属化的巨变,将辩论从客体转移到与该对象的相互作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更多的语言学吸引在聚光灯下,同时奠定这个新成立领域没有争议的最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