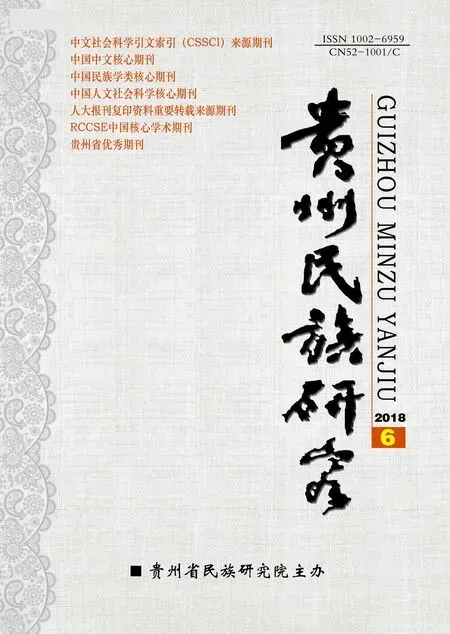近代蒙古族思想文化革新的哲学维度思考
顾德警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南京 2100310)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治、经济机制发生了李鸿章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社会背景下国内逐渐形成了启蒙与救亡的思想运动,蒙古地区的社会面貌和文化思想相应地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尹湛纳希、罗卜桑全丹等人对于长久以来束缚蒙古族民众思想的宗教信仰提出反思与批判,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因此成为蒙古族哲学的思想与启蒙运动。虽然近代蒙古族思想文化革新并未对民族发挥完全的思想启蒙功效,但其对于蒙古族民众对于民主思想和马列主义在本地区的传播和接受发挥了很好的铺垫作用,使当时极为落后的蒙古族和其他地区一样共同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哲学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根本,近代蒙古族思想文化革新的根本价值在于其从根本上对民众所信奉的喇嘛教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予以批判质疑,动摇了依附于神权的封建统治,因此对于当时蒙古族思想文化的革新自然要从哲学维度予以审视。
一、社会环境是促成近代蒙古思想文化革新的哲学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蒙古族思想文化革新顺应了世界范围的思想启蒙潮流,但是又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思想启蒙运动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自19世纪中叶,启蒙运动传入中国,当时国内独特的社会背景促成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对国内情况的深入思考,蒙古地区也不例外。[1]
(一)物质基础
20世纪初,蒙古地区的传统畜牧业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由于清政府的衰败,清朝末期,政府逐渐放弃了对蒙古地区游牧经济的各类优待政策,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废除了清初以降的“禁垦蒙地”政策,征收了原本属于蒙古旗盟的土地、牧场,清理了各旗原有的私垦土地,该政策诱发了严重的农牧冲突,并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此外,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大规模地开展对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掠夺牧区产品和原材料,对自然经济造成猛烈的冲击,形成了蒙古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在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蒙古族民众长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古民族社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同时,伴随西方列强的进入,西方传教士也随之进入蒙古地区,形成了强大的教会势力,基督教民和非基督信众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加深。蒙古社会多种多样的矛盾使蒙古民族生活艰辛,社会矛盾重重,也使蒙古地区经济愈发衰败。为了谋求民族发展和振兴之路,部分有危机意识的进步蒙古思想家开始反思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力图从根源方面为民族未来发展探索新的道路。
(二)意识基础
1.宗教思想
藏传佛教于元世祖时期进入蒙古地区,并逐渐成为蒙古民众共同的宗教信仰。清朝统治时期,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蒙古地区寺庙林立。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藏传佛教的地位开始衰落,但是由于长时期的思想统治,藏传佛教依然是蒙古民众最为重要的精神信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从地方政府到西方列强,再到蒙古贵族和教会势力,现实社会带给蒙古民众深重的灾难和苦痛,无从解脱的蒙族人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因此当时的蒙古地区笃信佛教,一般家庭的男丁都把进入寺庙作为重要的谋生出路,而非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这种搁置生产专心佛教的行为不仅减少了民众的收入,同时大量的僧侣存在也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现实社会的深重苦难和政府与宗教势力的共同推动下,宗教思想成为禁锢蒙古民众的精神枷锁,上层喇嘛利用各种宗教手段向信徒索取财物,而普通民众为了得到菩萨保佑,往往也是倾家荡产。藏传佛教不但导致蒙古地区人口锐减,而且导致蒙古经济基本陷入停滞状态。虽然鸦片战争后藏传佛教式微,但是近代以降宗教势力仍然是影响蒙古民众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史料记载不难发现,近代以降蒙古地区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宗教势力的影子。由此可见,宗教思想对于蒙古地区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宗教势力通过宗教思想对民众在思想和经济两方面进行了双重捆绑,严酷剥削和压迫群众,导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2]
2.儒学影响
儒学是清政府推崇的国学,因此在清王朝时期,蒙古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学的影响。儒学的进入推动了16世纪时佛教思想进入蒙古地区之后的第二次文化大融合。儒学文化的进入,是蒙古文化发展的新契机,在此契机下,形成了一批新的知识阶层,他们不仅把汉族文化引入到蒙族地区,还用蒙文予以再创作,这使当时代蒙古知识界逐渐由僧侣为主体向多元文化主体转变。儒学进入草原,不仅促成了新的文化阶层兴起,也为蒙古地区探求新的精神家园奠定了文化基础。
3.民族文化意识觉醒
18世纪以来,虽然佛教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随着蒙古社会的相对稳定发展,蒙古地区的民族文化复兴意识渐趋强烈,这一时期,撰写蒙古史书成为当时各部落的风潮,这些部落通过史书表达了对历史辉煌的向往,以及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了对佛教文化引入草原的意义的批判与反思。例如,罗卜桑丹津在其所著的《黄金史》中,用将近一半以上的篇幅记述了成吉思汗的辉煌和智慧箴言,作者希望以此来启蒙“黄金家族”和蒙古民众。而18世纪中期的史学家拉希彭斯克则在《水晶珠》中表达了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大肆传播的状况表达了质疑,认为蒙古“约逊”(理)才是治理蒙古的正统思想,表达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
二、近代蒙古思想文化革新的哲学成就
(一)形成“世界实有”唯物主义自然观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宇宙起源是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一直以来,在蒙古哲学思想史上,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指世界万物都是腾格里(天)创造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一点从《蒙古源流》中提出气、水、土三大曼荼罗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便可看出。到近代社会,尹湛纳希对物质构成的宇宙起源作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宇宙源于阴阳二气,因于五行法则。尹湛纳希所说的“阴阳”即蒙语的“阿尔合必里克”,在这里,被他赋予了新的含义,包含了世界本源是物质的、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阴阳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发展等三层涵义。这个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关于世界本原的神造说,相较于之前的气、水、土的本源说,更加丰富和深刻,具有明显的进步性。[3]
(二)探索了唯物主义本体论
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后,本体论问题便成为西方经典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一直以来,神学唯心主义一直在蒙古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统治地位,无论是萨满教、藏传佛教还是后来引进的喇嘛教,都从意识深处认为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这种思想在哲学上便是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或精神的问题。在唯心主义神学思想支配下,社会的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阶级之别成为必然,民众的抗争毫无意义,统治阶级用宗教思想来削弱人们的斗志。但是在当时罗卜桑全丹等蒙古启蒙思想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探索,对于本体论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关于喇嘛教提出的“有限的世界是虚空的”此类观点,罗卜桑全丹指出,人生来需要学习通明事理、与人有益的本领,而不是在此生为了来世幸福而潜心读经,并以世界各国民众注重生活、发展生产、注重教育的现象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例证。曾经经历过僧侣生活的罗卜桑全丹对于喇嘛教的欺骗性有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当时喇嘛教传入蒙古时,达赖喇嘛就说引入喇嘛教,蒙古将昌盛,但是从元朝至今,蒙古地区生产经验、人口发展一年却不如一年,以历史佐证宗教的欺骗性。虽然罗卜桑全丹和尹湛纳希的唯物主义思想较为朴素,但是这对于由神学唯心主义长期统治的蒙古民众来说,无疑具有警醒和启蒙作用。
(三)丰富了蒙古辩证法思想
辩证认识事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近代时期蒙古族思想家在辩证法方面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尹湛纳希对“在”与“空”就进行了辩证讨论,他认为“在”与“空”虽然不是一个词,但是两者实际上表达一个意思,在即是空,有了“在”才有“空”,“空”也是“在”,两者具有明显的辩证关系。为了佐证这一点,尹湛纳希以喇嘛教的经卷为例,指出既然喇嘛教“以空为本”,为何要收罗万卷。他对于有和空的辩证关系论述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按照喇嘛教教义,万物皆为空,但是追求虚空又让人一事无成,因此不如追求存在,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有当时列强奴役和封建剥削必将成空之意。而罗卜桑全丹更是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其思想涉及到客观事物运动变化、成对思想、矛盾转化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矛盾的特殊性等多个方面。蒙古思想家在辩证法思想方面的发展,有力地批判了佛教的“虚空观”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四)提出唯物主义进化方法论
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这个思想对罗卜桑全丹有深刻影响,在他的《蒙古风俗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思想。关于世界是如何形成的,罗卜桑全丹认为人类、飞禽走兽互通言语,但是由于人的聪明和欲望,鸟兽与人类分开,为了避免人类循声找到果实,鸟类年年变换鸣叫声,而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聪明,语言也形成了多样变化,他的这种思想肯定了世界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也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便是对进化思想的肯定和应用。罗卜桑全丹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总结,而是在对蒙古风俗的变化中透露出来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鉴于蒙古民族当时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现实,罗卜桑全丹指出国家的时局必然会变化,蒙古民族当时艰难的发展境遇必然也会得到变化,这一点从他关于“美好时光更替”的肯定变可看出。[4]正是由于秉持了发展变化、进步的思想,罗卜桑全丹对于当时蒙古王公世袭的制度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通过各种实例对这种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意识制度进行反驳,如他曾经以农民的儿子额日锡林吧的事迹为例,指出其虽然是农民的儿子,但是通过学习做了翻译官,且教授出的学生也都做了元朝的高官。进化论是唯物主义方法论之一,近代时期,以罗卜桑全丹等人为代表的蒙古思想家在论著或学说中用不同方式肯定了进化论,这和当时蒙古地区追求虚空或者权位世袭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把认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哲学认为认识源自物质,客观事物在意识中的反映,由于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认识并不完全和客观事物一致,认识的发展经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近代时期的蒙古思想家在认识论方面有所发展,如尹湛纳希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起落观察,指出日光和月亮的起落根源在太阳,便是在自然界客观事物观察基础上形成的正确认识。尹湛纳希指出由于世界各地气候地理条件不一致,因此便形成了地形的不同和季节的差异,而气候的差异也是造成开花、结果不一样的重要原因,把物候作为自然界千变万化的重要原因。他的这些思想也都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总结而形成的关于事物现象到本质的规律性认识,肯定了认识的来源是客观物质或实践,并提出了“穷思极虑而悟其理”,对于如何达成理性认识进行了解释。罗卜桑全丹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如其在论述蒙古民族在饲养牲畜方面的特长时,指出蒙古民族日常劳动便是饲养牲畜,一来二去,便知晓了其中的诀窍,而人们若想知道某个地区的风俗,便需要考察地方歌谣,以此来观察当地人的品性,要做到这一点,便是认真观察。不难发现,尹湛纳希和罗卜桑全丹在关于认识的来源上观点趋同,都肯定了主体的抽象思维能力,这种理性认识将蒙古哲学思想的认识论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作为探究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哲学,其研究对象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它为人类认识、人类种族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进步可以从根本上为民众认知世界、改造社会提供新视角。近代以来,在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蒙古民族仁人志士大胆突破喇嘛教宗教思想的藩篱以及封建主义制度的陈规,对当时现实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和症结予以思考批判,“批判的武器”——这种哲学维度方面的进步推动了蒙古民众意识形态层面的启迪和开化,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批判的武器”也推动蒙古哲学跨入新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