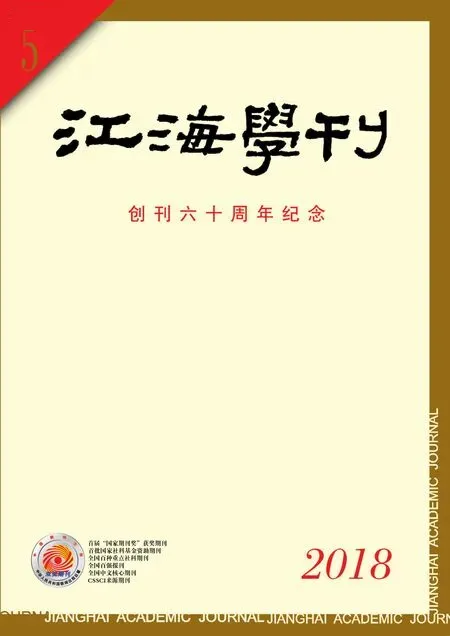论博丹国家主权理论的自然神学基础及其困境
内容提要 博丹的“绝对主义转向”实质上是更换其国家主权理论的哲学基础,由历史主义转向自然神学。博丹的自然神学将上帝视为世界的创造者、第一因和第一原则,“存在巨链”完美地将世界联系为一个和谐的等级秩序,对政治哲学中的绝对主义国家主权构成了坚实的支撑。博丹的自然神学和绝对主义政治哲学内含的君主论、神义论、整体主义虽然难以对抗人民论、人义论、个人主义的现代潮流,但其中揭示的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被取消,经历了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的现代哲学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
博丹(Jean Bodin,1529/1530-1596)因其主权(sovereignty)学说为世人所熟知,“主权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永久的、绝对的权力”①早已从振聋发聩的政治哲学下沉为全世界的常识。然而,博丹国家主权理论背后的自然神学基础却少有人问津。这一方面是因为博丹的国家主权理论太过耀眼,即便霍布斯、卢梭更换了其哲学基础,整个大厦仍然稳固,其博丹色彩并未被冲刷殆尽,似乎追究其哲学基础成了一个多余的问题。另一方面,深入到博丹自然神学内部的专家们多将其作为一种卓越的智识成就来赏玩,并未将其与现代政治理论根基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导致博丹国家主权理论和自然神学之间的严重脱节,甚至导致整个博丹研究的去政治化。因此,澄清博丹国家主权理论的自然神学基础,恢复它们之间的密切关联,不仅有助于重塑完整的博丹理论形象,更有助于厘清自然神学在现代早期政治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现代政治哲学发展的诸多根本线索。本文通过博丹的自然神学转向、建构和后世走向三个方面来阐明:博丹洞察到了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明确选择了更新自己的基础理论来为国家主权学说奠基,但在当时看来近乎完满的自然神学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潮流相悖的根本特征,国家主权学说的自然神学根基被后来人放弃,不过它所留下的基本问题却没有随之取消,现代政治哲学家们并没有圆满地予以解决。
博丹的自然神学转向
政治理论领域中,西方研究博丹的“首席专家”朱利安·富兰克林(Julian H. Franklin)指明了博丹在政治理论上存在着“绝对主义的转向”(The Shift to Absolutism),即博丹的早期思想与《国家六论》之间存在着从宪政主义到绝对主义的转变。②尽管有学者坚持博丹早期思想与《国家六论》展现的绝对主义之间只是一种顺承、放大、展开的关系,③但富兰克林的观点得到了政治理论界的有力支持,④而且,鉴于富兰克林的作品主导了西方政治理论界的博丹研究,“转向论”也几乎成为定论。⑤然而,富兰克林在其作品中从未讨论博丹政治理论立场转变背后所隐含的博丹哲学立场的转变,富兰克林甚至很少涉及博丹的后期著作。把博丹的所有著作合观,而不是只盯住《国家六论》和博丹早期作品《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下文简称《方法》),⑥已经越来越成为研究博丹理论的趋势。⑦必须通过分析博丹晚期著作《七贤聚谈》和《普遍自然剧场》⑧中蕴含的自然神学来反观绝对主义背后所必需的正当性基础和论证思路,在更加抽象和深刻的层次来理解博丹的国家主权学说。虽然这在博丹学说内部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后见之明,但这种后见之明对理解博丹的国家主权学说乃至整个现代政治哲学的内在深层次困境极富启发意义。简言之,从《方法》到《国家六论》的绝对主义转向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不是时局的逼迫,而是博丹本人哲学立场的转变,是博丹从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主义转向了自然神学。⑨
作为法学家的博丹,在图卢兹法学院学习期间就已对法学内部的两大流派,即中世纪罗马法学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法学,都有所吸收又都表示不满。他的法学立场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选择。一方面,作为人文主义法学的拥抱者,博丹对中世纪罗马法研究不满。他在学生时代的《就共和国中青年的教育问题对图卢兹元老院和人民发表的演讲》(1559)中就已激烈地批判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追随者们,⑩在《方法》中博丹明确支持人文主义法学对中世纪以来罗马法研究的批判:“技艺和科学,如大家所熟知,绝非与特殊性相关,而是与普遍性相关。……(罗马)民法只不过是一个特定国家的立法罢了。”按照人文主义法学的看法,自巴托鲁斯(Bartolus of Sassoferrato,1313/1314-1357确定在世)和巴尔达斯(Baldus de Ubaldis,1327-1400)以来的罗马法研究神化了《国法大全》,将其视为永恒的理性,它是完美的、普世适用的,因而只能解释不能改动。然而,自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以来的人文主义法学以文字学、修辞学、历史学的方法“证明”了罗马法并非如此,将之降格为历史的、特殊的、有局限的法律。博丹将其定位成“一个特定国家的法律”,可谓深得人文主义法学的精髓。
但另一方面,作为人文主义法学的批判者,博丹认为人文主义法学太过依赖文字学,特殊性、历史性、相对性太强,离法学追求普遍理性的目标越来越远。他在《方法》中要求真正的法学家“不仅有原则和法庭实践,而且习得最精致的艺术和稳固的哲学,理解正义的本性,不是根据人的意志而变化,而是由永恒的法所确立。”他承认中世纪罗马法自以为是的普遍主义应该被人文主义法学击破,但又心有不甘,他的雄心抱负是要恢复法学的普遍主义。而他所采用的法学方法是比较法。博丹的比较法是一门涉猎极广的学问,其中固然包括了各国(包括历史上的)宪法、刑法、民法等传统法学门类中的比较,从中提炼法的普遍原理,但它的范围远不止法学,天文、地理、气候、星象、经济、文化……几乎无所不包,要从所有知识中提炼出“法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称博丹为“十六世纪的孟德斯鸠”。
在以比较法求普遍法的学问中,最重要的材料是历史,博丹的成名作《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是写给法学家和立法者而不是历史系的学生看的。崇敬历史,向历史求教,历史中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真理,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特征,博丹在《方法》中将这一特征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在将历史区分为神圣史、自然史和人类史之后,他表明普遍法主要还是依靠人类史,但人类史异常复杂,“因为人类史通常来自人的意志,而人的意志游移不定,漫无目的,所以我们看见每天都有新法律、新习惯、新制度、新风尚,而且人的行动总是不断地陷入新的错误,除非他们遵从自然(即正确理性)的指引。”因此,法学家必须练就对历史抽丝剥茧的功夫。此时的博丹对写史求政治之道的马基雅维利充满了好感,奉之为师。
十年之后,在《国家六论》中博丹对马基雅维利态度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果历史不足为训,那么,没有哲学的马基雅维利只不过在历史中学会了狡黠,其实是“最无益的圆滑”。博丹批评马基雅维利历史有余、哲学不足的时候,他的自我期许和努力方向已经明确地指向了哲学。博丹对马基雅维利态度的转变,主要不是因为宗教战争的白热化使得博丹和常人一样通过贬斥马基雅维利来攻击梅蒂奇王太后,而是博丹哲学立场的转变: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主义不能为普遍法提供可靠的、稳定的依据,只有自然神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从最深层次的哲学立场转变来看,富兰克林所言的“绝对主义转向”是博丹从或然性的历史主义向必然性的自然神学的转向。
博丹的自然神学建构
从政治哲学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看,《国家六论》是博丹的巅峰之作,但从博丹思想的发展来看,《国家六论》只是半成品。简言之,他的自然神学理论在《方法》中萌芽,在《七贤聚谈》和《普遍自然剧场》中完成,而在《国家六论》当中仍处于苦苦求索、尚未得解的状态。《国家六论》首版(1576,法文)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追求,知识异常广博,却未形成系统化的自然神学对庞杂的知识加以条理化,结果成了政治哲学史上最不堪率读的著作,东拉西扯、冗长乏味、布局散乱。博丹以自然神学重新为国家主权奠基的努力首先体现为《国家六论》拉丁文版(1576)的大量修订,他在其中强化了其自然神学的立场,但体系化的自然神学仍然没有完成。
麦克雷(Kenneth Douglas McRae)在重新校订诺尔斯(Knolles)于1606年翻译的《国家六论》并为之写长篇“导言”(1962)之时,就已经触及了博丹哲学立场转变的问题,并发现:“拉丁文版透露了一种更加强劲的对人文主义思虑的强调,一种对残酷行为更加尖锐的谴责,和一种明显的仅从国家政策的立场来判断问题的不情愿。简言之,博丹的价值正在发生变化,虽然轻微却是可以察觉的。他正在从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它常常沉沦为一种麻木不仁的残暴)转变为一种新的立场:他对所发现的任何不义都予以强有力的反击,甚至对法国君主制历史上的事情也如此。”拉丁文版与哲学立场的转变相关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从历史的比较中抽象出普遍法的历史主义已经多有怀疑;二是对自然神学展开正面的论述,以取代历史主义作为主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怀疑历史主义有效性的种子早已埋在《方法》当中。博丹对“人类史”的定位是意志论的,而意志论为底色的“人类史”必然是千变万化、难以预测、难以捕捉的。意志论对于博丹的主权理论特别重要,在《国家六论》中意志是主权的哲学内核,相应地,“人类史”的或然性也会随之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西方悠长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传统中,意志论与理性论的较量从未停止,而博丹作为强化国家、权力、主权的理论代表,明显地属于意志论的阵营。如果说16世纪由宗教纷争引发的乱局迫使国家建构加速展开,那么,主权作为国家的标志和实质则体现出博丹在政治哲学上找到了解决之道,但新提出的主权学说必须以哲学和神学上强硬的意志论来支撑,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主义天然不能幸免的或然性、相对性和特殊性必然导致它被放弃。在《方法》之中,博丹的意志论尚未饱满,仍然能够与历史主义共存,忍受其或然性、相对性、特殊性,而《国家六论》已经不再容忍,放弃历史主义也就在情理之中。在《国家六论》里面,博丹确实还是喜欢像马基雅维利一样讲故事,以历史来证明他的观点,但在许多地方,都流露出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口吻。比如第1卷第5章讨论奴隶制的时候,博丹的整个语调和篇幅的安排都透露出这样一种基调:历史上那么多国家有过又怎么样,亚里士多德支持它又怎么样,它就是反自然和反上帝的!《国家六论》的创作时间处于《方法》和《普遍自然剧场》《七贤聚谈》之间,但它的哲学立场更接近后两者而非前者。
针对历史主义,博丹在晚年的《普遍自然剧场》中明言:“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所有有记录的时期、时代和城邦当中不可能建立起(法学)学科的边界,因为它基于人的判断和错误,以至于有些法官认为值得嘉奖的而另外一些法官却认为应当受到惩罚……我意识到,所有的人的法令、判决和法律都是依人的意志和欲望轻率提出的,除非它们依靠着神法——即自然法——的指引他们瞎眼的脚步走上一条超越迷宫的金光大道。”那么,博丹发现和依靠的“金光大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神学呢?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先澄清博丹做出神学和哲学选择的个人定位:他并不是以神学家自居站在神学的脉络中进行选择,而是作为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去追问“真正的宗教”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构成了博丹和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本质差别,从宗教政策的立场上,二者都坚定地支持政教分离、宗教事务低于国家、宗教是国王掌控的内政、宗教冲突不得破坏国家统一,但马基雅维利从不操心“什么是真正的宗教”,而博丹却坚定地认为这个问题是为国家主权奠定最坚实根基的关键所在。博丹的最后一部著作《七贤聚谈》,通过虚拟七位宗教立场不同的贤人针对诸多根本问题的讨论,博丹试图给出一种自然宗教来作为消弭一切纷乱的根本之道。
博丹虚拟的七贤分别是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自然哲学家、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怀疑论者和伊斯兰教徒。学术界对于其中哪一位最接近博丹本人有不同的说法,也都能从七贤的对话中找到证据。但博丹实际上是在同情地理解各家基础之上的博采众长。在纯粹神学的问题中,他主张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是世界的第一因,是第一原则,是永恒的;创世是出于上帝的自由意志而非任何“必要性”;世界在上帝之中,而不是上帝在世界之中,世界并非永恒的,而是有始有终的,它的存在被金质的巨链所捆绑,万物由此构成了上下相安的秩序。从博丹这套神学的基本要点来看,它更接近古罗马晚期的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奥古斯丁所持的上帝绝对论、德性光照论、自由意志论在博丹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无论在《普遍自然剧场》还是《七贤聚谈》当中,他完全没有像路德、加尔文一样援引奥古斯丁去攻击阿奎那。易言之,博丹没有将自己定位在神学论辩和宗教改革维度去解决神学纷争,而是力图超然于其上去平息宗教冲突。强调上帝的绝对地位、绝对意志和第一立法者形象,与博丹毕生通过强化主权来缔造国家、克服混乱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他后半生的哲学和神学努力是前半生政治哲学努力的延展和升华,为前半生的政治哲学提供更为坚实、更具内在一致性的支撑。
博丹的自然神学若止于此,则很难避免“食古不化”的讥评,萨拜因就说博丹只是“从神学的废物堆中拣出了主权这个理念”。博丹的自然神学还有两个要点,既充分地展现了其现代性,又将现代性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
第一,博丹的自然神学虽然以追寻“真正的宗教”为旨归以重申上帝的绝对地位为支点,但它其实融汇了大量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内容,是一个具有明显科学意味的整全体系。从题材上看《普遍自然剧场》和《方法》《国家六论》就存在明显的差别。它不再讲历史故事,而是分析各种后世看来属于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的问题。目的是阐明:自然是人认识上帝的良好途径,认识自然就是在接近上帝,自然的完美最终会证明上帝的完美,自然法是指引人类行为的法则。博丹的思路不仅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普林尼开始追求的自然哲学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和现代早期的科学革命是高度吻合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模式,试图将宗教、自然、人文熔于一炉,为人们讲述一个自上帝至花草完全融贯的世界。据《普遍自然剧场》的著名研究者布莱尔(Ann Blair)所言,博丹就是要把这本书写成常识性读物,而在德语世界它后来确实也做到了。《七贤聚谈》在前三卷强化了《普遍自然剧场》的主题,将自然哲学、自然科学与神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随着科学革命的迅猛发展,各门科学脱离神学,甚至与哲学也分道扬镳;各门科学之间也相互划清界限,在日益分化和专业化的新世界中,百科全书式的建构不仅被放弃,甚至被认为是徒劳和错误的。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博丹的许多分析被证明是错误的,进一步减损了他著作的影响力。
第二,博丹自然神学的核心价值是“和谐”(Harmony),与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秩序”(Order)形成呼应,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博丹在《普遍自然剧场》和《七贤聚谈》中花了大量的笔墨论证“和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谐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取得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是由上帝保证的,正是有了上帝的神性渗透整个世界,纷繁复杂的“多”才可能而且必然和谐地统一为“一”。而且,博丹特别强调和谐绝不意味着整齐划一,“和谐有赖于每一事物本质的和谐,是一种有赖于与其对立面交融为一的和谐。”具体到人事上,博丹特别强调“宽容”,信仰问题不能施加强制,强制不会导致虔信而只会导致最可怕的无神论。在《七贤聚谈》里他承认每种宗教当中都有合理成分,而且没有任何强求七教合一的意图,唯一不能宽容的是无神论。博丹在《国家六论》中明确论证了宗教是国家统一的基础,但他从未主张强制性地将国家在宗教问题上整齐划一,他始终在追求一种融所有真理为一体的“真正的宗教”。
但是,现代世界并没有像博丹所希望的沿着寻找“真正的宗教”的道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世俗化成为主流,宗教不仅丧失了统摄一切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主导地位。尽管博丹的自然神学融合了科学和人文,力主和谐和宽容,但它恐怕是以宗教为基础规划世界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绝唱。
正如政治哲学中的绝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过渡形态的政治理论,作为其深层次基础的博丹自然神学也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位于阿奎那神学和霍布斯哲学之理解。博丹的自然神学,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博丹在《国家六论》当中为什么把“主权及其限制”作为基本论式,为什么全书当中到处都是“神法和自然法”对主权的约束,为什么“正当”与“合法”的字眼充斥全书。以强化权力还是限制权力来理解博丹的绝对主义政治哲学很容易将“主权及其限制”视为悖论。但以自然神学的基础来看博丹的“主权及其限制”,它其实不是在讲主权及其“限制”,而是在讲主权及其“成全”。是神法和自然法成全了主权,使它有了可以和历史上所有特殊例子相对抗的绝对力量。唯有如此,主权理论才是可以克服宗教战争的有效之方,也唯有如此,主权理论才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这正是博丹的抱负。
博丹式自然神学的困境
博丹晚年融贯了绝对主义的政治哲学与整全的自然神学,然而它们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将博丹的绝对主义及其自然神学基础放到更广阔的政治理论背景下,其主权理论的脆弱性以及引发的大问题会充分地暴露出来。然而,当这些大问题暴露出来,我们会发现博丹所提出的具体方案虽然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需要追求好政治的人们认真面对。
第一,神义论难以对抗世俗化,但主权必须拥有绝对根基的逻辑并没有被取消,在世俗化的新世界中主权始终根基不稳。
博丹的主权学说意图用神义论政治的绝对一元性克服宗教和政治的多元性,这是绝对主义的基本要义,也是自然神学的旨归。君主绝对权力的根基在上不在下,在上帝不在人民。他特别强调主权的绝对性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多元性已成无法回避的事实,转向自然神学的选择在神学上与加尔文有很大的共性:离开阿奎那,回到更古老的基督教传统,强调上帝的意志,而非上帝的理性,以上帝为原点重塑世界的统一性。他甚至比回到奥古斯丁的加尔文走得更远,他回到的是《圣经·旧约》所代表的犹太教传统,其中又混合着新柏拉图主义。然而,以宗教救政治的基本思路在世俗化大潮中迅速变得既不可行,也不可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格林说博丹“仍旧是半个中世纪的人物”,萨拜因说他“没有进入现代”。在现实中主权确如博丹所言居于宗教之上,成为现代国家的定海神针,但其根基并没有锚定在博丹所设想的神义论上。主张绝对主义和国家主权的政治哲学家们对博丹的自然神学表示异议,菲尔默倒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和神学传统来为它们辩护,不过他把论证的重心更换为父权论;霍布斯则坚决地剔除了主权理论的神义论根基,代之以彻底世俗化的社会契约论。自霍布斯之后,以神学的观点和逻辑论证政治秩序安排的学说迅速失去了政治理论上的论证效力。
然而,更长远的问题是,基督教的神义论被世俗化大潮冲刷而去,主权绝对性所必需的绝对支点又将安放在何处?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世俗化努力不仅没有彻底解决反而完全暴露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当他将人的自我保存设定为绝对支点的时候,他自己都发现原来利维坦只不过是个“会死的上帝”(mortal God),因为建基于人之自我保存的利维坦不能根除这个绝对支点所蕴含的“反叛的激情”,利维坦如若不能保卫人的安全,人会自动启动自我保存,返回自然状态(战争状态),利维坦即被杀死。换言之,世俗化本身无法提供绝对性,主权的根基在世俗世界中就无处寻觅,萨拜因说主权“飘浮在空中”,对于博丹是不对的,而对于霍布斯之后世俗化了的政治理论倒是不错。从霍布斯起,在世俗世界中寻找主权的根基就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君主论难以对抗人民论,但人民论存在着被君主论逻辑置换的巨大危险,而且,人民取代君主拥有主权,却背负上了须得永远自我证明的义务。
博丹的主权学说是系统化的“君主论”,《国家六论》从头到尾都在力辩君主政体的合理性,而且,他并没有主动地把主权和主权者严格区分开。他对君主制的维护与奥古斯丁、阿奎那以来的中世纪政治传统是高度吻合的,与马基雅维利的共性也很明显,即便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君主制也具有极高的优越性,因此,在政治理论长线脉络中,博丹绝非异类,反而非常主流。人民在博丹的主权学说中并不享有重要地位,在绝对主义君权神授的秩序观当中,民众处于最底层,他们只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质料,他们没有成为拥有意志的政治主体,君主作为秩序的枢纽才能为共同体赋予形式,君主了解人民的本质和性情只不过是主权者必须去理解治国的质料。不过,博丹之后不久,人民不仅摆脱了质料的地位,而且迅速成为最具能动性的政治主体。上帝死了,人民当立,民主成为现代世界的潮流,在神义论的意义上,人民取代了上帝成为新神,成为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完成新神加冕的正是卢梭,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证了人民主权。
然而进一步追索,当卢梭苦心孤诣地试图以“公意”(General Will)作为人民的政治本质取代上帝的意志成为主权的绝对支点之时,吊诡的事情发生了,主权“来自下民”(from the under)的逻辑却被对立的主权“来自上帝”(from the above)的逻辑悄无声息地置换了:人民具备了上帝的优点,正义、全能、永不犯错,却也同时具备了上帝的“缺点”,神秘、“专断”、不可批评。这是神义论的借尸还魂。只要在最高的、绝对的主权头上再安置其根源,它就必然“不食人间烟火”,因为主权是可见世界的顶端,六合之外,只能存而不论。当人民被卢梭置于至尊之位的时候,也就被推入了不可言说的神秘境地。于是,人民主权必须回答“我们人民是谁”这个永远在理论上找不到可靠答案的问题。卢梭的人民主权并没有解救霍布斯,只不过把问题推向了更深的层次。自然神学在卢梭那里不仅没有被根除,反而以某种变体再次回归,充分证明了博丹的自然神学转向把握住了现代政治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政治领域的绝对性(主权)必须立基于神学意义上的绝对性(上帝或其变体)。
第三,整体主义难以对抗个人主义,但个人主义清除了整体主义蕴涵的神秘主义之后,主权的神圣性却难以为继。
博丹的主权学说毫无疑问是整体主义的,他毕生都在追求建构起百科全书式的整全学说,自然神学既是他整全学说的地基也是其基本的思维逻辑。绝对的上帝授予君主绝对的主权,凭它制造一个统一、和谐、正义的人间秩序。许多学者指出博丹学说带有神秘主义的品质,并不是因为他讲了很多现代人不以为然的怪力乱神,而是他汲取了犹太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思维逻辑。上帝越是最高意志,整个学说的神秘主义品质就越浓厚,这意味着世间万事“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世界是复杂的整体,运作自有上帝的旨意,岂可为凡夫俗子所知。凡夫俗子不知,不见得就没有道理,恰恰相反,背后有着天大的道理。神秘主义是整体主义必不可少的元素。博丹选择了充满神秘主义思维方式的自然神学,直接导致他在哲学建构上的乏力,他亲新柏拉图主义而反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主义、亲意志论传统而反理性论传统的选择严重抑制了他在自然神学内部构造出一套高度理性主义体系的可能性。所以《国家六论》条理不清、组织不善,而且难以摆脱文艺复兴式的历史分析作为其基本材料;《普遍自然剧场》和《七贤聚谈》都是以文艺复兴式的对话体裁展开,各种宏大的主题在阐释之后都归于带有神秘性质的综合或升华。而个人主义却通常与神秘主义不合,霍布斯的理论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结合,他甚至声称要像拆装钟表一样研究政治学,把政治学变成几何学那样显白无误。霍布斯就是要简明地通过加减个人的自我保存就得出利维坦,里面没有任何神秘,而且他的理论是公认的思想史中条理最为清楚、组织最为缜密的学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盛,霍布斯式的算术加减大行其道,一切用个人主义无法说清楚的东西都被弃之不顾。
然而,更长远的问题在于,个人主义与世界和政治所必需的神圣性背道而驰。霍布斯式的个人主义将个人神圣化而将其余所有都去神圣化了。施特劳斯严厉批判霍布斯理论是“政治无神论”,并非空穴来风。在整体主义的框架中,因为有神秘主义的加持,说“主权神圣”并无任何不妥,但在个人主义的框架中,说“主权神圣”是几近荒谬的。当我们轻率地嘲笑博丹的整体主义之时,可曾想过主权的神圣性在个人主义的框架内如何维持?如果放弃主权的神圣性,主权还能维持吗?如果因每个人心中除了自己再无神圣,主权即被瓦解,政治秩序还会存在吗?如果会,它将是什么样子?霍布斯式的个人主义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也频频遭遇新整体主义的反扑,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学说,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精神”为至高点构建完备的世界秩序,建立新的神圣。尽管他极力以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证明绝对精神的演化之道,但马克思和很多哲学家都斥责他陷入了神秘主义。博丹、霍布斯、黑格尔的主权理论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正、反、合关系,如果黑格尔学说没有成为主权公认的新基础,那么,博丹制造、霍布斯打破的主权神圣就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博丹的答案很大一部分、最基础的部分被摧毁了,但哲学家们却没有提供有效的替代品。
博丹站在古今之间,他的主权学说给出了现代政治的问题框架和初步解决方案,并且努力通过自然神学的建构为这套方案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或许对他的解决方案及其自然神学基础不满,但决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霍布斯、卢梭、黑格尔这些大哲学家手中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尤其是,当我们走到博丹方案的对立面,会发现自己将陷于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问题的实质在于博丹国家主权理论背后的自然神学发现了现代政治的诸多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博丹不是巫师的话,也是一名成功的预言家。”
①Jean Bodin,OnSovereignty, Julian H. Franklin ed.,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p.1. Jean Bodin,TheSixBookesofaCommonwealth, Kenneth Douglas McRae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84.
②Julian H. Franklin,JeanBodinandRiseofAbsolutist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41-53.
③参见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Adrianna E. Bakos,ImagesofKingshipinEarlyModernFrance:LouisXIinPoliticalThought, 1560-1789,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99, 101. 朱琦:《博丹论法学家的历史素养》,重庆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12-16页。
④参见Daniel Engster,DivineSovereignty,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8-49.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奚瑞森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2、411-415页。
⑤标定富兰克林学术地位的著作主要有:Julian H. Franklin,JeanBodinandRiseofAbsolutist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Julian H. Franklin, “Sovereignty and the Mixed Constitution: Bodin and his Critics”, InVerhandlungeninMunchen, Munich, 1973; J. H. Burns ed.,TheCambridge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145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98-328. Julian H. Franklin, “Introduction”, In Jean Bodin,OnSovereignty,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pp. ix-xxvi. 著名思想史专家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曾说:“对于博丹政治理论的常规解释,我认为,仍然为朱利安·富兰克林三四十年前那些著作和论文所支配。”(Richard Tuck, Sleeping Sovereig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0-31.)
⑥Jean Bodin,MethodforEasyComprehensionofHistory, 1566, Beatrice Reynolds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⑦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第218-219页。 Daniel Engster,DivineSovereignty, pp. 47-49. Donald R. Kelly,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ext of Bodin’s Method”, In Julian H. Franklin ed.,JeanBodin, Aldershot: Ashgate, 2006, pp.123-151.
⑧Jean Bodin,ColloquiumoftheSevenSecretsoftheSyblime, 1593, Marion Leathers Daniels Kuntz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Jean Bodin, Universae Naturae Theatrum, Lyon, 1596.
⑩Jean Bodin,AddresstotheSenateandPeopleofToulouseonEducationofYouthintheCommonwealth, George Albert Moore Trans., Chevy Chase: The Country Dollar Press, 1965, p.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