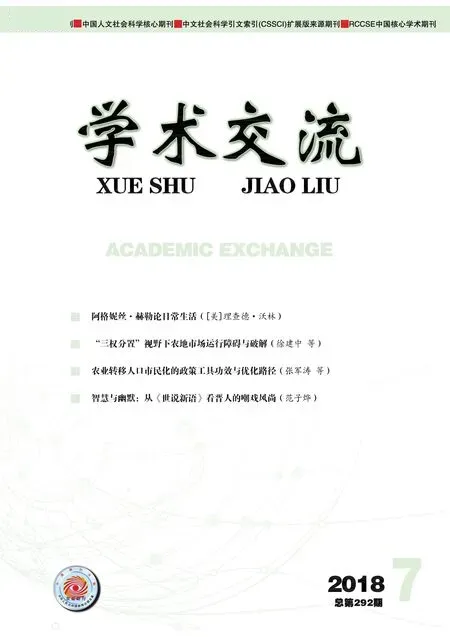传统文化之利他思想及其对个体捐助行为的影响
高 阳,于海瀛
(1.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01;2.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 150025;3.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2017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1]显示,2016年我国个体捐赠额占捐赠总额的21.09%(约293.77亿元),人均捐赠100.74元;同年,美国个体捐赠额占比捐赠总额72.3%(即2 820亿美元,约合18 585.5亿人民币),人均捐赠1 207.2美元(约合7 957.1人民币)。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八分之一,而人均捐赠仅为美国的八十分之一,何以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刺激个体捐赠是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利他思想”,这些思想以不同的理念和形式展现,并影响着中国捐赠的意识和行为。
一、传统文化之利他思想
1. 以仁爱为本的儒家文化之利他思想
源自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对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广泛而久远的深刻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孔子与孟子的学说,代表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既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又是做人的道德目标,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仁”是个人道德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社会的依据。何为“仁”?《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如何达到仁呢?《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要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成人之美。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要求是,《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可见,“仁爱”即利他,利他即仁爱。
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创造性地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提出著名的“性善论”。此论主张人生来就有善性,只是这种善性是作为“善端”存在于人心之中,它是“仁”得以实现的基础。《孟子·公孙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4]“仁之端”,即明代陆王心学所说的“良知”,也是佛教所指的“善根”。“良知”“善根”是与生俱来的,是由人类的遗传基因决定的。所谓“恻隐之心”,即同情之心,怜悯之心,爱人之心。恻隐之心与慈善行为关系密切。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的:“慈善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的一种厌恶,”“怜悯与慈善关联,慈善借一种自然的和原始的性质与爱发生联系。”[5]
总之,孔孟之道以仁爱、慈善为灵魂,要求人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儒家主张仁爱,但并不否定利己,而是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地向外扩展自己的仁爱行为,以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去利益他人。不仅要利益“身边人”,还要利益“天下人”。儒家《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6]
基于仁爱思想,儒家形成了自己慷慨大度的义利观和生死观。《论语·八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义不为,无勇也。”[7]仁与义一体,仁者必然重义,重义者必定仁爱。故仁义并称,用以表达美德。基于仁爱的实现,当一个人面对义与利,乃至生与死的两难选择时,儒家主张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孟子· 告子》:“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为了仁义,最宝贵的生命都可以舍弃,何等慷慨;而为了仁义,慷慨解囊,当然不在话下。在实现仁义的一定情境中,视名利如草芥,视金钱如粪土,乃至舍生取义。这种当仁不让的慷慨人生态度与君子风度,对个体捐助行为有重要影响。
2. 以淡泊为本的道家文化之利他思想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庄哲学是道家文化的思想核心。《道德经》(《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文化的经典文献。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佛家文化以“空”为真谛,而道家文化以“道”为根本。不可名状却无所不在的“道”,是宇宙生命之本,与佛家的“心”相通。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净淡泊,无为而治,超越世俗,逍遥自由。道家文化虽然不像儒家文化居于主流地位,但在上流社会和广大民间,均具有根深蒂固的深远影响。古代达官贵人,知识分子,在内心世界和社会行为上,无不是“外儒内道”。
道家虽然崇尚自然,淡泊无为,认为“道”比“德”更具根本性,但对世俗德性依然肯定,一向主张弃恶扬善。在道家文化和道教中不乏劝善去恶的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9]老子反对前者崇尚后者。反对巧取豪夺,为富不仁,主张安贫乐道,好善乐施。道家也像儒家和佛家一样,主张仁爱或慈悲,实行利他主义。
道家的利他思想,源自“虚无”和“淡泊”的人生态度。其“虚无”哲学,引领人们认知生命与财富终归虚无的真理。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老子主张知足常乐,推崇俭朴淡泊的简单生活,反对骄奢淫逸的奢侈生活。他反对锦衣玉食,声色犬马,宁愿粗茶淡饭,麻衣草鞋,享受淡泊之趣。骄奢淫逸,身心俱疲;俭朴淡泊,简单快活。广厦万间,夜眠不过一床;美酒满缸,饮之不过几两。睡在金床上也可能痛苦,卧在草席上未必不乐。以俭朴为美,以淡泊为乐的人,绝不会为富不仁,吝啬财富,反倒会慷慨解囊,散其余财,以利益他人,自得其乐。
3. 以慈悲为本的佛家文化之利他思想
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尊的古印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在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融合的本土化过程中日益深入人心,对国人的世俗人生观和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颠覆性的重大影响。佛教以“五蕴皆空”“诸法无常”为根本义理;身体力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潜心修持“戒、定、慧”;进而实现转迷成悟,离苦得乐;最终达到明心见性,了生脱死。因果定律和慈悲精神,是佛家思想的重要内涵。较之佛教的“空”“禅”“悟”等深奥玄妙的义理,比较易于认知和践行,所以在普通百姓中更为普及,影响甚大。有关因果报应和慈悲为怀的精神产品,在封建社会时期屡见不鲜。这些精神产品,直接影响到个体对寺庙和民间的捐助。
因果定律是佛教的基本原理。佛教的因果定律与作为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之一的因果关系,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根本区别。佛教之因果概念,有自己的特殊内涵和行为指向。佛教所称谓的因果,叫作“业因果报”,也叫“因果报应”。“因”就是原因,也叫因缘。“果”就是结果,也叫果报。“业”是指一切身心活动,分为身(行为)、口(言语)、意(意识)三业。“报”就是“业”的报应,即由三业的善恶所导致的后果。因就是业,果就是报。种善因得甜果,种恶因得苦果。因决定果,果来自因。所以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佛教苦口婆心,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由此可见,佛教的因果定律,是直接指向善恶报应的。
慈悲为怀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佛教是以慈悲为本,忍辱(苦)为行的宗教,“慈航普度”是大乘佛教的宗旨。菩萨心肠是修佛的根基,修菩萨行是佛教的根本修行,修菩萨行即慈航普度。最慈悲者是菩萨,修菩萨行,包括诸多方面,其中的布施是一个重要方面。布施包括法布施和财布施,前者指弘扬佛法,后者指施舍钱财。钱财布施虽然不是修行的根本,但也是圆满功德修成正果的助缘,最能牵动普通百姓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的,是钱财布施所带来的福报。佛教认为,钱财布施是在因田里播种善种,会得到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临门”的福报。钱财布施带来的福报以及当事人追求幸福感的情感诉求,是激发个体捐助行为的强大内驱力。财物布施不在多少贵贱,贵在发露真诚的慈悲心,佛教中广为流传的“贫女施灯”的故事,对个体捐助行为仍有重要影响。
儒家的利他思想是基于自我的“自我利他主义”;而佛教的利他思想是否定自我的“无我利他主义”。虽然佛教主张由入世而出世,注重“借假修真”,因而确认世俗生活的相对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说,佛教彻底否定以自我为中心,主张如壮士断腕断绝自我。为此,可以不惜身家性命,区区钱财更是微不足道,故佛教一向奉行“舍得主义”。佛教的“无我利他”思想,基于博大的慈悲情怀和圆成佛道的宏大誓愿,是驱动个体捐助行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4. 以行善为本的民间文化之利他思想
儒、道、释的仁义之理,善恶之思,因果之辩,慈悲之心,在民间转化为以“行善”为本的民间思想体系。这一通俗易懂的民间思想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影响力,几乎不亚于儒、道、释互补的精英文化,对个体捐助行为具有直接的深刻影响。该思想体系主要体现于见诸文字的“善书”和见诸言行的“天命”。
“善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态。所谓善书,又称劝善书,发源于先秦,成熟于两汉,兴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延续至民国。善书融会儒、道、释要义,并加以民间化改造,以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主旨,教化百姓积德行善。善书有上千种之多,以《太上感应篇》《明心宝鉴》《了凡四训》《玉历宝钞》等为著名者。而以讲唱的艺术形式宣传佛教、道教的唐代“变文”“道歌”,宋、清时期弘传道教的“道情”或“渔鼓”,则是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的艺术化的善书。
“天命”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以“天”为人格神的“天命论”源远流长,影响相当深远。《论语·八佾 》记载:“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7]天命观念,在民间老百姓心里根深蒂固。老百姓坚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人算不如天算”;“人不报天报”。民间天命思想的本质是抑恶扬善,与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它虽然有唯心色彩,但具有积德行善,利益他人的客观效果。
二、传统文化之利他思想蕴含的利他情感
情感是个体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所做出的一种心理反应,与认识过程不同,情感和情绪不是对客观对象本身的反映,而是对对象与主体之间的某种关系的反映, 所以它表现为对待客观对象的一定的主观(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人的活动、需要、要求以致理想,亦即与人的利害有密切的联系。对象与主体需要的不同关系产生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情感又驱使主体采取不同的活动,以符合主体的要求和需要。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本质,是人最重要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爱”与“乐”的情感,是激励个体捐助行为的强大内驱力。
儒家利他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仁爱”指能同情、爱护和帮助人,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孟子认为“仁”发端于恻隐之心,佛教利他思想的核心是“慈悲”(“慈悲”指慈善和怜悯)。不难看出,传统文化的利他思想本身包含着利他情感,这种利他情感的特质是“爱”。“爱”是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正能量的美好感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是所有宗教的内在情怀。传统文化之利他思想,既是理性上的大我境界,又是情感上的大爱情怀。个体捐助行为,固然需要主体对捐助的精神价值有深刻的理性认知,但更重要的是爱心。只有对捐助对象有发自内心的同情之心、怜悯之情、爱护之意,方能有个体捐助的慈善之举。
传统文化之利他思想所包含的情感因素,除了“爱”还表现在信奉和实施利他思想的主体享受“乐”的情感回馈上。“乐”是利他情感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像“爱”一样对个体捐助行为有重要影响。快乐原则同生存原则一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普遍原则。西方文化是悲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来源于孔子,他肯定了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这种乐感文化所蕴含的乐生思想、饱满的乐生精神,是一种风雅的、细腻的和高度艺术化的东西,即艺术人生”[10]。这种乐感文化,很早就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之中。《论语·雍也》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3](“之”指“仁”)。《论语·述而》提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1]。孔子认为,仁爱的人心胸坦荡悠然自得,能够安贫乐道而没有忧愁。因为博大的仁爱之情使心灵安详,所以孔子享受仁爱之乐而不知老之将至。孟子因为内心氤氲仁爱之情故身心挥洒浩然之气。“仁爱”不仅是高尚的思想,而且是快乐的情感。“仁”就是“乐”,是最高级的精神享受,由此看来,实施利他思想的个体捐助行为,作为一种仁爱行为,会让捐助主体得到快乐。
三、利他思想影响个人捐助的理性作用与情感作用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表明,个人安全、社会归属、爱与被爱、被人尊重、自我实现等动机和需要,是个体捐助主体实行利他思想的内在心理机制。由此可见,利他思想与行为包含必然性的个人需要,纯粹的利他思想只存在于有限的情境中,如坚贞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或偶发的下意识行为等。佛教认为这正是人生之苦的根源,也是人不能“了生脱死”的根源。佛教还认为,行善希冀回报,哪怕只是精神回报,也不是真行善;只有完全忘我的行善才是至善。就普遍人性来说,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量个体捐助行为表明,绝大多数捐助人都期望得到回报,但不是物质回报而是精神回报。心理研究发现,在捐赠决策过程中:一方面,那些心情快乐的人,往往更乐于进行个体捐助,从中获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另一方面,某些身处逆境心情悲伤的人,也往往会选择个体捐助,借此消除内疚或哀伤等负面情绪以减缓心理压力。当人们祈望被宽恕时往往更易于产生慈善之举,一旦人们因为做了亏心事而良心不安,他们往往会选择帮助他人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此外,对当事人或某项目的感同身受心理,也是影响个体捐助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人们往往更加愿意帮助那些与自己个性特点或个人经历相近的人。个体捐助行为,既可以让快乐的人经由雪中送炭的慈善行为,让个人心理锦上添花倍感快乐;也可以使悲伤的人凭借个体捐助产生的“心理代偿”作用,缓解心理压力得到心理平衡。总之,体现利他思想的个体捐助行为,包含着必然的合情入理的利己需要。因此,尽管个体捐助被认为是无私的,但很多筹募者还是会设置奖励回报,例如“感谢卡”或其他让支持者感受到幸福等情感的奖励,奖励的设计能够体现出强大的情感回馈。
然而同时,人是具有思想感情的宇宙精灵,思想是理性的,感情是感性的。理性的思想与感性的感情,在理论上可以截然分开,而在行为上却融为一体。对于具体的人而言,总是思想包含情感,情感包含思想,思想与感情相互交织,水乳交融。当特定思想与情感稳固地交织在一起时,会形成一种不轻易改变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就是情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通常为不同层次的个人情操所主导。情感在利他思想转化为个体捐助行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较之其理性作用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作为心理现象之一的情感,对人的生命和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西方学者认为,情商是个体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本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以及人生未来的关键性的品质要素。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2]
中国传统文化之利他思想之所以能转化为个人捐助行为,是因为它具有理性感召和情感激励的双重作用。在理性方面,利他思想体现真善美的价值观,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要求,因而为捐助主体所认同所赞赏,乐于自觉自愿地付诸实践。在情感方面,利他思想包含利他情感,对人我关系的处理合乎人之常情,顺应人们以情感诉求为核心的心理机制,因而便于捐助主体实行之。利他思想向个体捐助行为转化的机理,既包括上述利他思想的理性功能与情感功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以动机为基点,以需要为目的,以情感诉求为枢纽的心理机制。人的行为活动是受动机支配和调节的。动机是极其重要的心理现象,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关键性影响。动机、心理过程和心理特性,是人的心理现象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心理学上,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个体行为,并使行为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内部驱动力,即人的各种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并向着某一目标进行的。[13]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需要,就不会有行动的目标,需要反映某种客观的要求和必要性,是个人行为产生的源泉。[13]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由以下由低级到高级五个等级的需要构成的,即由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与孟子的“人的恻隐之心是与生俱来的”观点一样,马斯洛认为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天生的,正是这些“天生的”需要成为激励和指引个体行为的巨大力量。
慈善事业是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个体捐助是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途径。个体捐助较之团体捐助,更能体现慈善行为的利他本质。因此,对于慈善机构来说,一方面要把对人性的认识确立在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利他思想中合情入理的利己因素,认识个体捐助行为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个体捐助者的情感诉求,把握好个体捐助者以情感诉求为枢纽的心理机制,以捐助者的情感需要为主要动力,推进个体捐助行为。要想促进“我要捐”而不是“要我捐”的自觉的个体捐助行为,归根结底要在个体社会存在状态和社会总体发展状态的基础上,实现公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群众个人情操的不断升华。为此,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现实生活和时代特点,批判性地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扬弃其中某些唯心主义糟粕,吸取其中的利他思想之合理内核。要遵循社会规律、文化规律和心理规律,充分发掘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人我互利和谐共存的利他思想,以及这种利他思想内涵的助人为乐、利他为美的大爱情怀,以此推进我国当代的个体捐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