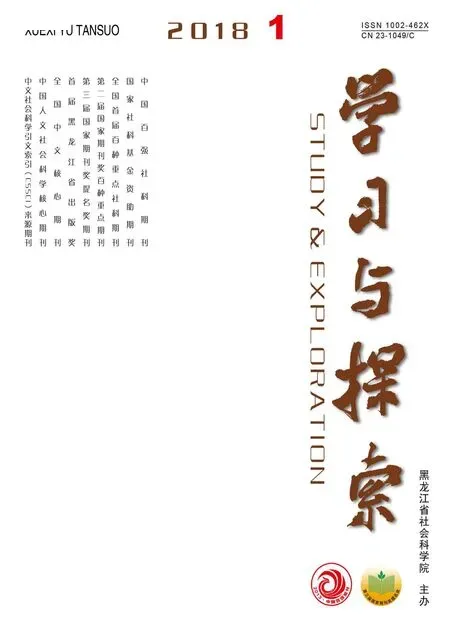论胡先骕的人文思想
柴文华,张凛凛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广义的“人文”与“自然”相对,狭义的“人文”与“自然”“神学”“科学”相对。“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义近,指尊重人、关心人、热爱人等。“人文主义”即是“人文精神”的体系化或逻辑化,与“人本主义”义近,与“自然主义”“神本主义”“科学主义”相对。“人文学科”应该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学、人学、文学、历史学等。
在“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中,胡先骕特色鲜明,他集植物学家、教育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有自己的哲学理念、科学智慧和诗人情怀,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他以美国文学批评家、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学说为思想基础,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过激观点进行了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人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
一、思想基础
胡先骕对白璧德本人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学精深博大,成一家言,西洋古今各国文学而外,兼通政术哲理,又娴梵文及巴利文,于佛学深造有得。虽未通汉文,然于吾国古籍之译成西文者靡不读,特留心吾国事,凡各国人所著书,涉及吾国者,亦莫不寓目”[1]。他认为白璧德是一位中西合璧、文哲兼通、关心中国的思想家。
胡先骕对白璧德的学说内容做了较为详细地介绍。
首先,白璧德的学说包含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白璧德认为,西方近代“物质之学”“科学实业”昌盛,而“人生之道理”“宗教道德之势力”衰微,突出表现在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趋于功利而自以为是;社会上是非善恶观念淡薄,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互相残杀。究其原因,主要是科学异化和物人不分。科学发达,本来应该增加人们的福祉,但现在却成了“桎梏刀剑”;物质和人事本来各有各的规律,不能相互替代,但现在却“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导致了“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等[1]。白璧德不仅批判了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科学异化和物人不分,而且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主要思潮也进行了批评。白璧德认为,以文艺复兴和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近代西方运动本质上是“极端扩张”的运动:其一,以人的幸福和快乐为目的的知识和征服自然能力的扩张,以培根为代表,“注重组织与效率,而崇信机械之功用”[1];其二,情感的扩张,以卢梭为代表,“对人则尚博爱,对己则尚个性之表现”[1]。这两者统称为人道主义,其人生哲学的重心是进步主义,导致了以物质代文化,以情感代道德的结果。原以为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行就能进入“神圣光明之域”,实际上是向大战场而行。当时以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为代表的“先觉者”已经意识到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的负面效应,他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成为当时的热销书。
其次,白璧德在批判西方近代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人文主义学说。白璧德认为:“盖人事自有其律,今当研究人事之律以治人事,然亦当力求精确,如彼科学家之于物质然。”[1]即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人自身的规律以治理人事,并建立在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从而使人们都知道“为人之正道”。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从哪里获取“为人之正道”呢?白璧德认为,“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而归一之”[1]。具体而言,“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至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1]也就是在广泛吸收东西先贤学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变化”,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1]“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赡,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1]。胡先骕非常赞赏这种人文主义,认为“有心人闻先生之说者,莫不心悦而诚服也。”[1]
最后,白璧德重视东方特别是中国“古昔”文化。白璧德不否认中国文化有落后的地方,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认为不应该“倾水弃孩”,“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而应该“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1]。中国文化优于他国文化之处在于“中国立国之根基,乃在道德也”[1]。白璧德引用一位法国批评家的话说,“中国向来重视道德观念,固矣。而此道德观念,又适合于人文主义者也,其道德观念,非如今日欧洲之为自然主义的,亦非如古今印度之为宗教的。中国人所重视者,为人生斯世,人与人间之道德关系。”[1]白璧德认为,中国文化重视现实的人伦关系,其重视道德的传统最符合人文主义。白璧德还从批判实验主义的角度谈论过孔子,他的理论前提是:“彼古来伟大之旧说,非他,盖千百年实在之经验之总汇也。”[1]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的学说不仅影响了之后的两千余年,更是对他生前数千年道德经验的总结。白璧德引用一位汉学家的话说:“孔子……为民族之先觉,取荒古之经籍,于其深奥之义理,加以精确联贯之解释,而昭示世人。又周游列国,大声疾呼,力言其国古来逐渐积累而成之道德,切宜遵守无失。”[1]建立在无数实在经验基础上的孔子学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有助于解决人类精神的统一问题。孔子认为人类的共性在于“自制之礼”,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等人文主义哲人的观点是契合的。主要观点在于“若人诚欲为人,则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于此天性加以制裁,使为有节制之平均发展”[1]。白璧德表示:“尝佩孔子见解之完善。盖孔子并不指摘同情心为不当,(孔子屡言仁,中即含同情心之义),不过应加以选择限制耳。”[1]“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1]白璧德在这里对孔子的“克己”“中庸”说等进行了充分肯定。
胡先骕是在中国较早介绍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的,尽管用的是文言文,且自认为“不免失真”[1],但总体上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精髓的把握是准确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是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传统批判的产物,其核心内容是:提倡“人律”,批判人的物化,坚持“适度”的原则,主张“内在制约”。其包含现代性反思、提倡“节制”和“中庸”等思想,颇具中国传统道德特色。应当指出的是,胡先骕翻译和介绍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翻译和介绍,而是为了给“学衡派”寻求批判新文化运动、倡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工具,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又恰恰具有这样的底蕴,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包括胡先骕在内的“学衡派”学人“攻玉”的“他山之石”和提倡人文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批评
承继白璧德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思路,胡先骕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及其观点提出了批评。
总体而言,胡先骕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功利主义者,倡导的是功利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美德精神如中正、克己等相违背,学问根底浅薄,喜欢标新立异,听不进不同意见,不辨是非,不知国情,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灭和西方学说的风靡,后果严重。如他所云:“即彼自命为新文化之前锋者……其求学之时,惟一之愿望,为在社会上居高位,享盛名。自来既无中正之修养,故极喜标奇立异之学说,以自显其高明。既不知克己复礼为人生所不可缺之训练,故易蹈欧西浪漫主义之覆辙,而疾视一切之节制。对于中西人文学问,俱仅浅尝,故不能辨别是非,完全不顾国情与民族性之何若。但以大而无当之学说相尚,同时复不受切磋,断不容他人或持异议,有之则必强词夺理以诋諆之。结果养成一种虚憍之学阀,徒知餔他人之糟,啜他人之糟,而自以为得,使中国旧有之文化,日就澌灭,欧西偏激之学说,风靡全国,皆此种学者之罪也。”[2]新文化运动者所提倡的艺术、哲学、文学是“冒有精神文明之名,故其为害,较纯粹之功利主义为尤烈焉”[2]。他们“己不立,能立人;己不达,能达人,天下有此理乎?……终无补于世道人心耳”[2]。
我国复杂的有季节性特征的气候条件、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独特历史背景,使得雾霾污染呈现较为突出的复合性特征。也就是说,从地理空间上看,雾霾污染呈现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趋势,污染浓度高值区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三角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大区域,其中京津冀地区污染最为严重。②
胡先骕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盲目学习西方的做法,认为那样会出现“买椟弃珠”的后果。他指出,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以后,西学蜂拥而至,“孰知西方文化之危机,已挟西方文化而俱来,国性已将完全澌灭,吾黄胄之前途,方日趋于黑暗乎。”[2]胡先骕自我表白说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因为他亲受西方教育,又是“治物质科学之人”[2],但他说的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针对“吾人之求西方文化之动机”[2]而言的。白璧德“以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鄙弃古学,不免有倾水弃儿之病,吾则谓吾人之习西学,亦适得买椟还珠之结果,不但买欧人之椟而还其珠也,且以尚椟弃珠之故,至将固有之珠而亦弃之”[2]。胡先骕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学的学习仅得其皮毛,未学到精髓。不仅如此,连自己家的珍宝也丢弃了,因而犯了买椟还珠和弃固有之珠两大错误。
胡先骕还专门批评了胡适的一些文学观点。其一,死活文学之说。胡适认为“中国的古文,在两千年前已经成了一种死文字”,“死文学决不能产生活文学。”[3]胡先骕认为这种观点“毫无充分之理由”。比如,《史记》与杜诗,是我国文学中的代表作,它们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永恒价值,岂能说成是“死文字”或“死文学”?这不但“不能取信于人又岂由衷之言哉!”[3]胡适自己要创造一种白话文体,“如诗外有词,词外有曲,各行其是,亦未尝不可。”[3]但把中国传统文学硬说成是“死文字”或“死文学”,而自己提倡的都是“活文字”或“活文学”,自命为正统,这不仅欺世罔人,而且很难有生命力。事实上,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从未产生一种出类拔萃之作品”[3],原因很明显,因为“无欧洲诸国历代相传文学之风尚,无酝酿创造新文学之环境,复无适当之文学技术上训练,强欲效他人之颦,取他人之某种主义,生吞而活剥之,无怪其无所成就也”[3]。说得严重一点,“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若以此为归宿,则难乎其为中国之文学已。”[3]其二,“想说啥说啥”的自由表达说。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论有一种主张,即“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这么说就这么说”[3]。胡先骕指出,这话乍一看有些道理,似乎有“修辞立其诚”之意,但仔细推敲起来却很难站得住脚,其含义犹如滔天洪水冲决一切堤坝,恣意横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就是不问此话是否应该说,是否应该于此处说;“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就是不问此话是否合理,“是否称题,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动人,是否坚确明辨可以服众。”[3]其结果便是“意之所至,‘臭尸’‘溲便’之辞,老妪骂街之言,甚至伧夫走卒谑浪笑傲之语,无不可形诸笔墨”[3],“此种之革新运动,即使成功,亦无价值之可言。”[3]
“学衡派”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派别,它与新文化运动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对提倡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批判是“学衡派”学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其中以梅光迪批判的最为激烈。他发表有《评提倡新文化者》等文,认为提倡新文化者是诡辩家而非思想家;是模仿家而非创造家;是功名之士而非学问家等。胡先骕的批判与梅光迪的思路大体相同。这种批判具有双重性:其一,具有合理性。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开时代风气之先,在引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也有偏激的一面,即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近代文化的盲目推崇。而胡先骕并非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认为可以“各行其是”,他所反对的是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水弃孩”。这应该是理性的、清醒的。因为我们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盘西化”,我们所要走的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既需要向西方学习,也需要汲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资源。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包括胡先骕在内的“学衡派”学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守护、转化和弘扬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和借鉴价值,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其二,具有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对新文化运动批判过度,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维护有余、分析不足,未能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这不仅是胡先骕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包括“学衡派”在内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共同局限性。
三、哲学人学思想
胡先骕虽然主要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但也有自己的哲学理念,主要表现在他的人论中。
胡先骕认为,人类有两点是与动物类似的:一是身体的构造,二是情欲;有三点是动物没有而人所独有的,理智、道德与宗教观念和自制力。这是从“人禽之辨”中揭示人的特质,是一种哲学人学思想。正因为人类有理智、有道德与宗教观念、有自制力,才无愧于为“万物之灵”,才创造了文明。按胡先骕自己的话说:“以有此人类所独具之要素,人类之行为乃超于情感之上,至有舍生取义之事,更上者乃有超乎理智之上之玄悟。故释迦能弃尊位与亲属而不顾而求出世之法。人类之异于禽兽者,以此;人类之能上进、文明之能光大者,以此。”[4]
在胡先骕看来,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智、性情、道德、自制力等都是需要通过训练来提升的。就幼童来讲,他们没有经过上述训练,与成人相去甚远。“饥则啼,饱则嘻,见食物玩物则索,其姊若弟不与之,则攘夺斗殴,其父母呵责之,则躃踊号哭;必也年事稍长,知识日开,自制之力始渐增进。成人未有以小儿行为为楷则者,非以其任性不知自制,而近于禽兽耶?”[4]就“成人”而言,人人心中都有“理欲之战”,理胜欲者为君子,反之为小人。但要做到理胜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成为君子,“必须有勇猛精进之道德训练”[4]。
就人的“自制之力”而言,胡先骕认为主要表现在遵守礼法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社会,都不能没有礼法,否则人们不能一日安居。他分别批评了卢梭的“民约论”、尼采的“超人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等,认为这些学说的共同特征是提倡本能冲动,违背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节制”之德。
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核心,很早就关注到人性问题,陆续出现了“性相近”“食色,性也”“性善”“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恶”“性三品”“性善恶混”“双重人性论”等学说类型。胡先骕非常赞赏汉代扬雄的“善恶混”说,认为“人性之为两元,扬子所谓善恶混者,殆不刊之论”[4]。虽为“上智”之人,其情欲和普通人一样,与禽兽没有什么差别。但他的理智、道德、宗教观念足以让他不断进步,他的自制力足以抵御利欲的诱惑。虽为“下愚”之人,除了先天就有“罪犯性与精神病者”[4],都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都具有“自制之力”。概括地讲,“上智”之人的人性中包含恶的成分,“下愚”之人的人性中包含有善的成分,因而不论是圣贤还是常人,其人性中都兼含善恶。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和孔孟荀的人性论相矛盾呢?胡先骕对此做了辩护,他认为:“孔教虽主性善,然不过以为人性具有为善之端倪,而要以克己复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工夫。……孟子虽言性善,然不过以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各具仁、义、礼、智之‘端’而已。荀子……主性恶之说,……以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4]所以“古今中外之圣贤,未有以人性自来即能止于至善者也”[4]。
从胡先骕对人的阐释来看,其观点属于“哲学人学”中对存在事实本体的探讨。人学可以分为“科学人学”和“哲学人学”两大类。“科学人学”侧重于用实证的方法对人的形而下世界做量化研究,包括考古人类学、民族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心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等。“哲学人学”侧重于用实证和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对人做形而上的纯思,是一种对人的本体论结构进行思考和建构的观念体系。“哲学人学”所可能涵盖的对象是多方面的,如存在的事实本体,即在“人禽之辨”中所凸显出来的人的本质特征;存在的价值本体,即从“应当”的角度所展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即做人的最高标准[5]。人对人自身的认知不会穷尽,我们可以从多维视域去探究。如果高度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是具有自觉性并能不断使之内化和外化的生物,内化即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等,外化即是不断调适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胡先骕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理智、道德和宗教观念、节制力等,这可以归结为一种理性人类学、道德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相互结合的观点,的确抓住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元素,对我们今天理解哲学人学也有帮助。人性善恶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是用道德判断去说明人性,胡先骕认同扬雄的“善恶混”说,亦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
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
胡先骕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之一,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也有明显的“尊儒黜道”倾向。
胡先骕对儒学是极力推崇的。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文化发源国,构成世界的文化中枢之一,虽然数千年来屡遭内乱外患,但一直巍然挺立,这绝非偶然现象。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能扩张版图,同化异族,而胡先骕认为这只是表面观察,事实上,“吾族真正之大成绩,则在数千年中能创造保持一种非宗教而以道德为根据之人文主义,终始勿渝也。”[2]这种人文主义是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孔子的学说尽人皆知,包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己复礼,以知仁勇三达德,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者也,又以中庸为尚,而不以过与不及为教者也”[2]。后来孟子、荀子把孔子学说发扬光大,加上汉武帝的表章及宋明程朱陆王诸贤之讲求,遂成为“中国惟一之习尚”[2]。虽然思想定于一尊可能产生某种束缚,但总体而言,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使得“匹夫匹妇每有过人之行,惊人之节”[2]。白璧德“以为中国习尚,有高出于欧西之人文主义者,以其全以道德为基础故,洵知言也”[2]。胡先骕还指出:“自孔子同时主张博学笃行以来,知行合一,已为不刊之论。泛观欧西近世学术史,每觉有博学明辨与笃行无关之感,于是知中国文化之精美,而能推知其所以能保持至于今日之故也。”[2]面对当时“政府官僚之腐败”“国民道德之堕落”[2],胡先骕坚决反对西方的功利主义,大力提倡儒家所倡导的“以节制为元素之旧道德”[2]。胡先骕所期待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发达,新旧文化咸能稳固,社会进步,政治修明。具体来讲:“庶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万不可以程朱为腐儒,以克己复礼为迂阔。一人固可同时为牛顿、达尔文、瓦特、爱迪生,与孔子、孟子也。”[2]
胡先骕对以道家为重心的非儒学说多有批评,这种批评是以文学史叙述为背景的。胡先骕在文学上对浪漫主义一派主要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浪漫派徘徊于追忆与希望之间,“不甘为遵礼守法之健全国民”,一味追求“归真返璞”“返乎自然”[4]。从中国文学史来看,浪漫主义的危害非常明显。中国思想界的浪漫主义首推老庄。老子的无为而治、鸡鸣犬吠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与西方卢梭的返乎自然是同一宗旨,“不协于人事也”[4]。庄子的逍遥齐物,“薄礼乐刑政之用,泯是非义利之辨,极端之个人主义之鼻祖也”[4]。“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之言……与标准人生及一元哲学之宗旨大相背驰也。”[4]这些末流邪说庞杂诡谲,在当时充斥中国,“杨墨各趋其极端;申韩仪秦,各以曲说行其志,而遗害于天下。”[4]就文学而言,商周时期的文学代表着北方民族的民族性,所以《三百篇》咏歌刺叹,均以人事为归。屈原的《离骚》开南方文学之先河,秉承了楚人好鬼的习惯,“藻缋以美人香草之辞,遂为后世浪漫文学不祧之宗”[4]。尽管屈原有忠君爱国之忱,“然究不若变风变雅之真切也,而末流所届,乃有助教冬郎之靡丽,寖至疑云疑雨之淫纤矣”[4]。到了晋代,老庄之学大兴,浪漫主义风行,“人尚玄言,世轻笃行,不亲官守,谓之雅远;不矜细行,谓之旷达。上者不过楚狂接舆之徒,下者不惜为名教之罪人、社会之蟊贼,如嵇康之自承不堪、刘伶之酗酒裸逐,皆其时所谓贤士大夫也。”[4]当时的佛学也是附会老庄,“未知佛家出世之要旨,复鄙弃儒家入世之精义。”[4]六朝时期,文体益坏,“诗歌之靡丽,骈文之浮嚣,彰彰在人耳目”[4]。胡先骕认为中国的浪漫主义思想,对国家社会的消极影响很大,令人恐惧。同时浪漫主义对个人行为的消极影响也很大,具体表现为“喜矜奇立异,破弃礼法,以自鸣高尚”[4]。他们自命为才子或名士,扬言礼法非为我辈而设。“如刘伶之裸体延宾,究为佯狂奇诡,不近人情也”[4]。
从胡先骕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来看,他的基本立场是弘扬以儒家传统伦理为重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在近现代命运多舛,出现过被边缘化的状态,但在今天却迎来了“一阳来复”“柳暗花明”的转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我们应该像包括胡先骕在内的“学衡派”学人呵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样,以同情和敬意对待她,立足现代视域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积极努力。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胡先骕对以儒家传统伦理为重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包含有片面化因素,因为他未能深刻指出传统儒家的负面元素和危害。胡先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的另一面是基于反省浪漫主义对以老庄为核心的非儒思想的批评,主要揭示其蔑弃礼法、主张放任、返归自然等所导致的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其中固然有理之所存,但他对包括道家、墨家等非儒学派学说的理解显然不够全面真实,不利于人们把握它们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事实上,不论是道家还是墨家等学派都有其自身的独特和深刻之处,比如道家的批判精神、自由意识、哲学思辨、自然美学,墨家的科学精神、逻辑体系、平民意识、节俭思想等都具有现实生命力,也应视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胡先骕:《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1922年第3期。
[2] 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1922年第4期。
[3] 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1923年第18期。
[4] 胡先骕:《文学之标准》,《学衡》1924年第31期。
[5] 柴文华等:《中国人伦学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