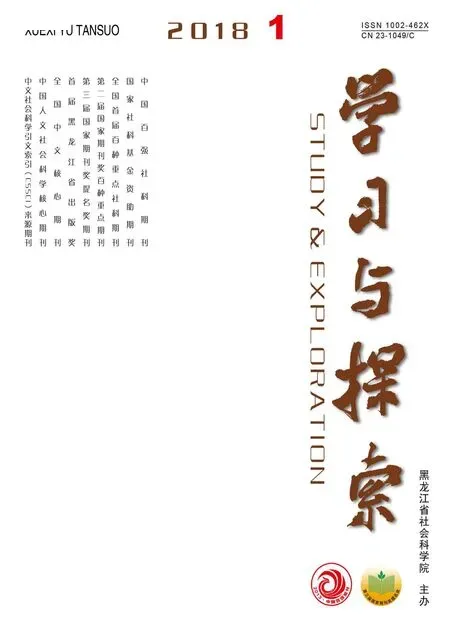时间形式的时候化: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及其当代现状
郑 作 彧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武汉 430074)
一、社会时间形式的基本概念
在任何学术领域当中,时间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一直以来,各种时间研究若不是将时间视为一种既定的物理事实,就是将其视为一种抽象的心理建构。因此,时间研究若不是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还有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近乎玄学的讨论,但仍不脱离“物理时间—心理时间”这条思考光谱[1]。不过,最晚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开始,时间就获得了独特的社会学意涵,让社会学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学科观点的时间研究途径。涂尔干指出,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同时这种制度也会构筑出有相应韵律的社会集体生活[2]。例如通过时间历法的建立,社会群体能不约而同地实践团圆围炉、包粽子赛龙舟、吃月饼赏月等活动。以此观点视之,时间既非实存物质,也不是心理建构,而是自人际关系之间生成的“社会事实”,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时间”[3]。以此观点视之,时间也不会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物,而是可以一方面借由对时间制度的分析、另一方面通过经验研究方法(例如“时间运用调查”(time-use survey))对相应的特定时间制度下的行动与互动所进行的调查来加以呈现与研究[4]。于是时间也成为社会学当中相当值得研究且不可忽略的主题之一[5][6]。
虽然涂尔干的社会时间概念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但细致地看,可以发现在当中有涂尔干没有明确指出、但概念上却可以细致区别出来的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时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时间制度不仅是单位的划分,例如月、周、日、分、秒等,而且这些单位也会被赋予实践意义,例如工作时间、下班时间、节庆假日等等。这些制度虽然不是绝对的律令,逼迫所有人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但它会形成一种行动参照框架而影响行动。时间这种外在影响行动的制度规范层面,可以将之抽象地称为“社会时间结构”。另一个层面,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根据自身所处的时间结构,形成一种安排日常行动与协调社会互动的观念与实践方式,并进而形成整体社会运作的韵律样态。这种透过观念与实践所形塑成的行动与互动模式,本文称为“社会时间形式”*社会时间结构与社会时间形式,以下一律各自简称为时间结构与时间形式。。而这两个层面虽然在概念上可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也是相互交融无法截然二分的。因为一方面社会制度是实践的参照,亦即时间结构架构出了时间形式;但另一方面,也唯有人们真的参照法规来实践,才成就了社会制度的有效性,即时间形式让时间结构得以有效成形[7]。
一旦考虑到时间具有社会事实的面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时间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镶嵌在社会当中,并且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8]。近年来有不少研究指出,当代社会的时间跟涂尔干所描述的他那个时代的时间已经产生了差异。许多学者也纷纷使用不同的理论概念来描述时间在近代的改变。例如,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加速流通周转以增加获利,造就加速了生产与消费的后福特主义,形成“时空压缩”的现象[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提出了“时间的虚化”,指出时间的测量因为全球性的标准化,让今天的时间从空间地点分化开来,造成社会同步关系从特定的地方脱离开来了[10][11]。而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在信息化的网络社会当中,社会秩序产生了混乱,社会生活出现了越来越普遍的不连续性与韵律的解构,造就了“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12]。罗萨(Hartmut Rosa)则总结这些看法,认为造成去同步化的“加速”是当代社会时间的核心特质,并且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世界的运作因为各自的速率不同,造成彼此去同步化、脱节开来,因此导致了新的异化形式[13][14]。*当然,讨论近代时间的改变的学者,远远比本文所举出的这几位还要多。然而由于篇幅与主题的限制,本文无法对文献进行详细的综述,只能列举几位代表性学者。其他更多的详细整理,参见:Rosa,Die Vera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05;Cheng,Soziale Geschwindigkeit: Ein theoretischer Grundriβ und eine zeitpolitische Fragestellung,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2012.
不论是“压缩”“虚空化”“无时间”还是“加速”,这些理论都提醒我们,时间的改变是今天时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这些理论却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虽然都声称在讨论社会时间并且强调社会时间有着不同于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特殊性质,但他们对时间概念的使用却都相当随意,既没有分析时间结构、也没有探讨时间形式的相应改变。这使得他们的社会时间理论实质上是缺乏经验基础的玄妙概念[15][16]。
如果时间的改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但过往的理论却因为缺乏经验基础而具有不足之处,那么坚守涂尔干的社会时间概念,分析时间结构与时间形式的改变,也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以弥补过往研究的缺失、提出具有更坚实的基础的时间社会学理论。
关于时间结构的改变,过去已经有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然而时间形式的改变至今却少有综合性的分析,尤其是时间形式反映了在时间结构当中人类行动乃至整体社会活动的运作逻辑。了解时间形式也就是了解人类生活与社会运作的方式,因此对时间形式的改变进行分析与探讨有其重要性。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之下,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随着时间结构的改变时间形式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具体而言,本文的任务在于分析面对时间制度的变迁,相应的生活实践与互动安排模式产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并且进一步追问这种转变会为当代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
尽管本文主要将聚焦于时间形式的改变,但为了分析的完整性,依然会根据论证的需要而交代时间结构及其变迁。今天学界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即人类历史当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主要是从最早的自然时间结构经过标准时间结构而成为今天越来越显著的弹性时间结构。因此相应的时间形式分析,以下便对应这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
二、时间结构的标准化与时间形式的时序化
1. 从自然时间结构到标准时间结构
今天,人们一拿起手表或抬头看看时钟,许多时候时间大多都以“秒”为单位、标准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若以历史的层面观之,如此精致的时间结构其实是相当近代的事。一般认为,在钟表发明之前,时间结构主要奠基在自然变迁的规律变化之上[17]。尤其在农业社会,自然的变化与人类生产息息相关。当然,在这一阶段,人们可以根据宗教因素(例如“公元”“圣诞节”)、政治因素(例如“年号”)或文化因素(例如以七日为一周、“中秋节”),将时间单位赋予了人为的意义,促成人为的规律性集体行动,构成了时间最原初的社会性结构意涵[18][19]。然而不论是自然环境的韵律,还是原初的时间测定和人为意义,相较于分秒必争的现代生活,都是相当松散且随地区而异。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所要担心的就是如何应对自然的变迁。因此,这个阶段也许可以称作“自然时间结构”。
自然时间形式一直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四季变换总是会决定人类外出是要穿棉袄还是短袖衬衫。但是近三百年来,相对松散的自然时间已经不是决定人们生活运作的主要时间结构了。近代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人为、抽象但又客观的时间符号,这可以作为时间结构变迁第二个阶段的一个特征。此一阶段的形成来自于多种同样重要的决定因素与后果的共同交织。其中,时间测量工具的发展与进步是较容易被经验所理解到的第一个基本要素。18世纪人类发明了钟摆并接着发明出钟表之后,人们出现了用数字准确计算、区分出时间单位的工具,用以单独抽象地呈现出脱离于自然环境情境的时间[10][11]。
时间测量工具的发展与进步,虽然让人们发展出抽象而精准的量化时间,但仅仅是时间长度的精准测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帮助。若时间测量工具要对社会生活发挥作用,则必须还要有第二个要素,亦即时间参照的标准化。“时间参照的标准化”意指在某一社会当中的日常生活,根据独立于个人或地方、普世同一的单位对时间进行划分,并把每个划分出来的时间点定置下来。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一个普世同一的时间参照,让每个人可以不受物理上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指出同一个时间点。例如,当代人们普世地将一天测定为24个小时,一年有12个月、365天;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指出同样一个被划定为“12月24号下午3点”的当下,以此去实现社会活动。泽鲁巴弗(Eviatar Zerubavel)的经典研究指出,跨地区的标准时间参照,最初起因于18世纪英国邮政机构的运作[20]。当时该机构为了让邮政服务能够有规律地运作,并务求信件包裹能按时送达,因此建立出一个跨地区的时间参照。那时即把伦敦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当作参照标准。后来随着铁路交通的兴起与电报的发明,让跨地区的活动渐渐蔓延到全球[19]。在中国,自晚清以来西风东渐,英国兴起的标准化的时间参照也逐渐传入中国,特别是当时作为租界的上海最先将此引入社会生活。1911年之后,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被视为现代化的代表,因此将标准时间参照普行于中国,直至今日。*关于标准时间结构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史,可参见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时间如何的标准是一回事,但标准时间如何细致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则是另外一回事。促使客观、标准化的量化时间符号和生活运作紧密地镶嵌在一起,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并堪为促使新时间结构的出现的第三个要素[21][22]56-97。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时间一直都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这样的重要性同时表现在两方面:量化时间,这牵涉到劳动力的价值估算;以及质化时间,这关系到所有劳动的同步化。马克思(Karl Marx)指出,让抽象的劳动力得以具体估算的重要转换媒介,就是工人进行生产劳动的时间[23]。工人将自己的劳动过程用时间单位加以衡量,然后将这段时间贩卖给资本家进行产品增值;这段劳动时间是属于资本家的资本而不属于工人自身、成为工人进行交易的异己对象物。于是标准时间在资本生成的过程中从生活的参照变成交易的依据。除此之外,在20世纪初期,工业资本主义企图透过对劳动力在每个分工部门的配置尽可能地提升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仅在于工作时间要多长,还更在于工作时间在何时。质的时间在此发挥着所有行动者的同步化的功能。人们必须依照一个既定的上下班的时候而行事。这最终透过工作时间法规的建立,影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全面的日常生活作息[22][24][1]112。
时间测量工具的进步、时间参照的标准化、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些因素最终催生出一个普遍共享的时间法规制度,且所有人都以此法规作为期待框架来运作生活。因此,这个时间结构可称作是“标准时间结构”。
2. 时间的时序化
在自然时间结构当中,日常生活大多依循着自然环境韵律而进行,因此“时间”较少是一个社会性的产物,也不太有制度化的原则。换言之,时间在此阶段,总的来看还不太具有社会性的形式,因此也许可以称之为“自然时间形式”[24]107。
如前所述,自然时间结构不曾完全丧失其重要性。但是时间结构的标准化,让人类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以自然环境韵律为主,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根据标准时间参照来加以安排[25]。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时间本身借着标准时间参照,是以一种抽象的、线性前后交替的数字象征系统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行动的安排与社会互动的协调,亦即时间形式,也对应标准时间参照来运作。这种时间形式,也许可以借用古希腊文称作“序时”(Χρνο, chronos)形式[26]21-34[27]309-328。“序时时间形式”于是也成为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最主要的时间形式。
虽然“序时”是一个存在已久的概念,在希腊神话当中它也具有时间之神的形象;但若不是伴随着时间结构的标准化,序时时间形式不可能出现成为一种主要的时间形式。也就是说,“序时”这种时间形式,并非先验既定的,而是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经由一连串让时间形式变成序时的过程,亦即一个时间形式的序时化(chronologization of temporal form)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若应对着时间结构标准化的过程来看,时间形式的序时化至少产自几个生成层次。
首先,每一个行动与互动事件,要从自然律则当中抽离、独立出来(本文称为“事件的单子化”)。在自然时间结构当中,人们由于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时间参照,因此行动与互动都必须借由一个自然环境现象或事件来当作客观指涉。这使得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甚至被自然环境所限制。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人类的生活已经渐渐可以不用受限于自然环境的韵律。就像大部分店家营业与歇业的时间,在正常情况下已经不再与天气和季节有关。行动的安排与互动的协调,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大多数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独立于自然环境而进行的。
其次,所有独立出来的行动与互动事件,以合于数字的方式加以单位化(“以合于数字性的方式单位化”以下简称为“数字化”)。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标准时间参照是一个由时间测量工具构筑出来的数字象征系统。这个数字象征系统成为人类行动安排与互动协调的参照系统。其中,每一个行动与互动事件都可以用一个时间测量工具所指涉出来的数字形式表现出来,每一个事件也因此占据着一个数字。事件必定占据着一个数字,但也只能占据一个数字。例如,一个婴儿的出生时间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是以一个时间测量工具所指出的数字时间点表示出来的。在成熟的标准时间结构当中,它甚至只能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一个婴儿的出生不可能是在一个时间测量工具无法指示出来的数字时间点发生。而且它只能占据一个数字时间点。一个婴儿不能既是在下午三点出生,但同时又是在晚上九点出生。
在“婴儿的出生”这个例子当中,同时也清楚地表现出一个情况:在时间结构标准化之后,单子化的事件强烈地受到数字逻辑的支配。若人们回到现象本身去看,事实上婴儿的出生并不以任何时间测量工具作为前提。一个婴儿就是这样出生了,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了。但婴儿在出生之后,为了将这个个体镶嵌进整个社会运作当中,因此把一个数字时间点冠在这个婴儿的出生之上(即出生证明、户口登记),自此这个婴儿的出生便占据了一个数字时间点。换句话说,出生时间点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且是事后冠在“出生”这件事上,而不是相反。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人们却总是说“这个婴儿在下午3点出生”,而几乎不会是“下午3点发生在婴儿出生的时刻”。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把时序时间参照当中的数字时间点当作是一个先验既存的外在条件,出生反而被当作是一个后来才发生在这数字时间点上的事。所以当人们问起“这个婴儿是何时出生的?”,总是通过如“他在下午3点出生的”这种方式来回答,且因为数字逻辑的支配性而不用再去追问“但何时是下午3点”这种问题。
这种具支配性的数字逻辑,不只是将从自然独立出来的事件放置进数字象征系统当中,而且这个数字象征系统由于是按照数字顺序排列下来的,因此便形成了时间序时化的第三个生成层次,亦即所有的事件都会以先后连续的方式排列起来。每一个事件都占据着一个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是镶嵌在整个依序排列的数字关系当中,这最终形成一个线性的排列顺序。于是所有事件会按照自己所对应的数字时间点,以“前、中、后”意即“之前、现在、稍后”或是“过去、当下、未来”这种形态呈现出来[28]。这种顺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从“前/之前/过去”经由“中/现在/当下”变成为 “后/稍后/未来”(亦即过去的未来,会经过现在,然后变成未来的过去),且这三个部分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彼此之间具有一种时态和因果的关系[29]。正是这种“置于顺序关系当中”,使得所有事件呈现出一种因果流逝性,成为序时时间形式的一种重要的特质。如埃里亚斯(Nobert Elias)所言:“时间”这个表述,其实也指出,两个、或更多持续变动的事件之流逝的位置和片段,是“置于关系当中”的[8]。
如此一来,标准时间结构当中的许多行动与互动事件,就不再依附着自然环境的律则或现象,而是一种以数字的(因此也变成为量化性的)、由时间测量工具所指涉出来的、依循因果时态顺序逻辑呈现出来的流逝性关系。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和莫顿(Robert K. Merton)曾疑惑,为何人们常用物理时间概念来描述社会时间[30],使得时间的社会性几乎被忽略或忘记。但是,若人们注意到伴随着标准时间结构而出现的“时间的序时化”,那么也许可以猜测性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序时化所构成的量化的、因果顺序的形态,正好和物理学的时间理解方式重叠在一起,而在近几个世纪自然科学所获得的成功的影响下,让人们渐渐遗忘了社会时间的社会建构性质与社会行动本质。于是,序时就成了支配行动和互动的主要实践形态[31]。
3. 普遍的同步性
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时间的序时化造就了一种与标准时间参照上的数字时间点对应起来的行动与互动原则。以此人们便得以订定一个如“9点出发、10点碰面、11点离开”的安排方式。在此之后,用不着预言家,每个人都可以预知什么时候自己会上班、下班,什么时候会放假。不过,当代社会在微观层面上,现代人彼此生活交织的复杂程度相当高;在宏观的层面上,当代社会已然是一个“世界社会”,各个领域的交织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所有行动者的所有行动与互动,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升,更进一步需要一个机制,让人们可以降低社会复杂性[32]。
在时间结构的标准化过程当中,如前所述,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有人渐渐都以同样的模式去安排生活。如此,人们不只可以通过时间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而且一旦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模式安排生活,那么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知道其他人在什么时候正在从事什么类型的事务。共同的时间安排模式并不是一种强制的行动命令,但会有一定的约束力,形成一个广泛的期待框架。例如,星期二下午3点,在期待框架中被认为是一个上班上课的时间:我在上班上课,同时也可以期待别人此时也在上班上课。大年初一是放假的日子,因此我放假的同时也可以期待别人也在放假。借此,社会的集体社会互动的构成也会更加容易。人们可以先行推测他人的行动,以此安排自身的行动[33]。就像是音乐会的举办人可以猜想,他应该要在晚上8点,而不是上午11点或是凌晨3点来举办音乐会,因为在普遍的同步性所带来的期待框架当中,人们在上午11点时正在上班,凌晨3点时正在睡觉,而晚上8点则是愿意参加文艺活动的下班后自由时间。或是在同步性高的社会群体当中,交通流量管控中心可以预测哪些时段是交通尖峰与离峰时段,以此安排交通号志的运作,维持交通的顺畅[34]。于是标准时间结构与序时时间形式,为社会运作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韵律性质:普遍的同步性。当然,也有某些职业的工作时间并不在此框架当中,乃至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生活运作也处于期待框架之外。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这些期待框架外的职业与生活也成为常态的例外,因此仍符合期待框架。例如,虽然大年初一是假日,但我仍可以期待餐厅是开业的,警察、消防队员是上班待命的。
但同时,普遍的同时性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谁该遵守由谁订定出来的、需要共同遵守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行动时态安排模式并不是由个人任意构筑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工作时间的分析便显露出来,一个时间制度对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也许是有利的,但对于另外一些社会群体来说却可能是有剥夺性的。这使得在普遍的同步性情境中,人们该如何观照与避免会带来剥削性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便成为时序时间形式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时间结构的标准化过程当中,这主要反映在相关法规在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工作时间的制定上。尤其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这特别表现在阶级之间的“时间权力”之争夺上[35];而工作时间则是最重要的斗争场域[36]。因此,时序时间形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便在于如何制定出一个较为公平的共有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特别是较为公平的工作时间法规[37][38]。在中国,标准工作时间法规的制定,主要起于1929年由当时南京政府所制订的《工厂法》,初步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8小时的原则,延长的工时则需多付给薪资,而一日最多只能延长两小时,每周工作总和仍不可超过48小时。这个法规的制订肇因于当时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兴起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影响,亦即是一个阶级斗争之下的场域产物[39]81-87。
4. 意外的时间化
到目前为止,关于日常生活的安排与社会互动的实践,都仅仅指有意图的行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计划表实现。人生当中总会遇到许多不是意图所欲实行的事件。这种非意图的事件,可以粗略分为两种。一种是正面、带来好处的,人们通常将之称作“惊喜”。爱情是最典型的例子。爱情总是没有原因、突然地发生。没有人知道何时会遇到真爱,真爱也没有办法计划与预料。它任何时刻都可能会发生,但在真正发生之前,没有人能料想到它真的会发生。换句话说,非意图的行动事件,比如爱情,并不处在标准时间结构的制度当中,也不处于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当中。爱情的发生只能靠缘分,它会发生就会发生、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
但如果非意图的行动交织之发生带来损害性的后果,那就不怎么浪漫了。会带来损害性、负面的非意图的行动交织之发生,通常称作“意外”。如同惊喜,意外无从预料与计划(人们也不会想计划)。它总是突然到来,且在意外真的发生之前,意外不被认为会发生。换言之,意外同样处在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之外[40]199[41]。意外的发生,就是那样发生了。比方驾驶人从来不会刻意、也没想到过要以两辆车相撞的方式产生社会互动,但车祸总是就那样发生了。
由于意外会带来损害,且因为意外处在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之外,因此它的发生会破坏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随即破坏掉行动时态配置模式,从而破坏整个行动与生活的秩序。所以人们在面对意外时,往往手足无措,生活接下来的计划也会打乱。为了能够继续行动与生活,在意外发生之后,人们必须要修复生活的时态秩序[42]。
虽然在意外发生之时,它是无以名状且无可把握与知晓的,但是当它发生之后,它却又是无可争议地存在着。因此,若要修复时态秩序,就必须得把已发生的意外摆置进行动的视野当中,亦即把已发生的意外放置进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当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将意外的发生赋予一个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之上的时间点,使之具有可追溯的因果关系[40]202[43]。比如“9·11”恐怖袭击、“二月”革命,就是直接用数字时间点去命名,以此修复被意外破坏的序时时间链[44]。将意外放置进序时时间链当中,以此修复行动时态模式的做法即“意外的时间化”,成为社会运作韵律相对立于“普遍的同步性”的另一项特质。
意外的时间化不止可以在意外发生之后重建时态秩序,这个时间形式的特质还有助于在事发之前去维护时态秩序。因为它将意外披上了一个时态因果的外衣,宛如在根本上意外必定伴随着一个原因,只要人们可以避免原因就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于是,人们便可以在意外没有发生的时候,相信既有的时态秩序,不用整天担忧行动的下一步可能并不会接续到行动的目的,而是接续到一个意外事件之中[45]。
意外一直都会发生,意外的时间化也总是当代社会运作的重要原则之一。然而在近五十年来当时间结构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变化,使得人们除了要面对已发生的事情以外,也得开始面对随着时间结构的改变发展出来的新状况。
三、时间结构的弹性化与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1.时间结构的弹性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开始使用一些术语例如去规范化、解构化、动力化以及最常使用、也是本文主要采用的术语:弹性化,来形容逐渐广泛地改变的时间结构[46]。当代时间结构因此也一般称作“弹性时间结构”。亚佩尔(FriedrikeBenthaus-Apel)整理并指出,时间结构弹性化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47]69:第一,社会生活韵律以弹性的方向去传统化,以往认为应是假日、睡觉的时间,而今越来越有可能是正在工作的时间;第二,社会与经济事务在时间层面上产生了弹性化,人们开始不去企求未来有个稳定发展的计划;第三,工作时间的弹性化。这三个层面当中,特别是工作时间的弹性化,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造成最根本的质变[47]70。换言之,弹性时间结构的出现,普遍被认为主要来自于工作时间弹性化[48]。
关于工作时间弹性化的起因,哈维对于后福特主义的讨论是一个经典研究。哈维指出,1973年之后兴起后福特主义不再追求生产效率极大化,而是更重视产品的创新与更替。这也代表企业转向更弹性的生产模式。为了因弹性积累的生产,劳动力的安排也必须更弹性。而弹性的劳动力安排就意味着弹性的工作时间[9]。由于哈维指出这一改变始于1973年,因此,这一年也许可以视作是第三个时间结构变迁阶段的起始点。
“弹性化”主要意指工作时间从标准工时偏离开来[49]。它必须奠基在标准工时、亦即标准时间结构之上。如果没有这种标准,就没有偏离、弹性可言。而“工作时间弹性化”(弹性工时)意指在标准工作时间的基础之上给予一段调整工作时间结构边界的弹性空间。所有延伸到“标准”的工作时间边界之外,或是萎缩到之内的工作时间形态,都因为具有松动了(特别是由工作时间法规所客观界定了的)既有时间结构边界的特征,而可以视作是弹性工时。轮班夜间工作、假日工作、部分工时工作等等,都包含在此范围之内。
弹性工时一般认为始于一家名为M.B.B. (Messerschmidt-Bölkow-Blohm)的德国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所实施的“错时上下班”(Gleitzeit)制度[50]。当时,该公司为了解决当地上下班时间交通堵塞的状况,因此于上下班开放一段时间可以弹性地上工与离开。这开始在标准工作时间结构上松脱了工作时间的边界性。1973年之后,弹性工时更是开始蔓延到各地的工作时间法规当中。被当作国内法规制订重要参考基础的德国,1992年制定的工作时间法开始清楚声明,虽然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但若是在6个月或24周之内每日工作时数平均不超过8小时,单日工作可延长至10小时,这等同于合法地宣示工作时间弹性化的可能性与空间。另外,由于服务业的成长,德国的夜间、假日与轮班工作比例也不断地攀升。1991年,夜间、假日与轮班工作占了所有劳动者的38%;但是在2004年大幅攀升到51%[51]。至于部分工时工作,根据OECD,在德国的比例近年来同样显著地持续攀升。2000年约七百多万人,到了2013年却已达约一千多万人,占了总劳动人口的1/4,且趋势从未减缓。
虽然在西方被视为弹性时间结构开端的错时上下班制度,在中国的实施相当晚,直到2010年前后才在一些交通繁忙的城市(如北京、沈阳、重庆)开始实施;但真正重要的弹性工作时间制度却较早便已进入实际操作层面[52]。根据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1995年3月颁布的《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标准工时制度为“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但同时《劳动法》第39条规定:“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36条、第38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5条对弹性工时制度做了进一步的确定:“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这为劳动行政部门确立了制度性的弹性工作时间。1994年国家劳动部颁布的《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也明确标示出中国的弹性工时制度的确立。
而在所有经济产业当中,一般认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制度的主要产业。*当然,实施弹性工时制度的不是只有第三产业;而且第三产业也有许多类型,因而无法一概而论说都施行了弹性工时制度。但是就比例而言,第三产业的确是施行弹性工时制度的主要经济产业,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间结构弹性化的趋势,因此具有代表性。关于弹性工时的历史发展、在各个产业当中的情况,以及其与时间结构弹性化之间的关系,详细的研究可参阅Promberger,Wieneuartigsind flexible Arbeitszeiten? Historische Grundlinien der Arbeitszeit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2005.第三产业的比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弹性工时的普遍程度[9]。而在近代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都在不断攀升,连带让弹性工时不只表现在工作法规上,也显著表现在就业人员的比例上。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之前,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一直都占所有就业人员的10%以下;然而改革开放之后,比例不断大幅攀升。截至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已经高达所有就业人员的40.6% 了[53]。即便是在其他以标准工时为主的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也同样因为国内近年来推行的“带薪休假”制度即鼓励民众可以在法定假日之外自行安排假期,因此让工时产生了弹性化趋势。虽然目前带薪休假制度在国内的推行进度略慢,但可以预见弹性工时势必会成为国内未来主要的工作时间形态[54][55]。进一步,整个时间结构也会随着弹性工时的蔓延而越来越弹性化,从而让弹性时间结构成为当代社会主要的时间结构类型。
之所以工作时间弹性化造就了时间结构全面的弹性化,是因为弹性工时制度与实施该制度的产业让许多人、而且有越来越多人生活不再由一个外在既与的结构性边界所划定,而是被给出了一定的弹性空间,让人们根据当下所需考虑的情况决定工作与自由时间。这使得时间结构的弹性化并不是仅存在于工作时间的范畴,而是必须让人们在全面去边界化的日常生活当中,根据情况重新去将生活组织边界化、结构起来[56][57]。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弹性时间结构”不是一个已经与“标准时间结构”完全断裂开来的全新的社会情境。如上所述,弹性化的时间结构奠基在标准时间结构之上;而且现代社会当中,不论哪里,目前都尚未出现“整个社会所有工作时间都弹性化”的极端情况,甚至事实上以标准工作时间为主的企业至今仍占大多数。换言之,“弹性化的时间结构”必须仅视作一个相对来说越来越显著的趋势过程[58]。不过,时间结构的弹性化也不仅降临在以弹性工时来进行工作的人们身上。由于在社会当中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因此,当有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时间结构被弹性化的时候,所有与此人相关的重要他人(例如家人)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时间结构弹性化的成长趋势越普遍影响力就会越大。
2. 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时间结构的弹性化,意指一个松动了时间标准性的有效性的趋势。卡斯特尔指出,弹性时间结构当中的时间越来越不是一个既与的因果事件链,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的共同性也越来越弱。行动的安排与互动的协调越来越依据情境变化而时常弹性变动,时间也因此越来越缺乏指示行动的标准性。这种缺乏行动指示功能的时间,卡斯特尔称作“无时间的时间”[12]。罗萨接续着此概念指出,由于“无时间的时间”不再具有预先指示事务的功能,因此人们必须自己去规划自己的时间计划,以构筑自身的行动和生活时态模式,重建时间的行动指示功能。罗萨把这种越来越普遍的时间重建任务,称作“时间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 der Zeit)[17]。
不过,不论是卡斯特尔还是罗萨都缺乏一个更透彻的阐释。因为“无时间的时间”和“时间的时间化”,其实都还隐含两种不同的时间形式。一种是“有时间的时间”或是“已经时间化的时间”。从卡斯特尔和罗萨的理论脉络来看,“有时间的时间”或是“已经时间化的时间”显然意指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有着清楚的标准时间参照,即井然的序时时间顺序以及有效性高的共有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这种时间形式显然即是上文所提到的“序时”时间形式。
伴随着时间结构的弹性化,序时时间形式已经越来越不具有优先的支配性,因此出现了另一种“无时间的时间”或是“没有时间化的时间”。“无时间的时间”或“没有时间化的时间”并不是“非时间”,只是这种时间的序时性已经被松动了。时间标准性变成一个仅是理想的参考,但行动互动事件不存在一个既与的数字时间点,而是散落、还原成行动互动事件自身。这种与“序时”截然不同的、伴随着时间结构弹性化而来的时间形式,也许可以借用古希腊文中与序时相对的词汇命名之“时候”(καιρó, kairos)。*Kairos在中文一般翻译成“时机”,亦即一个“机会时刻”。但正如下文将会提到的,kairos在原本古希腊文当中并没有带着 “机会”这一正面意涵,而是更接近中文的“时候”之意,这也是本文所欲采用的意思。“时机”这一正面相关意涵是在后来的神话与宗教的影响下所添加上的。虽然“时候”在中文当中被当作一个单独名词来使用是一个不怎么正规的做法,但由于kairos在当代欧美语境当中也是一个讳涩、非口语的词,因此“时候”这种非正规的中文名词反而也比较贴近欧美语境当中提到kairos的感觉。本文以下会更进一步讨论“时候”的概念,以彰显采用kairos以及将之译作“时候”的原因。在最早的希腊神话当中,“时候”是宙斯最小的儿子的名字,一个掌管“机运”的神祇[26]33。随后,特别是在基督教《圣经》的脉络当中,“时候”这个词汇被赋予了更多的宗教意涵,指涉一个由神给予的、带来机会与机缘的时间点,一个“恩典时刻”[27]5。虽然直到今天,“时候”一词仍大多是在宗教文本当中被使用,但如果特别不去看宗教赋予的神学意涵而是回到“时候”原先在古希腊文当中的字义,那么“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中立、普通的指涉“时间”的名词[27]33[59]。只不过“时候”时间不同于“序时”时间,并不是指一个连续的、流逝性的、可测量的量化时间,而是一种无连续性的、发生性的、质性的时间形式。在这种形式当中,“时候”是行动与互动事件的发生本身[60]。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以“时候”为表现型态的时间形式,本文称作“时候时间形式”。
“时候”是事件发生本身。这也就是说,“时候”的发生没有一个既定的时态关系。行动与互动没有既定的因果顺序,也没有事先就可以无疑地被给定发生的时间点。行动的安排与互动的协调就只在发生的时候发生。这句阐释“时候”的称谓,也许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以帮助概念的厘清。比如在时间结构标准化之后,如果人们有个可以正常运行的时钟、且这个时钟跟随着由BIPM所测定、发布的时间讯息来运作时,那么人们便可以指出一个客观的“9点”,且这个“9点”还可以指示人们在此当下该从事何种事务(比方上班打卡时间)。“9点”即是序时时间形式的一个表现形态,它处在一整个数字象征关系当中,亦即处在“10点之前”以及“8点之后”,因而具有一个前后交替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人们虽然拥有一个时钟,但世界上不存在着发布客观时间参照的BIPM机构,且这个时钟有电的时候就走得快一点、快没电的时候就走得慢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可以说“9点”就不再是一个被规定在序时时间链上的点,而仅发生在时钟的指针指在“9”这个数字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是9点,只要指针对在“9”这个数字上;但同样的,任何时候也都不再是9点,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标准时间参照,也没有一个序时时间顺序让9点具有序时时间形式当中的意义。“9点”于此就不再被序时地规定下来,而是被还原为“9点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这种“9点的发生只在9点发生的时候发生”,便是“时候”时间形式。
“时候”这种没有被序时化的时间形式,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出现方式。第一种是序时化不存在或是还没有开始,所以社会时间处在无序时化的状态。自然时间形式便属于此。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完全不存在时间结构的阶段,但是时间结构标准化之前,大部分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多将行动与互动的计划与记录联结上一个可共同经验的自然现象,或特殊的自然事件。不过什么自然现象或自然事件要拿来当作参照,多是任意随俗的。在这个阶段当中,行动与互动事件的计划与记录就随附在整体自然当中任何可能的现象或事件。
在时间形式的序时化当中,各个行动和互动事件被绑在标准时间参照的诸数字时间点上,且这种数字逻辑乃具有支配的优先性。因此,当人们询问关于行动交织时发生的问题、亦即“何时”问题时,在序时时间形式当中,往往都会去寻求一个标准时间参照所指涉出来的数字时间点加以对应之以当作答案。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序时化让“时候”时间形式就此消失了。相反地,在时间结构弹性化之后,开始出现了时间形式脱离序时的优先支配性,亦即罗萨所说的“去时间化”(Entzeitlichung)的趋势[61]419-450。这促使“时候”时间形式因为“去时间化”趋势而再次出现。
在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过程中,人们并没有真的完全放弃标准时间参照、共同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然而,由于后福特主义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情况当中拥有一个能将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弹性地搬移实际发生时间点的空间,因此事务和相应的数字时间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薄弱了。例如,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下午五点在期待框架中被认为是一个下班的时间,且大部分的人都遵循此期待框架在此时间点下班。但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形式(如错时上下班制度、轮班制等),以及越来越多参与这些工作时间形式的人,不再准时地在下午五点下班,而是下班时间会随着情况在一定范围当中被推移离下午五点。这时候,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人们必须把行动和互动事件的发生从一个确切的数字时间点松脱开来,使之无法再自然而然地可以用一个数字时间点指出来。例如,一位以不定时工作时间作为工作形态的员工,虽然就工作时间法规的规定,其最长工作时间有长度限制,但下班时间已经不再是一个标准时间参照能指出来的数字时间点,使得这位员工只能在他被给予的工作任务完成、得以下班的时候才能下班。
在此种情况中,“时候”并非单纯任意随俗地对应着自然环境的原始的行动交织型态,而是奠基在序时时间形式之上;但因为时间结构的改变,使得行动和互动程度上从序时数字时间点松脱、散落开来。这种“时候”的时间形式不是一种原初的时间形式,而是一个经由特殊变迁过程而来的结果。这种变化过程,本文称为“时间形式的时候化”(kairologization of temporal form)。
3. 有条件的同时性
伴随着时间的时候化而来的社会现象,可以粗略区分出个体以及集体两个层面。
在个体方面,以时间的时候化为原则的生活,首先是以弹性工时为主要工作型态的那些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事务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散落开来。但这些事务并不是完全交由个人凭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而是被规定一个事务必须完成的期限。如果人们任由这些事务散乱着,那么当逼近期限之时,就容易使事务全部堆在一起只能手忙脚乱。这也成为当代社会人们常面临“多任务”(multitasking)的危险的主要原因[69]244。为了避免多任务的麻烦,“时间管理”概念,便成为日常社会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任务之一[62]。每个面临时间形式时候化的人,都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于此,共同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的有效性也开始越来越弱。
因此,在集体的层面上,整个社会的普遍同步性也会越来越薄弱。由于社会依然相当复杂,人们依然需要行动与互动,因此普遍的同步性的弱化便造成整个社会的大范围的互动会越来越困难[63]。这会让人们越来越难评估其他人在当下正在从事何种事务。人们除了必须为避免自身“多任务”而安排自己的事务之外,也必须和其他需要互动的他人个别去协调和安排碰面、互动的时间[64]。于是,“普遍的同步性”开始被“有条件的同时性”取代,成为当代社会运作的特殊的韵律性质。“有条件的同时性”意指,由于时间的时候化所造成的普遍同步性的弱化,因此社会互动必须要满足如事前计划、行程安排和相互约定等特殊条件,这样将所有行动者加以同时化方可实现。
时候时间形式的“有条件的同时性”此一特质,也为社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问题来自于阶级斗争式的时间权力之平衡问题。然而,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越来越多人不再被一个具有控制力的时间规范所束缚,而是被给出一个空间,要人们(在期限之前)自己去规划处理事务的行程。这使得人们面临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个别地去和需要互动的他人协调一个互动的时间,并以此安排自己的规划。换句话说,时间权力去中心化了。时间权力的平衡与协调不再在于阶级之间,而是在于每个需要(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互动的人之间。
本文最后将会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建议,在弹性时间结构与时候时间形式当中,“时间生态学”可以是解决时间权力问题的可能出路。
4. 风险的常态化
“有条件的同时性”所处理的,是伴随着时间的时候化而散落开来的有意图要实现的行动互动事件。然而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事件是非意图性、有损害性,但却是偶然发生的。
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非意图、损害性的行动交织之发生会被当成意外,即排除在序时时间顺序之外而成为一个无可视见的行动交织之发生。除非在意外发生之后,为了修复序时时间形式才会将意外加以时序化。也就是说,“意外”被掩盖起来了。然而在时候时间形式当中,序时时间顺序在一定程度上散裂开来,让事件本来就不具有一个密切相连的数字时间点。若要使之确切发生,人们必须事前计划、自行组织、彼此协调,满足行动交织之发生的同时性条件。即具有支配性、掩盖意外的序时时间顺序松脱开来,因此非意图的损害性发生会渐渐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事件是理所当然、时间到了就会发生的,但也没有事件是一定不会发生的。于是,在满足同时性的条件时,除了意图要使之实现的事件之外,没有意图要使之实现的事件也会开始显露出来、且越来越被顾虑到。随着时间形式的时候化,有越来越多的意外人们并非对其一无所知,而是其存在于行动视野当中的既存事件、成为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顾及的事件;或是用佩罗 (Charles Perrow)的术语来说,即越来越多的意外在当代社会当中变成“常态意外”(normal accidents)。不过,由于时间的时候化,因而这种意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意料之外”,而是会被转进“风险”的范畴当中[65]。由于时间的时候化,使得非意图的损害性事件开始在行动的视野当中被视见并顾及到。这种情况,借用佩罗的说法,也许可以更准确地定义为“风险的常态化”,这成为时候时间形式当中对立于序时时间形式“有条件的同时性”的另一项特质。
近五十年来,风险论述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兴起,“风险”也成为一门重要的研究议题[39][66]529-548。风险的根本特质之一便在于风险来自于社会行动之中[67]。在所谓的“风险社会”(Risiko gesellschaft)当中,任何的行动都可能会伴随着非意图的损害。没有绝对的安全性,也没有无风险的行动[68]37。任何行动都是有风险的,也就是说,任何行动都会有产生风险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40]。
一个因为不确定性而会带来风险的行动,一方面意指当它带来损害时,它是这个损害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就算它最终没有带来损害,它还是有风险的[69]。于是这意味着,风险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言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概念[70],或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是风险社会,是因为把开放的未来当作风险而当下化了[68]45,而是说风险行动既不会带来损害、但也会带来损害。换言之,风险关涉的是一种既会发生、却也不会发生的损害事件。风险不指向过去、当下,也不关于未来,它不指向任何序时的时间;风险只指向损害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候。比如一座核电厂的兴建是有风险的,并不是因为它在未来可能会在哪个时间点带来辐射外泄,而是因为它会带来辐射外泄,不论这个辐射外泄是不是真的在哪个时间点发生。
不过,风险不只来自于行动的“不确定性”,否则它跟“意外”也就没有区别了。一个风险会伴随着一件意外而具体发生,但是意外的发生并不必然都是属于风险的范畴。在意外发生之前,没有人会想到意外会发生。意外是在意料之外的。但相反地,风险的发生却是在意料之中的。风险被标示为“不确定”,不只是说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是同时也表明人们知道风险是不确定的。于是,“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
风险不确定性的确定性,首先意指因为风险意识,所以人们知道风险是一件会发生的事;但人们无从知道,风险会以什么意外的形式发生[65]。其次,人们虽然不知道风险会以什么样的意外形式发生,但是人们却确切地知道风险会带来什么损害。例如,2011年3月11号,日本发生大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袭击核电厂而造成放射性物质外泄。海啸袭击核电厂而造成放射性物质外泄,是一则意外,因为人们没有意料到核电厂会因为海啸事件而造成放射性物质外泄;但是“放射性物质外泄”对于核电厂的存在来说却不是意外,而是一个早被意识到的风险(因此在德语当中,如核灾那样的风险往往也被描述为“有所意料的大型意外”即gröβter anzunehmender Unfall, GAU[74]361-379。同样地,一旦一件意外是被意料的事件,这则意外就会被转化为风险[40]201。
“风险是被知觉到的可能行动后果……‘风险’这个概念的使用,其实有个前提,亦即可能的损害事件的光谱是可知晓的……若一件意外是不可计算,或是不会被计算到,那它就称不上风险了”[66]533。于是,风险本身是一个可想见的事件,而不像“意外”被序时性掩盖住而不被考虑。这使得在建立自身的行动时态配置模式时,风险作为一种非意图的损害性发生,与意图性的事务都会一起被考虑、包容进去。虽然人们从未会去主动实现风险,但由于“时间形式的时候化”以及需要自我建立行动时态配置模式的需求而被突显出来,故而行动总是会伴随着风险。因此,伴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也开始发展出两个应对风险时的主要任务。
第一个是加强面对风险的能力[72]。风险是无可避免的,它在会发生的时候就是会发生,且其带来的后果是无法不去面对的损害。若人们在行动的同时,越能有多方面处理风险的准备,那么风险实际发生时所造成的损害便越有可能减轻[73][68]38。这带来一个结果,亦即一个行动越是被认为是有风险的,就越会带着“风险会发生”的假定去进行。就如同飞机起飞前,每位乘客都需要系上安全带、被教导逃生设施的使用方法就是为了在飞行时能够具备面对意外的能力以减轻飞行风险一样,而这也等于假定飞行是有风险、且会发生的。虽然人们当然不认为飞行风险一定会发生,但也不认为一定不会发生。由于加强面对风险的能力是一件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因此风险计算与风险管理在当代社会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让保险制度变得相当普遍[74]。
虽然加强面对风险的能力很重要,但它得具备一个前提,亦即人们要知道“有风险”这件事,这就是应对风险的第二个主要任务,即风险“知觉”。虽然在“时间形式的时候化”的影响以及行动时态配置模式需要自我建立的要求之下,行动的风险性越来越显露出来;然而行动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风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却不是人们自然而然就会知晓的。此外,就算人们知道一个行动有风险,也可能会因为该风险带来的损害被认为小到没有威胁性而忽略其风险。今天在风险研究当中人们已普遍同意,风险知觉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后果[75]。于是,风险治理就成为当代社会应对风险时的第二个重要任务。风险治理主要关涉的问题是:“对于谁来说,风险是未知的,所以这些风险是未知的,以及如何让这些未知的风险变成社会知觉和解释的对象?[66]533”显然,风险治理的问题牵涉到非常广泛的层面。今天,这些广泛的问题在社会学当中已是一个专门的主题,甚至可以归属在一个称作“风险社会学”的次领域当中独立探讨。由于这个问题在本文当中不可能继续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不拟再加以论述。但行文至此已经可以指出,今天的社会被称作是“风险社会”,并不是因为人们今天的生活比过去更危险;而是因为时间形态的改变,让人们更会去顾虑到风险[11]3。而这个改变,按照本文的分析,则主要是来自时间形式的改变,亦即是“时间形式的时候化”的后果。
四、新时间形式下的新问题与新方针
社会时间是一个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的社会现象。本文将社会时间区分为时间结构、时间形式两个层面,并聚焦在时间形式层面检视时间形式的改变与当代现状。
对应着时间结构从自然时间结构、标准时间结构、到今天的弹性时间结构这三个时间结构的变迁阶段,时间形式也可以区分出三个变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应自然时间结构的“自然时间形式”,这当中人类的行动与互动模式主要依赖自然韵律而进行,相对来说较少社会性质。第二个阶段是对应着标准时间结构而来的“序时时间形式”。时间形式的序时化主要包含了“行动的单子化”“数字化”“顺序化”这三个生成层次。在序时时间形式当中,人类的行动和互动模式在有意图的实践方面呈现出“普遍的同步性”;在没有意图、也不希望实现却实现了的实践方面,则是以“意外的时间化”来面对各种意外。第三个阶段当中,由于1973年兴起的后福特主义及其促使的弹性工时的普及与随之而来的弹性时间结构,因此产生了“时间形式的时候化”,造就当代的 “时候时间形式”。在时候时间形式当中,普遍的同步性逐渐转变为 “有条件的同时性”,意外的时间化也逐渐转变为“风险的常态化”。
时间形式的改变,不仅呈现出人类的行动与互动安排的模式,而且在不同的时间形式当中,也会出现相应的时间问题。如上文所述,在标准时间结构与序时时间形式当中,最重要的时间问题是阶级之间的时间权力的争夺,具体则表现在工作时间长度、上下班时间、假期的多寡等等关于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边界的划定争议。然而在弹性时间结构与时候时间形式当中,由于时间边界松动了,时间权力去中心化,因此时间问题也再不是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问题,而是罗萨所说的“时间的时间化”问题,亦即时间的安排问题。
林德斯巴赫(Jürgen P. Rinderspacher)认为,由于时间权力的去中心化,因此人际关系之间为了互动而产生的时间协调问题(亦即本文所谓的有条件的同时性),不再只是存在于阶级当中,而是存在于所有需要协调的角色之间,也就是存在于所有行动者及其环境之间。由于“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的探讨观点今天一般同意“生态学观点”能提供很大的帮助,因此林德斯巴赫借此提出了“时间生态学”的观点,他认为这会是研究当代时间形式当中的时间协调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76][77]。生态学观点认为,诸个体共存于一个关系环境整体,并强调在此环境整体当中,个体之间需要有健全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达到环境整体健全互惠的平衡[78]。若将“时间”与“生态学”结合起来,那么时间生态学的基本立场便会是:社会环境当中的诸行动者彼此之间的行动协调应该追求公平性,避免不适当的时间权力宰制,让社会生态环境当中的诸行动者都可以互惠地满足彼此的时间需求。由于社会时间(如本文开头所述)是一种可经验性地观察的社会事实,因此时间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就可以透过制度检视与互动逻辑分析,经验性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时间协调模式,并且批判性地诊断行动协调的公平性问题。
如果对时间形式变迁及其当代现状的分析揭露了当代时间形式的特质与问题,并且时间生态学提供了研究此问题的切入取径,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当代时间形式当中的各个社会领域里的各种时间生态情况,进行批判性的经验研究。也就是说,未来的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时间运用调查也就是说不能只是通过统计来呈现一群个体一定时段之内花了多长的时间作了什么活动,而是必须更系统性地研究当人们在进行时间安排的时候,会遭遇到哪些其他相关的社会角色的制约与影响,以及这当中是否蕴含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且该如何解决。*关于时间生态学路径下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一些值得为此参考的个案研究,详细的介绍可参阅Cheng,“The Ecology of Social Time: An Outline of an Empirical Analytic Framework of the Sociology of Time”, Time & Society,2017.当然,这绝非本文、甚至只是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值得为此对我们的社会进行大量而丰富的经验研究。本文也期许,时间形式的时候化不单只是一个理论分析,而更是未来诸多相关经验研究的理论基础。
[1] Werner Bergmann,“The Problem of Time in Sociology: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at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Sociology of Time’”,Time&Society,No.1,1992,pp.81-134.
[2] Émile Durkheim,TheElementaryFormsoftheReligiousLife,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3] Barbara Adamand,TimeandSocialTheo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4] Jonathan Gershuny,Time-UseSurveysandtheMeasurementofNationalWell-Being,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Centre for Time Use Research, 2011.
[5] 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 景天魁等:《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 Elizabeth Shove,“Everyday Practice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ime”,Elizabeth Shove et al.,Time,ConsumptionandEverydayLife:Practice,MaterialityandCulture,Oxford: Berg,2009,pp.17-33.
[8] Norbert Elias,ÜberdieZeit,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9] David Har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AnEnquiryintotheOriginsofCultureChange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0.
[10] 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TheRaymondFredWestmemoriallecturesatStandfordUniversity,Standford/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Anthony Giddens,Modernityandself-identity——SelfandSocietyintheLateModernAge,Standford/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 Manuel Castells,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TheInformationAge:Economy,SocietyandCulture,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6.
[13]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4] Hartmut Rosa,Resonanz:EineSoziologiederWeltbeziehung,Berlin: Suhrkamp,2016.
[15] 郑作彧:《驾驭速度(?)的理论:评哈穆特·罗沙〈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文化研究》2008年第7期,第244-257页。
[16] 郑作彧:《社会速度研究:当代主要理论轴线》,《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08-118页。
[17] Klaus Laermann,“Alltags-Zeit: Bemerkungen über die unauffälligste Form sozialen Zwangs”, Rainer Zoll,ZerstörungundWiederaneignungvonZeit,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8,p.326.
[18] Robert Levine,AGeographyofTime:TheTemporalMisadventuresofaSocialPsychologistorHowEveryCultureKeepsTimeJustaLittlebitDifferently,NY: Basic Books,1997.
[19] Witold Rybczynski,AmFreitagfängtdasLebenan,Reinbekbei Hamburg: Rowohlt,1993.
[20] Eviatar Zerubavel,“The Standardization of Time: A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No.1,1982,pp.1-23.
[21] Günter Scharf,“Zeit und Kapitalismus”,Rainer Zoll,ZerstörungundWiederaneignungvonZeit,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a,1988,p.143-159.
[22] Palmer Edward Thompson,“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andPresent,No.38,1967,pp.56-97.
[23] Karl Marx,“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In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Berlin: Dietz Verlag,1968,p.23.
[24] Nigel Thrift,“The Making of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John Hassard,TheSociologyofTime,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p.107.
[25] Radhakamal Mukerjee,“Time, Technics and Society”,in John Hassard,TheSociologyofTime,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S, 1990,pp.47-55.
[26] Elliott Jaques,“The Enigma of Time”,in John Hassard,TheSociologyofTime,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0,pp.21-34.
[27] Hans Rämö,“An Aristotelian Human Time-space Manifold. From Chronochora to Kairotopos”,Time&Society,No.2,1999,pp.309-328.
[28] Werner Bergmann,DieZeitstruktursozialerSysteme:EinesystemtheoretischeAnalyse,Berlin: Duncker & Humbold, 1981.
[29] Niklas Luhmann,“Temporalstrukturen des Handlun-gssystems”,in Niklas Luhmann,SoziologischeAufklärung,KonstruktivistischePerspektiven,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1981,pp.126-150.
[30] Pitirim A. Sorokin and Robert K.Merton,“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and Functional Analysis”,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XLII,No.5,1937,pp.615-629.
[31] Anthony Giddens,TheConstitutionofSociety:OutlineoftheTheoryofStructur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32] Niklas Luhmann,DieGesellschaftder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97.
[33] Niklas Luhmann,Vertrauen:EinMechanismusderReduktionsozialerKomplexität,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1973.
[34] 汤姆·范德比尔特:《马路学》,台北:大块文化2009年版。
[35] Cheng Tsuo-Yu,“The Ecology of Social Time: An Outline of an Empirical Analytic Framework of the Sociology of Time”,Time&Society, No.20,2017,pp.137-164.
[36] Hartmut Seifert,Konfliktfeld Arbeitszeitpolitik,Entwicklungslinien,GestaltungsanforderungenundPerspektivenderArbeitszeit,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6.
[37] Oskar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PolitischeundkulturelleDimensionendesKampfesumdieArbeitszeit,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1984.
[38] Günter Scharf,“ Wiederaneignung von Arbeitszeit als Lebenszeit”,in Rainer Zoll,ZerstörungundWiederaneignungvonZeit,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pp.509-530.
[39] 彭南生,饶水利:《简论1929年的〈工厂法〉》,《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第81-87页。
[40] Wolfgang Bonβ,VomRisiko,UnsicherheitundUngewissheitinderModerne,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1995.
[41] Niklas Luhmann,SozialeSystemeGrundriΒeinerallgemeinenTheori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4,p.442.
[42] Alain Badiou,BeingandEvent,New York: Continuum, 2005.
[43] Wulf-Uwe Meyer,“Die Rolle von Überraschung im AttributionsprozeΒ”,PsychologischeRundschau,No.39,1988,pp.136-147.
[44] Jacques Derrida,“Autoimmunity,Real and Symbolic Suicides: A Dialogue with Jacques Derrida”,in Giovanna Borradori,PhilosophyinaTimeofTerror:DialogueswithJürgenHabermasandJacquesDerrida,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pp.85-136.
[45] Christian Kassung,“Einleitung,”ChristianKassung,DieUnordnungderDinge.EineWissens-undMediengeschichtedesUnfalls,Bielefeld: trascript,2009,pp.9-15.
[46] Julia Egbringhoff.“‘Den Alltag beherrschen’-Ausprägungen und Folgen ‘neuer’ Erwerbsformen am Beispiel von Ein-Person-Selbständigen”,in Margit Weihrich,G.GünterVoΒ.tagfürtag:AlltagalsProblem-LebensführungalsLösung?NeueBeiträgezurSoziologieAlltäglicherLebensführung,München: Rainer Hampp Verlag, 2002,pp.21-46.
[47] Friedrinke Benthaus-Apel,ZwischenZeitbindungundZeitautonomie:EineempirischeAnalysederZeitverwendungundZeitstrukturderWerktags-undWochenendfreizeit,Wiesbaden: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1995,p.69.
[48] Markus Promberger,“Wie neuartig sind flexible Arbeitszeiten? Historische Grundlinien der Arbeitszeitpolitik”, Hartmut Seifert,FlexibleZeiteninderArbeitswelt,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 2005,pp.9-39.
[49] Hartmut Seifert,“Arbeitszeitpolitischer Modellwechsel:Von der Normalarbeitszeit zu kontrollierter Flexibilität”,in Hartmut Seifert,FlexibleZeiteninderArbeitswelt,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Verlag,a,2005,pp.40-66.
[50] Hans-Jürgen Rauschenberg,FlexibilisierungundNeugestaltungderArbeitszeit:derarbeitsrechtlicheEntscheidungsrahmen,Baden-Baden:Nomas,1993,p.29.
[51] Hartmut Seifert,“Zeit für neue Arbeitszeiten”,WSIMitteilungen,2005,pp.478-483.
[52] 沈同仙:《金融危机与我国弹性工时制度的实施》,《阅江学刊》2009年第2期,第98-103页。
[53]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
[54] 周敏慧:《实行带薪休假制度的意义、现实性与保障体系》,《消费导刊》2008年第1期。
[55] 周建新:《〈劳动法〉下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的影响与对策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4期。
[56] Werner Kudera,“Grenzen der Flexibilisierung-Zum Verhältnis von individueller und betrieblicher Zeitökonomie”,in Werner Kudera,G Günter Voβ,Lebensführung und Gesellschaft.BeiträgezuKonzeptundEmpiriealltäglicherLebensführung,Opladen: Leske + Budrich,2000,p.292.
[57] Gerd-Günter Voβ,“Der Strukturwandel der Arbeitswelt und die alltägliche Lebensführung”,in Karin Jurczyk and Maria S. Rerrich,DieArbeitdesAlltags.BeiträgezueinerSoziologiederalltäglichenLebensführung,Freiburg im Breisgau: Lambertus, 1993,p.111.
[58] Helga Nowotny,Eigenzeit:EntstehungundStrukturierungeinesZeitgefühls,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90,p.102.
[59] Roland Boer,“Revolution in the Envent: The Problem of Kairós”,Theory,Culture&Society,No.2,2013,pp.116-134.
[60] Felixó Murchadha,ZeitdesHandelnsundMöglichkeitderVerwandlung:KairologieundChronologiebeiHeideggerimJahrzehntnach,SeinundZeit,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1999.
[61] Rosa Hartmut,Beschleunigung:DieVeränderungderZeitstruktureninderModern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62] Karin Gottschall and G. Günter Voβ,“Entgrenzung von Arbeit und Leben-Zur Einleitung”,in Karin Gottschall,G Günter Voβ,EntgrenzungvonArbeitundLeben.ZumWandelderBeziehungvonErwerbstätigkeitundPrivatsphäreimAlltag,München & Mering: Rainer Hampp Verlag,2003,pp.11-33.
[63] Karin Jurczyk,et al.,“Die Zeiten ändern sich-Arbeitszeitpolitische Strategienund die Arbeitsteilung der Personen”,in Werner Kuderaand G. Günter Voβ,Lebensführung und Gesellschaft.BeiträgezuKonzeptundEmpiriealltäglicherLebensführung,Opladen:Leske+Budrich, 2000,p.54.
[64] Karin Jurczyk and Maria S Rerrich,“ Einführung: Alltägliche Lebensführung: der Ort, wo ,alles zusammenkommt”,Karin Jurczyk and Maria S. Rerrich,Die Arbeit des Alltags,BeiträgezueinerSoziologiederalltäglichenLebensführung,Freiburg im Breisgau: Lambertus,1993,p.26.
[65] Charles Perrow,NormalAccidents.LivingwithHigh-riskTechnologies,New York: Basic Books,1984.
[66] Peter Wehling,“Vom Risikokalkül zur Governance des Nichtwissens, Öffentliche Wahrnehmung und soziologische Deutung von Umweltgefährdungen”,in Matthias GroΒ,HandbuchUmweltsoziologie,Wiesbaden: VS Verlag, 2011,pp.529-548.
[67] Urlich Beck,Risikogesellschaft-AufdemWegineineandereModern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68] Niklas Luhmann,SoziologiedesRisikos,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1991,p.37.
[69] Gotthard Bechmann,“Einleitung: Risiko-ein neues Forschungsfeld? ”,in Gotthard Bechmann,Risiko und Gesellschaft,GrundlagenundErgebnisseinterdisziplinärerRisikoforschung,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3,pp.7-31.
[70] Niklas Luhmann,“Risiko und Gefahr”,in Niklas Luhmann,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KonstruktivistischePerspektiven,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1990,p.140.
[71] Olaf Briese,“ Die Aporie des gröΒten anzunehmenden Unfalls”,in Christian Kassung,Die Unordnung der Dinge,EineWissens-undMediengeschichtedesUnfalls,Bielefeld: transcript, 2009,pp.361-379.
[72] Heinz-Kurt Wahren,Anlegerpsychologie,Wiesbaden: VS Verlag, 2009.
[73] Stanley Kaplan and John B.Garrick,“Die quantitative Bestimmung von Risiko”,in Gotthard Bechmann,RisikoundErgebnisseinterdisziplinärerRisikoforschung(2.Aufl.),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1997,pp.91-124.
[74] Wolfgang Krohn and Georg Krücken,“ Risiko als Konstruktion und Wirklichkeit.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Risikoforschung”,in Wolfgang Krohn,Georg Krücken,RisikanteTechnologien:ReflexionundRegulation,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93,pp.9-44.
[75] Mary Douglas and Aron Wildavsky,“Risiko und Kultur. Können wir wissen, welchen Risiken wir gegenüberstehen?”,in Wolfgang Krohn,Georg Krücken,RisikanteTechnologien:ReflexionundRegulation,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3,pp.113-137.
[76] Jürgen P Rinderspacher,Gesellschaft ohne Zeit,IndividuelleZeitverwendungundsozialeOrganisationderArbeit,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1985.
[77] Jürgen P. Rinderspacher,ZeitwohlstandinderModerne,Berlin: WZB,2000.
[78] Michaelet Begon,et al.,Ecology:FromIndividualstoEcosystem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