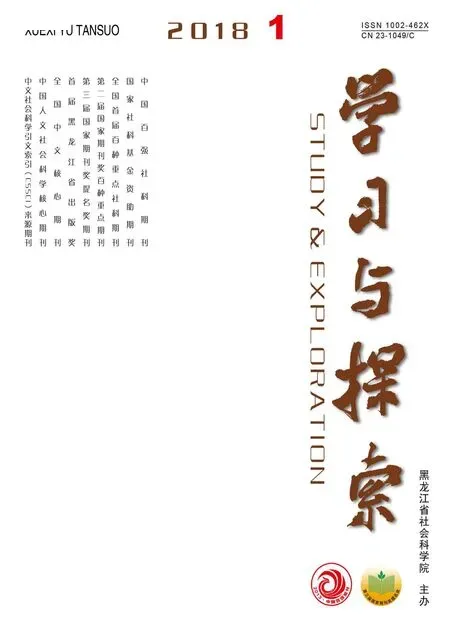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
马 驰
(上海社会科学院 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1]报告凸显了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情怀,坚持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立意高远、针砭时弊,对我们当下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深刻学习与领会。
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情怀也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重要论述中。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2]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
19世纪中叶,德国产生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扮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派这一极不光彩的角色。该学说的理论渊源来自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鼓吹对“抽象的人”即所谓“真正的人”的崇拜,把历史的现实的人还原为自然界的“类”。在文艺创作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描写所谓“完美人性的人”,倡导“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向资产者摇尾乞怜;这是一种保守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思潮。这种思潮虽有善良愿望,但纯属乌托邦。他们不理解现实的社会关系、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基本事实。他们既不愿看到两极分化的现象,又不想去追究产生这种令人痛苦的社会现实的根源和求索消除人世间黑暗的出路。他们天真地幻想只要没有穷人,便会万事如意。他们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具有软弱、动摇和耽于幻想的痼疾。这种政治倾向和文艺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马恩经典作家的无情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哲学等方面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即集中批判了这一反动思潮的诗歌创作和文艺观念。恩格斯指出,卡尔·倍克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飘浮在德国市民的朦胧幻想的‘云雾中’”的诗人。他们把资产者美化成善良的“博爱家”,把无产者丑化为逆来顺受的奴才。他们的诗歌的特征是“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所致。“他们的诗歌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止血用的三包沸腾散’。”[3]恩格斯还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只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文艺要歌颂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在恩格斯看来,文学作品应该对现实关系作真实的描述,应该把人物、事件的描述同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同时文学应该正面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革命的无产者”是马恩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文艺要讴歌社会进步力量,这一具体的文艺评论不仅坚持了唯物史观,而且这一重要的见解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马恩经典作家的全部文艺论述中。
1927年,鲁迅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啊,诗啊,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而说的。”[4]421-422鲁迅在演讲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就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会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虽没有在演讲中明确回答文学“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等问题,但通篇都显示出他对“民”(更准确地说是对平民)的关怀,而不是抽象地关注“人”;通篇都显示出他对平民的关怀和建立真正的平民文学的期待,鲁迅是为平民而代言。他还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4]421-422从《新青年》开始,鲁迅就以睿智而深刻的理性精神和强健而坚韧的自由意志从事文学活动,既坚持了符合艺术目的性的自觉的审美创造,又充分展开了以情感因素为指归的自由的审美创造。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指斥那些“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是“教训文学”[5]18-24;“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画报上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而一些“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争光’”,鲁迅称之为“玩把戏”的文艺[5]335-337;他还告诫左翼作家:“无须在作品的后面有意的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当文艺堕入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或某项具体政策的图解时,“那全部作品中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便荡然无存[7]。在鲁迅看来,好的文艺作品是自然而然、情不自禁地创造出来的,如果一味强调创作理性的有意识控制,那样的作品就会矫情、失真。文艺创作犹如童心的复活和再现,本来应是自然、纯真的感情之流露,倘若有意为之,往往事与愿违。鲁迅用做梦和说梦的不同来说明这个道理:“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5]467-469文艺创作就像做梦似的,作家一任自己的感情自然流淌,从而获得艺术的真实。“变戏法”的艺术也是一样,倘若有意而为,就会虚假;如果无心而作,反而有真,“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4]24。有意为之、装腔作势之作,最易引起读者大众的幻灭之感。
还有一场“历史公案”也大致能够反映出鲁迅的上述思想。1929年9月,梁实秋在《新月》2卷6、7号合刊上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文章,用他的精英意识奋力抨击鲁迅关于文学具有阶级性的观点。 在文中,梁实秋把精英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无产者首先应该甘于忍受自己的不平等命运,但不要团结起来形成一个阶级,然后再通过“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产者。人是不平等的,但阶级却是没有的。无产者可以成为有产者,有产者也可能成为无产者。阶级意识只是几个“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为了夺权需要,把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工具。 为了更有效地攻击这种把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阶级意识,梁实秋特别讽刺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是个“硬译”和“死译”出来的东西:“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
鲁迅在1930年3月的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硬译”与“文学阶级性”》一文,对梁实秋予以反驳,文章题目中的两个双引号,指的就是梁实秋的那两篇文章。鲁迅提出,所谓永恒人性其实是虚伪的。虽然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5]204。有产者的喜怒和恋爱与无产者的喜怒和恋爱,是不同的两回事。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以前产生的各种社会观把社会或者理解为人群共同体,或者理解为人的外部环境。其实质都是把社会理解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实体,都是一种“实体化”的社会观。“实体化”的社会观是人们对“社会”经验直观的产物,是以作为头脑当中的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这样,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就被抽象掉了,人不再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8]。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就不会真正理解由真实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马克思在批判各种已有的社会观和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马克思认为,为了真正理解社会,“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9]。在这里,马克思确立了理解社会的出发点——“个人”。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鲁迅从弃医从文那一刻起,就把他意识到的“改变国民精神”的历史使命宣告于世了。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艺术家要做“革命人”。他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4]544革命作家在个人的自由创造中,只有融入深厚的革命情感和进步的社会意识,才能写出革命文学。人不能在一刹那中命令自己具有某种情感或不具有某种情感,人的情感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它像喷泉里的水、血管里的血,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因此,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作家,必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面流淌几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没有如恩格斯那样直接提出文艺应该正面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但为人民而写作、为人民代言却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他的创作价值正体现在人民的需要之中。只可惜鲁迅的精神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及文人中真正扎根。
毛泽东出身农家,懂得农民的辛酸与悲苦、理想与追求。因此,农民问题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关注的大问题。他对农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民是人民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脊梁,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并提出“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人民群众历来是作品“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评判者,并以戏剧与观众的关系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地提出文艺要塑造新人形象的要求。他说:“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那里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10]《讲话》澄清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发展了恩格斯提出的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但哪些人是“新的人物”,他们“新”在哪里?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具体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把能否改变社会环境确立为新人的重要标志。他们认为思想是重要的,但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为了实现思想”,必须“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的“新人”。
1944年元旦,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首次演出《逼上梁山》。该剧只演了不到10场。1月9日晚上,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演出后十分高兴,当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1]
人民性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并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给予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也催生了文艺新作的涌现,促使当时的解放区产生了一批堪称经典的文艺作品,它们至今依然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艺术上具有永久的魅力。毛泽东人民本位文学观的确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载道说”“娱乐说”的文学观念,注入了新内涵,体现了新文艺底层关怀的人文精神。这种文艺观虽然质朴,不乏很强的目的性,但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解决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重新提出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8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结合对改革题材作品的评价对“社会主义新人”及其塑造问题从理论上展开了探讨,指出塑造和描写“新人”是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的、一贯的要求。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不同,恩格斯曾把这些“新人”称之为“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苏联文学界称之为“社会主义英雄人物”,中国在80年代以前则称之为“工农兵英雄人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之后,在改革形势下,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在成长。因此,文学界普遍认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职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评论界看法尚不尽一致,有的学者主张新人必须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有的强调新人必须有不同于传统的先进人物的“新”的时代特质。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新人应当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不应该是一个模式、一种类型。其基本思想特征应该是既体现社会主义理想,同时又在性格、才智、情操等方面具有新的境界、新的气质。社会主义新人,无论是正在成长的或是已经成熟的,无论是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或是日常平凡工作岗位的,无论其性格、经历、命运、业绩如何,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捍卫者,都有着大无畏的主人翁精神和历史首创精神。社会主义新人的提法既继承了社会主义文艺坚持塑造新人的先进性,又适应了中国新的形势,把新人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不难看出,无论从马恩经典作家提出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鲁迅倡导“贫民文学”;还是毛泽东提出“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邓小平提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直至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虽所指的对象和表达的语汇有所不同,但人民情怀却是一致的。不过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人民”本是个政治术语,在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如何界定人民,马恩经典作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用这样一段表述来界定“人民”:
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2]。
不难理解,毛泽东仍然是在政治范畴内界定“人民”的,如果我们将这一政治概念直接“移植”到文艺实践,势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这里的 “人民”是政治标准,不是法律标准。这个标准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来的,并不是经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条文。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它却具有类似法律的效力。
第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是什么?“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什么意思?这里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艺实践中,今天是朋友,明天变敌人这样的荒诞剧并不鲜见。
第三,毛泽东采用了“人民”和“敌人”的两分法,但“人民”和“敌人”在逻辑上并非一对“矛盾概念”,而是“反对概念”;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人不是人民,就是敌人。有些人不问政治,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态度冷淡,但也不反对和敌视社会主义事业;有些人觉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动摇:对于这些采取中间立场的人,该划在“人民”一边,还是“敌人”一边呢?
第四,毛泽东的定义不说个人,只说“阶级”“社会集团”,似乎判定某人是不是敌人不是根据他本人的表现,而是看他属于哪一个阶级,似乎敌对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敌人,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不会变成反革命。这很容易堕入唯成分论。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对“人民”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个关键概念在当下的内涵、外延廓清,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当下的文艺实践。
同理,习近平提出“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也是十分正确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要认真界定“人民”的具体范畴,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理论工作者应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对人类思想史上的有关人民以及人民主权的学说进行全面的梳理,重建一个适宜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人民概念,这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还应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其根本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结合当下具体文艺创作,这些论述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习近平还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他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人民”,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民性的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还提出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体现了他的人民主权意识,同样意味深长。既然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消费者,那么作品的好坏就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然而,在以往一个时期的文艺创作与文艺评价中,人民群众不仅很少有权力评判作品,同时文艺作品的创作与生产也很少将人民群众的需求考虑进去,导致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只能被动地阅读和观看。“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文艺的评判权交还给人民,这是对人民群众鉴赏能力的信任和肯定。这一重要论述为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规范,也提高了人民群众在整个文艺活动中的地位和价值,增强了人民群众在文艺创作活动中的参与权与话语权。习近平还在讲话中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将人民作为文艺评论的标准之一提出来,与“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并列而成为文艺评论的四个标准,就以具体的形式,确立了“人民”在文艺作品评论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如何评判作品的好坏优劣,恩格斯较早提出了“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并且认为这两个标准是“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作为一种经典论述,这两个标准已深入人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科学标准为评论界所广泛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保留了这两个标准,又新提出“人民”与“艺术”这两个标准,不仅体现出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留下了重要的阐释空间,启迪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艺术”与“美学”标准的具体内涵,“历史”与“人民”的价值尺度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最终将我们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224页。
[4] 《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6] 《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593页。
[7]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10] 《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2页。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1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