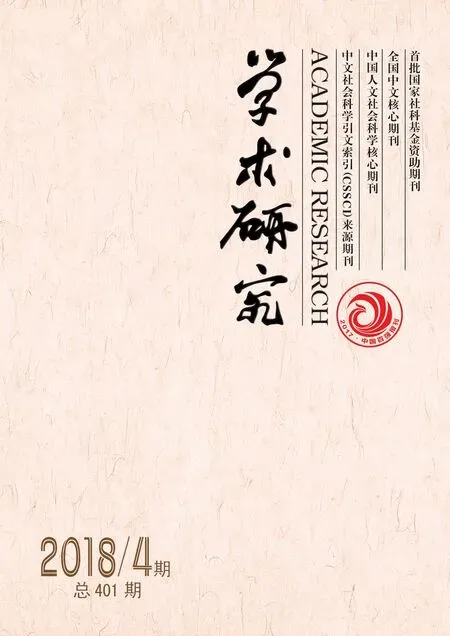从“盐徒惯海”到“营谋运粮”:明末淮安水兵与东江集团关系探析*
王日根 陶仁义
明朝政府对海洋管理整体上持禁止的态度,细分之下,又有“海外”与“近海”之别。“海外”或称作“远洋”,禁“海外”即朱元璋颁布的“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a《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第3640页。本文所用《明实录》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版本。主要针对粤闽浙等地与“海外诸番贸易”的海上私人群体。嘉靖时期“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b谢杰:《虔台倭纂》,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的浙江巡抚朱纨,因不加以区分闽浙海域与北部(近海)海域的不同,刻板执行海禁政策,遭到闽地官员弹劾而被杀。隆庆初年开海是“远洋”海商群体利用商业力量向政府“倒逼”的成功之举。“近海”即海运,指的是沿袭元代沿着海岸线而进行的漕粮海运,由漕运衙门所在地淮安府出海,向北经山东海域中转至天津、京城乃至辽东一带。拙文《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c王日根、陶仁义:《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以下简称《淮安海商》)对明代海运进行了梳理,指出明代官方并未能够一直严格执行永乐时期定下的“罢海运”政策。战争是促成海运恢复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在万历二十年(1592)开始的入朝征倭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时便已有所体现,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的辽东战争中更是格外明显。由盐徒灶丁征募而来的淮地水兵于战争期间“营谋运粮”,兼具了海商性质,这一特征被孤悬海外、亟须稳定粮饷保障的毛文龙所看重,从朝廷争取到这支队伍,在维系东江集团生存的同时,得以割据一方,于战争期间有效地牵制了后金军队,使之不能放手南下。
中外学者围绕毛文龙展开的讨论已经从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的是非评价转移到探讨其背后的海上贸易。韩国学者郑炳喆在《明末辽东一带的“海上势力”》一文中认为:“对于以往研究中关注不够的毛文龙海上活动,包括连接皮岛在内的辽东沿海一带诸岛,旅顺—登莱—天津的海上路线交通及海上贸易等”给予了细致考察,a该文发表于2005年4月的韩国明清史学会主编的《明清史研究》第23辑,本用韩文写成,经国人翻译后于2015年底发表于《中国民族边疆研究》,较之作者郑炳喆发表于2004年的《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毛文龙势力的浮沉为中心》,多了对东江集团“海上贸易”部分的考察。赵世瑜在《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一文中指出:“无论是东江自身的屯种,还是明廷的拨饷,都无法完全解决这里的生计困境,即使是朝鲜的粮食援助,也需要靠通商来进行交换。因此,海上贸易成为这里解决困境的最重要手段,中国北部海域的商业贸易由此成为东江镇的生命线。”b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晋商、徽商、山东登州商人以及苏杭商人参与其中,但多是个案且相对独立,并没有解释这些商人是通过何种渠道或凭借什么特征为毛文龙所看重,并建立起商贸关系。考虑到粮食作为东江集团生存第一需求,自嘉靖倭乱后期以来,凭借对黄海、渤海海域的了解和所掌握的行船技巧,淮安海商在淮安至山东登莱、辽东乃至朝鲜的海上商路上有着重要地位,淮安民间私人海上群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在《淮安海商》一文中,已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囿于材料,对当时被朝廷征募、兼具海商性质的淮地水兵群体仅作略述处理,今以所发现的相关资料进行补充论证,在加深对东江集团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对明末近海海上商贸活动做一研究上的扩展。
一、盐徒惯海:明末水兵的构成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挑起辽东战争。次年春天萨尔浒一战,明军大败,丧失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直到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军将领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才有所改观。自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初十期间,毛文龙“带沙船四只,装军士一百九十七名”,“到处招抚、到处锄逆,到处约会”,陆续收复沿海众多岛屿,并于七月十八日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在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毛文龙向朝廷提出了“一面速发大兵渡三岔河以为牵制,一面调兵二万,从海道径至镇江,并发粮饷,以助进剿,以卒前功”c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7页。的要求。
“镇江大捷”一扫辽东战争爆发以来明军屡战屡败的阴影,尤其献叛将佟养真等人于阙下更是自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经辽东巡抚王化贞上报朝廷后,毛文龙立即被升为“副总兵,赏银二百两”,相关人员一同受赏。d《明熹宗实录》卷13,天启元年八月丙子,第654-655页。对比毛文龙的塘报与朝廷实录中对相关事件的反应来看,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塘报或经过辽东巡抚的审阅再上报,为朝廷所知晓时间间隔大概在20天左右。如从七月十九日取得镇江大捷到王化贞上报朝廷,毛文龙升为副总兵已是八月初七了。情理上,这显然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其要求从海上派兵的主张亦得到皇帝同意:“但文龙深入虎穴,力扼孤城,外援不至,恐归义之众不免复溃……但一鼓胜,气易衰,三方兵力未凑,急宜策应用保万全。上可其奏,命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总兵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水兵八千为后劲,参将管大藩将之,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皆选四将为副,王化贞挑广宁精兵四万,据三岔河,与西虏合,相机进取。经略熊廷弼严勒兵将,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e《明熹宗实录》卷13,天启元年八月丙子,第654页。由于当时明廷内部党争激烈,不和的王化贞与熊廷弼对是否应该乘胜追击后金意见相左,f《明熹宗实录》卷14,天启元年九月癸丑,第704-708页。兵源补充未能及时到位。八月,镇江被后金夺回,毛文龙逃亡朝鲜,但朝廷对此表示理解,并未降罪:“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扬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a《明熹宗实录》卷14,天启元年九月甲寅,第714页。被重新起用的大学士叶向高在赴京途中上奏支持毛文龙:“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忧)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若枢。经督抚诸臣皆极一时之选,必能同心僇力,毋忌成,毋旁掣,共灭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隐忧。此实普天臣民所共想望。”b《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元年十月庚辰,第751-752页。在朝廷要员的认可与支持下,毛文龙继续在朝鲜、镇江一带从海上对后金伺机攻击,使得后金军队不敢放手南下。
缺乏必要的海上兵力,是毛文龙败走镇江、不能收复失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辽东战争爆发以来明军兵源不足情况的真实呈现。募兵事宜虽自战争爆发便已经开始,但当时募兵对象主要是陆兵,四十六年闰四月初,“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今日最急无如议兵、议饷。募兵须选有膂力善骑射者,令主将训练。”c《明神宗实录》卷569,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第10702页。虽然也同时抽调登州府水兵1500名前往辽东支援,但水兵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重新开启的海运粮道。d《明神宗实录》卷576,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第10703页;卷586,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丙戌,第11219页。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水兵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才被官员所认识,兵部左侍郎杨应聘在汇报募兵情况时指出:“今以经臣分布之议,酌量水陆之兵,应于南北兼募……”,即从浙江、淮扬、南直等处大量招募水兵,“又查淮扬等沙兵甚强,船只甚便,且因海至,登莱旅顺,一水可航,应调五千名。访得浙江南洋游击管大藩廉勇而精于水战,今升参将,令其督率,并前调南直水兵二千名,浙江水兵三千名,一并挑选统领随带沙号战舡、应用器物,由海渡辽。”e《明神宗实录》卷589,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己巳,第11292页。在探讨这些水兵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为何要从“淮扬、浙江、南直”等地募集水兵?实际上这里只是两个区域,即浙江省及淮安、扬州二府所隶属的南直隶,文献中所载的沙兵、直兵、淮兵亦时常被泛称为南兵。从这两地募水兵,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衡量。明代得以立国,就是建立在成功降服张士诚、方国珍这两个江浙强大水上力量(盐徒群体)的基础之上。对于万历帝而言,入朝征倭进入第二阶段后,除海漕大量使用浙直粮船供应粮饷外,亦同时征募了两地水兵:“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东征经略以前役缺水兵无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讲海运为持久。二月,别将陈璘以广兵、刘以川兵、邓子龙以浙直兵先后至。”f陈建撰、江旭奇补:《皇明通纪集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639页。辽东战争爆发后,兵部尚书黄嘉善亦建议从这两地继续招募水兵,以助平乱:
兵部尚书黄嘉善题为夷氛转炽、兵力尚单,仅议调水陆精兵以备战守事。职方司案呈到部为照…近闻屯住新城日日谋我,兼又造船遣谍侦我虚实,潜有航海内讧之意,则旅顺登莱未可视为无事。惟是岛屿风涛之险,非素习水性者而骤驱之。是问燕人以越路有裹足不敢前耳?安能资其防御哉?臣酌之时势参以报闻,援辽之兵莫若调之土司、防海之兵莫若调之浙直。查得浙江、南直沿海额设水兵,遇汛岀洋,习知水道,且便捷勇敢,称海上长城。g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7,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1集,1926年,卷内页40a-40b。由于《筹辽硕画》书中仅注明己未(1619)仲秋,并未标明奏折具体时间,对比万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日的黄嘉善对山东巡抚王在晋的回复来看,水兵征募事宜当在这一时间段内,或有先后之别,但对本文史实陈述并无影响。
黄嘉善出任兵部尚书多年,并有实际地方军事经验,期间多次请辞皆不为万历帝所允,其意见势必能对皇帝产生积极影响,虽然其在万历帝死后迅速被罢免,但从浙直征募水兵的方针却是一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客观而言,这种应战争突发而招募的水兵,基本上就是由盐场的盐徒、灶丁转换而来。有明一代,淮安、扬州二府的众多盐场有大量从事煮盐的盐徒、灶丁。嘉靖朝倭乱之际,胡宗宪在布置(南)直隶江南海防事宜时发现:“查得沿海民灶原有采捕鱼虾小船,并不过海通番,且人船惯习,不畏风涛。合行示谕沿海有船之家赴府报名,给与照身、牌面,无事听其在海生理,遇警随同兵船追剿。此则官兵无造船募兵之费,而民灶有得鱼捕盗之益。”虽然“此松江海洋设备之大略也”,a胡宗宪:《筹海图编》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9-180页。但是在盐场更多的淮扬一带,“人船惯习,不畏风涛”的情况当更是不在少数。
万历十四年(1586),被视为“天下将才第一”、熟悉盐徒、灶丁的淮安人王鸣鹤明确指出:“(南)直隶盐徒惯海,可为船兵。”b王鸣鹤:《登台必究》;《中国兵书集成》委员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20-24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出版社,1990年,第5045页。自嘉靖倭乱平定以来,凭借对黄、渤海域的了解,淮安民间海上力量开创了从淮安到辽东跨黄、渤海域的海上贸易路线。这一点通过万历元年(1573)旋开旋罢的淮安海运便可证实:“通踏湾泊程次,逐一明白,及访得沿海官民,俱称二十年前傍海潢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来,土人、淮人以及岛人,做贩鱼虾、芩豆,往来不绝,其道遂通,未见险阻,群情踊跃。”c孙承泽著、李洪波点校:《畿辅人物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83页。为此,漕运总督王宗沐便要求海漕船只必须配备淮安、山东的水手来保障行船安全:
拟仍照遮洋旧规,每船用军十二名,然各军固是生长海滨,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带,原非素所经渉,止令各卫所毎船派拨旗军九名,仍将原船余下军人行粮、月粮银两尽数扣解,毎年于淮安、山东地方雇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毎船分配三名拦头执柁,以足十二名之额。待后各军习熟海道,渐次减雇,仍将原军拨补。d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8户部7,《续修四库全书》第11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此次海漕因在海上遭遇意外而被迫停止:“风雨冲坏粮船七只,哨船三只,漂消正耗粮米几五千石,淹死运军水手十五名。……乞敕详酌将海运姑暂停止,仍以额粮十二万,尽入河运。”e《明神宗实录》卷14,万历元年六月壬戌,第441页。海漕虽未能够继续施行,王宗沐所期望的由淮安水手向别处水手传授“拦头执柁”技巧的计划亦未能得到实施,但这也使得这项技能一直为淮籍水手所延续,在辽东战争之际以另一种形式凸显出来:“如募兵……水兵惟淮浙熟谙水性,南兵各给以四两。其余土著水兵则亦减至二两矣。”f毕自严:《抚津事竣疏》,《石隐园藏稿》卷5疏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3册,第551页。淮浙水兵与土著水兵待遇上的差异当是淮浙尤其是淮安籍水手对黄海、渤海海域水道的熟悉以及驾驭海船的能力所造成。
当然,水兵待遇上的差别除了“惯海”外,盐徒、灶丁群体另一个重要特征“勇”,即黄嘉善所言的“便捷勇敢”,亦是战争中所亟须的。倭乱严重的嘉靖朝,协助平定江苏沿海倭乱的郑晓在奏折中详细记载了南直隶盐场灶民奋勇杀倭寇的细节。g郑晓:《剿逐江北倭寇疏》、《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端简郑公文集》卷10、卷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5册,第403、432页。虽然灶丁们奋勇杀倭的直接动力是为遭倭寇杀害的亲人报仇,但这在明代官员看来,实为民力可用、民心可用。
天启二年(1622)进士陈仁锡综前人述论,亦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充分征募灶丁卫戍辽东:
自淮安以达天津,其地薄海,多盐场,盐场灶丁恒以勇力闻。昔曾率之御倭,今宜从灶户中选其壮健者充之。合计各路盐场,其灶丁亦当踰万,因而宽之以利, 之以恩,赏则倍于官兵,罪则轻于众犯,务使其心乐为我用。于是北至静海、南至利津,盐场既广而灶丁亦众,驱之海滨可以御倭,守之于淮复可御盗。军卫之属,协以助之,而得无关之隘;盐课之征,减以利之,而得不食之兵。粮运可以无虞,中原可以强固。h陈仁锡:《练灶丁》,《无梦园初集》漫集1,《续修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218页。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便是当时淮安府境内的严重水患,万历以来,“大水”、“巨浸”、“海啸”等引发“城内行舟,民舍荡然”、“房屋牲畜漂溺无数”的水患记录不绝于淮安府方志之中。i阜宁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民国阜宁县新志》卷9水工,《阜宁县志(合订本)》,出版信息不详,1987年;《天启淮安府志》卷24《丛纪志二》祥异;《淮安实录备草》卷18。辽东战争爆发后,当地水患更是严重,民间海运的主要出海口庙湾一带,“天启初元,山阳县里外河连决十余处,庙湾汇为巨浸。至崇祯四年,河决新沟、建义、苏家嘴,至七年三月始获筑塞,庙湾之民,荡析流亡,转死沟壑,何其惨也。”a阜宁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阜宁县志(合订本)》,第70页。为此,朝廷征集“荡析流亡”的淮人为兵前往辽东协助剿灭后金,既可缓解当地民不聊生的状况,又可解辽东兵源不足和士兵不习水性之急。大批淮兵被征募到登州地集合、修整,等待派遣辽东。万历四十八年十一月,“淮扬浙江共募水兵六千六百余名,令参将管大藩统领赴辽。”b《明熹宗实录》卷3,泰昌元年十一月丙戌。
二、营谋运粮:毛文龙与淮兵的联合
镇江大捷后,明廷与毛文龙的融洽关系仅仅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一方面当时朝廷疲于应付后金从辽沈一带的陆地进攻,而各地频发的灾害亟须救济,c由于当时正处于一个小冰川期,极寒、干旱、洪涝、地震等各种极端自然灾害现象频繁。加上镇压层出不穷的民间起义均是极大的支出,当然最主要的是一直以来在重陆轻海的固定思维之下,毛文龙并不能如愿得到朝廷所承诺的粮饷、兵源保障。其不满情绪在天启三年(1623)年底毛文龙取得凫关大捷后爆发了出来:“但臣屡疏请饷,户部屡以匮乏为辞,又一兵民并言为托。……矧登津俱有岁额粮饷,孑臣海外,独无定议,三年以来,止给银一十一万两,运米二十万石,其够养官兵,够养马匹乎?”d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3-384页。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页。毛文龙的抱怨并未起到作用,天启六年(1626)九月,毛文龙再上疏:“前请加饷,两年以内,分文未增,所请器械,两年亦未运至,所请船只,今方鸠工,未得一帆船之用……”,要求朝廷允许“东江于胶淮等处自行买运”。e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383-384页。这一建议早在天启三年(1623)八月,其上奏塘报中便已经提出:“然户部既谓必不能养,臣宁忍视纵之投奴?则于万不得已中,设有一策,比壬辰征倭事例,使南直、山东、胶淮等处,招商买米,令其自备粮石,自置舡只,到鲜之日,核其地头米价,外加水脚银两,凡船装十分,以八分米,二分货为率。……除一面差官赍臣出海文引,往胶淮等处招商外,一面冒昧上陈,伏乞皇上垂念海外情形……凡招通输粟者,悉如臣议。”f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75页。天启三年年底的毛文龙之所以敢于对朝廷粮饷供应如此愤愤不满,大发牢骚,无疑与其在更早时候便已经和淮地粮商建立起了稳定的供应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毛文龙在他们的支持下,得以维系东江集团的生存,利用皮岛自立山头,并开始尾大不掉,对朝廷政策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天启五年(1625)年底,朝廷不得不“改授登莱巡抚武之望为南兵部添设左侍郎,以岛帅不受驾驭,与之不和故也”。g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362页。
毛文龙又是如何与淮地粮商建立起了联系?征募到辽东的淮兵或是其间关键因素。
由于中国北部冬季时间较长,海域冰冻,自每年农历十月到来年三月左右都是冰封期,之后才能恢复通航,故而上文述及由管大藩征募而来的浙淮水兵只能滞留于中转地登州等待前往辽东,这一举动给当地带来了繁重的管理负担。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辽东经略袁应泰上奏朝廷抱怨指挥不动募集而来的新兵,尤其提到了淮籍将兵:“淮扬都司金冠,江南营加衔都司王表,各领兵一千名,于万历四十七年内到天津,借口淮扬巡船不堪补验,必须拆造,羁延三年不出海。……而客岁守备王锡斧等,领淮浙兵七千余名,十月到津,竟营谋运粮,不肯渡海,此犹在都门外者。”h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 、李鸿彬 、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150-151页。“羁延三年不出海”并非袁应泰夸张之词,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一月,淮安海商便已经在山东一带进行海上粮食贸易的活动:“闻浙江海船、松江太仓沙船、淮安雕船时至山东宁海买米”。i《明神宗实录》卷576,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乙卯,第10913页。由于当时明军在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淮兵自然不愿被派遣至辽东前线送死,而是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海上行船技术,与重开海运后的淮安海商们“营谋运粮,不肯渡海”。或言之,他们海商的成分多过了水兵成分。朝廷对这种情况自是不能接受,三月,兵部再次要求募集而来的水兵前往前线,却激起了淮兵的强烈反应,差点发生兵变:
援辽诸将多迂途观望,不时至兵部覈实以闻仍再申限。计副总兵管大藩等所统浙、直水兵九千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川兵五百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京营南浙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三名,除渡海应遇顺风当稍为宽限……管大藩部将张国卿所领江南水兵道亡几尽,淮兵至登者以修船候风为名,逍遥逾岁,守备李际阳督之登舟辄刃伤,几殆。
十月二十日,朝廷“加都司金冠游击将军,同守备保世宁等统领淮兵四千六百三十九员名,战船一百三十八只出海援辽”。a《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元年十月丁亥,第765页。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淮兵滞留登州。
天启二年(1622)四月,御史李时荣上奏:“山东骤增军兵,谷价腾踊。陶朗先出海之师万人,刘国缙集辽三千,最骄横而难制,淮扬募兵七千为最,何以建复辽之策?”b方孔炤:《全边略记》,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3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五月三日,“总理三部侍郎张经世疏言:今日欲使奴酋不来,莫若接济毛文龙以为牵制。顷部议以闽兵三千过海,宜催之速来,淮兵八千已至登莱,并贾祥所领浙兵三千一百同闽兵俱当速发为文龙用。……上是其议。”五日,兵科左给事中朱童蒙疏陈兵务六款中,再次督促发兵:“御史游士任募淮兵先后到八千七百。登莱弹丸,兵民杂处则民苦,米价腾涌则军苦,月粮一万五千则官苦,宜分一半过海听毛文龙调度,其余散之北边险要,以资防御。”兵科官员朱大典亦持同样的观点:“而淮兵知道东省者,既不受登抚之节制,又不听天津之调援,殊为二东隐忧”。c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 、李鸿彬 、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270页。七日,朝廷同意山东的出兵意见,却一度难以调动:
管兵部事大学士孙承宗题,御史游士任募兵淮上,檄赴齐东,议者屡言其为登莱扰害。而领兵游击孟淑孔欲分作两班,三月为期,及瓜互代,则道途往来,谁为输供?客店居民,几堪骚扰?况假归者逐影疾驰即暂止者,亦刀环入梦究不得一卒之用。顷毛文龙请兵五万期捣奴巢,而张经世亦请将淮兵勒期渡海,接应文龙。但孟淑孔统御无方,众心未附,士任亟当,疾趋登莱,查点督发,一则割已操之刀,自有成算,一则结未了之局,可无偾辕。上敕游士任星驰约束分派,毋致生事,如稽延推避,罪有所归。d《明熹宗实录》卷22, 天启二年五月戊戌、庚子、壬寅,第1088、1092、1095页。
此时的毛文龙刚进驻皮岛,正将之辟为基地。e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第39页。虽然尚未发现相关史料表明其在此时向朝廷申请淮兵为其所用,但是从朝廷对淮兵从“援辽”到“接应文龙”的改派来看,这个时候的毛文龙或许已经注意到淮兵兼具海商的功能,对其粮饷保证有莫大益处,从而向朝廷提出了改派淮兵为其所用的申请。反言之,即便毛文龙并无此申请,朝廷也乐得将这批“毒瘤”兵员交付出去,以消除他们对地方及其他部队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漂泊海上的毛文龙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六月,对毛文龙颇为欣赏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亦极力促成淮兵归毛:“夫文龙以二百人往,胜乃为倖,败则其常,不菲朝廷。试问江淮召集之兵之供亿,不烦海内之征调,收功固足壮国威,即取败亦无伤于国体,奈何海上官军,恶成乐败,创不必然之议论,隳豪杰直前之气,令三军咋舌而相戒哉……试问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f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275-276页。为此,王在晋上奏朝廷,一边着手裁兵,以减少淮兵驻扎山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一边努力响应毛文龙发兵之请:
今边塞之兵,习骄习玩,事事仿样,种种效尤。一人哗,则众思哗;一人窜,则众人思窜;一处增饷,则各处尽思增饷。僻处且然,何有冲边?内地且然,何有远戍?自援辽募兵未尝得兵之用而海内受兵之害极矣。人思添兵而臣独思减兵,以苦兵甚于苦虏也,御兵难于御虏也。彼登莱所急者,水兵耳。陆兵安所用之?青齐之劲卒,甲于县宇。彼江淮之兵,又安所用之?台臣之往募也,谓江淮之人之习海也,乃见海而惕,望登而避,惧奴而缩。莱州原非冲海,驻兵于此,恐至登而受巡抚之节制也,无节无制之兵可用乎?恐至登而属总兵之训练也,不训不练之兵可用乎?恐至登而乘船出海为奴所攻、为风涛所泊也,不习舟、不习海之兵可用乎?江淮应募者多系臣乡人,闻风蚁附,原非强敌,奈何何駴视之。毛文龙固请兵矣,而欲江淮之兵接应,陆兵不能泛海,登莱向苦无舟,此又未必然之事也。募臣游士任所募水兵三千驾所造船只,及时渡海。再查江淮陆兵中有习水者,量行挑选,接济毛文龙,协力以图攻取。a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233页。
王在晋裁兵数量颇多,“疏报清汰冗兵冗员,计关门汰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一片石等处汰兵四百五十八名,又裁革冗员参游都司备总等官二百余员,其余汰家丁、汰杂流、汰薪水,一年所省可几四十万。”b《明熹宗实录》卷23,天启二年六月癸酉,第1132页。裁兵完成后的七月七日,王在晋连同天津巡抚毕自严再次“各请以闽兵淮兵渡海,接济毛文龙”。c《明熹宗实录》卷24,天启二年七月辛丑,第1189页。裁兵的威慑力非常明显,淮兵战斗力在帮助山东地方镇压白莲教之乱中表现出来:“淮兵驱斩夏镇妖贼,运道复通。淮兵与贼交锋杀死大半,贼穷无路,从东路白山逃走沙沟营,哨官姚文庆等率领营兵、乡兵赴彼截杀,斩贼五十余名,将前抢去粮船七只撑回韩庄,余贼尽归滕县。”d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四),北京:京华印书局,1968年,第1663页。淮兵的表现使得他们出海援助毛文龙再生变数,山东巡抚赵彦请求朝廷留下淮兵,在协助山东维护漕运的同时助剿白莲教:“臣见湖广道吴之仁,请留广兵三千、福建兵三千名镇守济宁、张秋,以防漕运,忧深虑远,深所敬服,再请暂留班军以靖妖氛。闽广兵及班军皆为辽而征调者,经略留之,以靖东妖。矧东省为经臣所节制,兵不足,又留江淮兵八千,协平辽贼,何叙功之不及耶!”e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264页。但迫于辽东的军事形势,兵部没有同意:“署兵部事侍郎张经世奏,原议以御史游士任淮兵及招练兵俱调发,渡海接应毛文龙,奉旨屡矣。乃士任仅先发官兵一千五百余员名,渡海策应;余七千余员名,具调赴邹滕,合剿妖贼。……秋风已厉,渡海无期,乞严旨督催,得旨,游士任募到淮兵着遵旨督发渡海,不得以赴兖剿贼,致误接应。”f《明熹宗实录》卷24,天启二年七月庚申,第1229页。淮兵没能留在山东剿匪,也与毛文龙坚持要求派淮兵为其所用有关。八月十四日,兵部同意了毛文龙的请求:
兵部覆平辽副总兵毛文龙请兵请饷疏,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奴则有余。朝廷何爱三十万金钱,不以饱海外之义旅而收其一臂之用。至臣部前所题闽兵与招练兵,其渡海有日,独淮兵屡奉旨过海而裹足淮扬,藉口剿妖。宜速行催发,并报开船日期,以无误军机。g《明熹宗实录》卷25,天启二年八月丁丑,第1264页。
直至年底,淮兵方渡海支援辽东完毕,虽然“五千淮兵之渡海者,率飘泊于各岛未有一到”,h《明熹宗实录》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癸未,第1470页。但他们随后迅速为毛文龙所收拢,参与众多军事行动,成为其收复辽地的重要力量:“又令淮兵整备舡只,在千家庄住候。”“江淮兵从千家庄进,浙直兵从水口进……”。i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第22、26页。到了年底,据毛文龙在向朝廷请粮所陈述的相关内容来看:“今臣有江淮浙南北游营征东等处兵八千余名,挑选辽兵三万七千余名,再用招练辽兵二千余各业共四万七千余名,其募足五万亦易之矣”,j陈建撰、江旭奇补:《皇明通纪集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2349页。其辽兵基本上都是从投奔其而来的10万辽地灾民中分选而来,不习水性,毛文龙由皮岛进攻后金,渡海作战是唯一的运兵方式,淮兵能够“整备舡只”,使得他们在人数众多的辽兵当中依旧保持着特殊的位置,堪称在毛文龙麾下的一支技术兵种,故而在其心中位置靠前。这种情况直到天启六年之际并未发生大变,天启六年(1626)九月,朝廷准备整顿东江势力,派工科王梦尹巡视海外,其建议朝廷“南兵之当裁也。”原因是“臣闻南兵出海时,名虽数千,至岛不及一千,毛文龙虑其虚弱,遂以辽人补之,四五年来,阴阳之消磨,饥寒之零落,又不知凡几矣。况以北人补南兵,名虽南而实北,何益乎?乃糜东江之饷三分之一,合无除堪留驾船水手之用外,以辽人归入辽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还,去姑存之虚名,成画一之纪律,庶名实相称而士伍无假借矣。”a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380页。虽然王梦尹列数南兵种种弊端,如南兵北人之异、“老病不堪”、多耗粮饷等等,旨在裁减南兵,但是这些现象的背后亦说明淮兵在毛文龙队伍中的特殊性,一直都未曾改变。
南兵在东江集团中的特殊性在毛文龙被杀、其部属孔有德叛变占据登州后依然存在,甚至得到了加强。崇祯五年(1632)年底,官军俘获出海补给的叛军船只一艘,审讯后发现“然贼欲出海,操舟必须水手,水手尽是南人”。“虽然贼船每出,必辽叛多于南人,示监制也。”为此,官员提议利用南人乡土关系达到瓦解叛军的目的:“傥得南来水犀分布海面,以为南人接应,将如磁之引针,水之就溼,有不倒戈缚叛而烝徒楫之者乎?”这里所说的南来水犀所指依是淮安水军:“为今之计,惟有仰藉淮安江北之水犀慨发三千,驾坐原舰,星速赴登,布列于长山庙岛之间。”b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崇祯存实疏钞》卷1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卷内页第9页b、第10页、卷内页第58页a。
清《阜宁县志》人物传中,记载了融淮兵与海商为一体的人物:
陈幼学,字献可,英勇负壮志,天启间甲子,佐运辽粮,岛帅毛文龙嘉之,荐授参将,与尚可喜善。顺治间,可喜封靖南王,挈幼学南征,积功至骠骑将军。
张梦凤,字凤灵,高邮人,久居庙湾。尝行贾海外,往来毛文龙军幕,识耿仲明、尚可喜。耿、尚入清骤贵,统师南征邵北,阎毅公以义侠杀人,缧绁待决,梦凤素重毅公,为言于耿、尚,得令提毅公军前推问,遂免死。c阜宁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阜宁县志(合订本)》,第209、211页。
陈、张二人最初均以海商身份与毛文龙建立起了联系,而在后毛文龙时代又在军事方面发挥着影响力。虽然有学者认为“毛文龙旧部的投降,并未如学界成说所言,为满洲建立起一支水军,或是显著提升了他们的水上战力”,d陈韦聿:《毛文龙旧部的降附与满洲之“水军”:史事的考虑与成说的商榷》;李其霖主编:《宫廷与海洋的交汇》,新北:淡江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第344页。但这显然也不影响陈、张二人商、军合一的身份。
三、结语
有明一代,实行海禁的根本原因是维护疆域稳定,但“计往者倭奴之入闽浙为甚,苏松淮扬次之,登莱又次之,而辽左则绝无至者,其地形水势不便也。”e《明神宗实录》卷543,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第10321页。地域的差异使得明朝在海洋管理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南北直隶的江苏、山东海域,一直牢牢为朝廷力量所掌控,“罢海运”政策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在“禁海外”的浙闽粤等地则是“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f谢杰:《虔台倭纂》,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第231页。的情况,而浙直淮扬的海滨之民(盐徒灶丁)为朝廷征募为兵,而非入海为寇,但同样兼有商人的属性。毫无疑问,战争是促使朝廷对海禁政策做出调整的最直接动力,允许海外贸易的“隆庆开海”是倭乱后的顺应民生和国计之举,而入朝征倭及辽东战争亦促使朝廷迅速重开近海而行的漕粮海运。本文所要观照的重点并非明金之间的相关战争史实,而是在探析淮安海商团体在保障东江集团粮饷、海上互市所起作用的基础上,探明东江集团主导(毛文龙)时期的班底,揭示淮安海上人群在明末军事形势变迁下的变通应付,显示淮安海上人群相较于闽浙地区的海上人群处于更加掣肘的状态,生存环境更为恶劣,更难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