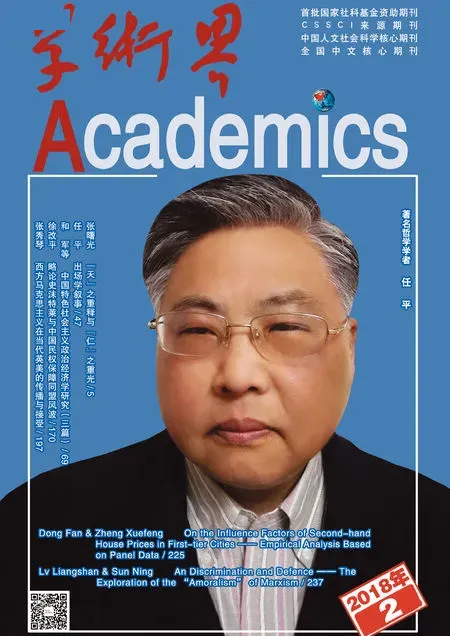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美的传播与接受〔*〕
○ 张秀琴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从总体来看,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主要议题是:文化、历史与经济。当然,这三个议题之间并非彼此孤立,相反,经济学渗透在文化与历史中,且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传统经由英国传播到美国之后,几乎贯穿整个美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使得其哲学、文化和历史研究都充满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底蕴(尤以对《资本论》的研讨为例)。这一英美传统,其主要研究范式,则是在分析法框架指导下的理论探索,其旨趣主要在致力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20世纪工程”。虽然其研究路径也即分析方法,在全球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接受史中具有独特地位(特别是与欧陆的唯理论传统相较),但毫无疑问,192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于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其文化研究传统,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暂不论英美学者圈子言必称的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实际上,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才走进马克思的),仅是法兰克福学派一批代表人物因二战而在美国的学术移民,就对整个美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环境造成了至今不可忽视的持续影响。然而,即便如此,英美马克思主义依然一如既往地(有意无意)“游移于”人本主义(文化主义)和科学主义(结构主义)之间,以期从中找出一条更为适宜和符合时代精神的英美式“马克思主义道路”。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
“马克思在英国生活工作了30年以上,这一事实无助于他的思想在英国左派中的传播”〔1〕。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1970年代末期)将1950年代—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归纳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接受情况,主要表现在“这三大领域: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其中,“作出最大努力的方面也许在经济学”〔2〕。知识分子为此致力于探讨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文学领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问题(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爱德华·汤姆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特里·伊格尔顿以及“汤姆森—安德森之争”);二、史学领域的英国乃至欧洲如何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问题(霍布斯鲍姆、佩里·安德森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组、“多布之争”等);三、围绕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群所展开的有关马克思生产理论和价值理论的论争(斯拉法、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等)。这其中,(除了政党以外)分别扮演重要平台作用的机构和杂志包括: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新左派评论》(1960年创刊)和《资本和阶级》(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创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柯林尼克斯也认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英美世界“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3〕。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还是上述三个问题领域的研究,都早已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4〕只不过直到二战后,才逐步形成上述三大领域和话题,而这些领域和话题形成较大影响力,则是在1960年代以后。
这一作为分界线的1960年代,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英国、且以《新左派评论》为媒介逐渐进入英国知识界之时,可以说,这个杂志1962—1983年间的实际领导人是佩里·安德森,正如安德森本人在1976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所介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代表人物(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都让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他所领导下的《新左派评论》杂志即致力于弥补这一“令人羞愧的差距”〔5〕,向英国知识界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6〕于是,《新左派评论》主动承担了翻译大量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艰巨任务。霍尔也曾于1990年提出,“如果没有那些‘欧洲文本’(即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和随后的葛兰西的翻译作品),这些文本在学术界内部并不被阅读,那么文化研究不可能发展自己的项目:它无法生存;它也不可能成为在自己方向内的学术领域”〔7〕。由于这一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收”主要聚焦于“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家”(特别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8〕,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市民社会)思想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主体建构论)思想(包括稍后的福柯知识权力论)对于英国学界的“先入性”持续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体现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观念、汤普森—安德森之争,甚至体现在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9〕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结合”中,直至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英国才形成了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一、“新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以爱德华·汤姆森等为例);二、“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威廉斯等为代表);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以柯亨等为代表〔10〕)研究等。〔11〕它们所对应的子议题分别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研究(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等为例)、社会过渡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以爱德华·汤姆森和霍布斯鲍姆为例)、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以柯亨为例)。
虽然我们可以把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化研究”阵营,扩展至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以区别于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政治和经济研究聚焦做法——如佩里·安德森所说的“文化转向”),然而,20世纪中后期(20世纪50—60年代)日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却无疑使得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尤为趋于凸显。而后者又是以20世纪60年代相继创办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12〕(和《新左派评论》〔13〕)为主要媒介的。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促使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发生第二次“断裂”(继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同社会学的“断裂”之后的再次断裂,这次是“断裂成一种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是这次断裂的产物和标志,并因此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力图开辟一条不同于第二、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也即一条“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基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物质、社会和历史存在条件”的考察)〔14〕的道路。与稍早(20世纪30、40年代)出现并繁荣发展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相比,英国文化研究一方面与前者具有不可忽视的共同点,也即坚持将文化诸形式和现象纳入社会关系的范畴予以考量,并在这个意义上力主他们所谓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与前者不同的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更加力主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捍卫,因此,虽然二者都反对所谓(由文化工业所导致的)“大众文化”,但英国文化研究并不因此如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走向一种“精英文化”的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领域,英国进步知识分子于1946年组建了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该小组的“最大关注点之一是复杂的、漫长的和混乱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5〕问题,这里简称为“社会过渡理论”〔16〕。历史学家小组大体可分为两派,即“强调人类动力”的人本主义一派和“强调结构”的科学主义一派〔17〕(后者也称为结构主义)。实际上,通过他们对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思想的发挥,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成员尽管彼此之间也有论争(如著名的汤姆森—安德森之争),但都难以改变他们主要游移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基本格局。从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第一,提出了自上而下的史学观(以爱德华·汤姆森为代表),并因其对群众(如工人阶级等)的历史创造性的关照而赋予其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色彩,进而为日后的英国左翼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过渡理论议题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二,社会过渡理论,也即英国等欧洲地区的现代化之路(以霍布斯鲍姆为例),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如同意识形态研究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那样)。第三,对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一个独特贡献,它包括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和戴维·麦克莱伦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
而正如麦克莱伦所指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个独创。该学派正式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主要特点就在于,以分析的(含语言分析、逻辑分析、行为决策分析等)方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特别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群为主要文本依据)。从总体来看,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以后又因代表人物在英美间的学术迁移而带有跨国属性的学派(甚至跨至整个英语界)。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基因。柯亨(G.A.Cohen)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最重要的创始人,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为英美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特别是其经济分析议题) 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虽然,这已是经过其改造或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了。其基本定义可归纳为:在一种“有限的政治意义上”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理论,也即一种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式(或经济结构)相互作用”的时代发展的学说。这样的学说,它本身以哲学人类学也即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为基础。这一“基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此之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如卡尔沃顿、悉尼·胡克)虽然也通过融合本土的实用主义而进行理论传统的再造,但其所产生的理论影响远不及60年代后产生的戏剧性变化深远。〔18〕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包括早期手稿)在美国的公开出版以及新左派运动的推介,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主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过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如其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美国学界的思想贡献,由此也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诸流派的持续涌入。在这一涌入过程,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既致力于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术传统,又使它在新的“汇合”与抽象中成就了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理论路径和思维方式,即力图“绽放”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围绕着两大学派、两大议题而展开:其一,“文化议题”的主要理论贡献者是美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包括诺曼·莱文、本尼托·奥尔曼和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其思想传统主要源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一派,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二,“经济议题”则是以罗伯特·布伦纳等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影响其思维范式的则主要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一派,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界持续关注的话题。当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当代美国时,这一问题也无不例外地引发了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讨论,他们接续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一派的传统做法,即立足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之源的强调,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之维。为此,在接受和消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他们特别强调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研究,〔19〕以期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否定的立场,并基于此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分析当代文化问题。
在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辩证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十分核心的范畴,对它的理解将决定着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为此,他们不仅立足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争,以重新阐释辩证法的概念,而且还基于辩证法的文化研究,以重建辩证法的当代社会批判功能。通过对辩证法的重新释义和功能重建,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一派实际上掀起的是一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史上的范式革命,其基本内容包括:强调主—客体互动关系的主体总体伦;以经济—文化有机体论为视角的总体叙事框架。所谓强调主—客体互动关系的总体论,指的是当代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在坚持主体—客体辩证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主体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的支配或主导地位,并将之诉诸于哲学自主性的逻辑。如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论辩证法观显然强调的是对作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的揭示,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也视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由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当成了资本本身的一种作用和‘资本’这个词的含义的一部分”〔20〕;莱文的马恩对立论则提出了自己的辩证法研究就是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他看来,前者指的是从黑格尔到马尔库塞和卢卡奇的“社会现象学”传统,而后者则指的是肇始于恩格斯、经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在苏联体系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体系中被定型的、一种历史宿命论式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化,但却无论如何要通过“给唯物主义重新下定义”来“保留黑格尔的主观活动概念和意识干预物质的和社会世界的概念”〔21〕。同时,对于主体总体论的强调又是以经济—文化有机体论为叙事基础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几乎当今所有知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都会涉及经济学问题,他们要么是立足于文本(特别是《资本论》)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要么从考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由来与发展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在他们看来,这已不是一种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综合研究或总体研究,是一种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种文化逻辑来研究的叙事框架。
这显然并非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而是有其深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于辩证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正如詹姆逊所总结的,其所具有的三个典型特征分别是:第一,强调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属性,也即将辩证法置于社会历史领域而非自然或科学领域;第二,将心理学因素纳入辩证法考察的视域,同时将文化和上层建筑置于经济基础相等同的决定性地位;第三,消极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传统中的贡献。〔22〕因此,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反映的不过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同,当代美国学者大多强调辩证法的主体维度和文化特质,同时又不放弃传统的二元论格局,因此,他们继续用卢卡奇等人所贡献的总体范畴力图一方面表达对传统苏联模式机械论或决定论的不满,另一方面,又传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传统。但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一派不同的是,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只是从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获得理论资源,而是主要致力于晚期著述来开拓性地推进当代社会批判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而扩大了内涵的文化概念就充当了这一批判分析的工具和切入点,总体辩证法也体现在这一过程之中。文化已不仅仅停留在精英和高雅层面而走向大众,而且开始以“资本”等形式扩展到文化之外的其他社会结构和层面。
其次,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共包括三个构成部分,即以罗默和埃尔斯特等为代表的“分析学派”、以奥康纳和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派”和以布伦纳为代表的“经济学派”。虽然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一派影响而形成的“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一直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独特性的贡献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如果说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一派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明显隶属于文化研究主题而处于隐形地位的话,那么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一派中,政治经济学则逐渐褪去哲学隐身衣,成为“主角”。当代美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皆直接以“经济议题”来展开其相关论述。如:生态派从文化、自然与社会辩证关系的角度〔23〕探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性矛盾与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灾难性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分析学派则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借用新经济学的通用原则(如博弈论等)来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经济学派则更是立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的考察来提供“新传统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官方的正统经济学派,例如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尽管在学术史上其阵营内部也有分歧(如早期的斯威齐和当代的布伦纳),但他们都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分析中的超经济因素〔24〕之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首要性。这样的“经济议题”,即在承认“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意义的前提下而展开对社会总体中的“超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开放式、多元式的关照,显然是受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一派的影响,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论”。
在“经济议题”下,当代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重新解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问题领域,力图重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和实践旨归。同时,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一派思想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在时间上拉伸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长度,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纳入视域;另一方面,在空间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跨度,将目光扩及含非传统欧美国家在内的全世界范围。而在这一阐释过程中,他们又各自基于自身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和新原则,例如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布伦纳认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由水平关系(存在于不同剥削者之间、剥削者和生产者之间)和垂直关系(以不同社会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为划分依据)所构成的宏观结构的变化。这种宏观结构由于是一种综合的、累加的效果,因此表现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定要素。而布伦纳之所以要提出“社会财产关系”,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他的社会财产关系更多地侧重于对生产关系的强调,而且对生产关系的探讨不仅涉及以阶级斗争为形式的垂直层面,还同时包括在水平层面上对同一阶级不同阶层的比较分析。再如分析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根据埃尔斯特的解释,个人主义方法论指的就是“全部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可以以各种只涉及个人(他们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的方式来解释”。也就是说,个体的理性行为是为社会现象(例如剥削)建立普遍理性选择解释的微观基础。而罗默则表示,“一个人的阶级属性不应被看做是在他从事经济活动之前就已既定的某种东西:它是一种产生于市场行为的经济特征。一个人成为某一阶级的成员,是由于他的理性行为,是由于他在面对约束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最优选择,而这些都是由他拥有的财富所决定”。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在“经济议题”下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主要立足于科学主义立场上的前提下,他们对自然的关照、对个体主义的凸显以及对经济发展统计数据背后的属人的超经济因素也即政治共同体的首要性的强调,也不无体现了以主体为导向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总体论的某种倾向。〔25〕这或许表明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逐渐选择创造性地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力图从一种介于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方案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历史复杂性。
三、结 语
综上所述,英美两国由于共同语言文化背景和共享学者资源等因素,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着互相影响的交叉关系,这会通过它们分享的共同研究方法和共同研究主题而凸显出来:前者指的是分析的方法;后者指的是文化、历史和经济议题。
注释:
〔1〕〔2〕〔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5,326、327页。
〔3〕〔5〕〔8〕〔英〕柯林尼克斯等著:《盎格鲁·撒克逊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何方?》,赵锐译,载雅克·比岱等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3、85、87页。
〔4〕并在1930年代有了一定气候,直至二战期间,达至第一次高峰(处于英国共产党领导下);二战后至1970-80年代,则处于低潮期(由于撒切尔上台、随后的苏东解体等事件的影响,虽然70年代受欧洲大陆左翼运动影响,有一个所谓“红色欧共”的短暂活跃时代)。直至1990年代以后,又有一个“复兴”时期出现(相关研究,请参见Keith Laybour, Marxism in Britain: Dissent,Decline and Re-emergence 1945-c.200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6〕实际上,这是欧陆文化对英美文化的“融入性影响”,如同二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大学环境之间的历史联结”(参见〔英〕柯林尼克斯等著:《盎格鲁·撒克逊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何方?》,赵锐译,载雅克·比岱等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6-87页)。
〔7〕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 53(summer 1990), p. 16.
〔9〕以柯亨的这本书(1978年初版)所奠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被视为“第一个完全的英语世界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参见〔英〕柯林尼克斯等著:《盎格鲁·撒克逊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何方?》,赵锐译,载雅克·比岱等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10〕还有同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埃尔斯特、约翰·罗默、赖特和布伦纳等。这是一个极具“异质性”的学派(特别是其在美国的发展),不仅名称不统一(“理性选择学派”“9月小组”“市场社会主义”或“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等),而且其论争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局限于经济学,还涉及历史和政治。
〔11〕关于前两种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出现被认为是在“1980年代初期”(参见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1.);关于第三种英式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时间,被界定为以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初版为界。
〔12〕参见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c., Taylor&Francies, 2005 (from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80), “preface”, p.vi. 根据文献记载,1964—1968年,霍加特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CCCS,该中心于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创办),1968—1979年,霍尔继任中心主任(ibid.)。该中心从1972年开始出版《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霍尔身后,分别又由理查德·约翰逊和乔治·拉瑞恩等继任中心主任,直至2002年解散(其间,20世纪90年代还曾与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合并,并因此将教学对象从研究生扩充至本科生)。
〔13〕该杂志于1960年年初由《新理性者》(由爱德华·汤姆森等人创办)与《大学与左派评论》(由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创办)两个左翼杂志合并成双月刊《新左派评论》(NLR)。斯图亚特·霍尔出任首任主编(爱德华·汤姆森、雷蒙·威廉斯等为编委会成员)。1962年起,佩里·安德森出任第二任主编,随即开始大量译介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其后,虽然杂志社经历多次人事变革和理论论争,但日益成长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左翼理论平台,并拥有著名左翼出版社——VERSO出版社,直至2000年安德森再次入主该杂志。
〔14〕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c., Taylor&Francies, 2005 (from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80), “Introduction”, p.12.
〔15〕〔17〕〔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38页。
〔16〕即“the Transition theory”,20世纪50—80年代的相关论述包括:R.H.Hilton and Christopher Hill,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Science&Society, 17(4), 1953, 340-351; Eric Hobsbawm,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Marxism Today, August, 1962; Maurice Dobb,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Marxism Today, September, 1962; Paul M. Sweezy, “Feudalism-to-Capitalism revisited”, Science&Society, 50(1), Spring, pp.81-84, 1986等,以及布伦纳之争时期的相关著述。如果说这些“过渡理论”主要聚焦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大纲》中的相关章节中所探讨的主题,也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如何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的话,那么佩里·安德森则将这一过渡理论探讨的时段前溯到了“古代社会如何向封建主义过渡”议题(参见他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参见李佃来、梁小燕:《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追踪》,载《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10》,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19〕例如伯特尔·奥尔曼的《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诺曼·莱文《辩证法的内部对话》、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辩证法的变奏》等。
〔20〕〔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21〕〔美〕诺曼·莱文:《辩证法的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22〕F·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Verso, 2009, p.6.
〔23〕特别是过度生产、异化消费和技术理性主义。
〔24〕也称之为政治共同体因素——特别是阶级理论。
〔25〕再如佩里·安德森曾敏锐地观察到,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本身所具有的两个维度(水平和垂直),使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中,既保持一种不变的结构性宗旨,又难免表现出对这一宗旨的某种“偏离”。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The Positive Role of Governance in the Wa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mp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Style
—— A Corpus-based Case Study of Lianghuiwang〔*〕 -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econd-hand House Prices in First-tier Cities
——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 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上的突破点”〔*〕
- 城市治理的差序参与〔*〕
——基于“市民服务热线”的分析视角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