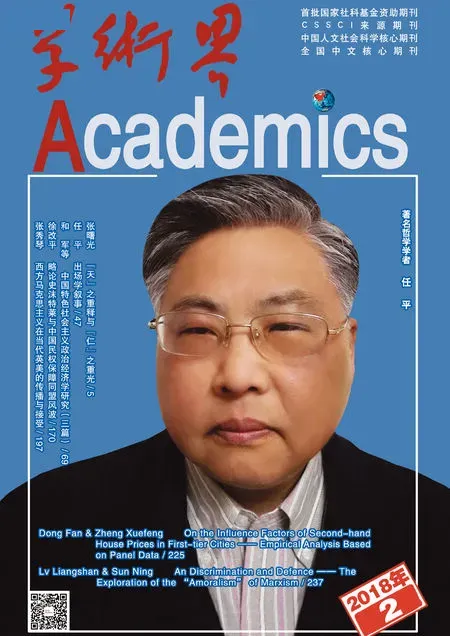略论史沫特莱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
○ 徐改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1932年12月18日,以宋庆龄和蔡元培为领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来年1月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不料,该分会刚一成立,就发生了北平分会会长胡适与上海总部因意见相左导致他被同盟开除的事件,史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其时为1933年3月13日。“民权保障同盟风波”之所以值得研究,除了研究界早就重点关注的它在民国政治史及宋庆龄政治生涯中的特别意义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史意味:该事件不仅主要涉及到胡适这位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还牵涉到左转后的鲁迅及另一位比较重要的新文学作家林语堂;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社会活动家、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下文均简称其姓史沫特莱)在其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当年的史沫特莱经此事件转变了她对胡适和林语堂的态度,更加深了与宋庆龄、鲁迅的友谊,中国政界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与史沫特莱这样的美国左翼社会活动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及分道扬镳,其实关涉到如何认识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政治阵营划分的大问题。笔者不揣冒昧,想通过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的全程梳理,求得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限于所论问题的复杂性及论者自身见识的有限性,必然会存在不少不足,还请方家指正为盼。
一、胡适初步领教史沫特莱及宋庆龄对民权同盟的非常操控手段后的果断切割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于1932年12月中旬的上海,还在该组织筹备期间,他们就有在国内各重要都市设立分会的打算。基于这个远景规划,1932年11月底,史沫特莱就到北平,着手成立北平分会的事宜,以致分身乏术,没来得及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的会议。在北平居留期间的史沫特莱,除了与胡适、李济等智识阶级接触以促成分会成立外,她还有与上述时贤不能直接言说的秘密——她在积极物色人选,希望其在即将成立的分会中暗中起引领作用。1933年元月,史沫特莱拿着一封来自北平陆军反省院的在押人刘尊祺(时名刘质文)写给宋庆龄的求助信件,希望费正清帮他翻译,由于该信件笔迹潦草后者无法胜任而作罢。这是费正清夫人维尔玛提供的信息。〔1〕史沫特莱返回上海的时间不详,但她出席了1933年1月17日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会议是见于报道的。在1月25日民权同盟上海临时执委会的会议上,她以在北平所收信件为依据,提议代表上海总会出席北平分会的杨杏佛就包括信件书写者所在的北平陆军反省院等监狱展开调查。限于开会的特定场景,出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充足时间阅读该信件,而是基于当局对政治对手的一贯严厉态度,该提议被顺利通过。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于1933年1月30日正式成立,胡适被推举为9个执行委员之一。杨杏佛代表总会做报告时,感慨说:“争取民权保障是18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还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此话给胡适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写《民权的保障》时原文引用以示推崇)会议推定杨杏佛、胡适、成舍我三人为代表,赴北平监狱视察和慰问政治犯。当晚11时,他们面见北平军事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获得了次日视察监狱的许可。第二天,也就是1月31日10时,三人依约视察了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两处监狱。2月1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第一次执委会开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他领衔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及检察院发送了电报,要求惩办枪杀记者刘煜生的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这是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以来重点推动的工作,现在北平分会成立了,也要就此事向当局施压,以确保中国新闻从业者不再受政府官员的迫害。2月2日,即将乘车返回上海的杨杏佛对记者发表谈话,对其视察的监狱有如下判断:“总括言之,监狱方面待遇较看守所稍好,惟军事机关所属之监狱,政治犯亦均带脚镣,不无遗憾。”这两则消息都被北平《民国日报》记者于2月2日在《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第一次执委会》的大题目下做了统一报道。限于当年的交通条件,杨杏佛返回上海,向民盟总会报告其视察结果,应该是2月6日的事了。〔2〕
2月1日,当北平的胡适还在应和着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就刘煜生案向当局发电报之时,在上海的民盟领袖宋庆龄及史沫特莱就写信给他,敦促他用她们附寄的《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向当局抗议,要求他向当局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2月4日,胡适收阅这些材料后,对控诉书的真伪产生怀疑。因为,在他本人视察过程中,并没有在押犯告知这封控诉书所罗列的酷刑。胡适感触最多的是政治犯们对戴着脚镣的生活倍感痛苦,监狱伙食很差——一如上文杨杏佛对记者的表态。起初,只是严谨的习惯使然,2月4日当晚,他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合写一信,说明情况,并说自己还收到类似中文文件。胡适这里所说的类似文件是同属北平陆军反省院在押人韩麟符所写信,此信更强调监狱对在押人员精神上的禁锢,并提出五点对应的改进意见。综合自己所闻所见,胡适认为史沫特莱所转信是伪造的。
胡适的这个判断对吗?今天,中国大陆学界广泛采取的说法是,此信绝非伪造,为关押在北平陆军反省院的刘尊祺所写。当初,刘尊祺从《中国论坛》上得知民盟成立的消息并与狱友商量后,直接给宋庆龄写了揭露反省院黑暗现状的英文信件,被《中国论坛》所刊登,民盟通过决议派杨杏佛到北平调查情况,实施营救。据笔者考查,这些说法都源自刘尊祺在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所写纪念文章《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只是,多数研究者依此确认当年胡适所收信件真实的同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刘尊祺说当初是看到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才写信给对方,希望得到援助,其信先被登载在《中国论坛》上,然后才有了3月份杨杏佛视察反省院的事情,而且杨与他交谈时,明确提到了自己是奉孙夫人之命来视察的。事实上,杨杏佛视察监狱是1933年1月31日的事情,刘尊祺的信登载在2月11日出版的《中国论坛》2卷1期上,3月则是由他的信引发的事件高潮——胡适被民盟开除的时间。自然,指出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晚年刘尊祺有意作伪。〔3〕不过,他的回忆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当初引起胡适怀疑的缘由:由于意在引起收信人重视,所以,几个地下党员写作时也许综合了他们所知的所有监狱酷刑而不是如实陈述自己所处监狱的事实。这个写作策略也成功引起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的高度重视,从而有了派杨杏佛去北平视察监狱时包括了写信人关押地的议案。
倘若刘尊祺的写作方式已经让胡适怀疑其不是真实书信的话,史沫特莱及宋庆龄的做事方式则让胡适坚定了自己的论断不误的信念。依书生之见,派杨杏佛去监狱视察,至少要听取对方视察后的意见,再做进一步决定。但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不等杨返沪先行发表控诉书,还强势要求胡适进一步向当局提出更激进诉求的做法,只会更让他生疑。因此,2月4日晚胡适致蔡元培和林语堂的信中,首先明确表达的就是对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就发表匿名文件的做事方式之质疑。由于初知问题,胡适的措词相对客气,他只是担心,上海总会的做法有让自己蒙受携带伪造文件的嫌疑,恐怕以后无法获得当局配合,很难再继续调查监狱。如此说辞表明,没弄清楚问题时的胡适,虽担心自己名声受损,但还以同人自居,考虑着组织的持续发展。不料,此信还没发出去,次日一早,胡适就看到当日《燕京新闻》(英文)上发表了自己前一天收到的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这证明两位女革命家果如其给胡适的信中表明的那样,已自行发表了邮寄给他的材料,她们无须与调查过北平监狱的同仁沟通而我行我素的办事方式,本来就让胡适非常郁闷,而早前陪同胡适等人调查监狱的张学良外事秘书王卓然看到同一报纸后,还来电质问胡适,何以出现如此与事实不符的报导。出于种种考虑,胡适当下给《燕京新闻》编辑部致信,指明该报发表关于北平陆军反省院的材料与自己所见不符,也与自己收到的其他来自该监犯人的书信不符,并称自己还收到过写信人冒称住在他家的类似中文稿件。当晚,胡适把同样的信息也传达给了蔡元培和林语堂,在给他们两位合写的第二封信里,由于已经判断出宋庆龄、史沫特莱是有意为之,胡适直言“这是大错”,并认为“此等行为足以破坏本会的信用。应请两位主持澈查此行项文件的来源,并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决议此种文件的翻译与刊布”。这表明,当胡适完全洞察到对方的革命家手段后,对民权同盟是否有正当议事规则产生了严重怀疑,信的最后,他说:“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认识到自己有可能被迫成为匿名信件携带者的胡适,当然明白,与对方的及时切割就是对自己声誉的最好保护。
为了向更多公众说明自己的政治态度,2月6日北平的《民国日报》发表了胡适对政府逮捕政治犯的主张:“(一)逮捕前必须得有确实证据;(二)逮捕后须遵守约法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三)法院侦查有证据者,公开审判。无证据者,即令取保开释;(四)判罪之后,必须予以人道的待遇。”〔4〕胡适还强调指出,上海的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在成立之初,并没有针对营救政治犯制定“规定原则”,这是对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私下来信强势要求他向当局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公开反驳。
或许是觉得对记者谈话只列举原则而说明不足,2月7日,胡适写了《民权的保障》一文,表明自己对民权运动的认识:“渐渐训练我们养成一点爱护自己权利并且尊重别人权利的习惯,渐渐训练我们自己做成一个爱护自己所应有又敢抗争自己所谓是的民族。”而“要做到这种目的,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要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尊重法律,—面要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法定权利”。在胡适看来,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他直言对方的道路是“错的”,因为,“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就成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永远成了个缠夹二先生,永远没有出路。”〔5〕
二、史沫特莱致胡适书信的不同风格
初看起来,胡适接连3天的系列行动,有反应过度的嫌疑。那么,他大幅度动作的背后,到底有哪些顾虑呢?
事情还得从史沫特莱说起。话说1928年底来到中国时的史沫特莱,已经是在美国本土和欧洲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资深社会活动家了,她游刃有余地与出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同人种的男人们打交道,同一时段的胡适颇有到处留情的倾向。于是,就出现了下文这样让热衷于猎奇的读者最喜闻乐见的情形:1929年8月10日,史沫特莱在给桑格夫人的信中宣告,胡适有极强的“生物冲动”,并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我要的话,我可以把他搞得家庭破碎”。依照保守的社交原则,一个女性如何判断出一个男性有极强的生物冲动呢?在中国语境下,宣称可以搞掉对方的家庭,其间一定有为外人听来极具冲击力的故事发生。1930年的大年初一,史沫特莱措词强硬地要求胡适,必须两天后带蔡元培去她家和印度教授维嘉见面。信末,她嘲讽胡适尽和王公贵妇及垃圾往来,直言自己不独不崇拜胡适,还告诫对方:“如果你逼人太甚,有一天我会写文章证明你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为了中国,我有一天会这样做。我注意到你们这个时代的圣人成天吃喝。吃喝会影响体型,体型会影响脑袋。脑满肥肠的圣人对中国一点用处都没有。请注意!喔!宴席不断的圣人请注意!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一个圣人。我在此处用这个字眼是嘲讽的意思,你的圣气一点都感动不了我。我把你留在我这里的上衣穿起来,发现那颈圈是超大号的。”〔6〕到底胡适对史沫特莱做过什么“逼人太甚”的事情呢?今天的我们毫无线索。倘若只从胡适保留下的资料来看的话,一般人是看不出两人交往甚密的痕迹的,唯一的解释是,他对自己招惹到史沫特莱一定有过相当顾虑。但不管怎样,或如史沫特莱所说的,“为了中国”的关系,胡适仍被邀请到她积极张罗着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里。北平分会刚成立,胡适就接到了来自史沫特莱的信件,也许,除了附寄控诉书的内容让胡适心生疑问外,史沫特莱的来信本身也颇让胡适狐疑。何以如此推测呢?请容许笔者略占笔墨对这封以往研究者只关注其字面含义的信件略做介绍。
信一开始,史沫特莱为自己没用民权保障同盟的正式信笺写信道歉,申明这是由于参加反对顾祝同事件开记者招待会太忙所致。如此开头至少有两重涵义:首先,果然实施的是“谦恭”的方式,〔7〕早前她给胡适写信可没这么讲究礼节;其次,暗示斗争已紧急到不顾事关公事必须公事公办地使用公家信笺的程度了。如此郑重铺垫后,史沫特莱写道:“我应孙逸仙夫人和林语堂之请,现将附寄的一份文件送给民权保障同盟北方分会,请您及时进行处理。您考虑能否立即召集在北方的会员开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请求您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使这个敢于送给我们这份呼吁书的罪犯受到迫害。我个人认为您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立即去见负责官员,提出最强有力最坚决的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并要求有权进入陆军反省院与犯人会晤,并监督他们立即实行改革,对那些虐待犯人的负有罪责的人员,必须立即撤换。”从这样的叙述里,我们看不到史沫特莱本人参与的蛛丝马迹,除了必拉的宋庆龄这面大旗,不属于秘密小组的林语堂也被她拉来做挡箭牌,而且其要求具体明确还不容置疑。倘若胡适不按此方针办,下面的话就等着他:“我们已将这一报告书全文公布了,这就意味着,除非你们分会立即采取步骤,那些犯人将要重新受到虐待。”——若你胡适不作为,犯人们所受的罪里就有你的一份!我们也好奇,胡适面对后者如此前恭后倨的一封信,该是怎样的感受?
当年,让胡适生疑的还有史沫特莱的第二封信。2月2日,也就是其第一封信写出一天后,史沫特莱又给胡适及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写信,这次是以林语堂的名义通报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开展工作情况的说明。在这封信中,史沫特莱提到了她们要在中外报纸广泛刊登中英文版本的控诉书造成国际关注的事件来给政府施压的计划。这位言必行的革命家,在3日就将控诉书邮寄给了美国的国际劳工辩护委员会,〔8〕虽然胡适当年无从得知她的这个行动,但她给胡适附寄的2月2日发行的上海《大陆报》(英文),还是让胡适领略了她的斗争谋略:只见该报第一版头条在《民权同盟组织揭露的北平监狱酷刑》的新闻大标题下,配有两个提示性小标题:“新自由同盟发布为释放政治犯而行动的控诉书”“描述反省院酷刑制度的犯人来信”。全文刊登刘尊祺所写控诉书之前,有6小段的情况说明:释放政治犯的请求是经孙逸仙夫人签署由民权同盟执行委员会发布的;来自北平军事反省院的信件说明,根植于专制残暴的旧王朝的酷刑制度不仅存在于北平,而且遍布包括租界监狱在内的全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诉求是唯一终止酷刑之道,它使中国减少野蛮的同时,还将释放出不计其数的关在监狱里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干劲。与保留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的史沫特莱所邮寄的英文控诉书相比较,《大陆报》全文发表的同时,还在具体段落前加了:“辣椒熏”“戴脚镣”和“机枪监控”等小标题,把最令人发指的酷刑标示给读者,很好地呼应了民权同盟的呼吁。只是,这样的宣传攻势,并不是胡适认可的议政方式。在史沫特莱来说,她的连续写信当然意在敦促胡适按总会计划行事,可实际上却及时促使对方醒悟到彼此从政治理念到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都截然不同的事实,于是,胡适要用上节所述的一系列行动来说明己见,以免发生任何误会。
三、民权同盟总会对胡适态度的转变过程
只是,胡适的节奏再怎么紧凑,限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交通及通讯条件,他的声明也不可能被上海的同仁们及时知悉,那篇《民权的保障》更是发表在2月19日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第38号上,上海民权同盟总会的人即便有阅读北平出版物的习惯,一时也无从得见。那么,在上海的同仁们又是怎样推进着最终被称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的事件的呢?在笔者看来,以完全洞悉到胡适不可能服从组织规矩为转捩点,上海民权同盟总会对胡适有一个由敷衍解释给台阶下到断然开除并公开谴责的转变过程,这就是下文的重点所在。
2月7日上海《大陆报》以《杨铨谴责监狱条件》为题发表了回到上海的杨杏佛对他北上调查监狱的基本意见。此处的“谴责”,其原文为deplore,若是降低调门的话也可将题目译为《杨铨对监狱条件深表遗憾》。与其2日在北平的谈话相比,这回杨杏佛不仅以具体数字说明陆军反省院以关押政治犯为主的事实,也解释了监狱居住条件差的客观原因,最富爆炸性的消息是,一个叫黄平的在押犯本因湖南当局认定其为共产党被判刑六年而收押,事后湖南省来电报证明他不是共产党人后还被关押在监。只是,这些材料也不能印证已发表控诉书的真实性。更值得注意的,还是杨杏佛对民权同盟任务的陈述:“中国民权同盟的任务是不仅为北平乃至于全国的监狱带来必要的改革,而且致力于消除监狱内对待某种政治犯的不公正现象。”这与前几天史沫特莱等要求胡适直接向当局抗议并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目标之间还有相当距离。按照胡适在2月4日能接到史沫特莱1日上海来信的速度,可以推测的是胡适4日和5日写给蔡林的信,收信人在8日就可以接到。因此,杨杏佛7日谈话应是既不知道胡适意见,且不知道总会有“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新口号下,用自己的话表述着最初公布的民权保障同盟宣言。
在北平的胡适,首先收到的是林语堂2月9日给他的回信,林解释说,“此报告系由史沫特烈〔莱〕交来,确曾由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会传观,同人相信女士之人格,绝不疑其有意捏造,故使发表”。林信中还承认,蔡元培和杨杏佛和他都认为此事有问题,“须彻查来源”,“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并表示:“现此临时组织极不妥当,非根本解决不可。此事尤非破除情面为同盟本身之利益谋一适当办法不可。”〔9〕林信表明,至少写信时蔡元培、杨杏佛和他本人对上海总部某些人士的行事风格有不完全认同之处。这解释一定程度上给了胡适继续猜测的方向。接着收到的杨杏佛10日所写信,更坚定了胡适对民权保障同盟运作方式的怀疑:杨杏佛先是表达了自己对2日《大陆报》的观感:“亦甚诧异,嗣曾告会中诸人,文中所云,即使有之,必在入反省院前,不能笼统加入反省院也。”这段话,印证了胡适的判断有一定道理外,也证明杨杏佛当时也没领悟到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核心人士的斗争策略,他应和着胡适,声称要在会上专门研究他质疑的问题,还大倒苦水说:“弟等奔走此会,吃力不讨好,尤为所谓极左者所不满,然集中有心人争取最低限度之人权,不得不苦斗到底,幸勿灰心,当从内部设法整顿也。”〔10〕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成立民权同盟时,以史沫特莱为首的几个人就先行组建了秘密小组,其成员中并没有杨杏佛(下文论述),杨杏佛去北平前,上海的民盟全国执委会上史沫特莱的确给大家出示了一封控诉书,并提议他调查北平监狱。但杨并没被告知说:不管你调查结果如何,在你回上海前,我们要先行发表手中的控诉书。2月8日,当上海民权保障同盟中的核心人士不仅从蔡元培和林语堂那里,更从《燕京新闻》上知道了胡适的意见后,自然意会到杨杏佛2月7日的记者谈话没交代清楚胡适质疑的事实。于是,就有了2月9日杨杏佛到上海后的第二次声明,其重点是,包括杨杏佛本人在内的视察人员之所以看到北平监狱的状况还勉强过得去,是因为狱方早在几天前就做了准备。这声明本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也给胡适一个台阶。结果,胡适看到报纸后,立即在11日给杨杏佛写了封质疑的信,此信与声明笔者都找不到原件,但杨杏佛在2月23日给胡适的回信完整保留了下来,由此我们推断出胡适质疑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所谓几天前(several days)就与监狱方面联系与实际“几小时前”(severa hours)联系,对于说明当局是否有意提前做准备是有极大差别的,尤其当初胡适等人选择在晚上11点向对方提出视察请求的情况下;其次,胡适和杨杏佛等视察中条件最差的“陆军监狱”被改成了“反省院”,这就有可能给外界造成控诉书属实的印象。杨杏佛如此解释出现让胡适大动肝火的细节之原因:“因原文为英文(史沫特莱女士所记),打字后送来修正,嫌其过长,乃决定请语堂与史女士删短后再校阅送出。是晚大家皆忙,而又急于送稿,遂将宣传委员会章送史女士处,请删短后即发,而忘却全文尚未经详阅校正。”〔11〕这段话表明:正是史沫特莱对原文原意的重大改动,才有了胡适初见声明时的愤怒。而亲自改动了杨杏佛的声明,让它由阐释视察经过的声明变成一个控诉北平军政当局有意作伪的声明,从而给民权保障同盟解了围的史沫特莱,还拿着自己做过手脚的声明当信史去说服别人,在被修改的杨杏佛声明见报当日,她给费正清的信中明确告知对方,由于监狱早有准备,所以胡适等人被骗了。可见,史沫特莱正是引发和操控民权保障同盟风波的关键人物。
不过,杨杏佛的声明只是暂时应付了外界因胡适在《燕京新闻》的公开信引发的对民权同盟的质疑,对于引发了此事的胡适及接受了他想法的蔡元培、林语堂等相关人士来说,民权保障同盟还需给个解释。于是,2月12日该同盟召开了相关会议。由于原始资料匮乏,我们无从了解会议进程,但就会后部分人士的行动来看,此次会议当然让暗中操纵同盟的秘密小组感到欣慰:蔡元培和林语堂就被说服且被责成给胡适答复,在他们联署写给胡适的信中,否认了胡适认为个别人擅用民盟名义发表控诉书的说法,他们强调,既然发表经由执委会同意,如有过失,应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其次,胡适所述冒称寄自他家的信件不为上海民盟中人所知晓,既然该信是写给北平分会的,请胡适等人直接查处。这实际上是和胡适打官腔,意在反驳胡适声称有人专门捏造信件以达到政治目的之说法。他们还通报说,史沫特莱会有信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12〕杨杏佛14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在这次会上“史沫特烈女士甚为焦急,详述此项文件发表之经过,最后结果以实在情形由蔡、林两先生向兄解释,闻史女士昨夜彻夜不眠,草长函答兄,用航空函寄上”〔13〕。两信都提到了史沫特莱,虽然语句都不多,但史沫特莱作为始作俑者的尴尬也是一目了然的,现今公开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并没有这三位郑重预告的史沫特莱致胡适信,我们也就无法得知史沫特莱本人对此事的陈述。只是,与此事相关的其他人给胡适的信件都被有收藏习惯的胡适保留了下来,倘若当初史沫特莱真写过这封被同仁们广而告之的信的话,胡适为什么不保留呢?笔者的猜测是,史沫特莱只是在会议上用通告写信的方式来打消上海同人疑虑而已,事实上,她对胡适无法也不可能交代问题,胡适也就无从保留其来信了。真相到底如何,就看日后是否出现史沫特莱的相关资料了。
看来,蔡元培、林语堂不属于史沫特莱所声称的小圈子是明显可见的,这从他们最初对胡适质疑的错愕与承认同盟存在问题就可以推测,而杨杏佛呢?有人倾向于他也属于是秘密小组。笔者却略有质疑。费正清回忆录里明确记载着史沫特莱对他的观感,〔14〕这个被史沫特莱鄙夷地以“豪猪”相待的杨杏佛恐怕也和蔡元培、林语堂乃至胡适一样,都属于被“谦恭”地加以利用的一类人,否则,就不会有杨杏佛自叙被“所谓极左者所不满”的状态了,可以确认史沫特莱正是杨笔下“极左者”之代表,他14日给胡适的信里还安慰胡适,说发表的控诉书决不是由“我等携带或捏造”。这都是他事先没被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邀请参与商议斗争细节的自然流露。因此,说杨杏佛也是秘密小组成员有明显说不通的地方。
四、政治观念之分歧是民权同盟风波的主因
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一场漩涡的胡适,又是如何认识并最终激化这次风波的呢?其实,早在接到林语堂2月9日的信后,胡适就大致明白了原委,但他依然回复说:“我绝对信任她的人格,她不会捏造此种文件,但此间有人专造此种材料,最易受欺,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是也。”这是胡适2月13日写给林语堂的信(不知何故被北大版《胡适书信集》的编辑者系在了张元济的名下)。〔15〕在北平的费正清夫妇当面听到的胡适意见是:“此信是艾格尼丝在这儿的几个共产党朋友撰写的,作为一种手段以激起反抗国民党的情绪,然后交给她,相信以她出名的狂暴,她一听到任何社会不公正就会把它公开出去。”〔16〕看来,作为主张发表文章必须署真名以示负责任态度的胡适并不知道,发表匿名文章,本是史沫特莱在中国参与创办《中国论坛》时的编辑习惯,这个原本旨在保护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作者不受当局迫害而采取的办法,被史沫特莱这回用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当局的斗争中;而胡适反感的利用他人名义伪造发件地址以达到政治目的方式,在史沫特莱那里也不是问题,她还是个参与政治运动的新手时就干过这类事情。〔17〕
即便并不知晓史沫特莱丰富的斗争经验及现今的斗争宏图,作为有明确政治信念的学者,胡适不仅无法接受林、蔡的解释,杨杏佛作为当事人公然说谎的行为更让他愤怒。在他2月11日质疑杨杏佛的信未得回复后,胡适行动了:2月19日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这是胡适对中文读者全面阐述自己改善政治犯待遇的意见;2月21日的《字林西报》上胡适向英文读者讲述他们视察北平监狱的实况,北平分会1月30日成立,当晚7点决定视察,11点与杨杏佛等面见张学良获准,次日上午10点即前往。由于时间仓促,狱方应该来不及多做准备——在用事实说明杨杏佛说谎后,他又重申了自己的建议。
如果说胡适起初给《燕京新闻》的信只是给民权同盟捅了娄子,让她们利用控诉书在国内外报刊掀起对当局抗议高潮的计划因胡适的指伪陷入尴尬之时,宋庆龄尚且能容忍,她与史沫特莱一起还尽力给外界及胡适本人一个交代,以期换得胡适得到“颜面”后的罢手。不料,面对着史沫特莱动过手脚的杨杏佛声明,胡适对这个专为他铺就的台阶并不领情,他的英文谈话充分表明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对不合理组织规则的明确抗拒。因此,革命家宋庆龄果断改变了对其斗争方式。2月22日,就在看到胡适英文谈话的第二天,以宋庆龄和蔡元培为落款的上海民权同盟总会给胡适发电报,要求他确认与该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的谈话是否属实,胡适没有回复。对他来说,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意见,他早在半个多月前的中文报刊上就谈过了,现在只是考虑到杨杏佛说谎的声明是以英文发表在上海报纸上的缘故,他才在上海的英文报上重申己见的。当年的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也应是看到《字林西报》时,才全面得知了胡适对于政治犯的意见,否则就无法解释她们何以在2月中旬没有任何动静。有参照价值的是,3月1日,鲁迅在信中好奇地询问台静农:“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18〕鲁迅疑问之时,已是胡适被开除前夜,正是上海民权保障同盟的多数人并不阅读北平中文报纸的侧面印证,当然,也说明不积极参与事务的民权同盟执委会委员对于事态发展的好奇与隔膜。
自然,2月21日的《字林西报》,也让杨杏佛意识到,有必要对胡适做个解释——前一节里笔者已详述过了。只是,他虽解释清楚了,自己并非有意说谎。但此信最让胡适失望的还不止于此,而是杨杏佛轻描淡写地说,他的意见常被记者记录错,因此不必太计较。看来,直到此时,他都没意识到胡适计较的与监狱方提前“几小时”联系改为“前几天”联系所体现的对于事件定性的根本性差异,此前以咱们不是匿名文件携带者安慰胡适的他对变相承认我等就是匿名文件携带者的转变也不在意了;杨杏佛的马虎还在于,接到胡适对他变相说谎的质疑后用置之不理的方式来敷衍,且不曾将胡适的新质疑与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商讨,从而刺激胡适选择在英文报纸公开驳斥他,导致史沫特莱等必须再次公开应对胡适的挑战,最终酿成胡适被公开开除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有意思的是,杨杏佛倒是意识到了胡老师与同盟政见有异,可惜他却浅尝辄止地将其理解为标新立异,他提醒对方这会让同盟有瓦解的可能,〔19〕而丝毫不曾意识到此时的他们已不复同道的现实。
不过,以宋庆龄为领袖的上海民权保障同盟却没杨杏佛这么马虎,也没再把胡适当同人的打算了。在第一次致电未得胡适回应6天后,同盟再次致电胡适,认为他攻击了该会“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基本章程,若不公开改正的话,就要求胡适出会。胡适依然只字不回,这样的强硬态度,无疑惹怒了因他而意外遭受困扰的上海民权保障同盟。3月1日出版的《中国论坛》严厉谴责胡适,称他“除了指明有人试图冒用他的名义公布河北第一监狱在押犯的一封信件”,没有任何别的证据支持其观点。文章斥责胡适“毫无根据地诽谤同盟”,主张立即开除他。〔20〕3月3日,同盟临时执委会开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开除胡适并通报媒体。史沫特莱正是会议上力主开除胡适者,这个信息是周建人给周作人的信中透露的,他很委婉地说“盖执行委员中有几位美人比较的略激烈也”。〔21〕加入上海民权保障同盟的外国人总共就3名,除了那位查不出太多信息的乔治·M·巴妥(Gorege M Battey)外,另两名都是美国人,史沫特莱外,就是伊罗生。史沫特莱作为此事的推手,激烈是可以理解的,伊罗生作为《中国论坛》的编辑,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者与积极参与者,积极支持也是自然。〔22〕
此次风波,从表面上看,以宋庆龄为领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赢了,在胡适默认自由出会的情形下,还开会决议开除并广而告之。宋庆龄更在随后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两次公开点胡适的名,把他树立为反对同盟“革命性”斗争的反面典型。她斥责胡适的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23〕。自孙中山逝世后,经过漫长的蛰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第一次出面组织的党派组织,为避免刺激当局,她曾再三宣称它不是政党,可从对胡适的处理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然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纪律严明的党派组织。直到写文章谴责胡适时,作为政治家的宋庆龄都没意识到,政治观念的不同才是胡适与她分开的主因。
自青年时代起,渐进的社会改良就是胡适改造中国社会的主要态度,“推倒这个鸟政府”是他思想中罕见的激烈表态。就他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而论,从最早的批评孙中山之“知难行易”说,到蒋介石主政时开展的“人权与约法”讨论,胡适的出发点都是唤醒民众个人的独立意识与人权意识,批评当局的违反人权与法律的行径,胡适的政论,都是直陈其错误以促使其进步,而无推翻政党及政权的最终目标。“九一八”后,外患日重一日的现实,更促使胡适有意改变以往的批评路线,转为积极建言建策以抵御外侮。在他看来,张学良主政北平时,政治措施已有改进,他愿以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身份提出合理化建议,促使政局更文明;而革命家宋庆龄此时还持与蒋介石主导的民国政府做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原则上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解决政治犯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应该说,同盟在成立当日出于自存目的发布的头条宣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与胡适之间的确存在反对国民党专政滥权的共识,只是,随着工作的开展,以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主的核心小组与当局的斗争情怀很快占了上风,“即刻的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新口号,就是明证。胡适却认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其实是和当局要革命权,姑且不说历史上没有政权会自动给反对派革命权,就现实而言,外患日重的中国也经不起革命的大风暴了。
五、共产国际的影响及胡适与杨杏佛对民权同盟的不同认识
没有资料直接表明,史沫特莱和宋庆龄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才有此等作为,但当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给上级的汇报中有如下说法:“过去的报告中我向您通报过成立‘民权同盟’的情况,在我们的影响下,该同盟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并在报刊上有力地揭露了敌人的恐怖活动和刑讯逼供等行为。这些做法逼得曾是该组织成员的一些反动派出来反对,所以同盟开除了北平的教授胡适。”〔24〕这就很坦白地承认了第三国际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中所起的作用,也承认了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的行动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一定程度上说,民权保障同盟是共产国际介入中国事务的一种新方式,那就是以共产国际的秘密成员(宋庆龄、史沫特莱、伊罗生)和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为核心,吸引蔡元培、杨杏佛等与孙中山有过一定共事经验的人,以及近年批评当局的社会知名人士及媒体从业者(胡适、鲁迅、邹韬奋可为代表),并试图运用核心成员掌控全局。周建人也加入了同盟,限于资历,只能做旁观者与随大流者,但他却能感受到史沫特莱因其共产国际成员的身份而在同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旁证。〔25〕既然共产国际支持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建及运作,作为其分部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在当年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黄慕兰的回忆录里就记录了地下党派朱伯琛去担任同盟秘书的事情。〔26〕
胡适当年可能不知道这些背景,他只是对自己不自觉中卷入党派纷争而愤懑。3月4日,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的消息后,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27〕接着就记载了日本人已进入承德,守军将领汤玉麟不知下落的时事。而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同仁还聚在胡家,试图和上海总会的人就涉及胡适开除相关的同盟奋斗目标等内容进行商讨,胡适说:“我自然不愿意和上海那帮人辩争,陈博生、成舍我、任叔永诸君要写信去质问总会,我也无法阻止他们。”〔28〕言下之意是,大敌当前,不必再做徒劳无益之事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上至国家大事小到身边朋友的无能为力。事实上,总会也果断拒绝了北平同仁的商讨。此后,北平分会再无任何呼应上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的行动。与之相应地,是该组织成立时利用各党派人士作保护色与当局作斗争意图的流产,在其他大城市组建分会的蓝图亦再无下文。
上海总会里与胡适密切交往的三个人对胡适的被开除反应如下:杨杏佛在1933年3月7日的《大美晚报》上声明,同盟已公布的文件,确实揭露了监狱黑幕,胡适认定的基本如实反映北平陆军反省院的来信又被他用来说明监狱黑暗;他重申同盟开除胡适的原因在于对方认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为根本荒谬。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杨杏佛的转变值得关注:初知不真实的控诉书被总会不经视察者核实就发表时,他在惊讶之余安慰胡适,说自己在同盟的处境也很艰难,并对胡适表示要改组组织,随后的他非但没有实践诺言,反而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史沫特莱等人的做法。本应严格把关的政治声明,他放手让史沫特莱去删改,被胡适严重质疑并公开批驳后,还对改变他本意的修改不以为意。如果说这些还勉强算得上是马虎的话,那么,胡适被开除后,杨杏佛的再度声明则表示,他自愿为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目标说话。而这个过程,其实是早年追随过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杨杏佛与独立知识分子胡适作为老朋友由不涉及党派利益时广义上的政治同盟,到事关党派利益时各自廓清面目的过程。胡适被开除17天后,蔡元培写信来:“知先生对民权保障同盟‘不愿多唱戏给世人笑’,且亦‘不愿把此种小事放在心上’,君子见其远者大者,甚佩甚感。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29〕也许蔡元培的信已基本道出了林语堂的心境,此后好长一段时期,他与胡适没有书信往来。
胡适对杨杏佛观感又如何呢?他在6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为了民权保障同盟事,我更看不起他,因为他太爱说谎,太不择手段。”〔30〕被胡适指责为不择手段的杨杏佛,屡屡出头露面坚持陪伴宋庆龄与当局的斗争,终于招致自己在6月18日被当局暗杀,成为胡适所预言的“被虎咬”者,他的惨死让蔡元培这位同盟会老会员对当局不抱任何幻想,在杨杏佛公祭仪式上的“元培虽老,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表态,充分表露出作为前辈的蔡元培对致杨杏佛死于非命的黑暗世道的愤慨;同日,蔡元培还声言辞去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的职务,他对同盟前途不得而知的黯然表态与同时段宋庆龄的激烈抗议形成鲜明对比。〔31〕初知噩耗的胡适,对杨的被害进行过一番猜测后,分析说,“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但不料他死得如此早而惨,他近两年来稍有进步,然终不能够免祸?”前后相隔两天的日记里,胡适对杨的做事风格都做了毫不留情的剖析,对其不幸只以深感“人世变幻险恶”而了事。〔32〕这样的认识对全面了解杨杏佛有一定帮助,但也暴露出没真正介入到现实斗争中的胡适,对黑暗政治的隔膜,而鲁迅和林语堂分别用果断出席杨杏佛的丧礼与不到场暗示了各自对民权保障同盟事业的支持与逃离。
六、史沫特莱的后续革命经历及其事后对参与同盟事务的三位中国重要作家之评价
随着杨杏佛的被暗杀,上海民权保障同盟也就被迫渐次停止活动。整个组织只维系了半年,该会所展开的营救牛兰夫妇及其他著名共产党人的被捕事件也没取得实质性进展,除了廖仲恺是何香凝之子,陈赓是蒋介石救命恩人的原因被直接释放外,蒋介石面对以儿子蒋经国被苏联释放为条件的释放牛兰夫妇的条件都毫不动心,依然将其关押在监,直到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失控他们才趁乱逃离。胡适所抨击的救犯人主要靠人情的现状依然存在,那位在北平陆军反省院写控诉信的刘尊祺,并没有如史沫特莱所吓唬胡适的那样,遭更多的罪,而是托协助胡适等人去该监视察的王卓然的关系不久就被释放。这位引发民权保障同盟风波的始作俑者,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从来没有说清过当年自己写的信,是怎样到达收信者手里的,即便收信人就是他再三确认的伊罗生。而美国传记作家露丝·普拉斯披露说,史沫特莱的政治导师明曾伯格才是拿到该信第一个版本之人,〔33〕明曾伯格是共产国际在德国成立的国际反帝大同盟的实际掌舵人,为了营救牛兰当时也在中国。这样的信息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子打一开始就罩在这个事件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组织也以损失了积极出面与当局斗争的猛将杨杏佛的性命为代价而无形中宣告了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史沫特莱极端的革命斗争精神鼓励和支持了宋庆龄,同盟成立前她因营救牛兰夫妇而与宋庆龄建立的友谊得到了巩固与加强,虽说她作为共产国际特殊成员的事情除了宋庆龄等共产国际成员以及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事务的人知道外,外界对之无论当时还是事后的很多年以后都一无所知,以致于她的首部传记作者麦金农夫妇对此都断然否认。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留意到,上文叙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结尾的故事时没了史沫特莱的影子。陈锦骍在《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文中也早就注意到了她没追随宋庆龄对胡适进行公开抨击的事实。为什么呢?原来,在推动胡适被开除后,日本人在中国的进一步渗透使得为史沫特莱收集情报的人员都离散了,民权同盟的激进主张事实上也无法从当局者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因胡适的意外不听安排又在舆论界颇显尴尬,史沫特莱也就回到了她的写作事业中去。早在1932年她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委托,要写一部中国红军反围剿的书。为此,中国共产党秘密安排一些来自中央苏区的红军指战员给她讲述红军的故事。夏天时,她住在牯岭与附近的红军指战员们交谈,继续收集资料。只是牛兰的绝食让她又迅速返沪投入斗争,〔34〕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实是牛兰被判刑后,由营救牛兰而扩展至所有政治犯的政治斗争之延续。在现实斗争一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写作一部中国红军史的宏愿又占了上风,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的支持。他在给皮亚特尼茨基(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信中希望对方帮助史沫特莱在苏联做两件事情:“(1)与苏联文学界建立联系;(2)让她能在高加索休息几个月,同时她想在那里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埃韦特让苏联的共产国际干部为史沫特莱的苏联行做如此周到的安排,当然不是为了培养一颗文学新星,在提出此请求前他的一段话很值得全文引用,其内容如下:“请您与史沫特莱谈谈她在中国今后的工作。迄今为止,不仅我们,而且我们的邻居都没有使用她。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样解决问题: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得到一些文学方面的长期任务,这可以保证她在这里呆下去,并像从前一样,可以利用她为中国做一般的工作。如果您认为合适,那您肯定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帮助。”〔35〕最终,5月17日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并在苏联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的写作。因此,杨杏佛被暗杀作为民权同盟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发生时,史沫特莱不在现场。
史沫特莱与中国文坛的三位重要作家的关系,经过这场由她本人推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也发生了变化:胡适与她不独不可能亲昵相处了,而是政见严重分歧到无法做朋友了,以致于麦金农夫妇的传记说,胡适和德国使馆人员交流,希望对史沫特莱《法兰克福报》的记者身份予以吊销,但他们却将事件发生的时间认定为1932年淞沪会战前。〔36〕虽然此说有不通之处,但却充分表明研究者心目中两位当事人关系之恶化;1934年秋,在苏联和美国呆了一年多的史沫特莱再回中国后,听说了林语堂不出席杨杏佛丧仪的事后,果断将其精准定位为“善变的批判性自由主义智识分子”,后来这两位还在1940年代纽约举办的中国问题辩论会上,各自表述了对国共两党的信任并唇枪舌战了一番;自始至终参加同盟各类公开活动的鲁迅,无疑是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在鲁迅的有生之年,两位女革命家都与他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36年鲁迅牵头出版的《克勒惠支版画选》中,史沫特莱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她不仅帮助鲁迅从版画家那里获得版画,还动用了部分共产国际创办英文宣传刊物的资金资助其出版。《克勒惠支版画选》不仅是史沫特莱与鲁迅友谊的象征,也是连接德国与中国的左翼文艺活动的桥梁,更是史沫特莱积极参与世界革命的见证。但是,由于她私自把资金用于非组织规定项目,致使自己被共产国际从特别成员队伍中除名,宋庆龄与她的友谊也因此而终止。这样的结局,当年的鲁迅并不知情,对于史沫特莱这样有独立精神的政治活动家来说,被共产国际排除在外她也许并不特别在意,而失去与宋庆龄的友谊却成为她难言的伤痛之一。限于篇幅,容后专文详论。
离开中国后的史沫特莱,把她在中国的岁月与观察精炼成《中国战歌》一书,在1940年代初的史沫特莱笔下,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初衷不过是获得言论出版自由,对政治犯的公开审讯及停止刑讯逼供,秘密屠杀及改善监狱条件——只字不提民权同盟风波过程中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影响而经宋庆龄坚定表述的“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斗争诉求!在《民权》一文的开头,她还提到,胡适在《新月》上的文章“为政府的法律应该尊重人权的主张提供了清醒的理性的论证”。〔37〕简述了民权同盟组织的主要活动后,史沫特莱直言该运动的失败——丝毫没有中国大陆地区研究民权同盟的多数文章出于政治正确而带有的习惯性夸饰。如果说《中国战歌》在史沫特莱著作中以客观见长的话,那么,《民权》一文庶几可以作为代表。就在这篇从历史大脉络上看相对客观的文章中,史沫特莱对自己从创建同盟中的秘密小组到促成组建民盟北平分会,从修改杨杏佛声明到最终开除胡适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这样的处理,耐人寻味。因为写作《中国战歌》的时代,还是美国支持中国抗战之际,并不存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代对史沫特莱这样的左翼人士的迫害问题。
同样的克制,还体现在史沫特莱对林语堂的记录中。虽然她明确指责林语堂不敢公开投身革命斗争,但她对林的定位却颇让有的中国大陆读者难以接受:“他让我想起了薄伽丘,那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不直接攻击教皇,只嘲讽个别僧侣淫荡的作家。在学者的等级序列中,林语堂博士大概居于胡适博士和革命的鲁迅之间。”〔38〕史沫特莱把林语堂比作薄伽丘无疑拔高了前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把其学术成就看得高于鲁迅,更是没有学术训练者的胡乱猜测,可这评价也反映出史沫特莱力求客观的追求。林语堂的晚年也提到过史沫特莱,他在《八十自叙》中就简述了民权保障同盟的经过,只是语气平淡,几无褒贬。〔39〕看来,年纪更大些时候的林语堂,经历更多沧桑后也没了在美国辩论时的激情。
《中国战歌》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还要数以《鲁迅》为篇名的一章。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左联”为鲁迅五十岁诞辰举办的纪念会上。那天,鲁迅的言谈举止“无不散发着难以言表的和谐和十分完美的人格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傻蛋那样笨拙、不优雅”〔40〕。应该说,鲁迅在其诞辰纪念会上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坦诚剖析及他对文艺青年的劝告都让史沫特莱欣赏,后一部分内容尤其是她与其他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交往中难得听到的内容。当然,她更看重鲁迅对黑暗现状的深刻批判,这主要通过鲁迅坚决拒绝包括史沫特莱在内的人们帮助他去苏联养病和“左联五烈士”事件后鲁迅的沉痛哀悼来体现。在相对舒缓的叙述中,鲁迅敢于秉笔直书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都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史沫特莱认定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而非中国的高尔基的评价,在后世看来,尤为可贵。可以说,经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后,史沫特莱与以胡适和林语堂为代表的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彻底分道扬镳了,她对鲁迅的亲近,除了对方的人格魅力外,更多基于反抗黑暗现状的共同事业上,当年的他们都认定苏联是人类解放的先驱,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希望,因此,鲁迅就成为史沫特莱在中国期间唯一持续保持友谊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他们的友谊是20世纪30年代中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向左转途中的佳话之一。
注释:
〔1〕〔14〕〔16〕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79-80、82、80页。
〔2〕许为民:《杨杏佛年谱》,《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1991年)第2期。
〔3〕在回忆宋庆龄的文章发表两年后,刘尊祺又写了纪念杨杏佛的文章《一次难忘的谈话》,登载在1983年9月10日的《文汇报》上,该文也把杨杏佛与自己谈话的时间确定为1933年的3月。而早在这两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之前,刘尊祺在私下也持有如此看法。还在宋庆龄逝世前一年,当他见到重返中国的昔日《中国论坛》编辑伊罗生时,就明确告诉对方,当年自己是因了后者编辑的刊物登载了他发自监狱的信件而引起杨杏佛的视察监狱并亲自与他谈话的。Harold R.Isaacs, Re-encounters in China,M.E. Sharpe Inc. Armonk ,New York /London ,p.100.
〔4〕〔31〕陈漱渝、陶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5-106、123页。
〔5〕姚 鹏、范桥编:《胡适散文》(第二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51-352页。
〔6〕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76-178页。
〔7〕史沫特莱教导费正清,将来参加民权同盟北平分会时也成立一个秘密小组,若有议案,要事前达成共识以便在全体会员大会上通过,贯彻这条路线时必须谦恭,在外面丝毫不表露出已达成共识,并声称她在上海就是这么做的。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76页。
〔8〕〔33〕〔34〕Ruth Price, The Live of Agnes Smdle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32,232,225-228.
〔9〕〔10〕〔11〕〔12〕〔13〕〔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5、186、191、187、188、191-192页。
〔15〕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84-585页。
〔17〕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52页。
〔18〕《鲁迅全集》(1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
〔20〕刘小莉:《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4-65页。
〔21〕朱正:《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
〔22〕陈锦骍:《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兼析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3〕宋庆龄:《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2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45、431页。
〔25〕周建人:《周建人谈民盟》,收入陈漱渝、陶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26〕《黄慕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163-164页。
〔27〕〔28〕〔29〕〔30〕〔32〕《胡适日记全编》(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202、202、223、226页。
〔36〕Janice & Stephen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merican Radical,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1988,p.156.
〔37〕〔40〕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Foreign Languages Press,Beijing,2003,pp.96,67.
〔38〕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Foreign Languages Press,Beijing ,2003,p.96.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史沫特莱文集》(1)即为《中国战歌》的中文版,其中没有这句话。
〔39〕林语堂:《八十自叙》, 台北:大汉出版社,1977年,第108页。
——兼论《民权素》创刊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