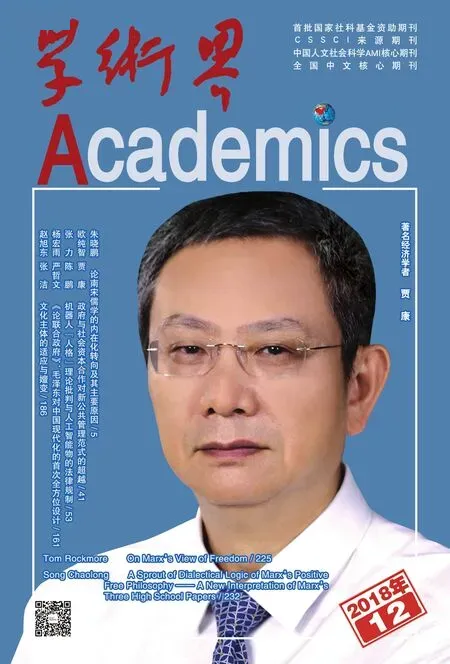一个宗教驯化人类的假说
○ 盛 洪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达尔文说:“人的各个不同的种族就和驯化了的各种家畜很相象。”〔1〕近些年关于人类驯化了自己的说法又引起了关注。一些人类学家发现,人类变得较少攻击性,甚至体现在了男性的脸部越来越像女性的。〔2〕漫长的史前演化过程和方式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在文明史以后的文献中,经常能看到蛛丝马迹。如基督教里有牧师,取自牧羊人之意。在基督教中,就是把一般民众看作是羊群,需要有人来牧。《新约》记载,耶稣曾说,“我是好牧人。”(10:14)无独有偶,在中国也有带“牧”字的职位,并且起源很古老。《尚书》载舜帝说,“咨,十有二牧!”即十二州牧。州牧到汉代还是一个官职。《说文解字注》将牧“引伸为牧民之牧”。把民众比作羊群,也许会引起现代人文主义者的愤怒。然而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人类是否有着与其它动物一样的需要驯化的野性?
一
应该说有。首先是凶残。人类与黑猩猩同属人科。黑猩猩生性残忍,经常会在相邻部落的黑猩猩落单时发起攻击,将它杀死。在黑猩猩部落中,成年雄性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一半,这说明有约一半的雄性黑猩猩在与周边部落黑猩猩的打斗中丧生。〔3〕黑猩猩的残酷性,经常见于一些文献中。在某些现代原始民族的习俗中,也有杀人习俗。杀人并非是报仇或者为了经济利益,而仅仅是证明一名男子的勇敢。一个男人积累的头颅越多,越说明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人类与黑猩猩是近亲,700万年前才与黑猩猩在演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与黑猩猩有98.4%的共同基因,共享着好斗和攻击的基因。
在各民族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更能看到人类生来残忍。如希腊神话记载,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与其母合谋,阉割了他的父亲并推翻了他的统治;但克罗诺斯也害怕自己的孩子推翻他,所以他的孩子一出生,就被他吃掉,只有宙斯除外。这不仅残酷,还是在亲子之间的残杀。罗马城的传说是,国王努米托被弟弟阿穆略篡夺了王位,并把他女儿的两个孩子投进水中,但被一只母狼救出收养。兄弟俩长大后将外祖叔阿穆略杀死,使外祖父努米托重登王位。后来兄弟俩建立了罗马城,只因命名新城的意见不和,又互相残杀,最后罗慕洛杀死了勒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城。在《希伯来圣经》中也记载,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只因为忌妒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这三段记录文字,不仅是记录了三件普通的杀人案件,更是将作为一个民族始祖的行为记录在案,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民族生长的根上埋下了残酷和嗜杀的文化基因。
在中国上古时期,杀人也是经常之事。关于我国上古时期的暴力故事,文献中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祭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的残忍程度。据考古专家,我国自仰韶文化时代到殷商时期,盛行人祭制度,即将人用作牺牲,献祭给上天或祖先。“殷墟地区发现牲人遗骨就有4000多具”。〔4〕有人推测,商人一直有杀俘献祭的传统,甚至在俘虏不够的情况下,也通过当时的周人捕捉羌人作为祭祀之用。〔5〕商人的残暴本性可以从商的最后一个王身上看出。商纣王杀其叔父比干,也是一个亲人相杀的案例。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杀父弑君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人类的残暴本性。
人类的另一个野性就是纵欲,这似乎与人类的另一个近亲——倭黑猩猩有关。如在希腊神话中有不少记载。宙斯作为众神之王,却是一个非常放纵的个体,他的妻子们多是他的直系亲属,如姐妹、姑姨甚至是侄女或孙女,所以是近交或乱伦;他经常以引诱和强暴的手段占有妇女,如对赫拉、伊娥和欧罗巴所采取的手段。说到强奸,在那样古远的时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冥王哈迪斯将珀尔塞福涅抢走强奸;这使我们想起罗马历史中的强掳萨宾妇女事件,应该被理解为大规模的掳夺和强奸。后世有不少这一题材的作品,我们在佛罗伦萨看到过“强掳萨宾妇女”的雕像,其结构与冥王掳珀尔塞福涅非常相像。至于乱伦,古希腊从第一个神——地神盖亚就开始了。她与自己的儿子——天神乌拉诺斯交合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女儿,还生了六个巨人。另一个极端的乱伦例子则是俄底浦斯的杀父娶母。
应该注意的是,上述记录的事情都是非常古远的,希腊神话的一部分来源于西元前八世纪的《神谱》。对当时人的行为,不应以现在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不过这一传统还是传之久远。我们在被凝固于西元70年的庞贝城遗存中看到,这种纵欲的行为似乎丝毫未减。我们看到大量作为壁画或雕塑的男女交媾作品,也看到非常夸张的男性生殖器模型,甚至还有人兽交媾的绘画或雕塑。
在中国,大概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只是我们很难在上古文献中看到。这大概是因为后来文明时代的著作家们对以前的“污秽的”记载进行过清理。只有个别记载,只因是对“恶人”的谴责而保留了下来。如商纣王荒淫无道,“酒池肉林”。《史记·殷本纪》记载:“(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除了物质享受奢华,还有男女间的纵欲。
总体而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天生就有着暴力和纵欲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仅是违反道德律令,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败坏和衰落。如暴力会使人类走向灭亡;而纵欲会破坏正常的交配结构,乱伦和近交会导致后代的缺陷增多,多代后就会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逐渐衰弱下去,强奸则会损害家庭的基础,也会削弱后代的身心;而滥交则会将性病传染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也导致人类身体的衰弱。
二
问题是,其它动物,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不也是很暴力和纵欲吗?为什么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没有衰落的危险呢?其实,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又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那就是人类的智力远高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可以想象,当暴力和纵欲乘以智力时,会产生什么不同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后果呢?首先,如果黑猩猩的暴力乘以人类的智慧,就只能使暴力带来更为残酷和恶劣的后果,即杀死高出一个数量级的人。直到今天,尽管距轴心朝代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人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抵御住暴力本能和智慧的结合,核武器的杀人“效率”高出黑猩猩千万倍,人类仍有可能因自己的暴力基因乘以智力而埋葬自己。
至于纵欲,早有专家说过,人类是灵长类中最好色的物种。这也是因为人类的智力。由于人类运用智力而获得了更高的生产力,使得人类获得的营养远超出维持生存和生育后代所必需,多余的性欲代表着较多的生产剩余。一般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只是在特定的季节发情,并在雌性排卵时交媾,完成了生育任务后就少有交合。而人类更多的是为了享乐而不是为了生育而交合。这就带来纵欲。不仅如此,人类的智力还会将纵欲变成一种艺术或文化,如绘画或诗歌,反过来又会刺激纵欲的持久和发展。更有甚者,人类还把性当作一种商品或礼物买卖或赠送,创造出大规模性交易的场所;人类还将印刷技术与艺术能力结合,发展出色情刊物和色情影视产品。这都是灵长类近亲所不能做到的。
实际上,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有对暴力和纵欲的自我克制的本能,〔6〕使得它们不至于因这两个缺陷而走向毁灭。然而由于在近数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大脑有了显著的变化,智力能力迅速增长,就打破了人类能力和人类自我约束力的均衡,暴力和纵欲的缺点越来越不能被容忍,成为可能毁灭人类的致命缺陷。因而,人类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将其驯化。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看到,这种力量就是宗教。问题是,驯化人类是宗教的目的吗?或者说,宗教是否明确意识到,它的主要功能是驯化人类呢?首先要看宗教对人类的看法,即人类是否是一个健全的物种,无需驯化,还是一个有着根本性缺陷的物种,需要驯化呢?如果需要驯化,人类是否可驯化呢?在本文中,我们选择基督教和儒家传统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看,人类就是一个有缺陷的物种。这主要体现在原罪说上。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只有经过天主的恩典和救赎,才能免去原罪。也就是说,人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物种,只有经过宗教的驯化,才能克服他们的缺陷,比较健全地生存。“原罪”概念是由奥古斯丁首先提出的,他指出“人的邪恶是一种动物的本性”,〔7〕与我们今天认识到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共享残暴和纵欲基因几乎是一个意思。当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这就是“原罪”的隐喻。话音未落,该隐就杀了弟弟亚伯。杀人显然是原罪。
奥古斯丁还说,人未出娘胎就有的原罪,来源于父母交媾。这是一种不洁的行为。而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原罪是对纵欲的一种描述。对性行为的羞耻感并不是来自正当的性行为,而是过度的淫乱的性行为。只是在远古时期,人们很难一下子就分得那么清。奥古斯丁还是比较冷静和清醒,他在论证了原罪主要来自情欲以后,还是强调了婚姻的正当性和好处,实际上对原罪所指的性行为有了限定。
对于人类是否可驯化的问题,基督教的学者,奥古斯丁给出了明确且权威的回答。他指出,“与动物相比,人是如此地灵秀,人的邪恶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但人的本性并不因此就变成了动物的本性,所以上帝之谴责人,是因为人的缺点使人的本性受到玷污,而不是因为人的本性自身,这本性并不因自己的缺点就被毁灭了。”〔8〕简单地说,人总体上还是一个比其它动物更好的物种,只是有一部分与动物相同的缺陷,这不是创造人类的上帝的错,而是人类自己的错。基于这种判断,人类是可以救赎的。
在中国,似乎较少对人性缺陷的强调,却有“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只有荀子有几句人性恶的议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这里说人的本性就是贪婪、嫉妒、好色,最后归于残暴。这与犹太教—基督教提出的原罪相差不大。
鉴于此,就要纠正邪恶的人性。荀子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然而他似乎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人类可驯化吗?他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意思是说,人之所以想受教化、学礼义,恰恰是因为人性本恶,没有善,才要学善。但这没有回答黑猩猩为什么不学善。所以,回头再看孟子的性善论,也许更为细致。孟子尽管强调人性善,但这很类似于前述奥古斯丁所说的,原罪只是人被动物性玷污了,但人性并没有就完全变成了动物性,是更为侧重于发现人的“善端”,以说明人是可以被驯化的。孟子也承认,“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乎就是承认了人与黑猩猩的近亲关系,然而孟子侧重于“几希”的差异上,即人的四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仔细想想,黑猩猩一样儿也没有。这就是人可以驯化而黑猩猩不可驯化的原因。
那么,宗教是怎样驯化人类的呢?首先是要使人敬畏。怎样使人敬畏呢?利用人的失败。实际上,人的缺陷之所以称之为缺陷,就因为其一定会带来人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失败就是暴力争斗不断,这不仅包括族群间的战争,还包括族群内的互相残杀。还有一个失败就是性病流行,导致族群的体质衰弱,也会导致人类个体更早的死亡。总而言之,就是人类更多和更早的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他面对的是一个悲惨的人生,或者生于苦难,或者死亡。古希腊的悲剧文化就诞生于这种人生,产生悲剧的原因都与人的原罪——暴力和纵欲有关。如《俄底浦斯王》就经典地涉及了这两个方面,弑父是暴力的极端,娶母是纵欲的极端。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中指出,“《伊利亚特》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史诗,其中的角色由杀人与被杀的冲动所支配。”〔9〕悲剧就是对人的原罪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哀叹。
因此,宗教的产生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克服自身的缺陷——暴力与纵欲,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仰,既是一个征服人心的过程,也是一个驯化人类的过程。在犹太教—基督教中,信徒们把全知全能的神称作“我的主”(my lord),就是一种被驯化之物种对牧养他们的主人的称呼。这说明他们完全顺从于这种驯化与被驯化的关系之中。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既可以靠一个个人的皈依,更多的是由于信仰一个恰当的宗教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改进,减少了暴力和纵欲,从而使该人群有所发展,而与之竞争的其他人群由于没有信仰这一宗教而继续衰落下去。后者或者走向灭亡,或者改信这一宗教,以克服自身的缺陷。于是,在克服原罪方面有成效的宗教就会扩展开来。
三
以犹太教—基督教为例。在创世纪第一杀人案,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耶和华立刻给予了惩罚,他对该隐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后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6:6)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6:7)于是就带来了大洪水,“惟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逃过此劫。这是耶和华对人类最严重的一次惩罚,以大多数人的生命为惩罚对象,应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到后来,上帝就直接为人类立法,这就是摩西十戒。其中有“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是直接针对暴力和纵欲的。这两条戒律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极为新颖和激进的。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杀人和淫乱才是正常的。人类也不是马上就接受了这两条戒律,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的奖惩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旧约》中,以色列的某某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受到了惩罚。有些时候就直接是“耶和华就叫他死了”,严重的时候就让以色列的敌人强大起来,打败犹太人,并且奴役他们许多年,等等。这样的记载在《旧约》里出现过51次。
有时某某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会国泰民安,打仗就会胜利。这通常也伴随着以色列部族对耶和华信仰的建立。开始时,“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12:3)或者国王“只是心不专诚”,或者“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逐渐就“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15:12)“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15:14)最后才“除掉邱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
可贵的是,这些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进入到宗教经典。信众们都要阅读,《旧约》里奖善罚恶的记述会潜移默化地进入信众们的头脑,经过多个世代的延续和更替,信众们被日复一日地驯化,也就坚信“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是不可逾越的规则。根据人类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这种宗教驯化对人类的影响,经过相当长时间已经不是一个外在的教育了,而对人体基因产生了影响,甚至表现在他们的身体特征上。〔10〕在今天,“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不仅是大家公认的普通规则,甚至是大多数人的本能,即不需要告诉他们违犯后要受到什么惩罚。
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那里的居民信奉着希腊罗马的原始宗教。然而,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说,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正是因为希腊诸神们不能提供一个符合道德的社会秩序,即没有克服暴力和纵欲的有效功能,所以很自然被基督教替代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督徒被驯化得对性行为有着本能的羞耻感,他们认为除了生育目的的性交外,其它性交都是不洁净的、罪恶的。除了一些例外情形,基督徒也都被驯化成温和的人,他们认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与他人的冲突是值得骄傲的,而动用武力则不仅是罪恶的,而且是羞耻的。杀人多的男人不再会被人崇拜,而只会被认为是恶魔。在现实中,对比一下希腊罗马时期的人,现代的欧洲人几乎是脱胎换骨。这正是基督教驯化的结果。
四
在中国,这一过程在夏商周的历史阶段中展开,尤其到了周代,就有了显著的成果。如前所述,殷商时期有人祭传统,仅在殷墟地区就发现了4000多具人祭人殉尸骨。胡厚宣先生据甲骨文的资料估计,自盘庚迁殷至商纣亡国的273年间,至少有14197人被用作牺牲。〔11〕这不仅意味着把人的生命等同于其它动物,而且暗示着在非宗教领域,普遍存在着有目的的杀人,而人们习以为常。而这种情况到了周以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祭现象大大减少。周代八百多年间,现在发现的人殉人祭有9具,文字记载的仅两例。〔12〕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成熟。据胡适认为,儒家形成于殷商时期,本是一群专司礼仪之人。他们对民间形成的礼,即习俗,最为熟悉,也发现了礼作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有效性。他们经历了商周之变,也吸纳了周族的礼,综合为以周公—孔子为宗师的儒家传统。在殷商时期,礼在社会内部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礼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这是互动各方都接受的行为规范。显然杀人的行为不可能形成礼,因为这不是各方都接受的行为规范,如果非要形成均衡,就是杀人者得被杀。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不会有杀人之礼。纵欲的性行为也不可能形成礼,因为强奸、乱伦和乱交等会带来对家庭秩序的破坏,人们可能会处于类似俄底浦斯的无所适从的境地,这也是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周代社会的颠覆,因而礼本身也起到了抵制纵欲的作用。儒家强调礼,就是在抑制暴力和纵欲,就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敬互爱。
在另一方面,周族与殷商的历史轨迹不同。殷商在成为天下共主以后,是一个不可一世的霸主。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就更容易使用武力并获得胜利。这时人类基因中固有的暴力因素就会不受约束,更容易发泄出来,那些战俘就会被用来作为人牲以施行报复。而“小邦周”则没有这样的优势,也就没有形成人祭传统。至今考古工作几乎没有发现先周时期在泾渭流域有人祭人殉实例,在周原甲骨中也没有找到人祭的记载。〔13〕在周灭商的过程中,周是与周边的众多小邦结成联盟,在周建立以后,采取的分封制,以奖励那些在伐商时出过力的诸侯国,因而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间秩序,也没有较多的对外征伐,就没有形成以战俘为主的人牲制度。
周公对殷商的覆亡作了深入的思考,也对殷商的祭祀制度进行了省察。他继承了先周的不用人祭的祭祀制度,吸纳了殷商儒家的礼的精神,对国家祭祀制度进行了改革。终结了人祭陋习,将主祭的对象从商的先王改为天,而将周的先王们作为配祀,使祭祀摆脱了负面因素,而更多地发挥敬畏上天,敬奉祖先,团结族人,形成价值共识的正面作用。而礼的形式,尤其是仪式,对民众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即所谓“祭神如神在”。当人们身处礼仪之中,就会受到一种气氛的感染,就会产生与周围人群的精神共鸣,仿佛祭主,无论是天还是祖先现身,人们也会力图在这种氛围中洁净自己的精神,遵循公正的价值。中国的汉族一般每年有四次祭祖,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人们会形成一种准本能的内在文化精神,也会对人的基因产生影响。
当然,民间的礼早在儒家诞生之前就长久存在,但商周之际发展起来的儒家传统对礼产生了强化和扩展的作用。如前所述,儒家起源于民间,熟知民间的礼,这些礼本来就是从民众中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把它们记录和汇集起来,加工整理并反哺民间,显然是借用了孟子所说的四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把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对抗人性中的缺陷——暴力与纵欲。而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定居农业使家庭更为稳定,更容易形成成熟的家庭秩序和乡规民约,也就更容易接受以礼为基础的儒家教化。礼既然是从民间来的,也就不是外在的规则强加于民众,也就更为有效和易于实施。
在民间礼的基础上,儒家进行了思考和提炼,抽象出了道德价值,如义、仁、天、道等。基于当时中国人的特点,基于儒家的取向,儒家经典中较少有“不可杀人”的戒律,可能是因为无需这样表达,而是正面表达要爱其他人,爱其他生命,如“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爱人”。而“仁”,包含了“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含义,都是要约束和克制自己,目的是不要伤害别人或侵犯别人的利益,行为标准就是遵从礼。
尽管在国家层面,儒家传统并不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有时道家或佛家会占上风,但是在民间,由于儒家以民间的礼为价值源泉,又强调礼在民间的行为规范作用,儒家在民间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商到周数百年的驯化与熏陶,已使周朝人,从平民到贵族,形成了视暴力为凶残,视纵欲为羞耻的主流文化价值。例如,在前述春秋时仅有的两例人祭发生时,都遭到了当时国内外的谴责,宋司马子鱼评论宋襄公使郑文公杀鄫子时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鲁藏武仲评季平子杀莒俘以祭时说“鲁无义”〔14〕。说明这仅有的两起人祭案例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例外。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是对诱导人祭人殉的人俑的强烈谴责,当然人祭就更要不得。
在两性关系上,中国民间的礼与儒家传统造就了汉民族相对节制的两性关系,即使是正常的两性感情也多采取比较含蓄的表达,形成了世界上最稳定和成熟的家庭制度。两千多年来,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构成了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强奸、乱伦、乱交以至兽交行为,都会遭到普遍的谴责,纵欲的缺陷总体上得到了抑制。
据一些学者的估计,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暴力倾向大大降低。在两万多年前到6000多年前之间,人类的暴力死亡率约在10%~20%之间,而到了西元前的最后1000年的末期,这一比例显著降到了2%~5%。有些人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其它因素,在我看来,这恰是轴心时代以来高级宗教或类宗教传统发展并驯化了人类的结果。正是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0年这一段时间,出现了轴心时代,犹太教的经典《摩西五经》已基本完成,为基督教的诞生做好了准备;儒家经典,如《诗经》《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和《孟子》等都已完备,经过春秋战国的崛起,到了汉代已成文化主流。
五
以上就是以基督教和儒家为例,粗略地讨论了宗教驯化人类的形式与过程,我们也从中发现驯化人类的不同形式。这也恰恰构成了不同文明的特性。由于上古中国社会成长于规模很大的定居农业区域,人们之间交往的频率和稳定性较高,会较快形成礼的体系,并能成为有效的社会规则,所以儒家更倾向于激发人内心的善端,以此来克服人的缺陷,更多地采取讲道理的方式让人们接受道德价值。而上古时期的希腊和罗马,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的空间相对狭小,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得家庭关系不够稳定,习俗形成较慢和缺乏规则性的效果,因而在希腊和罗马本土上并没有发展出抑制人类缺陷的宗教传统,只有等到有着严格规则和有效手段的基督教这剂“猛药”的到来,用超越于人间习俗的宗教戒律,通过人内心的宗教感来产生作用。
本文关于宗教驯化人类的假说只是提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在这个轮廓下,还有很多问题: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暴力和纵欲倾向在一些人类个体身上明显复发;宗教在驯化人类的过程中也难免走过了头,压抑了人类的正常欲望,也就压制了与之相关的艺术与科学的创造性。这些都是应该承认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人会指出,宗教并没有真正压制住人类的暴力基因,只是改变了形式,从社会内的个体间的暴力转变为国家间、民族间甚至文化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当然,这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正是笔者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注释:
〔1〕〔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青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页。
〔2〕〔10〕Robert L.Cieri,Steven E.Churchill,Robert G.Franciscus,Jingzhi Tan,and Brian Hare,“Craniofacial Feminization,Social Tolerance,and the Origins of Behavioral Modernity”,Current Anthropology,Vol.55,No.4 (August 2014),pp.419-443.
〔3〕张岩:《人性与文明:基于经验的人类史观》,中评网,2016年12月23日。
〔4〕〔12〕〔13〕王元朝:《人祭习俗商盛周衰原因新探》,《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李硕:《周公传——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微信公众号“叙拉古之惑”,2017年7月3日。
〔6〕〔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赵芊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7〕〔8〕〔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42、343页。
〔9〕〔英〕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11〕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
〔14〕周兴:《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