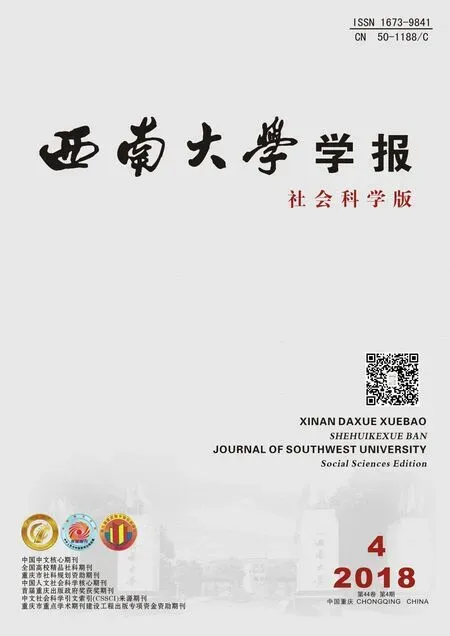“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王 桂 妹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以“破旧立新”的强悍姿态获得了历史突围的巨大动力,在这一弃旧向新的过程中,“旧”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惰性、一种阻力而存在,还有其能动性的一面,而由新旧论争所构成的思想张力正是“五四”的精神特质之一。如果以“大五四”的文化视野来理解“五四”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就需要从单一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和情绪中跳脱出来,理性看待“反对派”的作用和价值。回眸“五四”以降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史,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的文化纠结和论争始终不绝如缕,当年的新旧文化论争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看似胜负已分的新旧文化之争实际上并没有尘埃落定。说到底,文化的转型并非仅凭一次论争就能彻底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的守旧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失败者甚至被当做“不值一驳”的小丑,其价值需要重新估量。重新审视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并非要抹杀“五四”的精神光芒和历史作用,这也是基本的历史限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反对派”既有在历史现场被指认的一面,也有被历史建构、重塑的一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历史规约中发生了从“反对派”到“反动派”的性质转变,而后者往往才是反对派被固化的“当下”面相[1]。分析和清理“反对派/反动派”的历史再造过程,也是重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对派”价值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成了绕不过去的关口,尽管他们在论战中并未居于中心和前沿位置,相比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而言,他们只是参与了零星论战,对五四反对派施以旁敲侧击,但基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树立起来的“旗手”和“方向”地位,在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尤其是新中国的现代文学阐释史中,鲁迅被放大为主力与先锋。鲁迅有关“反对派”的言论,即便是只言片语也往往被重点引证,作为打击“反对派”最有力、最犀利的武器和最终定论。在当代编纂的现代文学史中,“反对派”被塑造得更加反动、更加面目可憎,而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成了打击“反动派”最有力的主将,这体现在诸多现代文学史对论争的描述中。相对于鲁迅而言,林纾成了最鲜明的反证,对林纾的价值重评,除了正面评判其文学的贡献得失及传统文人的精神人格特质以外[2],更应破解被后代历史不断形塑的“反动派”和“小丑”的面相。
一、周作人:出尔反尔与绝不宽容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期,五四新青年以“双簧信”方式将林纾引入战阵,打破了无人理睬的寂寞局面,展开了第一轮新旧论争。论争的最终结果是“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误”[3]而告终,林纾高悬免战牌,五四新青年初战告捷。尽管这种“请君入瓮”式的论战方式并不为新青年派全体所认同,但终究为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历史性出场打开了局面,五四新青年对林纾的不尊不敬、揶揄谩骂自然也就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性。直到1924年林纾逝世前后,新青年派才开始重新评价林纾。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林纾有过两次“平心而论”的评价,承认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的贡献:“但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彩。”“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4]林纾逝世后,胡适撰文评价其白话诗:“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5]1924年,郑振铎也对林纾的性情人品、白话诗、小说、传奇、古文创作进行了全面评价,尤其是肯定了林纾在小说翻译方面的卓越贡献,称赞林纾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可算是一个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易见到的”[6]。胡适和郑振铎的评价,对林纾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代表五四人对林纾作了较为全面公允的评判,当然,这并不代表全部五四新青年派的态度。
同样是在1924年到1925年间,《语丝》上的几位新青年同人因林纾的评价问题发生了一些龃龉,其中以周作人态度的转变最值得玩味。周作人先是对林纾进行了正面评价:“林琴南先生死了。五六年前,他卫道,卫古文,与《新青年》里的朋友大斗其法,后来他老先生生气极了,做了一篇有名的《荆生》,把‘金心异’的眼镜打破,于是这场战事告终,林先生的名誉也一时扫地了。林先生确是清室孝廉,那篇小说也不免做的有点卑劣,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他又从当下青年们趾高气扬而懒散的风气论及林纾的优长:“‘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但有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尽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译过几本世界的名著?中国现在连人力车夫都说英文,专门的英语家也是车载斗量,在社会上出尽风头,——但是英国文学的杰作呢?除了林先生的几本古文译本以外可有些什么!……回头一看我们趾高气扬而懒惰的青年,真正惭愧煞人。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吾师的时候。”[7]周作人的这番言论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双簧信”主谋之一刘半农随后致信周作人,对自己当年的唐突表示悔意:“你批评林琴南很对。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不过他若止于发卫道之牢骚而已,也就罢了;他要借重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8]二人尊林纾为“师”为“前辈”,五四新青年确实是读着林译小说成长的一代人,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所有中坚人物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沈雁冰等,他们都曾公开表示自己所受林译小说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林译小说和林纾古文哺育了五四一代新青年。
周作人、刘半农的信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在“写在半农启明的信底后面”,钱玄同直接表明态度说:“据我看来,凡遗老都是恶性的。罗振玉说,‘盗起湖北’;林纾说,‘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见《蠡叟丛谈》中之《妖梦》)这两句同样‘都是最卑劣的话’。”他对尊林纾为“师”和“前辈”尤其不满:“这话我不仅不同意,竟要反对了。反对之点有二。一,何以要认林纾为前辈?若说年纪大些的人叫做前辈,那么,年纪大的人多得很哪,都应该称为前辈吗?……二,何以后辈不可唐突前辈,而前辈可以教训后辈?……我以为前辈底话说得合理,自然应该听从他;要是不合理,便应该纠正他,反对他;他如果有荒谬无理的态度,一样应该斥责他,教训他,讥讽他,嘲笑他,乃至于痛骂他;决不可因他是前辈而对他退让。……一九一九年林纾发表的文章,其唐突我辈可谓至矣。我记得那时和他略开玩笑的只有一个和我辈关系较浅的程演生。我辈当时大家都持‘作揖主义’底态度。半农亦其一也。有谁‘过于唐突’他呢?至于他那种议论,若说唐突我辈,倒还罢了;若说教训我辈,哼!他也配!!!”[9]钱玄同依旧持五四新旧论争时的强悍态度,在他眼里,林纾是“恶性”的,不配做“前辈”。有意味的是,在受到钱玄同的一番批评之后,周作人的态度急转直下,紧随钱文发表了《再说林琴南》,不但收回了先前对林纾的正面评价,而且更进一步全盘否定:“林琴南的作品我总以为没有价值,无论他如何的风行一时,在现今尊重国粹的青年心目中有如何要紧的位置。……林琴南的确要比我们大几十岁,但年老不能勒索我们的尊敬,倘若别无可以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因为他是先辈而特别客气。”[10]林纾的翻译、卫道与年长在此都已毫无价值可言了。
一向以温和面目示人的周作人,出尔反尔的意气式评判十分值得深究。周作人与钱玄同皆为章门弟子,二人交谊颇深,周作人称钱玄同为“畏友”[11]。周作人对林纾态度的翻转与钱玄同的批评有直接关系,从更深层的历史扭结上看,钱玄同的批评提醒了周作人的门派意识。清末民初,以章太炎和林纾分别为代表的唐宋、魏晋文之争,不但夹杂着清末文风的流转兴替,更连带着时代嬗变所带来的北京大学人事的去留和起落:“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学主文科。”[12]129林纾入主北京大学文科,增强了“桐城派”既有的声势:“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第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盻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12]130民国的到来直接导致林纾文坛盟主地位的失落及桐城派的去势:“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12]130基于这样的历史前因,五四“新青年同人”与林纾的论战虽是“新旧”之争,但也夹杂着清末以来的文坛“旧怨”和门户之见。身为“章氏门徒”,周作人竟称林纾为“我们的师”,显然大为不妥,招致钱玄同的强烈不满也在情理之中。钱玄同的激烈情绪更点醒了周作人,他再评林琴南时看起来就更像表白书和悔过书:“林琴南死后大家对于他渐有恕词,我在语丝第三期上也做有一篇小文,说他介绍外国文学的功绩。不过他的功绩止此而已,再要说出什么好处来,我绝对不能赞成。”[10]周作人虽然于1926年因不满章太炎的复古倒退而发表了著名的《谢本师》,公开声称与太炎师脱离,但也坦承能有资格成为其老师的只有章太炎一人:“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13]钱理群认为,周作人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和章太炎真正脱离师生之谊,1932年章太炎再度北游,周作人执弟子礼甚恭,师生关系并未受到影响,章太炎审定的《同门录》中,周作人“大名赫然在焉”。周作人晚年著《知堂回忆录》谈及当年,“似乎有几分‘悔其少作’”,“最终仍是以章太炎为师的”[14]。这种师生门户观念,影响了周作人对林纾的态度。
还应承认,身为章门弟子的周作人,同时也是站在新文化和新青年的立场上去评判林纾的,受刘半农的启发而认定林纾想借助“荆生”、借助武力打击异己思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这也是当时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等对林纾的共同指责。时至1930年代,周作人对林纾才逐渐恢复理性评判,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肯定了桐城派的历史功绩,承认新文学革命运动源自严复、林纾等晚期桐城派中坚:“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15]44他也肯定了林纾翻译的功绩和自己所受的影响:“当时林译的小说由最早的《茶花女》到后来的《十字军英雄记》和《黑太子南征录》,我就没有不读过的。”[15]531935年前后,文坛上兴起纪念林琴南的风潮,周作人又写了《关于林琴南》一文,大段抄录十年前的《林琴南与罗振玉》,只字未提态度决绝的《再说林琴南》。针对《人间世》第14、16期发表的两篇一味赞扬林琴南的文章,周作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是林琴南的翻译与原文有出入的地方并不见得传达出原文的精神或比原文更精彩;二是林琴南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旧文化而只是拥护“三纲”而已。周作人反对持“全取”态度:“说他一切都是好的,卫道,卫古文,以至想凭借武力来剪除思想文艺上的异端。无论是在什么时代,这种办法总不见得可以称赞吧,特别是在知识阶级的绅士淑女看去。”[16]
“想凭借武力来剪除思想文艺上的异端”是周作人认定林纾最不可饶恕之处,这也是五四新旧论战中击败林纾的最后一根稻草。林纾的小说《荆生》一出现,新文化阵营便对“荆生是谁”发出了种种猜测,由最初认定“荆生”乃“林纾自况”转而认定所指乃北洋军阀徐树铮,于是,妄图以武力镇压新思想便成为林纾的一大罪名,也成为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但是,连新青年派也承认,这一推测最终并未成为现实,新旧论争终究以笔战告终。以虚构人物生发联想而给林纾定罪终究欠妥,这恐怕也是胡适、郑振铎等人给林纾盖棺论定时并未涉及这一点的原因,但这却是周作人始终牢牢抓住不放的关键性把柄。晚年周作人谈林纾时再提“武力镇压思想”,导致他对林纾更为决绝的批判态度。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青年时代”时,虽然已能从容谈及兄弟二人,尤其是鲁迅对林译小说的喜爱,但对林纾的批判也同时升级:“到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来用武力镇压,在《大公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徐姓),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17]75《知堂回忆录》谈及“林蔡斗争”,虽称自己不由得作了一次“文抄公”,但在抄录《公言报》言论及林、蔡往来辩驳的书信之前,还是对林纾做了态度鲜明的批判:“林琴南的小说并不只是谩骂,还包含着恶意的恐吓,想假借外来的力量,摧毁异己的思想,而且文人笔下辄含杀机,动不动便云宜正两观之诛,或曰寝皮食肉,这些小说也不是例外,前面说作者失德,实在是客气话,失之于过轻了。虽然这只是推测的话,但是不久渐见诸事实,即是报章上正式的发表干涉,成为林蔡斗争的公案,幸而军阀还比较文人高明,他们忙于自己的政治的争夺,不想就来干涉文化,所以幸得苟安无事,而这场风波终于成为一场笔墨官司而完结了。”[18]在晚年周作人眼中,林纾成了比军阀还不如的恶劣文人。总体上看,在对林纾的历史评价问题上,周作人显露出他“绝不宽容”的一面。
周作人所认定的林纾不可饶恕之处,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批判林纾并把他最终定性为“反动派”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这一固化为“常识”的问题,后来学者做了多方面的辨析工作,认为认定“荆生”为徐树铮并无真凭实据。张俊才指出“荆生”并非指徐树铮,乃是“理想化的卫道英雄的化身”[19]。陆建德认为新文化阵营故意把荆生附会为徐树铮,乃是一种运动之术[20]。陈思和认为徐树铮并没有充当“荆生将军”,也没有干涉新文化运动的企图,而从林纾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但我觉得林纾是否真向徐树铮建议干涉新文化,恐怕也是一个疑问。因为以两人的亲密关系,林纾若真有所谋,只需直接向徐建议,也用不着费力写了小说来暗示。据当年在徐树铮办的正志中学的学生回忆,林纾在正志中学上课讲授《史论》,每周二小时,那时他虽然与新文化运动公开论战,打笔墨官司,但在课堂上从未批评过新文化运动和陈胡诸人,也可见君子风度一斑。”[21]这也是郑振铎当年评价林纾是一位从不依赖富贵权势的“清介之学者”。但中国新文学史几乎未加分辨地采用了“荆生即徐树铮”这一说法,因此有学者慨叹:“林纾为《荆生》蒙冤已近90年了,各种新文学史的作者是否愿意还他清白,还是未知之数。”[20]
二、鲁迅顺手一击的委婉与深刻
钱理群在比较周氏兄弟的论战和批评方式时认为“和周作人温和敦厚的批评比较起来,鲁迅的笔确实是尖刻的”,但鲁迅“比周作人的温和判断,要深刻得多”,“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而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无招架、还手的余地”,当然,有时也“确有过苛之病”,比如在论争中将施蛰存斥为“洋场恶少”、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等[22]。但实际上,鲁迅绝不仅仅只是“疾恶如仇”这一副尖锐面相,正如周作人所说:“鲁迅去世已满二十年了,一直受到人民的景仰,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可计算,绘画雕像就照相所见,也已不少。这些固然是极好的纪念,但是据个人的感想来说,还有一个角落,似乎表现得不够充分,这便不能显出鲁迅的全部面貌来。这好比是个盾,它有着两面,虽然很有点不同,可是互相为用,不可偏废的。”[23]在对待“林纾”的问题上,鲁迅就显露出了他的丰富性,不但与他平素的犀利尖刻不同,也与周作人对林纾指名道姓、态度坚决、牢抓一个虚构罪状不放的态度形成反差,鲁迅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显露出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的一面。
对于以“卫道”自认的林纾而言,五四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一系列抨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倡言家庭革命的主张,最让他痛心疾首,因此,林纾此时发表的诗、文、小说尤其强化了对“孝”的卫护和对“非孝”的抨击。林纾在《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的信中一再指责“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乃是“禽兽之言”“禽兽行”,又借白话新乐府《母送儿》等讽劝世人感念父母生养之恩,与其去提倡父母无恩的新学堂还不如退学在家读《孝经》。林译小说也往往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用外国小说阐明“孝”乃普天下的道理,无论中西。林纾更表达了身为圣人之徒要誓死捍卫伦常的决心:“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之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24]
在五四新青年与林纾的酣战中,鲁迅对林纾直接进行批判的地方并不多,先是在《新青年》6卷2号“什么话?”专栏中辑录了林纾《孝友镜·译余小识》中的一段话:“此书为西人辩诬也。中人之习西者恒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管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亦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25]胡适在该专栏开设之初解释说:“我们每天看报,觉得有许多材料或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此项材料很有转载的价值,故特辟此栏,每期约以一页为限。”[26]鲁迅把林纾这段话放在栏目中,虽未评判却也有了“示众”的效果。鲁迅集中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针对“孝道”问题进行批驳,抓住了林纾的“痛处”,因而较其他新青年们的揶揄、嘲讽甚至谩骂更见深度和力度。鲁迅以生物界的进化论作为生命起点的科学依据,提倡“幼者本位”和以“爱”为基础的现代家庭亲子关系,批驳中国传统以“人伦”为起点的“长者本位”观念和以“恩”为基础的家庭父子伦常关系:“‘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是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27]爱本是自然赋予生物界的天性:“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27]随后,鲁迅直接引用林纾的劝孝白话新乐府,借以批判一味以“恩”抹杀“爱”而又责望报偿的旧道德:“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27]鲁迅虽未提及“林纾”之名,但所引诸如“圣人之徒”“有人”“‘卫道’的圣徒”之类都是林纾广为人知的言论。与其说鲁迅是把林纾作为批判的靶子,不如说他所针对的乃是以“孝”为核心的旧礼教、旧道德的全部。呼唤中国出现觉醒的父母和觉醒的人,这才是鲁迅的深刻之处和过人之处,由此可以见出鲁迅的境界要远远高于周作人。
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不时提及林纾的名字或“名言”,也是在借这些人所共知的“当代典故”来讽刺当时的社会。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潘梓年署名“弱水”批评鲁迅词锋的尖酸刻薄,并拿林纾和鲁迅做比较:“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了吧。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先生了!”[28]109-110对于这种讥讽,鲁迅也反唇相讥,同样接着林纾的话题说下去:“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服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象他的东拉西扯。”[28]112-113针对文坛的混乱以及有些人的悲观哀叹,鲁迅也以林琴南为例来说明文坛终究要淘汰那些失去了价值的存在:“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29]由照相馆挂在门口的梅兰芳照相,鲁迅论及中国人的审美观问题时也顺便提到了林纾:“林琴南翁负了那么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热心于‘识荆’的人,我虽然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谢丸药的功效,所以印上的,并不因为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往矣,且从略;近来虽则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铜版而已。”林纾、创造社诸君在这里不过是随手一击的陪衬,鲁迅真正要讽刺的是男扮女装的梅兰芳以及国人“审美的眼睛”:“我们中国的为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30]上述几处,都是鲁迅借林纾作为反击论敌、讽喻当下的由头或比照,虽然意不在林纾,但同时也起到了旁敲侧击的作用。
此外,鲁迅还有几处提及林纾,但并非讽刺批判,而是在中性甚至偏于正面肯定的意义上谈论林纾。他谈及中国文坛翻译的不足与期望时说:“《Hamlet》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Don Quichotte》则只有林纾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君正在大发《Don Quixote》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31]鲁迅由自身感受到的翻译之难,进而驳斥林语堂对中国译界的批评:“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话,为时已久……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32]显然,鲁迅是在肯定意义上谈及林译并借以讥讽那些“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而不务正业的“西崽”了。
综观鲁迅对林纾的批判,始终没有像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那样指名道姓地抨击和嘲骂,也和周作人出尔反尔、不肯饶恕的态度有所不同。鲁迅往往是适时顺手一击,不失其批判立场,同时也潜隐着他的幽默与宽容,这与鲁迅对待“章士钊”和“学衡派”等复古派的冷嘲热讽不同,也与鲁迅在诸多论战中的峻急、犀利、不留情面的风格不同。
青年鲁迅对林译小说颇为着迷。周作人谈及清末文坛对鲁迅影响很大的三个人中,严复、梁启超之外便是林纾:“对于鲁迅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得,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里面十多篇长短诗歌,都是由鲁迅笔述下来,用《楚辞》句调写成的。……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成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鲁迅对林译小说的痴迷随着后期林译小说的随便与粗糙而渐生消退厌倦之意:“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了关系了,但是对于他的国画还多少有点期望……到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来用武力镇压,在《大公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姓徐),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17]73-75鲁迅对林译小说从“热心”模仿再到“厌倦”直至完全断绝,而对林纾“丑恶面目”的“不齿”则是周作人而非鲁迅的态度和立场了。对用小说施行人身攻击泼污水的行为,鲁迅并不赞同,他在初刊于《新青年》的《孔乙己》后记中曾说,用了小说施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33]有学者谈及鲁迅与林纾的学术关系时,认为鲁迅之于林译小说确实经历了从痴迷到背离的过程,但并非就此断绝关系,毫无瓜葛,如果从以小说创作来影射现实社会的人和事的角度看,“鲁迅之于林纾的接受链又在断裂中得以修复”,“用小说笔法来影射现实社会的人或事,顺手一击而不露斧凿之痕,鲁迅之于林纾,可谓一脉相传。他们的区别,并不在于运用方式的差异,而在于各自所处情势和文化语境的变化”[34]。也有学者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射现象时把林纾和鲁迅相提并论:“在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影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依然存在。最早林纾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即用影射笔法攻击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后来的白话文学中,鲁迅则可谓是这种笔法的开先例者,他的《药》即影射了许多晚清名人。《故事新编》中许多历史小说更以影射叙事来体现其杂文精神。《奔月》中的逢蒙暗指的就是高长虹,《理水》中的‘鸟头先生’、‘一个拿拄杖的学者’分别影射的是考据学家顾颉刚、优生学家潘光旦。《补天》顺带影射了胡梦华,甚至《起死》写庄子死时还不忘以‘上流的文章’来暗讽一下林语堂。”[35]诚然,“影射”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影射用意也大为不同,应细加区分,不应一概而论。
鲁迅始终对林纾保留了一份宽容与敬意,这从鲁迅对林纾的称呼可见一斑,主要有以下几种:中国的“圣人之徒”、有人、“卫道”的圣徒、近世名人、林琴南、林琴南翁、林琴南先生、林纾。这与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人对林纾带有戏谑侮蔑的各种称呼如“桐城谬种”“某大文豪”“清室举人”等相比,再与鲁迅对其他论战对手的嬉笑怒骂相比,确实显出了鲁迅对林纾宽容厚道的一面。至于鲁迅在与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戏称林纾为“禽男”[36],属于兄弟二人私人间的偶尔笑谈。鲁迅谈及尊师之道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37]鲁迅虽未因章太炎复古开倒车而公开断绝师生关系,但也并未失去自己的批判立场。在鲁迅这里,林纾固然无法和章太炎相比,但由鲁迅的话也足以见出他的尊师之道和为人之道,从未对林纾出言不逊,这与他对师者的“敬”、对母亲的“孝”可放在一起,是受传统教养影响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方面,鲁迅确实不是决绝的战士姿态,也不是全新的施行家庭革命的“新青年”,但这也正显示了鲁迅作为真实的“人”的品格,显示着他的复杂丰富,以及他的温柔敦厚之风。
三、《现在的屠杀者》及其他:新(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批判林纾”考辨
鲁迅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6卷5号的《现在的屠杀者》,长期被认为是针对林纾的批判,这一看似确凿的指认背后,实际上有一番复杂的演变。
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新文学的首次造史,文学革命及新旧派论争是作为新文学发生的关键问题和主要问题来讲述的。“大系”专辟《文学论争集》和《建设理论集》记述新旧文学论争的来龙去脉,其中《文学论争集》第二编“从王敬轩到林琴南”和《建设理论集》中“发难时期的理论”主要涉及五四新青年派和以林纾为主的守旧派的论争,囊括了较全面的论争文献:首先是引发论争的“双簧信”,即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和刘半农《复王敬轩书》及双簧信的反响,即崇拜王敬轩者《讨论学理之自由权》和戴主一《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其次是蔡元培《答林琴南书》并附林琴南原书、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严复《书札六十四》、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此外,还附录了林纾小说《荆生》《妖梦》。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论及这次论争时勾勒出如下的事件流程:先是钱玄同、刘半农用双簧信方式演出“苦肉计”以便给旧文人“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而后林纾放了反对的第一炮,并与蔡元培书信辩驳;三是林纾“谩骂之不已,且继之以诅咒”,发表《荆生》《妖梦》以希望有“外力”来制裁、压服,最后随着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安福系的倒台,自然没有力量来对新文学运动实施压迫了。1930年代前后的新文学史论涉及五四新青年与林纾的论争,基本没有超出“大系”的阐释方式及资料范畴,而在这些最接近历史现场的脉络梳理中,鲁迅并没有出场。
援引鲁迅的言论支援五四文学革命派,使鲁迅现身于新旧论争的讲述方式,较早出现在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第三章“与反对者的论争”中,大段引述了林琴南攻击五四新青年的影射小说,并由林、蔡书信中“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的辩论进而联想到当下:“现在虽然也还有不少人主张‘要想白话文作好,须文言文有根底或先读一些古文’,抱着和林琴南一样的见解;然而古文的章句词汇的不足表现现代生活的一切,已是众人周知的事实,除了使白话文部分的文言化以外,我们在文言文里能学些什么呢?”李何林随即举出鲁迅《写在“坟”后面》一文作为反证:“有些人却道白话文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作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38]无论是李何林引证鲁迅的话还是鲁迅原文所指,都不是针对五四时期旧派的,而是有着各自批驳的具体对象,鲁迅批驳的是1926年《一般》月刊中朱光潜的言论,李何林针对的则是1930年代的文坛复古的乱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编纂的新文学史,在述及文学革命之“思想斗争”时,适当增加了鲁迅的言论比重,引用了《呐喊·自序》和《趋时和复古》中对刘半农的评价,并没有把鲁迅带入五四的新旧论争现场。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旧之争,还是以林纾的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和《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及林蔡书信、严复的书札等为核心内容,只是去除了刘半农和钱玄同的“双簧信”而替换为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序引”中的一段话,以佐证“前驱者们战斗的艰辛”。还增加了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以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面临的校内外反动声音的猛烈。从总体上看,其阐述方式和史料征引显示了对基本史识的尊重。
随着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受到批评,其后的文学史一方面极力强化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对鲁迅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进行拔高。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鲁迅站到了五四新旧论战的前沿并成为打击“反对派”的主力和领导。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即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新旧思想论战直接定义为“以鲁迅为首的文学革命阵营和封建文学及右翼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当时攻击封建文学最彻底、最有力、最能制敌死命的是鲁迅。一九一八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后来收进《热风》里面的那些《随感录》,全都是攻击封建文化和封建文学的文字。”[39]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来论述五四新旧论争,针对林纾致蔡元培信中的“尽废古书,用土语为文学”等言论指出:在对封建势力的反攻的迎战中,新文学阵营分化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投降的态度”,一是鲁迅和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的态度”。“人民大众的口语能不能用以创作呢?蔡元培回避了这个问题,鲁迅则肯定地、坚决地、正面地答复。”[40]这个答复即《现在的屠杀者》。将《现在的屠杀者》作为针对林纾的批判,已经成为文学史讲述五四新旧论战的方式,并逐渐延续到后来的诸多文学史著中。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大多采用并强化了上述阐释方式。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说:“《荆生》发表不久,李大钊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鲁迅也在自己的杂文中批驳林纾等,指出‘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揭露守旧派活在现代却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实是‘现在的屠杀者’。”[41]刘中树、金训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明教程》(修订版)指出:“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都对林纾言论的反动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李大钊指出,林纾之流只能‘隐在人家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者作篇鬼哭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宽宽心。’鲁迅更深刻地揭露了复古主义者的罪恶是‘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经过新文学倡导者的严正驳斥,林纾等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42]把李大钊视为文学革命的先导,把鲁迅视为打击敌人最有力的斗士,这显然是带有特定时代痕迹的文学史阐释方式,在这种思路中,《现在的屠杀者》成为针对林纾的批判文章并为后来有关林纾的专门研究成果所采用。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即把鲁迅《现在的屠杀者》与其他批判林琴南的文章并列在一处[43]。张旭、车树昇编著《林纾年谱长编》在二者之间更建立了直接对应联系:“5月,针对林纾《致蔡鹤卿书》斥白话文为‘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的说法,鲁迅托名‘唐俟’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随感录’栏发表了《现在的屠杀者》,以讽刺的文字反驳道……是文其实对林纾等人进行了批驳。”[44]需要指出的是,《林纾年谱长编》的一处重要错误,即鲁迅《现在的屠杀者》开头所引高雅人所说的话“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并非出自林琴南致蔡元培的书信,林纾五四时期的文章也没有这句话。林纾反对的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及“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这种极端做法,至于林纾自己,则在1897年就用通俗白话作过几十首“闽中新乐府”,当时曾印行一千部,风行一时,后来又在1919年作了通俗白话诗《劝世白话新乐府》发表于《公言报》。正如胡适所说:“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作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45]
鲁迅在《新青年》6卷1号至6卷5号上发表系列“随感录”,正是新旧论争最激烈之时。新旧论战日趋白热化,1919年2月17至18日《荆生》刊出,3月18日《公言报》发表林纾《致蔡鹤卿书》,3月19至20日《妖梦》刊出,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蔡校长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在北京大学校内,代表新思想的“新潮社”于1918年11月成立,《新潮》杂志第1期于1919年1月1日出版;与之相对立的国故月刊社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住宅召开成立大会,《国故》1卷1期于3月20日出版。新旧思潮的冲突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鲁迅“随感录”确系有感而发。相较而言,鲁迅对同期以刘师培、黄侃等为首的“国粹派”有更激烈的批评态度,他在1918年致钱玄同的信中曾毫不客气地斥骂:“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46]鲁迅痛骂的矛头所向,显然是以刘师培为首的国粹派。客观地讲,就鲁迅《现在的屠杀者》而言,所针对的确实是五四新旧论争时期的守旧派、复古派、国粹派,林纾自然可以算在其中,但这篇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林纾。
剖析新文学史上“鲁迅对林纾的批判”及《现在的屠杀者》如何变成针对林纾的批判文字,并不是要为林纾开脱。作为滚滚时代大潮中的“逆流”,林纾及守旧者、保守派早就注定了失败结局。但“旧”并未因此而丧失其全部价值,“新”“旧”竞争共存是“五四”的基本面相,认识“旧物”、重估“反对派”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也有被历史不断塑造、改写的过程,梳理这种嬗变、重塑,探寻材料的取舍、增删和阐释的走向,也能认识到时代思想的流变。而当下的现代文学史著,已经不再像1930年代的新文学史那样,为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和文学革命者的筚路蓝缕之功而详述新旧派的论争,也不会再像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因强化政治而深描新旧双方的阶级对立。更多的新文学史著对“论争”作了淡化和简化处理,如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便采取了一语带过的方式:“1919年3月,当林纾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书》,攻击《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时,《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便以各种方式,刊出多篇文章,对林纾的言论作出有力的反驳和批评,形成‘新旧思潮之激战’。”[47]有些文学史著则是调整了阐释方式,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二次修订”本中论及五四新旧思想论争,一改以往的激烈态度说:“几次论争双方都难免有意气用事之时,措辞激烈,甚至以怒骂代替说理,但拂去历史灰尘,仍可看到论争的价值,包括守旧派的某些观点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针砭价值。”[48]以此为表征,可以看出史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出了五四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坚守“五四”的正面历史价值,又能以理性的心态看待“反对派”的存在价值,正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新文学史家应有的姿态。
参考文献:
[1] 王桂妹.“反动派”的建构与消解:“甲寅派”阅读史[J].文艺争鸣,2014(6):69-76.
[2] 王桂妹.在“狂人”的精神文化链条上:林纾人格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94-101.
[3] 只眼.林琴南很可佩服[J].每周评论,1919(17):2.
[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79-280.
[5] 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J].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267-268.
[6]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J].小说月报,1924,15(11):1-12.
[7] 开明.林琴南与罗振玉[J].语丝,1924(3):5.
[8] 刘复.巴黎通信[J].语丝,1925(20):1-3.
[9] 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J].语丝,1925(20):3-8.
[10] 开明.再说林琴南[J].语丝,1925(20):5-6.
[11] 周作人.药味集·玄同纪念[M]//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9.
[1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3] 周作人.谢本师[J].语丝,1926(94):221-222.
[14] 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4:170-171.
[15]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6] 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十九篇·关于林琴南[M]//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53-154.
[17]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M]//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8]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下·蔡孑民三[M]//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87.
[19] 张俊才.林纾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226.
[20] 陆建德.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J].中国图书评论,2009(2):21-32.
[21] 陈思和.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读书札记二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3):272-287.
[22] 钱理群.与周氏兄弟相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6-17.
[23]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笑[M]//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99-100.
[24] 林纾.腐解[M]//畏庐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
[25] 鲁迅.什么话?[J].新青年,1919,6(2):245.
[26] 胡适.什么话?[J].新青年,1918,5(4):435.
[27]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新青年,1919,6(6):555-562.
[28] 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9] 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3-264.
[30] 鲁迅.论照相之类[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6.
[31]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5.
[32] 鲁迅.“题未定”草[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9.
[33] 鲁迅.孔乙己·后记[J].新青年,1919,6(4):375-378.
[34] 贺根民.鲁迅接受林纾——痴迷与背离[J].粤海风,2009(4):63-66.
[35] 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射现象[J].贵州社会科学,2013(9):81-87.
[36] 鲁迅.190419致周作人[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3.
[37] 鲁迅.330618致曹聚仁[M]//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5.
[38]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45-46.
[39]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50-51.
[40]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4-25.
[41]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31.
[42] 刘中树,金训敏.中国现代文学简明教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43-44.
[43] 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476.
[44] 张旭,车树昇.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334.
[45] 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J].晨报六周年增刊,1925:267-268.
[46] 鲁迅.180705致钱玄同[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3-364.
[47]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57.
[48]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