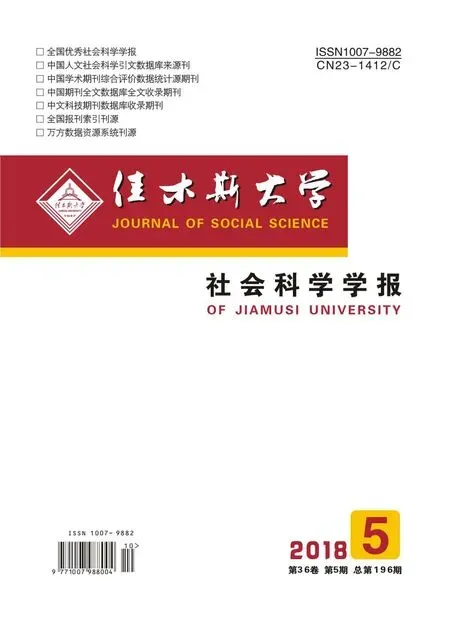发现差异与歧义的“日常”民间*
——重读《马桥词典》兼论韩少功的创作转向
马玲丽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
《马桥词典》以“词典”的形式写小说,通过日常生活只言片语的碎片化场景,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长期处于昏暗、边缘、孤绝状态的民间世界。这个世界屈就在中心世界的一隅,是惯常于被忽略的“多余”。充斥着中心世界难以理解的差异与歧义,它以自身的存在揭穿了中心世界的假象和谎言。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放弃了前期写作中对乡土中国启蒙式批判的自信,代之以日常式的犹疑。这并非批判的退守,包含着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真正理解和尊重,将自己与同时代的作家区别开来。《马桥词典》不仅可视为韩少功写作的自我突破,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向纵深处开拓的范例。
一、“词典”小说与全息性生活展示的可能性
《马桥词典》以词条的形式叙述小说,对韩少功而言是刻意为之,“我从80年代起就渐渐地对现有的小说形式不满意,总觉得模式化,不自由,情节的起承转合玩下来,作者只能跟着跑,很多感受与想象放不进去”[1],韩少功的文学感觉一向具有超前性,尽管小说文体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但对小说文体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只要我们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会承认,仅就形式而言传统小说不仅束缚了创作主体的才智发挥,更无可避免地修剪着生活的旁枝蔓叶,将网络化的日常生活简化、集中成知识观念,形成各种有意或无意的观念,无形地简化或遮蔽了人与存在语境的复杂关联。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对阶级、人性、生命、历史、社会的认识更多是来自整体的概念而不是纷繁复杂的生活,我们对人的认识来自抽象的知识而非特定的人生,导致“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语言与生命的复杂关系,一次次成为重新困惑人们的时代难题”[2]的尴尬局面。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小说形式的不满,只有在一个以日常生活为写作对象的语境中才会成为一个自觉的问题。“历史终结”之后的今天,许多对社会和历史的固有认知已随着宏大叙事的拆解而分崩离析,然而从“整体划一”的“现代”进入到“零碎分散”的“后现代”文学景观,要么如新生代小说陷入无力自拔的欲望,要么如新写实小说津津乐道于平庸的生活,或者如新历史小说干脆遁入历史的虚幻之境,沉醉在自我妄想之中。当代文学现状逼迫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进入到以日常生活为描叙对象的“后现代”时期的文学,如何在既不简单抛弃现代文学遗产(放弃启蒙姿态,坚守启蒙立场),又能克服生活本质平庸面的同时,做到以谦和、宽容的态度,从社会边缘处对中心社会发出质疑,从蛛丝马迹的日常生活碎片中发现故事、命运、文化等重大问题。
这方面,《马桥词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经日常生活语言的变革通往社会深度评判的典型案例。人类凭借语言把握世界,语言写就的小说、诗歌、戏曲、散文,留下了很多经典之作,历史社会的文化积淀,都能在语言变革中找到蛛丝马迹。然而人们总是凌驾在语言之上,吃不透自己的语言。语言常用来描叙事实,更重要的是,语言也表述思维,表达人生,但由于对语言的轻视,“语言与事实”、“语言与生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细致的甄别和深入的思考。如果我们完全抛开一些抽象观念,在概念无法抵达的地方,以语言为突破口,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进行持续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究,将会看到怎样的世界?
《马桥词典》收录了马桥方言中的一百多个词条,这些词条的逐一铺开,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长期处于昏暗、边缘、孤绝状态的民间世界。这个世界屈就在中心世界的一隅,是惯常于被忽略的“多余”。虽然它在规范之外,在中心阐释所不能有效抵达的角落默默地存在,但一旦我们深入到这个世界的内部,就会发现它有着自己的精彩。马桥人将马桥之外的任何地方都称之为“夷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而相对于“夷边”的马桥是马桥人生活“中心”,他们风俗、性情、人伦、性、政治等一系列的生活情状在词条的释义中缓缓铺开,这些词条或者来自马桥的历史传奇人物,如“九袋”、“马疤子”、“盐早”,或者发现了一些处在社会历史幽冥处的人物,如马鸣等四大金刚,或者描叙的是马桥的民间风俗传说,如“结草箍”、“走鬼亲”、“企尸”、“放锅”、“煞”,或者是纯粹的乡间俚语,如“怪器”、“狠”、“话份”等,也有一些意义诡异、语意颠倒的语言,如“散发”,“放转生”,以“觉”和“醒”喻人糊涂和清醒,将“科学”视为懒惰。围绕这些词条,摊开了许多日常生活的片段,依稀出现一些小的叙事、零碎的场景和人物速写。《马桥词典》津津乐道的还是隐匿在词条背后的人及其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大体上是一个相对静止的世界,但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还是缓慢地融进马桥人的言语中,马桥人在时代的侵蚀和重压之下的生活的,他们的反抗和妥协,失败和创痛,都在微不足道的日常语言中隐性流淌。
从这一点说,《马桥词典》尽管在形式上受到诸多质疑,它其实没有违背传统小说最根本的东西,只不过它不再束缚于围绕人物形象塑造结织故事,而是借助词条(语言),展开一种全息式的写作,恰如生活本身那样,无中心、无主题,允许大批人物与各类事件相继登场,又能随时隐灭,展示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多方关系和裂缝,即使一些人物消亡,事件终结,但是继续关注其潜在的影响。较之传统小说诸如以故事、情节、人物、环境等表意单位为中心的方式,更要求创作主体对常规的生活中具备不拘成规的洞察力,可以说,韩少功通过《马桥词典》的形式试验,找到了能较好容纳自己理性思辨爱好的小说形式。
二、词条释义中人物的丰富与复杂
尽管《马桥词典》与传统意味的小说相去甚远,但是传统小说的某些叙事手段仍然依稀可见,比如,人物依旧承担着串联片段的功能,人物命运有始有终。《马桥词典》出场了约三十个左右的人物,他们各有特色,描写充分人物有本义、复查、铁香、万玉、志煌、盐早等,《马桥词典》扬弃了传统小说通过情节的发展逐步刻画人物形象的写法,人物一出场便用词条框定其主要性格,再用释义的方式形象化展开。有些人物贯穿始终,在全书中不间断地频繁出场,如党支部书记本义;更多的是集中出场,譬如,“觉觉佬”、“哩咯啷”、“龙”这三个连续出现的词条集中刻画了马桥最会发歌的人万玉,而“不和气”、“神”、“不和气(续)”、“背钉”、“根”、“打车子”,这几词条集中描摹的是马桥的奇女子铁香,“汉奸”、“冤头”、“红娘子”、“渠”则集中刻画了盐早不幸的命运和扭曲的性格。局限于词条释义的形式,人物多只能以片段的方式出场,在这些片段中人物或许只是充当起串联起词条的符号,在空间的转移中引发议论和思考的道具。但是我们仍能大致勾勒出这些人物的大致轮廓,知晓他们大致的命运始终。
这里不打算将所有人物一一述说,而是挑选几个笔者最感兴趣的作为分析的对象。本义作为马桥的支部书记也就是马桥最高执政者,他在马桥最有“话份”,他说城里人“家家没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能做巴掌大”,他还把毛主席语录里“路线是个钢,纲举目张”说成“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他指鹿为马,将“文盲”说成“流氓”。由于本义有“话份”,马桥人将他的一言一行视为权威,从不质疑。这样的一个人,却难以置信地与马桥红花爹爹罗伯有“男人之间不正经的事”,而他的老婆也偏偏跟着村里最不入流的三耳朵跑了。
再如“觉觉佬”万玉,他是马桥最会发歌的人,他没有胡子,长着极淡的眉毛,刨着光头,离了婚,带着一个孩子,总是拖着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他据说有点下流又很多情,常喜欢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他常替女人挨打,一次次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无一例外都是为女人打抱不平。他一生最辉煌的经历是曾代表村里去县城表演样板戏,却将自己化妆成“洋相公”而拒绝剧组制定的农民扮相,对表演革命剧情也毫无兴趣,只想演“觉觉歌”。他出人意料的拒绝了锄头的艺术和没有女人的艺术。万玉死后,村人才发现这个人没有“龙”,然而,他的坟头常能见到一些面熟或面生的女人在哭泣。
铁香则是马桥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她的父亲是丐帮级别最高的“九袋爷”戴世清,从小在大户人家里长大,家里曾经有保姆和仆人,因受不了政府的管制,发誓要找个共产党做靠山,十六岁那年挺着大肚子,独身闯到马桥,软硬兼施地做了本义的老婆。她长相“不和气”,从长乐街嫁到马桥,带来了一种芬芳却有害的气味,使得马桥一度植被凋零,六畜不安,她很“神”,用马桥人的话说是“神魔附体”。她喜欢在男人堆里混,支使男人们乖乖地跟着她卖力,据说勾引过文化馆长、照相馆的小后生和煌宝,却最终抛开一对还在上学的儿女和村里最有“话份”的丈夫本义,跟着村里“最不像男人的三耳朵”私奔了。
传统小说围绕主人公设置情节,集中力量刻画他们性格:要么通过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将人性的善恶纠合充分展示,要么以排斥公共生活为前提,将个体深层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渐次呈现。不可否认,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人性的关注和深入挖掘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当这种知识观念走向它的极端时,尤其是形成了所谓‘内部/外部’截然对立的学术神话,人与其存在语境的所有联系无形中也就被自然切断。这时候,善/恶的伦理性,再此顽强地阻击着人对存在的进一步追问(社会的、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等)。”[3]《马桥词典》则对这种方式的质疑与挑战,它不再集中全力塑造人物,而是采用速写的方式,点出人物的主要特征,本义的“话份”、万玉的“觉觉”、铁香的“神”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性的展示也不再固定性格描写和内心叙述上,而是与人物存在的语境广泛关联,每一个人及其经历,都是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说,本义、万玉、铁香等人物形象,无不与他们社会的、阶级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乃至性别的、成长的背景有机相连,呈现出裂缝蓬生、模糊暧昧、飘滑游移的状态,这正是韩少功倾注了极大探究兴致的地方,最具“话份”的本义,老婆却跟最不具“话份”的三耳朵跑了了,最多情的万玉却没有“龙”,铁香的“神”最终难逃“根”的宿命。控制人物的知识“边界”消失之后,个体恢复了在其存在语境中的活力与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活着的生命之中,还延续到了生命的死亡之后。万玉、铁香“散发”之后,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持续对马桥人的生活产生亦真亦幻的影响。
三、充满差异与歧义的“马桥”民间
人物的复杂状态一旦楔入历史,相应会带来了人物背后历史、事件言说的模糊性,由此,韩少功发现了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显然,这个差异性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对照,是标准规范的中心世界和马桥世界的差异性较量,而这一切是通过一个隐含的对比视角,一位马桥的外来者——来自规范语言的代表、有着知青身份、充满怀疑而又温和睿智的“我”的视角和感知中逐一展示的。
首先是语言与事实的差异关系。散匪马疤子在历史教课书中面目是清晰的,平反之前是“规劝会暴乱头目”,平反后是“抗日英雄”。而然在马桥方言“大发起”、“一九四八年”等几个词条里,他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所在。马疤子到底是真心“投诚”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派来卧底的“假投诚”分子,还是匪性难改、伺机反水的散匪?在不同的话语场域被设定成不同的形象,哪一个是马疤子的真正面目?不仅外人难以猜测,或许,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清楚了,马疤子自杀之前耳朵聋了,这是一个象征——他已经听不懂各种喧嚣的话语了。那些围绕马疤子发生的真真假假的事件,只留得一些零碎的场景认任由后人述说。按照他儿子光复的说法,因短短两天时间的误差,马疤子阴差阳错地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改变了光复的命运。这沉甸甸的祖辈历史,在马疤子的孙辈眼里,更是化作轻飘飘的虚无——并不比一瓶汽水更重要。再如时间的歧义性。不仅历史事件面目模糊,历史纪年同样难以识别。历史事件中那个独一无二、确凿存在的“1948年”,在马桥人的记忆中,“1948年”既是“长沙大会战那年”,也是“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又是“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更是“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那个均质的、方正整齐的“1948年”,被各种人的时间的歧义性感知搅得一塌糊涂。于是作者发现“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相比之下,我们一直奉为真理的所谓的客观时间、统一的时间、直线的时间,其实只对物质世界有效,一旦应用在人的感知中,就只是一种脆弱而虚幻的谎言,它并不像表面呈现给我们的那样一往直前,确凿无误。历史事件由经语言描述之后,就已经离开了事实,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靠近、永远没有办法“抵达”和“再现”历史事实。
其次是差异性思维方式。比如“罗江”这个词条,写到知青与马桥人的处世差异。一些知青渡罗江时想赖账,他们觉得自己跑得快,靠岸之后不付钱便逃之夭夭,不料摆渡的老倌扛上长浆不紧不慢地追着,三里、四里死死地咬着,绝不停下脚步,直至这群累的东倒西歪的知青乖乖地交钱,老倌居然还给他们找还了零钱。知青们显然惯常于从现代社会理性思维逻辑思考老倌的行为——傻到为三角多钱撇下大批生意不做;而老倌则显然从边缘社会以伦理为主导的思维逻辑去衡量知青的行为——坐了船就应该付钱。差异的产生有各自的话语生成体系,很难用智慧
有时,思维差异之大还达到了无法理喻的地步。如住在神仙府的马鸣之类的四大金刚之“懒”,他们从不出门做工夫,从不沾锄头扁担一类的农具,无论哪一级的领导去劝说、去辱骂都无济于事。他们反过来嘲笑终日忙碌的村里人,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文革,外界一切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们无关,是一群完全没有现实感的人,完全生活在生活之外的人。这个差异之大,不仅是相对于外来的“我”,而且也是马桥人都不能认可的。远离了公众的言语和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存在就是“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就不能成其为人。然而这个“无”和“空白”,却对马桥人制造出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现实”,在他们看来,马鸣他们用“科学”为自己的懒惰辩护,“科学”无非是“学懒”的代名词。因而对“科学”产生了恐惧和憎恨,马桥人从此不相信任何科学,看到公路上的汽车就用扁担敲瘪,将发来的科学种田的小册子撕成纸片卷烟丝,对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广播的科学喂猪无动于衷。
种种迹象表示,与中心世界惯常于理智地接纳词(事物)不同,马桥人是通过具体感觉去理解一个词(事物),他们在具体使用环境、具体氛围、具体事实中形成对词(事物)的判断和情感,形成与普通话相异的修辞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说,马桥正是因为这些无处不在的“差异性”而彰显出一个与普通话世界相异的独特存在。这种差异性已很难用先进/落后,文明/愚昧,好/坏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作判断,它以自身的存在抵制着一个被普通话概括的世界,而世界的丰富性正是通过差异性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处在中心生活的边缘处的马桥人凭借自身的语言认知,避免了被政治话语“一体化”的命运,成为抵制中心世界霸权地位的对立面,这也是马桥世界存在的意义。但也引出了一个现在看来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一个交流与互动越来越频繁的现代社会里,没有“话份”的弱势语言(边缘世界)面对掌握了“话份”的强势语言(中心世界)的扩充和征服(差异的日渐消磨),会怎么样呢?
事实上,马桥世界的独特性正在普通话的入侵中节节败退,这种溃败早在政治革命时期就已经上演。马桥方言与普通话的微妙处境“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也道出了作为“没有话份”的马桥语言悲剧性的现代处境,语言的变化更替透射出复杂的权利抗衡,来自政治中心的语言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刺目地镶嵌在马桥方言中,“觉觉歌”、“同锅”、“怪器”、“公田”、“母田”等充满生命力的语言,在“阶级”、“生产”、“模范”、“科学”等苍白、空洞的外来词汇的入侵中泯灭遗忘。这些强行嵌入马桥语言中的外来词语,由于缺乏感性的生命力,类似于马桥“你老人家”一类的废话,不具实际含义,只是一些正式场合必须的堂皇套式。罗伯学哲学时的“打玄讲”,讲着讲着就要变味,不是讲红军毒辣,就是给马疤子鸣冤。本义在罗伯追悼会上的发言背上一大段自己都不明白的革命话语之后,切入正题“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也许,漫画化生活场景并不是农民文化素养的低下,而在于我们对规范之外的边缘世界所持的一贯傲慢态度,不屑一顾地斥之为“愚昧”、“落后”。也许,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外来语言携带着异质文化和意识形态,强迫他们脱离自己熟悉的语言和生活进入到一个异质的文化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不知所措,或者茫然地为外来物腾出位置,或者固执地回到自己的轨道。
九十年代标示着一个更加茫然时代的到来。外来词汇由“强制性”入侵转变为“化入式”快速融进,“电视”、“涂料”、“减肥”、“操作”、“彩票”、“砌长城”、“提篮子”等象征着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化的词铺天盖地涌入了马桥。如果说,政治化时代的外来词汇以其空洞抽象,尚未对马桥人现实生活造成有效冲击的话(在边缘化的乡村,政治往往大打折扣),当代词汇却是携带着现实生活方式一涌而入的,比如“砌长城”已成为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买彩票”寄托着很多人发家致富的梦想。一方面马桥想融入社会现代化步伐,与外界良好沟通,必须学习公共语言;而另一方面,“怪器”、“放锅”、“打发起”等源自古老罗人生命深处的古老而带着强悍生命力的语言,渐被“电视”、“国道”等茫然无知的现代物所滤洗,他们对外来物的入侵无法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抗拒(更多的是积极迎合),当然也无力守护自己的表达,在一味的妥协中湮灭了自己。如果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交流,结果是弱势语言的消亡和泯灭。那么,差异性消失之后,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语言大同世界?而现代语言的快速更替又将怎样续写大同之后的“再分歧”?韩少功不无忧虑地提出了这些问题,马桥是乡土中国的缩影,马桥的处境,实际上也是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当然不是一部小说所能回答的了。
四、“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的词典”与韩少功的文化姿态转型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语言更替带来的所有问题,那么,对差异的理解和宽容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4]401,这是韩少功对马桥世界差异性感受之后得出的感悟,蕴含着韩少功对乡土日常持有的宽厚、从容、深邃的文化姿态。如果我们将韩少功的写作作一次纵向的梳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批判风格的转型。韩少功在早期作品《月兰》、《西望茅草地》中专注的是政治历史批判,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作品《爸爸爸》、《女女女》则抛开现实循入历史,开展文化批判,这两个阶段的批判重点不同但性质一样,都可以纳入精英知识分子文明/愚昧式启蒙批判范畴。九十年代初期的《归去来》从作者的价值立场上看是一个暧昧的文本,小说设置了主人公“黄治先”和“马眼镜”的双重身份,相应的带来了“启蒙”和“日常生活”的双向视角,作者对民间乡土的态度也在双向的文化审视中游离。这种情感游离在《马桥词典》中变得明朗,它告别了韩少功前期创作中强烈的政治关怀和文化寻根意识等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而转向一种纯粹的“日常”立场。深入到乡村核心的韩少功,身上沾满了乡人的气息,当他把自己当做马桥的一员重新打量乡村时,他发现乡村生活真相远在文人一厢情愿的视野之外。“马桥世界”,并没有回避与主流社会的联系,但对政治,文化等大问题的考察不再以正面的方式进入,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细致考察日常生活(人)如何分解、承担了时代和历史主题,因而也获得了全新的审美感受: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入侵中的马桥,突出的是其“日常民间”的一面,呈现的是乡村自足的文化意识形态;马鸣的超脱、飘逸与丙崽的愚钝、痴蠢决然两样;马桥弓的繁复浑厚也取代了鸡头寨的愚昧封闭。如果说站在精英文化立场上韩少功看到的只能是传统民间的愚昧和闭塞,寻找到的只能是“劣根”,而站在日常民间的立场上的韩少功,则发现了一个理性上难以判断和情感上难以割舍的乡村。从启蒙式的明朗转变为日常式的犹疑,并非重演鲁迅式“启蒙者被启蒙对象同化”的悲剧,是韩少功批判立场的退守,而应该理解成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化——只有尊重差异、歧义,才能对现实和历史持真正的同情和理解态度,才能探索到社会、历史的真相,这是知识分子启蒙传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调整。
这正是《马桥词典》的独特性,在面向日常生活的写作中,他既不像张承志那样用孤绝的文化姿态与社会保持距离,也不像余华等先锋小说家们那样在虚幻的历史语境中癫狂,也不像新写实作家池莉、刘震云等那样与日常生活和解,更不像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那样表现出精神的日常化沉沦。韩少功似乎是在透视生活种种劣质之后,仍愿意潜伏在生活的深处,用一颗温和平常而非偏激的心思考生活,在对日常生活庸常和常识的思考中跳出“惯例”和“从来如此”,挑出它们当中的谐谑、惊惧、无奈、乐趣、自由甚至诗意。韩少功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方式呼应了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思路:“尝试建立日常生活的清单和分析,以便揭示日常生活的歧异性——它的基础性,它的贫乏和丰饶——用这种非正统的方式可以解放出作为日常生活内在组成部分的创造力。”[5]也许,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注定无法支撑一种整体性的政治文化想象,现阶段,作家能做的恐怕只有潜心到日常生活的角落,在只言片语之中,揭穿、破坏语言生殖、繁衍背后的假象、陷阱和谎言,才能不断地逼近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这正是韩少功所追求的小说道德——在“自相矛盾”、“不知所云”的困境中,“反对独断论”[1]10。因此,我们应该从当代文学史高度上,将《马桥词典》不仅看做是韩少功写作的自我突破,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革新开拓的范例。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