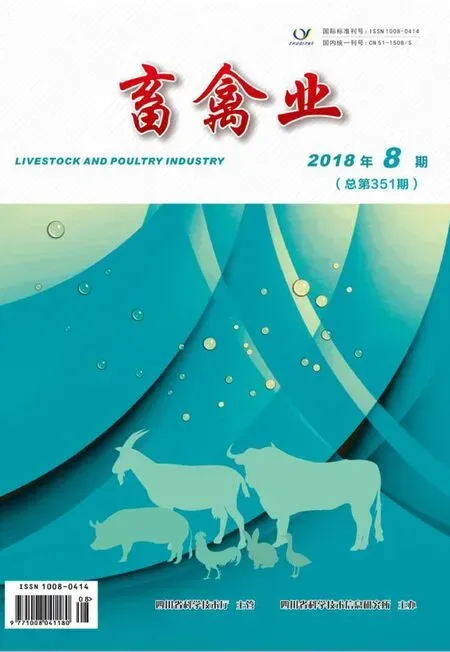论动物疫情应急处置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刘天发
(重庆市江津区石门畜牧兽医站,重庆江津402260)
1 补偿标准低留隐患
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的原则是“早、快、严、小”,即发现报告疫情要早、应急响应要快、处置措施要严、疫病控制范围要小。要落实好这一原则,其中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必须对疫点周边的易感动物进行强制扑杀,并按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给予200~500元的经济补偿。但由于补偿标准与养殖者间的实际损失差异较大,因而在发生疫情后,经常会出现隐报、瞒报、迟报的现象,扑杀动物也常遭到种种刁难和阻碍,不但延误了处置最佳时间,且难度和损失也加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隐报延时机
为避免报告疫情后动物被强制扑杀造成的损失,在疫情发生的最佳处置时间内,养殖者往往抱着侥幸心理,自行寻医问药处置,使疫情漫延扩大、损失增加。当出现疫情失控时,才不得不报告,但此时疫情处置的最佳时间已经错过,损失已无法挽回。
1.2 转匿卖动物
为逃避动物的强制扑杀、减少经济损失,有的养殖者只顾眼前个人利益,不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违规将病死、染疫动物藏匿、转移、变卖,不但造成面源污染扩大、处置难度增加,且也留下了更多疫情隐患。
1.3 动物乱丢弃
控制、处置疫情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迅速有效地对病死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止疫情扩散、控制住疫情。这一措施对规模养殖场执行较为容易,但对农村零星散养户执行和监管难度却较大,他们因自身损失较小、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缺失,把涉及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法律义务行为视为个人行为,将病动物随意乱抛乱弃,或随意挖土填埋,不但达不到无害化,且还留下了疫情隐患。
1.4 损失谁买单
养殖者认为:动物疫情处置是政府组织指挥的、各部门人员共同参与的,属于社会公益性的强制行为,不是社会团体或个人的自愿行为。处置疫情的费用和强制扑杀动物造成的损失政府应当全额买单;把处置费用和扑杀动物损失分摊转嫁给养殖者显然不合理。因此,在处置疫情强制扑杀动物时,常常向政府提出各种苛刻条件、讨价还价,甚至寻找种种理由和借口,拖延、阻碍疫情处置时间。
1.5 尸体处理难
疫情处置中,难度较大的是强制扑杀动物无害化处理地难找。因无害化处理地的选择有严格的要求,不是随便选择一个地方都可以的。实际操作中,难就难在国有土地价格昂贵且很难找到合适地;集体土地全部分包给了农村居民,哪家都不愿意将扑杀动物埋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因此,在寻找无害化处理地时,要么遭至拒绝、刁难、阻挠,要么蛮天要价求赔偿,并由此引发矛盾和纠纷。
2 疫情认定程序繁琐
《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动物疫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其中重大动物疫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初步认定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在2小时内将情况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卫生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报本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4小时内向国务院报告。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动物疫情报告后的顾虑较多,且处置工作又不宜公开报道,因此,对疫情的处置既不能接受社会监督,又很难做到快速反应。
3 兽医部门处境艰难
动物疫病应急防控工作是社会公益性的政府行为,也是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应急条例》和《预案》的要求,重大动物疫情的处置均由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指挥部在兽医部门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做好疫情的监测、报告,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疫病诊断,迅速对疫情等相关情况做出全面分析,并制定疫情控制和扑灭的技术方案。调集动物防疫人员参加疫情的控制和扑灭工作。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提出封锁建议,并参与组织实施。指导监督对疫点、疫区内应扑杀的畜禽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工作;对疫点、疫区的污染物等实施消毒和无害化处理;对饲养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严格消毒。指挥部组成部门虽然进行了分工,但实际情况是,除较大范围的疫情外,在具体操作上,经常是畜牧兽医部门一家“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兽医技术人员长期处在防控第一线,矛盾和困难往往都集中于畜牧兽医一个部门,遭遇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4 处置经费拨付迟缓
多数地方对处置动物疫情所需经费的拨付办法是,先由疫情发生所在地镇(街)政府垫支,待疫情处置结束后,再由镇(街)政府向县级人民政府提交经费拨付,经指挥部办公室审查后再提交县财政部门审核,最后经县政府审批后再财政部门拨款。这样以来,即最快的时间也要3或4个月,一般都半年时间左右才能将款项拨付到位。但财政拨付的数额与镇(街)垫付的数额往往有较大的差额,部分镇(街)为减少因垫付带来的“亏空”,往往有钱也不愿垫付,致使强制扑杀动物的补偿费迟迟到不了位,不但给动物疫情的处置工作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延长了处置的时间,经济损失也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