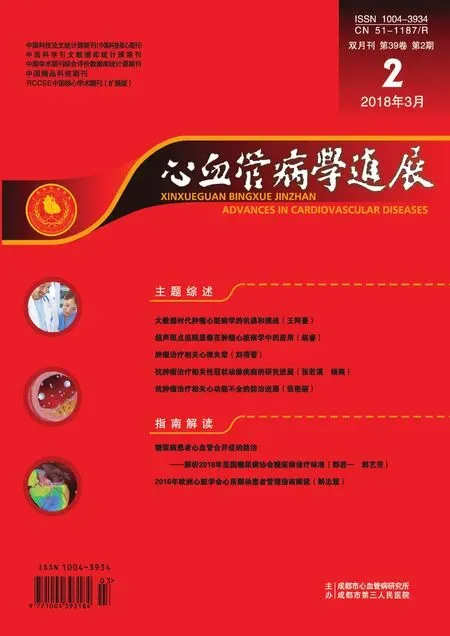Liddle综合征研究进展
蒋晖 综述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四川 成都 610031)
近年,单基因致病型高血压引起越来越多心血管领域临床医生的关注。单基因致病型高血压是指由单一基因突变直接引发的高血压,其遗传方式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迄今已明确了多个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的致病基因和突变位点,Liddle综合征是其中报道较多的一类单基因致病型高血压,现对其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病因及遗传学特征
Liddle 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单基因高血压,由Grant Liddle 等在1963年首次进行详尽描述。Liddle 综合征的主要病因是编码远端肾小管上皮钠通道(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ENaC)的基因发生功能获得性突变。
ENaC存在于肾小管、结肠、肺等组织特化的上皮细胞腔面的质膜中,主要负责钠离子的跨膜转运。在肾远曲小管中,ENaC 调节原尿中钠离子的重吸收,从而间接影响血压。肾小管远端ENaC包含α、β和γ三个结构相同的亚单位,即αENaC、βENaC和γENaC,分别由SCNN1A、SCNN1B和SCNN1G编码。Liddle 综合征的遗传学基础是编码ENaC的基因(SCNN1B 和SCNN1G)发生功能获得性突变。
Liddle 综合征最常见的突变是β和γ亚单位C羧基末端和富含脯氨酸的高度保守的 PY基序错义突变、无义突变或移码突变[1-4]。β和γ亚单位的基因突变可阻止神经前体细胞表达的发育下调基因4-2与ENaC上的PY基序结合,导致远端肾小管大量的ENaC不能被内吞和降解,使ENaC的密度增加且持续活化。ENaC持续活化引起钠重吸收增加,容量扩张,从而导致高血压[3]。
国内外报道的Liddle综合征病例ENaC基因突变多位于β和γ亚单位,但也有因α亚单位胞外域存在错义突变而造成多个家族成员罹患Liddle综合征的报导[5]。
2 流行病学
以前认为Liddle综合征非常罕见,各地仅有零星报道,其发病率<1/1 000 000[6],目前不知晓Liddle综合征的确切发病率。Tapolyai等[7]对149例高血压伴低血钾或伴高碳酸氢盐血症的美国退伍军人进行检测,发现9例(6%)具有Liddle综合征表型。中国研究人员探讨了不明原因的年轻高血压患者(330例,14~40岁)Liddle 综合征的发病情况,对低血钾者进一步行基因检测,5例(1.52%)确诊为 Liddle 综合征,其亲属中有12例同样确诊为 Liddle 综合征[8]。
Liddle综合征有不同的种族背景,包括亚裔、白种人以及非洲裔[9]。黑人似乎更容易出现水钠潴留、血浆肾素活性抑制以及对醛固酮更敏感。大约6%的黑人顽固性高血压患者存在SCNN1B变异,此外,其他候选基因也很重要[10],提示不同种族间也许存在差异。
随着临床医生重视度的提高和基因检测的开展,估计Liddle综合征的确诊病例将增加,而Liddle综合征也许并不是一个罕见疾病。
3 病理生理
ENaC是细胞膜上的一种糖基化大分子蛋白,ENaC通道属于非电压依赖性通道,对Na+的选择性远高于K+,ENaC可被阿米洛利阻断,且开放和关闭都很缓慢,因其对利尿剂阿米洛利敏感,故也称为阿米洛利敏感性上皮钠离子通道。ENaC的生理功能主要是调控跨上皮细胞的钠离子转运,负责钠离子的限速重吸收,因此ENaC对于维持钠平衡、细胞外液容量和血压起重要作用。Liddle 综合征主要的病理生理机制是远端肾小管ENaC基因突变,使ENaC持续激活,转运异常,对钠的重吸收增加,细胞外液容量扩张,血压升高,醛固酮和肾素的分泌受到抑制,钾重吸收减少,出现低钾血症、代谢性碱中毒,从而产生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临床症状。
醛固酮敏感的远端肾单位包括远曲小管的后段(distal convoluted tubule,DCT2)、连接小管(connecting tubule,CNT)和所有的集合管,其中皮质集合管称为CCD(cortical collecting duct)。Liddle综合征由ENaC基因发生功能获得性突变所致,但并不清楚远端肾单位上ENaC功能增强的确切部位,Nesterov等[11]利用Liddle综合征小鼠模型,从另一角度探讨了其病理生理机制。研究人员采用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记录不同醛固酮水平小鼠肾单位碎片上阿米洛利敏感性ENaC电流,检测DCT2/CNT或CNT/CCD过渡区的ENaC功能,结果显示Liddle综合征小鼠与对照组相比,ENaC在肾小管管腔膜顶端上的表达明显增加,高盐摄入组尤为明显。钠重吸收增加的区域位于DCT2/CNT,DCT2/CNT区域ENaC的高反应性可能是Liddle综合征的主要病理生理机制。另外,CNT/CCD区域ENaC对醛固酮的反应性增加也许可解释Liddle综合征所具有的盐敏感性高血压的特性,这对于人们理解其他形式的盐敏感性高血压和低醛固酮性高血压的病理生理也具有潜在意义。研究提示抑制DCT2/CNT区域的ENaC 活性,可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的一个治疗策略。
4 临床特征
Liddle综合征的病因及病理生理机制决定了其临床表现。典型临床表现包括:高血压伴低血钾,严重时可发展为代谢性碱中毒;肾素及醛固酮水平降低。Liddle综合征患者除了血压高、对常用降压药反应差,往往伴有低钾相关症状,如乏力、心悸等,因其临床表现酷似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故又称为“假性醛固酮增多症”,很多患者初期被误诊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此外,基因表型的变异性也使其难以识别,更易造成误诊。Liddle综合征与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临床方面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血浆醛固酮水平低,对醛固酮抑制剂螺内酯不敏感,而对上皮钠通道抑制剂(阿米洛利、氨苯蝶啶)非常敏感。
Liddle综合征常表现为早发高血压,甚至严重的高血压,多数患者年龄不超过30岁,文献显示低龄化特征明显,最小仅10周[12],近期也有10月龄女婴确诊为Liddle综合征的报道[13]。由于早发高血压、未及时确诊、无针对性治疗、血压控制不佳等因素,患者往往较年轻就出现严重的靶器官并发症,如脑卒中、心力衰竭、肾衰竭,甚至主动脉夹层[6]。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Liddle综合征患者除了血压高,并无其他典型症状。一些儿童可表现为生长迟缓、个子矮,随着对血压的精准有效治疗,其生长情况可得到改善[14]。Liddle综合征孕妇应警惕胎儿生长受限和先兆子痫。
5 基因型和临床表现的关系
关于基因型和临床表现的关系问题,中国一项回顾性分析[1]进行了仔细的描述和分析。该研究纳入国内北京协和医院2002—2015年12例确诊的Liddle综合征患者。所有患者都有间歇性头痛或头昏,4例有心悸,1例因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接受了射频消融术;9例感觉肢体无力。平均发病年龄为(15.5±3.3)岁,尽管每日补钾,大多数患者的血钾水平仍<3.0 mmol/L;所有患者的血浆肾素、醛固酮水平降低。5例患者服用螺内酯(60 mg,每日3次)2周后血压与血钾水平无改善。所有患者服用氨苯蝶啶(50~100 mg,每日3次)后血压都得到良好控制,血钾也恢复正常。基因检测显示11例患者有8个等位基因发生突变,其中3个基因(p.Gln568Ter、p.Pro603Alafs和p.Pro617Serfs)为新近发现。该研究发现突变基因相同的患者具有完全相同的临床表现,即使突变位点不同,其临床表现也仍然相同。当然也应注意研究的局限性,如病例选择的局限性、未对所有家庭成员进行突变基因的测序。今后需系统性地研究Liddle综合征的人群特征,尤其是遗传特征以及发病情况。
对于基因型和临床表现的相关性,文献结果并非一致,例如一个土耳其家庭尽管具有相同的突变,先证者及其家族成员之间的临床表型却不相同[15]。临床表型的差异可能与杂合基因的表达程度不同有关,提示其他与血压调节相关的基因可能影响了杂合基因的表达,研究其相互作用对醛固酮代谢及血压的影响,有助于发病机制的探索[16]。
6 诊断
Liddle综合征是儿童、青少年早发严重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病因,对于非常见病因的儿童高血压患者需警惕此类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高血压伴低血钾、类似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肾素及醛固酮水平降低以及对螺内酯反应差都是重要的临床诊断线索,确诊Liddle综合征需行基因检测。父母一方如果患有Liddle综合征,建议行遗传咨询,以便对高危个体较早地进行针对性监测[17]。
全基因组测序(whole-exome sequencing,WES)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患者可提供广泛的评估,以识别致病性的遗传变异,这可能会避免一些侵入性、昂贵和/或耗时的检测手段。二代测序技术为具有孟德尔遗传规律疾病的分子诊断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在已知的单基因致病情况下,WES也非常有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显著遗传异质性的疾病,运用WES可识别和确定少见基因,或者发现新的基因[14]。
7 治疗
基因检测有助于早期确诊Liddle综合征并指导精准治疗,因此,病因筛查非常重要。对于儿童高血压患者,不进行病因筛查而直接处方降压药是不恰当的[18]。Liddle综合征的常规治疗包括限盐,口服阿米洛利或氨苯喋啶,这两种药物都是ENaC阻滞剂,大多数患者效果明显,在治疗期间需监测肌酐水平,尤其是已存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某些Liddle患者可能仅对阿米洛利或仅对氨苯蝶啶有反应,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突变基因[19]。在使用了ENaC阻滞剂后,如果低血钾得到纠正而血压仍高,加用β受体阻滞剂或血管扩张剂也许有益。
Liddle综合征孕产妇的治疗经验有限,文献[20]提示:妊娠时优选阿米洛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其归类为怀孕期B类用药,FDA B),而氨苯蝶啶干扰叶酸代谢,通常避免在妊娠期间使用(FDA C)。Liddle综合征孕妇由于存在更多的病理性ENaC 通道,随着孕周增加也许还需加大阿米洛利的剂量以控制血压。目前尚不知晓哺乳期使用阿米洛利或氨苯蝶啶的安全性。
Liddle综合征有多种突变型,因此治疗的针对性、广泛性以及治疗率仍是问题,针对发病机制的分子治疗值得期待。
8 总结
Liddle综合征是一种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常表现为早发高血压伴低血钾,初期易被误诊。内分泌科和肾科医生对该综合征较熟悉,而心血管科医生对其相对陌生,临床诊治工作中应予重视,早期诊断及精准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1] Cui Y,Tong A,Jiang J,et al.Liddle syndrome:clinical and genetic profiles[J].J Clin Hypertens(Greenwich),2017,19(5):524-529.
[2] Nakano Y,Ishida T,Ozono R,et al.A frameshift mutation of beta subunit of 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 in a case of isolated Liddle syndrome[J].J Hypertens,2002,20(12):2379-2382.
[3] Yang KQ,Xiao Y,Tian T,et al.Molecular genetics of Liddle’s syndrome[J].Clin Chim Acta,2014,436:202-206.
[4] Sawathiparnich P,Sumboonnanonda A,Weerakulwattana P,et al.A novel mutation in the beta-subunit of the 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 gene(SCNN1B)in a Thai family with Liddle’s syndrome[J].J Pediatr Endocrinol Metab,2009,22(1):85-89.
[5] Salih M,Gautschi I,van Bemmelen MX,et al.A missense mutation in the extracellular domain of αENaC causes Liddle syndrome[J].J Am Soc Nephrol,2017,28(11):3291-3299.
[6] Abbass A,D’Souza J,Khalid S,et al.Liddle syndrome in association with aortic dissection[J].Cureus,2017,9(5):e1225.
[7] Tapolyai M,Uysal A,Dossabhoy NR,et al.High prevalence of Liddle syndrome phenotype among hypertensive US veterans in Northwest Louisiana[J].J Clin Hypertens(Greenwich),2010,12(11):856-860.
[8] Wang LP,Yang KQ,Jiang XJ,et al.Prevalence of Liddle syndrome among young hypertension patients of undetermined cause in a Chinese population[J].J Clin Hypertens(Greenwich),2015,17(11):902-907.
[9] Bogdanoviĉ R,Kuburoviĉ V,Stajiĉ N,et al.Liddle syndrome in a Serbian family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underlying mutations[J].Eur J Pediatr,2012,171(3):471-478.
[10] Jones ES,Spence JD,Mcintyre AD,et al.High frequency of variants of candidate genes in black Africans with low renin-resistant hypertension[J].Am J Hypertens,2017,30(5):478-483.
[11] Nesterov V,Krueger B,Bertog M,et al.In Liddle syndrome,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 is hyperactive mainly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aldosterone-sensitive distal nephron[J].Hypertension,2016,67(6):1256-1262.
[12] Assadi FK,Kimura RE,Subramanian U,et al.Liddle syndrome in a newborn infant[J].Pediatr Nephrol,2002,17(8):609-611.
[13] Aziz DA,Memon F,Rahman A,et al.Liddle’s syndrome[J].J Ayub Med Coll Abbottabad,2016,28(4):809-811.
[14] Polfus LM,Boerwinkle E,Gibbs RA,et al.Whole-exome sequencing reveals an inherited R566X mutation of the 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 β-subunit in a case of early-onset phenotype of Liddle syndrome[J].Cold Spring Harb Mol Case Stud,2016,2(6):a001255.
[15] Büyükkaragöz B,Yilmaz AC,Karcaaltincaba D,et al.Liddle syndrome in a Turkish family with heterogeneous phenotypes[J].Pediatr Int,2016,58(8):801-804.
[16] 朱鼎良.从基因看高血压和内分泌疾病的关系[J].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2,18(1):1-2.
[17] Vehaskari VM.Heritable forms of hypertension[J].Pediatr Nephrol,2009,24(10):1929-1937.
[18] Simonetti GD,Mohaupt MG,Bianchetti MG.Monogenic forms of hypertension[J].Eur J Pediatr,2012,171(10):1433-1439.
[19] Warnock DG.Liddle syndrome:an autosomal dominant form of human hypertension[J].Kidney Int,1998,53(1):18-24.
[20] Awadalla M,Patwardhan M,Alsamsam A,et al.Management of Liddle syndrome in pregnancy: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J].Case Rep Obstet Gynecol,2017,2017:6279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