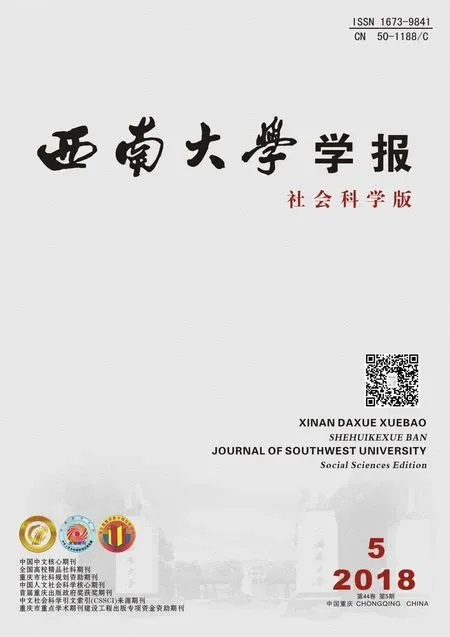霍布斯不是现实主义者
——论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的规范面向
唐 学 亮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在西方思想史上,霍布斯的地位极其特殊,几乎所有的严肃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位旗帜性人物。施特劳斯称他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众所周知,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的“美洲版前言”中修正了这一说法,把如此殊荣奉送给了马基雅维利。参见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但是,霍布斯依然属于他所谓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第一波中与马基雅维利并列的两大弄潮儿,参见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6页。,施密特称其是“一个真正有力且系统性的政治思想家”[1],奥克肖特称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为“用英语写就的政治哲学中最伟大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杰作。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只有区区几部著作在范围和成就上可以与之并肩”[2],塔克称“霍布斯创造了英语哲学”[3],如此等等。但与此同时,一个可悲的地方在于“他的最伟大的著作获得了广泛的征引而不是细致彻底的阅读”[4]viii。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思想史上少有的滑稽现象。有人认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有人认为他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有人认为他是自由主义的鼻祖;有人认为他是经验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理性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先驱,有人认为他属于自然法传统中人,可谓人言人殊。然而,在如此高度争议的霍布斯思想研究中,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学者居然达成了一个大体一致的意见,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霍布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我国相关学者几乎一致的附和*主流的观点参见潘亚玲,时殷弘:《论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载于《欧洲》1999年第6期,第13-21页;吴征宇:《从霍布斯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思想的古典与当今形态》,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第73-84页;孔小惠:《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及其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载于《国际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4页。。
虽然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内涵极为丰富,其并非一个严密规整的学术流派,而是“一种哲学倾向和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系列假定而不是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5]、“一个松散的框架”[6],甚至有学者称它是“一顶笼罩着许多不同理论的‘大帐篷’”[7]。但是,纵然如此,现实主义诸理论也具有某种“家族相似”,否则就不可能用统一的现实主义来涵括其旗下的种种理论。著名学者唐纳利总结了三条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所共享的基本主张,即人性对政治的作用、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的权力和利益属性[8]9。唐氏所总结的这三个主张可能是受到沃尔兹理论启发的结果。沃尔兹有著名的三个“意象”(image)理论,他认为关于国际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冲突的原因,有三个经典的“意象”或主张,第一是人性和人的行为,第二是国内结构和组织状况,第三是国际无政府状态[9]。但是作者认为,这三个“意象”之间并非扁平并列而是结构性的关系,前两者只是冲突的直接原因,后者才是根本性的。其实,唐氏的这三个主张之间也并非平铺并列的关系,前两者即人性和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后者即国际关系的权力和利益导向的基础和原因。这就是说虽然这三条都可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主张,但是三者之中,前两者是基础、根本,后者是在前两者基础上的对国际关系的整体认识和结论性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前两者可称为现实主义的实体性主张,后者则是一个关系性主张。而且,国际关系学者也正是基于前两者才把霍布斯认定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至少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三个主张,即国际关系的权力和利益导向,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子内涵,一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具有权力和利益的偏好和优先性,主权国家之间,一如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之间一样,处于战争状态;二是认为国际关系处于规范真空状态,蕴含着道德和法律虚无主义。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分析霍布斯人性论的真正意涵及其权力观。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在什么意义上霍布斯说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否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的权力战争导向。余论部分根据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和散见于其著作中的国际法思想,建构一个可能的霍布斯主义的国际法纲要。在此基础上展现“霍布斯不是现实主义者”。
一、人性论与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人性论,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人的自私自利本性(egoism)[8]9-10,本节我们将要具体地考察霍布斯的人性论是否如研究者所说是心理自利主义的以及其是否可能导致“权力政治”。
(一)霍布斯的人性论
霍布斯的人性论向来饱受诟病,因为他不但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讲人必然要追求对每个人来说是善的东西,而且在其前期的政治哲学著作中他也持完全相同的观点,“人性的必然使得人们想往(will)和欲望自身的善(bonum sibi),也就是对他们来说善的东西,规避有害的东西”[10]78-79,“每个人都欲望对他来说善的东西,规避恶的东西”[11]115。更有甚者,他还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论物体》中给出一个更加极端的人性概括,“甚至在子宫中的胎儿也有意愿地移动肢体以规避令其烦扰的事情或追求令其愉悦的事情”[12]407。这几句话在霍布斯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主流的解释认为这典型地体现了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他是“心理自利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的人性论者。其实此攻讦不甚恰当。就人性恶来说,这显然是欲加之罪,因为在霍布斯那里,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他的善恶概念不是传统的道德范畴,而是一个生理学、心理学的概念,并且与个体高度关联,霍布斯的人性论是一个描述和自定义的链条,根本没有善恶评价的空间。下面我们将重点转向对所谓“心理自利主义”定位的讨论。虽然众多学者借此展开对霍布斯人性论的批判,但是很少有学者从正面界定何谓他们所说的“心理自利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一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13]。卡夫卡也认为很难对其进行定义,所以他干脆把“心理自利主义”限定为他所谓的“狭义非最大化的自利主义”(Narrow Nonmaximizing Egoism)[14]44。实际上卡夫卡所给出的描述性标准比较类似于霍布斯学者吉尔特的观点,吉氏认为“心理自利主义”指的是这样的一种主张,即“人们从来不做专为他人利益之事或者因为相信有些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行动”[15]。如果按照这种解释的话,霍布斯显然不是所谓的心理自利主义者,因为他并不否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朋友间的友爱以及仁慈等利他甚至在某些时候会伤害自身的行为。在《利维坦》中,他明确把仁慈定义成“欲望对于他人的善”[4]30,而且不仅如此,人有时还会“欲望对于普遍人类的善”,这被他称为善良天性[4]30。所以他的人性理论与孟子所说的“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16]334相去甚远。但是,如果我们把霍布斯表面上的欲望一直追溯下去,往往会发现表面的、直接的欲望下面存在一个内在、间接和自我的动机,而这个动机往往与自我的考量而不是客观的自利相关联,这不但具有明确的文本依据,而且在霍布斯的传记中也可以生动地看出来[10]24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布斯最多算是一个动机论的自利主义者。如果诉诸霍布斯的方法论,我们对此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除了所谓的“分析-综合”法之外,霍布斯另一个重要的证明方法即是定义法,下面就让我们根据其定义法来推演定义运动的过程。首先,让我们看看霍布斯关于善恶的定义:“那些被任何人爱好或者欲望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善(good);那些被他憎恨的对象和嫌恶,对他来说就是恶。”[4]28其次,根据霍布斯的这个定义以及他心理机械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善就等于爱好或欲望,恶就等于憎恨或嫌恶。第三,我们知道,意志对霍布斯来说,就是“在斟酌中直接导致行动或者不行动的最后一个爱好或者嫌恶”[4]33,从这里可以得出,意志实际上也就等同于爱好或嫌恶,只不过是斟酌中的最后一个而已。第四,综合以上三个定义,“人性的必然使得人们想往(will)和欲望自身的善(bonum sibi)”,其实就只是前一句话的简单翻译或者同义反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吉尔特的论断,即霍布斯的自利主义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自利主义”[15]。
霍布斯的这种“同义反复的自利主义”(或者说动机论的自利主义)与自私自利(或一般所说的“心理自利主义”)存有较大的区别,这种自利主义并不否认客观上的利他行为,比如仁慈、无私的爱以及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等,但这种外在的利他行为根源于主体直接的主观欲望。仁慈是因为我想对他人施善,换句话说,我有施善的欲求,无私的爱是因为我对特定的人有纯爱的欲望。以孟子的恻隐之心为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16]220-221,在霍布斯看来,路人之所以实施这种营救行为,恰恰在于此时其有营救的欲求,如果不实施这种行为,他可能将遭受良心的谴责,至于为什么会遭受良心上的谴责,这纯属个体体验之事,不属于霍布斯的关注范围。无论如何对于这种内在的、根本性的动机,我们很难把其界定为一种自我利益,更别说是物质性的利益了,否则,这样的心理学无法在学术上进行讨论或者没有讨论的意义。学术界之所以对霍布斯的这种“同义反复的自利主义”嗤之以鼻、弃如敝履,是因为他们对霍布斯所说的“善”“恶”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并把他的心理学当成了纯粹的自私自利,当他们以道德、德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的时候,觉得它们是如此不堪入目,如此不登大雅之堂。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与对霍布斯的人生竞赛喻的误解是同样的,都是对概念、定义及其背后理论基础的误解,下面就让我们进入霍布斯的权力观,一探其究。
(二)霍布斯的权力观
除了以上很多学者所误解的所谓的心理自利主义的人性论之外,学者们往往还根据霍布斯的权力竞赛喻来证成他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种权力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明确提出,“幸福是持续地获得一个时时欲望的东西,也就是持续的成功(prospering)”[4]34,“幸福就是从一个欲望目标到另一个欲望目标的持续过程,对前者的获取只是达到后者的手段”[4]57,“人类的一般倾向就是对一个个权力的经久不息的追逐,至死方休”[4]58,等等。据此,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中也应像个人一样,持续地、永无休止地追求国家权力的支配性,也就是国家权力比较间的盈余,因为霍布斯说过,“一个人的权力抵抗和阻碍另一个人的权力的效果:权力就是一个人超过另一个人的权力盈余。因为平等的权力相互对抗和摧毁;它们的相互对抗就被称作竞争”[10]48。我们认为以上现实主义的论证路径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联想,它严重地忽略了霍布斯自己的论证思路和方法。如上文所述,霍布斯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定义法,现在就让我们根据与上文相同的方法来推演霍布斯的论证过程。首先,根据定义,一个人的权力就是“他获取某种将来的明显的(apparent)善的当前的(present)的手段(means)”[4]50,在这个定义中,权力与善联系在了一起,并且霍布斯点明权力只是一个手段。其次,根据上文中的定义我们知道,善就是“那些被任何人爱好或者欲望的东西”[4]28,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把权力与人的爱好或欲望挂起钩来。第三,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人或者说生命与爱好、欲望之间又有何种关系呢?人有没有可能没有欲望的时刻呢?霍布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对他来说,“生命本身即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和恐惧,就像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4]34-35。很多时候人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欲望,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变形的欲望而已,即欲望没有欲望的时刻,而且即使暂时忘却心理的欲望,生理的欲望总是逃避不了的。第四,综上所述,既然人的生命、生活是欲望的运动,而欲望的目的就是善,达至善的手段则是权力,那么,人生的一幅自然的画面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对权力的无休止的追求嘛!可以说权力止于何处,生命就止于何处。由此可见,霍布斯的权力观,只是一个逻辑推演的中介和相对于前设目标的手段[17]145,是自然生命过程机械运动性的表达,其本身不是目的,因此不具有政治的属性[18]442,更难套用到国家身上。在这点上,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对霍布斯的解读毫无疑问是错的,因为无论是卡尔[19]、摩根索[20]67,还是怀特[21]103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霍布斯的这个权力当成了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这是一种误读。霍布斯所说的权力只是自然生命过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根本无法证成无论个体还是国际社会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角逐行为,因为如此一来,权力就成了目的并因而成为了政治性的权力,这与霍布斯的权力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和概念体系。而且,霍布斯的权力观是建立在个体生理和心理基础上的,其根本无法简单地套用在国家之上,因为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人造的而不是有机的、自然的政治体,这与中国古代那种家国同构的、有机性的政治观不可同日而语,和自然人相比,这种国家观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机制,更遑论它的生理机制了。
所以,那种试图借助于霍布斯的人性论和权力观来证成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的路径是行不通的,除非学者们抽离霍布斯的语境以及方法论,只是纯粹运用他的个别结论,这也是霍布斯研究界经常采用的“六经注我”式的霍布斯主义的(Hobbesian)解读方式。但是我们要说,这对霍布斯有失公平,并与之无关。“剑桥学派”“三剑客”之一的波考克(J. G. A. Pocock)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并挖苦某些霍布斯学者:“他将轻声地告诉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说这些话时,霍布斯并不是这个意思,至少并不确定地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发现它对你有用时,你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在你的思想前加上‘霍布斯曾说过’这样的字眼,更不要加上冒充的‘霍布斯说’这样的现在时。诸如‘如果我们在既定的情形下重复霍布斯的这些话,那么接着将产生如下的结果’之类,就更是你的意思了。”[22]对此,我们深以为然。
二、自然状态论与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普遍采用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理论来证成国际自然状态及其潜设的主张,这些主张主要包括国际战争状态以及国际道德与法律的虚无主义,与此相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认为在国际社会,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权力及利益的关系,主权国家一如个人在自然状态中一样,持续性地追逐国际权力的支配地位。
霍布斯在论证完人作为普遍战争状态的自然状态后,确实辅助性地以国际社会的无主权状态来例证他的自然状态理论。他说:“尽管从来没有过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战争时刻,然而国王和其他的主权者却由于相互间的独立,一直处于相互嫉妒和争斗(galdiator)的状态和情势,他们的武器和目光分别指向对方,也就是说,他们在边境线上筑碉堡、派驻军、架枪炮并持续地刺探邻国的情报,这就是战争的情势。”[4]78并且他也确实说过,“暴力和欺诈是战争中两大主要的美德”[4]78。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的自然状态而没有任何国际规范和道德,有的只是国家间的争斗、欺诈和丛林规则,理由如下。
(一)在什么意义上国际社会是一个自然状态
1.霍布斯只是在其自然状态论作辅助性的例证时,提到国家间的关系一如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提到美洲原住民和内战的状况以作为同等程度的例证。但是熟悉霍布斯方法论的人都知道,在霍布斯著作里,其方法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证明的方法,其又可再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子方法,即“分析-综合”法和定义法。证明的方法是霍布斯方法论的本质属性,也是其自称作为政治哲学创始人[12]ix及其学说科学性的根本所在。还有一种是验证的方法,这种验证的方法亦可再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子方法,即社会经验法和内省经验法。验证法或经验例证法虽然作为霍布斯的方法论之一,但它只是辅证性的,而不是证明性的,“尽管一个人始终见证日夜更替,但是其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它们应如此或者一直如此。经验不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10]33。只有严格证明性的方法才是霍布斯政治科学标准和根本的方法,正如马克内利所指出的那样,“霍布斯并没有主张他的通过观察人们如何行动而提出的命题可以获得证明(establish):他仅仅只是声称确证(confirmation)”[17]87。因为例证往往只需要两种或者几种现象共享几个甚至一个特征即可,而事物的一个甚至几个特征,根本无法概括事物的本质,比如内战虽然在权力的实然状态上类似于自然状态,但是它们之间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在内战中,主权并没有从根本上失效,否则霍布斯就不会在《利维坦》的“回顾与总结”中指出,“每个人都有自然的义务在战争中保护在和平时期对其实施保护的权力当局”[4]490。因为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是根本不存在权力当局的,也就不会产生这么一条自然义务。既然内战只是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可以例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那么,美洲原住民和国际社会也只是在某一个或者几个方面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具有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根本无法从科学的严格性上证成国际自然状态论的结论,由此霍布斯只是在战争和无主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方面拿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例证自然状态,而并没有明确认为国际社会就是其所谓的自然状态或者说国际社会的状况符合其标准的自然状态模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霍布斯在上述引文中的那几句例证战争的话之后,紧接着就说,“但是由于他们支持其所属公民们的产业,所以由此不会导致出现伴随个人自由所出现的那种悲惨局面”[4]78。这句话中“伴随个人自由所出现的那种悲惨局面”就是典型的作为普遍战争状态的自然状态,所以霍布斯的这句话实际上等于明确地告诉读者,国际社会不符合他的典型的自然状态模型,“这段引文与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13章中关于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解释比较起来,它提供了一个相似,但非常不同的国家在自然状态中的解释”[23]138。
2.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分为两个层次,即事实状态与规范状态,以及具体的三个阶段,即纯粹事实性的前法权的自然状态I、以自然权利形式呈现的自然状态II和以自然法形式呈现的自然状态III。那么,学者们在何种意义和层次上推论出国际关系的自然状态论,我们似乎不是十分清楚。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推论过程必然也伴随着各种陷阱。因为我们知道霍布斯根据人性的四种要素——体力、经验、理性与激情[11]109——的平等与差异的状况,加之自然状态中资源的相对匮乏,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第一阶段,即前法权的、纯粹的自然状态的战争性事实,进而在这种战争状态下推导出规范性的冲突状态,这个阶段是一种加强版的作为自然权利形式呈现的自然状态,该状态是一种涵括了事实与规范双重性的自然状态,正是这种自然状态的残酷性是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人们才在理性的作用下,找到逃出自然状态的方法,这就是自然法。但是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法是软弱无力的,只能约束人的“内在领域”即良心,而不能始终约束人的“外在领域”即行为,所以这种状况逼迫人们走上主权契约建国的道路,成立主权国家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获取生活的幸福。
以上是对霍布斯契约建国的简单概括,但是从这种概括中,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很难套用这种模型。因为主权国家与个人之间具有许多方面的不可比拟性。比如,在霍布斯那里,人在体力、经验与理性这些硬实力方面是大致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模式并不能直接套用在国家的身上。一是因为体力、经验与理性在个人和国家那里,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甚至我们很难说国家的经验与理性这些概念,比如,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国家理性”问题中“理性”就根本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人意义上的计算理性、语词理性。二是因为即使可以谈论国家的体力问题,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像人与人之间的大体平等一样,是无法以道里计的。像摩纳哥、马尔代夫甚至朝鲜、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无法与中国、美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相提并论。尽管有学者认为,“正如2001年的‘9·11’所表明的,即使国际社会最强大的成员——美国,也能被其中最弱小的成员——一小群穆斯林激进分子——所伤害。当美国睡去的时候,最弱者也能从其背后捅上一刀”[23]180。这段话明显是在模仿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说法,“至于体力,最弱的人也有足够的力量或者通过密谋或者通过与他处于同等危险的人的联合而杀死最强者”[4]74。但是这一事件根本无法证明美国与这一小撮激进分子的大体平等,因为后者付出的是全军覆没的代价,而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只受到了些许的损害。何况,对国家来说,更没有严格的所谓“睡眠”状态。
再比如在规范性的层次上,我们也很难套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特别是那种极端化的个体“对万有的权利”(right to all things)。我们看到,无论根据对当今社会的观察,还是诉诸历史记载,都没有哪个国家主张霍布斯论证过的只有自然人才享有的那种完全自由的“对万有的权利”的自然权利,因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前政治、前社会的状态,而即使没有统一主权者的国际社会仍是后政治、后社会的状态,所以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3.如果我们从反面进行考察的话,假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适用于国际社会,那么,国际社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仍是一个无国际性主权的社会了。因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只是一个理论和逻辑起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在理性的指引下,通过契约建立主权性威慑以结束这种悲惨的自然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严格地把他的自然状态模型套用到主权国家或者主权者身上并将其视作自然状态中的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必然要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主权国家或者主权者要通过建立更高的主权来结束这种作为普遍战争状态的国际性自然状态。如此一来,世界国家、国际主权者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所谓的“国内类比”问题,这也正是英国学派针对现实主义学派如此解读霍布斯所产生的逻辑错位与断裂而给予的致命挑战[24]。世界国家显然不符合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因为霍布斯的意图只是通过授权契约建立一个适度规模的主权国家[4]107,而且更与国际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相悖谬,所以它不可能成为霍布斯甚至霍布斯主义的理论主张。关于这一点,霍布斯的追随者、法律实证主义先驱奥斯丁看得非常清楚。他说:“通常认为,若干独立的政治社会(主权国家——引者注),作为若干完整的社群来考虑,而且就其相互关系来考虑,它们等于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的。……然而,这些观念并非是完全正确的。由于这些相互联系的社会,其各自本身内部的成员是政治社会的成员,这样,在严格意义上,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政治社会是处于自然状态的。更大的社会,也不能因为相互交流的存在,而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社会。……基于各个独立政治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社会,属于国际法管辖的领域。”[25]因此,简单地把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模型套用到主权国家以及国际关系之上,这不能不是对霍布斯自然状态论的乱用和滥用[26]。
综上所述,霍布斯只是在例证或经验验证的意义上指出,比如在没有统一的政府对各国实行足够的威慑等个别方面,主权国家的关系类似于自然状态中人与人间的关系,但是例证不等于证明,类似不等于相同,其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模型并不符合他的严格、标准的自然状态模型。与此同时,英国学派却着重试图借助自然法概念把霍布斯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理性地重构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概念,然后在利益、规则、规范的基础上对霍布斯进行某种格劳秀斯化的解读。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对霍布斯的弱版解读的话,那么,英国学派就是对霍布斯的强版解读,我们认为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概念无法成为国际社会化、合作化甚至家庭化的理性基础,同时混淆格劳秀斯和霍布斯更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大疏忽[27],但限于篇幅和主题限制,本文不做进一步讨论。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虽然其含义并非如著名的霍布斯学者弗朗科斯·崔克德(Francois Tricaud)所声称的那样“是完全不清楚的”[28],但是确实包含着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内涵,其中无政府状态着实是自然状态的一个鲜明特征,而且即使历史的车轮驶至21世纪的今天,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无统一主权和政府的社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姑且可以把国际社会称作是一个国际性的自然状态,只是在使用时,我们必须对其内涵保持足够的警惕。
(二)国际社会是道德虚无主义的吗
现实主义学者普遍认为霍布斯持有这样的主张,即道德源于权力与政治[21]103-104,国家创造道德,国家之外既没有法律,亦没有道德[29]。我们认为这样的主张同样是对霍布斯的严重误读,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如下。
1.自然状态与道德。多数学者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道德真空状态,其中没有什么是不正当的,然后现实主义者以此类推,国家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前者主要的文本依据有以下三处。第一,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明确指出,自然状态作为一个战争状态,其“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非正义的概念,没有存在的余地。没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非正义。暴力与欺诈在战争中是两个主要的美德”[4]78。第二,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定义之后,霍布斯紧接着说了这样一句被许多学者视为道德虚无主义的话,“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名称存在之前,必得有某种强制性权力平等地迫使人们履行他们的信约”[4]89。第三,在阐释完自然法的条款之后,霍布斯这样说道:“自然法约束内在领域,也就是说,当呈现时,它们对欲望形成约束,但是对外在领域,即将它们转化成行为,并不始终如此。”[4]99
以上三处,看似证据确凿,实则不然,原因在于论者或者把它们抽离了霍布斯的语境,或者对它们做了片面的解读,总之都是不成立的。首先,就第一处依据而言,对霍布斯来说,没有公共权力,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这是十分清楚的,这也是霍布斯说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中不是真正的法的原因所在。那么,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法律就没有非正义呢?没有非正义不就意味着正义嘛!那么,为什么自然状态中人的行为都是正义的、正当的呢?这是因为,霍布斯在这里所讲的“自然状态”乃是我们前文中所讲的自然权利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的极端形式就是所有人都具有“对万有的权利”;而权利概念在霍布斯那里又基本上等同于正确、正当,因为“任何不违反理性的事情,人们就或称作权利(right)或拉丁文的jus或者无可责难的(blameless)运用我们自身的自然权力和能力的自由”[10]9,只不过在自然状态中,这种正当是相对的、主观的而不是客观自然法意义上的而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说所有行为都是正义的、正当的。因此,这个依据不足以证明霍布斯主张自然状态是一个道德真空状态,因为霍布斯在这里所用的自然状态概念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其只是我们前文中所说的自然状态II,此时,自然法的概念还没有产生,在这段话之后,霍布斯才重启一章讨论自然法问题。其次,关于第二处依据,我们就更好理解了,因为霍布斯明确地给“正义”下过这样的定义,他说:“当信约达成后,违约就是非正义,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信约。任何的非不正义,就是正义。”[4]89那么,自然状态中是否存在信约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信约达成的关键在于安全问题。当然,这里的安全,正如马尔科姆所正确地指出的,并不是政治国家意义上的一般条件,而是环绕一个个具体行为的具体情况[18]438。因此,在安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在自然状态中完全可能达成具体的、局部性的契约,这从霍布斯所说的“愚夫问题”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来[4]90-92。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指的是整体上的战争倾向,它并不排斥个别的和集团内部的契约现象。既然自然状态有信约的存在,当然就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存在,所以自然状态就不是道德的真空状态。再次,关于第三处依据,其就更不能说明自然状态的道德虚无性了,因为霍布斯并没有否认在自然状态中存在自然法,他只是说它只约束良心,而并不始终约束行为。约束良心,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真正的约束,行为的约束反而并不是本质性的约束,更何况霍布斯并没有讲自然法不约束行为,他只是说自然法并不始终约束行为。同时我们知道,对霍布斯来说,“自然法的科学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道德哲学”[4]100,即自然法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道德。既然自然状态中存在自然法,并且自然法始终约束良心,有时候甚至还约束行为,那么自然状态就不可能是没有道德的。
以上三条依据并不足以表明霍布斯主张国家、公共权力这些建制是道德的前提,自然状态是道德虚无主义的,它们表明的只是霍布斯认为这些建制是执行体现在自然法中的道德要求的需要[14]355。既然自然状态不是道德真空的,而且“国内类比”对霍布斯来说又是无效的,那么现实主义者的解读就失去了文本和逻辑的基础。正如奥斯丁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国际关系毕竟是一种后社会、后政治的关系,其中国家或主权者是必须讲道德的。
2.主权者与道德。以上我们驳斥了那种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道德真空状态的主张,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疑问就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无统一政府的状态,即某种意义上的国际自然状态,会不会形成道德的真空呢?在霍布斯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在霍布斯那里,国家是由主权者代表的,而主权者在普遍的意义上是必须讲道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从规范性上看,主权者是道德的。自然法是永恒的和普遍的,在上帝之下对所有人构成一体的约束,主权者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霍布斯与传统的自然法论者几乎无异。而且,根据霍布斯的第四自然法,既然主权者作为受益第三人接受作为赠与的主权,那么其就有相应的自然法义务不使得赠与者感到后悔,这个义务就是主权者所负担的总体性的“人民的安全”的义务[4]219。根据这一义务,主权负有制定“良法”的义务,而霍布斯所谓的“良法”指的就是“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明晰的法律”[4]229。此外,在其后期专门的法律著作《一位哲学家与一位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一书中,霍布斯更是把自然法与公平,特别是衡平法院联系起来[23]67-84,并声称“国王不受其它法律,只受公平的约束”[30]。所以,从规范的意义上讲,主权者应受自然法的约束,负有相应的道德义务,并且越到后期,霍布斯越是把这种道德义务实体化且与具体的司法机构联系起来。第二,从实然性上看,主权者也是必须要讲道德的。因为主权者的最大利益在于永保主权,而这就要求其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中,必须要细心关照人民的安全这一总的自然法义务以及其他相关义务,这就迫使主权者必须遵守自然法和公平的要求,必须时时注意使主权行为得到人民的支持。试想,如果一个主权者基于利益或权力的虚荣自负而穷兵黩武,不时地发动侵略战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不但违背了主权者保护人民安全的自然法义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既可能将在没有获得保护时另投明主,又可基于自然权利而拒绝履行作战义务。由此可见,霍布斯的保护和服从以及自然权利理论为主权者设置了一个紧箍咒和约束机制,这种约束必然会使其成为一个注重道德形象的主权者。诉诸中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君主都可称得上勤政为民,兢兢业业,殊少肆意妄为,我行我素。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知道,霍布斯所设计的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其标准的自然状态模型,并且自然状态也不是道德虚无主义的。相反,无论从规范性还是从实然性上看,主权者都是一个受到道德规范约束并遵守道德的人。那么,这样一个道德的主权者会不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疯狂地追求国际权力的支配地位,造成普遍性的国际战争状态呢?我们认为不会。因为,第一,自然法本质上是一个和平法,人们在理性与暴死恐惧激情的共同指导下,通过契约建国以走出自然状态的目的就在于取得和平与安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23]224-239。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主权者负有自然法义务,因此,主权者本质上必然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第二,主权者在行使其国际权力时,必然要受到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因为从规范上讲,其主权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从实效上讲,现代主权已经公共化,是一个法律和理性的体系,国家的权力或者说主权者的权力仰仗的主要还是公民的积极配合。这样一来,无论从规范性,还是从实效性上看,主权者在行使其权力时,必然注重权力的合法性问题[31]。如此,这个问题就转换成了人民会同意和支持主权者甚至通过战争的手段去追求国际权力的支配地位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的最大利益在于自保,在于过上和平与安宁的生活。既然是自保,那么经由自然状态战争的教育,在进入政治社会后,他们就不大可能再基于虚荣等激情进行具有侵犯性的行为。因此,他们也就不大可能允许和支持主权者去持续性地追逐国际权力支配的行动。第三,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不仅是单个国家主权建构的理想模型,同时它还是一个国家类型的筛选和过滤机制,通过这一机制,能够在国际社会区分出正常国家与非正常国家,并使前者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现代国际公法,在原则上,是以具有权利和义务的正常国家作为法律主体”[32]。这个正常国家就是被霍布斯理性化与和平化了的契约国家,由这样的国家所组成的主权国家体系,不再可能形成由主权者肆意追逐权力支配地位而造成普遍战争性的格局。因此,贝兹(Charles Beitz)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他明确主张霍布斯“认为国际自然状态是一个战争状态,在其中没有国家有一个压倒性的兴趣去遵守道德规则以限制对更直接的利益的追逐”[33]。此外,那种声称霍布斯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主张[20]36,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三、余 论
这部分我们将结合霍布斯的国际法思想评述那种认为霍布斯主张国际关系去法律化的观点。但是霍布斯毕竟不是格劳秀斯,其并非一个国际法学家,因此在梳理和建构他的国际法思想方面,我们只能根据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和散见于文本中的关于国际法的只言片语做一个霍布斯主义的解读,该部分旨在提供一个霍布斯国际法思想的论纲,目的在于试图从正面说明霍布斯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1.国际法总论思想。霍布斯并不是一个枯坐书斋、不谙现实的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揪心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回应现实的法律和政治哲学家,这也是“剑桥学派”霍布斯研究的一个基本预设。而就在他写作《利维坦》的时刻,为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奠定基本准则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达成,对这一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霍布斯不可能不知晓并以某种方式进行回应。在其代表性著作《利维坦》中,他非但不主张现实主义者所加之于他的那些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主张,更是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提出国际法的概念。他说:“关于一个主权者对另一个主权者的职责,则是由一般被称作万民法的法律来加以规定的,此处我无需对其进行讨论,因为万民法就是自然法。”[4]233这种把万民法或国际法等同于自然法的思想,表面上看来与格劳秀斯不同,因为后者明确地把国际法和自然法予以区分[34],但是如果我们细致地考察霍布斯的国际法思想就会发现,其很多主张很难说是自然法或自然法的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似乎认为在自然法之外,可以基于国家意志或同意另立国际法。不管如何,霍布斯确实认为在国际社会的主权者之间存有万民法的约束,而不是那种无法无天的丛林状态。
2.国际公法思想。霍布斯在文本中,不但在回应“愚夫问题”时提到个人的理性联盟问题,而且他还提到国际社会主权国家间的联盟问题。他认为“在其上不存在使他们都畏惧的人类权力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在其存续期间,不但是合法的,而且还是有益的”[4]153,而国家间的联盟当然就牵涉到盟约或者合约问题,国家联盟正是国家间通过契约进行合作的一种方式。霍布斯非但主张有时候国家间通过条约达成联盟,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且认为一个国家即使基于恐惧同另外一个强国达成一个不利的和平条约,该国的主权者也有义务履行之[4]86。
3.国际私法思想。霍布斯在《利维坦》和《对话》中,都用了不少的篇幅谈论各种形式的国际商业合作问题,并认为这种私人性质的国际商务往来,不但在很多的时候是合法的,而且还是有益的。而既然是国际性的商业合作,那么必然牵涉其中的国际私法或国际经济法的问题,正如著名的霍布斯学者马尔科姆在其著作中所说的那样,“贸易需要一个商法体系,借此不同国家的公民可以提起诉讼和寻求赔偿……并且在主权者与主权者这个层面,霍布斯同样认识到存在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程序处理诸如赔偿金的支付之类的问题”[18]452。由此看来,霍布斯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35],没有考虑到这一层面的国际法律问题。
恰恰相反,霍布斯明确主张国家间可以通过契约、条约等方式进行贸易和结盟,如此一来,主权国家必然顺理成章地要受到这些国际性法律的约束。或许有学者会质疑,认为这些限制主权行为的国际性法律规范,违背了霍布斯的主权绝对性原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是主权绝对性主要是指主权者意志的不受外在限制性和自由性,包括主权的最高性、不可分割性、自然性、永恒性、吸附性和统一性[36]。它并不排除主权者之间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自愿地达成契约以进行主权的自我节制,因此并不违背主权绝对性原理。既然主权者可以通过契约进行协商以建立国际性法律,那么毋庸置疑,主权权威就要受到这些国际规范的节制与约束。虽说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只约束人的内心并不始终约束人的外在行为,但是正如上文所论证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它是一个后社会、后政治的存在,因此,其自然法和国际法是一体约束包括主权者在内的人的内心和行为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国际规范的约束力毕竟不同于国内法,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到了今天,国际法的执法环境依然不尽人意,但是主权国家或者主权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国际性法律是对其的一种制约,起码没有国家明确站出来,声称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法,并主张那些现实主义者的国际关系观。
现代学者往往基于霍布斯的人性论和自然状态理论,认为霍布斯主张主权国家间的关系符合他的自然状态模型,其中没有道德和法律,有的只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无休止的争斗与战争;因此,他们认定霍布斯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然而,综合以上所述可知,首先,根据霍布斯的方法论,其人性论不是“心理自利主义”而是一种所谓的“同义反复的自利主义”;其权力观不过是自然生命机械运动过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权力在他那里仅有手段而不具备目的和政治属性。其次,学者们往往并不清楚霍布斯在何种意义上把国际社会看作一个自然状态,其实,他只是在经验例证的意义上把国际社会的某些方面比作自然状态,而这不是霍布斯政治科学的根本方法。即使退一步讲,纯粹的自然状态在他那里也不是一个规范的真空状态,而是具有道德和法律属性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后政治、后社会的存在,主权国家间的关系由于受到自然法和契约国家论等理论的制约,它必然不可能是道德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故那种认定霍布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至少为现实主义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的主流理论,是对霍布斯理论的误读和误用。霍布斯是一个和平主义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