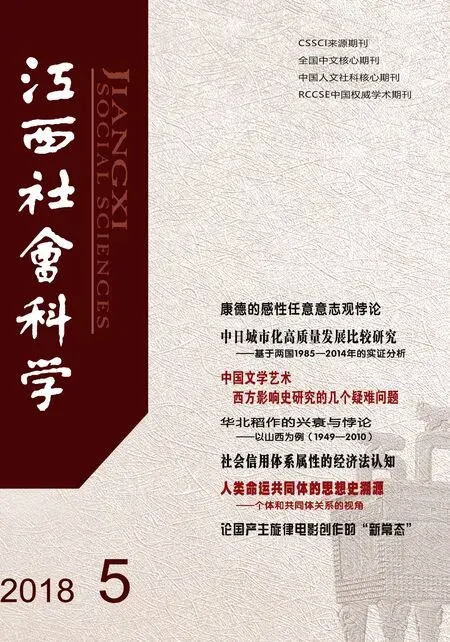消费时代电影的审美维度
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作出世界进入“消费图像时代”的预言。[1](P139)“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商品经济日益繁盛,消费已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消费社会形态率先成型。当今社会,消费符号功利性意义已成大众文化消费审美心理追求的主流,大众文化也不负众望,其为满足人们功利性消费心理已把感性审美的特质做到无缝对接。当前由于电子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文化的传播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先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纸质媒体逐渐边缘化,而互动双向个性化的电子图像媒介成了传播主流;加之消费主义语境下追求显性欲望以欢乐释放的感性审美为主流, 审美文化的“消费体验”的功利性转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的审美在科技美学与体验美学的引领下进入功利性审美的新阶段,这充分体现在电影审美上。
一、电影审美范式的调整:从形而上学走向形而下学
传媒技术及数字虚拟技术的广泛应用,其主要文化形态是技术之“真”的各式影像文化。这类影像文化的消费属性就是一味消解语义深度,只追求图像式的感官快乐。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像文化以追求感官快乐为主导,并极大冲击审美过程的理性反思, 从技术上让消费者张扬个性的审美表达变成现实。加之市场逻辑的横行,消费神话无处不在,它一面以感性的技术之“真”的图像化作品来满足人们的消费体验,同时又用世俗化的方式不自觉地去溶解精英文化,使其纳入消费的范畴,变成市场中消费者的体验对象。消费时代的文化市场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境况,以往孤傲权威的精英文化逐渐褪色;与之对应的审美潮流是消费者审美思想逐渐替代精英权威审美的泛审美趋势,也使个性化体验式美学成了泛审美时代的主流审美思想。
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实质上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狭隘圈子。[2]当然泛审美绝不是简单的低俗,而是大众审美的自我满足形态表现,通过本体的感知和客体生活经验的有效融合,来张扬人的审美感性,从而实现个体对客体主动的审美亲近。
大众电影新世俗神话出现在消费时代文化泛化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由于审美泛化导致艺术审美价值评判产生了变迁,倒逼电影艺术去寻求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综观近几年票房高的电影,大多都是以快乐为消费卖点的大众电影,其大多有别于经典电影对观念和思想的痴迷,而是致力于感知幻象的创意以让受众获得参与体验的快感,这种创意承载的内涵本质上是一个满足消费者欲求的虚拟性“消费物”。也就是说影片的消费意义指向形而下的肉身本我,以当下的快感体验求得欲望释放的快活,而不在意影片思想深度的挖掘和艺术价值的考量,也不求心灵的升华与精神触动。如果对审美泛化时代电影艺术试图寻求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的宗旨作一个归结:即满足形而下的快乐体验。其泛化的路径就是通过视觉体验到感官体验再到行为体验的不断递进过程,演绎了审美泛化的发展趋势,并表现出三种典型的电影审美调整范式。
第一,幻象范式。幻象范式的主要表现是影片致力于制造形式多样的以身体幻象为核心的形象符号,以吸引电影消费者的眼球。导演在电影中有意制造出身体的幻象,突出明星的风采,尤其是女性的性感惑魅,使影片中的情节设计、背景表现、艺术风格等都可能让人视而不见,但像奥黛丽·赫本的美丽、玛丽莲·梦露的性感却可能永远历历在目。消费时代性感明星成了各种媒体追逐的对象,也成了电影市场上不可或缺的形象消费,它既能虚幻满足人类本体欲求又是电影产业的重要卖点。
第二,暴力范式。暴力美学是消费时代下产生的一种感官消费的大众审美潮流。暴力范式电影充分运用数码技术介入摄影艺术中,集合着强烈的光、电、图、声、音的感官冲击,通过技术和艺术手段的加工把原生性的自然真实变形为绚美迷人的艺术真实,“武打、枪战和爆炸”等热暴力场面同“血腥、惊悚、恐怖”等冷暴力元素交互渲染,形成极具视听冲击力的感官效果。影片中经过想象加工的浪漫化的暴力图景,把暴力本来充满肃杀、乖戾之气的丑一扫而光,达到化丑为美的艺术效果。
暴力范式无视暴力带来的社会道德指责,也不对暴力自身理性反思,只一味地娱乐张扬,强调感官刺激,忽视对主题意义的追索,消解深度,表面形式的绚烂之极与思想内容的缺席构成后现代娱乐景观。其所迎合的是消费时代的感官消费潮流,把审美拉下高高的神坛,使美学趣味趋于大众化和通俗化。
第三,游戏动漫范式。虚拟现实技术的快速普及使视觉艺术鉴赏的行为体验成为现实,这就使游戏动漫范式电影在市场中异军突起。玩家可技术性地对电影主旨的审美表达进行拆解、加工和生发,从而重组出无限可能性,电影观众拥有对影片信息再加工的无限自由。观众对电影故事走向的自由选择实现了审美的民主化,对传统以权威为中心、观众只能被动接受叙事的审美形式造成极大颠覆,而个性得以张扬的体验性审美跨上前台。
神权美学向科技美学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符号与指涉的关系被粉碎。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通向一个不再以真实和真理为经纬的空间时,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于是仿真时代开始了。[3](P333)在仿真状态中,我们很难去分辨审美主体始终如一的审美心理、情趣和标准,而只能认真辨析审美主体流动自我在仿真审美情境中的个体体验。游戏动漫范式的行为体验是有我和无我高度融合的交互过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观众”在游戏电影中实为“交互者”或玩家,玩家在玩与被玩的交互娱乐中,凭自己真实的力量和引擎技术的把控能力构建一个虚拟化的多维审美空间,影片审美空间的设计既要忘怀一切,情投其中;又要有情节的跳动变化,玩家可以由个性化的意愿创意影片不同的结局,这种融合意愿和情感的创意体验,使人的心性也随情节的书写同步得到升华,营造了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游戏电影审美体验的价值就在于身临其境完美感知,在互动的过程中进行审美体验,达到心境和谐、情怀自适的境界。
大众文化中的电影艺术依靠数字网络技术制造身体幻象,设计暴力场景,提供动漫游戏化的行为体验,致力从视觉、感官、行为等层面来克服大众心理的焦虑,虽然它也许是趋时媚俗的,但受到文化消费者的青睐,并造就了大众电影新世俗神话。电影的新世俗神话的创造,主要是体验论美学崛起产生了强大的市场解构力量。由于体验美学第一次把审美对象的客观性和审美体验产物的主观性辩证合一,使体验美学和体验观念成了消费时代电影新世俗神话创作的主要推动因素。“美既不在心也不在物,美只存在于主客体的意向性关系中。‘美在体验’,亦即对象的‘美’通过‘主体’的体验才能得以呈现。”[4]以邱秉常的观点来看,唯体验才有艺术是消费时代消费者接受电影的不二法则,体现自我或我在其中是对电影观众的本体意识的充分尊重。这与以导演为中心的权威意识形成了偏差和矛盾。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科技美学的技术解构力量。数码技术对摄影艺术的介入提供了消费手段,从影像构成方式和摄影观念上都为传统摄影带来鲜活的艺术语汇和时代变革。数码摄影因其表达方式的前卫性和先进性,突破了传统摄影的想象疆域和艺术规范,从而引发了数码影像审美观念新变化、新的视觉冲击和崭新想象空间。如近几年票房高涨的《蜘蛛侠》《闪电侠》《魔兽》《捉妖记》等影片都有鲜明的动漫游戏气质,其故事审美样式的以娱乐为中心,叙事表现以非线性的技术化手段来呈现图像化审美意象,从而实现观众和影片一种互动性的审美感兴,它从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以往传统电影艺术的线性美学范式,最大限度地去满足观众宣泄和娱乐体验需要。
大众电影新世俗神话是在前所未有的高科技合成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强力支持下,基于新型的编码与解码的文化信息理论,在当今泛审美时代的核心思想体验论美学支撑下形成的,其美学新视点是视觉转向,其主要作品形态是高品质的、总带有虚拟性和感性的影像体验形式。[5]技术之真和体验之美达到完美结合,编码与解码的影像信息处理中观众得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人们借助它们对抗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压力、技术控制和文化霸权,实现了情感宣泄与心智娱乐,用来排解现实社会的压抑。当代大众电影以泛文化倾向试图寻求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以实现蕴含追求感官享受以及经典艺术深度消解的通俗化传播。
总之,从传统美学的形而上学视角审量,新世俗电影的审美意蕴和神学美学的先验的预设性是相抵触的。当代大众电影审美趣味的世俗化是一种反美学现象,也是审美自律的放任;其在满足人们的体验快感的同时,也将钝化文化消费者的艺术感觉力,导致消费者审美、情感和心灵的疲劳,不自觉沦为消费时代的文化审美麻醉品。
二、电影审美之维的寻绎:感性之乐与理性之思
电影美学是建立在精神共享和文明分享的基础上的,而以受众感性体验为代表的当代审美范式的电影艺术,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消费社会特有的商业化的轻浅与情性,而缺乏震撼心灵和深度永恒的“体验”。这不免引起人们对以体验为代表的当代电影审美范式的重新审视。
实际上当代电影审美范式纠结着消费时代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和艺术现状等四重背景因素,在其每一种范式表现中都有四重背景的交互因果逻辑。消费时代哲学正在失去以往的纯正理性而趋于世俗生活的感性,表现出尚用崇实的拜物倾向;而宗教的终极价值追求放弃精神信仰的执着热衷于物的冥想,感性的判断代替理性的顿悟,从形而上的现象变成形而下的现象;社会心理最突出的变化则是一切都感性化而放逐理性。当代电影艺术在如上哲学、宗教、社会心理诸因素的裹携下放弃了审美的自律性,屈从于消费逻辑和技术逻辑,使电影艺术律艺性得到空前的淡化而律物性渐行渐近,电影的审美也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向新型的受众身心消费范式。
电影审美范式的转向首先导致了审美主体的变化。由于电影、电视、网络和手机已成了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电子消费,电影审美也从特定的“文化圈”走向普通的“平民圈”,审美主体也由精英变为大众。与此同时电影审美范式的转向也导致审美性质的变化,电影审美对表层化、娱乐化、感官化的过度追求,使审美过程由“凝神专注”式冥思转向了“读图消遣”式接受,结果是电影审美感性化和消遣化得到强化,而电影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少甚至时常消失。
由于电影审美范式的审美主体和审美性质等美学细节的变化,促使电影从追求精神升华的传统审美理念里走出来,而把电影受众读图的快感作为审美表达,以平面时尚来消解深度的审美风格作为电影审美的主流。因此,那些有思想性、意境性和个性化的作品受到冷落,而那些满足形而下享受和感官欢娱的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就偏重形而下感性娱乐审美风格的当代电影审美范式而言,它漠视提供对世界的理性反思,而热衷创造娱乐,迎合受众,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
问题是电影一味以消费形象为快乐作为宗旨是否会在“审美物化”中丧失其自省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消费时代的电影已显露出物化的力量和结果——当代电影以身体幻象、暴力刺激、游戏品玩作为“形象商品”,推销给电影消费者,是超前满足电影受众的消费体验和占有欲,但人们购买的虚幻体验也许只能短暂的释放焦虑和失落,却很容易使人与真实自我相异化。因此,生存在充斥物化力量消费时代的电影艺术,应理性倒转审美泛化表象短暂快乐与受众内心永久失落的落差,弥合文化感性消费与文化理性审美之间的鸿沟。对此,美学研究者王一川建议:“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使其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6](P314)所以,大众文化当然不需要排斥娱乐化的感性包装,然而只有娱乐包装是轻浅的。灵动的娱乐只有和文化深层的底蕴进行巧妙融合,才有艺术魅力。
当然,具有娱乐化感性包装的大众电影,它从客观上关注人们的生存体验释放了人们的心灵焦虑,使人们的感性解放得以实现。大众电影以感性图视化来凸显人的身体,突出视觉功能在审美中的地位,丰富了人们的艺术感知模式。大众电影从平民文化消费需求出发,着重感性审美的表达,作品受到消费者近乎狂热的追逐。但另一面的精英电影,由于其秉承了理性的思辨叙事风格,反映社会生活充斥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和载道意识,其市场处境则显得冷清得多,大众电影和精英电影的消费情形呈现两极化态势。
不过应当清楚大众电影更符合文化产业的一种生产类型,它必须满足观众的消费心理,让消费者高兴买单来赚取市场利润,其只专注当下受众的感性诉求而无视消费者的理性关怀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消费时代的社会大众由于生活工作的压力,内心很容易陷入孤独和焦虑,其流于表面的感性的文化消费狂欢,实际上是怯于内心的理性的思辨,只是短暂的孤独情状的消解和麻醉。这就给了冷寂中的精英电影继续执着守望人类精神理性的理由,因为精神理性是文化的内核,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人文价值关怀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价值关怀的审美维度上大众电影和精英电影存在明显的审美价值的悖逆,从而导致电影审美文化感性之乐与理性之思的冲突。
完整生命体的人在认知社会的过程中,都是理性感性的二重并行。因此,在电影审美实践中,不能只一味强调尊重人的感性,而无视感性和理性的艺术结合。当今电影漠视理性、过度地张扬人的感性体验,是有悖“美的规律”内涵的,也是社会大众体验疯狂后却难掩内心焦虑的根本原因所在。消费时代电影审美之维的重构应在丰富的生活环境中找到表现人类自我的最佳契合点,“凝神关注”地甄别消费主义语境下雅俗混杂的视觉信息,防止审美的物化,避免陷入消费时代视觉纷乱的困境,在审美的独立与理性自觉中提高电影的艺术品位和境界。只有感性之乐和理性之思二元维度的统筹兼顾才能使当代电影走出电影文化的非艺术性、过度趋利化、过度娱乐化、过度符号化的消费怪圈,从而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
三、结 语
面对处于感性与理性审美之维悖论中的电影艺术,也许只有强化消费语境中的理性因子才能制衡其被市场逻辑所引导的轻浅和狂嚣。审美维度的寻绎必须强化理性之维的找寻,应从四个维度进行拓展,即对电影作品审美要看其是否有一种人生的生命价值考量具有一定的哲学高度;要看其是否注重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和时代环境的兼容性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要看其是否表达对生命个体精神世界在现实中破灭的强烈同情具有一定的感情强度;要看其是否除了感性图像化呈现的同时还不乏情感的诗意升化具有一定的美学向度。与此同时再将虚拟网络科技带来的新型审美想象力元素和文化平民化元素发掘出来,“引导其超越欲望宣泄造就的肉身快感,弥清仿像审美造成的视觉迷失,实现肉身与精神的完美统一”[2],那么消费时代的大众电影将前景辉煌。
[1](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2]傅守祥.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J].哲学研究,2006,(2).
[3](法)鲍德里亚.仿真与拟象[M].马海良,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邱秉常.数字动画艺术与体验美学[J].山东社会科学,2010,(4).
[5]傅守祥.泛审美时代的快感体验——从经典艺术到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转向[J].现代传播,2004,(3).
[6]王一川.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