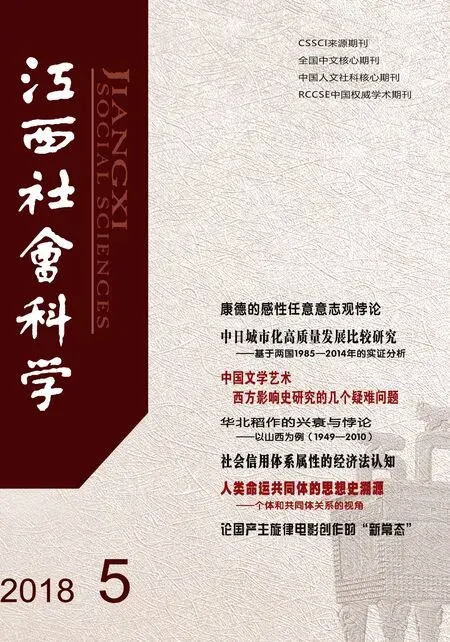华北稻作的兴衰与悖论
——以山西为例(1949—2010)
山西省的稻作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时期,《诗经·唐风·鸨羽》即有“王事靡,不能艺稻粱”的记载。[1](P129)此后,经汉、唐、宋、元、明、清之累代发展,其种植范围一度扩展到全省62个州县[2],并培育出在中国稻作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晋祠稻”,且以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意义而被历代文人骚客所赞美。[3](P397-410)因此,山西稻作史也经常被学术界提及,并产生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看,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个突出的不足,即缺乏对1949年以后稻作史的足够关注(就以笔者所见,目前仅有田雨等人的个别文章有所涉及[4])。事实上,这段历史虽然相对短暂,但其变化过程之剧烈与复杂,以及由此而反映出的生态、技术、市场、社会、政治等诸问题,却更富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更值得思考与探讨。
一、集体化体制的建立与山西稻作发展的历史高峰
1949年后,政府把增加粮食产量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长期任务,对此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努力,其中,水稻作为高产作物,又被寄予了厚望。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发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要求各地“多种高产作物”,特别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并提出要在12年内增加稻谷2.5亿亩的计划。[5](第10册,P633-657)1958年春,农业部在天津团泊洼召开的“北方水稻增产促进会”也强调,“大量改种水稻是迅速提高淮河以北低产地区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提出要在1957—1962年间使北方地区稻作面积发展到3亿亩,使稻田面积占比达到北方粮食耕地总面积的40%左右,“使常年受旱涝威胁的粮食低产的北方,变为和江南一样富饶的鱼米之乡”。[6](农业卷,P543-550)据此,政府在北方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稻改运动。山西因有悠久的稻作传统(尽管规模和产量有限),也把发展稻作农业作为其工作重点之一。它所制订的“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即把水稻纳入其重点推广的三大高产作物之列,并要求在规划期内稻作面积要由8.55万亩增加到60万亩,其中晋南地区要达到12万亩,晋中18万亩,晋东南5万亩,晋东3万亩,晋西2万亩,晋北20万亩。[7]山西省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实现这一目标。
(一)借助集体化体制,扩大稻田面积
历史上,太原、临汾等地就是山西的水稻主产区。随着北方稻改运动的兴起,这些地区也成为其推广重点。以1959年为例,太原市的计划比1954年的面积增加28.5%,单产增加159%,总产增加233%。[8]晋南地区的计划比起1958年面积增加了46.3%,亩产增加了153%,总产增加了128.3%。[9]特别是随着以计划经济为基本指导思想的集体化体制的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山西水稻种植推广到了全省80多个县区。[10](P266)这种以指令性计划维系稻作生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甚至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废止后,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1985年山西省给太原市下达了500万公斤的稻谷定购任务,尽管定购是采用合同形式的,看上去是自由的,但事实上这个指标是被作为任务逐级分解下达的,并强调各级政府监督执行,强调稻谷生产必须首先保证定购任务的完成。[11](P42)可以说,没有集体化体制的支撑,山西的水稻种植规模是无法维持的。
(二)开展水利建设
水稻生长的特性决定了其对水源条件的高度依赖性,能否提供充足的水源,也就成了能否实现稻改目标的先决条件。集体化时代的山西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不少与稻作生产直接相关。以太原为例,到1985年,水浇地面积由1949年的37万亩增加到81万亩,“平川地区基本实现了水利化”,为水稻种植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水源,尤其是汾河水库的建成,大大提升了稻田灌溉能力。据资料记载,1979年汾河水库的蓄水量达到36 370万立方,这是其建成以后蓄水量的历史峰值[12](P276),次年,太原市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峰值[13](P61-62、P94)。两者间的关系,不言而喻。
(三)稻作新品种的引进、改良与推广
从理论上说,一个好的农作物品种既要具备广泛适应性(即在不同气候条件下都能实现高产),也要有特殊适应性(适应特定的不利环境的能力,即与那些生长在最适条件下的品种相比,其生长所受环境的影响极小)。水稻尤其如此,它的这种特殊适应性就包括对深水、含盐浓度、低温、高温或干旱等不同条件的适应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特殊适应性是其获得高产的先决条件。[14](P2)因此,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优良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推广,对于实现稻改计划,也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山西提出了“良种普及化,栽培区域化,品种多样化,管理制度化,用种质量标准化”[15]的指导思想,并针对性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引进和推广新品种。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西引进的水稻新种就有14种之多,在其全部水稻品种中占比近80%。[16](P54-62)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还重点引进并推广过原野2号、十和田、东北杂交稻、“黎优57”杂交粳稻等新品种,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7][18]
(四)推动水稻栽培技术的改进
这方面的措施比较多,从生产流程来说,大致包括:一是在播种技术上,推动由“直播法”向“育秧法”改进;二是在育秧技术上,先后推广“湿润育秧”、“塑料薄膜拱棚育秧法”、“水稻温室无土育秧”等新技术,替代传统的“水育秧”技术,并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19][20];三是在田间管理技术上,持续推广新的浇水、施肥、除草、晒田、烤田、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提升稻作管理的专业化与精细化水平。①
在上述诸多措施和工作基础上,山西的稻作业逐步发展,尤其是1970年后的发展尤为迅速,并在1980年达到其历史最高峰(参见图1)。是年,山西省水稻播种面积达到18.33万亩,稻谷单产达到378公斤,总产达到69 290吨,分别是1949年的2.41倍、3.09倍和7.44倍。[10](P264-266)个别地区发展尤为突出,如太原市1980年的水稻播种面积达到10.53万亩,亩产达到429公斤,总产达到45 200吨,分别是1949年的3.26倍、3倍和9.78倍。[13](P97)

图1 1949—2010年山西稻作业兴衰趋势图
二、市场体系的重建与山西稻作业的历史最低
然而,图1又清晰地显示,在达到上述高峰后,山西的稻作业随即转入持续衰退之中。统计显示,到2010年山西水稻播种面积只剩下1.56万亩,稻谷总产量仅有4615吨。[21](P263)这一数字不但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要低很多,甚至远低于抗战前,仅相当于其1936年水稻播种面积的16.96%,稻谷总产量的32%。[10](P264-266)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的发生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巨变有着直接关系。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影响最大。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冲击了山西稻作体系的既有政治与社会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农村推行开,到1983年,该项制度已经在山西全省范围内99%的农户中建立起来。[10](P20)新体制把经济效益的提升放在首要位置,以市场化为发展方向,从宏观和微观等多个层面冲击着集体化体制支撑下的稻作经济。
从政府层面看,一方面,由单一强调粮食生产转向发展高附加值作物,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尤其是在一些具有稻作传统的城郊地区,新的发展战略更多地定位于向城市提供优质多样的农副商品。以太原小店区为例,该地传统上也是重要的水稻产地,但新体制下,当地政府更多地强调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尤其是蔬菜生产、健康养殖、农产品加工和休闲观光农业等。[22](P4-5)受此影响,粮食作物面积不断下降。1998年尚存留4725亩,到2003年则只有300亩,2004年后则彻底消失了。[23](P139、P262-267)另一方面,粮食征购政策的逐步废除,也解除了对农民生产方向的束缚。根据新政策,山西省自1985年起取消了对稻谷的统购,改为合同订购,并不断减少定购数量。1992年后更是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农民已没有来自政府的稻谷生产任务与压力。此外,新体制下地方政府显著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使得大批水利工程设施得不到及时更新维护,大大降低了供水能力。[10](P8)对于高度依赖水利体系的水稻种植业来说,其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从农户层面看,新体制下农民从集体化体制下的单纯的产品生产者,逐渐转变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10](P6-7)自家地里种什么作物甚至包括要不要继续种地,完全是农户基于经济理性和市场理性的一种自主选择。事实上,这种现象也被课题组②在一些传统稻作区的调查所证实:随着生产成本的提升,许多农民开始放弃水稻种植而转营其他行业。关于这点,后文再做详述。
(二)城市化和工业化深刻地瓦解了稻作经济的生态基础
就城市化来说,主要表现为城市扩张造成的对稻田的大量侵占。以太原为例,据统计,1949年时市区人口只有21万,面积只有30.11平方公里,但到1990年时市区人口已达163万,面积达到194.7平方公里[24](P284-285),分别是1949年的7.76倍和6.47倍。城市扩张所占多系周边粮田,其中就包括许多稻田。南郊区是太原主要稻谷产区,著名的晋祠稻就在这里,它曾一度负担着全市90%以上的稻谷征收任务。[11](P578)但随着城镇发展及各种建设用地的增加,该区平均每年减少耕地3000亩。[23](P26)与此同步,整个太原市的水稻种植面积也开始逐年下滑,到1996年时已只剩下3.875万亩,仅相当于其鼎盛时期的36.79%。[25](P215)要知道,太原一直是山西水稻的主产区,一度曾达到全省种植面积的60%;它的急剧萎缩,对全省稻作业形成了极大冲击。
就工业化来说,则主要表现为对稻作水源区的破坏。山西属于山地型高原,素以“十年九旱”著称。[26](P6)但在这样一个地理与气候环境下,其稻作传统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实际上是与其个别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关系,这就是在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地的断陷盆地区,因地质构造运动形成了一些河谷地带以及一些富含地下水的泉涌地带,为水稻种植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水源。[4](P19-20)但1949年以后,随着工农业的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剧增,这一特殊生态结构受到根本性破坏。太原晋祠稻的兴衰最为典型。
晋祠稻主要是指以晋水灌溉为依托的、以晋祠镇为中心的附近村落所生产的稻米。晋水发源于太原西南25公里的悬瓮山山麓下的难老泉,后汇集善利、渔沼等泉水,蜿蜒东南数十里,注入汾河。这些泉源多属冷温泉,常年水温17.5℃左右,富含明矾等各种矿物质[11](P16),流域内“土壤肥沃而略带碱性,是北方地区少有的适于农耕的‘水田沃土’”[27](P139)。因此,这里很早即有种稻的历史记载,并在历代官民努力下不断发展,其最盛时晋水流域90%以上的农田都种水稻[28](P78),所产稻米也以品质优良而享誉全国。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晋祠泉域内的工矿业开发不断加快,水资源消耗量急剧攀升,地表水大量截流,地下水超量开采,使晋祠泉系迅速瓦解。到1972年时,善利泉和鱼沼泉干枯;1994年后,晋水源头难老泉也彻底断流,晋水干涸。[25](P364)起初,人们还曾试图通过回收利用工业废水、农田退水、小泉沟的河水以及井水等勉力维持稻作规模,但终因费用太高且稻米品质显著下降[29](P202),多数稻农不得不改行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等旱作物[28](P170)。
(三)市场体系的发展提高了稻农生产成本,削弱了其比较优势
如众所知,与旱作物相比,水稻的种植有四个鲜明特点:一是灌溉需水量大,通常是普通旱作物的2-4倍[30](P242);二是劳动强度大,一般情况下老弱妇幼人员做不来;三是专业性强,技术水平要求高,耗时长;四是肥料需求大,远远超过以单个家庭为基础的农家肥的生产能力。集体化时代,这些问题都由生产队负责解决,农民只是一个单纯的、被安排的劳动者,不用考虑成本效益问题。但随着市场体制逐步建立,这些问题都转变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和市场要素而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特别是传统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水利体系向市场化转向,促使水资源日渐紧张,灌溉成本大幅度提升。以前述汾河水库为例,该库在建成后的头20年间(1960—1979),一直是无偿向下游灌区供水。但1980年后,它开始向“自收自支,定额上缴”的独立经营单位转型,供水政策随之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是对农业用水开始计量收费,不断提升收费标准,在短短15年间就提高28.57倍;另一方面是不断减少对农业用水的供应量,农业供水在其总供水量中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2007年曾一度下跌到55.63%。[12](P135-136、P199、P273)这些政策的调整,严重冲击了由该水库支撑的稻作生产。
与此同时,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则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以晋祠村为例,该村地处晋水源头,村内大部分耕地为水田,传统时代主要种植水稻和莲菜。但据调查,自20世纪90年代后,该村村民们种地的兴趣越来越小,更多地借助地处晋祠风景区的便利进行商业化改造,发展旅游服务业,到2005年,整个村子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晋祠村民“已经田无寸垅了”[28](P57-61、P170-171)。本课题组在晋祠镇进行相关调查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例如,曾经著名的稻作村落南大寺村、小站营村“已经完全不种植水稻”,北大寺村只剩下130多亩,长巷村只剩下60亩左右。出现这一状况与劳动力短缺有直接关系,年轻人大多选择出去打工,“没人愿意干这种费时费力且经济效益又低的农活”,剩下的稻农年龄基本都在60岁以上,且越来越干不动农活了。
此外,粮食市场全面开放后,大量南方所产质优价廉的大米进入山西市场,当地消费者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也大大缓解了当地的市场供给压力。
三、长时域下稻作业中的悖论现象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以上兴衰历程的还有一系列值得关注与思考的悖论现象。
(一)稻作业的兴衰与稻谷商品率的高低成反比,特别是在稻谷产量持续增加时,稻米的市场供应量反而持续走低
“物以稀为贵”。由于产量的稀少,稻米在山西市场上成为紧俏物资。因而,历史上其商品率也一直很高。据1936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该年度山西全省水稻产量的2/3以上销往外县,极少部分还销售到邻省,而在产地县内销售者不足1/3;个别县的外销率更高,如灵石达其总产量的83.61%,太原达到73.49%。事实上,如果单从调查统计的纸面信息来看,其商品率几乎100%,也就是说,山西的水稻生产是面向市场的。[31](第五编,P335)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一个类似调查,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山西稻作经营上的这一特点。据其调查,岢岚、石楼、河曲、偏关、平鲁等县所需稻米全部购自太原、崞县、汾阳、代县、原平等地;洪洞、朔县等地所需稻米的33%购自安泽、屯留、赵城、代县等地;与此相应,代县、临汾、襄陵、赵城等县所产稻米多半都销往曲沃、汾城、安邑、永济等地以及雁北各县。[32]
1949年后,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两点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其商品率的波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53—1961年间,年均达到64.2%,应该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与民国时期差别不大;二是1960—1980年间,年均16.12%,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三是1981—1990年间,其商品率又逐渐回升,年均达到45.28%。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商品率比较高的时候,多系其种植规模和产量都比较小的时候;反之,其商品率比较低的时候,则多系其规模和产量都比较高的时候(参见图2)。出现上述现象,无疑与集体化体制的兴废有直接相关,但其复杂性又远非后者所能解释。

图2 山西稻谷产量、播种面积、商品率之折线图比较(1953—1990)
(二)产量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预期中稻米消费的大众化,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产量的稀少和价格的相对较高,决定了在北方地区的历史传统中,稻米是一种特殊的消费物资,具有鲜明的贵族化甚至是政治化的群体性特征,普通百姓则很少有机会和条件食用。因而,中国北方地区很早就有“贵人食肉稻”的说法。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山西地区。光绪《五台新志》即记载:“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33](卷2《风俗》,P62)民国《山西省志》也有记载:产量微不足道,“区区之数仅供上流阶层食用……即使城镇居民,食用大米者亦不多见,只在商业繁华地区才有大米出售”;又载:“粳子碾成粳米(或大米),蒸干饭或熬稀饭,主要供上流阶层经常食用或过年过节、款待宾客时食用”,“糯子碾成糯米,通常用来给神佛上供”。[34](P223-2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稻谷种植规模、单产量与总产量都有成倍的显著增长。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稻米消费的大众化趋势,而是继续延续着其历史特征,且更具有制度化的特点。发生这一现象,固然有其客观原因,即总体上看,稻米产量在当地整个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仍然比较小,仍然属于稀缺物资。但从主观上看,更直接的原因还是政府的相关制度安排所致。具体说:一方面,对本地稻谷生产与征购工作的长期管控。例如,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山西省政府就规定:“种植商品性较大的稻谷等作物的农户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其应统购粮食的计算与其他农户同,所余之稻谷,按周转粮处理。即除留给稻农足够的种籽和一部食用稻谷外,全部售给国家,由国家兑换给同等数量的粮食。”[35]根据这个政策,其稻谷征购比例曾一度达到全省稻谷总产量的89.5%(1959年)。[10](P264)至于晋祠大米、府西大米等当地名产,更是绝大部分被征调入城市内消费。[11](P86-87)甚至在统购统销政策废除后,山西省及太原市相关部门仍采取诸多措施控制稻谷的流通,例如,它规定实行大米专营,在合同定购期内,“一律不准集团性、批量性采购”,并特别强调大米等定购品种“一律不得出省,以确保本市需求”。另一方面,实行特供政策,即只对部分特殊人员供应大米。这些人员包括住院病人在医院就餐者、特等革命残废军人、出生和原籍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国家正式职工、朝鲜族职工、航空学校空勤人员等。[11](P42-45、P216-218、P351、P364)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先军队,后地方”、“先城市,后农村”、“照顾饮食习惯”等稻米配售原则。[4](P35-38)
在资源相对短缺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因此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乃至腐败现象,则显然又超出了基层民众的忍耐力。例如,曾有代县人愤笔致书山西省粮食厅:“县政府、粮食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规定每月每人能领细粮37斤(包括白面13斤,莜麦8斤,大米十几斤,其余是小米),而劳动人民群众每人每月规定只给25斤粗粮(高粱与小米各一半),就是过节也领不到一些细粮。”指出分配上的这种严重不公平已经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镇和乡村的劳动农民群众大部分愿意外出找工作或到大城市做工”。[36]晋南专区的档案资料也显示,不断有群众“要求放宽大米的供应范围和数量”[37]。
对于这些批评,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不同程度地进行过修正完善,但稻米的专供政策事实上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直到粮食市场全面开放,外省大米自由进入山西市场后,稻米才真正进入普通市民家庭,并逐渐成为其饭桌上的主食品之一。[11](P586)发生这种转变及其内在逻辑,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
(三)技术的进步并没有遏制稻作业的衰落趋势
以技术水平的提升来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始终是北方稻作的努力重点与关键。这种努力与探索从未间断,即使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相关政府部门也没有放松。据文献记载,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试验和推广优良水稻品种始终是山西农业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10](P160-161),其中,引进和推广的新品种包括“涟香”、“胭脂稻”、“黎优57”杂交粳稻、“辽盐2号”、“秋优”、“联优”、“辽粳10号”等十数种,以及当地培育的“晋稻3号”、“晋稻5号”、“晋稻6号”、“晋稻7号”、“提纯晋稻2号”等,这些新品种亩产少者430公斤以上,多者500公斤以上。在育秧方面,先后推广了一批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技术,如“旱育希植栽培”、“旱育抛秧”、“全生育期地膜覆盖”等[25](P224、P266)[38](P170)[39](P76、P195)。在病虫害防治[40]、田间管理、新技术应用[41]等方面,也采取过许多措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时期山西的水稻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其具体表现就是水稻单产量不断增加,2000年时平均亩产达到482公斤,这是其历史最高水平。但值得关注的是技术上的进步并没有挽救当地水稻生产全面衰退的趋势。目前,山西仅在太原、忻州、临汾、大同等地保存着少量稻田,面积不足2万亩。而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山西著名的稻作区。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即以自然生态结构为基础的产业形态。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鲜见,稻作史专家游修龄曾研究指出,“种植的时间不能连续持久,屡兴屡废,人去政息,水田荒芜,不能巩固”,是元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稻作业的两大特点之一。[42](P281)在稻作技术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人们仍不能有效地避开这个历史窠臼,说明这显然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问题。
四、结 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山西的经验不是个案,1949年以来的华北各地大致都有类似的历程。在山东,济南是当地水稻主产区,历史最悠久,影响深远。1949年后,随着北方稻改运动兴起,济南的稻作面积与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一度从1950年的1.35万亩和212.5万斤,增加到1976年的16.65万亩和3170万斤[43](第4册,P382),分别增加了12.33倍和14.92倍。但改革开放后即转入持续下滑状态,特别是近年来更是急剧衰落。据统计,2012年时全市尚有11.3万亩,到2014年时已不足5万亩。[44]一些具有数百年稻作传统的村落如济南冷水沟等,也在新世纪初彻底告别了稻作历史。[45]据战海霞的调查研究,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快速扩张的城市化对稻田的大规模占用,生态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化导致的灌溉资源的匮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及因此而造成的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等。[46](P54-56)在天津,1949年时该地种植水稻34.95万亩,年产稻谷1.4亿斤;经过稻改运动,到1970年时扩展到140.1万亩,稻谷总产达到8.71亿斤。[47](P151-152)改革开放后也转入下滑状态,其间虽经政府多方努力且偶有反弹,但其整体衰退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到2003年时,天津只剩下10.17万亩水稻,年产稻谷0.96亿斤[48](P226-227),比1949年时都要低很多。在河北,情况要比上述省市好一些,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也有大幅度的衰退。据统计,1997年时该省尚有水稻田233.3万亩,年总产稻谷20.48亿斤[49](P427),但到2003年时已下降到113.4万亩和8.22亿斤[50](P279),分别下降了51.4%和59.2%。
这也说明,上述现象是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梳理山西经验发现,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生态、技术、市场、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问题互相作用的结果。其中,又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与反思。
其一,生态环境作为长时段、基质性要素,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规制性意义几乎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有关这一点,已是人尽皆知的共识,无须赘言。
其二,市场制度安排的两极化趋势。虽然自然生态环境极为不利,但北方稻作仍能历经千余年而绵延不绝,关键因素有二:一是市场的稀缺性,二是市场的封闭性。就前者来说,特殊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北方稻谷产量的高度稀缺性,也决定了其在具备粮食作物的基本特性的同时,更具有经济作物的大多数特性,如“地域性强、经济价值高、技术要求高、商品率高”,“要求投入较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等。因此,北方稻米的价格一般要比旱作粮食高许多。以1933年太原市场上所售稻米为例,它大约相当于同期小麦价格的1.75倍,小米的2.8倍,黑豆的3.68倍,高粱的5.6倍。[11](P370)受此影响,北方地区的民间更多地把稻作视为一种商品性生产。例如,20世纪40年代初,济南冷水沟人就告诉“满铁”调查人员,水稻在当地“完全是商品作物”。[51](第4卷,P9)就后者来说,受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传统时代的市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草根性特点,市场规模小,产品流通范围窄。例如,据统计,1925—1936年间太原市场上销售的稻谷全部是本省所产,其中78%来源于太原附近的阳曲县,其余则来源于其他产稻县;所售糯米也全部产自本省。[10](P82-83)换言之,正是这种稀缺性与封闭性奠定了北方稻谷的市场比较优势。1949年后情况发生巨变。一方面,在集体化体制下,稻谷被单纯地视为粮食生产而受到严加管控,其商品性与市场性特点长期受抑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市场体系的重建和快速升级使大量替代性产品涌入,在缺乏相应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市场的发展反而瓦解了北方稻谷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在笔者看来,这种两极化趋势正是种种悖论发生的逻辑起点。
其三,在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新市场体系面前,所有基于地方性经验的传统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面临着种种生存困境,而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存在意义与存在形式。
最后,不能不指出的是,还不能因为上述历史现象的发生就简单地否定集体化时代对乡村发展问题的探索。客观评价这些探索及其意义,还需要更深入和更复杂的努力与尝试。
注释:
①山西省农业厅《山西省1957年水稻干尖线虫病检疫实施情况报告》(山西省档案馆藏,农业厅档案C77-5-97)、《关于发动稻区农民积极除稗,提高稻谷产量和质量的联合通知 (196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农业厅档案C77-10-286),太原市南郊区农科所《关于水稻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意见(1978年3月)》(太原市档案馆藏,农牧局档案A015-2-34),太原市农业局《关于水稻白叶枯病等病害发生情况的调查与防治意见(1980年10月5日)》(太原市档案馆藏,农牧局档案A015-2-64)、《关于开展灭虫保苗工作的通知》(太原市档案馆藏,农牧局档案A015-2-26)、《关于批转南郊区〈关于当前秧苗管理与搞好水稻插秧的意见〉(1980年5月26日)》(太原市档案馆藏,农业局档案A015-2-67)、《关于转发市水稻顾问组〈抓好水稻插秧管理及田间管理的建议〉(1982年5月4日)》(太原市档案馆藏,农业局档案A015-111-109)。
②田雨《太原晋祠镇水稻种植的历史与现状调查记录》,太原晋祠镇,2013年8月15~25日。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曾得到田雨等同学的大力帮助,在此谢过。
[1]诗经[M].葛培岭,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2]闵宗殿.从方志记载看明清时期我国水稻的分布[J].古今农业,1999,(1).
[3]安捷,赵树忠.晋祠志[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
[4]田雨.近代以来山西稻作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5]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刘瑞龙.大量改种水稻,迅速提高淮河以北低产地区的粮食产量(1958年4月26日)[A].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5[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7]山西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1960年5月27日)[J].山西政报,1960,(11).
[8]太原市农牧局.太原市农作物种植计划指标草案(1959)[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牧局档案:A015-1-14.
[9]晋南各县农业生产计划表(1959年2月)[Z].临汾:临汾市档案馆,晋南专署农业局档案:19-121-145.
[10]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山西通志·农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1]太原市粮食局.太原市粮食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12]《汾河水库志》编纂委员会.汾河水库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13]贾玉祥,常风渊.太原农牧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14]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室.气候与水稻[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15]太原市农牧局.太原市1959年种子工作初步总结(1960)[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牧局档案:A015-1-14.
[16]山西省农业建设厅.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志[Z].太原:山西省农业建设厅,1959.
[17]太原市农牧局.太原市1960年种子工作计划[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牧局档案:A015-1-19.
[18]太原市农牧局.太原市1964年种子工作总结[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牧局档案:A015-1-39.
[19]太原市农林局.水稻温室无土育秧总结会议记录(1979年1月5日)[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林局档案:A015-2-54.
[20]太原市农林局.关于无土秧水稻观摩会议的汇报(1979年10月4日)[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林局档案:A015-2-54.
[21]山西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2]陈云霞.太原市小店区耕地地力评价与利用[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23]小店区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市小店区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24]山西通志·土地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5]安捷,任根珠.太原市志(4)[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26]山西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报告(上册)[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27]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15.
[28]李红武.晋水记忆:一个水利社区的历史与当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29]太原市尖草坪区委史志馆.太原市北郊区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0]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31]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山西实业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32](日)山冈师团.山西大观[M].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33](清)徐继畬.五台新志(光绪)[M].孙汝明,王步墀,续修.清光绪刻本.
[34]日本东亚同文会.中国分省全志·山西省志[M].孙耀,译.太原: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2.
[35]山西省粮食厅.农村粮食统购统销部分[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粮食厅档案:C70-1-49.
[36]山西省粮食厅.群众来信[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粮食厅档案:C70-3-33.
[37]晋南专署粮食局.关于合理安排粮食供应品种放宽大米供应范围数量的通知(1957年)[Z].临汾:临汾市档案馆,晋南专署粮食局档案:29-111-196.
[38]忻州地区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39]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山西农业经济[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40]太原市植保植检站.关于抓好稻蝗防治工作的几点意见(1988年6月11日)[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牧局档案:A015-121-64.
[41]太原市推广增产菌应用技术方案(1988年3月)[Z].太原:太原市档案馆,农牧局档案:A015-121-64.
[42]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43]济南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4]济南计划恢复10万亩水稻种植 黄河大米或迎“复兴”[N].济南时报,2014-03-08.
[45]赵兴胜.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研究中的惯性表述及困境:以济南冷水沟村为例[J].历史研究,2005,(2).
[46]战海霞.延续与变革:济南稻作业的历史与现状[D].济南:山东大学,2016.
[47]天津市农林局.天津市农林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48]天津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49]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经济年鉴(199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50]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经济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51](日)旗田巍.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概況[A].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C].东京:岩波书店,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