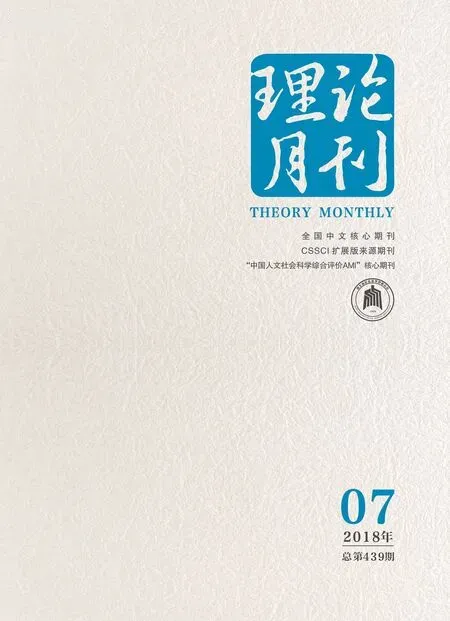从高青陈庄遗址看齐国起源的“西来说”与“东来说”
□潘润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齐国起源的“西来说”与“东来说”回顾
(一)齐国起源传统的“东来说”
对于西周初年的重要诸侯国齐国及其建立者姜太公吕尚的起源与身世,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说法。传统的东来说认为吕尚来自于东方的商文化地区,如《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1](p1477),认为其来自东方。后又记载,“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1](p1477),明确指出吕尚来自于商文化地区。战国诸子著作中也有类似记载,如《孟子·离娄上》中提到,“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2](p174),《吕氏春秋·首时》中也有“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3](p432)。
关于吕尚在投奔周文王之前经历,传统的“东来说”一般认为其来自作为商文化中心地区纣王陪都朝歌,甚至有着较为低微的屠牛出身。此说最早出于成书于战国早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棘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尊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4](p27)。传世战国文献中则见于《尉缭子》“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5](p31)和屈原的《九章》“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6](p145)。在后来的秦汉文献中这种说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战国策·秦策五》中记载,“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7](p698),《韩诗外传》中也有“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8](p263),《说苑·尊贤》中则记载,“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9](p178)。当然,这类说法与“伊尹起于庖厨”“傅说举于版筑”的传说过于接近,可能为战国时期美化先贤、宣传励志精神的小说家言,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至少说明了吕尚的出身可能与商文化中心区有关。
(二)近代以来新兴的“西来说”
随着民国以来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传统的关于吕尚身世的“东来说”受到了近代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成果的越来越大的挑战。最早提出相关问题的是傅斯年的《大东小东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和《夷夏东西说》。其中,1930年发表的《大东小东说》讨论了西周时期大东、小东的地理位置和具体内涵,主张燕、齐、鲁等国是在周公东征后才分封于东方。《夷夏东西说》则是傅斯年1933年的文章,主张“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10](p4)。按照这一观点,商人和周人属于东西方的两大不同民族,武王伐纣属于民族征服而非普通的改朝换代。1934年发表的《周东封与殷遗民》更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主张西周的分邦建国其实是一种对殷遗民的怀柔政策下的周人在东方的殖民据点政策。
傅斯年先生与齐国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文章则是1930年发表的《姜原》一文,该文将西周时期的姜姓贵族与商代甲骨文中的“羌”相联系,主张“姜”和“羌”为对同一民族内不同性别成员的称呼,“姜”即为“羌”。早在《大东小东说》一文中,傅斯年先生就主张“吕既东迁则为齐”,认为齐国起源于与姬姓周人结盟的姜戎吕国。在《姜原》中,更是认为“齐本是由四岳国里出来的,望伋两代仍用吕称”[10](p65),即河南西部的姜戎之地,关于姜太公出身底层的“愿者上钩”说法则为“战国末流齐东野人之语”[10]。吕思勉先生在同一时期,也写了一篇《太公为西方人》[11](p154),持类似主张。自此,齐国起源于与姬姓周人结盟的姜戎的“西来说”在近代以后逐渐成为定论。李玉洁在《齐国史》一书中认为,“齐国自西周封于齐,久居东夷地区。战国人经演义传说,误以为太公望为东方人。其实太公望为典型的西土之人”[12](p65),认为太公望是周文王时期关中地区的姜族首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研究先周文化而在关中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为我们研究姜姓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1981年,在扶风县刘家村发现一处有别于周文化的墓地,即刘家文化,“墓葬形制多为长方竖穴墓道,偏洞室居多,墓口多用不规则的土地块封堵。棺具结构奇特,为长方框形,无底无盖,仰身直肢葬为主。……隋葬器物主要是高领袋足鬲,双耳高领罐,腹耳高领罐,单耳罐及折腾肩罐和园肩罐。……这些都和宝鸡地区已知的姬周文化、西周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他们之间又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13](p24)。以高领袋足鬲、洞室墓和墓中随葬白石为特征的刘家文化被认为是与姬姓周人结盟的姜戎文化,从而使得作为姜姓诸侯国代表的齐国的“西来说”在考古学上几乎成为定论。2012年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发现后,由于M3中发现了来自于姜太公之女邑姜的“中臣鼎”,说明这一姜姓墓葬群与姜太公家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导致2016年有学者将M4的墓主认定为姜太公之女邑姜本人[14]。
由于长期以来西周时期的齐国贵族墓葬一直没有发现,关于齐国起源的“西来说”与“东来说”虽然各领风骚一段时间,但始终没有考古学上决定性的结论。2016年周书灿先生在《也论姜太公的身世、里籍与年寿问题——兼论古史研究的模糊性》一文中主张,“近年来学术界对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寿等问题的‘精确性’认识和研究,日益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单纯追求研究的‘精确’性,往往适得其反,只能导致与历史事实距离更远”[15](p26),值得我们深思。直到近年来高青陈庄遗址的重大发现,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认识。
二、高青陈庄遗址与齐国起源的“东来说”考古证据
即使是“西来说”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的近现代,也有一些考古证据指向齐国起源的“东来说”可能。比如山东地区与齐国同为姜姓诸侯国的逢国、纪国,就多次发现西周建立前商代的遗址。1983年在寿光纪国故城发现64件商代纪国青铜器,包括5件铜鼎、1件铜簋、1件铜甗,其中19件有族徽“己”,说明其属于商代纪国①参见:李沣《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东方大国纪国》,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efb3630101k9dc.html.。而春秋时期发现的纪国青铜器中有1951年发现于山东黄县东南的南埠一座春秋早期墓葬,铭文中多为“纪姜”,为纪侯嫁女之媵器,上博也藏有西周中期的纪侯簋,铭文为“己乍(纪侯作)姜萦(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另有康王时期的纪侯貉子簋,铭文为“己侯貉子分己姜宝,乍(作)簋”,可证纪国确为姜姓。关于逢国,《国语·周语下》中有“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16](第3卷p124),说明逢国亦为姜姓。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济阳发现了刘台子西周逢国墓地,出土大量青铜器,其中有“王姜作龏姒宝尊彝”,证明了这点。刘台子墓地中还发现一些商代卜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也记载,“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17](p1421),说明逢国可能在商代就已经在山东。与逢国、纪国有关的这些商代考古发现说明山东在商代就已有姜姓诸侯国,为齐国起源的“东来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
为齐国起源争论画上句号的考古证据是2008年在山东省高青县发现的陈庄遗址,其时代为西周早中期,填补了这一时期没有齐国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陈庄遗址“位于鲁北平原的小清河北岸,隶属于高青县花沟镇。北距黄河约18公里,东北距高青县城约12公里。遗址坐落于陈庄村和唐口村之间”[18](p100),其中的“城址近方形,城内东西、南北间距各约180多米,城内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18](p100),在陈庄遗址中发现了11座西周早中期的墓葬,包括长方形竖穴土坑墓9座、“甲”字形大墓2座。其中M17、M18属于成康时期,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国贵族墓葬。M17为木棺葬,仰身直肢,“在头端的棺外放置长方形的木器物箱。……箱内随葬铜器9件、陶器7件。铜器……器形有鼎、簋、爵、觯、觥、尊、卣、斗……铭文内容有‘丰启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丰作厥祖齐公尊彝’‘丰启作祖甲宝尊彝’等”[18](p100)。可见早在成康时期,齐国贵族墓葬中就大量使用带有东方民族特征的日名(参见张懋镕先生《周人不用日名说》[19](P173-177)),与《史记》中记载的西周早期“齐丁公”“齐乙公”“齐癸公”以日名作为谥号相符。
将陈庄遗址中的成康时期齐国贵族墓葬与同一时期的宝鸡石鼓山遗址相比较,可进一步验证齐国起源的“东来说”。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发现于2012年和2013年,包括M1至M4四座西周早期的贵族墓葬。其中“M3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圹墓”[20](p6),在墓葬中挖有壁龛以放置随葬器物。M3中共发现31件铜礼器,户卣、户彝等许多青铜器上有“户”铭文,应为墓主身份,亚羌父乙罍中有“亚羌”铭文并放置于墓中重要位置,说明墓主人为商周时期与姬姓周人结盟的羌人。更重要的是,在M3中还发现了一件作为先周时期刘家文化代表器物的高领袋足鬲,说明墓主人为姜戎贵族,也验证了傅斯年先生在《姜原》一文中关于“姜”即为“羌”的观点的远见卓识。周边多座小墓中也大量出土高领袋足鬲。与陈庄遗址中的成康时期齐国贵族墓葬相比较,石鼓山遗址在同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出现“亚羌”铭文,并有作为姜戎文化代表器物的高领袋足鬲,而这些在陈庄遗址的M17、M18中并没有出现,进一步说明齐国并非起源于西部的姜戎,而是来自于与纪国、逢国同源的东方姜姓,司马迁关于齐国起源的“东来说”传统观点是正确的。
三、高青陈庄遗址应为西周早中期的齐国都城营丘
由于高青陈庄遗址中发现大量重要的西周早中期齐国贵族墓葬,其城址身份也成为了学术界的重要讨论话题。目前有两大观点,一种认为其为齐国都城营丘,以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王恩田先生为代表;另一种认为陈庄遗址的规模过小,不可能是营丘,应为西周中期短暂的齐国都城博姑或普通的齐国边境城市,以朱凤瀚、林沄先生为代表。笔者认为,高青陈庄遗址应为史书中记载的西周早中期的齐国都城营丘。
关于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1](p1479)。这一认为武王封齐的说法已基本为史学界所否定,现一般认为齐国为周公东征后成王所封。《汉书·地理志下》中写道,“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21](p1323)。至于齐国都于营丘的时间,《齐太公世家》中记载,“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1](p1479)。齐国以营丘作为都城的时间大约为西周早中期,而这与高青陈庄遗址的使用时间正好是相符的。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营丘的位置一直争论不休。一说营丘即后来的齐国都城临淄。两者为一地,另一说则认为营丘位于山东昌乐。前说最早出于《汉书·地理志》,“临淄,师尚父所封”,“临甾名营丘”[21](p1645),并为郦道元、张守节所从;后说最早出于《太平寰宇记》,“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当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为营丘”[22](p373),将西汉时的营陵视为姜太公的都城营丘,理由为太公就封时与莱夷争国,故营丘的位置应与莱夷较近。两种说法虽众说纷纭,但都没有考古依据。而高青陈庄遗址作为发现齐国贵族墓葬的西周早中期城址,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否定陈庄遗址为齐都营丘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陈庄遗址的规模过小,如方辉先生认为,“有学者将其与太公所建造的营丘相联系,或认为是胡公所迁都的薄姑,从规模来看,均不足以担承‘大邦维屏’之重任。……与董家林相比,陈庄城址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西周早期,二者不可能属于同一层次或级别的城。也就是说,陈庄城址不可能是齐国都城之所在”[23](p104)。另外,没有发现作为都城所必需的宗庙遗址,也是否定陈庄遗址为齐都营丘的重要依据。
但是,这一否定观点过分拘泥于《左传》中“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17](p242)的都城定义,忽视了西周初年的特殊情况。众所周知,西周初年周公的分封属于周人对东方的军事殖民,东方的各个姬姓、姜姓诸侯国其实是周人在东方的殖民据点。在最初的殖民过程中,鲁、卫、晋并没有建立符合礼制的都城,而是将都城暂时建于可以有效监视东方原住民的军事据点之中。比如《世本》中记载“炀公徙鲁”,曲阜鲁国故城的考古发掘也只能追溯到西周中期,而没有发现任何伯禽时期的遗迹。卫国的都城也是后来才迁于朝歌,清华简《系年》中记载,“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24](p144)。可见康叔时期卫国最初的都城位于“康丘”,后来才迁到现在的淇县县城。晋国都城则是在晋侯燮父时期由唐迁于绛,2007年发现的覘公簋的铭文记载,“觇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从以上各诸侯国的情况可以看出,《左传》中分辨“都”和“邑”的宗庙标准其实并不适用于西周初年以控制东方的军事据点作为临时都城的情况。
齐国的情况更有其特殊性,位于薄姑故地的齐国需要同时控制商代的齐邑大辛庄遗址和薄姑都城苏埠屯遗址,无法同时将两者都作为姜太公驻扎的临时都城,所以齐国在两者位置中间新建军事据点高青陈庄遗址作为都城。齐国的国名“齐”也与高青陈庄遗址位于济水边的地理位置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齐国在建国之后长期保留返葬习俗,《礼记·檀弓上》中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25](p106),长期的返葬习俗使高青陈庄遗址一直作为军事据点而存在,自然没有必要保留宗庙和礼制所规定的像燕国董家林古城和曲阜鲁国故城这样的庞大规模。
说明高青陈庄遗址应为齐都营丘的最重要考古依据是遗址中所发现的祭天的天坛,“另一重要发现是位于城内中部偏南的夯土台基。……根据夯土台基形制和所处位置初步判断,此类台基可能与祭祀有关。从夯土台基保存的现状看,其周缘部分基本被晚期遗迹破坏,但夯土台基的中心部位却保存完好,且春秋、战国时的南北干道绕行圆台的西侧,由此判断,夯土台基的中心部位一直到战国时期仍未被破坏,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该台基中心仍然存有某种神秘或神圣的信仰色彩”[26](第7版)。祭坛在陈庄遗址中的出现使我们联想到历史上著名的周夷王烹杀齐哀公事件。《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1](p1481),《竹书纪年》中也有“(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索隐引纪年)[1](p1481)。从陈庄遗址中的祭坛可以看出,这一周代历史中极少见的天子杀害诸侯的事件可能与齐哀公的谋逆叛乱有关,周夷王因为听信纪国国君商代就在东方的谮言而诛杀齐侯也进一步印证了齐国起源的“东来说”。
综上所述,高青陈庄遗址应为史书中所记载的西周早中期的齐国都城营丘,其长期作为控制东方的军事据点而存在使得我们不能根据礼制而否定其都城身份。陈庄遗址最后因为齐哀公的建造天坛的叛乱行为而在哀公被烹杀后被废弃。
四、姜太公进入关中地区可能和周人与商王室的联姻有关
既然齐国起源于东方而非关中地区,那么就必须解释姜太公吕尚为何以及何时进入周文王控制区并成为先周贵族。笔者认为,姜太公在商朝末年进入关中地区可能和周人与商王室的联姻有关。
关于先周时期周人与东方商文化区域的联姻关系,史书中对此有大量记载。比如季历就娶太任为妻,“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1](p115),《诗经·大明》中对此的记载是,“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29](p752),可见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来自于东方殷文化地区。更著名的联姻事迹是文王时期的“帝乙归妹”。对于文王之妻太姒,《列女传》中记载,“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28](p14)。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和《易经》中所提到的太姒与商王室之间的关系。《诗经·大明》中记载,“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29](p754),认为太姒来自于“大邦”(即商王室)。《易经》中的泰卦也有“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30](p49),归妹卦中也记载“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30](p195)。从《左传》中对归妹卦的解释可看出这里的“帝乙归妹”指的就是帝乙嫁妹妹①《左传·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可见帝乙与来自有莘氏的太姒之间是表兄妹关系,太姒也来自于东方殷文化地区。王季、文王连续两代人与商王室的联姻极大地提高了周国在诸侯中的地位,成为当时商朝在西方举足轻重的西伯。
帝乙归妹的原因最初是为了消弥商周两大民族之间的冲突。《竹书纪年》中记载,在武乙暴毙于渭河流域之后,商人和周人一度处于激烈冲突之中。先是“文丁杀季历”[31](p1432),后又有“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27](p39)。在冲突后,帝乙不得不通过联姻关系来弥合与周人之间的关系并承认文王为西伯,从而使周国成为商朝在西方最重要的诸侯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太姒嫁入周国并非仅仅是父母之命,而是作为商王的表哥所安排,所以陪嫁的媵臣不一定全部为有莘氏族人,可能也包括商王所安排的“东海上人”吕尚等其他东方民族人士。与这一假设相似的有商朝初年伊尹的经历,其作为有莘氏的陪嫁媵臣进入商国并辅佐商汤崛起,《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3](p425),《史记》中也有“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1](p96),所以吕尚也有可能是作为有莘氏的陪嫁媵臣进入周国并成为先周贵族。吕尚在东方的纪、逢等同族可能也是因为他的缘故而在西周建立后被赐姓为姜姓。上文中提到山东的考古发现证实姜姓的纪国、逢国在商朝时就已经存在于当地,这与姜姓来自于商代羌人与姜戎相矛盾。笔者认为,吕尚及其在山东的纪、逢等同族成为姜姓可能是周人的赐姓。《列女传》中记载,“大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大王娶以为妃。生大伯、仲雍、王季”[28](p14),《诗经·文王之什·绵》中也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29](p760),可见太王之妻太姜来自于周原一带的姜戎。但是,《国语·周语下》中却记载,“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16](第3卷p124),将商代就生活在东方的逢国视为来自西方的太姜的侄子辈,说明逢国作为吕尚的同族在西周建立后接受了姜姓的赐姓。
总之,姜太公吕尚在商朝末年进入关中地区可能和文王初年周人与商王室的联姻有关,吕尚可能是作为有莘氏的陪嫁媵臣进入周国并成为先周贵族,这一假设比其在纣王时期通过“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方式投奔文王的传统说法更具可能性。
五、总结
早在民国时期,傅斯年先生就在《夷夏东西说》《姜原》等文中探讨了商周两大民族的东西对立关系和西周姜姓贵族在商代的羌人起源问题,这一先见之明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关于殷遗民和刘家文化姜戎遗址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但是,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经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对于齐国起源的“东海上人”传统说法。相反,随着建国后寿光纪国故城、济阳刘台子逢国墓地、高青陈庄遗址等一系列与西周时期山东姜姓诸侯国相关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与同一时期姜戎贵族的宝鸡石鼓山遗址相比较,笔者认为基本上可推断姜太公吕尚的身世应为传统的“东来说”。高青陈庄遗址应为西周早中期的齐国都城营丘,最后因为齐哀公的建造天坛的叛乱行为而在哀公被烹杀后被废弃。姜太公吕尚进入关中地区,可能和周人与商王室的联姻、特别是文王继位后的帝乙归妹有关。笔者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在民国先秦史大家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学术界对西周齐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