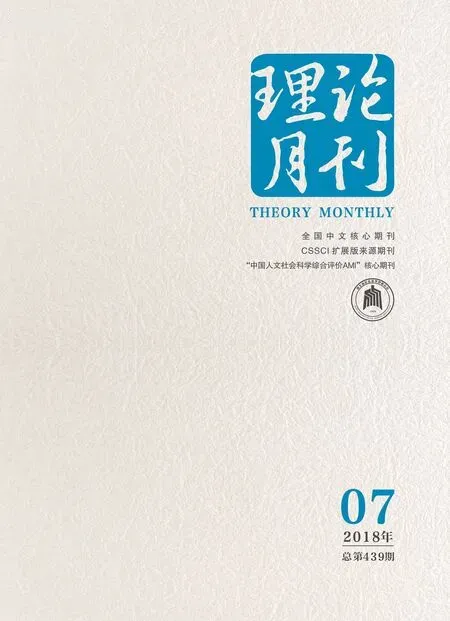经济伦理与农民城镇化动力的区域差异
□刘超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获得快速发展,城镇化率由1996年的30.5%提高到2016年的57.3%,年均提高约1.3%,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概念上,城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以及产业、空间、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狭义上则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定居的过程[1](p43-51)。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重要维度,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 171万人,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要群体,其能否顺利实现城镇化,直接关系到新一轮城镇化的整体进程。
(一)农民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界对于农民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转型与城镇化。该视角基本途径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定性与定量结合,来探讨全国范围内典型地区、各省份和省域范围内各市县的城镇化动力。其主要观点认为在工业化进程、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贸易的宏观背景影响下,自然资源禀赋[2](p44-49)、产业结构[3](p13-18)、人力资本[4](p59-66)等因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二是国家制度与城镇化。该观点主要集中在对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讨论,认为城镇化动力主要是因为制度改革造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转型。相反,中国的城镇化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的是现行的土地制度[5](p34-37)和户籍制度[6](p55-73),农民工不为城市经济体系所接纳,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突破现有城乡结构,撤销隔离城乡居民的户口制度,把城市吸纳的“农民工”适时转变为市民[7](p24-26),获得市民权利[8](p119-132),二者应当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
这些研究为理解该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市场转型理论通过对东中西地区的差异的比较,分析了宏观的资源禀赋的影响。国家制度理论以“城市—市民”为本位的视角,强调了农民工个体在务工城市的现实状态与改进举措。但这二者均忽视了农民工所处的乡村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制约。
城镇化的过程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国家政策推动,又包括微观层面的主体源——农民进城的意愿与行动逻辑。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人口流入,就地城镇化具有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属于人口流出地区,在现阶段约束条件下,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迁移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主流,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农民一般通过在城市购房的途径完成城镇化的目标。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农民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要理解农民城镇化的真实逻辑,必须要从农民主体的视角出发。
(二)“嵌入”家庭伦理的农民生计模式
波兰尼认为“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9](p15),该观点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迷思,提出了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型问题。中国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家庭不仅是“伦理共同体”,而且是“经济共同体”,其经济体的形态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家庭结构的塑造[10](p90-113)。中国农民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在家庭中,农民的经济行为要受到其所持的经济态度的影响,经济态度是决定具体经济行为的主观意志[11](p107-113)。农民家庭经济策略具有两种内涵:一是家庭作为经营与核算的基本单元;二是小农经营是家庭伦理取向,而非服从资本再生产规律。韦伯认为,“经济伦理”是“一种激发行动的实际推动力”[12](p492),在考察世界诸宗教之后,总结出:作为“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的理性主义”支配着西方世界理性化的市民生活[13](p101)。经济的理性主义发育程度成为能否进入现代社会,适应城市化关键的变量。本文延续这一理论预设,认为经济伦理是一种植根于人们经济交往关系中的实践活动和伦理道德观念,实质上是一种价值支配下的经济态度,形塑了农民的经济行为模式,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经济策略与经济态度。其决定了农民如何安排劳动力与支出的结构,制约了农民的经济行为,构成农民经济行为动机的基础,成为农民城镇化动力的核心变量。
中国目前正处于“半城市化”阶段[14](p107-122),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根据家庭结构和劳动力特质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子女在城市务工,年老父母在农村务农[15](p2)。在这一家庭经济模式下,一个农民工家庭能够同时获得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在全国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等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下,该家计模式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再生产性的特征[16](p19-32)。因此,“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是农民家庭适应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农民实现快速城镇化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此外,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模式主要受人生任务与过日子的逻辑支配着,“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包括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等这些环节,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命运[17](p66-85)。它是一套生存伦理,社会交往、生育制度和祖先观念等都以现实生活的逻辑来建构,蕴含着强烈的家庭观念[18](p260-270)。因此,中国农民经济态度是由家庭伦理生发,构成了农民经济行为的重要动机,同时农民生活面向决定了家庭消费的结构性支出。
本文研究所调查的农民绝大多数都属于“既进城又返乡”的状态,以农户中“父—子—孙”三代家庭为单位,主要通过论述不同区域经济伦理的实践维度与价值维度以理解农民城镇化动力问题。实践维度即农民家庭经济策略,其决定了农民城镇化的能力,并将其操作为三个指标:一是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生育数量与教育程度决定了劳动力价值,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决定了农民收入的高低。二是家庭消费结构。主要包括家庭消费和社会性消费。家庭消费依据家庭生命周期主要包括,抚育支出、教育支出、建房支出、婚姻支出等等。社会性消费主要指仪式性消费等。三是代际资源分配结构。家庭资源分配是面向子代抑或是父代,关系到农民用于城镇化的资源密度。经济伦理的价值维度即经济态度,其决定了农民城镇化的意愿。家庭伦理的核心是生育观念、代际关系和夫妻性别关系等生活规范。生活面向是指农民生活面向城市抑或是村庄,二者共同影响了劳动力在城市的投入程度与家庭资源使用的方向。
近年来,笔者在江汉平原、赣南等数地的农村进行调查,通过半结构式的访谈与参与式观察获得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本文灵感的来源及分析的基础。江汉平原属于典型的原子化地区,村庄历史短,村庄归属感不强,赣南则属于宗族性地区,村庄历史长,社会结构发育完整,村民认同感强[19](p108-129)。笔者与所在团队10余人于2015年9月在江汉平原S县Z村与C村进行为期20天的驻村调查,其中Z村共476户,总人口1466人,总耕地面积3864亩。Z村属于典型的原子化地区,绝大多数家庭是1980年代建造的平房,但村民外出买房的户数相当多,已经在本市县买房的比例大概在40%,买房周期在2010—2015年。笔者及所在团队20余人于2016年7月在赣南N县P村、S村与W村进行为期20天的驻村调查,其中P村共有680户,3120口人,总耕地面积2020亩。与Z村同样年代开启的打工经济,但当地农民的积累水平并不高,村民情愿在村建房,2010年之后开启了第二轮建房潮,而在外买房的家庭屈指可数。
二、外向型经济生活模式:江汉平原的调查
江汉平原地区是典型的原子化地区,该地区的家庭生活主要面向城市,实现了功能性的家庭分工,表现为不断积累的家庭经济资源,为进城获取最基本的资本。在家庭经济积累层面是典型的结构完整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实现了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家庭积累丰厚。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使得每个家庭孩子数量并不多,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极大,子代教育程度高,为子代进城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本。代际资源分配面向子代,父代为子代进城务工提供稳定支持,为子代进城定居提供物质支持,子代进城定居后父代持续输送资源。现代实用主义的家庭伦理与面向城市的生活共同使得子代与父代实现了接力式的城镇化。
(一)发展型家庭经济策略
1.家庭劳动力最优匹配。首先,务农与打工相匹配的代际分工模式。老年人负责田间照料和就近打零工,年轻人外出务工。江汉平原地区属于传统型农业耕作区,土地肥沃,人均耕地较多,约2~3亩,户均有10—15亩,并且机械化水平较高,每家每户都有1—2台拖拉机,有的还有插秧机和收割机,父代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农业种植,农业产出对于家庭而言仍然是可观的大项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一般很少受到家庭及村庄的影响,打工的时间长并且连续。由此,家庭的代际分工在土地和市场、农村和城市之间是高度整合的,父代依附于土地,并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有限的务工机会。子代长期不间断的打工,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力的经济效益。
其次,合理的性别分工使得女性最大限度地参与市场。老年夫妻负责种地、打零工和带孩子,生活开支小,具有较强的积蓄能力,年轻夫妻负责打工攒钱,有较多存款。婆婆和媳妇究竟由谁照看小孩,则取决于不同阶段孩子对母亲的依赖程度和老人的劳动能力,大多数情况下,两岁以内的幼童由媳妇照看,当幼童长大一些,年轻的媳妇外出务工。家庭中的女性照料者角色也依据经济理性而定,年轻的媳妇作为积蓄单位的时间大于消费单位,家庭劳动力得以实现优化配置,通过分工实现最大效用,家庭的积蓄能力强。
2.家庭大额消费面向城市。首先,子代结婚选择在城市买房。大多数家庭依旧是1980年代建造的平房,但村民外出买房的动力十足。买房周期在2010—2015年,并且大多数购房都是在本市范围。父母都希望子代能够尽最大可能地留在城市,当地的结婚条件之一便是在城里买一套房。“现在年轻人谈朋友结婚,都是问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在荆门买房子”“儿子结婚提要求要在城里买房,不然女方不同意”,农村建房没有吸引力,于是为了儿女的婚事,进城买房却成了村庄里的趋势。进城买房除了儿女结婚的需要,父母及子女们也还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对未来城市生活有着较高的预期,“在农村种田没出息,把儿女养大了,回到农村没面子”“农村父母以孩子进城为荣耀,在城里买房就光荣”,于是“一辈子的心血全为了让孩子进城”。
其次,对教育资源投入丰富。家庭中的孩子少,家庭资源可以实现向仅有的一个孩子的汇集,重视子女的培养,重视教育成为江汉平原地区农民的普遍行为规则。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农村的孩子普遍开始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只要他们愿意读书,就一直供到底”,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是家庭开支的大项目,这已经形成该地区农民行为的地方性共识。
3.资源代际传递向下流动。一是父代为子代进城务工提供稳定保障。大部分家庭父代都会在家照料第三代直到打工的子代回家,一般农民工返乡的年纪在50—55岁,这个年龄阶段农民工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就意味着父代照料孙代的时间较长,甚至一直到高中毕业。并且,父代照料孙代的日常花费一般是由父代支出,比如孙代的零食、玩具等等,子代则负责孙代的教育支出等等。同时,在农村居住的父代维持着稳定的社会交往,子代不需要返乡参加人情等仪式性活动,减少了打工的干预性。这样,父代为子代在城市务工提供了稳定的后方保障,两夫妻的务工收入能够最大限度地留存。
二是父代为子代进城定居提供物质支持。该地区女方父母不仅不会要彩礼,而且会准备一份相当厚实的嫁妆。这样,彩礼与嫁妆成为男女双方父母为子女建立家庭提供支持。通过婚姻实现了家庭资源一次性向下转移,结婚时双方父母都会给予小家庭一笔财富,成为他们城镇化的经济基础。
三是子代进城定居后父代持续输送资源。子代进城之后,父代通过种口粮田实现自养,减轻中年子女负担,中年父母通常都想多种一点田,获得更多的收入,为子女进城提供支助。等到子女进城以后,还负责为他们提供米和菜等农副产品。父母在持续不断的推动着子女的城镇化,代与代之间资源向下转移,实现代际接力式的家庭城镇化。
(二)现代型经济态度
江汉平原等原子化地区的家庭伦理表现为较强的现代性。首先,原子化地区农民没有强烈的生育数量与男孩偏好要求。农民传宗接代、家族绵延的本体性价值淡薄。整个家庭也并不会以此对子女提出生育要求,农民说:“父母不会给自己压力要求生个儿子”“生了儿子是名气,生了女儿是福气。”村庄社会舆论没有形成男孩偏好的压力。在村庄中获得认可并不是以孩子数量为标准,家庭经济状况及子女的培养质量成为村庄中相互比较的面向,农民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和子女培养。因此只生一个孩子成为农村家庭最为理想的选择。其次,原子化地区代际关系不平衡,代际交换较少。资源代际传递向下流动,是父—子间的单向的资源及责任的传递机制,父代对子代具有无限的责任,而子代对父代的反馈都是极为微弱的。父代对子代有强烈的抚育人生任务,而子代则无强约束的反哺责任,在城镇化的压力下,父代迅速沦为家庭资源的剥夺者。农村被城市所吸纳,人、财、物大量流出,村庄生活面向城市,农民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子代城镇化。
该地区村庄只是农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村庄历史较短,农民缺乏对村庄的记忆,村庄社会结构发育不完全,村庄内部关系松散,社会关系理性化趋势明显,呈现原子化特征。因此,村庄没有产生强大的价值与意义生产能力,也就没有了拉力,农民生活面向城市。此外,该地区由于打工经济的崛起,农民的经济收入出现快速分化,经济分化导致社会竞争,经济收入高的群体选择在城市买房,并将这一压力传递给其他阶层,子代结婚需要在城市购房,通过城镇化实现农民家庭向上的阶层流动。因此,在缺少村庄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城镇化压力转化为村庄社会压力,并沿着社会关系传递给家庭,家庭的城镇化功能凸显。村庄共同体面对城镇化压力快速瓦解,人、财、物大量流出,村庄空心化程度高,村庄被城市所吸纳并逐步瓦解。
三、内向型经济生活模式:赣南的调查
赣南地区是典型的宗族性地区,面对城镇化的压力,当地村民保持了相当强大的抵抗力。村民说:“我们这里以前很苦,现在生活好了,得过且过吧”“出去打工,非常想家里,没钱借钱也回来。”即使在城市获得可观的务工收入,也要回家建房,梯次建房行为是村民生活面向的具体例证。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低,较高的生育率限制了女性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家庭消费面向村庄,社会性消费占比高;在资源代际分配层面,父代权威高,具有调配家庭资源的正义性。传统型的家庭伦理对于生育的要求与对父代的反哺责任强大,农民生活面向村庄,村庄生活形成了完整的内生运转体系。
(一)维持型家庭经济策略
1.劳动力未充分利用。首先,女性高度嵌入生育任务与繁重家务。村民心目中最佳的子女结构为“两儿两女”。现在的家庭两儿一女结构是少数,更多的是两儿多女的结构。W村某村民,1976年出生,他们夫妻育有10个子女,8个女儿,2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第6胎,第二个儿子是第10胎。多生育不仅使得妇女必须在很长的时间都处于生育状态,而且生育之后,又要花时间照料。因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可以通过代际分工解决家庭的抚育问题,宗族性地区则必须通过夫妻分工,夫妻双方只有一方的劳动力能够完全市场化,形成了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从劳动力的总量来看,其都是有限的,当家庭人口在生育任务占用的劳动力过多时,其用于市场化的劳动力必然就相对来说会减少,必然降低家庭收入。
其次,村庄拉力重。当地的养老责任也同样高于江汉平原地区,子女有义务对年老的父母进行轮养照料。父代一般在50岁左右便选择回乡,较早结束了打工生活。同时,当地农民的生活具有浓重的村庄面向,对于村庄的归属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这导致当地的农民更容易返乡,更难忍受外面的打工生活。农民在清明节一定要回家祭祖,包括一些年轻人,特别是有了清明节假日以后几乎年年回家祭祖,春节时,大多数农民也会选择回家过年。父代较早进入退休状态,子代打工时间较短及易中断限制了农民务工收入的增长。
2.大额消费面向村庄。首先,村民选择在村庄建房。赣南P村村民情愿将收入用于村庄消费,将从城市打工获得的收入用于在村庄修建房屋,几户用尽若干年打工积攒的收入。且呈现梯次建房的特征。某户人家1999年建了第一层房子,2008年建了第二层,2016年建了第三层。建房是父代的核心人生任务,同样,在宗族性的闽西农村地区,自改革开放,当地总共有3次建房潮,第一次是1980年代分田到户之后,主要是泥土房。第二次是在1990年代,主要是砖房平房。第三次是2013年之后,当地已经出现了框架结构的三层楼房,花费30—50万,加上装修共需要70万左右,并且80%的家庭建房都需要借贷。
其次,婚姻成本高。由于子代结婚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彩礼是刚性支出。赣南彩礼这十年出现暴涨的趋势,2006年,N县彩礼大约是3万—4万,2012年涨到了10万,2017在彩礼约在17万左右,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彩礼越高。同时,彩礼是留给父母作为养老钱,而不是给予子代。父母希望嫁女儿为儿子结婚积攒一笔费用,如果家里兄弟多,并且没有成婚,彩礼要的会更多,所谓“嫁两个女儿换不到1个儿媳妇”。这使得子代结婚后往往面临着较高的债务危机,缺少向外发展的资源,限制了在外地买房的可能性。
再次,社会性消费占比大。与其他地方相比,宗族地区除了小家庭的消费以外,还必须对一些村庄的公共事务,本宗族内的事务承担责任。例如修路,修桥时的摊派。宗族内部家庭困难时的捐款,清明节祭祀活动支出,以及修族谱祠堂时候的摊派。对当地农民来说,开支不仅仅是小家庭内部的,还必须承担起所在的宗族集体,包括村集体与祭祀团体上的开销,并且,这笔开销的数量并不少。
3.资源代际分配均衡。首先,人生任务止步于结婚。父代对子代承担有限责任与义务,把子女养大,替儿子娶上媳妇,父母的人生任务就基本完成,是否建房及带孙子视老年人的意愿,由父母自主决定。即使父代帮忙带孙子,孙子的生活费用及教育费用也是由在城市务工的子代支付。
其次,伦理性养老责任。子女对父母则承担无限责任,儿子要为父母养老送终,有责任承担父母晚年的全部开支。在当地老人生活条件好,生活水准高,其所花费的家庭资源比其他地方多得多。老年人有病就必须医,很少有老年人自杀的情况。父代遵循“我把儿养大,儿养我到死”的逻辑。父代权威高,在家庭中扮演当家人的角色,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子代家庭实力抽强补弱,抽肥补瘦补偿较弱的一方。
(二)传统型经济态度
赣南等宗族性地区的家庭伦理表现为较强的传统型。首先,宗族文化是父系文化,传宗接代是宗族文化的核心规范与价值诉求。当地的男孩偏好尤其严重,男丁是维持宗族完整的重要力量,是仪式性规则的代表,具有维护地方性规范的功能。在社会性层面是面子竞争的重要展现,头胎生男孩说明这家有福气,风水好。在功能性层面,男丁是守护祖业,维系以暴力为基础的家族秩序的重要工具。在价值层面,男丁是传宗接代的重要手段,是经营死后世界的唯一主力军,是魂魄转化为祖先的通道,村民“传宗接代”本体性需求的保证,每个男性村民都有责任将自己这一支延续下去。在实现人生任务的过程中农民获得了生命绵延感与死后世界的想象,获得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这构成了中国农民宗教意识的某些特征[20](p60-67)。因此,父母有极强动力完成人生任务,实现圆满人生。其次,宗族性地区遵循的是传统的反馈模式子代对父母无限责任,代际关系平衡且代际交换强有力、深厚,受到强烈地方规范约束的代际情感。老年人虽然经济不独立,但是养老是刚性的任务,老年人自主性强,能够参与社会性的交往。
农民生活面向乡村,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村庄内的事务中,村庄里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包括宗族的事务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只要有需要农民就会回乡。当地村庄形成了一种保护性结构,一方面村庄具有价值与意义生产能力,村庄舆论规范强。村庄内部均是宗亲、姻亲关系,村民之间形成了团结紧密的情感共同体与生产互助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庄经济分化小,社会竞争弱,不会对村民形成很强的结构性压力。当地农村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很小,大部分家庭是收支平衡,很少有家庭能够有较多存款,这就使得当地农民家庭的同质性比较强,村民之间的社会性竞争相对较弱。因此,村庄内部的结构性社会压力小,大多数家庭的收入维持生活及子女读书等方面的开支,传统的生活习惯还在村庄延续,村庄内部也不具有很强的消费空间及展示性。因此,村庄具有很强的内生运转体系,大量的资源由城市流向乡村,村庄实体化程度高,村庄对村民进入市场环境具有较强的拉力,增加了适应开放市场环境的难度,农户面对城镇化压力具有缓冲空间与可选择性。
四、城镇化动力的区域差异
从上文所论述的农民经济行为与经济态度而言,其背后折射的是农民家庭对于对城镇化的适应性的问题。原子化地区农民家庭经济伦理与城镇化具有选择性的亲和性,推动了农民的快速城镇化;宗族地区农民的经济伦理与城镇化背道而驰,构成了其重要的拉力,阻碍了农民快速的城镇化。
(一)城镇化能力的差异
1.江汉平原地区农民城镇化能力强。首先,家庭劳动力全部投入家庭生产,获得了极高的市场回报与积累。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在城市务工,在家庭资源使用方面面向城市。父代不但要支撑起子女进城买房,而且还要继续靠土地的产出充当子女城市生活的辅助者。父代在完成子代的供养之后便会转入土地上的自养状态,成为现代化的秩序建构(order-building)和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制造出来的“废弃的生命”[21](p6)。农民城镇化是渐进过程的任务,子女的进城是在整个家庭内部展开的,家庭是子女进城和城市生活的依托。
其次,江汉平原自1980年后,计划生育便严格执行,受国家政策影响,农民与国家发生强烈共振,农民的生育观念转变迅速且彻底,家庭普遍呈现出少子化的趋势,每家只要一个孩子,生男生女都一样,成为农民们的文化自觉。农民家庭生活的意义面向主要不在于依靠生育行为来实现,而是转向了现世的生活。低生育率使得家庭在资源方面面临的压力少,能够为孙代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与培养模式。父代对子代教育资源的投入使得没有能通过教育途径完成城镇化目标的子代也具有相对较高的学历。求学与进城打工使得农村年轻的一代,对农村生活及农业生产渐行渐远,进入城市生活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长期生活在村庄和土地之外的农村的年轻一代,他们自身的离土化倾向明显,而他们身后的父母及家庭,也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子女“跳出农门”,子代进城是农民家庭的整体性需求。
2.赣南地区农民城镇化能力弱。首先,当地村民具有强烈的生男偏好,每个家庭必须育有一个男孩,女性的家庭角色便是生育和操持家务,这一群体承担着延续香火的人生任务,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将自己的生命嵌入到宗族绵延的长河中。高生育率与养老责任重导致当地的家庭无法实现最优化的劳动力配置,劳动力的价值化程度降低,利用效率降低,家庭积累薄弱,难以实现城镇化的财富积累。其次,较高的生育率也降低了子代接受高教育的可能。高生育率使得家庭的孩子众多,限制了家庭用于诸如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支出。生存性支出挤占了发展型支出,维持着简单的家庭再生产模式。
(二)城镇化意愿的差异
1.原子化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强。该地区农民缺乏对于村庄归属意义,村庄缺乏社会结构与村庄规范的制约,因此其更加会直接的融入城市,认可与接受城市的价值,并且将农村看作是落后的地方,而不愿意再投入过多的家庭资源。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存在的巨大进城压力,进城成为评判村民家庭村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进城压力通过村庄竞争进入村民家庭内部,沿着代际关系纽带向上传递,并为老人所感知。对父代来说,他们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方式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一种是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家庭经济生产;一种是以消极的姿态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消费支出,减少对子代养老及照料的依赖。
2.宗族性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弱。该地区村庄内部不仅存在着传统的人情、互助,而且具有强有力的内生型价值与意义生产能力。村庄生活缺乏经济竞争,有稳定生活预期,重视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村庄强公共性的生活模式。诸如人生任务等社会压力并没有转化为家庭压力,同时社会竞争并没有向经济竞争转化,代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是一种交换性的伦理关系。同时,对村民而言,村庄不仅是一个居住场所,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空间。当地的房屋空间一是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空间,二是神圣的祭祀空间。老人去世之前要被抬到厅堂,这样死后就能通过厅堂而转化为祖先。如果去世在外面,是不祥的象征,便不能土葬,需要火化。钱穆指出:“中国人的家,实即中国人的教堂”[22](p30)。厅堂与祠堂是结为一体的,通过白事仪式联结,生与死便结为一体,空间具有了世俗性与神圣性。因此,农民将村庄视作人生归属,村庄认同成为他们生命意义的组成部分,村民更愿意将从城市中获得的资源投向村庄,人口向城市转移动力不足。村庄生活使得人们有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收入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实现村庄内部社会关系再生产。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面向村庄,重视养老资源,家庭用于发展的资源必然就相对收缩,构成了农民城镇化的阻力。
原子化地区的农民以具有绵延性和伸缩性的弹性家庭为单位,以半工半耕为生计模式,以农村为根基、以城市为目标,通过接力式的代际支持实现了城市化[23](p66-74)。代际支持成为农民城镇化成本的基本分担机制,家庭劳动力结构完整,保证了家庭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市场化,家庭消费层面主要是面向子代的城镇化消费,父代为子代进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强有力的保障,与城市化相符的“发展性目标”对家庭资源的支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家庭的去伦理化导致其家庭功能性凸显,能够打破原来家庭成员角色的设置,自由地按照市场的原则对家庭进行再构造,提高其城市化的适应能力。而赣南等宗族地区的农民对于家庭生活的强调,夫妻分工的传统化,使得劳动力转化为市场价值程度低。同时文化意义上的“拉力”使得村民的生活具有内向性。当前,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民对于乡土的依恋偏重与完整的家庭伦理,无法突破原来的生育观念和尊卑体系,难以与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与构造相融合,其城镇化的适应性必然会遭遇到社会结构的阻挡与弱化。

表1:两地城镇化动力区域差异
五、结语
改革开放之后,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农民城镇化便是乡村社会剧烈变迁的表征,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体面进城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在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两地经济伦理形塑了不同的城镇化动力,劳动力配置、消费结构、家庭再生产的方案与生活面向,形塑了农民城镇化动力的差异。原子化地区缺少传统制约与束缚,能够完全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实用主义地对家庭的劳动力优化分工,对家庭支出进行合理的安排,从而顺利实现城镇化。相反,宗族性地区传统型家庭伦理与村庄公共道德构成了进入城镇化的阻力,它导致农民花费更多资源投入于与城镇化的现代生活背道而驰的体系,减少了融入城市的资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目标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城镇化的核心在“人”,实现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才是城镇化的最终目标。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而言,工业化是推动农民城镇化的根本前提,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情况下,打工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农民提供了广泛的优厚的务工机会,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同于制度主义所主张,中国农民城镇化道路经由国家普遍赋权而获得进入城市生活的渠道,本文认为国家应当充分尊重农民主体选择的“人的城镇化”,让农民成为主体,保证农民自主选择的权利,根据“进城”和“留村”两种方式,在鼓励农民向城镇集聚的同时,推动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实现自由的迁徙和诗意的栖居,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基于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