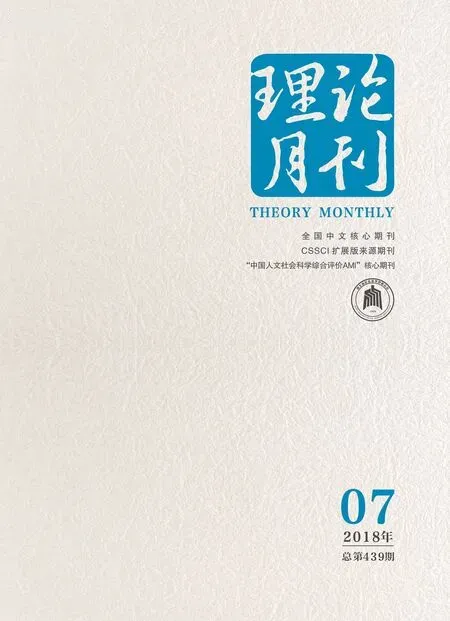《常棣》作者之争与“常棣”系列文本的形成
□张劲锋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关于《小雅·常棣》之作,其说主要有二:一为周文公“闵管、蔡而亲兄弟”所作,所据为《国语》[1](p45);一为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所作,本之于《左传》[2](p1817)。前说至唐为尊,后说宋降日显;今日学界则多由否定《常棣》与“管蔡”之关系入手,进而主张《常棣》纯为召公所作[3](p448)。然而,《国语》《左传》素为表里,若无确凿旁证,遽言此是彼非,难免妄断之嫌。那么,关于《常棣》作者的分歧究竟何以产生?周召分陕而治,又为何“纠合宗族于成周”的是召公而不是周公?这两个问题之间乃至与《常棣》及其相关文本的形成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试论之。
一、《常棣》作者之争的形成
《小雅·常棣》作者的争议,源自两条史料,一条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欲“以狄伐郑”,富辰谏之曰: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
所引与今《小雅·常棣》相合,称召穆公“作诗”。然《国语·周语中》与《左传》同述一事,却载富辰之辞云:
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
单引“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句,称为“周文公之诗”,未提及召公。
其后,《毛诗·常棣序》称:“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郑笺》释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意召公有感周公故事,乃作诗以亲兄弟。韦昭反对这种解释,认为是周公“闵管、蔡而亲兄弟”而作《常棣》,厉王时“亲亲礼废,宴兄弟之乐绝”,召公“复修《棠(常)棣》之歌以亲之”[1](p45)。杜预与韦昭说同,称召穆公“特作此周公之乐,歌《常棣》”[2](p1817),均以为《常棣》为周公所作,召公不过是重修了乐曲。其后,孔颖达从之定谳,以周公作《常棣》,召公“重述此诗而歌以亲之”[2](p407)。
宋后疑古风起,朱熹虽主周公作《常棣》,但却疑于《左传》《国语》之矛盾,反对杜预等“作诗为作乐”的解释[4](p246)。清顾梦麟认为朱熹“偶信小序”为非,称此诗“断不为诛管蔡所作”[5](p463),其后主召公作者,即以否定《常棣》与“诛管蔡”的关联为突破口,试图推倒周公作诗说。其中以崔述证之最力,称“作”为“前所未有而创之”,否定杜预等作乐说,并以《常棣》词“每每与其事(诛管蔡)相反”,驳斥《毛序》,今人多从其论[6](p257)。
杜预等以“歌之”混淆《左传》之“作诗”,显为弥缝之说;崔述等人证《常棣》与“诛管蔡”无关,也确有依据。然而,这只能证明《常棣》与管蔡无关,却不能否定周公与《常棣》的联系,《毛序》称“闵管蔡之失道”并无主语,崔述以此为楔,全属徒劳,反倒是使《郑笺》无法立足。总体来看,前人之说虽然目标是解决《国语》《左传》的矛盾,却都是以《毛序》乃至《郑笺》的解读为起点,或牵扯两书,弥缝诸说,或在经解中寻找漏洞,以证其伪,而没有认真分析二书记载“分歧”产生的原因,以至于是否真的存在分歧,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自然无法得出可靠结论。
富辰去宗周未远,引先贤之言,当不至有失。《国语》《左传》的材料或有先后,然若没有确凿他证,偏信其一均不甚谨慎,何况同记富辰之语,差异竟如此之大,也很难因于材料的先后真伪。其实,二书并无必然矛盾:尽管《国语》引“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称“周文公之诗”,但只言句出周公,并不意味《常棣》全诗为周公所作。《诗经》词句重出,每每有之,如《小雅》中《杕杜》与《北山》均有“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北山》与《大雅》的《江汉》《烝民》也都有“四牡彭彭”“经营四方”等词,岂可以片言断定出自何诗?且除《常棣》外,尚有另一“棠棣”,《论语·子罕》:
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此诗未见于《毛诗》,但“偏其反而”与“鄂不韡韡”兴义相同[7](p501),故无法判定原本没有更多的“常棣”存在,亦即无法证明《国语》所引即今之《常棣》。
《诗经》多见“诗中有诗”的现象[8]((p32-35)。仍以《北山》为例,除与《杕杜》重句外,其三章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序》释此诗为“大夫刺幽王也”。然《吕氏春秋·慎人》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却称“舜自为诗”。可见,“溥天”一句原应是周人熟悉的名言,据传为舜之诗,后周大夫成之以为新诗。
《常棣》亦为“诗中有诗”。在格式上,《北山》与他诗相重字句,亦同为四言,未见于他诗者则多为杂言。《常棣》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五四杂言,其余均为四言,既显得极不协调,又不利唱诵。而《国语》在提及此句时,还引“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因而此句不是独创,而是一句有着多种表述的成语。《常棣》的“作者”,之所以不将其改编成为四言,或径用“兄弟谗阋,侮人百里”,正说明此句源出有自,不能轻易。
五四句式多见于早期《周颂》,如《清庙》,《毛序》称“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其诗曰:“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维天之命》,《笺》释作于“居摄五年之末”,其诗云:“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昊天有成命》亦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故而,“兄弟阋于墙”一句源于周初是可能的,《国语》既言为“周文公之诗”,应即出自一首传为周公所作之诗。以此观之,则《左传》与《国语》并未直接说明《常棣》的作者,似以周召二公相继成之,两书龃龉顿消。
实际上,在早期《诗》学传述中,对这两条材料尚无明显的取舍态度,对于《常棣》的作者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说明。如《韩序》与《毛序》义同,均未言是谁“闵管蔡之失道”[9](p562)。且《鱼丽序》又称《小雅》:“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以《常棣》为文武治内之诗。《小雅谱》还云:“《常棣》闵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诗?”说明郑玄之时,尚有《常棣》为文王之诗的说法。
依学者考证,按《毛序》之例,“闵管蔡之失道”当是稍晚形成的“后序”[10](p34)。即便此说并非后出,《序》素有标明作者的习惯,如《大雅·公刘序》称:“召康公戒成王也。”《民劳》称:“召穆公刺厉王也。”而《常棣》尽管有《左传》《国语》之说,《序》仍未肯据言“某公闵管蔡之失道”,也足以明异。至于《毛序》他说,燕兄弟、行亲亲即为“治内”,故而“文武治内”“文王之诗”的说法与《韩》《毛》“燕兄弟”之说并不矛盾。综上可见,在早期诗学的传述中,是将《常棣》看作宗周礼乐制度、即“燕兄弟礼”的成果,并不归于某人的独立创作。
以上分析《左传》自有其证:《左传》虽未提及周公作诗,但富辰在“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后又曰:
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
其既曰“召穆公亦云”,说明“富辰”并不以召公为独创。他对“周公封建”与“召公作诗”的阐释,显然是将《常棣》诗义与“封建亲戚”的举措联系起来的。而“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的因果逻辑,说明在富辰看来,周诗、周德与周礼是相辅相成、甚至俱为一体的关系:一方面诗(“莫如兄弟”)将周德(“周之有懿德”)形象化,为礼制提供指导(“故封建之”);另一方面,诗本身又在礼乐体系内,其制作是周礼的要求,是周德的体现,召公是绍周公“怀柔天下”的懿德,行纠合宗族燕兄弟之礼而作诗。诗的义旨本就是“周德”的题中之义,“莫如兄弟”“捍御侮者,莫如亲亲”,则源自周人传颂的旧话,召公不过是将这种义旨与表述,再次表达出来,故称“召穆公亦云”。因富辰从周公封建引出话题,参以《国语》之说,故富辰应认为这种表述是源自周公的。
循此思之,《常棣》并不被看作是由某人毫无依傍地独立创作完成的,其中包含有传为“周公之诗”的内容,只不过召公对于《常棣》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左传》《国语》看似矛盾的说法,则源于二者关注重点的不同:《左传》经传色彩浓厚,偏重于义理的说解,虽以周公封建之德出发,但都是围绕诗句阐发主张,论点以诗义为据,侧重赞周之懿德与召公纠合亲族之义,故只提“召公”。《国语》则有着事语的特征,富辰谏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1](p45),是由史事出发,考虑的是实际的政治情势,其重点不在诗,而在富辰之“语”,引诗不过是为点出“虽阋不败亲”的结论,故只称所引句为“周文公之诗”。后人对《常棣》作者的争议,实质上是因将材料与语境割裂开来,从而产生了误读。
在春秋人乃至早期《诗》学的认知中,《常棣》是“燕兄弟”的仪式用诗,也是周德、周礼的产物。无论具体有谁参加了创作,诗最终都要纳入礼乐制度中运行,“歌颂之作,事归天子”[2](p608),而不归于作者,无法简单地归属其创作权。正因如此,《韩》《毛》才不言《常棣》作者,只称其为“燕兄弟”“闵管蔡之失道”,而《小雅·鱼丽》以上诸篇,虽不是同时而作,《毛序》却统称为“文武治内”之诗。
二、召穆公“纠合宗族于成周”而继作《常棣》
《毛序》与《韩序》认为《常棣》的创作旨义在于“闵管、蔡之失道”,然从《左传》富辰之言看,“周公吊二叔之不咸”的措施是“封建亲戚”而非作诗,纵作诗也是歌封建之义;召穆公作诗是感“周德之不类”,若说有启于周公,也是封建之懿德乃至周公之诗,并非“闵管、蔡之失道”。富辰所举两例是并列的关系。故而《左传》无法支撑毛、韩之说,《国语》更未提及管蔡,亦即二书不能为《诗序》提供依据。
对于“闵管蔡”说,古人早已怀疑,今人援引考古资料,驳之更详,故不赘言[11](p296)。如前论,《常棣》是在“周文公之诗”的基础上,由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纠合宗族于成周”促成的。尽管很难考证“周文公之诗”的原初背景,以及从周公之诗到《常棣》的具体演变过程,但《常棣》文本的最终形成,都是召公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政治背景、礼制框架下完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故而,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常棣》的创作背景。
关于召公促成《常棣》的年代,杜佑由“周德之不类”,推断是召公于厉王时赋于东都,孔颖达等从之,其后经解多执着于作者之争,较少讨论具体形成年代。今人则多主作于宣王时,如孙作云认为《常棣》中许多话是“影射‘彘之乱’的”,成于宣王之初[12](p376)。刘毓庆也认为《常棣》成于“厉王朝的大动乱”之后[13](p203)。不谈《常棣》的前文本与周公的问题,无论其确在厉王还是宣王,召穆公同《常棣》产生联系与厉王之乱有关,此为诸家之共识。
在以宗法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下,西周“封建亲戚”的同时,以一种“恩惠换忠诚”的方式,维系周王的权威与王朝的运转。随着亲尽恩疏,以及周王实力的下降,诸侯与周王逐渐疏离,周对东方的控制松动;同时,周与猃狁的战争频频失利,生存受到挤压,由于周王持续赏赐、分封,以姬姓为主的畿内贵族日益增多,力量不断膨胀,周王领土财产随之削减,由此构成了尖锐的“结构性冲突”[14](p142)。周厉王为摆脱危机,采取“专利”的行为,转移分化贵族财产,并重用“荣伯”,激化了矛盾,酿成了“彘之乱”[15](p318)。
通过对《五年琱生簋铭》等考察得知,召穆公作为宗子,极力维护宗法,重视兄弟亲情[11](p296)。《国语》载其曾谏厉王“弥谤”,主张保守传统礼制,反对厉王的举措[1](p11)。“彘之乱”使天子威严扫地,“诸侯不享”[1](p14),天子与亲贵的关系更加疏远,宗法秩序濒临瓦解。这种情势应即富辰所说的“周德之不类”,召公难免对此感到忧虑,这与《常棣》的内容以及《左传》的描述是相合的。
厉王被逐后,共伯等姬姓贵族执政,标志着周王与渭河贵族对抗的失败[14](p156)。而后“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16](p252),是为周宣王。宣王吸取教训,改变“专利”的政策,复行封建,封弟友于郑,冀以兄弟之国藩周,又将申、吕迁往南阳盆地,控制东南,同时纠结诸侯多次征伐淮夷,通过经营东方来缓解土地财政紧张以及西北的压力。
宣王一方面以武力重树权威,迫使诸侯复朝,甚至干涉鲁之嗣任[17](p1527);另一方面加强与东方诸侯,尤其是诸姬的联系,如《大雅·韩奕》载姬姓“韩侯入觐”,宣王赐命,并令其“以佐戎辟”,《毛序》更称此诗为赞宣王“能赐命也”;又《烝民》命仲山甫“出纳王命”,往齐筑城,控制大东。依《左传》与《常棣》之辞,且参考铭文所载召公事迹,可知宣王的策略与召穆公的主张是相合的。相比于厉王对封建带来危机的反抗,召公赞扬封建传统,主张团结亲族,恢复亲亲秩序。同时,召公作为拥立宣王的实权人物,在周发挥着极大作用,《大雅·江汉》云:“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可见召公也是宣王一朝政策倡导者与实际的执行者。
期间“召公纠合宗族于成周”,《车攻序》载宣王“会诸侯于东都”,《今本竹书纪年》亦言“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当即此会[18](p423)。《尚书·康诰》言周公于洛见“侯甸男邦”,并建康叔于卫,且在成周之会“主东方所之”[19](p875)。《令方彝铭》载,王命周公子明保至成周,会见训告诸侯及王室官员[20](p67)。可见,成周作为周用以“四方罔攸宾”的据点[2](p220),以及周公封建、确立“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政体的大本营,本就是会集联络诸侯之所[21](p302)。而周公家族显然在历次会同训告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也符合“周召分陕”的说法[2](p2207)。在历次成周会同中,必然要有享燕活动,《常棣》中的“周文公之诗”可能即出自历代周公会诸姬之燕乐。但后来周与东方沟通渐少,史籍及金文少见周公身影,召公在宗周发挥了更大作用,至宣王再会诸侯于成周,手握实权、且主持东征的召穆公,理所当然地取代周定公,成了“纠合宗族”的主持者,《常棣》当是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
1.2.1.2.5素养制定治疗室及配药室的各项行为规范手册,使用药品后尽早放回原处,操作后配药室的台面污垢,污渍,药渍及时清理,保洁员及护士也要定期对治疗室进行清扫,强调医疗工作者的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常棣》的形成并不孤立,《诗》中有很多成于宣王时的作品,都是在历次会合时,为笼络亲族、联系诸侯所定所用的。如《小雅·沔水》,《毛序》称其为“规宣王也”,当成于宣王时。诗中唱叹“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显然在平抑彘乱,以伦理亲情笼络兄弟,团结“邦(国)人”“诸友”。又《小雅·伐木》紧随《常棣》之后,今人考为宣王诗[22](p131)。其曰:“既有肥羜,以速诸父。宁适不来?微我弗顾!于粲洒扫!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笾豆有践,兄弟无远。”正是呼唤“诸父”“诸舅”“兄弟”,以改变厉王造成的“诸侯不享”、父舅“不来”的局面。
《常棣》是召公及周王会见诸侯,在享燕“父”(同姓诸侯宗亲,即兄弟)“舅”(异姓诸侯,即朋友)过程中,形成的众多歌诗中的一部分,其本事可从这些同时同用的诗篇中窥得大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雅·韩奕》。《毛序》释《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诗曰:
韩侯受命,王亲命之……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
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
韩侯娶厉王之甥为妻,入觐受命,“出宿于屠”时,“显父”为之践行,与诸侯相燕。韩为姬姓,始封侯与成王为兄弟[2](p475)。《笺》称:“周有厉王之乱,天下失职。今有倬然者,明复禹之功者,韩侯受王命为侯伯。”赐命韩侯,是宣王与召公“亲兄弟”、联络诸姬举措的表现,以厉王之甥妻之,更可见周为弥合厉王所造成伤痕的用心。
无论是赐命之初,还是出祖践行乃至娶妻之礼,无法避免有兄弟享燕之时。故而,《韩奕》与《常棣》的背景是一致的。依前论,韩侯入觐非孤例,周显然对众多“兄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进行过类似的赐命、享燕、联姻,所以也确实可以凭借《韩奕》,解读《常棣》之辞,并还原其形成的具体背景。
《韩奕》言“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宣王命韩时,尚追述韩侯先祖受命封建之荣与藩屏周室之责,令其继承祖志,为周藩屏。韩等诸侯之始封,多由周公主持,召公在“纠合宗族”之时,或也会追述诸侯于周公时受封之命,以及当初的亲亲之谊,故而以“周公之诗”为基础作诗也在情理之中。召公宁愿破坏诗体而不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一字,正是因此句即周公燕兄弟之诗,或是本出自周文公之口,甚或是周公封姬姓诸侯时的命辞,后入乐用于燕兄弟。
同时,《常棣》叙兄弟之情,后半却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似乎突兀。而由《韩奕》可知,正如周王以汾王之甥妻韩侯,当时也会有着众多赐婚联姻之事,使“父”“舅”与周王形成进一步的血缘关系。《常棣》末云“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因其妻同为周戚,与宣王的关系自然更近一层,此言既是祝福诸侯家庭和乐,同时也提醒他们从姻亲角度考虑,更加珍惜与周的情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常棣》应是召公与姬姓亲族相燕时,在传为本自“周公之诗”的旧乐基础上,结合当时情景,补充修订、继作而成。在召公之前,也许有很多人继周公参与了《常棣》的创作,召穆公后,亦当有瞽史编辑,但召公显然对《常棣》的定本发挥了决定作用,故《常棣》既可称“周公之诗”,又可称“召公所作”。
三、“常棣”系列文本的生成
《常棣》“兄弟阋于墙”一句,源于“周文公之诗”,另外,古籍中尚有“棠棣”之残章。那么《常棣》与佚“棠棣”是什么关系,“周文公之诗”与“棠棣”有何渊源,今本《常棣》的具体形成过程如何?这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文本的残缺,很难通过比较三者得出答案,但如这三个文本存在联系甚或继承关系,便可以通过一个与三者都有联系的中间文本,即《小雅·角弓》,来补全残缺的线索。
在意旨上,《角弓》与《常棣》同叙兄弟之情,不过《常棣》主赞“莫如兄弟”之情,《角弓》则历数兄弟反目之恶。古人常并引二诗,如《汉书·杜邺传》载:
邺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爱至者其求详。夫戚而不见殊,孰能无怨?此《棠(常)棣》《角弓》之诗所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书而讥焉,周召则不然。
杜邺认为二诗所作目的相同,同时又并提周、召。《常棣》均与周、召有关,故而杜邺似乎以为《角弓》也与二公相关,可见关系之紧密。
在表达及格式上,《角弓》与“棠棣”极似:《角弓》首云“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责难兄弟疏远;“棠棣”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称并非不思念,只是相距太远。尤其是“翩其反矣”与“偏其反而”,“翩”“偏”相假[9](p795),几乎完全相同。而且《角弓》云:“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多“五、四”结构。传为周公之诗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务)”,在《常棣》中显得极不协调,但却与《角弓》格式相同。
“周文公之诗”与“棠棣”,都与《常棣》存在联系,同时前两者又都与《角弓》有着明显的类同。因而,以《角弓》为媒介,我们可以得出判断:周公之诗与佚“棠棣”应有着密切关系,二者的文本内容与体式格式是接近的,不排除共同占有一部分文本的可能。周公之诗的原貌,应兼具了《常棣》《角弓》“棠棣”的特点,四者构成了一个主题相同、有着相似格式、共同占有一部分内容的系列文本。
对于系列的顺序,“周文公之诗”在《常棣》之前是可以确定的,《毛诗序》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以之为幽王时,而刘向以为“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刺之”,为厉宣幽三王之际[9](p796),大体与《左传》所述召公作《常棣》相近。孔子引“棠棣”而非议之,又不及周公之名,故必非周公之诗,以其文观之,作时也应与《角弓》相近或同时。鉴于“周文公之诗”年代最前,所以《常棣》《角弓》“棠棣”,都当是承此而来。也就是说,“周文公之诗”应该是系列的母本。杜预以《常棣》为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虽误认为召公的贡献只在于“歌之”,但相比周公之诗与“棠棣”、《角弓》在格式上的类同,说明后两者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母本的曲调;召公在“周文公之诗”基础上所作之《常棣》,则确实可能在继承文本之外,对音乐做了很大的调整。
《常棣》等以“周文公之诗”为母本并形成系列的现象,不是简单的模仿或引用;《北山》等“诗中有诗”、内含古人之言或高级礼乐文献的模式,也非偶然个例。这种现象从本质上反映了周礼体制下,仪式乐歌等制度文献的生成方式:述而不作,因旧成篇;在具体操作上,则是以旧为新,以尊成卑。《北山》中的“舜之诗”、《常棣》的“古人有言”“周文公之诗”等经典文献,乃至用于《颂》《大雅》等高级文献,实即为一种“原型文本”,《雅》正是随着宗周礼制的运行发展,在“原型”的基础上不断衍生积累而成的。“原型”也是靠《常棣》等“表型”适用于不同的时代场景和仪式,方得以持续焕发生机①此处借用柯马丁“原型与表型”概念,柯马丁认为周代青铜器铭文,有着一个共同的、现成的礼仪语言库,这个语言库被看做是神圣的,“铭文的撰写者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表达模式,而是要在一个有限的编码中进行操作”,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原型文本(prototext),铭文的创作不能独出心裁,而是需要在这种原型文本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嵌入“在这些本质上属于述行传统的神圣语言中”。原型文本借助“表型”(phenotext)的变体,使之适用于不同场景,这样促成了礼仪文献的层累与持续生成,形成了文本系列。[23](p112-113)。
由于这种生成方式是一对多且持续发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出现内容的偏离与覆盖,以及文本层次的混淆与失序。“表型”也会逐渐成为“原型”,甚至进入其他礼仪系统,支配表型的生成。我们很难断定《角弓》《常棣》、“棠棣”在“常棣”系列中的具体位置,但《常棣》与《角弓》的完整存留,说明二者在礼崩乐坏的前夜,应该尚发挥着作用。而“周文公之诗”与“棠棣”可能随着礼乐制度的运行,在层累更迭中被召公《常棣》与《角弓》等诗吸收,额外的内容在失去礼乐载体后,或逐渐失传;或在后世“去其重”的文献编纂过程中,因残缺或重复被删除淘汰,残留在“事语”之中。
就《常棣》与《角弓》而言,它们定本时间接近,运用场合也类似,《角弓》在格式上似乎更近于母本,但这并不能说明《角弓》在系列中处于更加靠近“原型”的位置。二者作为仪式乐歌,在礼乐自天子之时,其创作形成及运行使用,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脱离“原型”。然而在同一礼仪系统,或即说在“燕兄弟”相关礼仪之内,偏离“原型”或者“上层文本”的权限,取决于创作活动的主持者,主持者地位越高,其超越“原型”限制、自由创作的权力越大。因为“原型”的不可更易性,取决于由先王、先圣所做的“神圣性”,以及由神圣性产生的经典性。普通士人、乐史的言语显然不具备这种特性,所以他们必须最大限度地“述”,创作必须以“述”的形式实现。而天子与代天子行使权力的周公、召公,他们的话语显然具备神圣性与经典性,在“述”的基础上,能更多地实现“作”。故由《左传》所述,《常棣》应是母本最核心的遗存。
这种具有鲜明等级性的生成方式,不是取决于“诗人”的自觉,而是由西周的文献制度所决定的。“制礼作乐”确定了“官守其书”的文献制度[24](p53),文献活动成为一种“职事行为”,王官运行产生的文献即为制度文献,后世的《诗》《书》《礼》《乐》多是“王官”在职事之内所作文献的汇集[25](p95)。作为仪式乐歌的“诗”,既是礼乐制度的反映,也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它的创作、使用、传播依赖各种仪式,因而既有固定的生成模式、结构风格,也有固定的功能作用与适用场合,其内容、结构、感情不取决于作者,而是取决于仪式。诗在礼乐制度的运行中,要不断修改与丰富,但这种丰富是依照现实需要而进行的,有明显的规律性、延续性,诵古与造篇互为前提,无法原创。这也就决定了礼乐文献“原型—表型”的生成模式,以及大量“诗中有诗”现象与雷同近似作品的产生。
周公、召公都对《常棣》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常棣》并非一人所作,其前文本不单是“周文公之诗”,还会有更多的“古人之言”。而“召穆公作诗”前后,又会有瞽史等人参与文本的生成。即便《常棣》重新入乐之后,随着礼仪的变更乃至崩解,诗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也难免发生无意甚或有意的更改、变易。这样持续、复杂的生成方式,使得难以将其著作权单一化,只能说其确是一首周庭“治内”之作,是周礼的产物与周德的遗迹。如果将周礼、周德之肇端归于周公,即便周公或未直接参与创作,称其为“周公之诗”,也是符合古人之逻辑的。
当东周“王官失业”后,文献制度随之崩解,礼乐文献的创作、使用及其本身,由制度的框架中离析出来。由于礼乐自诸侯出以及礼乐的散佚,乐歌的使用更加灵活,乃至“鲁有禘乐,宾祭用之”[2](p1947)。春秋后“作者”与“立言”观念崛起,在“作者谓之圣”的认知与崇拜下[26](p3591),很多文献开始被追溯源头,引用时多称“某某之诗”“某某之典”,“周公制礼作乐”说也不断强化。出于对“不朽”的追求,作者并出,战国后著述渐专,文献创作活动进入了高潮[27][28],至汉刘向校中书“以人类书”,“手著”逐渐取代“层累”[29](p224),成为文本生成的主要方式。
同时,汉代对经典文献形成方式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由视其为“王者之迹”,转变为“六经皆孔子手定”或“周公作之、孔子述之”[30](p82)。在这种情况下,《国语》与《左传》“周公之诗”与“召公作诗”的记载,自然变得难以理解。由于周公地位的提升,以及周公“制礼作乐”说的接受,最终导致《常棣》的著作权被单一化,周公的作用被不断凸显,甚至在杜预、韦昭之时,已由本自“古人之言”的制度文献,变成了“闵管蔡之失道”的“周公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