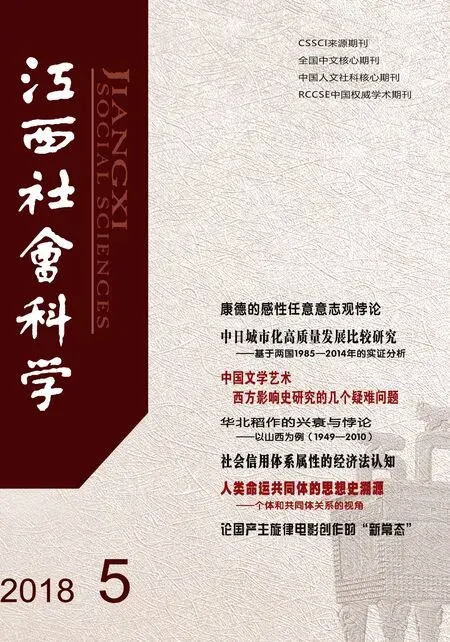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
1928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理论文章,一时之间,对于“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讨论甚嚣尘上。同年2月,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概述了“革命文学”的发起、过程和目标。他将1924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一文作为“革命文学”的滥觞。李初梨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革命文学”纲领性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以创造社同仁为核心刮起的“革命文学”风暴骤然降临,这是对大革命的反思,抑或是对文学功能的又一次定位?这成为重新研究的一个起点。就历史的大变动而言,成仿吾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并且试图去给他开一剂良药。然而就文学的功能来讲,他似乎又回到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理论的框架中,所不同的是,在使用何种思想或精神灌注上产生了区别。显然,经历了“文学革命”风暴的现代文学,已经与之前的文学有了巨大差异。而“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又有了很大不同。基于此种观念意义上的认识,通过以文学观念为中心的深层次思维来考察“革命文学”风潮内在所发生的动力机制,似乎更有利于去把握这一转变的核心要义。
一、从“建设的”到“怎样地建设”:文学观念转型的心态嬗变
从1915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式的心态逐步将“文学”推到革命的风口浪尖,经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理论文章,“文学革命”从理论论争到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的“文学”如何过渡到文学自身的革命中的。换言之,从“三界”革命到文学革命,文学从“新政治”“新道德”的社会功能到语言文字的革命是一种功能性的置换,在置换中,虽然工具的属性没有改变,但是对工具的指称已经从“文学”缩小到“语言”。与这种“缩小”的功能相伴随的是理论心态的变动。从“刍议”式的探索到尝试性的创作都显示了“文学革命”创造者的步步谨慎。而相反的,“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则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
如果仅将这种话语形式视作心态上的一种嬗变,那么则有简单化的嫌疑。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民国后的“文学革命”在政权确立、共和深入人心的时期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梁启超所倡言的破坏性的“革命”转为建设性的创造。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已经意识到“八不主义”所带有的“消极的”“破坏的”影响。所以在各处的演讲中已经更改为“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到了正式做“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时,已经彻底消除了否定性话语在文章和思想中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向,不仅是一种语言文字之于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风气上的改变,更是作为倡导者从主观认识到具体实践操作的一种理念转换。正是基于上述研究逻辑的推进,胡适在回答钱玄同“什么是文学”之问时便有了这种演化的结果,那就是“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1](P192)进言之,好的“语言文字”的表情达意就是“文学”,也因此,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转向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层层推进的逻辑演化使得“文学革命”的关注点逐步从文学转向“语言文字”,也就是说,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就是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所以改革的重点逐步推进到更深层次的更为具体的语言和文字。
与“文学革命”论者所提倡的论调相反,“革命文学”倡导者一开口便喊道:“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2](P160)文学似乎又一次回到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功能的逻辑顺序上去,其所面临的“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常常成为论调的笔锋所在。而所谓的“革命”已经脱离出“文学革命”本身所属的范畴,成为与“文学”并列的两种物事,甚至有将两者之间对立起来的矛头。从形式上讲,革命与文学并非天然对立的,然而在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文学的观念中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别与其说是一种革命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毋宁说是一种目的论所导致的结果倾向。因此,在“文学革命”者眼里,“革命”成了政治和社会改造的手段;那么,同样的情景,在“革命文学”者眼里,“文学”则常常成为对社会和政治漠不关心的代名词。也因此,两者之间关系的论争看似复杂关系的对立,其实质在精神动向上一脉相承,都是对于来自另一世界事物的一种反动。而错位视角产生的对立深化了这种矛盾,将其扩大为一种情绪化的语言,失去了文学论争应有的学理性。
如果进一步联系“文学革命”之外所提倡的另一主题,那就是“文学革命”的一大功绩在于“个人的发现”。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中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3](P5)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凸显出“人的解放”之于整个社会思想运动的功能,那么具体到文学领域,茅盾认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4](P298)由此可以显现的是,文学的个性化主张和要求成为文学独立于其他学科门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其核心的诉求则在于“个人主义”。然而,“革命文学”却主张将个人融入社会的熔炉中去,把“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化作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学生活,对于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大加挞伐;一边呐喊着“当一个留声机器”,将其作为时代“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5](P76)无论从社会革命对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诉求,还是从文学内部对于“个人主义”等思想的提倡方面来看,“文学革命”所要求“个人主义”的祛除而回归集体主义的主张,既是社会之于文学使命的一种要求,更是与社会联动在一起的文学的一种反思。
鲁迅认为:“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6](P238)但“革命文学”几乎同时承担着破坏与建设的重任,即一方面要“向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7](P238);另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展开文学革命的建设,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战线。“革命的作家不但一方面要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并且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的生命。在实际社会的生活中,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7](P143)因此,从心态嬗变上讲,胡适等谨小慎微的“建设的”言论,从否定到肯定语调的变动以及从“改良”到“革命”思想的成熟与“革命文学”大张旗鼓的宣扬与论争相比,理论自信的心态不可同日而语。进入“革命文学”阶段的理论家和创作者,“怎样地建设”已经预示了对于宏伟蓝图目标的清晰定位,即建立无产阶级文艺为社会服务,这已经大大区别于“文学革命”初期理论建设者们对于“文学革命”的定位,以及发生发展方向的把握。因此,从“文学革命”时期“小心求证”式的文学心态到“革命文学”时期大胆创造的文学心态,时代对于文学的急功近利的工具心态使得这种嬗变急促而激烈,虽然客观上也反映了一定社会之于文化的历史诉求,但更多的是文学自身的一种裂变。从刚摆脱“文以载道”的伦理道德等思想观念的束缚,又进一步陷入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纠葛,因此,这种嬗变不仅是文学研究中理论方法的一种改弦易辙,更是文化心态上的思想裂变。
二、“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功能嬗变
近代以来文学的生产与社会等领域方面的变革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古代的“文以载道”观念的余续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注重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思想在梁启超眼里已经演变为新的思想灌输的工具。在他看来:“文字不过一种工具,他最要紧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8](P4930)所以,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从工具论的角度讲,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现代演变,只是这种变动从内容上进行思想的替换和从目的上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方向。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工具论观念仍然受到新文学作家的推崇,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谈道:“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9](P9)无独有偶,罗家伦同样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工具论特质,他总结道:“思想革命是文学革命的精神,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10]据此推理,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而思想革命又是社会革命的工具。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上来,对于社会的改革,文学所起的作用大抵也仅限于此。但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文学革命”不仅意味着思想领域所载之“道”的变化,更具体表现为所用之“文”的工具性变化。因此,新文学家从“文以载道”观念所获的收益使得其在更大的程度上对“文以载道”观念进行了批判。当然,这里的批判一方面对于传统所载之“道”与今时今日的变化对比之后的理论所得,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论思想的反思。
与倡导“文学革命”的新文学作家的反思不同,“革命文学”论者积极倡导文学作为时代的留声机的功用。然而,正如论者所言:“‘革命文学’的内包如何?换言之,便是何谓革命文学(Kioestaa Revolucia Iiteraturo),连革命文学家自身,怕也弄不清楚。”[11](P1142)如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将“‘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更简单地表示的时候,便是‘文学=F(革命)’”[12](P8)。李初梨也认为:“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他的‘艺术的武器’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所以我们的作品,不是象甘人君所说的,是什么血,什么泪,而是机关枪,迫击炮。”因此,“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不是‘为文学而革命’的,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2](P166)由此一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在工具层面上实现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的革命,不仅论者在“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的转变中提供了作家之于这种转变的重要理论分析,而且提出了一种清晰的工具论思维的衍化走向。
当然,这种论调并非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论者所独创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著名论断。那么,对“艺术的武器”和“武器的艺术”的运用,实是马克思理论传入中国后在文学上的应用。所谓“艺术的武器”,即是运用艺术的工具力量来改造思想,而“武器的艺术”即是将艺术作为工具来运用,动员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文学的实践中。简而言之,“艺术的武器”即强调文学艺术的理论性,而“武器的艺术”即重视艺术的实践性。“革命文学”论者在接受马克思理论之后,结合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三种关系的命题,从工具论的角度直指这几组关系的关键联系部位。
李初梨在“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中首先关注的是作家这一创作的主体,因此他所提出的“武器的艺术”与“艺术的武器”的等同关系的成立是有先决条件存在的。其次,从“艺术的武器”向“武器的艺术”的流变,也切实抓住了时代和社会的动向以及对文学的要求的使命,所以,在流变中的工具论从“文学革命”倡导者所言的通过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进而实现社会改造为中心的工具理性转变为“文学是社会上的一种产物”,所以文学是反映一般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早在1919年12月,李大钊已经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13](P19)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观点在1924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已经演化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12](P12)到1928年,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2](P166)这表明随着“革命文学”从萌芽走向成熟,“武器的艺术”也逐渐成为“革命文学”的主要论调。最后,从目的论的比较出发,“文学革命”从一开始的思想革命工具逐渐转向关注文学本体内部的变革,而且更加注重“艺术的武器”所承载的“艺术”功能。至于“革命文学”,其从“文学革命”内部发生,在对“艺术”观念的认同上产生分歧,更加注重“艺术”与“武器”关系的结合,尤其偏重“武器”之于“艺术”的形塑,因此从“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的流变,既是文学观念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后发生变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又是反映在工具论层面不断衍化的一种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家的“艺术”与“武器”关系的理解,当时的文坛并非一味持赞成态度。鲁迅从“对方手”的角度对李初梨等人提出的观念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14](P211)显然,“武器的艺术”虽然成为社会的一种认识,但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所谓的转向,其实质是对“革命文学”的一种反动。最终,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做起“武器的艺术”的文章,大多只是一种噱头。与此同时,从“革命文学”生产的思维逻辑推理,“不革命便是反革命”的社会潮流驱使着一批批作家涌入革命的行列中,促使“武器的艺术”从论争走向共识。
三、“为艺术”还是“为人生”:文学观念从现象到实践的逻辑嬗变
如果将从“文学革命”时期到“革命文学”阶段看作文学观念流变的一条大河,那么“文学革命”是其源头,“革命文学”自然是其下游的蓄水池,而“为人生”和“为艺术”的论争则是大河的拐点。
关于“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争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文学运动的历史做一整体的概观,来厘清“为艺术”或“为人生”之于20世纪20年代整个文艺思潮的学术动力机制。
第一,文学整体观念上的“为人生”和“为艺术”是对立的。从现象出发,即使在整个文学观念领域,对于具体的“艺术何为”的问题的探讨并不能影响在风暴来临之时文学家对于整体印象的把握,鲁迅在回忆创造社与文研会成立的过程时就这一点鲜明地指出:
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15](P302)
也就是说,创造社成立初期,其在文艺上的观念并没有与文学研究会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在具体的文学倾向上表现出“重自我,崇创作,恶翻译”,因此与文学研究会形成方向上的偏差。茅盾也曾有过同样的回忆:“文学研究会这团体虽然任何‘纲领’也没有,但文学研究会多数会员有一点‘为人生的艺术’的倾向,却是事实。”[16]所以,即使在主观意识方面并没有刻意营造“创造社”与“文研会”的对立的局面,但是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影响无论是在两个研究团体之外的旁观者来看,还是在具体的集团内部的个人文学倾向上都造成一度紧张对立的艺术观念。茅盾在1921年接手《小说月报》之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两种艺术观念对立的情况:“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资料。”[17]所谓的“无所偏袒”背后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人生”与“为艺术”的理论对立。
第二,“为艺术”和“为人生”的对立不仅是文学观念背后政治思想差异的结果,而且有着具体实践层面关注点的不同。茅盾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中指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与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18]而创造社元老郑伯奇在《国民文学论》对“为人生”派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为人生的艺术’一派所主张的,或社会或文化上着眼,固然不无是处,若立在艺术的宫殿上说话,那当然是错的。人生派有两个大缺点,就是认艺术为工具,高唱空泛的抽象的理想人生。艺术只是自我的最完全、最统一、最纯真的表现,再无别的。”[19](P219)也就是说,“为人生”所关注的重点在“社会”,通过综合的形式呈现出“人生”之于艺术的重要性,而“为艺术”则将重点局限在“艺术”领域,因此也就产生了艺术的工具性理论的深入讨论。
吊诡的是,向来对于创造社等“为艺术”派理论的认识大都起源于其背后的“革命”逻辑,也就是他们在“革命文学”中所要求的文学为政治和时代服务的口号。对于文研会则倾向于认同其表现自然人生的自由主义立场及其思想启蒙的功用。这与两者在文学主张方面的反差是明显可见的。
细察之下,其实两者之间艺术观念的变动是有历史依据的。
其一,创造社和文研会在社团成立初期,对于艺术上的认识都没有过多政治干预的成分,如鲁迅所言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而来,因此一开始的论争仅仅呈现为艺术领域是“为艺术”还是“为人生”的目的,这丝毫不影响文学之于二者的重要作用,并且都将其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20](P140)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社成员在大量阅读、翻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对于文学观念的认识也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仅是文研会团体,创造社内部也产生分化,倾向于革命的郭沫若等人与保持艺术独立的郁达夫等人也产生分歧,因此在“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观念产生斗争的同时,两个团体之间的个体也产生了分化和交集。诸如此类的现象不绝如缕,而根本在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系列的文学观念的发生不仅在于时代的变动所铭刻在个体的记忆中的印象,留下了不同的痕迹,而且文学之于人生或艺术而言,仅仅只是一种工具性的理解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动的只是运用这工具的个人或团体,以及运用这工具的方式和目的。因此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而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中,学术创作和研究团体的分化导致在共同的目标和艺术手法上发生了变化,以创造社为主体的同人逐渐倡导革命的文学,将“为艺术”变更为“为革命”。而文研会成员,大部沿着“为人生”的路径,在“革命文学”高涨的年代依然站在自由主义立场进行创作,其所发生的“为人生”的变化,仅仅只是这人生随时代和社会变化而改变的“人生”,且形成一种较之于“革命”一派而渐趋保守的立场。
其二,“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不同,在文学团体活动的20世纪20年代成为排个性而尊团体的典型体现。社团的运作得益于众人的共同努力,但也与时代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后“五四”时期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得大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单靠个体的力量很难改变世界,因此,文学在融合吸纳各种不同文学观念的个体进行扩张行为,表明主观文学立场和观念的同时,也牺牲掉个体在文学团体中的声音。所以,从策略角度考量创造社的崛起,在鲁迅看来与“革命文学”的言论如出一辙,都是选择“对方手”以博得一时之名,进而以团体之力,如大量创办周报、日报、旬刊等形式进行文学活动。处处显示对立,标新立异的创造格局也使得在网罗各式的人才,尤其是青年一代,形成文学共同体的同时,呈现只破不立的动态持续。这其实已经与“五四”启蒙所倡导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相去甚远,尤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不仅大大地迈出了文学之于人生的重要关节,而且勾连起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与“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的传导管,输出思想之后撬动社会的变革不同,文学直接作为撬动社会的杠杆,不再需要思想传导的过程,而直接将文学表现为思想,省略中间环节的革命过程,也因此呈现出“为艺术”的“文学”只是纯理论的一种载体,而且是社会变革思想和理论的载体。所以,在“革命文学”时期的“为艺术”已经成长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而“为人生”的文学也开始走向社会与人生的融合,将个人融入社会,也就无所谓“为人生”还是“为艺术”。
总体而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后“五四”时期经历的最重要的文学观念转型的阶段,不同于清末民初从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等层面对“文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文学内部一场思想裂变性的革命,也不同于此后单纯地从政治干预与思想牵制等方面的理解,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包含了从外在的社会影响到内在的文学观念嬗变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这种嬗变既是对现代文学认知不断推进的一种结果化的想象论争,更是重新清理研究结果,力图与社会现实之间实现双向互动与沟通的桥梁与纽带。
[1]胡适.胡适文集(第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2]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的文学[A].“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4]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麦克昂.英雄树[A].“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A].“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9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9]蔡元培.总序[A].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0]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J].新潮,1920,(2).
[11]谦弟.革命文学论的批判[A].“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郭沫若.革命与文学[A].“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A].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14]鲁迅.“醉眼”中的朦胧[A].“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J].现代,1932,(1).
[17]茅盾.改革宣言[J].小说月报,1921,(1).
[18]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J].小说月报,1921,(1).
[19]郑伯奇.国民文学论[A].郑伯奇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20]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