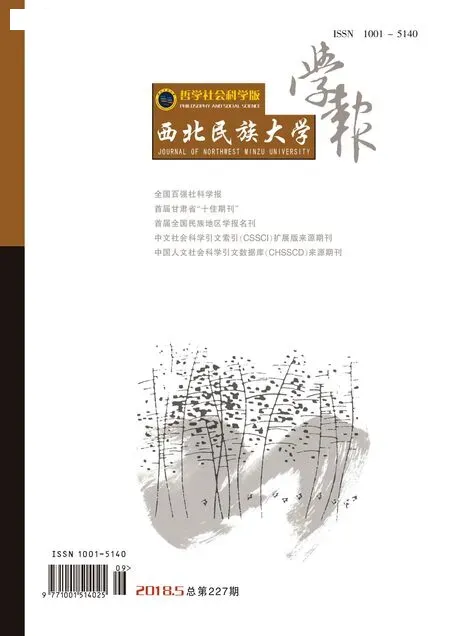日本诗话批评中的韩愈之论
胡建次,涂 亮
(1.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日本诗话是受中国诗话影响而产生、并伴随日本汉诗千余年的发展而兴衰的。日本诗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汉诗创作的格法,评论中国诗人及其诗作以及日本的汉诗及其作者,兼及日中汉诗间的渊源流变关系等。日本诗话是研究日本汉诗以及研究日中比较诗学的重要文本,它们作为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意义。韩愈是对日本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其诗文兼擅,在继承创新中注重以气脉贯穿,以奇崛之美为求,无论是近体诗还是古文创作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示出非常重要的价值,得到了日本文士的广泛关注与推扬。
一、对韩愈文学史地位的论评
(一)对韩愈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
在日本文士眼中,韩愈的文学成就颇高。菊池桐孙(1769-1849年)《五山堂诗话》云:“杜、韩、苏,诗之如来也;范、杨、陆,诗之菩萨也;李近天仙,白近地仙,黄则称落魔道矣。”[1]226菊池桐孙以“如来”譬喻韩愈,将其诗歌奉为创作的最高境界,与杜甫、苏轼二人并列,并认为其优于范仲淹、杨万里、陆游等人。
不仅如此,长野丰山(1783-1837年)在《松阴快谈》中更将韩愈作为评说的焦点,所论甚为深入。其云:
古往今来,天地之间,事物之尽善尽美者盖少矣,虽圣人犹未免焉。如汤之有惭德,武之未尽善,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是也。如韩文公之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然其文亦未免瑕颣,如《送孟东野序》户弦家诵者,而人或讥其臧。……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日月之明,有时而蚀,奚足伤其大且明哉![2]17
文能达意,非易事也。议论排奡,纵横如意,而天地景物,千态万状,及日用常近眼前琐细之事,任笔写来,未尝停手,斯能达其意矣。是在西土人亦难之,况于我乎?……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如韩文公焉[2]12。
且夫韩柳欧苏八家之文,已为千载之宗师,后之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犹作诗者不得不依沈约之韵也[2]13。
韩文公之学《孟子》,苏长公之学《庄子》,毫无模拟剽窃之痕,居然有闭门造车、开门合辙之妙[2]17。
长野丰山对韩愈推崇备至,谓其为“千载之宗师”。同时,他认为韩愈的诗文远承《孟子》一路创作取径与风格特征而来,毫无模拟剽窃的痕迹,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虽然仍有缺陷,但正如世间绝无完美的事物一样,依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值得后世高仰的。
(二)“杜韩并立”之论
日本诗话中所论及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杜韩并立”,其主要评说韩诗对杜诗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长野丰山《松阴快谈》云:
子美五七言古诗,惟韩文公善学之,至于五七律,未知属谁也。后人之诗不及子美,犹后人之文不及退之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惟二公足以当之矣[2]24。
古诗工于用韵者,莫如杜韩焉。杜诗长篇,或用一韵、短篇却屡换韵,千变万化,可以见其出入纵横之才矣。六一居士诗话曰:“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子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磋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哉?’坐客皆笑。”余谓:欧公,善论韩诗者;圣俞之言,虽出于一时之戏,亦可以悟古诗用韵之法矣[1]30-31。
韩愈擅文,韩文与杜诗并称为“千古之标杆”。同时,韩诗亦善于开拓与创辟,其承自杜诗,特别是体现在使语用韵等方面。长野丰山援引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的观点,认为韩诗用韵极妙,多用险韵,其才力之雄放令人叹为观止。他通过梅尧臣的评价来开悟古诗用韵之法,将其作为学诗之楷模。同样,中国诗话中亦多有相关论述,如张戒《岁寒堂诗话》言:“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3]458-459杜甫距韩愈所处活动时期仅二三十年,而韩愈却将他作为最重要的效仿和学习的对象,一反“厚古薄今”之风习,颇具胆识。他继承发展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奇险创新之风,并通过变化和开拓达到了与李、杜鼎足而三的艺术境界。由此可见,日本诗话对韩愈与杜甫关系的论评,呈现出与中国诗话趋于一致的评说特征。
(三)韩柳并称之论
长野丰山在《松阴快谈》中亦涉及韩、柳优劣之论,且多引柳宗元评韩文之言。韩愈与柳宗元并称为“韩柳”,盖君子和而不同,两人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在古文创作上志同道合、声气相通,开辟一条迥异于前人的康庄大道。
世儒论诗文,辄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而能公判者可与论诗文矣[2]13。
柳子厚论韩文曰:“退之所敬,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2]13-14
柳子厚评韩文曰:“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是子厚讥世之辞胜而气弱者也[2]16。
柳子厚状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而其作南霁云庙碑,皆骈俪之语,盖柳文佳者绝佳,而不免驳杂,固不如韩文之篇篇皆高古绝妙也[2]p16。
长野丰山引用了多则柳宗元对韩文的评价。前文引自《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则材料推崇韩愈之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认为他与司马迁不相上下,并胜于扬雄。因此,其谓柳宗元为“惟具明眼而能公判者”。后文引自《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认为韩文篇篇高古绝妙,推扬韩愈创作成就胜于柳宗元。东梦亭《锄雨亭随笔》云:
韩文公《示侄孙湘》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柳柳州《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二诗同韵,工力相敌。韩诗落句劣于柳,柳诗起句让于韩[2]282。
东梦亭以韩愈《示侄孙湘》与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进行对比。二诗同用先韵,功力相敌。韩诗落句即尾联“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不及柳句“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而起句即首联“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强于柳句“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二、对韩诗艺术风格的探讨
(一)关于韩诗总体风格
东梦亭《锄雨亭随笔》对韩诗艺术风格有诸多细致分析。
《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云:“天仗宵严建羽旄,春云送色晓鸡号。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戎服上趋承北极,儒冠列侍映东曹。太平时节身难遇,郎署何须叹二毛。”雍容雅丽,胜杜少陵《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高廷礼《正声》,取彼而不取此,何也?《宿龙宫滩》云:“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送严大夫》云:“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酒中留上李相公》云:“浊水污泥清路尘,还曾同席掌丝纶。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热何辞数爵频。银烛未消窗送曙,金钗半醉座添春。知公不久归钧轴,应许闲官寄病身。”此三诗虽绝妙,已开来人门户。《秋字》云:“淮南悲木落,而我亦伤秋。况与故人别,那堪羁宦愁。荣华今异路,风雨苦同忧。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宛然苏州语气。可见大家无不具诸体也[2]282-283。
东梦亭通过对韩诗的细致分析,认为创作于元和十年的《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诗具有雍容雅丽的特点,甚至胜过杜甫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韩愈《送严大夫》一诗描写桂林山水的清新俏丽,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堪称绝唱,开后来人之门户。同时,韩愈《秋字》一诗似韦应物。他转益多师,推崇盛唐诗人,未有厚古薄今之弊,甚为难能可贵。又如:
“是时雨初霁,悬瀑垂天绅。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造语俱奇,吾曹学之,恐有画虎之诮。《送无本师》诗云:“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此是诗之正路。《山石》《雉带箭》《汴泗交流》三篇,熟读玩味,可以得纪事之法也。《南溪始泛》三首,不让柳柳州《南涧中题》,黄山谷最爱此诗,以为有诗人句律之深意[2]287。
韩愈在《送无本师》中主张诗歌创作使字用语要“硬”,意在标新立异,并不主张诗的语言“佶屈聱牙”,而力图使诗歌创作达到平淡的艺术境界。同样,在这个时期所写《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归彭城》《山石》等,都体现出早期诗作清新雄豪的风格,也代表了其前期的创作水平。特别是《山石》一诗,黄震在《黄氏日钞》中称“《山石》诗最清峻”[4]。此诗作于唐贞元十六年,是一首记游诗,叙写了作者与二三子的游踪,颇具谐意。而《南溪始泛》则是其晚年名作,清新平淡,不再追求刚健奇崛的艺术风格。
(二)关于韩诗中的联句
唐元和元年,韩愈任国子监博士,结束多年的流离生活,回到长安,与孟郊等友人相会。韩愈曾于贞元十四年对联句诗进行过尝试,今重新兴起联句诗,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一个新境界。联句诗亦是韩诗创作的一大特色。虎关师炼(1278-1346年)《济北诗话》云:“予爱退之联句,句意雄奇,而至‘遥岑出寸碧,远目增双明’,以为后句不及前句。后见谢逸诗‘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觉举头双眼明’,始知韩联圆美浑醇,凡诗人取前辈两句井用者,皆无韵,而此谢联不觉丑,岂其夺胎乎?”[1]6
这两句出自韩愈《城南联句》。《城南联句》由韩愈、孟郊二人联至一百五十三韵,在联句体中蔚为壮观,诚然是“诗思孤耸”,也表现出了韩、孟二人建立在人生道义与诗学追求上的不渝友谊。
东梦亭《锄雨亭随笔》云:“韩文公《南山》诗,险语叠出,千古杰作,非大手笔不能辨之。后辈容易看过,不知斡旋之妙,谩拟此等之作,曰我学韩体。铺张杂然无复节制,多见其不知量。”[2]287
韩愈《南山》诗长达一百余韵,其创作之法类似汉大赋,连用五十一“或”字,又连用十四处叠字,险语层出、雕镂极工,将终南山描绘得穷形尽相。东梦亭惊叹其为千古杰作,非大手笔不能为之,认为后世之人难以模仿。
(三)关于韩愈“怪奇”诗风的评论
在日本诗话中也不乏对韩诗的批评之声,这主要集中在对韩愈“怪奇”诗风的论评上。皆川淇园(1734-1807年)《淇园诗话》云:
杜甫七言古诗,往往出奇语,以令其格顿高。如《逼侧行》中:“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之类,皆是奇语,而子美出奇,其意唯在以此约冗语,且使无失其神彩生色,譬犹名画用笔,大劈大画,宁失形似,无挫气势。如白乐天七言歌行,乃是俗画,但知模画象形而涂抹丹青耳,至如韩退之、卢仝,尚专尚怪奇,却亦是粗画恶笔,殆所谓里妇而效西施之病颦者矣[1]153。
皆川淇园认为,韩愈学杜甫之诗中的奇语,却剑走偏锋,沦为东施效颦。然而,事实上盛唐时期杜甫之诗已集前代诗艺之大成。为了进一步促进诗歌的发展,元和年间,白居易擅浅易诗风,韩愈尚怪奇诗风,各自形成了诗歌创作的一大方向,走出了一条诗歌创作的独特路径。而“怪奇”的艺术风格正是韩愈区别于他人之诗的创新与特点所在。
同时,津阪东阳(1756-1825年)《夜航诗话》亦云:“‘诗韵贵稳,韵不稳则不成句,故作诗必选韵,强斗险徒费力耳。……韩昌黎、柳子厚长篇联句,字难韵险,夸多斗靡,或不可解,抅于险韵,无乃庚沈启之邪?’此诫实宜鉴观,凡其音涉哑滞者,晦僻生涩者,一切宜弃舍耳。或其韵皆平稳,唯一句奇险,如油盏点水,尤可厌之甚也。”[1]334
此则诗话同样论及韩愈诗歌的奇险孤绝之处,认为其用难字、押险韵,不符合诗韵贵稳的艺术标准。清代,赵翼《瓯北诗话》曾云:“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5]1164此当为中的之论。
三、对韩诗创作手法的论说
(一)对韩诗格法的探讨
对诗格、诗法的探究是日本诗话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文士学习汉诗的主要方式与途径,因此不少论说呈现出“诗格化”的倾向。
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作诗审于用事,不可貂续偏枯,余既详言之于前矣。……韩退之《斗鸡联句》:‘成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句偏枯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盖谨之如此。”[1]391
“用事”乃谓文学作品中的寓事用典,切忌以坏续好,前后不相称,使诗文不够协调。津阪东阳借用韩愈之作来说明寓事用典需要谨慎细致。
一句中本自为对偶,谓之自对体,亦曰当句对,就句对。方板中用活时用之。……韩愈:“绛阙银河晓,东风右掖春。”……韩愈:“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右历举前修之例,学者可以取准也[1]320-321。
韩愈诗歌中常用对体,津阪东阳取《和席八》与《游城南十六首·遣兴》中的诗句为例,作为日本文士学习的标准。
唐人宴会赋诗,有同用一字为韵者。……韩愈《送严大夫》同用“南”字;《重阳日赐宴曲江亭因诏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进来,又中和节日宴百僚奉诏同用“春”字。韩文《送郑尚书序》:“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今人专分韵各探一字,不复知有是法也[1]355-356。
这则诗话重在分析唐人宴会赋诗以一字为韵的惯例。而韩愈《送严大夫》《重阳日赐宴曲江亭因诏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等,正是一韵到底的代表作。不仅如此,韩愈还在《送郑尚书序》中详细分析了这一现象,说明所选韵字都具备深层含义,是今人作诗的习效范式。
长野丰山《松阴快谈》云:“韩文公论文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可谓作文之要诀矣。”[2]11
韩愈论文重气、尚气、贯气,将“气”比作“水”,而将“言”比作“浮物”。因此,气盛与否便是写文章之关键,对于诗歌创作同样重要。
(二)对韩诗使字用语的论说
韩愈在字语使用上努力追求创新,用了很多奇语。日本诗话中也讨论到其语词颠倒的问题。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文字有颠倒可用者,‘裳衣’‘羊牛’,见《诗·国风》,此其滥觞欤。如‘图画’‘罗绮’‘弦管’‘毛羽’‘主宾’‘弟兄’‘淡浓’‘白黑’‘伊吾’‘卢胡’之类,固先后自在也,若其涉奇僻,不得流便者,前修有例,不足多效。然至其不得已,或随韵而协之,为历举古句以备副急之用尔……韩愈‘谁与同息偃’‘分知隔明幽’‘应对自差参’‘藏昂抵横坂’‘磨淬出角圭’……”[1]364
又转引《汉皋诗话》:“韩愈孟郊辈才豪,故有‘慨慷’‘珑玲’之语,后人难仿效。”按:魏武《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岑参诗‘苍然西郊远,握手顾慨慷’,扬雄赋:‘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又见《太玄经》,非创于韩孟也[1]366。
《初学诗法》云:“《艺苑雌黄》云:古人诗押字,或有语颠倒而无害于理者。如韩退之以‘参差’为‘差参’,以‘玲珑’为‘珑玲’,是○笃信。案:古人诗曰:‘俯仰迷下上’,又诗书置后先,又后日悬知渐莽卤之类是也。或以‘慷慨’为‘慨慷’,以‘新鲜’为‘鲜新’,以‘经纬’为‘纬经’,以‘稗’为‘稗’,以‘圭角’为‘角圭’,以‘参差’为‘差参’,以‘唐虞’为‘虞唐’,以‘红白’为‘白红’,以‘俯仰’为‘仰俯’,以‘玲珑’为‘珑玲’。又《汉溪诗话》曰:字有颠倒可用者,如罗绮绮罗、图画画图、毛羽羽毛、白黒黒白之类。”[6]236-237
韩愈才气雄豪、所作之诗奇崛颠倒,尽显怪奇风貌。同时与孟郊最为莫逆,是忘年之交、诗歌同盟,并开启韩孟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韩愈诗中所用“慨慷”“鲜新”“稗”“角圭”“虞唐”“珑玲”等词汇,既有对以往诗歌艺术表现的继承,更多的则是自身的独特创造,是韩愈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
林荪坡(1781-1836年)《梧窗诗话》云:
咏物最难矣,欲形模明备,则拘泥而近俗;欲象似婉曲,则乖离而远真[1]286。退之诗:“谁谓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风漪。”曰竹簟名含风漪,后人多用之。范成大诗:“一声霜晓谩吹愁,八尺风漪不耐秋。”……皆滥觞于退之[1]286-287。
咏物之作,最难求神似。韩愈以含风漪谓竹簟,正可谓得竹簟之神韵,为后人所赞赏与仿效。不仅范成大之诗,陆游《乙夜纳凉》亦云:“八尺风漪真美睡,故应高枕到窗明。”
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
韩文公《杂诗·此日足可惜》凡百四十句,通押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韵。《天厨禁脔》示古韵法,举以为证,盖七韵原为一部,似非叶音。顾宁人讥文公不识古韵,盖谓此篇及元和圣德之类,李光地辩之详矣。邵本,真文六韵从郑庠,而东冬江阳七韵一部独有异同,亦未详其故也[1]342。
“假对”,即借声对,以音取对也。然非较著者不为也。……韩愈:“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热何辞数爵频。”“爵”与“雀”通[1]356-357。
此二则诗话论及韩诗之声韵表现,韩愈才力雄豪,声律运用无不谐当,正可作为日本文士模仿的范本。
四、韩愈之论形成溯由
(一)中国诗话的传播与影响
日本诗话的兴起与中国诗话的大量传布密切相关。日本诗话最早可溯源于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作为“日本诗话之祖”,此书引用了大量中国诗话,为之后的日本诗话写作提供了范式。
市河宽斋《半江暇笔》云:“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式》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6]215
在经历了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诗话即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和第二部诗话即林梅洞的《史馆茗话》之后,由于中日两国较为频繁的信息交流与文化传布,最终促使日本诗话创作在江户时期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
《日本诗话丛书》是研究日本诗话的基本资料,共收有日本诗话59种,其中20家日本诗话引用中国诗学著作就达115种之多[8]207。日本诗话将中国诗话奉为圭臬,无论是创作旨趣还是文笔体例都明显留下了中国诗话的痕迹。由于文学思想性的传承,日本诗话中常常出现与中国诗话一致的结论,大量的日本诗话深受中国诗话的影响,多采用中国诗话的基本体制与言说方式评论杜甫、李白、苏轼、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诗作。而韩愈正是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诗论家除了认同中国诗学批评中的韩愈之论外,当然也时有自己的见解,这使得日本诗话逐渐出现本土化的特征,以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
(二)日本文士的推崇
韩愈古文被日本文士喻为“千载之宗师”。自日本足利时代开始,就有虎关师炼大声疾呼摒弃四六、回归韩柳之道,并身体力行,多有仿作。他推崇唐宋之文,对韩愈之作尤为叹服。同时强调复兴古文,反对骄丽文风,主张贯道、载道统一。他在《遇衡》中云:“予谓贯亦裁也,唯因物而异也耳矣。索之于钱也,贯犹载也。”认为“文章妙处,天然浑成万世一律耳。人或诚心覃思而自合也,若未至天浑之处,虽工有可改之字,虽奇有可换之言。若已至于天浑,自然文从字顺,格调韵雅,权衡齐等,不可移动,所谓醇乎醇者也。”[9]697-698在《答藤丞相》一文中,他希望关白藤原内经“从容谕明王,使天下学古文、跨汉唐、阶商周”,使“文明之化,兴于当代”,敦促统治者自上而下倡导古文、废弃骈俪之文。然终是形单影只,从者不众,未成气候。至德川时代,韩柳古文才真正成为日本文士的标杆。
韩愈作为唐代诗人的典范为日本文士学习与推崇。韩愈把“文以载道”放在第一位,同时主张“余事作诗人”,把抒忧娱悲的社会作用放在第二位。这个思想也与日本文士形成了共鸣。东梦亭就深受韩愈之论的影响,他在《锄雨亭随笔》云:“余壮年托苻栗斋刻韩文公‘余事作诗人’句,以为引首印,年过五十,毫无所成,然读书工夫,老而益壮。文公诗:‘吾老著读书,余事不挂眼。’欲取此句,更刻一印,恨无铁笔如栗斋者。”[2]304-305
此外,雨森芳洲“文宗韩欧”。伊藤长胤在《秋夜即事》诗中云:“字从羲献更无字,文到韩欧真是文。”[2]148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云:“海青陵皋鹤,诗文宗韩,尝为余诵其《秋夕》一联云:‘细视星成字,静听虫诵书。’只此十字的是昌黎。”[1]220学韩著名者还有赖襄,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称其“才高学博,刻意韩苏,魄力雄阔,最邃史学,故运用古事,镕铸剪裁,别开生面,七古排奡纵横,沉郁顿挫,具有昌黎、眉山之格律,近体亦精炼雅健,声调铿鍧,寓绮丽于雄浑,实不忝近世之哲匠矣。”[2]221
菊池五山(1772-1855年)亦直言:“余十年以前作诗,开口便落婉丽,绝不能作硬语,尝有‘画帘半卷读西厢’之句,为人所诵,冈伯和讥为女郎诗。尔后欲矫其弊,枕藉韩苏,方且有年,始得脱窠臼。”[1]198又云:“余诗见屡变。少时例趋时好,奉崇李、王,小变为谢茂秦。亦皆弃去,既学温、李、冬郎,年垂三十,始窥韩苏门户,颇有所悟,一切谢纤弱者。”[1]200-201
菊池五山正是通过习学韩愈之诗、作硬语、谢绝一切纤弱者,才摆脱被讥为“女郎诗”之创作弊病的,其终成日本诗坛一代大家。
(三)唐宋诗之争的影响
孙立在《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指出,“古文辞派以来,江户乃至明治时期的文学思潮基本上是围绕着宗唐还是宗宋展开的,这是儒者诗派之后江户、明治文学思潮变迁的显著特征。”[8]87这在日本诗话家对韩愈的论评中也体现得颇为明显。
友野霞舟(1792-1849年)《锦天山房诗话》记:“江村绥君锡曰:‘元和以来,从事翰墨者,虽师承去取不一,大抵于唐祖杜少陵、韩昌黎,于宋宗苏黄、二陈、陆务观等,至云溪,始右唐左宋,而犹未及初盛中晚之目,沧州出而后,始以盛唐为鹄。’”[2]159
长野丰山《松阴快谈》亦云:“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而唐宋诸家各有悟入自得处,都不一般。如韩柳欧苏王曾之文,欧虞颜柳蔡米苏黄之书,莫不皆然也。学之者亦各学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诸饮食,各有所嗜,以我炙而笑人脍,不已騃乎。”[2]24
在唐宋诗之争中,韩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虽然是唐代诗人,其诗歌却具备典型的宋诗作派,包括题材抒写、创作取径、意象运用、意致表现、艺术风格等。镰仓、室町时期的日本诗坛,宋诗广为流行,同样包括具有宋诗风格的杜甫、韩愈之诗。韩诗与宋诗类似,是由于北宋前、中期社会政治形势与中唐贞元、元和时期相似,而思想意识上的复古创新之风也颇为相近,故诗坛上出现了一股学韩而自创新调的风习。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思想影响了晚唐诗人,向下则启导宋人,其奇崛险怪的创作风格也被宋人继承与发展。唐宋诗之争客观上提高了日本文士对韩诗的关注程度,促进了日本诗话对韩愈评说的高频度出现。
(四)明代复古之论的辐射
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批评,与唐代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之间存在颇为密切的联系,而明代复古理论批评同样是日本诗话讨论的焦点。
韩愈开启了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具有独特历史地位与作用。长野丰山《松阴快谈》云:“明李于鳞、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果剽窃诗书耶,其引诗书必曰诗云云,书云云,至自撰之语,未尝攘诗书一语,是韩文公之所以去陈言也。物茂卿云:‘退之去陈言,而古则荒矣。’吁!陈言腐语可以为古哉?不思之甚。如于鳞《比玉集序》,读之似谜语,诚徘优之语哉!”[2]20
此则诗话重在例说韩愈“务去陈言”,“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创作主张。韩愈反对陈词滥调、软弱庸俗的“大历诗风”,强调用变化与创新代替陈言旧语,用硬语生新来消解软弱庸俗,倡导“词必己出”,不剽窃前人一字一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长野丰山认为,韩愈所倡“古文运动”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之论存在本质区别,李、王二人仅为剽窃古语古意,并无实质性开拓创新,与韩愈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追求是相背离的,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芥川丹丘(1710-1785年)《丹丘诗话》云:“王敬美曰:‘学于鳞不如学老杜,学老杜尚不如盛唐,何者?老杜结构,自为一家言,盛唐散漫无宗,人各以意象声响得之,政如韩、柳之文,何有不从《左》《史》来者?彼学成而为柳为韩,吾却又从韩、柳学,便落一尘矣。轻薄子弟遽笑韩、柳非古,与夫一字一语必步趋二家者皆非也。’余谓:旨哉斯言也!近物子首唱明诗,海内向风,夫人诵法于鳞,而争事剿窃,神韵乃乖。‘青山’‘万里’,动辙盈篇,纷纷刻鹜,至使人厌,岂谓之善学邪?余常诲学者曰:‘善学于鳞者,不肖于鳞。’听者莫不骇然,或疑或惑,而余自以为知言。假使王敬美听之,则必欣然莫逆耳。”[1]82
王世贞作为明代复古之论的代表人物,强调“文必秦汉”,相对于韩柳之文,他更推崇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这个思想也得到相当一部分日本文士的响应,并与主张习效韩柳的学者进行了论争。
同样,冢田大峰(1747-1832年)《作诗质的》云:“韩退之贬潮州刺史《次蓝关示侄孙湘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计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诗词情格调与臻矣,使人感慨焉者也。于鳞何不选取焉。”[6]402-403
明代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李攀龙《唐诗选》未选中唐元和年间韩愈的代表作《次蓝关示侄孙湘诗》,冢田大峰颇为不平,认为韩愈此诗“词情格调与臻矣”。而这正是部分日本学者对明代前后“七子”诗学理论批评的反驳。这些论述都从不同侧面提升了日本文士对于韩愈诗文的关注程度,也显示了日本诗话批评对他的普遍推扬。
综观日本诗话批评中的韩愈之论可以发现,日本诗话家们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学批评中的韩愈之论内涵,他们在承纳中有衍化,并有所创见,这从一场域反映了韩愈在东亚汉文化圈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韩愈是日本诗话批评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文人,其作品成为日本文士谈诗学文之摹本。然而,日本文人对韩愈并非盲目推崇,而是融入自身独特的持见与思考,他们所论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展衍了中国传统诗学批评中的韩愈之论,为韩愈作为东亚著名文人形象的不断建构与树立作出了贡献。由于日本诗坛的时代环境、唐宋诗之争的影响等,日本诗话批评对于韩愈的论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深入考察日本诗话批评中的韩愈之论,对进一步理解韩愈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