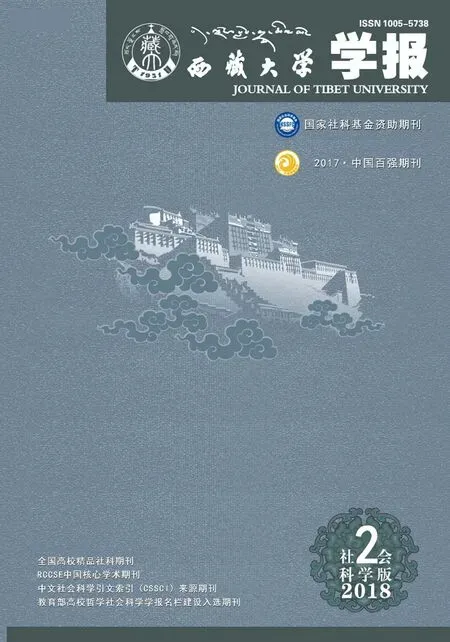民国时期拉萨城市生活初论
邹敏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诸多因素,民国时期(1912-1949)人们对雪域高原中心之城——拉萨的印象,大多是封闭、落后、中世纪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这个词语,似乎与拉萨没有任何关系。但事实上,民国时期,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推行“新政”等,“现代”的影子开始在拉萨出现。对于近代中国的城市而言,“现代性”不是被强加给某个城市的“既定项目,而是一组新机会,是能以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随意挪用的一组新工具”,从而形成不同文化在同一个城市中相互适应、渗透,并逐渐形成更为广泛的文化与物质的变迁,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生活的特征[1]。内地城市是“文化拼凑”的,放之藏区城市,也基本如此——文化交融、文化拼凑。现代性带来了拉萨城市生活的变迁,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但拉萨又与内地其他城市存在明显的不同,一是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二是更多的保留了传统。
本文选择考察民国时期拉萨的城市生活,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推动了西藏地方的现代化;二是这期间中央政府着力于改善与西藏地方的非正常关系,地方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一直在持续;三是期间抗日战争推动了拉萨商业的畸形繁荣,以上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拉萨的城市生活。
一、现代因素
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期间,“广泛接触了国外的新事物与新知识”[2],如英国在印度施行的政治统治,乘坐现代化的火车和轮船,参观印度的兵工厂、造币厂等现代化的机构,见到电灯、电话、电报、照相机等现代化的产品,这使得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一是他开始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表现出较强的兴趣;二是他开始“赞成现代思想”,并认为“现代思想”对西藏是有帮助的,“希望带领自己的国民①国民:当为“民众”之意。一起去推行。”[3]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着手推行“新政”,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藏军、改革噶厦组织机构、培养新式人才、创办近代实业等方面的举措。系列举措为拉萨注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并直接影响了拉萨的城市生活。
(一)新式藏军
达赖喇嘛在1912年“新政”之初对藏军进行整编、扩军,至1929年,藏军拥有10个代本团,1个贵族兵团和2个警察军营。1948年,藏军又进行了新一次的扩军,增加了4个代本团。这些藏军中,有3个代本团驻于拉萨的罗布林卡、鲁古广场和拉萨北郊,1个警察营驻扎在八廓街②八廓街:藏语音译,汉语也写作八角街。的冲赛康③冲赛康:藏语音译,也写作冲色康,根据藏语原意,可以解释为“观市房”“购物处”。达瓦.古拉萨城市历史地名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7-48.。
新式藏军“废弃了原传统的仿照汉军的旧制,改立为以外国洋式军建制”,[4]除了派遣贵族子弟、青年军官前往英、印学习考察现代军事编制、训练外,也聘请英、印军官为藏军教练。这些由英人训练的新式藏军,“操典、口令、军服也概为英式”,士兵们还会说简单的英语;藏军军旗也以“英国国旗为底,上有雪山及狮子一头”[5]。军队的变化,在拉萨吹起一股“英风”,推动了上层贵族对英式生活的追捧。
(二)警察
1923年,十三世达赖在拉萨增设“波利斯列空”即警察局,主要负责刑事案件和维持社会治安,其职责与“朗仔辖”列空④朗仔辖:藏语音译,汉语也写作朗子夏、朗子厦、朗孜夏等。朗仔辖列空负责拉萨的治安、卫生、税收、游民登记等事宜。有相同之处。
拉萨警察的境遇非常糟糕,他们“待遇极差”“每天上岗的时候,还抽空缝制藏靴,以贴补家里的生活”,“服装单薄,冬春两季,……在岗亭里冷得够呛,只好找个暖和的地方蹲着,一边晒太阳,一边纳靴底。”[6]这就是拉萨警察的常态了。查普曼描述的拉萨警察也大致如此:“我看到警察部队的一些人沮丧地坐在哨亭里纳着鞋底或干其他杂活”,“大门边有一个木制的岗亭,一位‘警察’正坐在那里,一会儿纳羊毛靴的靴底,一会儿数念珠。当我们过一片水洼地并溅起水花时,他全然不知……他身穿一件褴褛的旧式卡其布上衣,戴着一顶破旧的太阳盔,下身穿着褴褛的裤子和靴子,脸脏得出其(奇)。”[7]
拉萨警察平日缺乏训练,“既没有警哨也没有手铐”[8],他们有英式步枪,“但是没有子弹。步枪总是挂在岗亭附近的牟(某)颗树上,顽劣的街童常常把他们扛走,拿去做游戏,或者抖威风。”[9]
警察虽然负责维持社会治安,但是他们糟糕的境遇和低劣装备,加上朗仔辖的继续存在,以及西藏地方宗教传统的保持,使得他们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比如每年的传昭大法会期间,拉萨警察都要按惯例退出,将城市治安交由铁棒喇嘛负责。在此期间,无论僧俗,都受铁棒喇嘛管辖。因此可以说,警察的出现,只不过是拉萨多了一个新事物而已。
(三)电灯与邮电
从1913年开始,十三世达赖逐渐派出4名贵族子弟前往英国留学,他们分别在英国学习机电、矿业、邮电和军事专业,于1921年返回拉萨,随即投身于近代实业中,为拉萨的城市生活注入现代的因素。
如学习机电的强俄巴·仁增多杰返回拉萨后,在拉萨夺底修建了夺底水电站。该电站于1928年开始运转发电,最初仅向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供电。到1936年,大昭寺、小昭寺、热振活佛和司伦朗顿的官邸,以及“住在八角街的贵族、商民群众家里都安装上电灯”[10]。这座水电站一直运行到40年代后期,由于发电机严重磨损,才停止运行。
夺底水电站出现以前,拉萨人日常照明以酥油灯为主,20世纪初,藏商“从印度购进蜡烛,在拉萨出售,引起一些贵族和大商家的兴趣,于是他们在节日或宴会时用蜡烛照明”[11]。此外,随着印藏贸易的发展,汽灯作为一种新的照明用具,被引进拉萨,“有财力的都使用汽灯”[12]。电站的出现,将电灯带入人们的生活,“当时布达拉宫、街道及许多私人住宅都是灯火通明”[13]。不过由于供电紧张,夺底电站曾采用“封电”办法供电,即“暂时切断不急需用电户的电源,只限他们节日使用”[14]。
1925年,噶厦政府铺设拉萨到江孜的电信线路,设立电话电报局,随即又开通拉萨到日喀则、阿里、黑河、昌都的无线电路。[15]1948年,又设立了拉萨与昌都之间的电报局,老百姓和商人均可发报;同时,“拉萨、昌都之间建立了无线电话……这种电话,不论那(哪)个老百姓都可使用,每分钟收费五两银子,对商人非常方便。”[16]
新式藏军、警察、电灯、电话、电报等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因素在拉萨的兴起。但也要看到“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较量,以及在等级森严的西藏地方,并非所有的拉萨人都可以享受“现代”的内容,他们更多的是为上层人士服务的。
二、贵族的生活
西藏贵族多爱好城市生活[17],“通常藏官及世家多聚居拉萨,不愿他去”[18]。贵族不仅拥有权势和地位,而且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料,生活大多奢侈。民国时期,随着西藏地方商业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后期,因日军控制滇缅公路,使拉萨成为物资中转站,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国度的各种商品涌入拉萨,“拉萨市上,于各项奢侈品,无不应有尽有”[19],在八廓街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买的”[20],极大地刺激了贵族们的消费欲望。西方的生活方式随着贸易的发展和交流的增加,逐渐被引入拉萨,汉式的生活方式也持续被引入,从而在拉萨的城市生活中形成一种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拼凑的现象。
(一)贵族的宅邸
早期拉萨贵族多集中于市内的八廓街,民国时期受“英风”的影响,贵族们开始向城外搬迁,在拉萨郊区和拉萨河畔修建新式的花园别墅,在庭院中种植松、柳、果木。首先在城外盖起花园别墅的是思想新潮的车仁家族,随后是察绒·达桑占堆,他在拉萨河畔建起三层楼的花园别墅,成为全拉萨最漂亮的房子,其他贵族纷纷仿效[21]。这些新式宅邸虽然外观仍是藏式的,但在室内布局和装饰上都受到了“英风”的影响。
首先是窗户,早期贵族宅邸的窗户都是“用藏纸和布类密封的”[22],但这些新宅邸却多使用玻璃窗户。比如一位噶伦的府邸“房间按藏式风格装饰,但有一些玻璃窗”,宇妥的庄园安装着从印度驮来的“小格玻璃”[23]。擦绒庄园是“藏式庄园与英式农舍的结合”“窗子带有窗屏,整扇窗子镶着玻璃”[24],主楼顶棚“镶嵌着大块的玻璃”,东西两侧的卧房“朝南一面是落地大玻璃窗”[25]。
其次,室内陈设也开始仿照欧式风格尤其是英式风格,尽管起初可能有些邯郸学步的意味。如英国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曾于1921年拜访拉鲁府邸,对于其中一个英国式陈设的房间,他写到“此室非常暗淡,殊令人作不快之感想”[26]。但1936年到达拉萨的查普曼却没有这种感受,他只是如实地描述噶伦家“使用的是欧式桌椅”[27]。
擦绒新宅“外表为藏式”,内部却“带欧风”[28]。其府中很多英式家具,主卧室有弹簧床,还装有西式抽水马桶的新式卫生间[29];“一个房间的家具是英式的”,还有“一间自来水的舒适浴室”[30];另有一间很大的大厅,兼具佛堂和客厅的功能,“其内有一座很大的佛龛……前面是一张雕刻精致的桃木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百零八个银制的净水碗和一些银制的酥油灯具”,厅内还有擦绒的“两英尺高的坐台……坐台的前面有一种雕刻精美的漆木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银制净水壶、杵铃和一个玉石茶杯”,厅内还有“约一英尺高、三英尺宽和十八英尺长……内装有鹿茸毛”的坐垫,3张漆木桌子,以及其他银制的茶杯,地上是大理石,“总是闪闪发光”,墙上挂着精美的唐卡[31]。足见擦绒家在室内陈设上是英式、汉式和藏式的结合。
(二)贵族的饮食
民国时期,汉地的食品和蔬菜水果已经成为拉萨贵族日常饮食的基本构成[32],“上流社会的风气,每天总要吃一次中国菜”;“中国料理越发盛行,因而吃米饭的风尚大起”,以致米饭成为拉萨贵族们“常食的一部分,而且也使用筷子”[33]。此处所谓“中国菜”,系民国时期的习惯翻译,指来自内地的蔬菜。[34]不过,拉萨贵族在追崇汉地饮食的同时,也追崇西式的饮食。
上世纪30年代,查普曼在一位噶伦家午餐,先是“喝印度茶,吃饼干和杏干”,随后呈上的是“瓷碗里香甜的温牛奶中有三个香味扑鼻的饺子”“配有筷子和垫瓷碗用的藏纸方巾,每一道菜撤走后都要重新更换纸巾”。略微休息后,上小菜,有“洋葱胡萝卜炖羊肉、罐头鲱鱼、干虾、切好的绿桃、蜜枣、蜜饯、西瓜子、核桃、蒙古烤肉、牦牛口条、酱牛肉和水煮白肉”,每个人都有“一小碟作料(可能是酱油)和一个小瓷勺”“主菜盛在一两个漂亮的汉式大碗里”。整个午餐共上了15道菜,包括烧汁鱼翅、金枪鱼片、海参猪肉汤、洋葱鳗鱼、鲨鱼肚、芹菜、白菜、胡萝卜、果汁、蒸米饭、果酱包和蛋糕、甜面包干以及花形、桃形及马蹄形的点心等。[35]
可以看出,整个用餐过程非常考究,以汉式菜肴为主,食材丰富,包括从内地引入的蔬菜,如白菜、胡萝卜等,昂贵的海参和鱼翅,也有印度的茶饮,西式面包,可见中西饮食文化与西藏地方饮食文化的融合。
查普曼在擦绒家作客,餐前“擦绒夫人从一个银茶壶中倒出上好的大吉岭茶”,并给大家端出“面包、黄油、糕饼、硬硬的小圆面包及冰镇补丁”,均为西式饮食,擦绒还有“曾在印度培训制作欧式糕点及菜肴”的厨师。[36]
查普曼对在另一位噶伦家用餐的记载是正餐“以常见的无数快餐开始(有海参、鱼翅、鱼肚),以米饭加各种菜肴结束”[37],对于海参、鱼翅、鱼肚这类昂贵的食材,他使用“常见的无数快餐”,足见这类食材在拉萨贵族中的普及,怪不得时人称“拉萨世家官吏……偶或宴客,则海参鱼鳍应有尽有”[38]。
西式的饮品在拉萨贵族中也颇受亲睐,咖啡、威士忌、白兰地、薄荷酒等,几乎成为贵族们日常饮品。1930年,刘曼卿到擦绒家拜访,“仆人献茶、咖啡及牛孔,匙拨方糖,忖何以至西餐室”[39],即可见西式饮品。时人成拉萨世家官吏较欧化者,“每日必饮牛乳茶或咖啡……饮酒必饮白兰地或威克司”[40],以致在拉萨“请客时如果没有白马牌威士忌酒,(就)算不上讲究”。[41]1939年,时任噶厦政府仲译钦波的然巴新居落成宴客,“席桌为长方形,作西式排列……最使余注意者,为威克斯酒敬酒之酒妓”[42]。
另据英人记载,拉萨的宴会中,“薄荷酒最受欢迎,其次是本尼迪克特酒(Benedictine)”[43]。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拉萨贵族本身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英国人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在拉萨的英国办事处招待拉萨贵族时,“通常是孩子们喝柠檬汁,女人们喝果酒,男人们喝威士忌。”[44]
(三)贵族的娱乐
拉萨贵族旧有的娱乐方式主要是逛林卡。民国时期,多数贵族以听音乐和打麻将消磨时间,尤其是麻将在贵族中非常流行,以致摄政王曾下令禁止官员打麻将赌钱[45]。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拉萨娱乐方式单一不无关系。不过民国以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多,也为拉萨贵族带去了新的娱乐方式。
首先,电影被引入拉萨,且极受贵族的喜爱。邢肃芝说“他们看电影的方式很特别,一部电影要翻来覆去地看上十几遍,至把电影中的插曲唱得滚瓜烂熟了,才算罢休”[46],这一点可以从查普曼那里得到证实。
英人查普曼在拉萨期间常常为贵族们播放电影,多数时候一些仆人和僧人也会涌入房间一起观看。其中一部关于狗与主人的电影——《夜的呐喊》极受喜爱,“人们总是让我放这部片子,这部片子一演就是一个半小时,我们都腻透了,然而藏人却不嫌烦。”[47]除《夜的呐喊》外,查普曼等人也放一些他们在拉萨拍摄的片子,因都是人们熟悉的镜头,也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另外有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很能引起藏人的共鸣,总能引来一阵乱喊乱叫和哄堂大笑。”[48]
查普曼等人在拉萨时,有时也在邀请藏官晚宴后为他们播放电影,或到贵族家里为他们放电影。他们还专门为热振摄政放过两次电影,其中一次足足演了3小时。此外,他们还为拉萨的主要官员举行过一次电影晚会,官员们带着他们的家人、朋友一同前往;也为罗布林卡的卫兵、功德林的僧人们专门放过电影[49]。
国民政府入藏和驻藏人员也为藏人播放过一些内地电影。1930年抵达西藏的刘曼卿,“携有少数陈旧影片,公映之后,颇得各方好评”,此后有中央人员入藏,“藏人即以有无影片见询”[50]。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曾提出购置放映机播放电影,曾任拉萨小学校长的邢肃芝等人以拉萨小学为依托,通过举办恳亲会的形式放过几部教科片和动画片。相对英人播放的电影,这些电影对藏人似乎缺乏吸引力,“旧片子放映几次后,大家就不再感兴趣了”,后因“购片租片都有困难”,放映了几次就作罢了[51]。但也有内地电影大受藏人喜爱,如《渔光曲》在拉萨连续放映3个月[52]。
其次,是一些新玩意的出现,如相机、摄影机、收音机、唱片机、麦克风、扩音器等。
中央政府的驻藏人员和英国驻拉萨办事处的人员都会携带相机入藏。他们不仅自己拍照留念,也会为拉萨的官员、民众等拍照。慢慢的,拉萨的贵族、官员学会了使用相机。如擦绒就拍摄了大量照片赠送给美国人白纳梯,他还“借给美国人一架照相机,由他随意拍摄”[53]。查普曼在拉萨时送给热振摄政一架相机,并详细地讲述了如何使用[54]。摄像机、收音机也大抵如此。新华社记者还在拉萨拍摄到了一张时任噶厦四品官的车仁·晋美举着摄像机拍摄电影的照片[55]。19世纪40年代,在八廓街售卖的商品中也有“收音机和唱片机”[56]。
麦克风和扩音器在拉萨也是作为娱乐设施出现,而不是扩音的工具。查普曼等人应热振摄政的要求,“为他赶制了一台能对公众讲话的扩音器……摄政王坐在他的房间里能听清每一句话,这让他十分欣喜,兴奋得像个小学生。……他走来对着麦克风讲话,一开始大音量使他有点不知所措,但他逐渐发现听到自己的话音和笑声在身边隆隆作响实在是一大乐事”;他们还用“留声机播放了唱片,摄政王只是对最大音量感到满意”[57]。
一些贵族喜欢听唱片,“收集了各种汉地流行歌曲的唱片”,也有喜欢听京剧,甚至还能唱京剧的[58]。此外,网球、羽毛球、篮球等球类运动也随着中央政府的驻藏人员和英人的进入,被引入拉萨,也渐渐为拉萨贵族们接受。但传统的逛林卡仍然是藏人主要的游乐方式,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新的娱乐方式的引入而发生改变。
三、下层民众的生活
西藏地方等级森严,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级上等,达赖及藏王等属之;上级中等,噶伦及活佛、掌教喇嘛等属之;上级下等,代本、营官及普通喇嘛属之;中级上等,地主大家之后裔属之;中级中等,书记、小吏等属之;中级下等,兵卒及一般人民属之;下级上等,官员家族之仆婢佣人等属之;下级中等,男子无妻无家、女子无夫自为生活者及乞丐等属之;下级下等,屠夫、清道夫、收尸者及五金工人等属之。”[59]各等级之间界限分明,生活上,上等贵族“与普通贫民相较,则相去天渊也。”[60]前面谈及拉萨贵族的生活,此处以手工业者和乞丐为例,窥探上世纪20至40年代拉萨下层民众的生活。
(一)手工业者
西藏地方手工业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领主保有人身隶属关系”[61],而“不是自由劳动者”[62]。而且这种人身隶属关系基本都是多重隶属,在隶属于三大领主的同时,还要“受到由地方政府建立的手工业行会的管理,为政府支应差役,属于政府的雇工”[63]。正如李坚尚所说,“西藏第(的)手工业者,除了尼泊尔人,可什米尔人和回民外,均隶属于各级封建领主。他们除了向自己领主交人头税,服劳役外,有些行业还需要给有关部门支差或交税,如缝纫、铁木石行业、织毯业等。”[64]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手工业者的负担。
支差一项,以拉萨的缝纫业为例,每人“每年出差3个月至半年”,支差期间虽有一定的糌粑、酥油和藏银作为伙食和报酬,但实际是非常低的,藏银在1两至4两之间,一般以实物支付[65]。另外有两家属于哲蚌寺属民的木碗业从业者,“每人每年给哲蚌寺支差7-8天,给藏政府支差60余天,除管吃外,每天只给1钱5分的报酬。”[66]交税实际就是以税代差,每年根据手工业者技术水平的高低向行会缴纳一定的藏银。如拉萨缝纫业,每人每年缴纳3-150两不等的藏银。不论是支差还是交税,实际都是三大领主对手工业者的剥削。
手工业者还需和其他市民一样要负担各种杂税。藏俗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各种名目的税收,仅这一项,每户就要向朗仔辖交税14次。在一些重大节日中,每户又支付数十种税收,如在传召大法会期间,“凡属太阳能晒到的物品”,都要交税[67]。此外,手工业者有订婚、结婚和丧事等,均要交税,数量为藏银10-500两不等,同时还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藏酒、糌粑、哈达和酥油。而朗仔辖每年需要的糌粑、出背草、背牛粪、背水、背土等差,手工业者也均以交税的形式代替。
此外,拉萨多数手工业者的居住状况非常糟糕,住着极其破陋的房屋,如拉珠一家“住的是破漏的泥糊房子”[68],屠户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围墙,地面凌乱不堪,到处是动物角、蹄、骨头和碎兽皮”,制革工住在拉萨城城中的下等贫民区,“路边有成堆的粪便和垃圾”[69]。还有一些手工业者没有自己的住房,只好租赁贵族或者藏政府的房屋,“每年除支付房租外,还要送礼,献哈达”,为房东支差。如拉萨的一名鞋匠租用了一间临街的房子,“每年出房租1500两藏银,另交押金1500两。同时规定主人要支差时,随叫随到。”[70]
手工业者的地位低下,在森严的等级社会中,一些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乞丐,如五金匠人。民国时期,手工业者的地位“虽然逐渐从最下层的‘贱民’地位有所上升,但实质上与从事农牧业农奴的身份和地位相当,或更为低下”[71]。曾在扎西造币厂工作数十年的铁匠工人拉珠回忆说:“我们穷铁匠的地位是最低的……连贵族的门槛都不敢碰一下。”[72]如果完不成工厂的定额任务,“又要屡遭藏官毒打。”[73]
沉重的负担,手工劳作的艰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拉萨手工业者的生活贫困,日子常常难以为继。据调查,民国时期在拉萨的一位织氆氇业的手工业者,全年的收入在未计算额外负担时,还亏795两,足见生活的艰辛。[74]
(二)乞丐
拉萨市区乞丐众多,朱少逸称“凡曾至拉萨者,盖无不惊讶于乞丐之众多,而留一深刻印象也”[75],查普曼称大昭寺“门前成群的乞丐令人感到震惊”[76]。据记载,“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整个拉萨只有35000人口,其中乞丐约占总人口的20%。”[77]
和平解放前,拉萨市区的鲁固广场、城北的小昭寺附近以及西城门附近是乞丐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居住状况也非常糟糕。鲁固广场的乞丐“住在破布帐篷里,是拉萨最脏、最乱的地方”[78],“夜晚就蜷缩在破旧的小帐篷里”。有破旧帐篷的算是较好的,另外一些连破旧的帐篷都没有,一位“形色枯槁的老年妇女住在一间只容得下她的茅舍里,茅舍窄小不堪,如同狗窝一般”[79],另外一些则只能“挤在附近的玉妥①玉妥桥:汉语也写作宇妥桥、宇拓桥,由清政府拨专款修建,因桥顶使用琉璃瓦,又名琉璃桥。和马康萨桥下”[80]。另外有一部分居住条件稍微好些的是天葬师,“他们的住所中有一面墙是用草根泥砌成的,泥中加拌了动物角。一个破破烂烂的羊毛帐篷布支在屋顶上”[81],这种拥有土坯房的算是住宅条件不错的。
乞丐的日常生活当然是乞讨,但不同的乞丐略有不同。
生活无着落的人们,“白天讨饭,行乞”[82],“成群的乞丐依墙而坐,他们吐出舌头,竖起大拇指,哭着乞讨”,一些老人、盲人、残疾人和病人“整天坐在那里,在阳光下打盹,只是当有人经过时,他们才会醒过来轻声哭诉”[83]。乞讨的人们常常在口中念着“请先生大发慈悲”“请赐小小礼物”[84]等句子,以乞求施舍。一些小乞丐会跟在女性的身后,口中唱着赞美的歌谣,纠缠不休,直到乞讨成功为止。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乞丐们还会成群结队前往乞讨,如在“萨嘎达瓦节”这天,几乎全拉萨的所有乞丐都会出动,绕大昭寺一圈,等待施舍。
另有一些乞丐被称为“热结巴”①热结巴:藏语音译,汉语也写作“惹结巴”。,可以说是“高级乞丐”。他们负责管理被朗仔辖特许外出讨饭的囚犯,也负责清理拉萨市区的尸体、市场和更换八廓街的四根大旗杆上的经幡,实际扮演着天葬师、清道夫等多种角色。作为酬劳,西藏地方政府给予他们乞讨和管理的权利。热结巴有自己的头目,类似于汉语所称之“帮主”,他们对任何权贵都毫无畏惧,认为自己“有权要钱”,遇到官员荣升、贵族喜宴和节日时,只要“帮主”一声令下,所有热结巴便成群结队地前往乞讨,“如果没有付钱给他们,他们会疯疯癫癫地闯入大喊大叫,高声诅咒”[85],这种行为使得人们只好在他们到来时立即付钱给他们。
还有一类流浪艺人,靠卖艺乞讨。“在八廓街各处,总有流浪艺人一边表演,一边请求赏赐”[86]。这类乞讨者,来自不同的地方,表演不尽相同,有跳舞的,拉琴的,也有边唱边跳的,还有说唱艺人,他们大多都是三三两两的组合,或者带着小孩,如英人坎德勒记载在八廓街“广场的一角,有个街头卖唱的歌手拿着六弦琴,带着一些跳舞的孩子”[87]。
拉萨的乞丐大多是“衣衫褴褛,浑身积满污垢”,食物粗糙,不稳定,也不丰富[88],与衣着华丽,饮食讲究,住着花园别墅的贵族们形成鲜明对比。
四、拉萨城市生活的特点
(一)等级性
等级性主要源于西藏地方森严的等级与严格的界限,“各级各等之间,界限分明”“各级之间不通婚媾,不作交往。富贵者世为富贵,贫贱者世为贫贱”,更重要的是“各级各等之人员,对于本身所属阶级视为前生命定,行之若素,即极下级者,亦甘之如饴”[89]。
民国时期,拉萨贵族们纷纷新建花园别墅,房屋宽大舒适,室内“装饰布置,均富丽(堂)皇”[90],但普通民众的房屋却矮小狭窄,几无装饰。正如英人所描述的“富裕之家,鸠工庀材,架木砌石,筑成坚实之美屋”,房屋“大而适用,高楼常至三四层”;一般贫民之房屋,用最低贱的石料砌成,“屋小而陋,鞠为茂草……屋内布置,极尽简陋”[91],“除经堂外,往往膳食客厅,厩舍粪坑,同在一处”,极不卫生[92]。
贵族们生活奢侈,海参、鱼翅这类昂贵且不易得到的食材成为他们常见的快餐,少数贵族甚至饮酒必饮白兰地或威士忌。朱少逸在参加几次宴会后感叹,威士忌“酒可代表拉萨贵族之西方享受,内地人多以旅居边地为苦,实则边地中如拉萨者,其物质享受或且超越战时内地认识远甚”[93]。但对西式生活的追捧仅限于拉萨的上层贵族,对于“中下层民众而言,他们没有条件享用,也不认可西方饮食文化”[94]。
其实除住宅和饮食外,服饰与装扮也无不处处体现着拉萨人的等级。比如,当一位噶伦出行时,他可能穿着黄色的丝制长袍,他的秘书们可能穿着紫色或蓝色的绸缎长袍,他们乘坐装饰极为华丽的马匹,但他们的仆人则只能穿纺织的黑色长袍,而且脏得出奇[95]。贵族们无论男女都会佩戴各种宝石作为装饰,一名贵族妇女全身的装饰可值数千金[96],这些都是下层民众不可能享有的。
(二)自主性
拉萨城市生活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当外来生活方式被引入拉萨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继续保持。比如拉萨的贵族虽然修起豪华的花园别墅,但是房屋外形仍然是藏式的,内部陈设与布局也只是部分使用欧式、汉式陈设。日常饮食与娱乐也如此,电影、照相机等只是增加了拉萨人的娱乐方式,更确切的说只是增加了少数上层贵族的娱乐方式。而更明显的体现则是宗教生活仍然在拉萨城市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各种宗教节日如期举行,像传召大法会这种盛大的节日,英人不仅表示尊重,还在期间向喇嘛们熬茶布施[97]。此外,八廓街上转经的人群,贵族家庭中必有的佛堂等,都能证实这一点。总之,人们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因为新生活方式而发生改变。
自主性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在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之下,拉萨人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
民国初年,因历史的原因中央政府未能有效实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英人又趁机有意拉拢,使西藏地方有追随英国,脱离中央之势。因而有十三世达赖派遣贵族青年留学英国和印度,在英印政府的帮助下实施“新政”,并在诸多方面模仿英国。现代化的因素和欧式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拉萨。可见,拉萨城市生活中的现代因素,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更是东西方政治的较量,当然也是地方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较量。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政治的较量仍然在持续。比如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播放,中英双方的驻藏人员就为了各自的目的展开竞争。驻藏办事处看到“驻藏英人,常以放映电影为名,邀约藏中僧俗官员、世俗子弟,藉资联络,宣传国势,使藏人受其深刻印象(影响)”,提出中央政府驻藏各机关应经常供给电影,播放“有关抗战建国的影片”[98]。中央驻藏人员希望通过电影建构藏人的国家观,增强其“向心力”,英人却试图削弱这种国家观,扩大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和对英人的情感认同。因此双方选取的电影题材不同,对藏人的吸引力也就不同,驻藏办事处宣传“抗战建国”的政治影片自然无法与《夜的呐喊》这类影片相提并论。
1947年的热振事件也是西藏地方抵制国家权力的反映。噶厦政府以热振活佛亲近中央为由,逮捕热振,派藏军围攻色拉寺,搜捕与热振有关的人士,使拉萨秩序一片混乱[99]。之后噶厦政府又在拉萨街头张贴布告,指称热振等人的罪行为勾结“外人”[100],称他们是“僧界之恶魔”,以杖毙、挖眼、鞭打、永远囚禁等严厉的刑罚处罚他们[101]。噶厦政府的行为主动将政治冲突引入街头,在打乱城市原有生活秩序的同时,也在引导人们的选择,试图以政治的力量驱使人们免受汉文化的影响。但也要注意到,这些作为对个体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个体仍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拉萨出现汉式、欧式和藏式等多种生活方式的交融。
结语
综上可见,在民国时期拉萨的城市生活中,当一些人在追求新式生活与享受时,更多的拉萨人仍然坚持着传统的藏式生活,而且即使是那些追求新式生活的拉萨贵族们,也没有完全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得拉萨的城市生活如同一幅拼凑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西藏地方的)与外来的(内地的、西方的)多种生活方式,共同呈现。少数拉萨人虽然崇尚西式的生活,但西藏地方森严的社会等级,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加上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与西藏地方权力的持续博弈等因素,使得拉萨城市生活在吸收外来“新生活”时,仍然坚守传统,其城市生活的等级与宗教特性继续延续;同时又对“新”生活方式的选择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从而形成民国时期拉萨别具特色的城市生活:以传统的藏式生活方式为主导的多种生活方式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