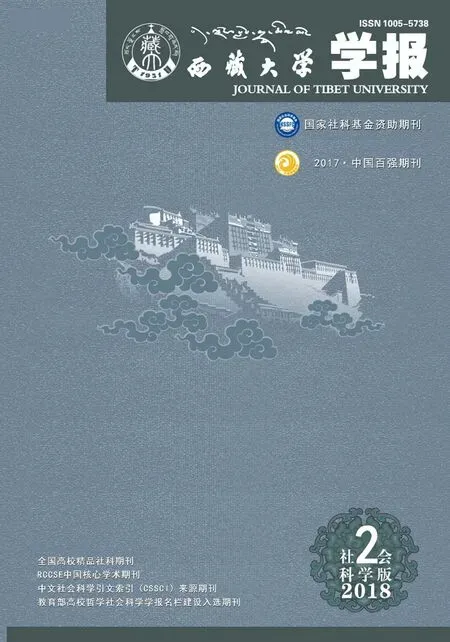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晚年关系的改善及影响
李 双 泽仁翁姆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是近代西藏最重要的两位政教领袖,两者的关系对近代西藏政治格局的变动乃至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有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关系是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早在民国时期,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为代表的国内主流媒体,就热衷于报道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领袖的关系,但大多被贴上“不和”或“失和”的标签。直到今日,学界仍与民国报人一样,重点关注两者不和方面,总结出两者矛盾的成因、冲突的表现、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等。①据笔者视野所及,今人专文论述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关系的学术论文均是两者失和方面的,有石开家.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前后[J].文史精华,1996(11):25—27;杨有富“.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失和始末[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2000(1):86—87;金雷.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20—24;孙宏年.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25—34;孙宏年.从平等到失衡:达赖、班禅关系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研究(1927—1933)[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32—41;陈柏萍.再探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成因[J].青海民族研究,2012(4):101—105;魏少辉,张皓.1932年达赖、班禅系统相互之攻讦与国民政府的处理[J].青海社会科学,2013(5):139—146;王文远.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矛盾的历史分期研究[J].攀登,2016(3):138—143等数篇。然而在两大活佛晚年,努力修补双方关系却研究较少。为何达赖和班禅突然改善关系?采取了那些改善措施?双方关系的改善,又是如何影响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借助档案、报刊、回忆录等文献,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攻讦停息与诚邀返藏: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重修师徒情谊
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出走内地,是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公开对立的开始。北京政府虽将九世班禅作为解决蒙藏问题的重要人物,但中枢式微,无力解决班禅回藏问题,甚至拖欠班禅十几万元的招待费。[1]1928年3月,九世班禅系统率先拥护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系统给予了高度重视,班禅系统也因此占据着中央主管边疆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的多个关键性的岗位,如蒙藏委员会委员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格桑泽仁,藏事处长罗桑坚赞等,[2]并在南京、北平、西宁、成都、康定等地设立办事处。由于达赖系统与班禅系统存在着利益竞争,“当九世班禅系统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联系并取得诸多实际利益后,立即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效仿。”[3]1929年9月,十三世达赖派贡觉仲尼、楚臣丹增等前往南京,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与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通道。
西藏驻京办事处和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设立后,因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双方关系也更趋复杂。尤其是国民政府决心改变西藏现状,抛出大量对藏利好政策时,围绕这些利益与权力之争,两个办事处将西藏内部矛盾转移到内地。
1931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举行,为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做准备。在国民会议中有关西藏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达赖、班禅系统发生争执,达赖系统电告蒙藏委员会,“以前后藏政教统归执掌,西藏代表应完全由达赖选任”;班禅系统则电称,“前北京政府时期,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人数,均系前后藏平均分配,此次国会代表应照前办理。”双方争执激烈。经蒙藏委员会居间调处,拟定由达赖选出六人、班禅选出四人为出席代表,又因双方请求,达赖方面增加列席代表三人,班禅方面五人。[4]为此,两大系统在国民会议代表总数上得到了平衡。在这场西藏地方代表名额之争中,达赖、班禅系统均积极参与,呈现出“拥护中央”的政治效果,同时国民政府采取平衡策略,暂时平息了达赖、班禅系统的矛盾。
这种平衡被双方以后的“事实表现”打破。达赖系统漠视颇受国民政府重视的西藏会议,又在康区挑起纠纷,并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扩大冲突,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渐有恶化之势。九世班禅则鲜明地拥护中央,在内蒙古宣慰,积极参与中央对蒙政策。在这种背景下,1931年6月,国民政府对外公布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次年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支持班禅返藏。国民政府给予九世班禅崇高的礼遇与政治实惠,冷遇达赖,这种区别对待,立刻引起达赖系统的强烈不满,不仅以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向国民政府表示抗议,而且对班禅系统展开了强烈的抨击。
次年5月20日,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等人致呈行政院长汪精卫。贡觉仲尼等在呈文中,译录了此前拉萨三大寺①拉萨三大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拉萨建的三座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为西藏地方最主要的势力集团和政治权力主体。有关近代拉萨三大寺政治活动详情参见邱熠华.论西藏近代史上的拉萨三大寺[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和西藏民众大会②西藏民众大会,是近代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体制中有僧俗和政府各级代表参加的一种议事形式。其详情参见詹嘉措.“西藏会议”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的示谕和宣言书,贡觉仲尼从四个方面对九世班禅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自己的诉求:①要求国民政府撤销给班禅的封号、印册及拟授职位;②要求查禁班禅购置的军火,并暂留平津;③取消班禅的巨额俸银;④裁撤班禅在各地的办事处。[5]面对达赖系统的抨击,班禅系统进行了猛烈的回击。1932年6月7日,洛桑坚赞以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的名义致呈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尖锐的言辞对达赖系统的攻击进行回击,历数达赖“祸藏”十条“罪行”。[6]同月15日,贡觉仲尼等不甘示弱,再次致呈行政院,抨击“班禅喇嘛种种阴谋,蒙藏委员会当局重重黑幕,破坏和平,危害边圉经过情形”,并请求行政院迅派公正大员彻底查明班禅系统“勾引英国侵略西藏、颠覆西藏、挑拨康藏纠纷、贿赂中央、驻青海设署练兵”等事。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试图调息两大系统的矛盾,就此问题表达政府立场,“政府对于达赖、班禅无厚薄之成见,待遇亦循旧制”。[7]但两大活佛系统属员相继投书报界,相互攻讦,经媒体广泛、持续性报道,给两大活佛关系蒙上沉重的阴影,也让主管西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颇为难堪。可以说,从一开始,达赖、班禅系统相互攻讦不只是两方的是非曲直之争,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和达赖、班禅系统之间围绕中央对藏治权的博弈”。[8]因此,达赖、班禅系统的攻讦停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康藏纠纷的演进、国民政府采取的政策及两大活佛的真实态度。
1932年8月之后,西康、青海地方军队相继击退藏军,并有合围拉萨之意,西藏亲英势力遭受打击,达赖系统主张与内地和好的势力抬头。同时国民政府电令十三世达赖,只要汉藏和好如初,康藏、青藏问题也会解决。蒋介石马上下令青海军停止进攻,并派胡宗南军进驻青甘界,以慑青海军。[9]为此,达赖系统改变先前在班禅返藏问题上的态度,逐渐放弃对九世班禅系统的攻击,以减轻国民政府方面的压力。同年10月后,达赖系统没有出现攻击班禅系统的激烈言辞。见此,班禅系统停止了对达赖系统的反击。特别指出的是,九世班禅本人的态度在攻讦停息中有着莫大的关系。班禅堪布会议厅批评十三世达赖“十大罪状”的宣言,事先并未请示九世班禅批准,事后九世班禅表示不赞同这种做法。[10]1932年9月30日,九世班禅认为“前藏代表以文字攻讦,京处起而驳辩”,又指出“该代表滥发宣言,要挟政府,不过是个性冲动,决非达赖佛及三大寺本意。复以京处处长不察是非,起而反驳,实无异给彼以挑拨之机”,因而“当经函令交责矣”。[11]
达赖系统注意到九世班禅的善意行动。十三世达赖的亲信贡觉仲尼向外界表示:“过去班禅与达赖因属下小人绕舌互疑,以致九世班禅无奈离藏出走,故今天无论何时班禅回藏,达赖绝不会反对。”[12]同时十三世达赖下令释放被拘的九世班禅亲属,并通过英国驻华使节送去了保证释放的函件,达赖喇嘛的信打开了班禅与达赖之间进行正式协商谈判的大门。
我曾两次致函于您……从一开始我们俩之间亲如父子的关系就一直充满着情和爱。……某些良心不好的仆从玩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伤害尽人皆知。但是您自然不会一时冲动想使西藏卷入战乱,西藏是由父子共同管理的。……自从您离开西藏至今将近十年了,而事情仍然是这种状况,我非常担心您的生命可能会遭不测。而且,假如您能返回“卫”地,师徒之间的关系就会像烟与火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我们的高贵的传统也将得到维持。因此,请您在这个问题上三思并给我一个答复,以便我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行事。
水猴年八月十日(1932年10月9日)发。[13]
十三世达赖诚邀九世班禅返藏的姿态,得到九世班禅的积极回应。1933年2月17日,九世班禅复函青海省主席马鸿逵,婉转表达“无赴青海意”,[14]进而打消了达赖系统的一大顾虑——“班禅械弹飞机车厢辎重,均已备齐,有不久即驻青海设署练兵,联合边吏,因之藏人对此,认为中央援助班禅,夺取西藏政教之权”。[15]另外九世班禅通过西藏地方政府派驻北京雍和宫堪布札萨·贡曲穷乃,先后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递交了三封书信,最后得到达赖复信,欢迎班禅派人来拉萨协商。[16]鉴此,九世班禅选派安钦呼图克图、堪布王乐阶、驻印代表康福安等十四人,由海路经印度前往西藏,与达赖商讨班禅回藏问题。[17]
国民政府对达赖与班禅关系的改善,颇为关注与支持。1933年1月30日,行政院致函前驻藏办事处长官陆兴祺,希望“其从中斡旋,设法达赖、班禅间情感”。[18]同年2月,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对达赖与班禅关系的改善,发表乐观谈话,“近来西藏达赖,已有盼班禅大师回藏之意,班禅大师,亦以国难当前,各方都应该团结,所以派安钦呼图克图先经印度回藏,接洽就绪,再行决定启程与达赖切实合作,以固边防,而奠国基。”[19]为进一步支持安钦使团进藏协商的工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特批安钦使团两万元经费,半作旅费,半作礼物布施。[20]同时,在青藏战争中,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恶的马步芳,放下成见,积极充当达赖与班禅关系的调停人,“愿达赖幡然憬省,准复班禅土地主权,双方重申旧好,永为党国国民,巩固西北边陲。”[21]“马步芳调解达赖班禅感情,达赖允使班禅回藏,马派王振满代表迎班回藏,再定期返藏。”[22]
达赖与班禅的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1933年6月2日,安钦呼图克图一行抵达拉萨。达赖为优待班禅代表,特设招待处于拉萨基堆宅。此后,达赖四次接见班禅代表,商讨班禅回藏问题。九世班禅代表“晋谒达赖上师,报告愿率属回藏,要求赐还后藏一切固有权利”。[23]十三世达赖同意“仍照藏俗旧例,达赖驻波达拉,主持前藏,班禅驻乍西孙波,主持后藏”,[24]“减免扎什伦布所属各宗谿历年拖欠的军费、租税,其他问题待九世班禅回藏后解决”[25]。达赖又表示“自觉年事渐高,而又念班禅久劳于外,颇表示欢迎回藏”,希望安钦呼图克图等人“速返内地,传达此意”。[26]对此,安钦和王乐阶联名电告班禅,“倘班禅果愿善意回藏,则两人间冲突可迎刃而解。”[27]“谓自抵藏谒达赖后,达赖意思极好,迭次表示欢迎班禅回藏,时间迟早听其自便。”[28]同年8月17日,在得到安钦来电后,“班禅大师不胜欣慰,特致电申谢。”[29]由此可见,双方取得了一些共识。九世班禅返藏出现了一丝曙光。
但达赖告诉班禅代表,此事尚需征询西藏民众大会的意见。不幸的是,该机构的两名最具影响的代表敌视班禅,垄断了会议,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这使达赖喇嘛大为不安,因为这将使事情更加复杂化,“因为那时十三世达赖的健康和意志均不如前”。[30]有关班禅回藏问题也因西藏民众会议的阻挠而搁置。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仍在为班禅顺利回藏而努力,在其临终遗嘱中强调,“尔等不听吾训诲,吾将去矣,师兄班禅在中央有力,应速请彼回,维持政教。前藏后藏僧民等,应听从班禅之教诲,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恼,于戏!(此系由藏语翻译成中文)”[31]有关这份仅见于汉文资料的十三世达赖晚年遗嘱的真伪,学术界尚有争论,但遗嘱中强调尽快迎请九世班禅返藏、重修达赖与班禅的师徒情谊及善待中央政权之语,并不违背十三世达赖晚年的心路历程。
二、主持追荐与寻访灵童:班禅和达赖师徒情谊长结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布达拉宫圆寂。同月20日,西藏驻京办事处向蒙藏委员会呈报了这一噩耗。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把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重要的宗教领袖身份放到第一位”。[32]之后,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一切褒崇典礼,务极优隆”,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凸显出中央对西藏之重视。[33]同时,按宗教仪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噶厦政府要向班禅报告有关事宜,由班禅主持集合僧众诵经超度。于是,噶厦政府通过驻京办事处电告班禅大师“大慈悲堪青达赖佛座,十七日傍晚圆寂,照例供养,已由贵代表安钦喇嘛呈递,尚请修法,祈祷佛身早日转世,圆满本愿等语,来电转达。”[34]当远在内蒙宣化的九世班禅得知十三世达赖病逝后,“深以众生不幸,顿失长老,远寄塞边,哀悼无极。且以达赖佛原为众生疾苦而坐化,凡兹众应如斯以求所愿,并冀其灵觉早日降生,重渡浩劫。故饬所有各喇嘛,即日为达赖佛虔诚诵经”,又“饬行辕堪布以至卫士,停止娱乐七日,一律素袍摘顶,以志哀悼。”
与此同时,九世班禅与国民政府一道,“通令各地,隆典祭悼,以彰殊动”,并“扶病撰祈祷达佛慧觉早临藏文赞一卷,交秘书厅缮发各寺,以资虔诵祈祷”。班禅大师在内蒙驻锡地百灵庙亲率蒙古僧侣,用黄布包裹楼阁金顶,不用法器,诵经七日,以志哀忱。又命令班禅会议厅派员分往蒙古、青海、西康、西藏、宁夏、五台山等地有关寺院,令僧众诵经追荐;拨供养金十万元,“以维藏局,而慰众生”。九世班禅电告西藏驻京办事处贡觉仲尼、阿旺坚赞两代表,“陈述请追荐情形,加以慰问唁”。[35]又电令安钦呼图克图为班禅致祭达赖代表,并向三大寺布施诵经超度。[36]
为彰显十三世达赖的历史功绩,九世班禅特电蒋介石、汪精卫、戴传贤、石青阳等国府要人,“请予从优追封达赖大师,并通令各省隆典祭悼,以彰殊勋。”班禅请中央从优追封十三世达赖的意图,与中央政府想法相合,“查达赖喇嘛护持正法,卫国安民,功绩昭著,似宜特予褒恤,以示优异。拟请钧府明令追赐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37]为表示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重视,国民政府特拨款两万余元,在南京为达赖喇嘛举行隆重的追荐法会,邀请九世班禅作为主坛人。[38]
1934年1月15日,九世班禅奉行政院命令南下,次月24日抵达南京。在拜会国府要人后,九世班禅与西藏各代表商议,顺应西藏僧民的意愿,将十三世达赖的追悼时间改为2月14日,恰是藏历正月一日,“预兆吉祥”。[39]在达赖大师追悼会追荐班次中,九世班禅大师紧随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党部代表之后,显示出班禅大师在达赖大师追悼会中的重要地位。2月14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诵经追悼大会中,九世班禅带病率领藏籍喇嘛在考试院考场宁远楼主席诵经追荐仪式。[40]九世班禅顾恋十三世达赖喇嘛,“心殊不乐”,在2月25日班禅寿辰时,“停止祝贺”。[41]
可以说,九世班禅大师在追悼十三世达赖喇嘛过程中,不仅按照宗教仪轨,主持诵经追荐,著书哀悼,还上呈中央从优追封达赖大师,协调达赖追悼大会的各项事宜,充分展现出了九世班禅大师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深厚情谊。有鉴于此,1934年3月,西藏驻京办事处承噶厦政府之令,致信班禅称谢:
敬肃者达赖佛座,示现涅槃,全藏众生,遽失怙恃,上月间各机关团体在京开会追悼,举行齐荐,荷蒙莅临祭奠,领导经坛,妙法宏施,留无边之功德,宝华供养,具最上之庄严,稽首拜嘉,弥殷悲感,肃囗申谢,敬叩崇安。
西藏代表阿汪坚赞、阿汪扎巴、贡觉仲尼、曲比图丹谨上。[42]
1935年上半年,西藏地方政府开始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次年秋,热振摄政选派三支寻访队伍分别往东北(安多)、东方(西康)、东南(达布和工布)。安多寻访队由色拉寺杰札仓的格乌昌活佛和俗官凯墨·索南旺堆为首。同年底,格乌昌活佛寻访队达到类乌齐,受邀前往玉树拜见九世班禅。[43]
依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寻访与认定,最终由国民政府定夺。1935年10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致电西藏地方政府,指出新达赖转世应遵守清乾隆年间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的金瓶掣签制度,“慎重寻访,不得故意指认,而维黄教法统”。[44]之后,国民政府依照历史定制,重新制定了《喇嘛转世办法》,规定达赖喇嘛等的寻访、征认程序、坐床等相关事宜,成为国民政府处理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主要依据。然而从一开始,西藏当局就有意规避国民政府的介入,不仅向国民政府隐瞒灵童寻访的具体情况,还阻挠国民政府对灵童寻访活动的正常干预,让国民政府颇为被动。在此问题上,九世班禅对达赖转世的真实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按照宗教仪轨,班禅对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负有协助之责,这是达赖与班禅多世互为师生亲谊的基础。九世班禅鲜明地站在中央政府立场。早在1935年九世班禅致电考试院长戴季陶时指出“将来对于新达赖之认定,当依照清制掣签,以维固有之宗主权”。[45]
九世班禅在宣慰西陲过程中,遵中央政府指令,派员前往蒙藏地区寻访,还特留心近期出生的蒙藏灵儿,选出三名灵童(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十四世达赖拉木登珠)。由于选定达赖转世灵童事关重大,班禅大师随时将寻访情形电告中央政府,商讨对策,“达赖佛转世事,虽据各方呈报灵异稚童甚多,而一时确定尚难,叨公关怀,自当随时商询,并与热振禅师妥善办理,复奉释虑。”[46]另一方面,格乌昌活佛拜访九世班禅,请示“达赖转生地点,与灵童姓名”,班禅大师不留私心,“即开给青海三童姓名地点,嘱酌之”。[47]
由于西藏与青海地方政府发生过武装冲突,安多寻访队担心青海当局从中阻挠,电呈蒙藏委员会和班禅大师请求帮助。鉴此,1937年2月17日,九世班禅大师派胞弟泽觉林活佛协助格乌昌活佛寻访队,并电呈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以期消除误会,请求协助:
前藏格仓佛率克迈色等三人,为找转生达赖,刻已到玉,延见之余,洞悉种切,惟该佛因青藏前经战事,内怀疑怯,行甚趑趄。当经面宣主席宽大之德意,从前战事,亦与格佛丝毫无关,可迳前往,格仓佛方释然。窃念寻见达赖,实为全藏官民所共期冀,关系中藏情感,至为重大,敢请推爱,于该佛抵青时,多予援助,分饬沿途军政长官,力加保护。[48]
1937年4月20日,为了进一步协助西藏寻访队在青海地区的寻访工作,九世班禅大师利用自身在甘、青等地区的影响力,向格乌昌活佛寻访队发给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执照:
查第十三世达赖转生所在何地,依打卦断验,前藏政府派才学巴格仓佛等前来寻访,班禅驻锡地玉树,迭接拉萨噶伦什噶等信,请予协助等语,窃念达赖大师与班禅在佛教上之关系,情同父子,无谕演至若何时期,均不能有间离,此次经虔诚祈祷三宝,打卦无误后,知己转生及其转生所在地,惟是事关系重大,且班禅滞留东土有年,遍历西陲,对于各处情形,比较熟谙,为此爰派觉策林佛及恩久佛等偕赴青甘蒙古果洛名地切实访寻,倘囗等达到,深希各族军政长官及负地方政治囗之僧俗官员等切实保护,多方襄助,予该员等便利,藉以早完使命,是所切要。
此照。[49]
同年5月,格乌昌活佛寻访队随泽觉林佛行抵青海西宁,礼节性地拜访了马步芳。之后,寻访工作在青海得到全面展开。九世班禅在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过程中,坚定拥护中央政府的认定办法,尽心尽力,并为西藏地方政府最终寻访达赖转世灵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6月28日,西藏地方政府特致电称谢九世班禅:
寻找新转生达赖与迎接赴拉萨,并以后教育一切事宜,曾蒙大师允许赞助。大师源与达赖有互为师弟之良好历史,关于此点,吾人极表示感谢。[50]
三、余论
纵观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一生历程,可以发现,两大活佛确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众多学者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总结起来有四大主因:一是历史原因,即中央政府对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和驻藏大臣愤国误事;二是外部原因,英、俄国侵略势力离间达赖与班禅;三是西藏内部原因,如两佛属员相互构谗;四是个人原因,十三世达赖“唯我独尊”。①有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的原因,参见金雷.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20—24;陈柏萍.再探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成因[J].青海民族研究,2012(4):101-105.笔者认为,以上确是达赖与班禅失和的部分原因,但不能将以上原因叠加,简单地认为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原因有两点:一是历史上,历辈达赖、班禅互为师徒,关系亲密,“有9位达赖拜5位班禅为师,有4位班禅拜4位达赖为师”,[51]正是达赖与班禅相互扶持,才开创和发展壮大了甘丹颇章政权,被藏族人民视为生命,两人的关系恰如西藏谚语“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这是历史的见证和藏民的信仰。二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相互间未主动攻击对方,民国期间两次赴西藏学法的法尊就指出“虽两方的手下人生过多次意见与纠纷,然他们师徒之间实未有异见”。[52]对于两大活佛矛盾的起因,十三世达赖在接见班禅代表安钦呼图克图时指出,“大悟过去双方积怨全系属僚挑拨”。[53]九世班禅也认为,“窃思班禅个人回藏,达赖在时即经欢迎,而迟迟未归者,即欲达到恢复汉藏旧有关系之初旨。且查噶厦函中各件,不过为一二当局之私见,决非民众公意”。[54]可见,两大活佛已逐渐认清两者矛盾之源。
1904—1912年的近十年间中,在内外压力下,十三世达赖基本处于漂泊之中,备受流亡之苦。在听闻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后,十三世达赖深切地为班禅的安危而担忧,祈祷班禅幸福平安,并因“派员迎之不获,曾为痛哭”。1930年,十三世达赖还哀伤地对国民政府委派赴西藏的全权特使刘曼卿说到:“吾与班禅原有师弟之谊,绝无若何意见,闻渠近日旅居蒙古,想亦有不适之苦,吾至以为念”。[55]远在内地漂泊的九世班禅也时刻挂念十三世达赖,“在雍和宫设坛诵经,以祝达赖多福多寿”。[56]可以说,两人相似的流亡经历,彼此之间又多了一份亲情间的关爱,成为互相倾诉的对象,进而推动双方晚年关系的改善。
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晚年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助于西藏内部的稳定与团结,还为缓解康藏纠纷与隔阂、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及国府掌握治藏主动权提供了条件。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从制定对藏政策伊始,就为努力恢复与强化与达赖、班禅系统的政治联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协调两系统的关系,以加强对西藏地区事务的管理、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57]1930年12月4日,在蒋介石致九世班禅信中,就特别指出“台端与达赖虽一时少有误会,仍望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御外侮,以解中央西顾之忧,是为至盼”。[58]在次年西藏会议中,国民政府认为“达赖班禅双方感情,拟藉此机会,以图解释为此”。[59]蒙藏委员会在其1929—1933年年度工作计划中,均将调解达赖、班禅之间的误会列为重要任务。[60]同时蒙藏委员会提出,“关于达赖、班禅之嫌隙,自应从中调解。关于达赖、班禅之地位,亦应持平处理”。[61]
国民政府调解达赖、班禅关系,既减少西藏内部矛盾,缓解西南边疆危机,又为中央政府介入西藏事务提供了条件。1929—1930年,贡觉仲尼、刘曼卿、谢国梁、谭云山代表中央政府入藏,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开始正常化。[62]然随着康藏纠纷、达赖与班禅系统之争等事件的接连发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跌入低谷。达赖与班禅关系的改善,则给国民政府重拾汉藏互信打开了大门。从这一层意义讲,安钦呼图克图不仅是班禅回藏协商的代表,也是中央政府入藏的代表。安钦呼图克图携带中央要人致达赖的函件,在安钦呼图克图晋见达赖时,递交中央要人致达赖的函件,并交换了时局意见,“至达赖对整个大局,亦颇关怀青藏间冲突,既因和约而化险为夷,康藏纠纷,亦主和平解决。”[63]达赖也特意委托安钦呼图克图“将答复中央各要人函件,托为转交”。[64]
总的说来,尽管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误会与摩擦,又因被迫卷入持续严重的西藏危机,先后流亡内地,命运从此多舛,出现分野,但作为近代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他们将个人命运与西藏、中央政府紧密相连,最终推动了他们心向中央。两者不仅在早年共同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在晚年化解矛盾、修补关系,延续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世代情谊,更是以此为契机,改善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