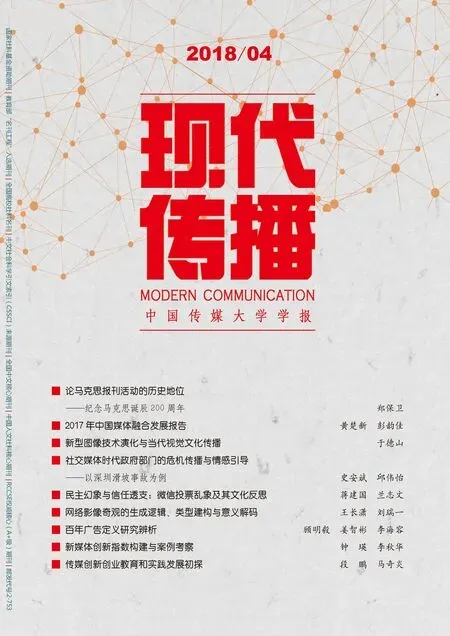圆融反复:论中国传统超验时空观对当代影视表达的影响
■ 冯 果 韩鸿滨
一、影视中的超验时空
电影、电视剧作为时空的艺术,本身就需要依靠对影像时空的压缩、变幻创造一定的假定性,以达到创作目的,因此荧幕中不乏用各种精巧解构手段处理其中的时空问题。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现实与幻境,常规与超验的时空变换的创作一直贯穿影视的发展,这种对时空关系处理的本能不仅源于人类自身共通的对生命时空的想象①,还承接各自的传统文化与集体性格,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当代影像的着重点,影响着当下影视的创作与发展。
自电影在西方诞生起便开始对时空表现进行探索。从布景或实景拍摄,到“最后一分钟营救”用蒙太奇创造时空,随着战后精神与物质的撕裂困顿,回到了哲学中寻找精神意义与时空自由:早期《一条安达鲁狗》等超现实主义电影用潜意识、梦境等对传统进行抗争和破坏,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影响,用非理性、直觉的认知方式去解决问题,呈现生命本质的心理状态,获得真实的体验。到了20世纪50年代左右,左岸派等现代派电影受存在主义哲学中克尔凯郭尔“孤独个体”、海德格尔“无家可归”与萨特“他人即地狱”等的影响,试图通过闪回拼贴等方式展现人的内心活动,以呈现迷惘与不知方向的现代。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封闭与世隔绝的不明时空,是A、M、X等不明身份的个体内心无序荒芜的外化,时空呈现出荒谬、封闭的状态。直至20世纪末,由《终结者》引领出的科幻时空成为当下西方影视探讨多时空维度的主流,世界真实性被质疑颠覆的《黑客帝国》、在痛苦真实与梦境中抉择的《盗梦空间》、只有觉醒良知敢于群起方可抗争宿命的《云图》……一系列时空穿梭的科幻电影填入超现实主义电影中梦境和潜意识部分的同时,用“黑洞”“虫洞”等科学概念联结,其间对未来生存世界的担忧最终都指向后现代中个体生存困境的探讨。
在西方的文化视域中,从经典物理学时空观到狭义相对论、再到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影响,从二元论到时空同一、再到现代西方的哲学影响。同时从最初身心二元对立到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作为理性的人,被放置在自然中优越的中心地位,相对应的,人的态度也成为了对自然之物的主宰占有。因此在笔者看来,西方的超验时空最终多归于用生命个体的斗争、恐惧或荒谬呈现对人类欲望、人与自然、现代文明科技的批判反思。反观中国,虽并未形成科学严密的时空理论体系,但人们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将佛、道中的超验时空观加以运用,并承接传统中天人合一、人与万物同生同构的气质,最终归于平和圆融的内向式生命体验。
从楚辞开始,古代中国就有“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②的质疑,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对时间、空间进行抽象研究。“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③,在定义了时间与空间后,“宇:或徙。说在长字久”④,随着对时间与空间延伸性的讨论,《墨经》将时、空看作是在运动中互为条件、相互依赖,在运动基础上达到统一整合,当最终时空处于“尽”⑤(时空尽头)时,则运动停止、世界变得寂静无声。以“物”观时空,王夫之以江河、灯烛作比,“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即今火”⑥,不同事物随着时空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事物亦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时间一来一往,天地永续运动。以“道”观时空,时空亦如道一般周行不息、回返往复,产生于心灵,由自我来度量,“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⑦,生于道最终又归于道。最终在由时间与空间契合循环且无限的时空里,以“心”观之,天地万物及其时空皆依赖于内心,时空在本质上属于主观,是自我意识的显现,天地万物及人身都是由人的心性、心识所创造。时间的长短成为心性想象长短的表象,长至几十年短至一刹那皆被心识所包罗,“一念三千”⑧,瞬时的内心活动在一瞬间就会产生整个世界,囊括一切空间方位和时间阶段,由此,多向度、循环往复的时间和空间融合交汇。共同在儒家从“仁”与“天生德于予”⑨生发出的“天人合一”与道家源自万物天然存在的“和合”规律而强调的和谐整体,以及“众生平等”的佛性的共同浸润下,最终指向飘渺奇幻又圆融安然的东方式生命体验。
虽然当下科学的时空观要求从时空的客观性、科学性出发,但不可否认,时空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无法离开“人”与“人心”。“经验”指人在“与客观事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⑩,相比于常俗的由经验总结的时空观,超出了时空与科学经验范围的超验时空观,更能展现心灵世界的深层意识,且带有着明显的东方式的主体性、超验性、直觉性甚至是魔幻性。在笔者看来,中国影视从初期发展到现在,其中不乏有大量的作品用回溯的眼光进行创作,其中呈现出的时空观与古代传统的超验时空观不期而遇,其间循环往复的超验时间与圆融贯通的超验空间及随之带来的人物在其间平和安然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了传统审美与精神气质。
二、超验时空中的往复时间
循环往复的超验时空观植根于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根源,天地万物由“道”化生而来,道贯穿其中,万物皆没有偏倚。这种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演化出的天地万物同根同源、“物无贵贱”,是一种“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的万物共生的天然和谐状态。“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在万物蓬勃生长过程中,看出往复循环的道理。“道”的周行不息表现于宇宙万物在时间中的转化,“周行而不殆”,万物生生不息,最终复归于朴、返回原点。传统的中国超验时空观中,“时间竖穷三际,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始无终的时间在空间提供的舞台中自由穿梭。
曾风靡一时的穿越剧常常以时间为突破口,利用观众的格式塔心理,将现实时间为人物赋予的种种前提条件补充缝合于穿越后的过去时间中,用模糊、可以自由流转的时间将故事穿行其中。《步步惊心》(2011)中,张晓从开片不如意的现代时间,意外脱身到过去康熙“九子夺嫡”时代成为马尔泰若曦,最终结尾处又回归到生活的现实时间。其间现在时与过去时的相互指向循环结构跨越了时空区隔,在时间的自由交错中张晓也从开始的叛逆反抗经过无可奈何世事变幻后,回归于原点。魔幻现实主义影片《长江图》(2016)以长江这条极富生命力与时间承载力的河流为载体,以现在时间与过去时间的不断相遇回溯,构筑了独有的属于长江的亦真亦幻世界。
在传统的超验时空观中,时间由“道”幻化而来,是无限循环、周行不息又回环往复的。亦真亦幻的时空摆脱了客观环境的禁锢,直接把握时间的内向式体验代替了常俗的主体对时间的外部感觉,是被主观化了的时间。意识流电影《小花》(1979)在写实的拍摄基础上,用意识流手法呈现随心理而变的时间流动。童年往事的记忆从彩色切入到黑白,黑白画面展现的过去回忆幻想,与彩色画面展现的现实时间寻找,将赵小花与哥哥童年的不幸和情深在时间的连续中融合,在过去时间和现在时间、幻觉和现实的自由组接中小花承接过哥哥的使命,向革命走去。《天云山传奇》(1980)中,20年前和20年后的两个时间维度因宋薇的回忆与情感驱使而不断相互交错,最终在内向式的时间体验中,逃离了貌合神离的婚姻,也在冯晴岚的墓碑旁与过去和解。《陌生的朋友》(1983)与《苦恼人的笑》(1979)中,亦是通过影片主体的心理世界展现过去时间的回忆和现在时间的不断穿插交织。第四代导演们通过视听语言的尝试所创作的这些早期带有意识流特色的影片,虽在技巧的运用中颇显稚拙,但用心理状态和情绪连贯使时间流动更为自由的创作冲动,却为中国电影艺术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
这种超验时间的流转变换源于主体的心灵,体现着主体的思维,并由其进行度量。“刹那”作为存在的极短的时间,谈及“现在”,现在已刹那成“过去”,谈及“未来”,未来已刹那成现在,时间被悬置、揉捏和平行,人物、故事、心境穿行其中。《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开篇以成年马小军“北京,变得这么快”的成年低沉声音开始,用心理时间回忆展开过去时间的故事,全片借旁白和画外音,用马小军的个人意识和回忆串联拼贴出青春岁月。或是“我的记忆好像出了毛病”、或是“千万别信这个”,马小军的回忆颠三倒四,看似不合逻辑,但正是这种成年后因年久与情感而变化的最本真心理意识,勾连起了承载不同记忆的分散时间,呈现出时而打断、时而快进倒退、时而跳跃的时间流转,将模糊跳切的记忆贯通。时间打破了因果与线性,事物循环之斗转星移、天道自然循环的“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大道化而为一的“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层层递进,最终以精神主体超越时空,道无始终、道体无限,在循环与新生中实现“齐物”“逍遥”。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分离的万物皆相互混同、没有分别,这是个体内在思维与外界相融合的境界,在此种循环往复的时间之境里,“心境与自然之时空同广阔无边,深邃无垠”,获得一种“游心之境、逍遥之境”,一种个体与万物相浑契的无穷体验。在现实题材影片中,《心香》(1991)通过对京戏代表的传统的不断心理认同,京京逐渐领悟到了传统的灵魂与魅力,结尾处与外公两人伫立于河边,迎风而来的帆船彷佛打破了时间的规约,将历史和现实、传统和当下契合地缝补在一起,所要凸显的精神世界的真谛与生活的本质最终跨越时间的阻隔通过传统而获救。《那山那人那狗》(1999)以倒叙性追忆展开,同时儿子又以“我”的口吻回忆上任第一天的准备,此时“我”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承担起当事人的角色。叙述故事回忆过去的儿子,以与父亲走山路送信为纽带,同时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里,用当下对过去的审视指向未来。儿子也通过回望儿时和父亲较“生”的关系,与当下随父送信的相处,在漫山遍野横亘绵延的绿色中,感知到时间的绵延循环。随着幽静平淡的送信山路,父爱与责任的情感也缓缓溢出。最终“我”承接着父亲的足印与父和解并找到价值,在接替父亲的行走中,继续时间的不断循环,呈现生命的绵延与往复悠长的情感体验。随着影片中时间流动转换产生的韵律节奏,和着传统中人与万事万物彼此和谐共生的理想生态观,传统古典独特的意境已呼之欲出,最终,通过片中主体的内心直觉体验,营造出了姚鼐在《望庐山》中“将游天地于一气”的终极心灵体会与时空境界。
三、超验时空中的圆融空间
圆融贯通的超验时空观植根于《周易》,“周”为环绕、“易”为变化,宇宙天地万物、社会生命万事都处在不断运动贯通的空间之中。圆融中的“随心而流转”从佛教尤其《金刚经》中生根发芽,空间无限性的“千”与时间无限性的“劫”共同组成了相对而生且趋于无限的超验时空,孕育出人与人、人与物、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众生平等”“无情有性”的万物共生。“六合五破之宇……空间之宇无论在平面四方或中央上下”,任何方向没有终点,亦没有止境,世界在其中是连环无端、无始无终的永恒过程,过去、现在、未来多个空间川流不息又相互叠套。《路边野餐》(2016)中以陈升的内心流转为依托,将真实生活的凯里、梦境魔幻的荡麦、安详宁静的镇远三个空间平行并置,构筑了平缓的生活流中随人物内心涌动而更迭的空间。凯里虽以陈升现时生活空间为主,但线性讲述中却多次被回忆中的过去空间穿插打断。这些由回忆造成的线性时空断裂使影片在虚幻与现实、过去与当下来回游荡,空间在相互叠加中变得不可捉摸。荡麦作为幻想出的平行飞地,与凯里或镇远构成了“两个世界”,它如同绳索的纽结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交汇,使观众随陈升的意识沉浸在空间的回旋交叠中。梦魇却真实生存的凯里,无限写实却梦幻的荡麦,归于安详的镇远,三个被并置的空间各自与彼此间虚实相生,过去、现在与未来多个空间彼此融合贯通。
传统的中国超验时空观中,相圆融贯通的空间“横遍十方,融此方、他方、十方世界”,此无量无边的空间植根于“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的万物平等皆可转化中,终直指我们心内的空间,可此可彼,随主观而自由变化随意跳接。神怪片常常就是在经验空间和超验空间的彼此融合里打破因果、割裂线性,使万物皆有灵的生命得以在空间中自由穿梭转化。《倩女幽魂》(1960)中阴冷肃杀的鬼魅、妖怪、地狱空间,薄烟笼罩的古寺人间,一人一鬼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被爱恨情仇打通。《画皮之阴阳法王》(1992)贯通融合阴间、阳间、阴阳界之间三个空间,阴阳法王和鬼魂在空间交错中随意游荡。《画壁》(2011)里姑姑掌控的仙境、仙女们生活的空间、寺庙人间、以及因朱孝廉闯入而产生的奇特空间,男女爱情、书生与书僮的主仆情还有仙女间的姐妹情,众多时空与情感都随着朱孝廉的“穿越”“冒险”而被打通,并终打破生死和地位的区隔。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西游记》(1986)中,其中由若干个“上路”—“化缘”—“打怪”—“求助”—“上路”多个空间平行同构而成的“九九八十一难”,及依据佛教宇宙体系划分的“三十三层天、十八层地狱、四大部洲”中,最终将心性修养表现在空间的贯通圆融里。这些被延展或打通或并置的空间,是被形象化的心象,在这种心与万物相契合的超验的无穷空间里,不断的相遇贯通圆融。
《周易·系辞》中曾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日月运行,四季更迭,唯有大道融通,才可往来获益。万事万物都在宇宙中以圆周形式运动,在这种圜道思维看来,既往的已退为历史,还未到来的还有待规划,只有在圆融无碍的空间、内向式的体验中,用“无住”破除“相”的束缚,不为事物停留,继而对过往心中了然,对未来有所预见,得到自在开放的心念,从而洞悉万物的变化,达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的大用。《大话西游》(1994)中贯通的空间不再是简单的平行轮回,而呈现出打破因果、因并不导致果的空间拼贴,人物随着这种空间的转换而不断转世,传统的爱情、欲望、权威、价值也被不断颠覆。陈升、花和尚及老医生等众人因怀念、愧疚、眷恋挤压而产生的内心执念,随着《路边野餐》中将过去、现在和未来魔幻交叠的荡麦空间,人物最深层渴望被轮回与补偿的情感,得以在与现实平行并置的另一空间中纾解。空间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观众也跟随主体进入此亦真亦幻的与现实平行的梦境,跟随主体承受不同的时空与内心情感的挤压,在剖开故事逻辑与内核之后,进而进行自身的反观,在空间的并行穿梭中得到排解和了悟,放下过去,也放下了我执,最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了悟停驻于真实的土地与鲜活的生命中。
四、超验时空中的生命平和
在循环往复、自由流动的超验时间和圆融贯通、跳跃和谐的超验空间中,传统的超验时空观孕育出了平和,这种平和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幻化而来,从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怜惜,到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将“仁者爱人”之心从对待人延展为对待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万事万物;从宋明理学中二程“人……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到王阳明“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用人的“身”“心”、与宇宙间的“人”“万物”做比揭示出的“万物一体”的和谐本源。从道家“万物群生,连属其乡……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把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作为理想的生态观,到《化书》“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自无情而之有情也”中老树与飞人、麦子与蝴蝶、甚至无情之物和有情之物之间的可相互转化。“夫禽兽之于人也何异”?人与动物同有“巢穴之居”“夫妇之配”,同有“父子之性”“死生之情”,亦同有“仁、义、礼、智、信”的性与情。在此种“天人合一”,人、宇宙、万物不可分离的和合统一中,其中往来穿梭的生命个体也呈现出安然包容的生存状态。“念念生灭,刹那之间,分为三际,谓过去现在未来……由一念无体,即通大劫,大劫无体,即该一念”,瞬时之“念”与久时之“劫”相互通融无碍,“个体小我的生命融入宇宙大我之中”,死与生从不固定不变,变化亦不意味着消失,生命也不再有绝对的终点。老庄“致虚极,守静笃”与“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也强调万物终究要返回根本(静的状态)才是时空转化的自然规律。
这种平和安然的超验时空观在藏族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俯拾皆是。电视剧《尘埃落定》(2003)讲述麦琪土司家族由盛转衰直至最终消亡,“傻子”二少爷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和故事的叙述者,傻与智并存,用从容坦然的生命状态、用超现实的寓言功能和“神”性,对权力、情欲、甚至生死都是来之则坦然接受,否之则不刻意强求。反观大少爷痴于权位、翁波意西执于传教、其余土司为土地和权力厮杀,最终都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作品通过现代生命意义与传统生命轮回、藏地佛教与汉区生活的结合,将二少爷平和安然的生存方式、万物有灵终归于空寂的宿命轮回一一呈现,最终用万物生命、权力纷争、喜怒哀乐这些“尘埃”都归向平息的时刻,直指人类甚至民族的精神状态。影片《静静的嘛呢石》(2006)依赖藏传佛教的生死观而展开,小喇嘛在从寺庙—藏历新年回家—又回到寺庙的世俗时空与神圣世界的游走与诱惑中,以全新的心灵奔向大法会。《皮绳上的魂》(2017)将复活的塔贝、琼和普一起护送天珠的时空,汽车、加油站和枪等现代文明出现的格丹找寻的时空,还有15年前占堆、郭日兄弟复仇的时空,交叉组接得以贯通。当格丹进入掌纹地后,他与自己创作的塔贝同时同地出现,也就将原有平行的三个时空提升至四个时空,以探讨超越了民族、宗教等更为宽广的命题。人与人的仇怨、人与鬼的相遇、过去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以西藏作为结点,这种时空往来交错的魔幻性在苍茫中浑然天成,彼此贯通的时空最终嵌入心理时空,得以指向每个个体最终平和从容的精神状态。当破除了对时间、空间的量的框定,微花不小、瀚海不大的心念也就随之而产生,当解构了时空的因果联系,才能超于世俗的理解,直至用平和的状态代替个体内心由于外界变幻而带来的禁锢或恐惧。通过对时空(世界)因果联系和必然性的消泯,在这个安然包容的环境中,个人内心的矛盾、或与大环境的冲突都在平和中被呈现。
万物在不断“成住坏空”(创始、稳定、毁坏、消灭)的过程中,随着客观界限的打破,最终宇宙万物不分彼此,回归于“梵”与“我”的统一。同时随着对世俗时空观的解构,时空也不再成为局限与束缚,生命个体不会再因时间的难以把控而感时伤逝,也不会再因空间的难以触及而哀婉叹息。《皮绳上的魂》中由小女孩托付天珠于男孩不成开始,由天珠被塔贝所捕杀的鹿吞食作结,不仅是对前面故事的补充,也是故事不停在上演的轮回。小女孩和鹿的生命形式转换,生、老、病、死的轮回经历,与生命有关的事物总在宿命般轮回复现。《静静的嘛呢石》里小喇嘛不管面对索巴老人的去世后,还是邻居新生的婴儿,都逐渐学会了抚平内心源于流逝产生的冲突。这种回旋不断加深观众意识深处的情感,这种时空的包容性、可延展性与轮回性中平淡朴素的灵光,使他们不再紧张未知,不再惧怕死亡,生命万物用从容安然的姿态在无限的时空变化中达到恒久。
线性的时空观与世俗的时空观被解构、消泯,传统的超验时空中将时间的先后与逻辑经验这些枝节去除后,最终只剩“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内向式平和体验,只剩人物在安然从容的生存状态中最纯粹的精神观照。《皮绳上的魂》中格丹从真实的现实时空走向虚幻的寻人之旅,一路追寻作品中的塔贝,也是对自我的寻找,直至最终在掌纹地觅到塔贝踪迹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回到了最初拿着天珠的责任。《静静的嘛呢石》中最后怀揣着孙悟空面具在大殿诵经的小喇嘛作为一个反传统却又继承传统的形象,也许真正悟到了什么是空。一如刻有真言的嘛呢石,虽然细小的变化时有发生,但依旧平和、静默,按照冥冥中的缘分与前定,以安静温和的心态、以心念自由的东方式生命力面对生命河流。
影视作为光影的艺术,是心灵外化与世界想象的展现。超验时空与中国影视结合后的往复循环、圆融贯通与最终呈现的宁静平和,融于意识流、武打片、神怪片等各种类型中,从早期的糅合运用一直传承至今,是导演不同以往的情感表达,也给予了观众与众不同的体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未知物种、领域与时空的探讨随即也越来越多,相应的,人类所不可知的领域范围也更加广阔,而这又恰恰为未来影视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鲜活的养料。中国的影视创作与观众的情感接受,植根于时间的往复、空间的同构、以及天地万物休戚与共的超验时空观中,其浸润在集体的记忆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代代传承延续,因此,当面对科技揭示出更多超越人类舒适圈的未知领域时,影视的呈现与观众的接受才得以更加的平和、从容。多向度的超验时空不囿于线性的束缚,与作品结合后主体性、直觉性甚至魔幻性的玄妙真实被展现,包孕着的流动、从容与空灵的东方意味也呼之欲出。
虽然当下中国电影对于传统超验时空观的表达并不少见,但形式与内容真正得以结合的还是集中于《路边野餐》《皮绳上的魂》《长江图》等这类小众艺术电影中,以时空的平行穿插、心理时空向物理时空的嵌入,探讨并终指向内向式的终极问题。相较于着重心理化时空贯通的艺术电影,在商业片与电视剧中,则多是像《画皮》系列,及由《西游记》《盗墓笔记》等IP所衍生出的这类神怪作品,其中时空并置贯通也多是为视觉的奇观化和奇异化服务。
被线性时间折磨、被固化空间困扰的现代个体,在科学割裂的时空框定下也失去与世界的统一。我们当以回望的视角进行终极问题的探讨,用独特的时空意义体悟生命,在东方式的传统超验时空观中以内向式的体验、心理的时间、平和安然的姿态作为归属,把个体的了悟扎根鲜活的土地、现于朴素的脸上、归于心念从容。从早期孔孟朴素的天人合一、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中人与万物同为一体的博爱,从道家万物和谐的自然本性,到“无情有性”的天地佛性,融汇这种由来已久的和谐共生是深入到时代深处将个体与历史结合反思后的表达,毕竟真正的影视作品“是对于世界的凝视”。
注释:
①西方亚里士多德哲学、但丁《神曲》的创作、印度的佛教、瑜伽、中国的上古神话中,都可见人类早期对时空探讨的端倪。
②程嘉哲编:《天问新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③④⑤雷一东:《墨经校解》,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80、194、83页。
⑥吴乃恭:《论王夫之“乾坤并建”的宇宙生成发展说》,《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
⑨查正贤:《论语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⑩冯契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经验”条目。
(作者冯果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鸿滨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