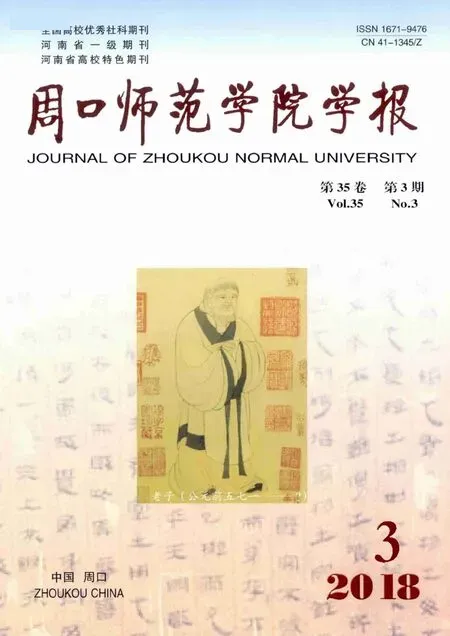孙全鹏短篇小说创作论
刘启涛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周口作家群的浮现是新世纪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一群体的产生有其特殊性。从地缘因素上讲,周口地处中原,且以农耕为主,可谓是传统乡土中国的重要缩影,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该地区作家创作的整体风格。从最初的刘庆邦到之后的邵丽和柳岸,周口作家大都表现出对豫东故土的深厚情结,这种情结在不同代际的作家那里有着不同的呈现。作为这一群体的后起之秀,80后作家孙全鹏有着清醒的艺术自觉。虽然他步入文坛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很快找准了自己的艺术方位。不过,身处当前城乡格局大变革的潮流中,孙全鹏这一代作家注定要去面对更多的困惑和纠结。这些困惑和纠结连同作者内心绵延不绝的乡愁,糅合成了将军寺村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意象。可以看出,孙全鹏的乡土书写并不像他的前辈那样纯粹,我们不妨从他近2年发表的10个短篇小说入手,来探析其作品的典型意义。
一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中,地域作家群的异军突起堪称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史上,地域自然和人文景观很少像这一时期如此原生态化进入作家们的艺术世界,周口作家群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创作潮流中呈现于公众视野的。大致来看,周口作家群的创作队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旅居外地的本籍作家,其中以刘庆邦、邵丽为代表;一类是生于本土长于本土(或者是外地求学本地就业)的作家,如柳岸、尉然、宫林等人。虽然前一类作家的艺术成就居上,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说,后者更能够体现周口作家群作为文学现象的本质内涵。周口作家群的队伍不可说不庞大,“有中国作协会员29人,河南省作协会员400多人”[1],其作品质量更是令人称道。
在当下文坛,全国以地域特色著称的作家群不下百余个,其中为学界广泛认可的也有数十个之多。对这些作家群生命力的考察,我们仅仅立足于作家数量的考察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不少作家群现象,如显赫一时的白马湖作家群、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虽然也是名家云集但是却昙花一现,有的甚至还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便已经烟消云散。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作家群队伍,不但要有高水平的作家出现,而且还要看她的作家代际结构是否能够保证创作上的可持续发展势头。只有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不断地向人们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作品,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作家群才能够得以成立。对一个作家群的考察,我们不仅要看这一群体是否有高水平作家的出现,还要对这一群体的梯队结构细加关注。
周口作家群中目前活跃的主要有60后、70后和80后作家等三大群体,其生命活力较为强健。这一群体出现了柳岸、尉然、宫林等一批重要作家,无论其创作成就还是队伍规模,都还远远未达到其极限。一方面60后、70后作家势头依然强劲,另一方面年青一代作家的成长亟待关注。实事求是地说,周口作家群的崛起在文学界业内的确颇受关注,但是否真的能够进入文学史并挣得一席之地,还有待更为长远的考量和评估。我们认为,周口作家群现象不应被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学事实,而是要把她视为一个发展中的事物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发掘以往作家作品经典价值同样重要的,是去关注新生代作家的成长过程和创作特点。因此,孙全鹏能够进入我们的视野并非始于偶然,在整个周口作家群的新生代队伍中,他的创作可以说代表了这一群体新的发展动向。
作家创作大都离不开独特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人生经历从根本上决定了作家们在题材上的不同选择。郁达夫就曾这样说:“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大家要笑话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转’。”[2]这当然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可却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作家创作上的成功首先离不开其特有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或许是作家本人的,或许是他周围的人乃至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作家在创作技巧上可以轻松实现超越,但是生活经验上却不能,即便是在科幻小说中,作家们也无法拥有活生生的体验,因为体验是发自心灵且触动灵魂的。故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然后方有一代人不同的文学。对于孙全鹏这一代作家来说,其人生经历不大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富有太多的传奇性,但是这一代人的经历中,却也有着诸多前辈作家无法体验的复杂性。
另外,与60后、70后作家们相比,80后新生代作家在创作资源上也有着很多前辈作家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代作家大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他们有的人即便不是文学科班出身,也大都有过较为集中的阅读和写作上的经验。虽然教育经历对于作家艺术水准的影响一直都存有争议,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即文学素养的提升使作家在创作中少走很多弯路。在周口作家群中,像孙全鹏这样具有文学硕士学位的作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之所以能够在艺术世界很快找到自己的中心坐标,与其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领域的专业训练不无关系。目前来看,孙全鹏在很多方面还算不上一个成熟的作家,但是他在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上,确实有着一些前辈作家难以做到的清醒。
孙全鹏的创作主要涵盖两大类题材:一是年轻一代农民(也包括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进城题材,二是乡土题材。而这两类题材几乎都是以将军寺村为背景展开,由此就不难看出,孙全鹏在文学事业上是有雄心壮志的。笔者姑且贸然揣测,这位年轻作家正试图以自己生长于斯的那个豫东村落(即将军寺村)为中心,在文学世界里打造出一个独立的艺术王国,而这个王国就像鲁迅的鲁镇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那样,蕴藏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将军寺村几乎成为打开孙全鹏艺术世界的一把钥匙,我们从他近年来发表的这10个短篇小说中几乎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对于新世纪文化语境下的周口作家群来说,这种艺术雄心无疑是最欠缺也是最值得期待的。
二
孙全鹏创作最多的一类是乡土题材。从这些作品的创作特点和艺术水准来看,孙全鹏完全可以说得上是位颇具潜力的新生代乡土作家,他对生长于斯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在他近些年发表的作品中,基本上都没有脱离故乡将军寺村这一地域坐标。只是在当前城乡格局大变革的背景下,乡土写作注定是充满困惑的。包括孙全鹏在内的年轻一代作家,在写到乡土题材的时候,既不大可能去追随现代文学作品中那种执着的启蒙精神,也无法像当年“寻根小说”那样,从风土人情的书写中发掘离奇怪诞的现代元素。孙全鹏的乡土书写主要是为他那强烈的乡土情结所驱动,他的这些小说在深入描写将军寺风土人情的同时,也触及了新型文化语境下农村所面临的危机。在他的小说《声音从半夜出来》《鸡笼子》《幸福的日子》《长长的秋风》《祖传军功章》等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平静的叙述中蕴藏的是对故土的复杂情感。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孙全鹏的故土情怀都是极为强烈的。将军寺村已经成为这位年轻作家创作中的一处精神原乡,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无不渗透着他的深厚情感。我们不难发现,孙全鹏也正在试图深入故土,从中发掘出独特的艺术元素,并在小说中呈现当下豫东乡土社会人情世故复杂的一面。在短篇小说《幸福的日子》中,孙全鹏塑造了一个有仁有义的父亲形象和一群善变的乡亲。小说围绕老锅叔养鸡这一事件,通过父亲的行为和周围乡亲们态度的变化,把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冷暖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刚开始拒绝了上门求教养鸡的乡亲,因为父亲不想坑害大家。在他看来,“养鸡跟打仗一样,看准了,要去干好,别管那些没用的”,而这些上门求教的乡亲都是急功近利地想挣钱。后来,父亲却被老锅叔的诚意打动了。可是,果不其然,老锅叔在养鸡之后就开始一点点发生变化,最终弄了个家破人亡。
《幸福的日子》算是孙全鹏发表较早的一篇小说,但是作者却能够一把抓住乡土社会遭遇商品经济冲击的现实,显示了他敏感的一面。事实上,孙全鹏这一代作家面对着一个现实,那就是乡土社会在后工业社会所经受的无情冲击,传统价值观念正在一步步被颠覆。无论作家内心深处怀有怎样一种强烈的田园情调,其最终都无法拂去那种沉重的感伤,这种感伤在《祖传的军功章》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小杰在将军寺的老家遭了贼,回去看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一枚祖父留下来的军功章,平静的生活由此发生了波澜。先是小杰在出售军功章的时候,被妹妹和妹夫瓜分了一份。而后,三叔偶然听到了这个消息,竟拉上10年未进家的老二来分一杯羹。清明前一天,老二打着给父母上坟的名义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了回来。当分别10年的哥仨坐在一起后,老二竟然顾不得寒暄就提出来要和大哥平分军功章。清明那天,老大去上坟,虽然去得很晚却还是没有见到老二和老三过来。
孙全鹏的乡土题材作品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这种沉重实质上正是作者厚重故土情感的另一种表现,它也体现了孙全鹏这一代作家可贵的一面。虽然这一代作家生活在一个物质上相对丰裕的社会中,但是他们仍能够从一个较为深刻的层面书写出当下乡土的普遍状态。在当前商品经济主导的文化语境下,乡土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受到金钱的严重侵蚀。孙全鹏的作品触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存在传统乡土价值观下的农民,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抗住外部的诱惑。《长长的秋风》中就写到一个抛家弃子的父亲,最后当这位父亲带着沉重的忏悔归来的时候,母亲却已经因过度劳累而早早与世长辞了。在这里,父亲对家庭的离弃固然是人性中抹不去的劣根性在作祟,但是它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乡土价值的礼坏乐崩。
孙全鹏在他的乡土题材中显示出了一种难以消泯的困惑,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作者对“根”的深厚情节,这个“根”就是萦绕其心头的将军寺村。我们从孙全鹏的作品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对这片土地的无穷眷恋,这种深情在他近期发表的《鸡笼子》和《我知道你不信》两个短篇小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虽然两篇小说情节设置的背景一个是乡村另一个是城市,但是二者之间可以进行互文阅读。《鸡笼子》写的是奶奶的故事,早年从不主动去碰渔网的奶奶为了养家成为捕鱼高手。一连九年,奶奶都是夜间出去打鱼,早上赶到集市上卖掉,再天亮后回家。直到一个夜晚,奶奶在撒出了九个空网之后捕到的竟是一只长着人手和人头的鱼。奶奶瞬间被吓坏了,从此不再捕鱼,并不断地对以前捕鱼的事情进行忏悔。而后奶奶便开始养鸡,并喜欢用柳条编成鸡笼子,鸡笼子编成之后,再放进去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可以说,奶奶养鸡已经不再只是为了生计,还是一种心灵上自我救赎的方式。最终,奶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心灵的救赎。这篇小说和孙全鹏之前的小说很不一样,通篇散发着一种诡谲神秘的气息。而在这种神秘诡谲的气息中,却流露了作者与故土的赤子情深。
《我知道你不信》写的则是一个来自将军寺村的送货员猴三。猴三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他首先有一个特殊功能,经常能够从空中看到一个跳舞的人。还有就是猴三很轻易地就相信别人,在常人看来一眼就能识破的诈骗事件,他却总是信以为真,因而做了很多让“我”大为光火的事情。后来,猴三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被养父逼婚的女孩子,竟然要不顾一切地帮助这个女孩子逃离自己不幸的家庭。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猴三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我”认为这是骗子的把戏,而猴三则认为这是天赐良缘。最终,猴三和“我”不欢而散后,在给女孩汇医药费的路上出了车祸。一个月后,当一个女孩来“我”的店门寻访猴三下落的时候,“我”终于为猴三的义举流下了眼泪。严格地说,这篇小说属于进城题材,但作者正是通过猴三这样一个善良而无心机的进城农民形象,写出了对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与当下社会的龃龉。可以说,这两篇小说构成的是一曲乡土的挽歌,它从两个视角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眷恋。这两篇作品的写法与孙全鹏之前的作品都不一样,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正在实现一种技巧上的突破。
三
我们再来看孙全鹏创作的另一类题材,即“进城”题材。孙全鹏这一代作家身上有着诸多特殊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既是计划生育运动中的“幸存儿”,也是高考和研究生扩招政策的“受益者”。与此同时,他们不但承受了分配制度被废除之后的就业危机,而且也经受了功利主义时代的挤压。80后作家们固然不会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经受饥饿和重体力劳动的考验,他们面临的苦难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而这些苦难在上代人看来大多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孙全鹏这一代作家的体验中有着前代人无法体验的复杂性,这种体验也只能由这一代人去书写,才能够带给人刻骨铭心的感觉。从孙全鹏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握这一代人特有的苦难。
在把握同代人命运的过程中,孙全鹏选择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就是人们的感情生活。孙全鹏作品中的青年一代,比如像《缺氧》中的张明、《心上秋》中的王刚和《再相逢》中的曹明明,都从不同方面典型地代表了一代人的集体命运。在这三个人物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来自农村,通过多年寒窗苦读上了大学,而后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而较为体面的工作,从而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这种机遇正是80年代初期高加林一辈梦寐以求的,今天的青年一代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了。可是,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之上,新一代农村青年在走出农村之后,如何才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孙全鹏笔下的人物并不比高加林时代轻松,他们往往都是做出了较为巨大的牺牲,牺牲的首先就是爱情。
以《缺氧》中的张明为例,这位勤学上进的青年因为家里供不起他读书,而接受村支书的援助,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只是村支书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张明大学一毕业,村支书就上门找父亲谈女儿和张明的终身大事。即便张明有一百个不乐意,可是父亲的一句话——“你花了人家的钱,就要听人家的安排”,使张明拒绝这桩婚事的所有底气泄得一无所有。在爱情和良心面前,张明终于向后者屈服。对于张明来说,上大学的机会实质上是他以爱情做抵押争取来的。虽然张明成功落户城市,但是他的另一半失败了。即便他离开了祖祖辈辈挣扎的土地,可是却从此开始了“一地鸡毛式”的悲剧生活。他一方面在贫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中和村妇般的妻子相濡以沫,另一方面却幻想着与女大学生贾丽秋的惬意时光。对于张明来说,贾丽秋无疑代表了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只是对张明来说,这种爱情终归只是一个泡影。贾丽秋说的“诗人没有爱情,就会因缺氧而死的”,无疑是对张明做出的一个精神判决,小说中的“鱼死事件”正是现实生活使张明精神窒息的一个隐喻。
从张明身上映射出来的青年一代的命运是黯淡无光的,在一批批进城大学生的奋斗历程中,隐藏了这一代人难以道出的悲剧命运。上大学非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张明等人的生活处境,反而使他们堕入新的生活苦闷,最终在死水般的生活中慢慢窒息。张明的生活悲剧源于一笔“良心债”,那么,假若没有这笔“良心债”,张明又是否能够拥有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呢?孙全鹏通过小说《心上秋》中的王刚给了我们答案。王刚没有张明那样被逼婚的经历,但是却饱受着成家立业的苦恼,最后终于因为一时寂寞失控而和感觉平平的服务员付梅发生了关系。后来一个叫秋的女孩即将给他带来一场幸福满满的爱情时,付梅却突然给他发来一条信息:“我怀孕了!!”这篇小说不无黑色幽默的意味,只是这种幽默让人看到的却是命运之神不怀好意的嘲弄。王刚所有的希望瞬间崩塌了,“那几个字像一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了王刚的心头。他抬起头,阳光火辣辣地烤着他,他的泪水又出来了,噗噗地往下掉”。我们不难理解王刚内心的挣扎,他在这种挣扎中成为下一个张明。
无论张明那窒息人心的生活还是让王刚哭笑不得的爱情,无不是在沉重地诉说农民子弟在进入城市之后的种种辛酸和无奈。这群优秀的农民子弟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为了扭转自己的命运,可以说牺牲了自己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就像《再相逢》中的曹明明,为了能够顺利留在县城,不惜抛弃与自己真心相爱的女友,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去追求教育局长的女儿。终于一步步爬上了校长的位置,但是却因为婚外情事件而被岳父动用关系赶到了穷乡僻壤的将军寺村。与张明和王刚相比,曹明明改变自己命运的心情显然更加迫切。就像他所说的“我不想再回农村去,我不愿再当个农民,你说我有这个想法有错吗?”曹明明不想做农民的想法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他改变命运的方式错了。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80后这代人成长的道路并无太多曲折,但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复杂程度却不比前几代人小。通过孙全鹏的作品,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像他这一代人,几乎都是经过勤奋刻苦完成学业,而后改变了自己与土地打交道的命运,他们对生活有着很多旁人无可领会的体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孙全鹏在写到青年一代的时候,他的笔触都是沉重的。在他塑造的青年一代人物身上,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压抑。他们在城乡之间的缝隙中碌碌地生活着,一方面渴望奔放或惬意的浪漫爱情,另一方面却又百感交杂地接受着命运的调弄。就像《尤克里里》中的“我”,虽然内心涌动着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但是却在一场浪漫的奇遇前畏畏缩缩,最终只能选择漫无目的地流浪漂泊。在孙全鹏的这些小说中,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往往是这种精神的流浪者,他们在一种命运的苦海中无所归依地随波起伏。
从某种程度上说,孙全鹏的“进城”题材是其乡土题材的一种延伸。梁鸿在谈及河南作家创作的时候,就曾经这样指出:“无论是以‘村庄’还是以‘城市’为起点,最终通向的都是一个问题,即人的存在问题。”[3]孙全鹏在写到农民后代进入城市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强调其农村背景,这位年轻作家唯恐一旦不提及自己的故乡就好像要迷失自己。如果孙全鹏在他的乡土题材中表达的是一种故园的离愁,那么他的“进城”题材表达的更像是一种游子的困顿。
总体来看,孙全鹏这10部短篇小说都是较为成功的,其中虽然也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不过,对于孙全鹏等年轻一辈作家来说,对他们做出理论上的定论还不免为时尚早。从孙全鹏近些年来的创作势头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作家。另外,我们从孙全鹏的创作中也能够看出他正在有意实现对前辈作家的超越,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一步步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而这种状态无疑正是当下周口作家群所欠缺的。只是孙全鹏在创作上的极致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假以时日的话,他也许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参考文献:
[1]任动.“周口作家群”: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4(1):41.
[2]赵李红.郁达夫自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70.
[3]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2.
——以广西高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