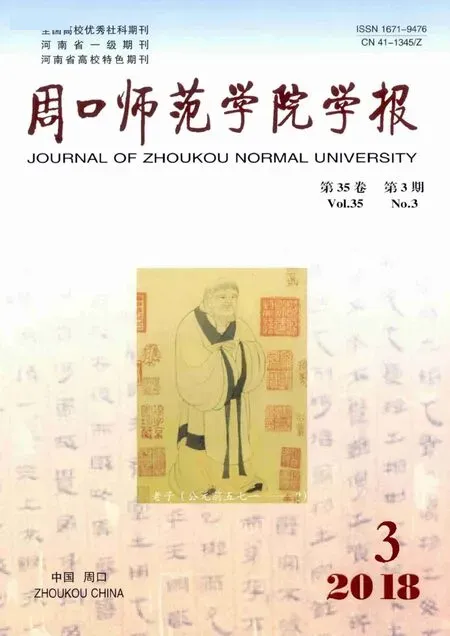论月亮在中国文化中的审美性
李 延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月亮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其审美意义当然要归功于人类对自然的审美。针对自然审美的发展,周均平先生说过:“全面审视我国古代自然审美观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由‘致用’自然审美观,再到‘比情’自然审美观,再到‘比德’自然审美观,迄至‘畅神’审美观的嬗变。”[1]因此,对于月亮在中国文化中的审美性,我们将借助“致用、比情、比德、畅神”来加以探讨。
一、月亮的“致用”价值及意义
在原始先民时代,因为生产力非常低下,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处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在大自然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惧怕它的“淫威”,匍匐在其脚下。在这种情况下,人对自然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崇拜之心,人与自然是在一种不平等关系中共处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物质实用性和物质依赖性。所以, 我们就可以理解人们对月亮的态度, 最初也主要是从“致用”的角度去考虑并审视的,比如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
(一)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应该是一种早期人类共有的近似于宗教崇拜的形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先民们的眼中,周遭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而且自己的生命力远远低于自然物,所以创作了很多神话人物,进行祭拜和敬仰,天地日月、山河湖泊,都由其主宰。以月亮来说,月亮神,有古希腊的阿佛洛狄忒,有中国的常羲(嫦娥),等等。先民们匍匐在这些神灵的脚下,把自然的崇高、人的渺小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周礼·仪礼·记》的记载,我们可见,先民们祭祀日月是分不同时间的,春分早晨祭日,秋分傍晚拜月,而且祭日时要朝东而拜,祭月时要朝西而拜。
(二)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是原始先民们有关生命的一种本能意识,而月亮因其外形和变化规律成为他们头脑中对生殖的直接反映。在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妇人月水》中可以看出,月亮的周期变化,引起了先民们的注意,特别是女性。美国学者哈婷写道:“原始人眼中,女人一定是和月亮具有一样的本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和月亮一样都有着‘膨胀’的趋向,而且还因为她们也有和月亮的公转时间周期大致相同的月经期。”[2]女性的这个生理现象与月亮的圆缺变化具有一致性,所以这生理现象被称为月水、月信、月经。月亮由缺到圆、又由圆到缺的变化规律,容易使女性联想到怀孕后生子的变化,先膨胀变圆,分娩后再次恢复。考古的发掘也能进一步证明原始先民关于生殖的崇拜。卫聚贤在《古史研究》列举了“庙底沟仰韶文化H7:48彩陶片残留的蛙纹下部有一圆圈,甘肃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一个彩陶盆内壁所绘蛙纹,尾部亦有圆圈,从而指出这些圆圈就是女性阴户的象征”[3]。而且,在国外的考古中也同样出现了这一现象,比如出土于奥地利的“威伦道夫的维纳斯”,其乳房和臀部等是夸张突出的。可以说,在原始先民那里,关于生殖的崇拜是没有地域差异的。生殖崇拜随着历史的演变,慢慢地被人们赋予文化的含义。傅道彬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论述月亮和女性隐喻关系时,认为女性代表母系社会没落后其在男性世界的忧伤。以生殖崇拜为起点,月亮与女性进入一个无比广阔的文化世界,或是情感交融,或是道德比附,或是心神畅达。
二、月亮的“比情”价值及意义
“比情”是人们把自身的情感变化比附到自然物上,从此自然界就具有了人的情感和意志。比情说在汉代《淮南子》中已略有所见,后世的诗学理论、画论都有很好的阐释。比如南朝钟嵘《诗品》就有说让世人把一些情感表现出来是借助于一定的事物的句子。而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提出,要把感情放到画中,则春山不同于夏山,秋山也不同于冬山。这样来看,借月亮来“比情”的作品是众多的,并且这里的“情”也是多样的,有对恋人相思之情,有对家乡、亲友的思念之情,也有孤独失意的文人情怀。
(一)以月寄托相思之情
爱情作为一大母题,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有时,爱情双方常常不能相处在一起,相隔两地的爱人,在残月、圆月之下,时时刻刻思念着对方。所以,月亮也就成为文人墨客们书写相思的意象。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用一轮明月把相隔两地的情人联系起来,同时不同地,但同样的月亮应该是他们相思的见证。晚唐诗人韦庄有一词《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回忆起,某年的某个夜晚,在花下初次见得谢娘的场景。多年之后,在这个残月低悬的夜晚,远处时不时传来几声黄莺的哀鸣。诗人和谢娘同为沦落他乡之人,念着重逢,可希望渺茫,只得望月惆怅。这种不得见的相思之愁,与孤星、残月相互为伴,一股伤感油然而生。又如李清照的一首词《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借着楼上的明月,传达出女子对在外漂泊丈夫的片片痴情。
(二)以月寄托思念之情
明月高悬,容易引起世人孤独的情愫,在这种孤独情感的感触下,除了引起恋人之间的相思外,也有对故乡和亲友的思念。首先,我们来看关于借月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徐陵在《关山月》中,直抒胸臆见月思乡。南北朝时由南入北的著名诗人庾信,在他的《怨歌行》中,以期望月圆的暗语来期盼着能够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唐朝白居易在《望月有感》中,由头顶的圆月想到兄弟姐妹,他们都流散各地,此时会不会也看着月亮流泪想着对方,这种离家的孤独,触人感发。当然流传最为广泛的要数李白的《静夜思》了,篇幅短小,朗朗上口,却意味深长,把中华民族的思乡情愫凝缩在寥寥数语中。除了圆月,残月同样也能让人潸然泪下。在温庭筠的词中多见残月,比如,“雁飞残月天”(《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以残月为背景孤星或孤雁为点缀,江烟袅袅,惹得情思朦胧,一片思乡之情缭绕眼帘。另外还有很多词句都可以称得上是借月思乡的佳句。
其次,我们来看关于借月表达对亲朋的思念。王昌龄在诗《芙蓉楼送辛渐》中,借玉壶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瑕和对洛阳亲友的思念。作为回应,李白把对老朋友的深切关怀,寄托给了明月,让它代替自己去夜郎探望。这样的借月“传信”的奇思妙想,诚挚感人。另外,从苏轼的《江城子》中,可以看到,洒在作者妻子墓前的月光,是凄凉的,十年生死,阴阳相隔,终不会再见,是一种肝肠寸断的思念。另外,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可以称得上是借月思亲的名篇。
(三)以月寄托失意之情
当然,在孤独的引导下,大部分的诗人会产生苦闷的失意,用来感叹仕途的坎坷,这时的月亮成为失意文人宦海沉浮的见证。用月亮来寄托失意之情的诗句,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在秋月美景的描绘中,反衬诗人被贬谪之后,落寞、孤寂之情。杜甫同样用反衬手法,他的《旅夜抒怀》中,把自己老年颠沛流离的凄惨形象借着雄浑的景色表现出来。而《宿府》则可以认为是,借着美好月色无人欣赏来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李白的《蜀道难》,是在月景的烘托、杜鹃的哀啼中营造出凄凉的意境,表现出诗人不能实现理想的惆怅。诗人自娱自乐的形象借着月光看得通透,自在之外难以掩盖此时诗人的无限凄凉。
三、月亮的“比德”价值及意义
关于比德的意义,在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中这样定义:“比德是春秋战国时出现的自然美的观点,自然物之所以美在于它可以与审美主体‘比德’,即从其中感受或者意味到人格美。”[4]实际上就是说,自然物的美与价值就是因为它们比附的人们的某种道德情操以及道德情操的价值,那么,月亮的比德价值就与书写月之人的道德追求相关。比如,高洁品质,恒常守一,崇高精神,等等。
(一)把月看作高洁品质的象征
月亮因其纯清、皎洁的特征,常常被历代的文人墨客用做高洁品质的象征。如在战国末年楚国屈原《九章·涉江》的诗句中,屈原借月亮表达他的志向。他从小就喜爱奇伟的服饰,这一爱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他喜欢腰佩着宝剑,头上戴一顶切云帽,身挂珍珠与美玉。可世间的人都被污浊了心灵,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只好坐上青龙驾的车子,与重华(帝舜)一道游列仙境。他登上昆仑山后,发出一句“呐喊”:我要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这句“呐喊”是屈原坚守道德节操的真切表达,他高洁的信念如同日月一般,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发出永不熄灭的光辉。诗仙李白在一首诗中歌道“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一》)。这是一首寄赠的诗歌,从诗意来看,是诗人的朋友罢官归隐,他们之间音信久疏,诗人写诗赠怀。这一句,是这首诗的点睛之句,前半句写到天空的清幽、江月的苍茫,后半句写出了诗人平静的内心,此刻情景交融,诗人淡泊志远的情怀、清新脱俗的心灵,在月光中十分祥和。
(二)把月看作恒常守一的象征
月亮以其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被看作是爱情恒常守一的象征。爱情是浪漫而甜蜜的,但在古代文人们很少直接表达爱情,而是找些相关的意象来代替,因此“月亮”就成了爱情的化身。我们就以《诗经·国风·邶风·日月》为证,这首诗把弃妇抱怨丈夫变心描述得非常真切。全诗四章,每章六句都以日月起兴,并用日月的恒常不变来反衬女子丈夫的朝三暮四同时弃妇在内心深处还留有对丈夫的怀念,仍然盼望着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心转意。在这里,日与月的作用除去起兴,剩下的就是引人深思,月亮和太阳能够这样长长久久地不变其形状、不变其规律,而能够做到长长久久地爱着对方,恒常守一的夫妻又有多少呢?月明之夜,苏轼想起亡妻,作词唱道“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并诉说自己对王弗的深切思念。“八卦”他的情史后,会发现他还有妻子王闰之和王朝云,虽然在古代三妻四妾很是正常,但这也说明了,爱情中恒常守一的弥足珍贵。
(三)把月看作崇高精神的象征
崇高作为审美范畴的一种,与崇高精神是不同的。崇高精神是崇高范畴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通常是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艰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当月亮与崇高精神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古代诗文中有很多作品是借月亮来抒发作者的雄心壮志。比如,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其一》,把贤臣谋士比作明月,不知道何时能够摘得,表达诗人求贤如渴的心理。这种焦急地、忧愁地盼望着贤达,是为了天下苍生能够安居乐业的远大政治抱负,崇高的精神不言而喻。到了盛唐的年代,文人们大都想立功建业、大干一番。比如诗人李贺的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马》)。望着远处的无边沙漠里,白沙似雪,巍峨的燕山上挂起银钩,心灵深处有一幅辽阔的边境图,想着何时才能为战马戴上镶金的辔头,驰骋在秋高气爽的战场上。表达诗人渴望能够大展抱负的情怀。
四、月亮的“畅神”价值及意义
“畅神”说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起源于魏晋时期,也有学者认为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就开始萌生。但无论此说发源于何时,它都是人们在对自然的美好向往中,得到精神的解放,它是“某种意义上的特有审美, 它能孕育出一种审美的情调, 培养出一种审美的人格,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自然中感受到精神的欢娱自适,是完全意义上形骸和灵魂的双重放松”[5]。它的价值已经不同于致用的实际功利审美价值、比德的品格审美价值、比情的情感审美价值,而是一种在自然美的陶醉中得到的生命体悟。比如,在月的永恒中感叹人生,在月的迷幻中表现豁达。
(一)在月中表现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月亮的圆缺变化,周而复始,以其永恒的深刻象征,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抒情感怀的意象,他们在月的永恒中表现出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静静地悬挂夜空中的这一轮明月,在历史的演进中,它早已经脱离自然界,成为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一个表征符号。在对万事万物无限敏感的诗人那里,或是比情,或是比德,更能体现价值的是畅神了,这时候的文学作品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吟咏之作,而是深层次地表达人生哲理的浩叹。在这浩叹之中包含着诗人浓烈的宇宙、生命意识,这种意识是在宇宙永恒中对生命短暂的哲理思考。
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可谓是古今称奇。这首诗的时节是春天,地点在江边,时间是晚上,闻着随清风飘荡而来的花香,在皓月之下展开对宇宙和人生的遐想:“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春江春花,还有年年相似的月亮,不同的是人在变,一代换了一代,在这种宇宙的无限、人生的有限中表达出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给人一种如庄子所言“白驹过隙”的感觉。当然,这样的感触在所叹之人那里,也是无解的。
在诗作以外,古代文章中亦有面对月亮而产生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就堪称经典。苏子与客泛舟夜游赤壁,在明月、清风和江流之间,引发出对人生的思考,怎样才算得上有意义的人生?客随即感叹道人生的短暂,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只得“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句话中包含了对宇宙永恒的艳羡。李白、李贺等诗人,在他们诗中用月亮去营造一个理想的、脱离现实的天国,从而期望摆脱现实生命不得长久的焦虑,客的话与此相类似,但又因“知不可乎骤得”而怅然若失,明月常有,而“我”不常在,只能“托遗响于悲风”。苏子则不然,面对相同的景色,他却发出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感慨,水有流逝,月有盈缺,在景与情中,抒发人生与天地变与不变的哲理。显而易见,苏轼与客的辩论,其实就是作者内心自我的独白,它代表了感伤和超然,这也是历来文人墨客借月亮表达宇宙人生哲理两种不同的解答。
(二)在月的思考中表现乐观与豁达
在上文我们就提到,素来文人墨客就有借月亮表达宇宙人生哲理的有差别的两种解答方式——感伤和超然,这种两种方式就是人生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感伤中多少会消极地面对人生苦难,而超然之下就是积极乐观地面对世间万物,表现出豁达的人生态度。《前赤壁赋》中苏轼对客的回答就是一种超然一种豁达,另外,“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词句中,表现出宠辱不惊般淡然自若的心态。又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句中,悲叹光阴易逝的同时,也同样表现出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另外,李白诗中的月亮是他观照物我的明镜,月下的独酌是他感悟人生的豁达。可以说,李白是用多重姿态生活的,有时他是一个羽士,有时是一个狂人,有时又是一个侠客,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醉翁。但姿态的多样并不能改变他的人格,他骨子里是浪漫与奔放的。这也并不是说李白没有苦闷、悲伤的时候,比如上文说到了他的失意,但他对这类不幸的处理,不像常人那样“哀怨又彷徨”,而是以一种怪诞似的放纵来表达乐观。而饮酒就是这种怪诞的放纵,他的饮酒方式一方面是豪饮,另一方面是独酌。其一,关于豪饮。在其《将进酒》和《短歌行》)等中都有描述,他用豪饮带来的狂醉麻醉自己。其二,关于独酌。独酌的环境常常是在晚上月下,如诗句“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独酌》)、“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春日独酌》)、“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这三首诗犹如水墨画般,在清淡的布景上绘上一轮明月。皎洁的月色下,一个飘逸的诗人在闻着花香,品着美酒,手里还不时地拨动琴弦,虽是一人,但并不显得孤寂,因为有山上的月、溪中的月和酒中的月。正如傅绍良先生所言:“酒被诗人当作通向生命深处的溪流,清月则被看作诗人观照物我的明镜;酒与月共伴诗人在酒兴和月色中走向充实与自信。”[6]在独酌中诗人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之地,感悟人生的豁达,走向自信与永恒。
参考文献:
[1]周均平.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05.
[2]M.艾瑟.哈婷.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M].蒙子,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23.
[3]卫聚贤.古史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68-169.
[4]李泽厚,汝信.美学百科全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23.
[5]赵春雷.中国古代审美自然观[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87.
[6]傅绍良.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与哲人风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