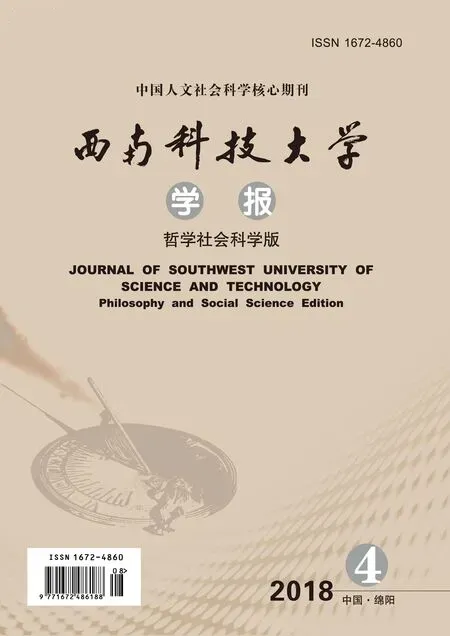论《史记》论赞对法家的评价
姜晓娟 蒋 蔚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史记》论赞,即“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序、赞、论的史论形式”。[1]4论赞不仅是《史记》体例的重要构成部分,更是司马迁个人史学观的集中体现。《史记》论赞内容博杂,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评价时,并没有单纯地局限于某一家思想,而是以辩证的历史发展观,以儒家思想孔孟学说为中心,普遍涉猎先秦诸子学说,且结合具体形式后做出自己的论断赞语。目前,《史记》论赞研究已成为《史记》研究的重要方面。在论赞思想研究中,学者多从儒、道学说来研究司马迁对二者的接受,而先秦其他家思想在《史记》中的体现却鲜有触及。张大可先生《史记论赞辑释》对《史记》中的论赞进行评述时对相关历史人物及其涉及的各家思想均有一定的评论,体现了张大可先生开放的史学研究视角。陈桐生先生的《论〈史记〉与法家》从《史记》整体文本内容入手,通过《史记》中主要法家人物传记以及司马迁对法家观点、行事的评价,认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从“整齐百家学说”的角度对法家学说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尽管司马迁因个人遭遇在《史记》中对法家思想批判较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司马迁从史学家的角度,对法家人物、思想以及行事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也吸收、借鉴了法家思想中的有助于社会发展、国家一统的治国方针,使得《史记》,尤其是《史记》论赞具有诸多法家评价的痕迹。本文拟从《史记》论赞中对法家学说及其主要人物的评价出发,探究司马迁辩证的史学观,借对法家的评论折射出个人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以及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双重评论模式下司马迁对法家评论的矛盾态度。
一、《史记》论赞法家评论的主要表现
法家是先秦时期诸子争鸣中的重要一家,在秦国于诸侯征战中迅速脱颖而出,以及在始皇帝建立、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成为汉武帝统治时期严刑峻法的直接受害者,外在政治高压与个人坎坷人生遭际使其对法家一系列理论主张有着矛盾、复杂而又深刻的认识。先秦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李斯、韩非,汉代数名循吏、酷吏等均被司马迁在《史记》中立传,在论赞中对他们也有褒贬不一的评价,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特别关照,从侧面折射出其对法家思想的个人思考,使《史记》论赞呈现出史学与文学意义上的双重艺术价值。《史记》论赞中的法家评论主要表现为以“变”为内核的进化史观、对严刑峻法的批判接受以及认可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暴力征战三个方面。
(一)对法家时移世易的进化史观的肯定
张大可先生认为:“《韩非子·五蠹篇》记载了法家时移世易的进化论历史观这些无疑都是司马迁所继承借鉴的历史思想资料。”[1]76《史记》论赞中表现的法家思想首先便是法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时移世易”的进化史观,其中有些观点即使放到当代社会也具有现实意义。如《高祖本纪》赞曰: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毒。葬长陵。[2]393-394
很多史学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强烈的天命观色彩,如刘知几在《史通》中就曾指出《史记》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一点便是“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3]717言司马迁在总结一个王朝兴衰得失时往往充满天命论的色彩,放大天命对人事的作用而忽略人事得失进行褒贬评价,是历史评价中的一大缺憾,正因如此,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的论赞往往被后世视为司马迁充满循环论的天命观。但张大可先生认为,司马迁“抽象地讲‘循环’,而具体却是讲‘变’,指出汉高祖救秦之敝,改弦更张而得‘天统’。”[1]67在司马迁看来,夏之政忠、殷之政敬、周之政文,这些王朝在改革前朝政治弊病时也存在自己的问题,从而造成新的统治隐患,这些问题到了秦朝亟待以新的制度改弦更张,进行解决,而“秦政不改,反酷刑法”,是说秦始皇非但没有改变制度,反而企图借助政治高压与严刑峻法来规范人民,这种行为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其实,司马迁并没有片面地将历代王朝兴衰归结为“天命”,而是认为政令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即“不变”所导致的,故而汉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承敝易变”,一改前代政治弊端,正是因为统治者顺应民心民俗,才得到“天统”。如果单纯地将这段论赞归为循环论或天命论,显然是没有看到司马迁个人对积极变法的肯定。
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开塞第七》中云:“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5]71韩非在《五蠹篇》中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4]439-440商鞅、韩非等先秦著名法家思想家在其著作中均表现出不效法古人,亦不遵循今人的社会改革观念,他们倡导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方法对国家进行治理。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表现出的法家“时移世易”的进化史观与韩非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是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肯定法家思想部分内容的典型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对法家诸多治理社会的理论主张进行评论时,首先肯定了其思想中的积极因子,这也是司马迁父子“整齐百家学说”的作史宗旨。
(二)对法家严刑峻法的批判
受个人遭际的影响,司马迁对国家法律的认知是复杂而深刻的。他既承认对于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的必要性,褒扬奉公执法的循吏,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统治者严刑峻法对百姓带来的灾难,这种复杂的认知,表面上是在影射司马迁本人对残苛暴政的否定,但深层意义上也反应出司马迁个人思想中儒道学说与法家思想的斗争。在司马迁看来:“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治理得好坏的本源。”[1] 344判定国家治理好坏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人心向背,而严刑峻法只能起到暂时的效果,不可能得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基于上述观点,司马迁在对《史记》人物的论赞中表现出对严刑峻法的强烈批判。如司马迁对先秦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有“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2]2237韩非子有“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2]2156的评价,从这些论断中不难看出,司马迁的个人思想是以儒道两家为主,因其不是一位法家思想的忠实拥护者,故而在进行评论时司马迁总是在儒、道两家观点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提出见解。司马迁在论赞写作中的这一特点在《李斯列传》“太史公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对李斯有“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2]2563之语。李斯作为一位有大功于秦,最后却惨死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多是扼腕,而司马迁却一反常人论调,认为李斯为人刻薄少恩,得到这样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并不值得同情。这种论调显然是站在道德评价的角度,对李斯盖棺定论。不可否认的是,司马迁在论赞中对这些法家人物的评价带有一定主观色彩,有失公允,商鞅作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一次变法的施行者,其严明的变法使秦国在战国时期迅速崛起,为秦始皇最终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其在《商君传》中提出的:“明赏之尤至于无赏也,明刑之尤至于无刑也,明教之尤至于无教也”[5]120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这样一位对历史有着积极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因执法过于严明而得罪权贵,最后被车裂而死,司马迁在承认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从德行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李斯咎由自取,不足可惜,从这种辩证而又矛盾的观点中不难看出司马迁个人对严刑峻法的极度厌恶之情。
司马迁批判严刑峻法和统治者的刻薄少恩,并不意味着否认法律的价值。在《循吏列传·序》中司马迁提出:“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即指出法令、刑法在引导人民和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司马迁虽然极其痛恶以严刑峻法苛待人民巩固统治,但并没有全盘否定先秦法家确立的治国原则,这也是司马迁个人辩证、进步历史观在论赞中的体现。
(三)认可促进历史发展的暴力征战
司马迁虽深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但其对儒道思想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儒道视角审视先秦诸子百家治国理政学说,从而做出自己的论判。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法家者,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者也。”[5]194正因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涉及到法家思想时总是与其他家思想比较来看,并非以单纯的法家视角审视问题。在战争观上,司马迁表现出对促进历史发展的暴力征战的默许甚至是推崇,显然与儒家所倡导的“非战”思想相悖。
张大可先生认为:“司马迁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中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摒弃了儒家的非战观点,承认暴力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接近于先秦法家学派的战争观,是一种进步的观点。”[1]141司马迁这种进步的法家战争观在《史记》论赞中集中表现在对统治阶级和历代军事人物的历史评价中。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对秦国的暴虐统治提出批评,认为“秦取天下多暴”,但同时又认为“然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序第三》),司马迁从客观上承认了秦国统一天下是历史运动的必然趋势,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与对严刑峻法的无情批判不同,这一观点是对秦一统天下的历史功绩的高度赞扬,与法家强调征战的思想具有契合之处。同时,司马迁对战争的观点充满辩证色彩,项羽依靠武力成就一时霸业,司马迁对其评论有“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2]339的评价,这是从根本上否定项羽妄图以暴力分割天下的不义行为,对于项羽最终结局,司马迁认为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2]339的总结很荒谬,在太史公看来,不义的战争、否定历史经验才是项羽不得人心,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对法家思想的评论是辩证的,他以儒家学者博爱的情怀与史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站在历史与道德的评价标准上展现自己辩证的法学观念,他既承认法家思想在促进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要作用,又认识到统治者高压政治与严刑峻法对百姓的伤害,既有以儒家学者角度对历史上法家人物悲剧结局的淡化,又能积极肯定法家改革思想在统一的社会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些在《史记》论赞中对法家人物、行事以及政策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司马迁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
二、借法家评论折射司马迁理想社会运行模式
受个人经历的影响,司马迁对法家思想所提倡的细密严苛的刑罚抱有极大的敌视态度,尽管司马迁在《史记》创作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坚持了史家的实录精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客观评述,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作者个人观点集中体现的《史记》论赞依旧隐约透露出其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史记》论赞反映了司马迁理想的国家司法状态,不仅系统论述了国家理想的政治形势,还对执法者、执法形式等做了规划,这种理想化的国家形式尽管在封建社会不具备实现的必要条件,但对国家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司马迁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在《史记》论赞中主要表现为对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管理模式的推崇、提倡简约宽缓的法令条文以及对醇厚朴实的社会状态的向往。
(一) 支持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管理模式
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代,思想方面正值汉王朝儒家兴起、道家衰落,司马迁对儒、道思想接受颇多。虽在治理国家的具体操作手段上儒道二家存在分歧,但二者均意识到“德治”对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性。作为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儒、道思想中共同倡导的道德观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而这恰恰是法家思想所不认同的,在两种对立思想观念的左右下,司马迁在论赞中确立了立足儒、道两家观点,评价法家思想的评论模式。其在《酷吏列传·序》中首先便引用了孔子与老子的政治理论: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2]3131
孔子与老子的这两句话指出法令与道德对治理国家的不同作用,认为清明的社会环境不能依靠细密严苛的律令实现,统治者应该重视德治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只有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太史公对二人的学说大为赞同,“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清浊之源也。”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治理得好坏的本源。”[1]344这是他对儒、道、法三家思想融汇后得出的结论。司马迁认为,高压政治下的严酷法令不仅无法让国家振兴,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相反,统治者施行德治,以礼规范百姓,人心自会归顺,社会自然也就清明。
在社会治理效果方面,司马迁推崇汉文帝时期的社会管理模式,认为汉文帝是西汉中兴时期一位贤明的君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汉文帝为人和善,管理国家真正做到了施行伟大的德治。在《孝文本纪》论赞中,司马迁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人。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2]437在《孝景本纪》的论赞中亦有所体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2]449司马迁之所以在论赞中对汉文帝极尽褒扬之能事,在于汉文帝统治时期广行仁义,汉文帝“除诽谤,去肉刑”“罪人不帑”,这些举措使让司马迁大为赞赏,认为这是统治者有“大德”的表现。虽然在对汉文帝的评价上不免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本质上还是符合其“惩恶劝善,为后王立法”的写史宗旨。
司马迁重视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对百姓的教化作用,提倡统治者以宽缓、人性化的法治手段进行统治。在《老子韩非列传》结尾论赞中,司马迁写道:“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申子、韩非子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将二者学说统归于道家的道德观,但却认为老子的理论主张比二人都要深远,这主要是由于法家处理问题的方式过于激进,单纯以法律条文为标准、缺乏人性化的国家管理模式势必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司马迁对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国家管理模式的推崇,反映了其作为一名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热情与正义,虽然从本质上看,法治与德治争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国家政权,但司马迁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敢于以尽可能自由、完整的思想体系抗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与制度,是其“法后王”这一著史理想的理论实践,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 提倡简约宽缓的法令条文
司马迁不仅在理论上认同德治对社会发展的必要意义,还进一步提出具体的治国方略,对简约宽缓的法律条文的提倡便是司马迁治国方略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道家倡导的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已经不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在改革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主张,很快得到施行,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律条文的愈加繁琐,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进行了严格规范,日益严苛的法律在加强统治阶级中央集权,打击权贵的同时,也使西汉中期的政治环境日益严酷黑暗。针对这种社会问题,司马迁在论赞中多次抨击严刑峻法对社会带来的弊病,针砭时弊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简约宽缓的法令条文的提倡。司马迁的这种主张集中表现在《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的论赞中。如《循吏列传·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3099
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即奉职守法之吏”。[1]327在司马迁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官吏的尽职守法,如果人人都能做到恪尽职守,那么就不需要严刑峻法的规范了。司马迁的这一主张,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颇具一致性,其在《商君书·赏刑》一篇中有“明赏之尤至于无赏也,明刑之尤至于无刑也,明教之尤至于无教也”[5]120的论述,商鞅认为,“严明的刑法的极致是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5]120司马迁和商鞅同样都将法律视为治理国家的必要工具,认为运用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自觉守法,优秀的执法者并不是借助刑罚的严苛压迫百姓,而是其本身便“奉职循礼”,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从对循吏的这段评价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期望国家执法者尽职守法,而不是以法令之严密故作庄重,滥行权利。司马迁的这一政治理想在《酷吏列传》的论赞中得到进一步表述: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司马迁将秦和汉初的国家法令条文进行对比后认为:秦朝国家法网严密,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细致的规定,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大家都逃避法网,“官吏用刑法,好比是负薪救火,扬汤止沸,无济于事”。[1]344反观汉初,国家法网并不严密,废除了原本繁琐的法律制度,法网之宽松甚至可以漏掉吞舟之鱼,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使国家陷入混乱,反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此,司马迁得出结论:治理国家重点不是严刑峻法,而是要重视德教,道德教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自然安定,也就不需要繁琐的法令条文了。
司马迁提倡简约宽缓的法令条文的实质还在于推行道德教化,“以德治国”始终是其政治理想的核心。司马迁对法家思想理论的关注是为其儒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而服务的,尽管司马迁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承认并肯定法令与酷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中的重要作用,但从道德评价层面来看,这种治国方式与执法态度并不符合太史公政治理想,这种辩证的纂史观恰好暗喻了司马迁反对暴政的思想观念。
(三) 向往醇厚朴实的社会状态
法家理论体系中,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国家机器得以井井有条地正常运转,商鞅在《商君书·画策》中提出:“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5]138在商鞅构建的法家治国体系中,天下的清明政局依靠的是明确的法律体系,而非道义。
《史记》论赞中对法家思想的评论所体现的是司马迁向往的敦厚朴实的人民生活状态,是依靠社会上下共同的道德修养所实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这是司马迁对法家评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吕太后本纪·赞》: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高后统治时期惠帝无能,故天下的实际领导权在吕后手中。然而在这种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的环境下,天下竟然能做到“刑罚罕用,罪人是希”的局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推行老庄的无为政治。司马迁对这种社会状态予以高度评价,达到天下刑法少用这一理想政治局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法律的规范,而是与民休息的政治决策一改秦朝暴虐政治,司马迁肯定这一执政理念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其在《史记》中不惜笔墨对汉文帝统治时期清明的政治局势与蒸蒸日上的社会风气进行颂扬,认为汉文帝是理想意义上有德行的国君,而文景之治形成的欣欣向荣的社会风尚本质上与法律条文的推行没有直接关系,他所向往的“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鸡鸣吠狗,烟火万里,可谓乐者乎!”的局面是在汉文帝这样有德行的君主的治理下实现的。这里,司马迁有意无意地提及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刑罚方面的问题,其真实目的除了影射武帝一朝的暴政之外,还在于削弱法律在治国过程中的作用,醇厚朴实的社会状态并非需要严苛的法律条文才能实现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偏见。司马迁一边肯定法家在治理国家中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弱化刑罚的必要地位,不得不说是司马迁个人思想矛盾的体现。
(3)实现杭州港与杭州市城市发展、产业发展真正的相互衔接和协调。港口的发展与港口所依托的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港城一体、港为城用、城以港兴、港城联动、衰荣共济”,这是世界港口城市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港口经济是维系港口和港口城市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是港城互动最容易切入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因此港-城协同发展是港城互动的永恒主题。杭州港总体规划需要更紧密地与杭州城市规划相结合,从单纯的港口规划扩展到基于港口、物流、工业、城市协调的“大港口”规划,正确处理杭州港与杭州市发展的关系,实现港口规划与城市规划真正的相互衔接和协调,将是杭州港总体规划工作的又一个难点。
司马迁对武帝一朝所推行的高压政治的批判在《史记》全书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认识到“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在客观上承认了刑罚在国家机器运转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评论过程中,司马迁个人的心理天平还是偏重于对道德教化的认可。其向往的醇厚朴实的社会状态从本质上来说是依靠“德治”实现的,而法家人物所提倡的刑罚、战争等统治工具只能起一定的辅助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家写史产生的思想倾向上的特点。
三、双重评价体系下法家评论的特点
刘国民先生认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存在着感情和理性的矛盾。”[7]所谓“感情和理性的矛盾”,即言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既有史学意义上客观理性的史学评价,也有其作为一名儒家学说忠实拥护者所引发的道德评价。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矛盾,一方面是司马迁个人遭受过严刑峻法的严重迫害,身心受到重创,这种情况下,在评价中难免将个人情绪过分带入到历史人物评述中,展现出对法家人物的否定;另一方面,司马迁是一位儒道学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本人对儒道思想中“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有着深刻的历史认同感,故而难免从道德层面审视法家思想与法家人物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从而造成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二元对立”。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表现出双重评价体系下对法家思想和人物的矛盾情感。这种对法家评价肯定中带有一定否定,否定中又不乏肯定的矛盾情感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执法者命运之关注凸显道德评价视角,以及对法家人物明显之贬抑和对儒道人物热情的颂扬两个方面。
(一) 通过对执法者命运之关注凸显道德评价视角
司马迁肯定法治必要性的同时不忘加强对执法者个人命运的关注。《史记》中涉及的法家人物主要有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以及历代执掌法律的律官,从历史发展进程角度来看,这些法家的大部分人物都对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法家注重社会改革,强调战争的必要性,改革可兴除社会弊病,正义的战争可以促进国家安定统一。司马迁在对这些法家人物的论赞中首先肯定这些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功用,但最终着墨的重点却放在对这些法家人物个人命运的关注上。
“死”是“太史公曰”论赞中一大主题,司马迁十分重视每一个历史人物的下场。[1]303对待法家人物的历史结局更是尤为关切,在关注法家人物结局的同时,司马迁不忘对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做简短的剖析,或干脆以饱蘸抒情的笔调,书写自己的感性思考。如在《商君列传》结尾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写到:“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在司马迁看来,商鞅在秦国最后的悲剧结局是因其为人残暴少恩所导致的,故而司马迁在论赞中对商鞅各种刻薄行为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评,带有鲜明的个人好恶色彩;《李斯列传》中,“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也是一反传统论调对李斯之死做揭露,将李斯这样一位对辅秦有着重大功业的法家人物与秦二世、赵高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交织在一起,反映了他丑恶、软弱的一面;再如《孙子吴起列传》中,对吴起有:“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的评价,吴起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革新家和军事家,虽然谏说魏武侯施行德政,但在楚国推行改革时却因个人少施仁义最终丢掉自己性命,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结局,司马迁用“悲夫”来作结,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作者个人的嘲讽意味。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这种写作态度削弱了其最终结局的悲剧色彩,未能引起读者对这些堪称时代先驱的改革家们的认识,这是其道德评价视角占据评论上风的典型表现。
司马迁道德评价视角在《酷吏列传》的论赞中表现的很明显。司马迁为酷吏列传有一部分原因是通过对酷吏暴行的揭露,隐喻社会政权之残酷,从而揭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司马迁对酷吏的态度显现出牢骚的成分,读司马迁这部分论赞文字,感觉并不像是在阅读史家作品,更像是阅读一位文学作家对一己之观点的抒发与宣泄,这与其“发愤著书”的写史理想不谋而合。
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学家,在史书中对这些法家人物的悲惨结局的记载无疑是带有一定个人情感色彩的,对于法家代表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司马迁表现出不同于对其他悲剧性人物结局评价的冷漠性,而这种冷漠的根源在于其道德评价占主导地位的评论倾向占据了司马迁这一部分内容的编纂,诚如刘国民先生所言:“司马迁在分析法家人物悲剧的原因时没有具体地分析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原因;只从道德人格上入手,而没有揭示历史的必然因素。”[7]这不得不说是司马迁《史记》创作的一大缺陷。
(二)对法家人物的贬抑与对儒道人物的颂扬
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贬抑和儒道人物的颂扬首先表现在经常引用老子、孔子的观点对法家思想以及治国理念进行驳斥,这一表现在前文已有论述;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也引用过韩非观点,不过其目的却是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而进行驳斥。如《游侠列传·序》中引用韩非“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2]3181的观点,紧接着便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己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3181的论述对其进行驳斥,认为儒生往往为世人所称赞,而扶危济困的游侠也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从这样的写作方式来看,司马迁对两家思想的褒贬也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在人物合传中,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也表现得极为明显。秦朝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思想与儒家思想存在明显对立,并将儒家思想视为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一家,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没有为韩非单独列传,反而是将其与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进行合传。在文末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四人的思想做了简短的概括,二家思想无论是在思想倾向还是治国主张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老庄提倡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而申不害、韩非正好与之相反,其思想较为激进,主张依靠个人努力争取名利,且治理国家应严格按照法律章程行事。将这样两家风格迥异的人物合传,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对二者进行对比,而结尾以“老子深远矣”作结,即使不着褒贬,作者个人褒贬之情也立现了。
结语
综上所述,司马迁作为深受儒、道二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优秀史学家,尽管受个人人生遭际的影响,在对与儒道思想存在一定对立的法家人物、思想等的评价方面存在一定偏见,但在《史记》论赞中仍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肯定了法家思想中“时移世易”的治国理政理念及有助于社会统一的发展观念。从《史记》论赞对法家的诸多评价中,读者可以管窥司马迁个人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其倡导的社会道德观、简约宽缓的法令条文以及最终所要达到的醇厚朴实的社会风尚体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司马迁在《史记》论赞中具有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共存的双重评价标准,对法家思想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改革措施方面,司马迁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法家人物悲剧结局的淡化处理具有明显的道德评价视角,对提倡严刑峻法的法家人物的贬抑和对儒、道两家人物的颂扬体现出明显的个人好恶,这显然与史学家作史所提倡的客观历史评价相悖,这也构成了《史记》论赞鲜明的思想特色。《史记》论赞研究方兴未艾,未来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以文史互通的眼光和多学科融汇贯通的视角,取得新的成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