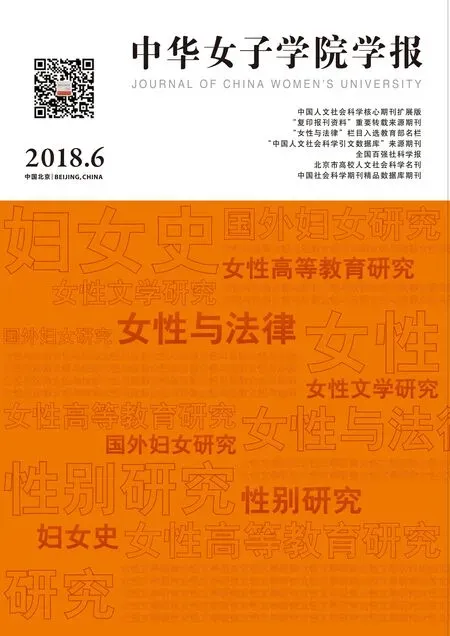激活争论与反思传统 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
魏开琼
女性学学科建设已经不算是个新的热点话题了,中华女子学院正在从事的女性学资源库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具体的历史时刻,资源库的建设有助于立足现在、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从而进一步推动女性学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围绕女性学学科发展中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与大家共同探讨,进一步探索女性学学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以期推动更多人加入女性学学科发展的队伍中来。
一、女性学在大陆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基础
提起女性学,一般人倾向认为,这是一个源自西方知识界的学科。美国妇女学在陈述自己的思想谱系时,通常会追踪到20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里师生对现有知识结构中为何没有女性声音的追问,并将60年代后期启动的女性学研究项目作为女性学学科开始的标志。[1]1-4随着研究、教学与服务妇女与社会行动的深入,实践与理论的相互滋养,女性学成为一门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在内的新兴学科。社会性别作为该学科的首要分析范畴,部分决定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的界限。此外,女性学在学科性质上强调其跨学科的特性,研究方法上强调社会性别与阶级、族裔等其他要素交叉的分析方法,教学法上强调女性主义教学法的运用,这些建构了女性学学科的基本样貌。随着知识生产越来越精细,专业分工越来越具体,今天的女性学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一环。女性学的研究成果在丰富女性学学科内涵时,也促使其他学科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检视其学科假设与核心概念,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比如在政治学领域,传统上讨论正义问题时,因为家庭被归于私人生活领域,是不涉及家庭正义的,但正是妇女学的追问,使得政治学假设的公私领域的划分、正义的内涵甚至包括权利的理解等得到扩展和深化。[2]171-197
在全球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图景中,必须意识到美国启动的女性学学科版本并不是唯一的,每个国家都会结合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本国的女性学学科的样貌与形态。中国的妇女学学科发展受到两股力量的综合影响,一方面是内生的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与解决妇女现实问题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与国外知识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前者在内地妇女学发展中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邓颖超等人就意识到整理中国妇女运动史料的重要性,到80年代全国妇联恢复工作以后,在其下属的妇女干部学校(中华女子学院的前身)成立了妇女业务教研室,进行女性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工作。此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名称先后更名为妇女运动系、妇运理论系等。2001年,中华女子学院成立了内地首家女性学系,2006年开始本科人才的招生工作。自此,从机制建设上宣告了女性学的正式成立。
从以上简短勾勒的历史来看,如果不受名称局限的话,女性学在大陆的发展是有其内生基础的,具有自己的独特发展历程。鉴于此,我们在从事女性学学科建设资料库建设时,应将眼光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整理出内地女性学的家谱,这将成为中国妇女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面向与组成部分。
二、女性学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是相互促进的
目前,女性学的学科界定还存在诸多争议,这种争议的局面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如果学科地位尚未确立,专业建设是否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学科发展简史来看,学科制度化进程也就是学科地位确立的过程,其中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其他相近学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通过学科边界的确立进而形成自我保护的手段。从现在的学科格局来看,那些形成独立建制的学科会形成三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包括定义具有独特性的学科硬核、划定清晰的学科边界和构筑学科的技术或者组织壁垒。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今天不同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趋势,彼此在研究对象上互相渗透,研究方法也互相借用,自成逻辑的知识体系也不再是学科追求的目标。[3]这种情况下,学科之为学科的意义,可能是基于其内在相对成形的知识体系和相对统一的认识规范,也可能是出于劳动分工、同行交流、获取支持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今天的学科,不只是认识的工具,更是社会进行知识管理和促进知识发展的工具。[4]
今天讨论学科建设时除了要注意到学科与领域融合的趋势外,还要继续回应女性学学科在研究、课程与机制建设、社会服务等应然层面的问题。此外,作为学科探讨的成果也需要在人才培养层面来进行检验与落实,专业人才服务社会后反过来又能进一步促进学科建设。考虑到大学人才培养具有相对的周期性和稳定性,学科层面的探讨未能达成完全共识不应成为影响人才培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理由。人才培养的主要面向是社会需求,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知识生产来看,今天大陆女性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机制和平台都远远不够,人才培养的机构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无法满足社会对女性学专门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在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急需主管学位教育的部门给予支持,支持女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启动女性学研究生人才的培养。此外,关于女性学人才的出口是否只对应于妇联系统这个问题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内地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初与妇联系统是有强烈的亲缘性的。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学人才培养就是服务妇联系统的。但是社会的需求在改变,今天仍然将女性学人才的出口局限于妇联系统就有点故步自封了。从国际国内层面来看,今天凡是在工作中涉及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的组织与机构,都需要专业的女性学人才的加入。
在这点上,本次女性学资料库建设除了围绕传统学科内涵的界定从事女性学学科建设的资料库建设外,还可以考虑放眼国际国内社会对专业女性学人才的需求,收集女性学专业建设领域的现状,总结现有的人才培养经验,分析影响人才培养的障碍,探索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女性学专业人才的建设方案。
三、倡导重新检视女性学学科中的核心术语
女性学领域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与潜力,在通过研究、教学与实践推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方面还大有可为。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学学科还存在社会认知与社会接纳严重不足的短板,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其隐含的观念变革与显性的知识生产诉求短期内无法达成能被广为接受的共识。不管怎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女性学也到了需要自我反省的时刻了。在此,本文分享美国女性学学科研究的当前动态,作为未来女性学建设的参考。
美国女性学在20世纪90年代鼎盛时期,差不多的四年制本科大学都开设了与女性学有关的系或项目。此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女性学系也产生了诸多变体名称,但也是在“Women”“Gender”“Sexuality”这几个词之间进行再组合,凸显哪个名称表明该系的师资力量、研究重点与研究路径。同时,在妇女学学术共同体内,开始主张对这个领域中的基础性假设进行重新思考。2012年《重新思考妇女/性别研究》一书的出版,便是对这一主张的回应。该书由女性学中的18个核心术语组成,每篇文章聚焦一个术语(比如女权主义、跨学科、交叉性等),每位作者的写作均围绕这些术语是如何被理解、被运用的,并解释了它们在知识生产和知识排斥上所起的作用。该书的写作框架受福柯知识谱系学的影响,对每个术语的叙述和历史采用诊断式的方法,凸显看似达成共识的术语,其实也是具体情境与历史的产物。在具体内容的组织上,该书主编要求所有作者围绕一个核心术语讨论时,按以下问题来展开他们的分析:(1)到目前为止,妇女学中的这一术语以及其叙述的谱系学是什么?如果重新思考这个术语,妇女学中哪些谱系学是我们可以追踪的?(2)这个独特的术语在妇女学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此使用,自它从知识上、机制上、管理层上或教学上带来了什么结果?(3)这个术语在妇女学内部带来了什么样的张力?这个术语又证明了什么?在谈到这个术语时,哪些已经或者可能会受到忽视,甚至是否认的。这个术语会怎样被理解和使用?它有可能会指向其他形式的妇女学吗?[5]7
这种自我反思强调,将批判指向自身,检视女性学正在使用的术语以及我们如何在使用它们,其背后的假设与预设是什么,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时,我们设定了实践中的何种路径依赖,又可能遮蔽了什么样其他的可能性。这样的发问,不仅在思考女性学的核心术语时是有用的,而且它对进一步规范女性学的学术生产与写作也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