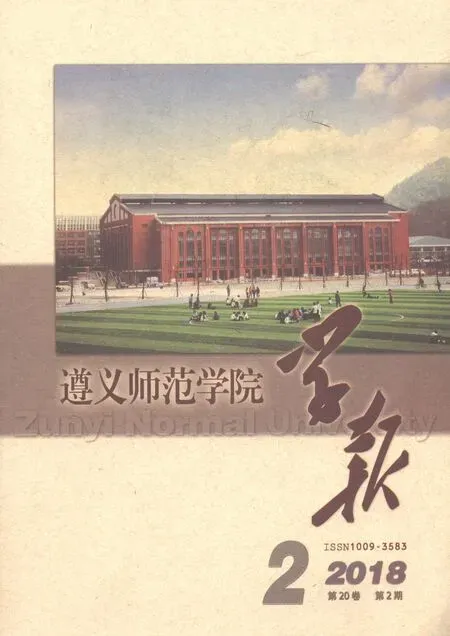红、黑、白
——托克维尔论民主在美国
刘依平
(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人文社科部,广东珠海519041)
从起源来看,由于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因此其人种、肤色、相貌等生理性征都属于“不由自主”、天生注定的东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地理方面的区隔被各种欲望及由此而来的技术所超越,人群的流动和混杂势所难免。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原本并无其他含义的人种、肤色等外在标志随之与各种冠以“文明”名义的身份联系了起来,就意味着更多。在19世纪30年代初,当年轻的法国贵族阿列克西 德 托克维尔到达美国后,他在这块新大陆上发现了很多的新鲜事物,特别是美国式的民主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他甚至认为这种以平等为根本特征和至上追求的民主社会恰如神意,无可阻挡,势将推行至各个民族。与此同时,他对美国社会也有所忧虑。其中,有一种在托克维尔看来专属于美国的危险。它与美国这个民族的开始和未来都有关,这就是本文所要谈及的红、黑、白三者与美国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红与白:美国的印第安人
托克维尔说过,“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1]而且美国这个国家是最适合观察其开始和发展的。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来自欧洲的文明人毫不费力地从印第安人那里接手,在这里“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尽管这些移民彼此之间就其移民的目的、自我管理的原则等实有很多不同,但是,这些人,特别是英国移民,又是相似的: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因同样的宗教压迫而各受到政治方面的教育;他们比其他欧洲移民更懂得权利和自由的概念……总言之,他们或多或少地具备英国民族的“一般特点”。不过,在建立北美殖民地的过程中,这些英裔美国人(Anglo-American)也存在一些差异。至少在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他们一南一北分成两支,未能完全融合。
与上述从欧洲移民至这块新大陆的人们相比,如所周知,最初的原住民是被称作为印第安人的人种。在分析这个种族被摧毁直至灭绝的原因时,托克维尔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文明与野蛮的区分。[2]在托克维尔的笔下,这一人种以狩猎而非农业为生;他们在北美大陆活动——那里有以他们命名的山谷;有冠之以某个部落之名的河流——却并未因此拥有它。这是因为“文明是人们在同一地方长期劳动的结果。它代代相传,每一代都得益于上一代。使文明最难在其中建立统治地位的民族,是狩猎民族。”[1]所以,在与所谓优等文明的遭遇战中,他们最终落败:“他们的茅屋到处都被文明人的房屋所替代;树木被伐倒;无人之地渐渐有了人烟。”[3]托克维尔记录了他在美国之旅中遇到的一个人的原话:“印第安人是个正在灭绝的种族。他们不具有文明(civilization):这一点害死了他们。”[3]在描述环绕休伦湖(LakeHuron)的丰饶土地时,托克维尔这样说道:“在这里,大自然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世界上没有哪块土地像这块土地这样肥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文明人已经到来。”[4]
尽管存在如上区分,但托克维尔并未贬低、甚至对这一不复存在的民族表达了高度的颂扬之情。他曾亲身与一名印第安人不期而遇。起初,这名印第安人的出现给他和他的朋友带来了不愉快。这位不速之客的脸上“显露出所有将这个种族与其他种族区分开来的特征。他极黑的眼睛闪烁着野蛮人的火光,这种火光仍在(美国的)混血儿脸上可以看到,其消失则只能等到混合了白人血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出现。”[3]但很快地,托克维尔发现该印第安人虽紧跟着他们,却并无恶意。而且,后者的一个笑容就使托克维尔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印第安人”:一个是严肃的、使人恐惧的,一个是仅因笑容就展现出其天真和友善之情的。在紧随其后的与一名欧洲移民的偶遇中,托克维尔甚至从这位白人与该名印第安人的对话中感受到某种“愉悦(pleasure)”,尽管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二人因起源和民情的差异是如此地不同。在托克维尔眼中,以这位白人为代表的美国拓荒者实际上是将对野蛮人生活的喜爱和作为文明人的自豪混合在了一起。同时,尽管他们喜欢印第安人胜过喜欢他们的白人同胞,但他们并未视这些红色[5]人种为与己平等之人(equals)。
二、黑与白:美国的奴隶制
先进文明对野蛮文明的征伐古已有之。同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奴役也是源远流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公民”特别地与政治地位有关,亦即是要持久地参与城邦治理和承担城邦的公职责任,这样的人才能叫做“公民”,甚至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人”。自然,这样的人必然具有理性。撇开被等同于野蛮人的外邦人不论,在古希腊城邦以内,妇女和奴隶也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之所以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因为前者只具备不充分的理性,至于后者则完全没有理性。因此,对于这些无法实行自我统治的奴隶的役使就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安排。不过,亚里士多德本人非常注意区分“自然奴隶”和那些由于军事征服而沦为奴隶的人。而且,他还论及对奴隶的“正当对待”,提议可以鉴于奴隶提供的服务而给予他们以自由。
从以上可见,古代城邦的公民实际上不仅人数很少,而且还有着排他性的政治权利。按照卢梭的观点,这种被亚氏视为自然的奴隶制实际上一头是自由之极端,一头是奴役之极端,而且前者只有依靠后者才能得以维持。“若不是奴隶极端地做奴隶,公民便不能完全自由”。[6]正因为此,托克维尔区分出两类社会:一类是贵族制,一类是民主制。与欧洲封建社会一起,古希腊和古罗马都被托克维尔认为属于贵族制的范畴。然而,虽然古代的所谓公民实际上享有封建贵族的“特权式的自由”,但这并不代表其治下的奴隶就比民主社会的奴隶更可悲。相反,在美国,欧洲人对非洲裔黑人长期地施加暴力。是这种力量上的不平等使得这些肤色迥异于白种人的可怜人成为了奴隶。而成为奴隶的黑人由于长时间无力反抗,慢慢地养成了一种被托克维尔称之为“奴隶的思想”和“奴隶的奢望”。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他们憎恨其主人,倒不如说他们更羡慕后者的财富和权力。
根据托克维尔的说法,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悲惨境况,其原因在于美国独特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迥异于古希腊城邦的奴隶制。“古代人给奴隶身上带上链子,但让他们思想自由,允许他们学习知识。奴隶主也言行一致,遵守他们所定的原则。在古代,受奴役的期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奴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获得自由而与主人平等。”[1]而今日美国的黑奴无论是在自由度方面,还是在种族来源上,都与其主人不同。
从降生那一刻起,美国的非洲裔黑人就因其肤色而将这象征着“耻辱”的外貌特征传续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对于肤色和种族的成见,而且这种成见之根基看似无可动摇,并进而成为两个大洲甚至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强烈不同。[7]在美国,“蓄奴制的无形的和短期的压迫与种族差别的有形的和长期的压迫极其有害地结合在一起来了。”[1]也正是因为如此,较之于古代城邦的奴隶制,美国的这种状况带给其社会的潜在威胁要更可怕。此种因历史造就、日后也伴随着历史而变化的不平等关乎美国未来的社会状况,因为人们天生有一种偏见,也就是起先与己在法律或财富等方面不平等的人已与自己平等以后,仍会长期看低这些人。所以,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根植于民情,并总是以回忆的形式融入进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8]之中。这一暗流潜藏在美国的民主之中,[9]使其社会自始至终都带着某种“根本性的紧张”。[10]
不过,让托克维尔惊诧的是,以上的紧张程度在当时美国已经废除黑奴制的北方州县更高。按照托克维尔的看法,“蓄奴制是对劳动的玷辱;它给社会造成了好逸恶劳的恶习,而随着这种恶习而来的,则是无知、高傲、浮夸和奢侈。”[1]托克维尔认为它将对美国南方的性格、法律和未来发生巨大影响。然而,或许是因为长期共存的习性,这里针对黑人的法律虽然依旧非常严苛,但白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比较具有弹性,对黑人柔和以待的事例并不少见。而在国土的另一头,法制虽然已经松弛下来,但平日生活中的细微处,不平等依然照旧,甚至还更为严酷。之所以会这样,托克维尔分析认为,根子出在经济利益上。北方的主人睿智地发现,蓄奴可能还会成为财富增长的绊脚石。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最终美国人打了一场代价不菲的内战。[11]
三、民主在美国:相似者
对于美国境内的两个种族而言,他们之间并无共同之处。唯一相似的则是因为他们都位居白人之下,都受到白人的压迫,因此都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带给这两个种族的后果却是不一样的。印第安人有着某种未开化民族天生的自豪感。“他们拒绝接受文明,而且拒绝的原因,主要的不是出于仇恨文明,而是出于害怕自己变得与欧洲人一模一样。”[1]而非洲裔黑人一再努力地希望同他们的主人混为一体,却没能办到。在托克维尔看来,前者的傲慢和后者的奴性使他们都归于悲惨的境地,且都无可挽救。
与之对照,幸运的、骄傲的欧洲白人独享所有的“人类特权”。这些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呈现出一致的状态;对政治和自由的体验与理解也是相似的;甚至,正是过往的灾难和由此带来的贫穷,为他们来到新大陆后的平等提供了最好的保障。诸此种种都表明,只有在这些白人这里,美国的民情才向托克维尔展示出其单一的面目:“它到处都由相同的元素构成。它的各处有着同等的文明程度。”[12]
所以,除去印第安人和黑人,全体美国白人都是相似的。这种相似性为他们提供了彼此发生关联的纽带。依照托克维尔的观点,在贵族社会中,处于不同等级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政治纽带。“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13]而在美国式的民主社会中,从一开始就并不存在这种类型的政治链条。“在这个社会里,既没有大领主,又没有属民;而且可说,既没有穷人,又没有富人。”[1]如此一来,对于这些刚刚脱离欧洲等级社会的人们,他们之间如何形成社会?美国人的相似性提供了一个中介,一个第三方,亦即相似者,在民主人的自我与他人之外打开。[14]
上述相似性可以为美国白人带来同情与互助。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景象是使美国的民情变得温和的重大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当人们“在思想和感情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也就是说,他只要省察一下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人的任何苦难他都不难发现,一种内在的本能使他在苦难扩大的时候立即就可看到。在对待陌生人或敌人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使他不加歧视,因为他的省察马上会发生作用。这种省察同他的怜悯心一结合,使他在同类受苦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身受其苦。……人人都有人类共通的同情心。……人人都喜欢如此。他们虽不慷慨,但很温和。”[15]因此,不可否认,即便是在南方的白人奴隶主身上,他们也“愿意承认奴役黑人是一种罪恶”,[1]“其行为时而受他们的利益和高傲偏见所支配,时而受他们的怜悯心所左右”。[1]然而,一旦道德和利益发生冲突,无论是联邦北部还是南部,托克维尔预言:种族的同情心也是无能为力的。种族之间的差异及由此而来的偏见依然坚不可摧。
所以,相似性的确可以带来人们之间的同情与互助,但这种相似驱使人们更倾向于某种嫉妒。每一个与己相似的人都是他在追求这个世界的福祉时所遭遇的竞争对手,先前在贵族制下仅限于本阶级内部的竞争也就因此扩展到所有人。[14]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奴隶制难题。“南方的美国人有两种担心的情感使他们永远保持超然孤立的状态:第一,害怕自己掉价儿而与原来的奴隶黑人平等;第二,害怕自己降格而处于邻居的白人之下。”[1]
因为利益的缘故,美国社会的白人对于奴隶制——其实也是对于一个族群的差别对待的问题的存废同时受着良心和利益的拷问。在白人内部,他们想要彼此相似,不容存在差异,这是因为差异就是对相似的威胁。为了捍卫这一脆弱的认同性,人们更倾向于对整齐划一的强求。“人心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1]
四、结语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是托克维尔非常看重的。在他看来,民族或国家就如同人一样,其成年后的各种习性与其幼年时期的养成密不可分。因此,无论是评价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应该追溯他或它的过去。就此而言,托克维尔是一以贯之的。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将1789年之后的几十年视为一个整体,通过追溯这60年的历史,他不断地连接旧制度的开始与结束,并加以对比。这样,托克维尔的分析就若隐若现地揭示出旧制度的灭亡:哪些正在走向结束,哪些正等待着新生。
类似地,当年轻时候的托克维尔因国内1830年七月革命而避至美国,这里带给他的新体验使其对于开始和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思索。在这里,他看到一种仅半个世纪之多的新政治文化。这块土地上的英国白人自始就怀有一种种族上的傲慢,待到他们成为“美国人”,此种情感又被由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而来的个人骄傲加诸其上。所以,“美国的白人既以其种族自负,又以其为美国人自负”。[1]在这双重自负的背后,则是他们对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的压迫。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黑人被奴役到不能再奴役的地步,而印第安人则被放任自由到极限。奴役对黑人造成的后果,并不比放任自由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后果更为致命。”[1]虽然有时候可以看到出于人性之天然而使这三者,红、黑、白,暂时地靠近,但终究敌不过偏见和法制的力量。
尽管托克维尔当时认为种族问题专属于美国,与民主无涉,[1]然而,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美国当时新开辟之俄亥俄州的情形:在那里,“民主被推进到罕见的极限……大多数人只是过客而已。”[12]——托克维尔警示我们,这种非社会的场景是民主的极端画面,是民主人应该尽力避免出现的现实和未来——如果今天在语言、习俗、教育、法律、血统甚至外貌特征都各异的种族或移民共处同一个国家,却永远不能融为一个整体(all),这岂不是现代民主的极端场面?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Harvey Mitchell.America After Tocqueville:Democracy Against Differenc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Alexis de Tocqueville.“A Fortnight in the Wilderness”,in 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by James T.Schleifer,ed.by Eduardo Nolla[M].Indianapolis:Liberty Fund,Inc.,2010.
[4]Alexis de Tocqueville.Letters from America,edited by Frederick Brown[M].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5]Nancy Shoemaker.“How Indians Got to Be Red”,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M].1997,102.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美)茱迪 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M].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法)莫里斯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Michael Mann.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0](美)文森特 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1]威廉 李 米勒.奴隶制与宪法[A].(美)肯尼思 W 汤普森.宪法的政治理论[C].张志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2](法)托克维尔.美国游记[M].倪玉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法)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M].崇明,倪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