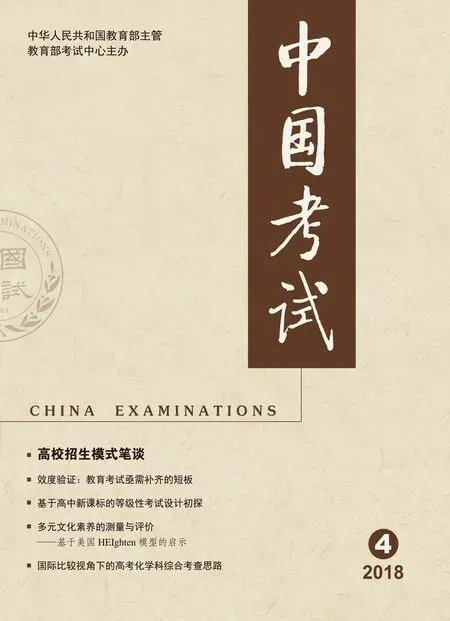“证明”抑或“改进”:综合素质评价价值取向探析
程龙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在继承和批判泰勒目标评价模式的基础上,1967年美国著名的教育评价专家斯塔弗尔比姆(D.L.Stufflebeam)提出了CIPP模式,其中C代表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I代表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两个P分别代表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和结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斯塔弗尔比姆认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prove),而是为了改进(improve)。”[1]因而,CIPP评价模式也被称作决策导向评价或改良导向评价。本文用CIPP评价模式的基本思想来检视我国正在进行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证明”学生已有的素质水平,还是为了促进学生素质在原有水平基础上的“改进”?综合素质评价虽然经历多年探索,但其价值取向依然扑朔迷离。在价值取向目的尚未明确的前提下,开展综合素质评价的前景并不看好。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取向进行探讨,以发挥评价的正面导向作用。
1 综合素质评价“证明”价值取向的表征
通过对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综合素质评价的指导意见和各省市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进行分析,发现综合素质评价存在“证明”价值取向。“证明”是指根据可靠的材料作出真假性的价值判断。具体到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就是根据学生提供的证明材料,判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水平。综合素质评价的“证明”取向,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 国家政策文件的明文规定
2002年12月30日,《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中规定:“高中应探索建立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增加反映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研究性学习、社会公益活动及日常表现等真实、典型的内容,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提供更多的学生成长信息,逐步使中学对学生的评价记录成为高等学校招生择优录取的重要参考之一。”[2]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规定:“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内容。”[3]2014年12月10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中规定:“教师要指导学生客观记录在成长过程中集中反映综合素质主要内容的具体活动,收集相关事实材料,及时填写活动记录单。”[4]
从最初的“评价记录”“重要参考”,到最近的“客观记录”“活动记录单”等规定,可以看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是对学生已有综合素质的“证明”。每一个高中生拿着学校开出的这份“证明”接受高校招生考试的筛选。但综合素质评价“证明”的“参考”价值又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证明”可信吗?谁来参考?如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证明”作用接受着严峻的考验和质疑。
1.2 综合素质评价方案中的体现
2004年新课程改革开始实施,各省市相继研制了本省市的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这些方案在评价的内容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主要是因为评价内容的制定深受《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区2004年初中毕业生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的6方面内容影响。在正式实施的评价过程中,各省市在这些评价内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其分化成二级、三级测评点。
在评价过程中学生的内在综合素质变成对外在指标的“验证”。虽然各省市在评价方案中确定了本省市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但是为了将这些内容具体实施到评价中,各省市对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和测评指标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例如,以广西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为例,其中规定道德品质、公民素养、交流与合作能力评价结果设定为“合格”及“尚需努力”2个等级;学习态度与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结果设定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4个等级。学生内在的综合素质变成对这些外在指标的验证。同时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是有或无的问题,而且还要测量出程度上的差别。这种一一对照的线性思维,深受评价目标导向模式的影响,注重的是静态、鉴定、选优评价,主要是评价的证明功能[5],即不仅要证明学生有没有,还要鉴定学生的等级。
在对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使用上,如果将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作为毕业或升学的依据,意味着学生的综合素质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毕业或升学,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成为学生毕业或升学的一张“通行证”。这种“通行证”也成为学生毕业或升学的一种“身份证”,以广东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为例,其中对于评价结果的使用规定为:学校将评价结果通知学生个人及其家长,作为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依据之一,也作为高等学校录取或退档的依据之一。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沦为这些外在标准的“证明”,成为附属品。
1.3 研究者的研究佐证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一种评价方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种价值取向究竟是“证明”还是“改进”呢?不同的研究者亦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对国内已有研究者的观点进行梳理,综合素质评价的“证明”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2点。
第一,综合素质评价“证明”价值取向体现在对目标导向教育评价模式的推崇。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综合素质评价采用的是对学生素质“外显化和行为化”,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呈现也主要是“等级加评语”的方式。综合素质评价停留在“验证”学生对已有素质测评点的达成程度,是一种到达度评价。
第二,综合素质评价的“证明”价值取向还体现在仅仅“为了评价而评价”。学校重视的是评价资料的填写、完成规定的评价材料和任务,但是却并没有发挥出评价的育人价值[6]。学校对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视大多是将其演变成另一种“考试”形式,综合素质评价的理念与应试教育中的分科考试实有“异曲同工之处”。目前正在进行的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学校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评价”和“选拔”,而不是“育人”与“发展”之功效。
从已有研究者的研究中可知,综合素质评价在实施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重视评价的“证明”作用,忽视评价的“改进”作用。但是由于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弄虚作假行为,将会导致综合素质评价的“证明”作用大打折扣。
2 综合素质评价“改进”取向的意蕴
如果说综合素质评价只体现了“证明”而没有体现“改进”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不客观、站不住脚的。“改进”意味着在原有的基础上作出改变,使其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意味着通过评价使学生在原有素质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改进”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2.1 国家政策文件的应有之义
2001年6月8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7]2002年12月30日,《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充分发挥评价的促进发展的功能,使评价的过程成为促进教学发展与提高的过程。”[2]2003年3月31日,《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实验)》提出“建立发展性评价制度”“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历程”[8]。2014年12月10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中规定:“全面实施综合素质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认识自我、规划人生,积极主动地发展;有利于促进学校把握学生成长规律,切实转变人才培养模式。”[4]
无论是“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还是建立“发展性的评价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和改进是国家政策的明文规定。与综合素质评价的“证明”价值取向相比,“改进”价值取向是综合素质评价的深层之意。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评价的“改进”功能却被“证明”功能所替代。因此,人们在实践中一方面抱怨评价的无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做,究其根本原因是忽视了评价的“改进”功能。
2.2 综合素质评价方案中的彰显
各省市制定的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方案既体现了评价的“证明”价值取向,同时也彰显了评价的“改进”价值取向。评价方案中对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改进”价值取向的彰显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
第一,体现在制定综合素质评价的原则上。罗祖兵等在对各省市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有22个省市将发展性确定为评价原则[9]。发展性原则已成为各省市制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主要原则。
第二,体现在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一种过程性评价,贯穿高中学生3年学习生活始终。布鲁姆指出:“过程性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学习者等级划分或鉴定,而是帮助学生和教师把注意力集中在为进一步提高所必需的特殊学习上。”[10]作为一种过程性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学生素质发展的不足,进而激励学生不断改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三,体现在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上。参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人员主要有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学校的行政人员等。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发展性评价,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日常进行的评价促进学生发展[11]。学生通过参与评价不仅评价他人,而且在评价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改进,并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提升。
2.3 研究者的积极倡导
虽然综合素质评价进行了10余年的探索,但是为什么要评价、怎样进行评价、评价的结果怎么使用等问题依然众说纷纭。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是我们进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前提。评价的取向不仅关乎人们对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认识,也会影响评价结果的使用。通过对已有研究者的观点进行分析,总结得出评价的“改进”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
第一,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综合素质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通过综合素质评价可为学校提供学生素质发展所欠缺的某方面信息,促使学校更加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综合素质[12]。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初衷之一是为了改变应试教育带来的学生片面发展问题,力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二,以评价促进学校变革。邢利红提出,通过发挥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导向、改进和促进等功能,能够有效引导学校工作系统变革[13]。徐岩等提出,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是引导学校对学生各方面发展的关注,更好地落实素质教育[14]。通过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反馈为学校改进教学提供参考。
第三,以评价完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崔允漷等认为通过建立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发挥评价结果在高校招生中的作用,完善高校招生制度[15]。综合素质评价试图为我国僵化的高校招生制度注入新鲜的“血液”,综合素质评价的“改进”作用不仅包括评价的内在价值,而且也体现在评价所产生的连带效应。
由此可见,综合素质评价的“改进”价值不仅体现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上,还涉及学校教学改进以及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等方面。综合素质评价的“改进”价值若能真正落实到实处,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必将起到推动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进行的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由于对评价的定位不清和价值取向不明,评价的“改进”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3 由“证明”走向“改进”的价值之思
从前述分析可知,无论是国家出台的政策文件还是各省市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案,都包含着“证明”与“改进”两种价值取向。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两种价值取向共存并没有什么矛盾,因而有研究者可能会质疑为什么要实现从“证明”到“改进”价值取向的转变呢?这是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会直接影响人们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时的基本价值立场、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随着综合素质评价的推进,可以发现两种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相互干扰。因此,厘清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取向是开展评价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证。
3.1 “证明”是“改进”的前提
综合素质评价是对学生综合素质所作出的总体性评价,因此需要提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水平的证据。综合素质评价的起始阶段是做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关材料的真实记录,根据真实记录对高中生的综合素质作出客观评价。对学生综合素质作出评价的过程,即是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作出“证明”的过程。
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之后,学生对于自己的素质发展水平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比较,才会有进一步“改进”的动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改进”,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功利性的改变”,即学生为了在下次评价中取得更好的等级或分数而在短时间内有意为之;第二种是“发展性的改进”,即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而长时间一以贯之的行为习惯。严格意义上来说,“功利性的改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进”,因为“功利性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逝及外在监督的缺失会出现反弹甚至倒退的现象。学生只有树立起了“发展性的改进”才会将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作为一项责任,而不是外在的任务。
“证明”是“改进”的前提,它为学生进行“改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空间。对于自己欠缺的综合素质,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需要努力改进。这样就避免了学生在改进过程中“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现象,可以集中力量提高欠缺的素质。
3.2 “证明”是方式,“改进”是目的
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需要依靠一定的方式记录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过程和结果。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通过为学生建立成长档案袋的方式,收集和记录学生3年来的综合素质评价材料和结果。高中学校在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时重视的是评价的“证明”作用,即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对考生升学的影响。有些高中之所以在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弄虚作假,就是因为担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证明”无法在高校招生录取时通过。这种以“证明”为取向的综合素质评价扭曲了评价的本质,反而为高中学校增添了更多负担。
综合素质评价“证明”与“改进”两种价值取向共存,是因为“证明”取向是评价的方式,而“改进”取向则是评价的目的。综合素质评价的提出是为了改变我国应试教育的困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有些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对综合素质评价目的的认识仍然存在偏差,认为评价只是为高校选拔人才而做,与自己的教学工作无多大关系。”[16]因此,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时,要跳出那种“我”与“它”的对立关系,实现“我”与“你”的相遇。评价不是为了他人而进行,评价是为了改善自身。综合素质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评价的表面(即“证明”),而不实现育人(即“改进”)的深层目标。目前,综合素质评价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评价而评价,通过评价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改进的作用被淡化。学校在引导学生做好综合素质评价记录工作的基础上,需要通过评价反馈出来的信息引导学生和教师作出改进。
3.3 “证明”是起点,“改进”是终点
综合素质评价始于对学生综合素质作出“证明”,为高校招生提供参考依据,但是评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蕴含了一定的行为导向,即通过评价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自觉改变。然而目前进行的综合素质评价却停留在了“证明”的起点阶段,离“改进”的终点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诚如李雁冰教授所言:“就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实践而言,综合素质评价已深陷目标取向与结果取向的泥淖中。”[17]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的教育价值被淡化,评价的“改进”作用成了虚假的摆设。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我们虽然得到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但是忽视了评价过程的育人价值。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好比“走马观花”,评价的作用就像“雁过无痕”。“证明”只是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表层价值,“改进”才是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深层价值。只有发挥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改进”功能,才能改变其若有若无的现状。
综合素质评价虽历经10余年的探索,但其评价的价值取向尚未取得共识。作为评价观与评价方式的统一体,理解评价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为评价的正常开展扫清认识上的障碍并指明方向。诚如斯塔弗尔比姆所言,评价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综合素质评价应在“证明”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向促进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改进”转变。
[1]MADAUS G F,SCRIVEN M S,STUFFLEBEAM D L.Evaluation models:viewpoints on educational and human services evaluation[M].Boston:Kluwer-Nijhoff Publishing,1983:125.
[2]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EB/OL].(2002-12-18)[2018-03-16].http://www.moe.edu.cn/srcsite/A26/s7054/200212/t20021218_78509.html.
[3]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2014-09-03)[2018-03-16].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
[4]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EB/OL].(2014-12-10)[2018-03-16].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4559/201412/181667.html.
[5]骆徽.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指标体系研究:基于CIPP评价模式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2(21):59-64.
[6]徐岩,丁朝蓬,王利.新课程实施以来学生评价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2(3):12-21.
[7]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2001-06-08)[2018-03-16].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309/200412/4672.html.
[8]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实验)[EB/OL].(2003-03-31)[2018-03-16].http://www.moe.edu.cn/srcsite/A26/s8001/200303/t20030331_167349.html.
[9]罗祖兵,吴绍萍.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统一性的问题及其对策[J].教育科学,2011(4):39-42.
[10]陈玉琨.教育评价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3.
[11]刘志军,张红霞.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现状、问题与展望[J].课程·教材·教法,2013(1):18-23.
[12]程龙.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招生“硬挂钩”的困境及其突围[J].中国教育学刊,2017(7):19-23.
[13]邢利红.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校的挑战与路径选择[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11):16-18.
[14]徐岩,丁朝蓬,王利.新课程实施以来学生评价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2(3):12-21.
[15]崔允漷,柯政.关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0(9):3-12.
[16]蔡敏.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现状、问题与对策[J].教育科学,2011(1):67-71.
[17]李雁冰.论综合素质评价的本质[J].教育发展研究,2011(24):58-64.